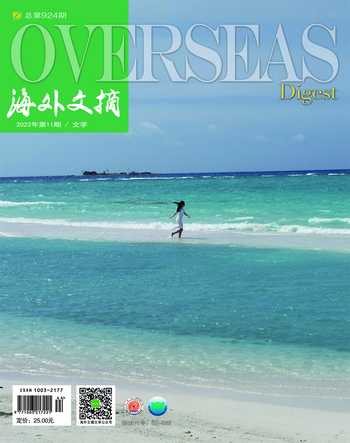光着膀子吃蛏子
黄吕群

渔乡人有着“光着膀子吃蛏子”的俗语。乍一听,尤其是对于一个内地人来说,想象这场面真是哭笑不得,并且不是一般的尴尬。
记忆里,我们这些男孩子是一条裤衩迎酷暑,光着膀子到处走。那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稀饭几乎是主宰着一日三餐,碗里除了地瓜就是地瓜丝,偶尔有白米粥,那也是稀得能照出你的脸。夏日里的晚餐时间应该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屋檐下,道坦上,洒下几瓢井水算是驱散了些许的暑气,而后随处可以摆上一张饭桌。尽管稀饭早已打好了,但是我们兄弟几个还是和父亲一样光着膀子呼呼地吃起来,那年月很少有人在秀腹肌,也很少有过几个啤酒将军肚。母亲在边上总是不停地为我们摇着蒲葵扇子。饭桌上总是离不开蛏子这道菜。清水煮,不放任何佐料,出锅时每只蛏子的壳都打开了,倒在碗里就像一团怒放的花,黄白相间,煞是诱人。爱小酌的父亲每次酒后总得喝上几口蛏子汤,不仅是味鲜,还能醒酒哦。
要是追求原汁原味,瓷杯中蒸出来的蛏子才是最地道,就算是今天酒店里的铁板烧也远远赶不上。母亲吩咐我们把蛏子一只只地立在瓷杯中,直到整个杯子的上下都挤满,煮饭时用饭枷垫着,饭熟时一打开杯盖,那种特有的清香味就氤氲了整个屋子。现在想起来躺着固然舒服,一旦站立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了。吃蛏子真是一大快事,味美还能明理。
如果是赶上端午或尝新的节日,要说必备的菜就是蛏子了。这一天母亲总是让我们兄弟几个穿上干净的衣服,会把蛏子洗得特别干净,然后用菜刀一只只地断开了壳后的筋。此时灶台上那口揩上猪油的大铁锅正在不耐烦地发出“吱吱”声,蛏子倒下去的时候就冲着那四溢的激情洒下料酒再用锅铲掀翻几下,放水焖烧再撒上些许小葱末,出锅的时候这蛏子就显得格外的安靜,上下两片的壳依旧是不离不弃。或许是母亲做得仔细,我们吃得也很谨慎,先是放到嘴里轻轻地一吮,满口的新鲜就留住了,然后也是轻轻地拿下上片的壳。不像那个豆腐泡,经不起一吸就把汤水溅到对方脸上去了,也没少招来责怪。在这样的节日里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一只完整的蛏子肉吃到嘴里,不像大姐还是那么小口地吃得很拘谨。但是在那艰辛的岁月里,像大姐那样乖巧的孩子又是何其多啊。
十月金秋晾鲜正当时。在舥艚这个千年渔都,秋风中、斜阳里、房前屋后,一排排的竹器篱箳晾晒着蛏子干,如同沙场秋点兵,场面蔚为壮观。质地坚硬的蛏子干便于贮藏,一年四季,总给人以海的味道。我们渔乡人几乎是家家都有这个特产。不用说逢年过节,就算是深夜来客家庭主妇也从容,不到一根烟的工夫,蛏子干上来了,烧芹菜,配木耳,滚豆腐,色味俱佳,补肾强身。不虚此行是渔乡啊。
小时候总是奢望口袋里能有几粒蛏子干当零食,也常常为此跟着大哥去赶海。海水退去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涂滩,涂滩上寂静无声,只有那来去如飞的捉蛏子人,远远望去,简直是奔跑在足球场上的运动员。原来他们单膝跪着的是如同小木船似的泥马,另一只脚要往后踩,这个泥马就带着你往前面跑,我们当地的蛮话称之为“泥遢”。
骑泥马的都有自家固定的涂滩,因为是养殖,蛏子也就相对集中,他们伸手就是一大把。而我们只能在涂滩上找寻那些闲散的野生蛏子。野生的味道固然鲜美,但是收获不大。大哥说蛏子洞小而冒泡,但抓到的往往是小蟹和海螺,半天下来腰际的竹篓还是在飘忽。犯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冒险侵犯那些蛏子王国。慌乱之中都忘记了手指上的小布套,尽管刺着了手,但也无妨,善良的蛏子绝不会给你留下疤痕。远处的泥马飞奔而来,叫喊声伴随着呼呼的海风,气势甚是吓人,但看着我们跑了又疾速而去。
此时的涂滩显得更为广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