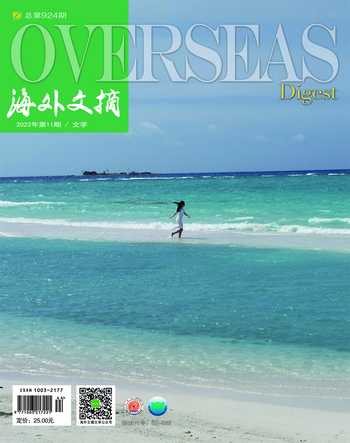两棵树上,一棵树下
刘醒龙

再到簰洲湾,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这些年,心心念念的情结。
出武昌,到嘉鱼,之后去往簰洲垸的路途有很长一段是在长江南岸的大堤上。江面上还是春潮带雨的那种朦胧,离夏季洪水泛滥还有一段时间。在时光的这段缝隙里,那在有水来时惊涛拍岸的滩地上抢种的蔬菜,比起别处按部就班悠然生成的绿肥红瘦,堪可称作俗世日常中的尤物。除了蔬菜,堤内堤外所剩下的就只是树了,各种各样的,一株株,一棵棵,长势煞是迷人。
有百年堤,无百年树。这句话本指长江中游与汉江下游一带平原湿地上的特殊景象。
因洪灾频发,大堤少不得,老堤倒不得,大树老树只是栽种时的梦想,还没有活够年头,就在洪水中夭折了。1998年夏天的那场大洪水,让多少青枝绿叶停止了梦想,也让不少茁壮的树木在传说中至今不朽。
第一次离开簰洲垸时,就曾想过,一定要找时间再来此脚踏实地走一遍。1998年8月下旬,搭乘子弟兵抗洪抢险的冲锋舟,第一次来簰洲垸,一行人个个穿着橙色救生衣,说是在簰洲垸看了几小时,实际上,连一寸土地都没见着,更别说只需要看上几眼就能用目光逼出油来的肥沃原野。除了几段残存的堤顶和为数不多的树梢,我们想看上一眼的簰洲垸被滔天的洪水彻底淹没。汤汤大水之上的我们,悲壮得连一滴眼泪也不敢流,害怕多添一滴水,就会带来新的灭顶之灾,连这少数树梢和残存的几段江堤也见不着了。
那年夏天,使整个簰洲垸陷入灭顶之灾的洪水,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凶猛的,多少年后仍无法忘记,偶尔需要举例时,便会情不自禁地拿出来作相关证明。前些时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非要将个人文集里早前写就的“簰”,按时下规定改为“排”。与其沟通时,自己问对方应当知道“簰洲垸”吧,“九八抗洪”时,不少媒体也曾按规定写成“排洲垸”,后来全都一一改正过来。又与对方说,《闪闪的红星》插曲所唱“小小竹排江中游”,武夷山九曲溪的导游词“排在水中走,人在画中游”,如此竹排哪能禁得起滔滔洪流?在大江大河之上,承载重物劈波斩浪,非“簰”所莫属。簰是特大号的排,但不可以统称排。正如航空母舰是超级大船,却无人斗胆称其为船。簰洲西流弯一弯,汉口水落三尺三——浩浩荡荡的长江上,能与重大水文地理相般配的器物,岂是往来溪涧的小小排儿所能担当!
2021年初夏,第二次到簰洲垸,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陌生的,因为第一次来时,从长江大堤溃口处涌入的大洪水,将最高的楼房都淹得不见踪影,平地而起的除了浊浪便是浊流,与此刻所见烟火人间,稼穑田野,判若天壤。很难相信,眼前一切所见,在23年前的那个夏天,全都沉入水底。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地里种着尤觉清香扑鼻的优质甘蓝,刚刚开过花便迫不及待地露出油彩梢头的油菜,还有那骄傲地表示丰收即将到手的麦子,用粼粼波光接上云天迎候耕耘机器的稻田,这些一眼就能看透的乡村田园图景,仿佛开天辟地以来即如是,不知洪水猛兽为何物!当年所见簰洲垸,只有洪水与舟船。如今的簰洲垸,小的村落有小小的车水马龙,大的乡镇有浓浓的歌舞升平。那些被水泡过的老屋仍旧烟火兴旺,喜气洋洋,一旁新起的高楼与新建的长街更加抢眼,临近小河的一栋栋农舍,颇得诗风词韵,如此流连,迥然于1998年夏天来过后,太多伤心下的欲走还留。
梦浅梦深,亦真亦幻的时刻当然很好,所谓美梦成真,就是将日子过得如同美梦一样。由于当年子弟兵的驰援才从最艰难的日子挺了过来,由于三峡大坝建成后对长江上游洪水的拦截,由于普天之下的民众都在勤劳勇敢奔向小康,一向狂放不羁的洪水也将凶悍性子收敛起来,哪怕是乘着最大洪峰笔直往东而来,不得不在簰洲垸顶头的大堤前扭转半个身子往西而去时,一改从前的暴虐,反倒以岁月流逝模样用浪花之上的江鸥点染一段温情。
最能表现这温情的是小镇边上两棵白杨,还有朋友反复告知的那棵杨柳。
说簰洲垸白杨树多,是事实,又不全是事实。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凡是依靠着长江的村落乡镇,没有不是将种白杨当成洪荒时节安身立命的最后机会。
1998年8月1日夜里,簰洲垸大堤没能顶住洪魔的肆虐,溃口了。后来通过视频看到,惊涛骇浪之中,那个名叫江姗的小女孩儿死抱着一株小白杨,硬是从黑夜撑到黎明。当有人来施救时,小女孩儿还不敢放手,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说奶奶让她抱着小白杨千万不要松手。奶奶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抱不住小白杨,随洪水永远去了天涯。洪荒之下,生命没有任何不同。那比狂飙凶猛百倍的浪潮来袭时,一辆辆抢险的重载卡车,顷刻之间成了一枚卵石,淹没在浪涛深处。一位铁汉模样的将军,到此地步,同样得幸抱着一棵小白杨。
23年过去,小镇边上的这两棵白杨树,长得很高大了,粗壮的树干拔地而起,那并肩直立的模样,其意义就是一段阻隔洪水的大堤。私下里,簰洲垸人,將一棵白杨称为“将军树”,将另一棵白杨称为“江姗树”。小镇的人这么说话,听得人心里格外柔软,也格外苍凉。不由得想起天山深处的胡杨,华山顶上的青松;想起西湖岸边的垂柳,洛阳城内的牡丹。在小镇中心的簰洲湾“九八抗洪”纪念馆,几张旧照片上,一群人正是紧抱着小白杨才让吃人不吐骨头的洪魔终成饿鬼。从纪念馆出来,再次经过那两棵高大的白杨树时,不禁抬头望向空中,万一灾难重现,这白杨可以给多少人以最后的生机?
在簰洲垸上游约十公里,有个地方叫王家月。1998年8月21日,全世界都将此地误称为王家垸。那天早上,自己随一个团的军人十万火急地赶到此地,打响“九八抗洪”的收官之战,在水深齐腰的稻田里封堵这一年万里长江大堤上出现的最后一个管涌。险情过后,封堵管涌的几千立方米的大小块石与粗细砂砾,成了平展展田野上的一处高台。
相隔23年,再来时,一场大雨将头一天的暴烈阳光洗得凉飕飕的,田间小路上的泥泞还在,当初都曾舍身跳进洪水的几位同行者,小心翼翼的模样,有点像是步步惊心。在离高台不到五十米的地方,自己到底还是站住了。
在高台正中,孤零零长着一棵小树。
不用问便已知道,不是别的,正是当地朋友业已念叨过许多遍的那棵杨柳。
夏天正在到来,仿佛是被最后一股春风唤醒记忆。发生管涌的那天正午,爱人下班时将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就在那棵杨柳生长的位置,对着手机,我没有说自己正在管涌抢险现场,只说一切都好!1998年夏天人们听到“管涌”二字,宛若2020年春天世人对“新冠”的谈虎色变。我对爱人说一切都好时,站在深水中的几位战士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过来!那天午后两点,险情基本解除后,与大批满身泥水的军人一道蹲在乡间小路上,痛痛快快地吃了几大碗炊事班做的饭菜。管涌现场仍有大批军人在进行加固作业,另有三三两两的当地人拎着各式各样的器物,在给子弟兵送茶送水。想着这些,心中忽地一闪念,那时候自己不将真相告诉爱人,只对她说一切都好,本是一句平常话,这种自然而然的表述,既是亲人之间相互关爱,也是发自内心的愿景。那时候,在这高台之下的深水里,身处险境的军人,谁人心里不是怀着青青杨柳一样的情愫,带着杨柳丝丝一样的牵挂。
相比从前,簰洲垸上上下下、堤内堤外一切都好了许多,那叫得出名字的两棵白杨,从风雨飘摇中挺过来,长成参天大树。那曾经指望三万年后才风化成沙土的块石砂砾高台,才几年就有杨柳长了出来,虽然只有一棵,却更显风情万种。这样的杨柳能长多少叶子呢?远远看过去,大约几千片吧,这是一种希望,希望小小杨柳用这种方式记住当初参加封堵管涌的几千名子弟兵。
曾经在干旱少雨的甘肃平凉,见过一棵名为国槐的大树,三千二百年树龄,毫不过分地说,那样子是用苍穹之根吸收过“三坟五典”的智慧,用坚硬身躯容纳下八索九丘的文脉,用婀娜枝叶感受了《诗经》、乐府的深邃与高翔。簰洲垸一带,注定没有见证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老树,能够见证的是分明应当向东流逝的长江,到了此地却扭头向西而去,将洪水猛兽与大小龙王都不太相信的奇观,都付与簰洲垸及其簰洲垸上的西流湾。不必等到再过二十三个年时,不必等到垒起高台的块石与砂砾变得与周围田野浑然天成时,更不必等到小小杨柳和高高白杨都变得千年国槐那样沧桑时,大江之畔无所不在,大水之中万物天成。历经过灾难的白杨全都是周瑜、陆逊那般青壮小伙模样,苦难中泡大的杨柳全都是大乔、小乔一样婀娜姑娘身姿,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走向新的梦想,比起已经固定下来的某种象征,更加令人向往。如同自己刚转过身,就在想什么时候再来看看簰洲垸,看看簰洲垸这里的两棵白杨、一棵杨柳。还有这两棵树上,还有这一棵树下,安详天空,锦绣大地!
一个人行走的足迹,往往就是历史的足迹。譬如这次去嘉鱼,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最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历史的选择。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的确算不上什么,但是当一个个生命被冠以战士的名号,并且由几千个这样的生命组成的集团,在一夜之间从黄河流过的华北大平原,驾驶铁骑疾驰到长江涌起的共和国粮仓一样的江汉平原时,他们的每一步行走,都会在大写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如果没有1998年夏天的经历,很难让人相信,一场雨竟会让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面临空前的危险,不得不让这支庞大的军队进行自淮海战役以来最大规模的兵力调动,而他们的对手,竟是自己国土上被称为母亲河的长江。在去嘉鱼的公路右侧,江水泛滥成一片汪洋,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亘古神话中的大洪荒。当我们又是车又是船地来到簰洲垸大堤上,面对630米宽的大溃口,不堪负荷的心让人顿时喘不过气来。那轻而易举就将曾以为固若金汤、四十多年不曾失守的大堤一举摧毁的江水,在黄昏的辉照下显出一派肃杀之气。这时,长江第六次洪峰正涌起一道醒目的浪头缓缓通过。正是这道溃口,让小小的嘉鱼县突然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正是这一点让原济南军区某师的几千名官兵在二十一小时之内奔行千里,来到这江南小县,执行着比天还要大的使命。
我是7月20日来到这个部队的,与这个团同师里的其他团队一道,于8月8日中午从原驻地出发昼夜兼程赶到武汉,然后这个团又马不停蹄地独自赶往嘉鱼。9日上午车队刚进县城,当地群众刚拥上来欢迎,命令就下来了——拦阻江水的护城大堤出现两处重大险情,数百名官兵连安营扎寨的地方都没看见,便跑步冲上江堤,一口气干了十一个小时。
说来也巧,这个团有八十三名战士是嘉鱼籍的,当他们从大卡车里跳下来,沿街冲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自己的亲人认出来。当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追上来喊着这些战士的名字时,他们除了回头应一声以外,连惊喜的笑容也没来得及给一丝。一个叫刘党生的战士,因其乡音被县电视台的记者辨出,而拍了一条新闻。家住乡下的父亲在电视里看见后,连忙来到县城里。父子见面时,刘党生正在江堤上扛着土包加固子堤。刘党生没空同父亲讲话。父亲就追着他来回走,并不时伸手帮儿子一把,后来干脆同儿子一道一人扛一只土包,父子二人一下子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另外一名戰士的遭遇更巧。那天他在堤下同战友一道值班。忽然见到堤上有自己村里的熟人,他连忙追上去打听,才知道挨着哨棚最近的那座窝棚就是自己家人此时的家。战士走进那被洪水洗得一干二净的家,同家里人简单说上几句话后,又回到值班岗位,从此再也没进过这近在咫尺的家门。
我在这支部队待了三天三夜,其间不知多少次,对当地群众来慰问时顺手贴上的一幅标语出神。标语是:来了人民子弟兵,抗洪抢险更放心。这时候,我总会想起团长张德斌和政委陈智勇反复说过的一句话:视灾区为亲人、把灾区当故乡。这句话来源于陈毅元帅的那句名言: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哪有儿子不孝敬父母!这个团的前身是新四军一师一团,向来以打硬仗闻名。团下属四个大功连队,淮海战役两个,抗美援朝一个,还有一个是在1975年河南驻马店抗洪抢险中获得的。时间选定1998年8月让这支部队在特殊地点上与历史和未来作了次碰撞。在三国古战场的南岸赤壁镇,有道名叫老堵口的江堤,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用泥土和芦苇筑起来的。当然这不是那支后来被解放军彻底击败的军队有意给对手留下的伏笔,但这无疑是常胜之师是否名副其实的又一轮考验。8月中旬,老堵口出现一个直径半米的管涌,从管涌里喷出来的江水达五米高。此时,旅游胜地赤壁镇,已被搬得空空如也!
团属炮营几百名战士冲上去,几乎用尽了生命的一切可能,奋战了几十个小时,硬是奇迹般的将凶猛的管涌制伏了。在我前往嘉鱼的路上,碰见一支海军陆战队的车队。当时天上雷雨交加,地上狂风怒吼,他们的行进更显威风八面。海军陆战队是去替换驻防赤壁镇的炮营,这样的威武之师却面临一场尴尬:当地的干部群众坚决不让炮营走!他们太信任炮营了。不知这些生长在古今兵家必争之地的人们知不知道,这场与洪水的决斗是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的最后诀别。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么棒的部队竟会说撤销就撤销!
对于战士来说,他们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们表现得格外珍惜。来到嘉鱼后,战士们最流行的有两句话:用汗水洗去身上的污垢,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兵;多吃点苦,将来做人有资本!团长张德斌告诉我,他们的家属也特别能战斗。
政委陈智勇同妻子是在老山战场上相恋的,他们有个可爱的儿子叫陈思。哪知小家伙患上严重的肾病,才十一岁两腿就肿得不能走路。他们好不容易找到国际知名肾病专家黎磊石教授,治了一阵,刚有好转,陈智勇就随部队上了抗洪第一线。小陈思在家苦思冥想,画了一幅如何为江堤堵住溃口的设计图:所用材料为钢筋水泥、橡胶和棉絮。我在电话里同小陈思交谈过一次。我问他是否给他妈妈添了麻烦。他奶声奶气地说,我是男子汉,怎么会哩!六次洪峰从嘉鱼通过后,团里的军嫂张燕从漯河发来一封给全团官兵的慰问电:“……我真想马上赶到你们身边,为你们洗衣、烧水、做饭,来安慰你们的疲劳。你们太辛苦了,在这里我代表军嫂们,代表家里的亲人向你们说一声真的好想你……”张团长挥动着慰问电说,这也是他们团的战斗力。
8月21日上午7时,我们还在这个团里采访,突然来了紧急命令,五分钟内五百名官兵便在张德斌、陈智勇的率领下驱车直赴发生险情的新街镇王家垸(注:2021年4月23日,重访此地,方知此村名为王家月)村。陈智勇后来说灾难考验人时,正是上帝对谁的垂青。面对他们的又是一个罕见的管涌,它在离江堤1500米的水田中,直径达0.75米,流量为每秒0.2立方米。發现它时,它已喷出一千多立方米泥沙。水田里的水齐腰深,管涌处,离最近的岸也有几百米,而离可以转运沙石料的地方有上千米。那一带是血吸虫感染区,可张德斌和陈智勇想都没想,就率先跳进水中,在前面为战士们开路。
我有幸在管涌现场目睹了这场与灾难赛跑的全过程。没在水中的稻穗上,战士们用肉的身躯铺成了两条传送带,团长政委不时高喊:决不能让簰洲垸的悲剧重演。有两个连队已在附近江堤上突击干了一天一夜的活,还要轮换休息,早饭都没吃,便又赶来抢险。陆续赶来的部队达两千余人,泡在水中的这些最早到达的官兵直到将两百多吨堵管涌的沙石料全部运到现场才上岸吃午饭,这时已是下午两点。
我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读到有关这次抢险的报道,所有报纸无一例外地都只让人从那句“两千多名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抢险”的语言中,才能感受到他们曾经存在过。我不知道那位被战士们背到管涌现场的泥石堆上的记者,是否写了这些消息中的一篇。我庆幸的是自己数次被记者们当作了抢险的战士,我为自己的鱼目混珠而自豪。我将这些报纸拿给一些官兵看时,他们飞快地扫了一眼,然后淡淡一笑。
这笑让我忽然来了个念头,既然大智若愚,那么会不会是大功若无?王家垸管涌下午1点45分才开始由技术人员倒下第一袋寸口石,但那些根据某些人的行程来写的文章却说中午12点险情就基本排除,那些显赫的名字又一次散着油墨香时,张德斌和陈智勇正带领战士苦战在水田里。从下水开始,二十一小时后,正是第二天早上6点20分,战士们用冲锋舟运完了最后一批沙土包将蓄水反压管涌的围堰垒好后,大家手挽着手,高举着红旗,唱起那首士兵们最爱唱的《当兵的人》。那一刻,朝阳正在升起,在他们的身后彩霞有一万丈高。没有任何镜头对准那一张张英姿勃勃,再厚的泥水也掩不去青春光彩的脸庞。
实际上他们无须别人来评说。听听大功三连的连歌:《这就是三连的兵》!听听大功六连的连歌:《打不垮拖不烂》!再听听大功八连的连歌:《英雄的连队英雄的兵》!三连连歌中有这么一句:“打胜仗,出英雄,为国为民立大功!”簰洲垸的悲剧没有重演,那位六十二岁的老专家曾泡在水中对我说:这些战士一个能顶几十个壮劳力,没有他们,长江大堤恐怕不止垮几十次!灾难像那个被关在瓶子里的魔鬼,一切的企图都成了徒劳。这是真正的大功,它将安宁与平常,不事声张地交还给还在享受平常与安宁的人,不使他们觉察到灾难曾与之擦肩而过,所以大功确实若无。
我真想在中国军队的序列中,这支部队的番号永远不被删改,我也想这么好的官兵应该尽可能久地留在部队中。我想嘉鱼的人民在面对日后哪个雨季的洪灾时,也会对记忆中的这支部队说,真的好想你!我还想,只要长江还在流,它就是这支曾与它鏖战过的部队数千名将士永远的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