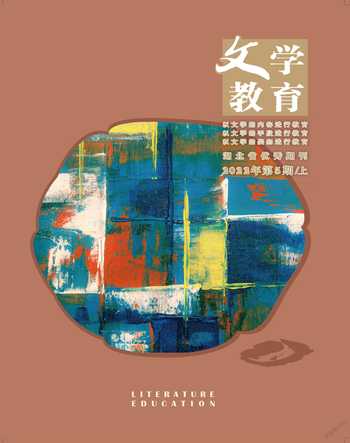论歌妓文化与晏欧词的书写
方兴
内容摘要:在诗词高度发达的古代中国,歌妓与文人们联系紧密。而宋词的创作方式也主要是倚声填词,且依靠歌妓们的传唱得以影响深远,此二者交织发展,从而形成宋代独有的文学和文化景观。宋代歌妓文化发展至顶峰,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学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宋初年,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词人们在延续了南唐词风的基础上,受到歌妓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晏欧词派的文人们在心态和创作方法上较前代均有所不同,体现出独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意蕴。
关键词:晏欧词 歌妓形象 城市经济 文化内涵 心理刻画
词至宋代,已然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再加之词本就是文学和音乐结合的产物,即兼具两种内蕴的艺术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宋时期歌妓制度和文化发展完备,歌妓的发展历史悠久,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宗教崇拜中的歌舞表演,在《尚书·伊训》中就有记载“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这些在宗教仪式中表演的女性可以看作是歌妓的前身。随着社会的发展,歌舞表演逐渐摆脱宗教元素,走向纯娱乐化。
尤其到了宋代,在宋太祖“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号召下,市井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了勾栏、瓦肆等一系列娱乐场所的兴起和繁荣,从而给歌舞乐妓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这一时期,歌妓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已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状态。而享乐主义的盛行让宋代文人与歌妓间的交往成为一种风尚。如此一来,歌妓与宋词的结合更为紧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宋词的题材,扩充了精神内核,提高了词的审美趣味;也让歌妓词逐渐成为宋词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内容。晏、欧二人在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柔情婉媚为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对婉约词有了更深的开拓,尤其是在对歌妓形象的描绘上一改前人过于香艳的指向,进而凸显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
一.灵感源泉:歌妓文化促进词之发展
在五代十国战乱不断的分裂局面结束之后,北宋迎来了统一,农业与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良好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汴京城内有商铺“一百六十多行、六千四百多家”。[1]强盛的国力让百姓们有了安定祥和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重文轻武”的政治导向极大程度地保证了文人们的生存权利,对于文人的种种优待一方面使宋代文人数量激增,另一方面对自身生活的挖掘与探索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重心;因此,娱乐行业便自然而然得到了发展。根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记载,当时汴京城内“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2]由此可见,城内最为兴盛的行业就是酒馆和妓馆,这些场所的大量出现为歌妓提供了得以安身的场所,同时也促进了音乐和歌妓制度的发展,而此类行业的兴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北宋经济的繁荣,所以将北宋经济的浪潮说成是“花潮”则一点也不为过了。
北宋时期歌妓制度趋于完备,且大体上承袭了唐代,根据欧阳炯《花间集序》中所描述的“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3]就足以反映出当时歌妓制度和文化的繁荣景象。歌妓一般可分为三类,即官妓、私妓和市井妓,这些歌妓都是以自身才艺表演为主要的生存手段,即卖艺不卖身。歌妓们大多出生贫寒,地位低微,即便是官妓也同样如此,唐宋时期教坊乐工中的歌妓均无正式身份,并且常被视作“奴婢贱人”,因此无论是受尽宠爱或是被厌弃,歌妓们都难逃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不幸境遇。尽管歌妓们在社会中处于下层地位,但姣好的面容、超群的艺术技艺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学素养让她们常表现出有别于社会底层人的见识与修养,这样一来,能歌唱能做诗写词的她们成为了文人士大夫最为亲密的朋友,也成为了历代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文学形象。
唐中期以后曲子词开始流行,不少文人都尝试依曲填词,到了宋代更是如此,正如王炎的《双溪诗余自序》中就评价了词是“长短句宜歌不亦诵”,而歌妓们的演唱则进一步凸显了词的音乐性,也就有了“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音”的说法了。在继承了婉约派好写物,善描摹的基础上,宋代文人们大力创作歌妓词,开始将歌妓们的生存状态、面容服饰、声腔体态以及内心情感等作为他们创作的灵感和材料,以这些材料入词无疑是丰富了词的内容和文化内涵;如苏轼就创作过不少歌妓词,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在苏轼的三百五十多首词中,其中大约有一百八十多首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歌妓,这些词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苏轼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词人们在作品中展露的真情实感引发了深陷苦楚中歌妓们的共鸣,于是她们通过自身演唱这种娱乐活动,将词人们的作品传播得更广,从而扩大了词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歌妓们与词人们相互成就,难以割裂,词一旦失去了歌妓们的演唱词就失去了最好的传播媒介及音乐性;而歌妓没有了能与其共鸣的词人们的关照也就缺少了让世人们关注和剖析其内心世界的视角,也很难在文学上留下属于她们的重要痕迹。在这样宽松的文化氛围中,词即是词人们与歌妓们在推杯换盏与交流唱和间最钟爱的“歌曲”。由此可见,宋代歌妓制度和文化的发展极大程度上的刺激了词人們的创作热情,丰富了宋词创作的内容,歌妓词的创作俨然成为一种文学风尚。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们也深受影响,创作了一些以歌妓为题材的作品,且凭借其区别于以往同类作品的独特性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二.创作方式:心理刻画辅之容貌描绘
毫无疑问,宋词沿袭了前朝华丽有余,却落于内涵空洞之窠臼,苏轼、晏殊以及欧阳修等人所创作的歌妓词在承袭绮妩媚的特质之外,将生动、率真以及清新之风注入其中从而使歌妓词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和艺术风貌。与词发轫之初注重描绘歌妓舞女们的容貌、服饰,甚至于色情的低俗格调不同,晏殊、欧阳修词中的歌妓们则展现出更多方面的特点,除了在容貌与歌唱弹奏技艺上词人们精心雕琢,无一例外的,晏欧二人开始对歌妓舞女们的内心进行探索,从而挖掘她们的心灵世界,显示出不同于传统艳情词过度沉溺感官描写的取向,更有意蕴和深度。
“富贵宰相”晏殊一生与歌妓结下不解之缘,根据周召在《双桥随笔》中所载:“晏元献虽早富贵, 而奉养极约。唯喜宾客, 未尝一日不宴饮……亦必以歌乐相佐, 谈笑杂初。”[4]由此可见,在晏殊宴请宾客的席间歌舞表演是必不可少的“佐料”,而歌妓们作为表演的主体自然就成为晏殊笔下描写的对象。晏殊平生创作了大量的歌妓词,这些词作在一定程度上虽难以摆脱其身份地位带来的桎梏以及晚唐五代艳词的影响,但晏殊词中对于歌妓的描写更显尊重和欣赏,有一种“远观不亵玩”的距离感;如“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条垂双袖卷”“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等,词人以旁观者的角度来描绘歌妓的美好,在他的描摹下歌妓词中的女性们别有一番韵味,这些女性们均以淡妆展现出清丽的面貌,甚至有一种超脱凡俗的气质,这样的精心雕琢足以显示词人对歌妓们的欣赏与怜爱。且晏殊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多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或是与景物描绘杂糅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整体,但形象和背景并不作为词中的重点,而是作者表达情绪的载体,如《凤衔杯》篇就完美地演绎了晏殊的创作方法,此篇主要通过描绘歌女在浓郁春色中因青春岁月转瞬即逝而产生了无尽的烦恼,以歌女和春色为背景着重凸显词人对岁月匆匆的感叹;又如《更漏子·菊花残》中词人虽描写歌妓美好的体态以及曼妙的舞姿,但词的落脚点在于对时光易逝的叹息和要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诸如此类的词还有很多。由此可见,晏殊对歌妓的描绘更多从第三者的角度出发,给予同等的尊重与理解,且不将其视为创作重心,更多是以这些人物形象作为表情达意的载体或手段。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上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学上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毋庸赘述,但他也有着宋代文人士大夫多情风流的一面,在宋代笔记小说中就记载了不少欧阳修与歌妓交往的韵事,如在钱愐的《钱氏私志》就写了欧阳修因与歌妓幽会而在宴会上迟到之事,而其名作《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就是欧阳修在宴会上所做;且此事在《古今说海》《词苑丛谈》等多部典籍中均有记载。根据史料可知,欧阳修初入政坛之时,就曾写下自己与歌妓“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在其代表作《采桑子》十篇中还能看到他与歌妓舞女们共游西湖的场景,因此,与歌妓舞女交往频繁的他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歌妓词。欧阳修笔下的女性形象众多,而歌妓只是其中一类,却是无法忽视的经典。在这类词中,词人对于歌妓形象的描写体现词人独特的审美观。与晏殊相同,欧阳修写歌妓舞女时更多着墨于歌女们动人的女性特点,如“玉如肌,柳如眉”,词人以美玉和柳枝来凸显歌妓们天然去雕饰的美貌。其次,欧阳修善于描写歌妓们绝佳的演唱技巧,如在《减字木兰花·歌檀敛袂》中就写到“歌檀敛袂。缭绕雕梁尘土暗起。柔润清圆。百琲明珠一线穿”,词人借以韩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和虞公高亢清越之音震动梁上灰尘来凸显歌妓们歌唱效果和技艺,同时又以百串明珠来比喻歌妓们声音之悠长与圆润,这样的技艺不得不令人折服。此外,在其创作的歌妓词中,词人多尝试用细腻的笔触来刻画歌妓们纯真的内心世界。以《诉衷情》为例,在这首词中,欧阳修笔下的女主人公早起梳妆,将眉毛画作远山状,以此表达对情郎的思念,一句“都缘自有离恨”点名分别的愁绪,正因为这种离愁别绪萦绕在心头以至于在演唱之时都要“拟歌先敛,欲笑还颦”,如此一来,词人将歌妓内心中对情人的思念,那种爱而不得之感刻画得淋漓尽致。总而言之,欧阳修虽较少创作艳情词,但他在艳情词上的创作逃脱了花间词人的藩篱,以一种无关风月的情感状态来描绘歌妓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歌妓词的审美内涵。
三.思想内蕴:借歌妓口吻以表情思
宋人尤重女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均能创作词,尤其是女性成为了宋代文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便奠定了宋词以婉约为美的基调以及善用寄托的创作特点。中国古代文学总体而言是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学,因此一些细腻的情感体验常需要借助女性的口吻来表达。歌妓们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她们依赖青春容颜生存,无奈容颜易老,身份卑微却对爱情有着无限的憧憬与向往,又在求爱不得后又落入无尽的失落与悲伤;以上種种均能引发与她们交往颇深的上层文人士大夫对自我人生的深沉思考,于是文人们将其写入词中以此寄托自身情怀。
古言有云“女为悦己者容”,足以见得女性对于美丽的追求,而容貌作为歌妓们赖以生存的因子,其重要性则不言而喻,但华美青春终是短暂的,于是词人们从歌妓们对于容颜衰老的哀叹中发现人生哲理,抒发独属于自身的人生体验,如晏殊的“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又如欧阳修所写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些词句均表达了词人们对于人生苦短多缺憾的思考。歌妓们身世凄苦,一生漂泊无定,这常引起处在被贬谪境遇中词人们的共鸣,如在宋仁宗皇祐二年,正值晚年的晏殊遭遇了晚年流落异乡的痛苦,辗转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晏殊创作了一篇《山亭柳》,他借助歌妓的口吻来表明自己的遭遇,先是描写了歌妓年轻时红极一时,而年老色衰之后,人去楼空,只能靠在街上卖艺,以“残羹冷炙”来糊口。这与晏殊《珠玉词》中其他赞美歌妓的词不同,在此篇中有他对歌妓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漂泊的忧愁。还如《破阵子·燕子欲归时节》中通过描写独自伫立在高楼上的女子来比拟自己家道落寞时的悲伤。同样是写歌妓的悲惨,欧阳修则更多着眼于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反思,如在《渔家傲·为爱莲房》中就有写多情女与薄幸郎之间的爱恨纠葛,“妾有容华君不省,花无恩爱犹相并。花却有情人薄幸”,在他的笔下,歌妓们的悲惨遭遇和对爱情的渴望是对当时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以及情爱生活艰难的真实关照。
自古以来,就有以男女之情来寄托政治之思的传统。从屈原的香草美人说开始,历代文人们在经历被贬谪,被去官之时都常以女子自比。显然,这与古代君臣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君主处于至高的地位,因此即使是男子,在君主面前都只能呈现阴柔的心态,此时他们的内心对于君主赏识的强烈期待与女性对于情爱的深切向往有着高度的重合,而借男女之情表达对于君主的尊敬更显忠厚与温柔。从而,词人们流离失所之苦闷与歌妓爱而不得之伤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用文人刘克庄之言总结即:“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论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5]这样的表达在晏欧二人的词作中也常有,如“当时清别离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就是写于晏殊被贬至宣州之时,他将圣上比作“意中人”,以一种极为悲伤的口吻书写了自己一路上的复杂心情,以及难见“意中人”的孤独之感,此类作品中的形象和情感表现细致,均是上乘佳作。如上文所言,词本身就拥有含蓄蕴藉,便于寄托的重要特征,而古代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决定了含蓄是词人们谏言献策最为妥帖的表达方式,因此词人们常借助女性口吻传递内心的政治情思。总之,歌妓们悲惨艰辛的身世和生活,与爱情的分离以及身份地位的地下都让她们情感体验丰富而又真实,这些独特感触与词人们的内心情感不谋而合,因而使得词人与歌妓这二者间的关系升华为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
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就曾强调过歌妓在中国古代的爱情、文学、音乐甚者于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因此对于宋词的研究也无法避免要对歌妓这类特殊群体进行关照。宋代歌妓制度与文化发展至顶峰,她们影响着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以及文学风尚。在歌妓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交流唱中,宋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均得到了提升,从而加深了宋词的文化和文学价值。晏、欧二人作为北宋初期文坛的领袖人物,在继承花间婉约词风基础之上,将自身独特的艺术视角、敏感多情的艺术气质以及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灌入歌妓词的创作中,创作出不同于前人的,充满生命力的歌妓形象,赋予了其新的审美和精神内涵,对之后婉约词的发展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3]李一氓.花间集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郭预衡.中国文学史长编: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2.
[5](宋)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A].全宋文[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