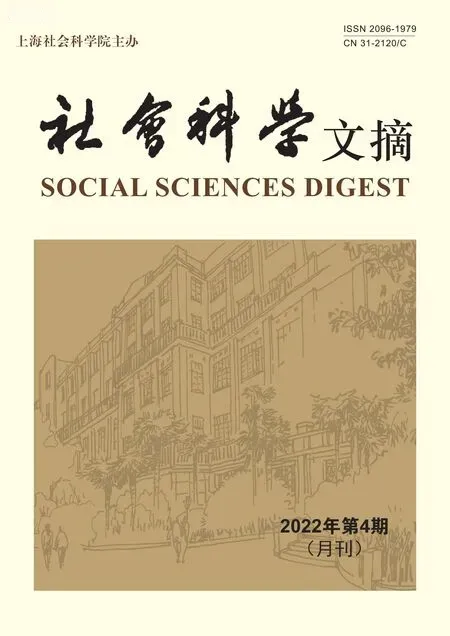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
文/杨光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摘自《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人民主权”旗帜下发生的,都是旨在实现大众民主的社会运动。显然,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是资本主义民主,无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冷战时期,我们从来不会怀疑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属性,倒是真诚地怀疑并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真实性。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成为“民主”的代言人,以至于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证明自己的民主性。如此有违事实真相的世界政治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他山之石:美国在民主话语权上的逆袭
美国是怎么“不战而胜”的?美国在民主话语权上的逆袭起着决定性作用。“十月革命”后苏俄推动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使民主成为一种潮流,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强大的压力。这时的美国也需要证明自己是民主国家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怎么做的呢?第一步,改造民主的含义。传统的民主含义都是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是实质民主,熊彼特将实质民主改造为程序民主,主张民主是选举产生政治家做决定的政治,这样就诞生了“选举式民主”概念,民主等于选举、竞争性选举等于民主,人民主权被置于第二位,或者说人民能不能当家作主就不重要了。第二步,改造民主的性质。资本主义民主被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或多元主义民主,这一学术工程主要是罗伯特·达尔完成的。由此,民主变成了掩盖不平等问题的一个“可爱”的词汇。第三步,在改造民主概念的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又改造了“合法性”概念。马克斯·韦伯首推合法性概念,原意是由合法律性组成的、有效率的政府就是合法性政治即值得人民信仰和服从的政治。半个世纪后,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将合法律性这个关键词置换成竞争性选举,由竞争性选举产生并有效执政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从此,“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的观念开始流行。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几代美国政治学者一直在论证着美国民主的普世性,完成了民主话语权上的“逆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民主理论的建构和表述上,美国政治学同行为冷战作出了重大政治贡献,其关键经验就是将自由主义思想社会科学化,让意识形态宣传以社会科学的面貌出现,使受众更容易接受。
那么,如何表达中国式民主?我们说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够沟通起来。然而,民主要落地,必须以各自的历史条件为前提,民主形式要与历史条件相适应,因此才有“西式民主”“中式民主”之说。作为西式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包括两大部分,首先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其次是民主的实践工具,实践形式是为了实现政治价值,或者说实践形式必须与作为历史条件的政治价值相匹配。研究发现,无论是作为自由主义内核的代议制、个人权利和多元主义,还是作为民主实践形式的竞争性选举,都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欧洲文明的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民主是欧洲文明的政治表达。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民主政治理论表述问题
在政治价值上,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的最强大最持久的政治哲学无疑是民本思想,它是以“社会”为“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或者说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的通约性。在中国的语境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表述为民本主义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一种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种表述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时代性转化。其实,梁启超最早把民本主义视为中国的民主,孙中山的民生、民权、民族思想也可以理解为民本主义民主的具体表达。在当下,民本主义民主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的人民民主思想。西方国家也在用“人民民主”这个词,这就是笔者一开始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人民主权、人民民主的旗帜下发生的,因此以人民民主很难区分民主的程度和民主的真假。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在不放弃人民民主的前提下,更多地使用自由主义民主。同理,我们在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候,也应该找回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本思想,以实现政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相统一的民本主义民主。
和自由主义民主一样,民本主义民主是一种价值模式,价值模式需要制度形式和实践形式去夯实。在政治制度上,相对于西式代议制民主,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政体或组织原则,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靠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也就是党领导的人大制度产生一府两院,后者反过来对人大负责。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此保障了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的社会活力,否则大一统就难以存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形成了新型的政治—市场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在政治—市场关系上,有集中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规划,也有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是事实上的民主集中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上,有集中式的严格限制的领域,也有登记备案制的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这也是事实性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无论是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大制度还是重大政治制度即中央—地方关系,抑或是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新型权力关系即政治—市场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贯穿的都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理解改革开放后权力关系的“钥匙”——为什么不变的政治制度能有机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民主集中制就是各种权力关系的纽带或中枢神经。
在政策过程中,相对于西方多党制下实行的“多数决原则”,我们是通过协商民主而达成政治共识,堪称“协商共识型民主”。共识民主概念也是西方学者论证的,原因是对“多数决原则”的不满。在现实中,比如美国国会立法,因为两党的对立,很多要求2/3多数的规定很难达到,法律就无法形成。美国民众强烈呼吁通过立法形式管控泛滥的枪支暴力,但是民众的诉求就是得不到回应,原因就在于不能满足绝对多数。相反,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国策,全民公决的简单多数就能通过,比如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比较而言,不迷信“多数决原则”的中国,各个层次的立法或者政策制定都实行协商民主。在全国层面的立法中,涉及国民切身利益的法律比如《物权法》的制定过程实行充分参与和协商,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也是充分征求专家意见和部门之间充分协商的结果。政府部门的政策一般关乎利益攸关方的切身利益,国务院有专门规定必须充分听取专家和民众意见的法定程序。在基层治理中,中国有关于“民主恳谈会”的很多经典案例,这事实上就是协商共识型民主。在乡村治理中,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在基层单位管理中,协商共识都是比票决制更普遍、更管用的民主形式;即使两种民主形式都使用,一般都是先协商后表决,没有协商的表决往往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或者是无结果式的无效治理。一句话,在中国各个层次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协商共识型民主的经验,无视这些宝贵经验而闭门造车、想当然地出台的一些在实践中已经行不通。也可以认为,协商共识型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政治过程中的生动体现。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不是摆设,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用来造福人民的。能够造福人民的民主就是真民主、大众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而有利于少数人的民主是寡头民主或者资本主义民主。因此,衡量实践中的民主只能依靠治理能力与治理程度,能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的可以称之为“可治理的民主”,否则就是“无效的民主”或“无效的治理”。要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仅有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选举式民主是远远不够的,不仅是因为参与者的能力、力量有强弱之分——强势集团的诉求往往更容易得到实现;而且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还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者政党或者政府的事,政党—政府基于民众利益表达的自主性回应就是关键性变量,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的政治过程最终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基于民众参与、自主性回应、有效治理所构成的政治过程堪称“可治理的民主”。“可治理的民主”是一种兼顾大众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概念,是真正的国家理论或者政治学理论,而只讲大众权利不讲国家权力的民主理论是去政治的、去国家的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可治理的民主”其实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理论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采取民主集中制政体才可能实现有效治理。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党和政府自然有更充分的关于民众诉求的数据,一些民众的利益诉求并不必然通过“代议制”而得到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制度和体制更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发展。相反,代议制是因代表各自、各地的利益而诞生的一种政治制度,政治是碎片化的利益分肥制,西方所有的政治原理都因此而产生,内化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和难以改变的利益结构,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人工智能时代并没有优势可言,大数据极有可能被碎片化而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
回到现实实践中,为什么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出现普遍性的无效治理?关键在于有民众参与而无自主性回应,或者因“否决型政体”而无法有效回应,国家长期处于内卷之中,无论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美国控枪的难题,说到底都是有参与而无有效回应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普遍性的无效治理大多是因为采取了作为代议制民主主要形式的竞争性选举。在欧洲,代议制政府的竞争性选举起源于封建制,国王不能搞定封建领主,封建领主组成议会以实现对王权的制衡。尽管国王和封建领主处于对立状态,但毕竟属于同文同种,比如通过战争、妥协最终达成共识而接受这套制度。但是,当这套制度即以党争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用在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尚处于封建制乃至部落制状态,国家认同没有完成,世袭土地制度仍然存在,结果党争更加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根本得不到执行。更重要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同质条件下出现的党争民主,在异质文化下就可能是分裂国家的制度性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着民主化运动,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也是理解目前乌克兰东西之间的内战、利比亚内乱的要素。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说“历史终结论”终结了,原因就在于出现了“中国模式”。我们很难给予中国模式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比较而言,如果说美式民主是被改造成自由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中国式民主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说民本主义民主;如果说实现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代议制民主,那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则是民主集中制;如果说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实践形式是竞争性选举或者党争民主,那么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实践形式则是协商共识型民主;如果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党争民主招致无效的治理,属于“无效的民主”,那么中国的协商共识型民主则能实现有效治理,属于“可治理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民主集中制—协商共识型民主—可治理的民主,就构成了以人民民主为价值原则的中国模式。实际上,西方的民主模式内部也有很大差别,比如英美更多的是多数决模式,而德国日本则具有共识型民主的特征。强调中国式民主,旨在说明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只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文明之中,否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政治现象:政治制度相似但治理程度有天壤之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有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民主模式的历史政治学
用西方政治学方法论,无论是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旧制度主义方法论,还是追求个人权利的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民主模式,甚至都会给出否定答案。中国的民主模式只能用诞生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历史政治学进行阐释。历史政治学追问的是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历史轨迹,而基于不同属性的历史所诞生的政治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民本主义民主根植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强大的民本传统为基础和资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是一个基因共同体,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由此所产生的现代性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比如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连续性、民主集中制与大一统历史秩序的内在连续性、协商共识型民主与协商政治传统的内在连续性、可治理的民主与“致治”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换句话说,历史政治学为中国民主模式找到了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
如果中国是引入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为核心的民主模式,那么自由主义民主、代议制政府、多数决民主等与中国历史文化是什么关系?无疑具有高度的紧张关系乃至对抗性关系,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毛病,正如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显示的那样。其实,美国民主理论家这样告诫追求民主的人们,如果既没有历史条件又没有现实社会基础,民主必然难以有效运转。改造了合法性概念的李普塞特也警告世人,竞争性选举的社会条件是均质文化而非异质文化,社会条件比民主形式本身更重要。
正因如此,中国民主模式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历史的中国”这样的大型政治文明体才有可能享有与生俱来的自主性而非依附性,才可能以自己的条件而不是他人的条件、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人的方式去实现中国的根本性政治议程——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