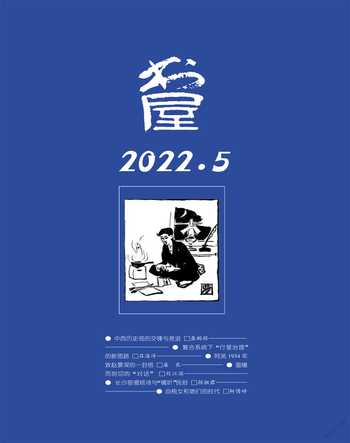抗战时期重庆的粤菜馆
周松芳
抗战时期,国统区有一句流行的名谚,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也就是说前方在打仗,紧张得要死,士兵衣食都无着,国民党官僚则在后方歌舞升平,大肆吃喝。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尤以重庆最为典型。
一
1943年7月28日,卸任驻美大使尚未归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人每日可领二十四两米,但总不够额;每月三十五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那〔哪〕能不坏?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作人看待!”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写于1945年1月28日的一篇文章更写到士兵饿死的情形:“由广西柳州运兵入云南,曾派某军官押运,此人在昆明市外西北五里许黄土铺住宿,该地保长负招待之责,据其自述,一路饿死或病死的兵颇多。押运官到昆明市后,即向负责机关领粮,但减价出售款归私有。士兵大致吃稀饭,难得一饱。士兵夜间许多人共宿一房,无床和被,少数人能坐,多数人站立。次晨开门,有人依墙而死。过此往楚雄交兵,据估计自广西柳州至交兵地点,死亡的士兵约占一半。”士兵的这种惨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早有亲录,1941年6月5日,他自重庆乘船去泸州途中,看见“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梅贻琦等旅客“船上三餐皆为米饭,四盘素菜,略有肉丁点缀”,但“兵士早九点吃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
至于后方的紧吃,虽然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及给酒席限价,且本人平日只喝白开水,生活也可谓俭朴,但自郐以下,无复论矣。从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总务及人事的参事陈克文先生的日记中,我们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他上通行政院长甚至蒋介石,下及很穷困的公务人员,所见所闻,自然堪为典型。比如1938年8月19日他在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处吃饭喝法国红酒,自觉有些过分,但也认为不算啥,因为奢靡之风遍及重慶:“重庆有名厨‘姑姑筵(系商标之名)者,筵席费因受节约运动之限制,仅取八元,惟另取酬劳金:登门卅元,出门城内六十元,城外二百元,迎者仍不绝,可谓豪矣。”以至于“汪先生闻此,对目前之节约运动,深致怀疑”。
其实焉用怀疑,行政院长孔祥熙一直就在带头搞奢靡之风,而且一直主动违反新生活运动之规定。早在南京做行政院副院长时期,一次(1937年11月4日晚)各部会长官欢宴他,那奢华气派就让陈克文瞠目:“主人十五人,客一人,共费一百九十余元,仅烟酒一项便是五十元左右。富人一席宴,穷人半年粮,真不虚语。际此国难万分吃紧,前方浴血搏战,国土日蹙之时,最高长官对于宴会所费,仍毫不吝惜,无一不以最上等者为标准,亦可叹也。”到了重庆,做了院长,虽然遵令制定了一些生活规则,比如行政院不宴请参政员,但别人不敢请,孔院长却亲自来请,而且亲自安排大超规格事宜,“(1938年10月27日)孔院长忽然要宴请参政员驻会委员”,仍宴必求奢,“新生活运动规定每桌八元,我们可以要每桌十二元的”,“事实上庶务科定的菜馔每桌还是十六元的”,超了一倍。又有一次(1940年1月12日)请行政院各部会的部次长、委员长、副委员长到嘉陵江畔山上新落成的外宾招待所吃晚饭,吃得在座的许多人都大发感慨:“有些人望望堂皇的饭堂气象,望望丰富的肴馔和不可多得的黄色牛油,很有感慨的〔地〕说,到底我们中国伟大,打了两年多的仗,居然还可以建造这样的新式建筑,居然还有这样讲究的西菜可吃,英法和德国打仗还不到半年,已经要计口授粮了。”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李先闻教授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受农林部派遣赴美接受善后复员训练,则以亲身经历描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初去美时,吃得尚称无限制。整块牛排,有二寸厚,半尺见方,馆子里都可买得到。但到1945年春天,到馆子就只能买碎牛肉饼和鸡杂了。好的部分都送到前线给士兵享受……”1945年6月回川以后,见在成都的世家豪族还大鱼大肉,“歌舞升平,酣醉通宵,哪像战事正殷景象”。
当然,假公济私是常有的。孔祥熙有多少私人宴请是假公之名?“(1940年4月13日)核了一批院长机密费开支的账目。孔院长请客的开销最大,每个月总在二三千元,每一次请客每桌筵费多者七八十元,少亦四五十元,水果烟酒还不在内。今日接到国防委员会蒋委员长的命令,限制公务员宴会:此后非机关核准,认为公务上必要者,不许宴客;经核准的,每客所费亦不得超过二元五角。将来各机关和公务员是否能切实奉行自然很成疑问,长官如不能以身作则,更行不通。孔院长这种请客能受限制吗?我想决不会有所变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许多法令之所以行不通,这也是一个原因。”如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使孔祥熙遭到了社会部长谷正纲的公然讥刺:“(1943年5月27日)本星期二院会席上,提到公务员生活补助费事,孔院长说,公务员生活困苦,余所深悉,但国库负担过重,一时想不出好办法;社会部长谷正纲说,安得无办法,有钱的人多出些钱可矣,还说了些其他的话。所谓有钱的人,其意即指孔院长。孔含怒说:‘谷部长你常在外骂孔某人有钱,革命党并不是人人皆系穷光蛋,有钱人参加革命的也不少,孔某人并不是参加革命之后才做生意赚钱的。你一言,我一语,形势殊严重。此殆半年来院会之最可记录之一事矣。”真可谓贻笑大方的丑闻了。
他们那些小公务员有多苦呢?陈克文日记中也写道:“(1940年11月7日)经济部的人说,某科员子女五六人,只能用盐拌饭吃,买不起蔬菜,更买不起肉类。”“(1943年1月17日)唐文爵从青木关来,诉说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看他消瘦如野鹤,公务员的苦状已毕露无遗矣。”且不说这些小公务员,即便清廉的高官,也同样是清苦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日常生活主要靠“每三个月分配到面粉一袋,每一个月分配到菜油七十二两,都不足用”,“她(蒋廷黻夫人)的幼子四宝患肺炎初愈,劝她买点猪肝给他吃。她说,价钱太贵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在陈克文日记中也有所反映。比如1939年4月7日:“徐公肃邀晚饭于飞来寺外交宾馆,客人有《中央日报》的社长程沧波,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总编辑陈博生,此外为铸秋、公琰和初次见面的朋友,共十一人。餐是每客两元的西菜,酒却是每瓶五十元的洋酒白兰地。白兰地喝了一瓶半,差不多一百元。酒是外国来的,牛油也是飞机从香港带来的。在这时候我们居然能够喝到洋酒和﹝吃到﹞香港的牛油,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这些东西自然是为外宾预备的,我们不过揩油而已。但问良心总是不安的。”这是抗战初期的公宴。及至抗战后期的私宴,也同样追求豪奢:“(1944年5月24日)郑道儒假铸秋寓请吃晚饭,席中均系行政院同事。厨子是有名的顾家厨(顾祝同的厨子),菜品有虾蟹、青鱼、鳅鱼、田鸡,都是目前不容﹝易﹞得的珍馐,耗费总在一万元以上。公务员生活虽苦,这种宴会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享受的。”而与粤菜有关的则是:“(1940年11月19日)曾养甫和甘乃光请我和之迈到他们那里吃乳猪。曾养甫自诩他的厨子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能手。菜确很不错,难怪他自己吃得又肥又白。他说乳猪只不过几元的价值,可是烧烤的用炭却费几十元,这也是一件怪事。”曾氏的豪奢,陈克文觉得怪,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则觉得愧:“(1941年10月13日)晚曾养甫请客在其办公处(太和坊三号),主客为俞部长,外有蒋﹝梦麟﹞夫妇、金夫妇及路局数君。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酒有Brandy,Whisky;烟有State Express。饮食之余,不禁内愧。”按:曾养甫(1898—1969),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与陈立夫同学,1924年获矿冶工程硕士学位,1925年初回国,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广州特别市市长、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等,1938年后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交通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得此肥缺,自然豪奢无忧,但也实在过分。不过他也做了件“大好事”,就是高薪礼聘蒋梦麟为顾问,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2年4月2日)孟邻﹝梦麟﹞师相告,曾养甫聘其为滇缅局顾问,月薪一千元,生活问题差可解决。师每月所入不足三子读书,月有亏空。近来全校人人不得了,然其尤甚者,莫师与月涵先生若。日前月涵先生女公子得西人家馆,月入可千元,今师亦得此,可稍免张罗之劳矣。”
二
重庆食风,必得外江相助。重庆是历史文化名城,古巴郡、江州和后来的渝州、重庆府治地,而且早在1890年中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确定为通商口岸,1895年《马关条约》又使重庆成为中国第一批向日本开放的内陆通商口岸,因之英、日、法、美、俄、德总领事馆陆续设立,但真正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商业的全面繁荣,则有待于1929年重庆正式建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从商埠向都市转型,特别是1937年之后,五方辐辏,始底于成。餐馆业尤其如此,大作家张恨水即有及时敏锐的观察:“客民麇集(重庆)之后,平津京苏广东菜馆,如春笋怒发,愈觉触目皆是。大抵北味最盛行,粵味次之,京苏馆又居其次,且主持得人,营业皆不恶。其理由如下:冠盖云集,宴会究难尽免,一也。入川之人,半无眷属,视餐馆为家庖,二也。莼鲈之思,人所俱有,客多数日一尝家乡风味,三也。餐馆就地取材,设置较易,四也……廿七年十一月廿日晚,密雾笼山,寒窗酿雨,书于枣子岚垭寓楼灯下。”
为我们留下记录最多的恐怕非顾颉刚先生莫属。顾氏是当红的大学者,也是著名的学术领导者,故每至一地,无不诗酒流连,应酬频繁,以致他小学的同窗好友叶圣陶先生在1938年都连连感叹说:“颉刚真是红人,来此以后,无非见客吃饭,甚至同时吃两三顿。彼游历甘肃、青海接界之区,聆其叙述,至广新识。不久彼即离此往昆明,云拟在郊外觅居,以避俗事。然恐避地虽僻,人自会追踪而至,未必便能真个坐定治学也。”他的诗酒流连之地,当然少不了粤菜馆;这多少也与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等职有关吧。
在列叙顾氏重庆粤菜馆生涯之前,我们不妨先简单介绍一下他抗战期间的行止。抗战军兴,学校和学人均纷纷南迁,顾氏则于1937年获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之聘,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前往甘、青、宁考察教育。1938年10月始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文史教授,兼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9年秋转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1941年赴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史杂志社副社长(叶楚伧任社长,顾主持社务)。1944年秋再回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1945年又任复旦大学教授并兼任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国出版公司总编辑。1946年2月离渝。自到重庆任职后,期间虽曾离渝赴蓉,但因为文史杂志社职始终未辞,还有其他诸多重庆的政学兼职,故始终在重庆时间为多。他曾自谓流连诗酒很多是出于工作需要,比如每月四千元的《文史杂志》主编费,便基本用于跟作者见面谈稿子了。
顾氏在重庆第一次上粤菜馆的记录是1941年1月31日:“饭于大三元……今午同席:予(客)、张姑丈夫妇、子丰夫人、珍妹、子丰二女(主)。”而1月29日他还在日记里说:“米贵至三百元以上一石矣,肉贵至三元以上一斤矣。大家觉得生活煎迫无法解决,一见面即谈吃饭问题。今年如不反攻胜利,许多人将干死。”大有即使饭吃不上,馆子还是要上的味道。
大三元是重庆著名的粤菜馆,早在1938年9月24日,《中央日报》即有大三元酒家招待新闻界月饼的报道。《宇宙风》1938年第六十九期沧一的《重庆现状》,罗列各商家,粤菜馆可只提到大三元一家呢:“商家呢,有沪杭的绸缎店,有冠龙、大都会等照相馆,有大三元、小有天等吃食店,有苏州、南京等处的种种老招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赴贵州宣慰,两广同乡会在贵阳大三元酒家设茶点欢迎,梁说贵阳大三元比重庆大三元还大,并题写了“贵阳大三元酒家”的招牌,也从侧面反映出重庆大三元的地位。或许因为大三元的名声,顾颉刚是屡屡与席的:
1942年8月27日:唐京轩邀至大三元吃饭,晤傅秉常。
1942年9月10日:访唐京轩、龚仲皋,与同到大三元吃饭。
1943年10月6日:到都邮街大三元吃茶。
1943年11月2日:回聚贤处,与诸人同到大三元吃饭。
1946年4月2日:到大三元吃饭。
大三元也真还胜流如云。国民政府行政院主管总务及人事的广西岑溪籍参事陈克文,在重庆期间上粤菜馆的总次数虽然不如顾颉刚,但上大三元的次数则不相上下,而且更有故事:
1939年1月8日:学生刘宗立邀晚饭于大三元,到内政部司长陈屯……皆农所学生。
1939年2月8日:晚间刘建明请晚饭于大三元酒家。除了著名﹝的﹞怕老婆的国府委员邓家彦和林翼中两人之外,其余都是不相识的。
1939年12月6日:陈树人夫妇请到城里大三元午饭。甘乃光夫妇、马超俊夫妇、刘蘅静均在被请之列。
1940年11月21日:因为有便车进城,和之迈、铸秋同到林森路访出名的女诗人徐芳小姐。后来同到大三元吃午饭。
1943年6月15日:上午和铸秋同车进城,邀律师陈廷锐夫妇吃茶于大三元酒家。
1944年8月16日:因事到市中心区,吃午饭于民权路大三元。
著名史学家刘节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据说生活极为清苦,但仍多上粤菜馆,其中两上大三元:“(1939年2月1日)仲博亦来,即与一同至大三元午餐。”“(1939年7月9日)仲博卧病数日,人觉稍瘦。同至大三元饮茶,谈至十时左右。”
顾颉刚去粤菜馆最早的是大三元,去得最多的则是岭南馆和广东酒家,日记中分别录得九次。陈克文去广东酒家也不少,并且说:“那里的风味和广州的茶居早市相差不远,有各色的广东点心。”又说:“物价虽贵,茶客依然满座。”
叶圣陶1942年去了一趟桂林,途经重庆,也特别来喝过一次早茶:“(1942年5月5日)晨起茗于广东酒家,进点。”
当时重庆最大最有名的粤菜馆,非冠生园莫属:“在每个星期日的早晨,重庆冠生园的热闹情形,恐怕是孤岛人士想像不到的。桌子边,没有一只空闲的椅子。许多人站立在庭柱旁边,等候他屁股放到椅子上去的机会。有人付账去了,离开椅子,不过十分之一秒钟,就被捷足先登,古人说席不暇暖,这里的却有‘席不暇凉之概。”并因着“座客完全是上流人”而想象全国的冠生园莫不如是:“从清早七时到十时,全国展开着这样一幅图画。”(画师《重庆冠生园的素描》,《艺海周刊》1940年第二十期)如此名店,著名的顾颉刚先生自然也有多去。
陈克文关于他自己在重庆上冠生园的最后一条记录,弥足珍贵:“(1939年7月12日)中午应刘昌言、郭松年约,和铸秋同到城内冠生园午饭。五月三日空袭以后,到城里吃館子这还是第一次。城内的馆子,现在只有两家,每日十一时以后,便关门不做生意,情况殊为凄寂。城内经过五月六月的空袭和最近两次夜袭,差不多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了。”也即是说,在敌机狂轰滥炸得几无一间好房,别的餐馆都不敢或不愿营业的情况下,冠生园成为硕果仅存的两家开门营业的店家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大餐馆里唯一的一家。如此敬业精神,焉能不成为重庆粤菜馆乃至重庆餐馆业的标杆?
叶圣陶先生则将冠生园作为其宴饮生活的重要参照:1942年5月5日夜,“祥麟以开明﹝书店﹞名义宴客,至冠生园。久不吃广东菜,吃之颇有好感。一席价三百元,以今时言之,不算贵。”1938年1月11日的一封信中说:“李诵邺兄之酒栈已去过,二层楼,且买热酒。设坐席八,如冠生园模样,颇整洁。”也以冠生园为参照来介绍朋友的酒栈。1938年10月8日在致洗、丐、伯、调诸先生信中,说到重庆有名餐馆生生花园,则拿上海冠生园来作参照:“规制如上海冠生园农场,本月二日曾与颉刚、元善、勖成前往聚餐,为卅二年前小学四友之会。”由此,可见冠生园酒楼在他心目的地位。
粤香村也是叶圣陶去过的酒家:“(1942年5月7日)吴朗西来访……君知余能饮,邀往一家售绵竹大曲之店。自菜馆不许饮酒以来,酒店之生意大好,客恒不断,几如茶馆。例不许售荤菜,只备花生豆腐干。各饮酒二两,遂饭于粤香村。”
粗略统计,顾颉刚在重庆期间,至少上过大三元、广东大酒家、广东酒家、冠生园、岭南馆、广东味、粤香村、广东馆、广东人家、珠江食堂、南国、广东第一家等十二家粤菜馆,这不仅超过所有其他人的纪录,也超过所有的重庆指南书的纪录。如此看来,对于我们今天考察粤菜的向外传播,特别是在重庆的发展,顾氏真是功不可没。
可惜当时重庆还有几家有名的粤菜馆,顾颉刚没有提到,或者忘了记录。比如南园酒家,陈克文先生曾于1939年1月9日应甘绍霖之邀在此晚饭。刘节先生也曾两度前往,而且初到重庆第一顿饭就是在那儿吃的:“(1939年1月31日)宿处既定,乃与仲博同至新川旅馆洗澡理发,晚至南园酒家晚餐。”“(1939年8月17日)晚上戒严,余方在南园晚餐。”此外,还有国民酒家、国泰饭店、陶陶餐室。
这样,依笔者寓目的文献材料,当时重庆知名的粤菜馆,如果说名流眷顾的粤菜馆至少有十六家,再加上时人记述不及而各指南书涉及的醉霞酒家、南京酒家、广州酒家、大东酒家、清一色酒家、四美春酒家,则达二十二家,如果再加上冠生园的另两家支店,则有二十四家了,这明显超过了除川菜之外的所有下江菜系。粤菜的向外发展,不避治乱,均粲然可观,委实值得我们珍视和骄傲。
——宋·王安石《咏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