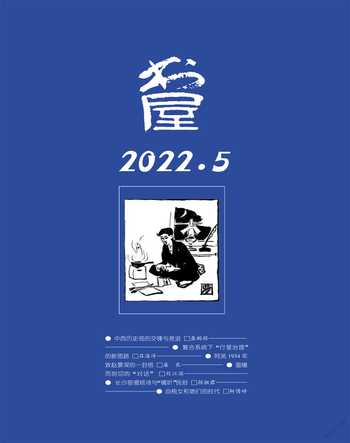鲁迅与新式标点
张素丽
新式标点符号的吸纳采用是汉语现代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遭遇新式标点,张德彝、王炳耀、马建忠、严复等人是早期向国内引介西方标点符号的几位,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鲁迅、周作人、胡适、高元、钱玄同、刘半农等紧随其后,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的出台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
在符号功用上,新式标点与中国传统的句读有根本的区别。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并无标点符号一说。旧式标点称作句读,标法比较简陋,以圆点号和顿点号为主,常常一号多用。文言写文章既不用标点,也不分段、不分行,但由于古文句式简练且结构变化不大,语气词、助词等虚词发达,句法上较为对偶匀称,文辞上重音句不重义句,因此简单的句读亦可满足阅读的需要。随着西学的大量涌入和文白转换的语体变革潮流,新式标点符号逐渐“侵入”我国的书写语言系统。
从形式上看,新式标点只是一套相对繁杂的符号系统,对今天熟練掌握这套符号规则的使用者而言,其意义似乎无足轻重,但这套符号却是“文法精密”的外在表征。首先,它引发的是一场“词法”“句法”“章法”层面的书写大革命,文章在书写上提行分段,外观上迥异于从前;其次,它促进了文字表情达意的句法功能变革,语法上产生诸多新变。郭绍虞将标点符号的引入称作“欧化”的一种“创格”。在五四时期,钱玄同非常重视标点符号在修辞上的“传神”功能,譬如新式标点可以让白话在语气上趋近“言文一致”;胡适、陈望道等人则非常看重标点符号彰显“文句之关系”的“达意”功能,认为它可以让白话的字句结构变得繁复丰满。
“文体家”鲁迅是新式标点符号的早期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提出“要清清楚楚的〔地〕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在鲁迅和周作人于1908年至1909年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中,已大量引入新式标点,极大地提高并深入拓展了汉语文字的表现力。学者普遍认为,《域外小说集》称得上是汉语书写语言革命的标志性产物,在《域外小说集》的“略例”第四条中,鲁迅对译文中新式标点符号的用法进行了说明:
!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
在这里,鲁迅对晚清时期尚较稀见的感叹号(!)、问号(?)、破折号(——)、省略号(……)所表达的口吻语气与具体用法进行了阐释,引号在这部译文集中是避用的。鲁迅所谓感叹号(!)表大声之说,不够准确,应为表“惊奇、赞叹”的语气。省略号和破折号在当时的书写文本中基本上是“前所未有”,它们的输入引起不少人的严厉抨击,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的大胆采用表明了他的革新立场和勇气。
被称作“摇曳标”(陈望道语)的省略号,在晚清至五四时期,对到底该用几个点来表示没有统一的规定。不同的作者,有的用五个点,有的用六个点,有的用八个点,还有用十二个点的,《域外小说集》中就有用九个点的现象,如“尼启丁先生、君毋尔、………当众人前、………主人且怒”。在具体用法上,《域外小说集》有用省略号模拟声音的,有用省略号表达无尽幽微情感的,还有用来表达意义“留白”效果的,位置上也是句首(或段首)、句中、句尾均有出现,可谓是“号尽其用”。
破折号是《域外小说集》中大量使用的另一种新式标点。破折号在意义上表补充说明或略作停顿,使用时既可插入句中,也可放在句末。破折号的合理调用可大大增加句子的结构灵活度,增强句子的语义密度,达到延缓语气流动的叙述效果,有助于形成精警精悍、幽婉从容的文风。《域外小说集》在破折号的使用上,极力挖掘这一符号的丰富表现力,取得了完全不逊于白话文创作的艺术韵味,如译文《默》中,牧师伊革那支说:“吾自愧,——行途中自愧,——立祭坛前自愧,——面明神自愧,——有女贱且忍!虽入泉下,犹将追而诅之!”这段话通过对破折号的密集使用,生动再现了伊革那支将女儿逼死、妻子逼疯后,悔愧不已又不甘承认的心情,形象模拟了他的语气由中辍滞涩转向急促愤激的状态,把他心口不一、推卸责任的心理特征呈现得惟妙惟肖。在翻译于1934年至1935年间的《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著,鲁迅重译自日本高桥晚成翻译版本)中,据统计,鲁迅对破折号的使用有三百五十五处,其中六十八处作为标号使用,二百八十七处作为点号使用。鲁迅对破折号的使用主要是用作提示性语句和直接引语之间的停顿,这与破折号的规范用法是有出入的,与高桥晚成译本中的使用也不相同,属于鲁迅在中国新式标点初创期的探索创新。破折号在视觉上横线形的漫长形体,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语体感觉,与作品的内容特质较为契合,这或许是鲁迅在这部译作中创格使用破折号的原因所在。
除了对省略号、破折号等单一标点的突破使用,《四日》等文本中更有对多种新式标点的综合运用。就用法而言,《域外小说集》对新式标点的应用基本上已臻于成熟。鲁迅之所以能成为新式标点的勇敢实践者,离不开他大规模阅读并翻译外国文艺语言体验的直接促发,对新式标点的“移徙具足”,是鲁迅“循字移译”之“直译”观念的重要表现。
1911年,在鲁迅的文言小说也是鲁迅生平第一篇小说《怀旧》中,引号被大量使用。这篇小说大致写于辛亥革命至民国初年的绍兴,刊载于1913年4月25日上海《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引号的采用使得这部小说的场景组织形式灵活多变,在体式上与白话小说中已很接近。《怀旧》借助新式标点对文言文本进行了最极端的改革试验,鲁迅的文言也因此成为清末民初“欧化”文言的重要构成。《怀旧》在风貌上全然迥异于古典文言文本。引号的使用让人物对话不再需要间接引语陈述,而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分行出现。“。!”“。?”“(……)”等标点符号的创造性运用,折射出鲁迅在符号层面的某种“表意的焦虑”,标点符号和语言文字之间的张力空前加剧,汉语书写的可能性被推到更大限度。王风认为,鲁迅清末民初的著译事业,实际上为他的新文学创作准备了新的“章法”。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怀旧》等早期著译中对新式标点的输入,为其白话汉语创作中文体标号的创新使用进行了充分准备。
鲁迅的新式标点实践是始于文言而非始于白话,这一点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意义非凡。这意味着,鲁迅所做的是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根本变革,其用法不仅与晚清白话报对新式标点的用法显示出区别,更提示了一条话语变革层面的个性化实践路径。新式标点在传统书写汉语中的全面引入,不仅为鲁迅的文章带来了全新的“章法”,更为其白话文写作中话语实践的创造性展开提供了资源依凭。自鲁迅的第一篇白话作品《狂人日记》起,他的新文学创作在“章法”“段落”层面就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文字与符号的张力极大地彰显出来。可以说,提行分段、划分章节是《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文本内部的最大修辞手段,省略号、感叹号、问号等标点符号的功效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妥当发挥。章节段落、标点符号与文字的巧妙组合使用,在鲁迅小说的故事场景、人物心理的刻画上,常起到逼真生动、形象贴切、言简义丰的叙事效果。以小说《长明灯》中的这两段对话为例:
“上半天,”他放松了胡子,慢慢地说,“西头,老富的中风,他的兒子,就说是:因为,社神不安,之故。这样一来,将来,万一有,什么,鸡犬不宁,的事,就难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来到府上,麻烦。”
“是么,”四爷也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鲇鱼须,却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说,“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呵。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萨么?我那时就和他不合,可是一点也奈何他不得。现在,叫我还有什么法?”
新式标点的引号,使得人物对话上的直接引语表达成为可能,人物对话内容和效果对文字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在《长明灯》的这两段对话中,第一段为了展现郭老娃说话的“慢吞吞”,鲁迅把逗号、句号、冒号、省略号与多个短句子交叉使用,将人物断断续续、装腔作势的说话口吻与腔调刻画得淋漓尽致。紧接着的第二段,为描摹四爷“悠悠然”的说话神态,鲁迅有意将句子拉长,标点符号的数量也明显压缩。再如,在《祝福》中,为准确呈现“我”与祥林嫂对话时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窘态百出的样子,小说频繁变换使用破折号、感叹号、问号、省略号、逗号等,细致入微地拟写人物的心理流变。除了通过标点符号来烘托渲染和摹写叙事,强化文字的独特意味,让符号呈现特定的修辞效果,鲁迅还会借用标点来突出文字的视觉或听觉效果,如用省略号的点数来模拟乐曲的循环往复,用点数的多少来传递声音层次的增强或递减,达到一定的“超文本”效果。
在鲁迅的白话文本中,如果说对标点符号的组合运用是作家在规则范围内的“号尽其用”,他对标点符号的创格使用则称得上是作家个体的勇敢探索。他有时会在文章不需要添加标点的地方“添加标点”,传达强调或评议的意思。譬如,“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中“(!)”“(?)”等的使用。这种“添加标点”式的用法,表明鲁迅对新式标点符号的体味和运用,在篇章布局的“章法”外,已然深入到表情达意的“句法”层次。从欧化文言到欧化白话,从局部采用到个体创造,鲁迅对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历程,为我们追踪其“欧化”实践提供了一个“有迹可循”的有益观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