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国调毪”仪式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分析
——以河池市金城江区那阳屯为例
李富强,黄 娟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国调毪”是河池市金城江区壮族村民对师公所做的还愿和祭祀仪式的称呼,也称作“国调”。“国调毪”流行于金城江区保平乡的纳六村﹑古帝村,金城江镇的上任村﹑下任村,东江镇的那阳村,五圩镇的塘降村等壮族聚居地。“国”是壮语汉译音,在壮语里是“做”的意思,“毪”是“舞”的意思,“调”是师公从事敬神祭祀和驱邪活动的一种称呼,属于“武教”类。“国调毪”意指跳“武教”类的师公做还愿和祭祀仪式。“国调毪”表演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仪式中诸多复杂的象征意味值得研究。目前学界对壮族“国调毪”仪式的记录仅在中国音乐家研究丛书中陈恒芳《壮族“国调毪”:河池东江那阳屯个案研究》调查报告有收录,暂无其他研究文献。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对壮族“国调毪”仪式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的壮族传统仪式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国调毪”仪式的生存环境
东江乡位于河池市东部,距离金城江区十千米。那阳屯位于东江乡东部,依东山傍西江,黔桂铁路从村子左面跨江而过,村前边是环江河,河水经此向南入三江口,最后汇入龙江河。那阳屯共有四十三户人家,有蓝﹑韦﹑陆﹑黄等九个姓氏,均为壮族。屯中中青年人大都外出打工,现居人群以老年人为主。
大体上来说,那阳屯壮族的民间信仰以原始崇拜和道教为主。原始崇拜是最古老的民间信仰形式,老树﹑高山﹑巨石等人们认为富有灵性的事物都可以是崇拜对象。例如,村口的大树是村落的守护神,在屋子的神台和女性房间摆放花束是向花婆祈祷家里能够增添子嗣。作为农耕民族,那阳屯壮族还崇拜土地神,开春农忙前,村中都要请师公拜祭土地神,如今这一习俗已慢慢淡化。那阳屯的道教是集传统道教和壮族民间信仰于一身的产物,当地师公做法称为“国调”,而道公做法壮语的汉译音称为“国道”。师公专门从事敬拜﹑祭祀﹑酬神等仪式工作,道公主要负责亡灵超度﹑送终等丧仪,一般情况下师公和道公各施其法,如遇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道公需要借助师公的法力驱邪。师公做仪式时既祭拜如三元﹑三光﹑功曹等道教神,又祭拜莫一﹑三界﹑灵娘﹑雷王等地方神,这种现象在广西十分常见,甚至分不清是师是道,是道是佛。同一个道场,道公﹑师公各占半边,各挂各的神像,各做各的法事,互不干扰,互不排斥,这也反映了壮族民间信仰观念的泛化。在此背景下,壮族民间信仰在“万物有灵”和多神崇拜的基础上,杂糅了道教﹑佛教的某些内容,成为一种新的“共生物”和“混血儿”。[1]金城江区一带壮族“国调毪”仪式正是这样的“共生物”,师中有道,道中杂师,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二、“国调毪”仪式流程
“国调毪”仪式一般有室内和室外之分,室外的祭祀活动有安龙﹑立社﹑还愿﹑游神四种,活动规模较大,多由几村联合举办,在村头或庙前平地举行,举办时间一般持续三至五天不等,祈求洁净村落﹑保境安民﹑增祺添丁。室内活动有驱邪赶鬼﹑招魂治病﹑接花架桥等,规模比较小,主要以求子纳吉和驱邪消灾为主。金城江区那阳屯村民请师公做“国调毪”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请师公来举行敬神祭祖的“还愿”仪式。如某家近年诸多不顺,家主请仙婆查找原因,仙婆言明其祖上曾向神灵许愿并承诺后代会还愿,但因后人未还愿而惹神灵发怒,须举行还愿仪式,家中才能恢复宁静安好。二是家中有非正常离世事件,也会请师公做“国调毪”。
一般“国调毪”仪式分为六场,从搭建神坛到收场,用时三天以上。金城江区师公较常做的还愿主题“国调毪”,其过程如下。
仪式前的准备:搭建神坛与香火台。仪式开始前,师公叮嘱主家准备祭品和方桌,砍来竹子和芭蕉杆。师公搭建神坛和香火台之后,在神坛前架好桌子,摆上酒﹑猪﹑鸡﹑糖﹑饼﹑花生﹑稻穗等祭品,在神坛周围贴上咒符﹑对联,在神坛后壁挂上神像画,然后在芭蕉杆做成的香火台插上咒令,点上香烛,香烛在仪式结束前都不能熄灭。同时,师公会在房屋外侧另摆张桌子供莫一大王,这是仪式中唯一单独祭拜的神。
仪式的进行阶段:围绕“请神—酬神—送神”开展。第一场是请神。锣鼓开响,师公戴上三元帽,身着黑袍,左手持法铃,右手持铁棒,吟唱经书,念毕,倒酒以示敬意,然后下筶,直到筶面朝上即算好。继而师公戴上面具喃唱经文,同时燃放炮竹,并按锣鼓节奏起舞,请三元﹑地主灵娘﹑三界公爷诸神到场助力。其间,主家在师公的指引下不断斟酒﹑摆上祭品,以讨诸神的欢喜。第二场以全筵供物酬神。主家摆上更多祭品,宰杀水牛,用牛血上供。第三场上演幽默剧《功曹﹑卜言与土地》,锣鼓节奏欢快,气氛活跃,逗乐观众。接着师公邀请三光﹑三元﹑地主灵娘﹑婆王﹑三界公爷﹑冯泗(冯仕)﹑冯远﹑莫一大王诸神前来施法,驱除妖魔﹑晦气。第四场请安家神﹑龙王﹑金童玉女﹑雷王﹑社王前来享用供物,福佑主家乃至整个村落。第五场再以全筵大供诸神,师公向诸神下跪,喃经﹑献酒﹑跳舞。“请神—酬神—送神”的环节如此不断重复,直到第二天下午。
仪式的结束阶段:仪式尾声,师公在神坛前用力敲锣,“铛”的一声,意味着诸神归位,宣布收场。师公用神剑砍烂神坛﹑香火台,将一切物品装到竹编的“龙船”上,敲锣念经,送圣外出。物品焚化后,仪式就结束了。
不同主题的仪式带来的效果虽有所区别,但从筹办“国调毪”的诉求来看,当地人通过筹办仪式向诸神供奉,以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因此,“国调毪”仪式普遍具有慰藉人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
三、“国调毪”仪式的重要元素
经书﹑法器﹑面具﹑神像画等是壮族“国调毪”仪式元素,它们也是师公使用的各种器物。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器物被赋予神化意义,代表着神的形象和权利。师公在特定场域中运用的器物即是对器物固定意义的延伸和发挥,从而保证仪式意义更加丰富和完整。[2]109其中,面具﹑蜂鼓﹑莫一大王崇拜是仪式的重要元素。
(一)面具
唱神必跳神,跳神必戴相。金城江区壮族“国调毪”仪式所用面具一般有十三面,包括莫一﹑三界﹑三元等。面具是人们从经书唱本中提炼出来的诸神形象,面具的刻画对色彩﹑构图有一定的艺术要求,须把诸神的特征尽量表现出来。每个神都有其特定的性格和相应的舞蹈动作,各司其职。如果遇到天灾,就要请师公跳三元,当地人认为三元有呼风唤雨的本领,可以让万物生长;如果不孕不育则要请婆王,当地人认为婆王掌管人类繁衍,请婆王到家中接花,妇女能怀孕得子;若是久病不愈,则请三界公来驱邪除魔,治病救人,保境安民。按照传统的壮族师公的说法,“国调毪”仪式应该有三十六神七十二相,共一百零八面面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面具都失传了,现在实际使用的面具数量远少于此。笔者访谈的兰玉广师公家中现保留有十三面于2007年雕刻的木面具。“国调毪”仪式中师公必须要戴面具,师公戴上面具意味着身份转化,当请的神来了,师公便是代神传话的人。据此而言,面具具有较强的象征功能。
(二)蜂鼓
蜂鼓是“国调毪”的主奏乐器,引领全场,“蜂鼓不响不开坛,以鼓为戒行三罡”。蜂鼓鼓腔以陶土烧制而成,鼓端大,中间细,一口呈喇叭状,一口为圆球状,腔内中通。鼓长有50—60厘米,壁厚1厘米。大鼓端直径有20—24厘米,小鼓端直径有10—17厘米,腰腔有5—8厘米。鼓身以8—12道绳勾紧两端,收拢紧绷,套上活结系于鼓腰,调整活结的位置可调节音高。使用时,右手拍击喇叭状鼓端,左手以竹片﹑竹棍敲击圆球状鼓端,可竖直或横放击打,因此,蜂鼓还被称为横鼓。南宁市西乡塘区陈东村﹑南宁市邕宁区﹑百色市田阳区﹑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等地也称其为岳鼓﹑瓦鼓。
蜂鼓是我国古代腰鼓演变后的诸形式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将其追溯到周代土鼓﹑唐代宫廷细腰鼓以及宋代桂林永福花腔腰鼓。土鼓最早是在祭祀时使用,在《礼记·礼运》中有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鬼神。”[3]后经证实土鼓即陶鼓,仅叫法不同。陶鼓乃为敬鬼神之器,以瓦为匡,以革冒之,以蒉桴击之。[4]北魏至隋唐时期,西域双面细腰鼓的传入影响我国古代陶鼓的发展。至唐代,细腰鼓(陶鼓的演变形式)广泛运用于宫廷音乐并开始南传,江西﹑湖南﹑四川﹑广西等地曾出土过相关实物。唐宋时期,腰鼓的生产和使用中心逐渐南移,宋代岭南成为腰鼓生产和使用的第二大中心,尤以广西为重。在传承中,腰鼓被多民族吸收并改造,演变成后世多种形式的双面细腰鼓。今天仍可见的瑶族长鼓﹑壮族蜂鼓﹑毛南族祥鼓就是古代细腰鼓的演变诸形式。[5]
蜂鼓在广西师公文化圈中享有“蜂鼓不响不开坛”的崇高地位。在金城江区“国调毪”仪式中,蜂鼓既作为乐器引领全场节奏,也作为法器联结神界与人间,是打开仪式神圣性的通道,一些地方不允许人们随便触摸和敲击蜂鼓。蜂鼓引领师公舞蹈,蜂鼓一响,皮鼓和锣钹紧随其后,时而严肃,时而欢快。从蜂鼓引领的节奏中即可看出各神或幽默风趣﹑或慈悲为怀的性情,也可渲染扑朔迷离的仪式气氛。基于前人研究,本文列举了开场请神﹑女性神用鼓﹑武神用鼓来凸显蜂鼓鼓点的特色。[6]“可”为皮鼓滚鼓声,“冬”为皮鼓声,“皮”为蜂鼓大端声,“打”为蜂鼓小端声,以四二拍节奏击打。
开坛请神时,锣鼓节奏有跳跃感,音色庄严沉静,以烘托神仙下凡之感,节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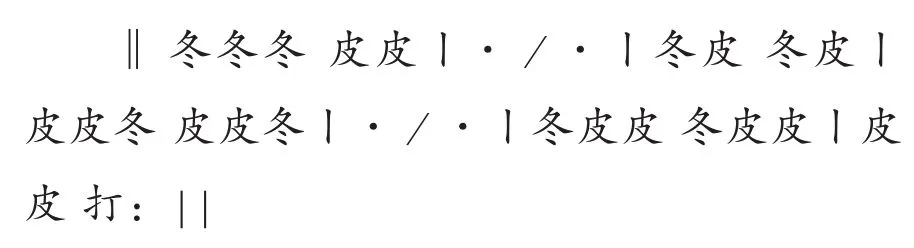
莫一和冯泗这类武神出场时,锣鼓节奏激烈,表现出英雄骑马出征与敌拼搏战斗的气势,节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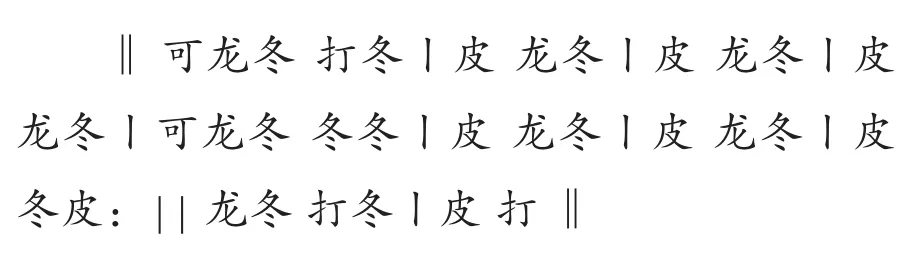
而灵娘和婆王等女性神的鼓点节奏平稳,音色明亮清晰,刻画出女性神温柔﹑勤劳的性格,节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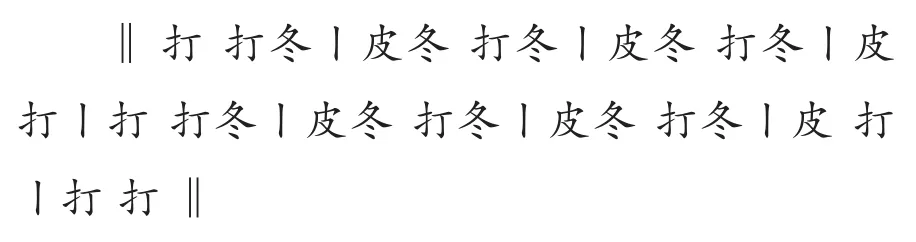
师公使用蜂鼓时将其横置于鼓架上,右手掌拍击大端,左手持小鼓条或者竹片击小端,击法有单击式也有连击式,连击可奏出丰富多彩的节奏花样。蜂鼓声尤为突出,确实有“合乐之际,声响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7]的可能。随着历史的推进,蜂鼓从最初娱神的法器演变成娱人的蜂鼓舞蹈﹑蜂鼓说唱。1956年河池市代表队改编的《壮族蜂鼓舞》登上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民间文艺汇演》的舞台,后被选至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如今,金城江第三小学建有蜂鼓说唱传习所,供校内学生学习壮族蜂鼓文化使用,以弘扬和传承蜂鼓文化。
(三)莫一大王崇拜
莫一大王是“国调毪”仪式中最重要的神,在仪式中独设一张桌子供奉莫一大王,并有独立的经书唱本。师公在收坛时要扮演莫一大王,将所有妖魔鬼怪杀死。在民间传说中,莫一是河池市金城江区公华村人,生时有虎来朝,瑞气环绕,面赤如朱。莫一凭借异人的能力为民除害,深受百姓敬仰和喜爱,后因剿寇有功,被朝廷封为通天圣帝,其神迹奇事沿传至今,各地尚建有莫一祠堂或庙宇福佑地方百姓。
莫一大王崇拜广泛流传于壮族民间的师公群体和普通百姓中,在一些地区建有莫一大王庙。关于莫一大王的真实性,学者各有说法。有的认为历史上确实有真人真事,有的认为壮族百姓对莫一大王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民族英雄的崇拜,有的认为莫一大王是壮族人民根据对现实中的巫师及相关宗教职业者的揣测或理解塑造出来的。[8]总的来说,莫一大王崇拜包含了壮族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情感体验和文化体验,可视为蕴涵壮族文化心理特质的“原型”代表。莫一大王崇拜“一方面反映了壮族社会历史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壮民族的文化态度﹑精神特质和民族性格”。[9]笔者亦赞同此说法,以莫一大王为代表的英雄崇拜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民族性格和心理的折射。与莫一同类型的其他民族英雄人物传说还有很多,如岑大将军﹑独齿王等,都是英雄利用超自然手段与皇权抗争从而为百姓争取利益的故事。莫一大王崇拜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象征着壮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过去,莫一大王崇拜是表达壮族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的理想与愿望;现在,莫一大王崇拜则是强化和巩固民族历史记忆的手段,是群众延续民族精神命脉的体现。
在关于莫一大王的长篇叙事诗中,壮族蜂鼓与莫一大王崇拜之间存在着渊源。[10]莫一因有功于朝廷而被封王,后因得罪朝廷而被斩首示众,莫一的头刚被斩断就腾空而起,飞向他的家乡河池市金城江区公华村。莫一让妻子把自己的头藏在瓦缸里,七天七夜之后才能揭开盖子。但到第六天,莫母偷偷揭开瓦缸,看到缸内有很多虫子在蠕动,便泼下一瓢水,顿时一群蜜蜂从缸内飞出来。蜜蜂飞进京城把皇帝和贪官们蛰得鼻青脸肿,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壮乡老百姓。此后壮乡百姓建莫一庙,养起蜜蜂,杀牛宰羊,仿蜂体做成鼓身,以羊皮蒙面,制成蜂鼓。乡民们抬牛羊,击鼓,来到莫一大王庙烧香纪念他。蜂鼓便在壮族民间流传至今,壮族师公认为蜂鼓可唤来莫一大王的神灵,为民驱邪降怪,消灾除难。历史上壮族蜂鼓的源起与莫一之间并未见有直接关联的记载,但诚如学者所言:“乐器与流传的神话故事之间无不体现出该民族的原始思维方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不论是乐器,或是与乐器相关的傩仪﹑祭祀﹑巫术的背后都是以生命为母题,承载着乡民重视生命,对幸福平安生活的美好期待。”[11]
四、“国调毪”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将宗教现象分为信仰与仪式两个范畴,认为“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12]。仪式是信仰的实践与表征,仪式研究更能表现信仰的核心内容及其文化内涵。
(一)“国调毪”仪式的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是指文化载体所反映出的人类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内容。“国调毪”作为一种村落仪式,是当地壮族人民精神追求和文化心态的表征,他们通过仪式表达自身对自然的敬畏和英雄的崇拜。
1.自然崇拜
万物有灵的信仰使当地壮族人民对自然十分敬畏,这表现在师公的面具纹饰和舞蹈动作上。婆王和灵娘是“国调毪”仪式祭祀的两位女性神。婆王被认为是人类繁衍的始祖,掌管着男女生育能力。兰玉广师公所雕的婆王面具上刻画着青蛙状的小人,青蛙蕴含多子多福﹑子孙繁衍的美好寓意。跳婆王舞时,一位师公手持一根代表男性生殖器的木棍,与另一位手持红帕的师公双手交叉上下摆动,表演男女互相暧昧的场景,表达对生命繁衍的渴求。当地人认为灵娘姓廖,是莫一的意中人,因其勤劳能干被奉为“护禾”仙女,保佑庄稼丰收。灵娘的面具上画有许多云纹﹑树叶和花朵,还塑有鸟类,足见自然崇拜影响深刻。师公起舞时主要模仿她在田间插秧的劳作场景,灵娘的勤劳能干是一种典范,可以引导村民踏实耐劳,勤恳劳作。壮族先民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创造出本民族的自然神形象和神话传说,这些富有想象力的精神文化在“国调毪”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2.英雄崇拜
莫一大王是金城江区壮族“国调毪”独有神台和唱本的地方神,享有崇高的地位,也是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的一个符号。当地百姓将莫一大王神化用于祭祀﹑巫术活动,认为莫一是诸神的大王,能把所有妖魔鬼怪杀死。此外,三界公和婆王等也都是被神化了的人,这是典型的英雄崇拜。人们将期望寄托在英雄身上,希望他们保佑未来生活的稳定和庄稼的丰收,驱邪逐祟,保境安民。“国调毪”仪式所用的莫一﹑雷王﹑冯泗的面具以大红色为主,表情严肃凶恶,怒目圆睁,眉毛上扬如利剑,是十分典型的武神形象。与之相应的舞蹈融入了许多武术动作,如执剑﹑翻转﹑踢腿等,体现出武神刚正不屈﹑高大威武﹑强劲有力的形象,能为主家驱邪避灾。透过“国调毪”的英雄崇拜可以窥探当地人的心态及生活追求,英雄崇拜背后承载着金城江壮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对生活稳定﹑身体健康﹑人丁兴旺﹑庄稼丰收的期待。
(二)“国调毪”仪式的社会功能
1.维系和增强社区内部的稳定性
仪式作为社区共同的行为,是社区在维护自己的边界时周期性举行的文化展演活动,也是保持社区稳定性的重要措施。从上文可知,“国调毪”是金城江一带壮族共有的信仰行为,除了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部展演,集体性质的“国调毪”仪式把区域内的村落联系起来,形成覆盖社区整体的仪式网络,保证社区价值观和价值规范的一致性,使社区内部保持稳定。另外,在仪式的参与互动中又强化了社区中的人的信仰,使其更加恪守信仰规范。这样庞大的仪式网络覆盖着一个个村落,也联结着每一个人,为仪式所倡导的忠孝礼义仁智信等道德规范的畅通运行提供可能性,并使道德规范普泛化﹑扩大化,使人们的共同信仰得到进一步强化,达到减少社会纠纷和民族矛盾﹑增强社区内部稳定性的作用。
2.提升族人凝聚力,巩固社区的公共关系
集体性质的“国调毪”仪式由附近村落联合成立组委会,各村成员共同参与筹款﹑采购仪式物品等环节,在外地的村民也要赶回参加。当地人认为参加仪式就是去沾福气的,这样在外面工作才能顺利平安。尽管个别年轻人存在“不能全信”的观念,但举办仪式时也尽可能赶回来参与,寻求心灵慰藉与精神寄托,增强文化认同感。信仰的灵验与玄妙使已经离开的人群重返乡土,形成社会整合,相对提升了族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亲属血缘内部的“国调毪”仪式由于耗资巨大,一般是三代人以上才能酬神还愿,家族所有人都要参与其中,远方亲人也必须回来参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们通过参与仪式追忆祖先,强化血缘联系,团结家族内部情感,形成和谐﹑团结的家族秩序。
3.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国调毪”作为金城江区壮族的信仰文化,是团结当地壮族人民的黏合剂,重组和整合社区社会秩序的同时,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调毪”仪式中的唱本及其倡导的价值规范会反复提醒当地人勿忘本源﹑尊重祖先,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基于共同信仰﹑共同诉求或共同利益追求而采取的实践方式,使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公共关系得以确认和稳固,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确保群体内部的稳定。仪式所形成的网络将村落联系在一起,给予每个成员联络感情的契机,无论是地缘共同体还是血缘共同体,都进一步得以强化。“国调毪”仪式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壮汉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
结 语
“国调毪”仪式的发展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都经历过“摧毁—衰退—复兴”的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民俗活动的生存状况有了改善。2011年,那阳师公队带着“国调毪”登上了第十二届铜鼓山歌艺术节的舞台,“国调毪”这个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呈现在大众眼前。2015年,在上海举办的“天地人神 萨满 东亚杖鼓祭”活动上,“国调毪”与韩国杖鼓﹑金秀坳瑶黄泥鼓同台演出。“国调毪”从隐秘走向公开,大众对壮族“国调毪”仪式的文化价值予以认同。传统民间信仰仪式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它会随着时代进步和物质生活提高而变迁,但它的嬗变是有迹可循的。仪式中所表现的人物和故事,是区域社会的历史现象和文化记忆,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心理。“国调毪”仪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最后都汇聚成金城江区壮族人民对民族延续﹑人丁兴旺﹑家庭和睦﹑幸福安康的追求与向往。仪式网络将社区联结成一个整体,从个体层面和社区整体上看,仪式起到维系社区内部稳定和巩固公共关系的作用,对平衡社会秩序和促进民族团结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