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山应》:文学是寂寞的人做寂寞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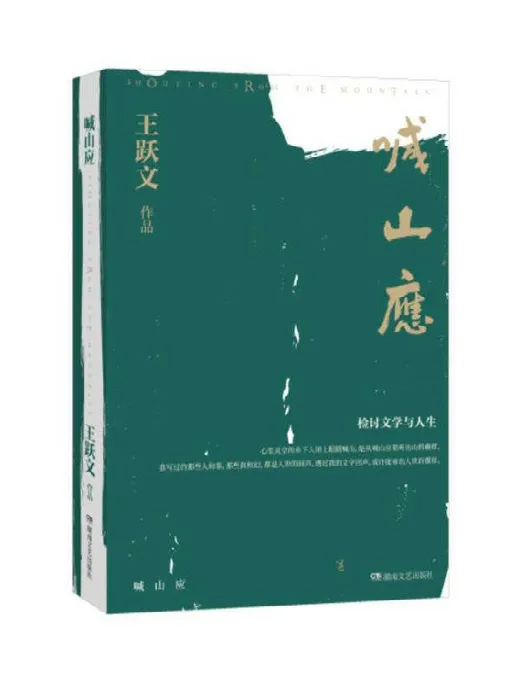
书名:喊山应
作者:王跃文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喊山应》为著名作家王跃文的全新随笔精选集。这本书既是王跃文对自己三十一年文学之路的回顾,也从某一个角度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喊山应》分为“我的文学原乡”“我的文学之路”“我的文学检讨”三部分,附录部分文学评论文章。

关注“十几岁”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新书漂流《喊山应》”,即可轻松参与新书漂流。
试读章节
我的文学原乡
溆水河从南边深山奔腾而下,流到我的村子漫水,水势早已平缓了。河两岸是宽阔绵延的平地,田里的庄稼,油菜、稻子、甘蔗、橘子、西瓜,四时不绝。老辈人没出过远门,直把家乡当平原。我同老人们谈天,告诉他们溆水流入沅江,沅江入贯洞庭,洞庭汇入长江,长江奔向东海。老人们却同我讲神话,说溆水边有座鹿鸣山,山下有个蛤蟆潭,潭里有个无底洞,无底洞直通东海龙宫。
家乡地名“溆浦”二字首次见诸文献,是在屈原的《涉江》里。2300 多年前,三闾大夫溯溆水而上,一个雪日黄昏,船泊吾乡。溆水两岸森林茂密,猿猴的叫声甚是凄凉,群山高耸遮蔽了天日,雨雪纷纷无边无垠,浓云黑黄塞满了天宇。诗人孤独迷茫,“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屈原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还将到哪里去。
我生长在屈原行吟过的土地上,这里至今保留着许多屈原的遗迹和传说。我自小踩着的土地,必定印有屈原的足迹;溆水两岸的芷草和香兰,必定是屈原采撷过的;旧县志说屈原坐过的亭子,虽夏暑而无蚊蚋;屈原垂钓过的江畔水潭,鱼至今还在水底儃佪。
沈从文说旧时溆浦人的营生靠的是“一片田地,一片果园”,说得颇有道理。溆浦农人自古相信一句话:人勤地不懒。溆浦人吃得苦,老天又赐下膏腴之地,这里的出产自是格外丰富。这方土地一年四季从不空闲,凡南方应有之物皆能产出。溆浦出产之物最可夸耀的是柑橘、红枣和西瓜,早已闻名遐迩。
世界上每一条河流都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溆浦的文明史同中原地区大抵同步,春秋时代这里虽为偏僻之地,却早已在王化之内。汉初置县,从此日渐鼎盛。自古多有文人高士流寓溆水,留下过华章佳句。自屈原开始,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唐代诗人王昌龄、明代学者王守仁等,都在溆浦写下过诗篇。王昌龄在溆浦作诗送别朋友:“溆浦潭阳隔楚山,离尊不用起愁颜。”
溆浦属古楚地,方言多古音古韵。杜牧的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诗用普通话读不怎么押韵,用溆浦话念出来,“斜”“家”“花”三字都是押韵的。
旧时山地封闭,往往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山水阻隔的绝塞之境,反倒成就了古老风俗的多样,且得保存和流传。正宗的傩戏、目连戏,如今在溆浦乡下均可看到。溆浦地方戏辰河高腔高亢悲怆,最宜表演古典悲剧,观之令人联想到屈原《国殇》的调子。溆浦民风天真朴拙,年节多有舞龙灯、唱船灯、唱蚌壳灯、划龙船之俗。凡风俗皆有典故,或为纪念,或为祈祷,或为庆祝,但年月久了,早已忘却本意,演化成纯粹的娱乐。这正是乡人可爱之处,凡年节总是热闹为好。
乡俗亦有古趣,尤见于节庆,又以年俗为盛。家乡童谣说:二十五,推豆腐;二十六,熏腊肉;二十七,献雄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夜,炮仗射!童谣用溆浦话念,“夜”和“射”也是押韵的。献雄鸡,指的是杀公鸡。进入腊月,溆浦人宰五禽六畜,忌用“杀”字,而用“献”字。大概是古时献祭之俗的遗风。过年不兴吃母鸡,得吃公鸡。用作年夜饭菜的公鸡,早在夏秋就阉了,长得极是肥硕。早早阉了备作过年的公鸡,亦称作献鸡。童谣所述时间,只是为了押韵,亦渲染操办过年的讲究和热闹。热热闹闹的童谣,也见出孩子们盼年的兴奋。正如俗话说的:大人望插田,小儿望过年。插田才有饭吃,这是大人想的事;过年才有好吃好玩的,这是小儿喜欢的事。
(原文有删减)
对话作者
文字的回声
文/王跃文 彭美琳
问:“喊山应”这三个字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答:我家老宅门口是山间平地,尚算开阔;四周却是群峰耸峙,山高涧深。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心里灵空的乡下人闭上眼睛喊山,能从“喊山应”里听出山的模样。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文学是寂寞的人做寂寞的事。我写过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透过我的文字的回声,或许能看出人世的模样。
问:您三十余年来笔耕不辍。这背后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
答:我只是爱着文学,就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我浸染红尘日久,耳闻目睹,亲见亲历,胸口时常激荡起悲悯和哀伤。如果我是画家,也许会在画布上挥洒很多惊世骇俗的色彩;如果我是歌者,也许会一路行吟长歌;可我是作家,就写小说。
问:从《国画》到《大清相国》,从《漫水》到《爱历元年》,您的小说作品不断满足着读者多层次的审美体验。您自己又是如何定义“好小说”的呢?
答:我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它是真的,甚至比现实还真。所谓“比现实还真”,指的是小说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这“真”中肯定有“美”“善”的一面,但也不能回避残酷黑暗的一面。小说家的良心,就是不能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
问:您如何看待自己身上不断变化的标签?
答:有人读《国画》,说我是官场小说家;有人读《大清相国》,说我向历史小说转型了;有人读《爱历元年》,又说我向都市小说转型了;我写《漫水》那样的乡村小说也有不少,是否据此也要认定我是乡村小说家呢?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有所谓“转型”,这些作品只能说明我创作的题材多样。但是,写作的过程,也是作家成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