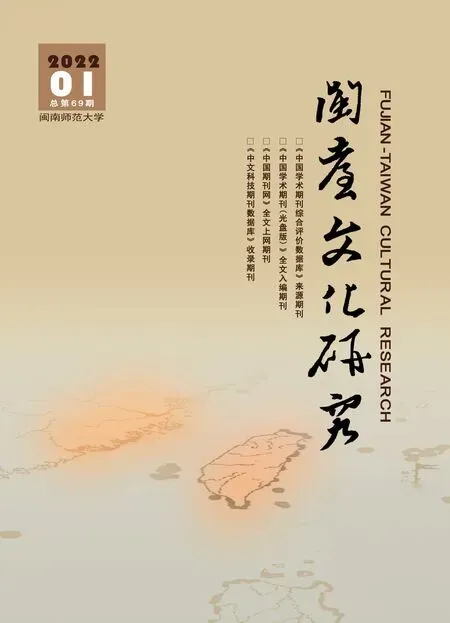清代官方崇祀天后父母考释
陈金亮
(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福建莆田 351100)
关于清代官方崇祀天后父母问题,学术界鲜有专文论及。黄国华先生曾就妈祖的父母名称及封号进行史料梳理。[1]清代官方崇祀天后父母与妈祖精神中的孝道观念密切相关。前辈学者已关注到妈祖精神中的孝悌观念。卢金城先生提出孝悌是妈祖精神的重要内涵。[2]姜家君先生认为妈祖是儒家孝道思想的体现者,是孝慈思想的典范。[3]潘真进先生指出孝悌观念是妈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精神中的孝悌观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4]李志英先生指出民国时期将天后宫改名为林孝女祠过程中,林默的孝女身份及其孝行是妈祖庙宇得以改名并留存的关键支撑因素。[5]陈丽婉女士以社会认知语境模式为理论框架,以陈池养《林孝女事实》为语料,从主题、总体结构和话语的风格三方面探讨妈祖孝女身份的建构形式。[6]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官方档案、地方志、碑刻等资料,对清政府推行崇祀天后父母的具体政策措施进行考释。
一、为天后父母追加封号
追加封号是清政府崇祀神祇的方式之一。清代官员士绅疏请加封天后父母共三次,最终获得褒封两次:
(一)雍正四年(1726),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疏请加封天后先代未获允
雍正四年(1726)正月十七日,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奏称,天后在康熙六十年(1721)对台军事行动中神功显著,呈请加封天后先代。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六月,时任南澳总兵蓝廷珍和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亲率水陆官兵前往镇压。蓝廷珍奏称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天后屡有灵验事迹:由于闽台地区六月台风频发,蓝廷珍和施世骠等向天后祈求庇祐,在天后护佑下,风平浪静。清军所到之处,各处枯井甘泉忽然翻腾涌出,足供清军食用。六月十六日午间,清军攻进鹿耳门,收复安平镇。正值退潮之际,海水反而加涨六尺。又有风伯助力,各船得以群拥直入。六月十七、十九等日,清军会师于七鲲身,血战杀敌。正值酷暑时节,七鲲身地处大海之中,为盐潮涨退之地,清军口渴难耐。蓝廷珍又仰天祈祷,正当潮退,清军在鲲身坡中扒开一尺左右,都有淡水可饮用。官兵们都感到惊讶,称颂神灵效顺。蓝廷珍原计划在平定起义之后,上疏题请褒封天后。但施世骠于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在台湾病逝,蓝廷珍身处台湾,奏请因此耽搁。雍正元年(1723),蓝廷珍升任福建水师提督。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蓝廷珍进京陛见时,面奏天后灵验事迹,乞请追褒天后。雍正皇帝命蓝廷珍上疏题请。雍正四年(1726)正月,蓝廷珍上呈奏折,提出两方面请求,一是乞请赐给匾额联章,此请求得到皇帝准许,后由蓝廷珍负责制造,悬挂在湄洲、台湾、厦门三处天后庙宇。二是奏请追封天后先代。礼部以江海海神的先代从未受到褒封,天妃在海岛显灵,已由康熙皇帝敕建祠宇,加封天后,雍正皇帝钦赐匾额,辉煌庙貌,最终驳回蓝廷珍追封天后先代的奏请。[7]
(二)嘉庆六年(1801),经册封琉球副使李鼎元奏请,追封天后父亲为积庆公,母亲为积庆公夫人
嘉庆四年(1799)六月,清帝命翰林院修撰赵文楷为正使、内阁中书李鼎元为副使,前往琉球册封尚温为王。李鼎元在册封过程中多次提及要奏请褒封天后先代。
早在接到册封任务不久,在京城期间,李鼎元在心中已酝酿,如果此次出使顺利,归来之后奏请追封天后父母,并奉祀于天后宫后殿。嘉庆五年(1801)元旦,李鼎元前往位于北京城马大人胡同的天后宫进香。此庙为福康安破擒台湾林爽文后,为答谢神恩而建。李鼎元观察到该庙正殿奉祀天后,后殿奉祀三官,西侧供奉关帝。李鼎元认为这种奉祀格局不合理。他提到天下受敕封为正神的神灵,往往褒及其父母。何况天后由孝女成神,后殿不奉祀其父母丢失了根本,“元旦日甲寅五更,恭诣乾清宫门朝贺,旋诣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天后宫进香。祠为故大学士贝子福公康安建。贝子破擒台匪林爽文……正殿为天后塑像,后殿为三官神像,西为关帝神像。余进香,心为之动。窃谓贝子建此祠,未尽善也。凡天下受敕封为正神者,率褒及其父母。况天后由孝女成神,后殿不祀其父母而祀三官,失其本矣。毋亦以天后父母未经受本朝封典,故不祀耶?果尔,何不吁请褒封乎?是贝子之疏也。此行仗神默佑,归定吁请褒封,崇祀后殿,以妥神孝酬灵贶。”[8]除前往马大人胡同天后宫外,李鼎元在沿途每遇天后行宫都前往进香。他观察天后宫“后殿俱未追祀后之父母”。
在往返琉球途中,遇到危险时,李鼎元多次向天后祈祷,发愿如天后能帮助解除风险,将向皇上吁请加封天后父母,“因与介山潜焚藏香,跪祷于天后曰:‘使者闻命,有进无退;家贫亲老,志在蒇事速归。神能转风,当吁请于皇上,加封神之父母。鼎元自元旦发愿,时刻不忘,想蒙神鉴。’祷毕,不半刻。霹雳一声,风雨停止。申刻,风转西南,且大。合舟之人举手加额,共叹神力感应如响”。[9]
顺利完成出使琉球任务返回福建后,李鼎元在与福建巡抚玉德的交谈中,又再次提起要奏请加封天后父母事宜,玉德回复称关于加封之事,等李鼎元回来后自己奏请,“以天后灵威、助风击贼,欲具折奏闻,请加封天后父母,并恭报回闽日期。玉公曰:‘加封事,公归自奏未晚。惟恭报回闽一折,不可迟;皇上悬望久矣。’”[10]
嘉庆六年(1801)正月二十一日,李鼎元上呈《为吁请加封天后父母事奏折》,在详细介绍册封途中天后显灵事迹后提出,天后以孝女成神,宋代天后父亲封积庆侯,母亲封显庆夫人,天后兄长及神佐都有获敕封,此后未经加封。李鼎元恳请嘉庆帝褒封,在天后宫后殿设位崇祀天后父母,以报答天后孝亲之思,“内阁中书臣李鼎元跪奏为吁请圣恩加封以酬神贶事。窃查使臣封舟出洋,例请天后于舟中虔诚供奉,历著灵感。此次臣同正使臣赵文楷于嘉庆五年五月初七日乘西南风开洋,于初十日酉时陡遇东北风,暴势甚猛烈,巨浪如山,实为危险。琉球接封大夫并伙长人等惶惧无措,禀请暂行避回五虎门。臣同赵文楷虔祷天后,风即渐息,至子正风转西南。十一日申刻望见姑米山,十二日辰刻即进那霸。迨自琉球回舟于十月二十九日行抵温州外岛北屺,风色不利,舟甚危急,又经虔诚叩祷,遂骤得顺风。自洋面至五虎门计程七百里,一夜便到。计去时在洋面行六日而至该国,回时亦行六日而出重洋。遇险得安,往来迅利,该国人及内地民人皆称神异。及臣抵闽后乃闻六月间飓风击碎艇匪船一百余只,是皆我皇上至诚感格,故屡致灵应如此。臣自京陛辞后敬凛圣训,沿途每遇天后行宫即洁斋进香。遍阅后殿俱未追祀后之父母。窃念天后以孝女成神,志或未尽,似应追封崇祀,以迓神庥。谨按:后父名愿,宋初官都巡检。宝祐五年因教授王里之请,后父封积庆侯,后母封显庆夫人,后兄以及神佐皆有锡命,此后未经加封。合无仰恳皇上天恩特赐褒封,在于天后行宫后殿设位崇祀,以答天后孝思,即以昭圣朝锡类之盛典。是否有当,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议施行,谨奏。嘉庆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1]
嘉庆六年(1801),经朝廷商议,最终同意崇祀天后父母,“六年议准崇祀天后父母,请照雍正三年追封关帝先代之例,勅封天后之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公夫人,由部行文福建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于莆田湄洲及清口惠济祠二处天后宫后殿制造牌位,春秋致祭”。[12]
(三)道光二十三年(1843),经浙江士绅官员奏请,加封天后父母“衍泽”二字。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年(1842),英军两次窥探侵扰浙江,都被风浪所阻。民众认为这是由于天后与观音大士显灵阻止夷船,保全境内民众平安。道光二十三年(1843),杭州府属绅士胡敬、浙江巡抚刘韵琦等奏请皇帝施恩,酬谢天后护佑。道光十九年(1839),天后封号在原有基础上又加封“泽覃海宇”四字,已增至36字,“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天后之神”。刘韵珂等人认为天后封号已十分尊崇,不敢再行奏请追加。根据南宋神灵父母曾受朝廷追封的先例,奏请追封天后先代,“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灵应懋昭,绅耆环请,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据杭州府属绅士前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胡敬等呈称,浙省地处海疆,民间崇奉天后。又省城外法喜寺供奉观音大士,为通省士民所敬信,凡商民人等往返海洋,及遇有水旱疾疫吉蠲走祷,靡不响应。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事,定海等处相继失陷。省城钱塘江下抵海宁州之尖山海口,尖山以外即属大洋,直达定海,汪洋巨浸,防卫难周。省中士民日走祷于天后、大士之前,恭求神力,默相国威。至是年十二月十八日,突有英夷火轮船二只驶至尖山口外,意欲窥伺省城,陡遇风浪大作,该船桅柁俱折,势将覆溺,仓皇远窜。及二十二年四月乍浦失守,十五日复有火轮船一只自乍东驶,甫至黄道关地方,复值风狂浪涌,不能前进,弃碇逃回,皆分防兵勇及沿海居民所目睹。查省城商贾辐辏,乃该夷歆羡之地,今两次窥探,俱为风浪所阻,不克前来。从此犬羊始无觊觎之心,井里得享敉安之庆,此皆我皇上诚格天人,故百灵效顺,俾根本重地危而复安。伏溯我朝海上战功,天后屡著灵应,是以封号频加……兹天后、大士驱除丑类,合省民心咸欲吁恳天恩借酬神佑。查天后封号已极尊崇,不敢再行请益。惟按之志载,神父林姓讳原,一讳惟悫,南宋庆元六年,曾追封积庆侯,又改封威灵侯,又加封灵感嘉祐侯。神母王氏,亦封显庆夫人……此次天后、大士默阻夷,保全境士,功在生民,理合呈乞奏请,追封天后先世,并加观音大士封号,以彰崇德报功之典……臣查杭州省城切进瀛壖,自浙东郡县叠陷,省中风鹤频惊,且侦探夷情,实有赴省滋扰之意。乃其船两次驶至,均为风涛所阻,登即遁回,从此敛戢奸谋,不敢复至,闾里得庆安堵,此固仰赖国威,然亦默叨神力……既据该绅耆等联名吁请,臣不敢壅于上闻。合无仰恳天恩俯如该绅耆等所请,准予追封天后父母,加增观音大士封号,井将海盐县白沃庙神列入祀典,以答神贶而顺舆情。理合恭折其奏,仗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奉朱批:礼部议奏。钦此”。[13]
道光二十三年(1843),道光皇帝下旨加封天后父母“衍泽”二字。道光《龙门县志》记载:“道光二十三年奉旨于积庆字下加‘衍泽’二字。”[14]同治《浏阳县志》称:“道光二十三年,浙江杭州绅士以天后与观音大士默阻夷船保全境土,呈请追封天后先世,奉旨加封‘衍泽’。”[15]同治《上海县志》:“道光二十三年夷务显应,加封神父母‘衍泽’二字。”[16]民国《霞浦县志》记载:“道光而还,以后位极难增追,封启圣原衔加‘衍泽’二字。”[17]
二、安设天后父母神牌于天后宫
清政府追崇天后父母的另一项措施是,在天后宫安设天后父母神牌。神牌或置于天后宫后殿,或在天后宫附近增建殿宇供奉。
上文提到,嘉庆六年(1801),册封副使李鼎元为酬谢天后护佑其顺利完成册封任务,除奏请褒封天后父母外,还奏请在天后宫后殿设牌崇祀,后由礼部行文福建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在莆田湄洲和清口惠济祠天后宫的后殿设置牌位祭祀,“六年议准崇祀天后父母……由部行文福建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于莆田湄洲及清口惠济祠二处天后宫后殿制造牌位”。[18]之选择这两个地方奉祀的原因在于,莆田湄洲是天后出生地,而惠济祠是护佑漕运祭祀天后之所,“祭于莆田、清口天后庙后殿。盖以福建莆田县湄洲为神诞育之区,江苏清口惠济祠并海滨各县为神护济漕艘海艇之贶,故二处之庙特编入会典专祠之条”。[19]
除湄洲和清口这两处天后宫以外,嘉庆年间,清政府还下诏要求各府州县天后庙设神牌祭祀天后父母。如嘉庆《连江县志》载:“诏郡邑应行秩祀处所增设神牌,祀以牢醴。”[20]同治《安福县志》称:“六年,定天后宫后殿崇祀天后父母,凡应行秩祀处所,令地方官安设神牌以时致祭。”[21]光绪《重修华亭县志》称:“嘉庆六年,封天后父为积庆公、母积庆公夫人。凡应行秩祀处安设神牌以时致祭。”[22]民国《南平县志》称:“嘉庆六年十一月间,奉旨天后父母制造神牌安奉,春秋致祭。”[23]民国《宿松县志》:“六年,封天后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公夫人,令地方官安设神牌于后殿。”[24]
受到宫庙空间的限制,许多天后庙并未修建后殿设牌供奉天后父母。有的宫庙只能在祭祀之日,临时借用场地致祭。比如,嘉庆八年(1803)之前,福建兴化府的天后宫,由于规模小,未建后殿奉祀,在祭祀当日,借用与之相邻的凤山寺设位行礼,“兴郡城中,天后特庙坐东面西,规模颇狭,向未有后殿奉祀三代神牌。每于祭告之期,暂假凤山寺禅室设位行礼,未免简亵,殊非遵旨敬神之意……大清嘉庆八年岁在癸亥嘉平月上澣知兴化府事加三级马夔陛敬立”。[25]
为开辟用于安奉天后父母神牌的空间,嘉庆六年(1801)之后,全国各地许多天后宫添建后殿,或在天后宫周围修建殿宇,这些殿宇被称为积庆宫、积庆公祠、先代祠、天后先代公祠、启圣祠、圣父母殿、佑德祠、育圣祠等。如道光《龙岩州志》称:“积庆宫,在天后宫西偏,嘉庆二十一年建。”[26]各地修建供奉天后父母殿宇的时间不一,从地方志和宫庙碑刻等资料可见,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都有相关修建的记载。
各地供奉天后父母的殿宇通常是在地方官的主持下修建。如同治《新建县志》记载当地天后宫由知县添建,“嘉庆六年,奉部添设天后父母神牌,八年知县吴元吉添建后殿,崇祀天后父母,并修葺大殿”。[27]光绪《东川府续志》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知府李德生和会泽知县黄梦菊发起劝捐,增建积庆宫后殿,“天后宫,旧在郡城南门外,通志载在俗祀。道光二十三年奉文追封天后父母,知府李德生、知县黄梦菊劝捐功德,增建积庆宫后殿,旋毁于兵火”。[28]光绪十六年(1890),潮阳知县陈垲增祀天后父母于后殿,“复以灵佑湄洲,追封先后,特起后殿。勅命垲以戊子冬来治斯邑,屡荷神庇……而后殿徒有表哉。上代册封设位享祀典礼阙如,守土之职也。缘有绅民倡议设位,遂于光绪庚寅春二月二十三日……查嘉庆五年追封天后圣母之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夫人,祭于福建莆田江苏清口后殿。兹仿而行之,裨守土官率绅民永远崇祀,以仰体朝廷为民祈福保安、推尊先代之至意云。是为记。钦加同知衔知潮阳县事津门陈垲谨识”。[29]
许多士绅积极捐资参与修建奉祀天后父母的殿宇。嘉庆年间,连江士绅林日锋献地建庙,“于时吾连李侯遵奉宪檄,方相度庙制,适林生日锋于庙浚隙地营小轩三楹,不计已赀,慨然以献。益叹后之妙灵昭应,俾是役不劳而前定也。乃龛置栗主以妥之。”[30]民国《永定县志》记载:“天后庙,在东关大桥头左……嘉庆十三年,邑绅赖奎旺捐金建启圣祠,祀后父积庆公、母积庆夫人,今亦废。”[31]道光十一年(1831),士绅捐资购地,在福州南台上杭街的绥安会馆天后宫增祀天后先代,“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谢景行、廖柱山、献廷、姜文波、李立侯、何松亭等复捐赀购买宫后山坡,增祀后之先代,嗣复经何松亭、谢履旋、李式轩、崇德、李佑贤诸人改建梳妆楼”。[32]
在地方官员和士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奉祀天后父母的殿宇得以修建而成。道光年间,连城知县凌光斗发动士绅百姓捐资重建天后宫,增造后殿,崇祀天后父母,“福建省连城县连邑城东神殿,昔日非不壮丽,年久为风雨剥蚀,今邑人士,佥欲革故而鼎新之,更增造后殿,崇祀天后父母,于两廊则尤加厂焉。第为费不赀,非万余金难免掣肘之患。邑中士庶久托帡幪,谅无不乐意而捐输者,将见画栋雕甍,神灵妥侑,愈锡福于无疆矣。况于一邑形势风水之说,复大有所禆益乎。余忝莅兹土,均荷神麻,因敬弁数言,为阖邑捐输者劝。特授连城县知县时凌光斗撰”。[33]
多数地区通常只供奉天后父母牌位,然而在福建一些天后宫出现供奉天后三代牌位的情况。莆田文峰宫系清代福建兴化府官祭天后的庙宇。嘉庆八年(1803),兴化知府马夔陛将凤山寺北堂归入文峰宫,率领通判、知县等捐俸创建三代祠,供奉天后三代神牌,至今在庙中仍保留有相关碑记,“皇帝御极之八年,申命推崇天后圣母三代春秋致祭,崇德报功,载在秩宗,典至钜也。兴郡城中,天后特庙坐东面西,规模颇狭,向未有后殿奉祀三代神牌。每于祭告之期,暂假凤山寺禅室设位行礼,未免简亵,殊非遵旨敬神之意。夔触目有感,时形踧踖,因躬历其地周视详询,乃知天后庙宇本属寺基,即以寺之北堂归入天后庙内。夔偕丞令等捐俸创建,虔祀三代神牌,北位南向,允符体制,堂前左右龙目各二,树影掩映,幽静森严,神所凭依。至若两庙香火,应令寺僧敬谨供奉,不得间断。是役也,数旬之内,樑栋聿新,妥侑有所。三代圣主在天之灵,当亦日鉴在兹,所以寿国寿民者永永无极,而岂夔等之邀福已哉!敬志肇建之由,泐之于石,用昭盛典云。大清嘉庆八年岁在癸亥嘉平月上澣知兴化府事加三级马夔陛敬立。兴粮通判加三级李承报,莆田县知县王镐,仙游县知县林大任,兴化府经历石元钦,董事举人郑远芳、附贡郭捷南。”[34]道光《莆田县志稿》亦有相关记载:“又郡城有行祠,在善俗铺,元至正十四年僧霞谷奉府县舍地建,面对凤皇山文峰,故名文峰宫……嘉庆八年,知府马夔陛、知县王镐就庙右隙地捐俸建祠,祀天后三代神主。”[35]嘉庆二十三年(1818),署兴协副将徐庆超又捐俸对三代祠进行扩建,“国家承平百余年矣,海波不扬,边烽日靖,惟天后之功独多。嘉庆八年,奉旨特建三代祠,取人本乎祖之义也。余奉署兴协,恭谒其地,见祖庙立于西偏,规模既隘,涵道弗疏,为之怃然。考诸莆《志》,此宫系水陆院山门,元至正十四年僧霞谷合两院为寺。因奉府县舍地建天妃宫,面对凤凰山文峰,故名曰‘文峰宫’。明万历元年浙江按察副使应魁陈公重兴。乾隆二十一年太守兆麟宫公扩凤山寺地捐俸创建后殿,至三代祠则太守夔陛马公实营之也,就凤山寺报功祠改为三代祠。夫三代祠何地也?春秋致祭何典也?非拓而大之,尚望其能安侑乎?时绅士君选陈君董建凤山永福寺,余就而谋之,喜捐俸以助,而营中部伍亦有同志,于是易其基址,壮其观瞻,偏者正之,塞者通之,神所凭依,罔不崇矣。至起盖僧房,复购东边闬地一所,添造厨房,置香灯产业以垂诸久远者,陈君之经营周至,不惟余乐其事之有成已也。爰是而为之志……大清嘉庆二十三年腊月日敬立”。[36]
同治年间,福州怡山院也修建有天后三代祠。同治五年(1866),钦差翰林院检讨赵新、内阁中书于光甲出使琉球册封国王尚泰,相传在往返途中遇风均获救。于光甲捐洋银五百两,修建福州怡山院天后三代祠,此事载于清佚名《无题碣》,“新建天后三氏祠,册封琉球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宫篆光甲捐洋银五百两。时大清同治五年岁次丙寅仲夏勒石”。[37]
有的天后庙除供奉天后父母外,还陪祀天后哥哥、姐姐。光绪十八年(1892),杭州城北天后宫因坍塌进行重修时,修建后殿,除供奉天后父母外,还以天后兄姊附于左右,“光绪壬辰夏月,前殿忽颓,赤日当午,砰然一声,榱崩栋拆,独像设扁额之属,一木支之,完全如故。异矣哉!非灵爽之所凭哉!巡抚长白崧骏公议重修之,发粮库金若干,属士绅丁丙董其役。先是,旧宇凡三重,前奉天后,后一重祀文武帝,而于神父母兄姊追崇之礼缺焉。丁君于是即其右边辟地树栌,移祀文武帝,即其故址,前为拜献受福之堂,为中殿以奉圣像,为后殿,以奉积庆公、积庆公夫人,以灵应仙官、慈惠夫人附左右,越十月落成,于是述其建置更易之始末以谂来者”。[38]
三、官方春秋祭祀天后父母
嘉庆六年(1801)以来,清政府将祭祀天后父母纳入国家祀典。祭祀天后父母的礼仪与祭祀天后相似。同治《乐昌县志》称:“天后庙,每逢仲春仲秋地方官择吉致祭。后殿,咸丰二年奉文建造致祭。晋封天后父母积庆衍泽公,林夫人王氏之神,礼同正殿。”[39]各地祭祀天后父母的活动通常由地方官主持。在祭祀日期、祭品、祭文、仪注等方面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从而保证祭祀的庄重性,彰显清政府对天后父母的尊崇。
(一)祭祀日期
各地祭祀天后父母的日期通常与春秋两季祭祀天后安排在同一天。道光《晋江县志》:“同日致祭天后之父积庆公、母积庆公夫人。”[40]民国《宿松县志》:“六年,封天后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公夫人,令地方官安设神牌于后殿,每岁春秋二季有司同日致祭。”[41]民国《尤溪县志》:“积庆宫,嘉庆七年奉文建祠,祭期同祭天后日。”[42]民国《海康县续志》:“六年,准内阁建后殿,崇祀先代,春秋一体致祭。”[43]
祭祀顺序安排上,通常在祭祀天后之前,先到天后父母神位前致祭。道光《平和县志》记载:“天后庙,在县后山。每岁春秋二仲上戊日致祭。……积庆公祠,在庙之左。于庙正祭之日,先诣位致祭。”[44]道光《龙岩州志》称:“天后先代公祠,以春秋二仲祭天后日则先行礼。”[45]同治《宁洋县志》也有相同记载:“天后先代公祠,以春秋二仲祭天后日则先行礼。”[46]
(二)祭品
道光年间,官方祭祀天后父母的祭品在一些地区已形成定例。福建一些地区祭品相似,其种类和数量大致如下:1.帛一,2.白瓷爵三,3.铏一,4.簠二,5.簋二,6.笾四,7.豆四,8.羊一,9.豕一,10.酒罇一。如道光《平和县志》:“积庆公祠,在庙之左。于庙正祭之日,先诣位致祭。祭品:帛一(白色),白瓷爵三,铡一,篮二,簋二,笾、豆各四,羊一,豕一,酒樽一。”[47]道光《屏南县志》:“天后庙后殿祭品:帛一,白色。白瓷爵三、铏一、簠二、簋二、笾四、豆四、羊一、豕一、酒罇一。”[48]道光《政和县志》记载:“积庆公祠,豕一、帛一、白瓷爵三、酒罇一、簠簋各二、笾豆各四、行一跪三叩礼,余照前殿仪祭。”[49]
有的地方祭祀天后父母的祭品与祭祀天后的祭品相同。如民国《宁化县志》:“庙前殿祀天后,后殿祀积庆公、积庆公夫人,春秋祭品用帛一、爵三、铏一、簠簋各二、笾豆各四、羊豕各一,前后殿同。”[50]但是有的地方祭祀天后父母的祭品规格低于天后。咸丰《文昌县志》称:“天后官,每岁以春秋仲月上癸日有司致祭。承祭官三献俱行三跪九叩首礼。祭品:帛一、牛一、豕一、登一、铡一、笾十、豆十。后殿祭品:帛各一,笾、豆各八。”[51]
祭品陈设方式,光绪《长汀县志》有相关记载(见图1)。

图1:祭品陈设图[52]
祭祀费用在一些地区系由官方拨给。如道光《莆田县志》记载:“天后后殿,每年春秋二祭银九两。”[53]“又添给致祭湄洲天后庙后殿祭品银九两”。[54]有的地方明确规定由知县捐养廉银办理祭品。如光绪《临高县志》记载:“后殿祭品,帛各一,笾豆各八,承祭官行一跪六叩礼,余同前殿。祭品由知县捐廉备办。”[55]咸丰《文昌县志》称:“后殿祭品:帛各一,笾、豆各八。承祭官行二跪六叩首礼。余同前殿。祭品由知县捐廉备办。”[56]民国《文昌县志》:“后殿祭品,帛各一,笾豆各八,承祭官行二跪六叩首礼,余同前殿。祭品由知县捐廉备办。”[57]
(三)祭文
道光年间,福建许多地区官祭天后父母已有统一的祭文。福建许多地方志都有收录,如道光《晋江县志》、道光《平和县志》、道光《建阳县志》、道光《屏南县志》、道光《龙岩州志》、同治《宁洋县志》、光绪《长汀县志》、民国《政和县志》、民国《宁化县志》民国《尤溪县志》等。这也从侧面反映祭祀天后父母的政策在福建执行得较为彻底。
兹将道光《建阳县志》收录的“祭天后先代祠祝文”抄录如下:“维道光某年岁次某干支某月某干支朔越祭日某干支某官某,致祭于天后之父积庆公、母积庆公夫人,曰:惟公德能昌后,笃生神圣之英。泽足贻庥,宜享尊崇之报。诞祥钟乎宋代,孝行聿昭。灵迹著于海邦,安澜胥庆。是尊后殿,用答前休。兹值仲春秋,敬荐豆馨。虔申告洁,神其格歆。尚飨。”[58]
上述祭文首先赞颂天后父母德行、恩泽惠泽后代,孕育了天后,应该得到世人尊崇。其次,赞颂天后孝行彰显于天下,在海邦灵迹显著,海不扬波,突出天后孝女以及海神的特质。最后,提及尊崇天后父母于天后宫后殿,春秋祭祀。
(四)祭祀仪注
官方祭祀天后父母的仪注程序主要有:签祝文、盥洗、瘞毛血、迎神上香、初献(奠帛、献爵、读祝文)、亚献、终献(不读祝文、不献帛)、徹馔、送神、望燎等。
道光《屏南县志》对于祭祀天后父母的仪注程序有详细的记录,兹引录如下:“天后先代祠仪注:祭期五鼓,主祭官穿朝服签祝文毕,起鼓。引生引主祭官诣盥洗所盥手毕,引至行礼处立。通唱:‘执事者各执其事。主祭官、陪祭官各就位。瘗毛血。迎神。’引赞:‘上香。’引主祭官于神位前。引赞:‘跪。叩首。’捧香生跪进。主祭官受香,拱举授。接香生上炷香于炉内,又上瓣香。毕,引赞:‘叩首。兴。’复位。行二跪六叩首礼,各官俱随行礼,兴。通唱:‘奠帛。行初献礼。’引赞:‘诣积庆公、积庆公夫人神位前立。’引赞:‘跪。叩首。奠帛。’捧帛生跪进,主祭官受帛,拱举授。接帛生献。引赞:‘献爵。’执爵生跪进,主祭官受爵,拱举授。接爵生献。毕,引赞:‘诣读祝位。’主祭官诣读祝位立。读读祝生至祝案前。拜仁祝版立于案左。引赞:‘跪。’主祭官、陪祭官、读祝生俱跪。引赞:‘读祝文。’读祝生读祝毕,捧祝版仍供案上。引赞:‘行三叩首礼。’各官俱行三叩首礼。兴。复位。通唱:‘行亚献礼。’兴初献礼同。(不读祝、献帛)。复位。通唱:‘行终献礼。’与亚献礼同。复位。通唱:‘彻馔。送神。’主祭官、陪祭官俱行二跪六叩首礼。通唱:‘读祝者捧祝,执帛者捧帛,各诣燎位。’读祝生捧祝,执帛生捧帛,祝文在前,帛次之,俱送至燎位。主祭官旁立,候祝帛过,仍复位立。通唱:‘望燎。’引主祭官诣望燎位立。祝帛焚半,引赞:‘礼毕。退班。’”[59]
道光《屏南县志》祭祀天后父母的仪注记载与道光《建阳县志》中有关祭祀天后仪注记载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祭祀天后与祭祀天后父母的程序大致相同。[60]但祭祀等级上,天后父母通常要低于天后。光绪《长汀县志》记载祭祀天后父母“仪注,前殿与文昌祠同。后殿与前殿同。但迎神送神仅二跪六叩而已。”[61]光绪《临高县志》记载祭祀天后父母“承祭官行一跪六叩礼”。[62]
五、结语
通过考察清政府崇祀天后父母政策措施,可得出以下结论:
由清代官员士绅三次疏请加封天后父母可见,清代由于在对台军事斗争、册封使出使琉球、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等活动中,官绅极力宣扬天后的灵验效顺,为酬谢天后护佑,官员士绅向皇帝奏请追封天后父母。清政府出于怀柔、祈福保安目的,对天后父母进行敕封。嘉庆六年(1801),封天后父母积庆公、积庆夫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追封衍泽二字。
嘉庆六年(1801),清廷下旨要求安设天后父母神牌于天后宫后殿,但并非所有天后宫都建有后殿。许多没有后殿的天后宫并未及时增修。地方官员往往采取变通的措施开展祭祀。但没有殿宇供奉天后父母神牌毕竟不符合体制,一些地方官员发起、主持修建,得到地方士绅民众积极配合。嘉庆至光绪年间,一些地区增建了专门祭祀天后父母的祠宇。这些祠宇,或是天后宫后殿,或是修建在天后宫附近,成为天后宫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嘉庆年间起,许多地方在官方祭祀天后当日,也同时祭祀天后父母,并逐渐有了相对固定的祭祀日期、祭品、祭文、仪注,祭祀天后与祭祀天后父母的程序相近。祭祀天后父母等级低于祭祀天后。
从相关文献记载、宫庙遗存来看,修建殿宇、开展祭祀天后父母活动,在福建地区得到广泛推行。宦游全国各地的福建籍官员、福建商人参与到相关活动,反映作为妈祖文化发源地的福建,对妈祖文化的推崇。
清政府崇祀天后父母也与弘扬孝道的教化目的密切相关。嘉庆年间福建连江士绅林占芳便明确指出:“追崇天后圣母先庙为积庆公,妣为积庆夫人,诏郡邑应行秩祀处所增设神牌,祀以牢醴。非独礼告怀柔,亦义取广孝也。”[63]孝道是妈祖文化的重要元素。明代以来,天后孝女形象逐渐突显,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机上救亲”的传说故事充分体现妈祖孝道。李鼎元在奏请崇祀天后父母时,提到天后系孝女成神,通过在后殿崇祀天后父母,以表达天后孝心。祭祀天后父母的祭文中,也强调天后的孝道。
注释:
[1]黄国华:《妈祖父母与封号之史料考》,《中华妈祖》2011年第1期。
[2]卢金城:《孝悌是妈祖精神的重要内涵》,《中华妈祖》2007年第4期。
[3]姜家君:《妈祖与儒家的孝道思想》,《文学教育•中旬版》2009年第5期。
[4]潘真进:《妈祖精神之孝悌观念》,《中华妈祖》2011年第4期。
[5]李志英:《从天后宫到林孝女祠——国民政府宗教政策之灵活性探究》,《中外无神论研究》2015年第2期。
[6]《天妃显圣录•历朝褒封致祭诏诰》,南投:台湾文献委员会,1996年,第13~14页。《内阁抄录礼部尚书赖都等为天后神功显著请追封先代事题本(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湄洲妈祖文化研究中心、莆田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7][8][9](清)李鼎元著,韦建培校点:《使琉球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3页,第72页,第185页。
[10]《军机处录内阁中书李鼎元为吁请加封天后父母事奏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湄洲妈祖文化研究中心、莆田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63~166页。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2辑13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7-38页。
[12]《一六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追封省城及海盐县等处神灵折》(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6-208页。
[13](道光)《龙门县志》卷六《坛庙》,清咸丰元年刻本。
[14](同治)《浏阳县志》卷十《祀典》,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5](同治)《上海县志》卷十,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16](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十四《祠祀》,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17]《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2辑13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7~38页。
[18](咸丰)《续修噶玛兰厅志》卷三中《祀典•天后祭典》,清咸丰二年续修刻本。
[19](嘉庆)《连江县志》卷四《坛庙》,清嘉庆十年刻本。
[20](同治)《安福县志》卷十六《秩祀》,清同治八年刻本。
[21](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六《祠祀》,清光绪四年刊本。
[22](民国)《南平县志》《祠祀志》第二十,民国十年铅印本。
[23](民国)《宿松县志》卷九《民族志•典礼》,民国十年刊本。
[24](清)马夔陛:《敕封天后圣母三代历圣殿宇肇建碑记》,载蒋维锬,郑丽航:《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碑记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25](道光)《龙岩州志》卷二《规建志•坛庙》,清光绪十六年重刊本。
[26](同治)《新建县志》卷二十二《禋祀》,清同治十年刻本。
[27](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一《典祀》,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8]《增祀天后庙后殿记》,载陈邦津主编:《道教在潮阳》,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9~160页。
[29](嘉庆)《连江县志》卷四《坛庙》,清嘉庆十年刻本。
[30](民国)《永定县志》卷十四《祠祀志》,民国三十八年石印本。
[31](民国)《建宁县志》卷六《祀典》,民国八年铅印本。
[32](嘉庆)《永善县志略》卷二《重建天后宫劝捐序》,清嘉庆八年修,钞本。
[33](清)马夔陛:《敕封天后圣母三代历圣殿宇肇建碑记》,载蒋维锬,郑丽航:《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碑记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34](道光)《莆田县志稿》不分卷,稿钞本。
[35](清)徐庆超:《天后宫三代祠碑记》,载蒋维锬,郑丽航:《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碑记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267~268页。
[36]蒋维锬、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碑记卷·无题碣》,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37](清)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重修天后宫》,清光绪宜堂类编本。
[38](同治)《乐昌县志》卷五《群祀》,清同治十年刊本。
[39](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五《祀典志》,清钞本。
[40](民国)《宿松县志》卷九《民族志•典礼》,民国十年刊本。
[41](民国)《尤溪县志》卷四《祀典》,民国十六年刊本。
[42](民国)《海康县续志》卷六《坛庙•庙》,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43][46](清)黄许桂主修,(清)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道光《平和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第127页。
[44](道光)《龙岩州志》卷五《典礼志》,清光绪十六年重刊本。
[45](清)董钟骥,陈天枢纂:《宁洋县志》卷三《建置志•坛庙》(同治十三年(1874)修),《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元年刊本。
[47](道光)《屏南县志·祀典》,稿钞本。
[48](道光)《政和县志》卷五《典礼》,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49](民国)《宁化县志》卷十二《祠祀志》,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50](清)张霈纂修;颜艳红,赖青寿点校:咸丰《文昌县志(上)》卷五《经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51](光绪)《长汀县志》卷十二《祀典》,清光绪五年刊本。
[52](道光)《莆田县志稿》《祀典》,稿钞本。
[53](道光)《莆田县志稿》《田赋》,稿钞本。
[54](光绪)《临高县志》卷五《建置•祀典》,清光绪十八年刊本。
[55](清)张霈纂修;颜艳红,赖青寿点校:咸丰《文昌县志(上)》卷五《经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56](民国)《文昌县志》卷五《经政志•祀典》,民国九年刻本。
[57](道光)《建阳县志》卷七《典礼志二》,钞本。
[58](道光)《屏南县志》《祀典》,稿钞本。
[59](道光)《建阳县志》卷七《典礼志》,钞本。
[60](光绪)《长汀县志》卷十二《祀典》,清光绪五年刊本。
[61](清)聂缉庆、(清)张廷主修,(清)桂文炽、(清)汪瑔纂修:光绪《临高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36~137页。
[62](嘉庆)《连江县志》卷四《坛庙》,清嘉庆十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