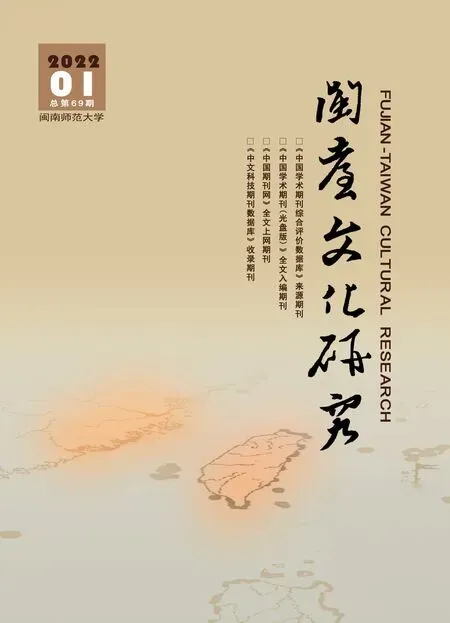解读黄锦树《雨》中雨意象的多重可能
郝海林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 100083)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黄锦树创作颇丰。他从早期的创作开始就在实践着自身的美学追求,作品霸气尖锐、怪异多端、戏谑荒诞,并以重构的姿态介入历史,嬉笑怒骂,冲击了马华文学的传统写实格局和美学规范,被王德威评为“坏孩子”。[1]《雨》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他再一次突破原有创作模式的又一力作。作家以灼热滂沱的南洋雨幕为故事背景,描写了胶林中四口之家的生死悲欢。他将相同的故事元素运用在各篇之中,宛若平行时空般展开变形,使得看似无关的篇章之间产生了幽微的关联。《雨》是黄锦树在大陆的被引进的第二部作品,也正是由此,他才渐渐进入到更多大陆读者的视野。这部作品之所以能让人如此沉浸,进而获得强烈的阅读快感,想必离不开小说中雨意象所建构的湿淋淋的、充满恐惧与梦魇的南洋世界。故事中雨意象的纳入,不仅使极具特色的地域风情得以陌生化呈现,更寄托着作家对个人身份、历史、生命深沉的关怀及文化承担。
从《雨》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华人承受的历史暴力和殖民创伤,父的失踪—寻找模式引发的身份认同、文化寻根问题,叙事美学上的先锋实验性等方面,都延续了传统对于黄锦树作品的论述。当然,其中也不乏谈及小说中的热带环境及雨水意象,但并未单就其展开细致全面的论述。结合文本细读,笔者发现,对于小说中雨意象的整体研究,尚有深入空间。因此,论文将以之为切入口,以自然与文学的双重视点对雨进行关照,深入作品细部,进一步探究其在小说中延伸出的多重“物质想象”[2]的可能,发掘其在整部作品中的意义与价值。
一、重返生命经验的通道
不了解黄锦树及其写作背景的读者,在最初进入《雨》这部作品时,最直接的阅读印象当为故事里处处落下的雨,以及由之产生的潮湿凝腻、梦幻压抑的感官冲击。黄锦树的写作生涯始于远离故乡到台湾求学之后,客居异乡,他却始终将远距离回望的目光投注于那片灼热的胶林故土。尤其在《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胶林中一家四口的基本元素展开故事变形,以唤醒个人童年至青少年时期的生命经验为创作支撑,在纸间建构起一个悲苦温情都历历真切的世界。雨意象作为整部作品变奏中一个不变的关键,不确定的故事氛围中的确定,似乎是作家有意为之。他借助雨意象集主客观为一体的特性,既搭建出独具南洋特色的地域风貌,构成小说的故事背景,又在主观层面上将个人沉重的乡愁负载其上。
黄锦树笔下的故事大都发生在雨天的胶林深处,然而这里的雨早已不同于下在传统文学中、充满诗情画意的绵绵细雨,而是呈现出南洋雨林特有的汹涌倾泻、连绵不绝的特征。在雨中流出白色巨网般胶汁的橡胶林、红毛丹,盘根错节的巨大古树,食人的老虎、白蚁……共同构成了绮丽磅礴的南洋风情。《雨》一号作品开篇便是一场突如其来、持续几天的暴雨:
好似一口瀑布直接泻在屋顶上……雨声充塞于天地之间。雨下满了整个夜。无边无际,也仿佛无始无终的……
打开大门,劲风带来雨珠飞溅。屋檐下奔泻着一长帘白晃晃的檐溜,远近树林里更是一片白茫茫的水世界,水直接从天上汩汩地灌下来,密密的雨塞满了树与树间的所有空隙。[3]
“南方以南”的热带文字给异域读者带来了陌生而神秘的环境体验,然而这确是下南洋的华人最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从感官层面回到物质本身看暴雨场景,其首先是形象可见之物。在这里,暴雨以其奔腾的气势在视觉上建构起一个封闭、原始、蛮荒、神秘的特定空间样态,将胶林中的一家孤立开来。一旦下雨,人物就会陷入一种被围困、等待和百无聊赖的生命状态之中。父亲不得已冒着生命危险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时,仿佛才是他们与外界接通的时刻。在偌大的外部世界和处处都显示出一种蛮性、肆意的热带环境的衬托下,胶林空间中一家四口的无助、人类力量的渺小,都极其鲜明地对照呈现。其次,雨的声音可听,更何况是这样磅礴的热带暴雨,“整个世界都陷落在雨声里了”,[4]雨声吞没其他声音,在听觉上也成为作家自身生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他在多年后仍对那雨声描摹得如此震撼。另外,雨还是全身性感知之物,潮湿凝腻,在感觉上对人形成一种包覆。由此,雨的场景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多维度的、立体的、闭合的存在。
黄锦树曾说:“亚热带的雨和热带的雨倒是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季风带之下。多年前离乡后开始写作,小说中即经常下着雨……参照的还是我童年迄青少年间的胶林生活经验。《雨》诸篇,是多年以后重返那背景的一个变奏尝试。”[5]以上在对雨场景极具感官冲击力的建构上,显见作家与叙述者合二为一,在窗外台湾的雨中书写着马来西亚的雨,回溯过往的生命经验。雨从多角度唤醒了沉睡在作家生命中的记忆点,成为其重返那一经验场景的通道。
南洋之雨不仅从客观上建构出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刻有作家生命印记的华人生存空间,同时在主观上也承载着作家沉重的乡愁。这也成为其写作这一系列故事最基本的欲望与冲动。首先,《雨天》以诗的形式被置于整部作品之首,且以雨意象为题,雨在这里即基调性地产生了这样几方面作用:从其物质特性出发,雨即为故事刷上了一层抒情色彩,使得作家回望故土的目光有处安放。它如一条线索,编织起后面故事的各要素,于无形中显出悲伤沉郁,使得各篇章整体氛围和谐,故事间暗合一种默契的韵律。其次,雨意象作为作家重返过去时空的一种媒介,带有回忆的性质,雨因而成为一个创作的触发点和契机。作家以一组关于雨的意象,牵动出潜藏于心的乡愁:“久旱之后的雨天”“湿衣”,墙面渗出的“水珠”“水泥地板返潮”[6],并借此在想象中重构过去。由眼前的景象,生发出对亡父和胶林旧家旧事的点滴回忆:“父亲常用的梯子”的细节,他的“橡胶鞋”和“他脚底顽强的老茧”,[7]“抒情的悲伤”[8]自此蔓延开来。
与开篇《雨天》中的乡愁相呼应的,《南方小镇》被作为整部书的结尾篇章,似乎也是作家有意安排。这篇小说共分为四部分——《归土》《南洋》《侨乡》《故乡》,四节标题在时间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环。读者跟随着叙述者行走的路线,重新走访这些极具象征意味的地点,三代华人移民走过的历史以及故乡、侨乡、原乡的三乡对照,在此间徐徐展开。第一部分《归土》,以母亲下葬的场景与阿嬷和中国亲人通信的回忆,折射出移民大历史中的一个微小缩影。叙述者从更关切自身的角度切入,探讨关于原乡、遗忘、生死、漂泊等围绕着海外华人移民的永恒命题。随后走访历史博物馆、遗迹、华人坟场,融入了代际更迭及历史变迁,乡愁所包含的群体也在逐渐扩展。在这里,雨不再作为一种展现南洋地域特色的,具象的物质存在,大篇幅地占据小说容量,而是在结尾被适宜地引入:“睡眠的深处有雨声。好像下了一夜的雨。但也许雨只下在梦里,在南方的树林深处,下在梦的最深处,那里有蛙鸣,有花香。”[9]在这里,雨所承载的乡愁已不仅仅关切个人,而是在自身身上套叠了历史与多人的命运,他们的乡愁。故事虽不尽相同,然而在本质上却凝结为一个共同体的集体乡愁——由父母亲族感性层面的情感牵动,到对华人移民整体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随着作家关注的命题逐渐走向深远与阔大,其伤怀与悲悯也就跃然可见了。
二、时间的功能和意蕴
黄锦树以雨意象重构奇异陌生的南洋故土,在重返的记忆中执着地书写灼热滂沱的南方经验,以寄托深沉哀悼的乡愁。除此之外,雨以其多变的形态,与时间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层面上,它不仅既发挥着叙述上的功能性作用,亦有自身的隐含意义。
首先,在叙事层面上,雨意象成为一种弥合现实与梦境的创作手段,是打破作品真与幻之间时间界限的关键。《雨》极具风格性地展现了作家黄锦树对梦书写的执着。作品中人物的记忆时常是破碎的、跳跃的、断续的,幻象与真实错位、重叠,使故事整体呈现出如幻梦般迷离的审美效果。梦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桥梁,我们进入梦境时常会发现,一切现实都变作符号被打乱。或在不同的场景中出现相同的人物,或与相同的人物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中,时空误入,物换星移。这也是黄锦树精简人物结构,却能在时间上做分岔、裂变、跳跃、增殖的一个关键。作品一号《老虎,老虎》,开篇即是雨天场景,“辛梦到他在大雨声中醒来”,[10]家人都消失了,他突然看到老虎从门外一闪而过。而等他在雨中梦醒,现实中也是大雨滂沱,雨引来了老虎,辛向老虎跑去。作品七号《另一边》:“雨骤然落下,屋顶仿佛重重一沉,地面似乎也在下沉。也许客人被雨留下来了。持续传入耳朵的声音刺激着梦,扰动它的声色、它的形状”。[11]而在梦醒之后,“门大开,那雨大得稠密得像堵水墙,逼人的寒意渗了进来”“也许是梦”。[12]雨意象在这里作为一种“模糊”的媒介,是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常用的一种错乱时间线的叙事技巧。同样的潮湿混淆了梦与现实同个场景的边界,使得梦在这里具有某种预示性,笔法魔幻。在真幻二者的转换中,营造出一种迷宫般的时空错乱感,使人无法脱身。这样,就为小说故事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与作品本身在时间上变形、分叉的形式内核相契合.整部小说因而陷入湿淋淋的梦魇,充斥着恐惧、不安和迷离。
另外,在叙事上,雨意象有时也会代替时间发挥作用。作品二号《树顶》,不再以描摹狂暴的雨水开篇。“雨停了。但父亲没有回来。那天冒着雨划船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许多天过去了,水也退得蛮远了,但父亲就是没回来”,[13]以雨的停顿作为开头,形成叙事上的悬念。短短两行,即交代了父亲在雨天出走至今未归的完整情节。雨成了时间线的划分,雨停了——雨正在下着——水退了,分别对应三个时间段,现在——过去——未来,父亲都没有回来。叙述者站在现在,讲述过去,又从过去,跳跃到将来,三个时间点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圈。同时,叙述者有意将“雨停了”从时间点的中间突出到开头,打破读者期待的时间顺序,营造出一种转折和突兀的停顿感。以这样的顺序反复强调父亲的失踪,也就更加突出地表达了等待的焦急、恐惧以致失望。
除了功能意义上雨和时间的联系,在象征意义上,同样如此。雨是水的形态,“它不仅会流逝,还会回卷”[14],如同时间。不同于传统文学作品中润物无声的细雨,热带之雨在故事中呈现出滂沱凶猛、腐蚀一切的气势。雨水的倾泻覆盖、冲刷一切,雨水的流逝带走、磨平一切痕迹,和时间流逝的内核相互呼应。在对马来西亚华人惨痛历史的书写中,作家有意借用此意象的物质特性来隐喻时间,昭示着在历史变迁中,惨痛过往终将被忘却的哀矜和沉重。这种创伤性书写在黄锦树的作品中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主题,也可见出作家对遗忘偏执而悲哀的抵抗。随着时代变迁,故乡连绵的橡胶林翻种成油棕,生活景观也不复往日,将他关于割胶的记忆完全颠覆,《雨》因而成为黄锦树的伤逝悼念之作。
在作品四号《拿督公》中,作家以直露、暴力的笔墨,大篇幅地描写了日军屠杀华人的惨状。然而在这种残酷中,却又哀沉地表达了一种时间流逝、历史终将被遗忘的思想。作家有意将雨意象置于文末,“雨后,大地处处重新长起了杂草”,[15]雨因而带有强烈的时间象征意味。在热带的大地上,腐烂消逝与重生的时间迅速到几乎可以重叠,同时进行。热带的雨孕育出了新的杂草,覆盖旧的一切,也意味着时间过后的遗忘。同样的主题在在最终篇《南方小镇》中表达得更为哀沉。在第四部分《故乡》中,叙述者和一位老人一起去密林深处,寻找即将被铲除的坟场。实际上,这个场景很好地提供了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重叠于一时的刻度。在这样的场景中,他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历史代际的变迁以及遗忘的迅速。叙述者寻找坟场的路程,即是顺着历史的脉络寻根,寻找新一代华人身份归属的过程,也是对遗忘的一种抵抗。华人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历史遗留的伤害一直存在着,然而途中所见的遗忘的必然性,使得这种对抗呈现出悲剧性的意味。
华人都是这样的,不断向前看,把过去忘掉……[16]
然后好大粒的雨滴就哗地突然从树叶上这里那里滚落下来,四野迷茫,一会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好像从雨水与泥土的撞击里,水花在你耳畔溅出一些字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17]
这里雨意象出现的时机是很恰当的,雨水的流逝与时间的流逝一样,都是无法阻挡、无法掌控的。最终只得借一句动乱相思中自我的叮咛与慰藉,收束狂暴冲刷中的大雨。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体,却反而更添无端悲感,独留时间流逝、历史遗忘和离乱追思的哀叹,余音不绝。
除上述时间隐喻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两处将雨意象与“细沙”和“沙漏”相关联的情景,而这二者在一般意义上都是被用作计量时间的工具。《后死》故事整体本身就是一个对时间的巨大隐喻,抽空了当下的存在,设置了一个过去和未来重叠的场景。故事结尾出现了一个玻璃瓶,它分隔了梦与现实、前世和今生,里面装着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自己,仿佛水中倒影一般互相观望。在这个情节的前后都出现了雨意象,雨使生命中的某些早已流逝的时刻得以重现。作品五号《龙舟》,是微缩版的家族叙事,以成年之后辛返乡的视角,揭开家族的秘密。在这个故事中,时间的重叠构成了一种神秘的家族命运循环。因为深爱着早夭的大舅,母亲生下了他,同样取名为“辛”,在生命的开始和姓名的安排上,都被刻意用来重复另一个人。“想到母亲而今的年龄恰是外婆猝死之龄,自己的年岁是大舅意外死亡时外公的年岁”,当辛开始意识到这种“一身而为多人”的家族乱伦和命运循环的时间感时,雨意象又适时地出现了。“感觉外头突然变天了,细细的雨洒了下来。像沙,像米,那样一把一把地被风的手抛下。远方轰隆轰隆的,像是浪,从更远的世界的尽头推了过来”。[18]这里,雨意象化身为不断流泻的沙粒,传达出一种被时间的巨手掌控命运的无力感和荒芜感。
三、生死隐喻
在文学和审美尚未自觉的时代,雨最初是作为农业生产中的必要条件受到重视的。水乃生命之源,它滋养万物至生生不息。正是基于此,先民对雨的神力充满敬畏和崇拜,并歌颂其内含的母性色彩及孕育的生命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狂暴的雨水同时对生命具有无法掌控的威胁与伤害,因此多以“淫”形容此种连绵不绝的形态,进而引申为绵绵无绝的惆怅和苦难的境遇。黄锦树巧妙地将生死这一重要命题隐喻于雨意象之中,使其具有更多重的阐释空间。
雨水在黄锦树的笔下是沉重的、神秘的。雨具有水的形态,因而其强大的震慑力和破坏力,其极具淹没性的物质力量,始终使故事笼罩着苦难和死亡的阴影。《树顶》中连降七天大雨,父亲因雨中的呼救声划船出去,此后杳无踪迹。作家着重以辛童真的视角,去观察雨水对死亡的威胁,突出渲染了一种恐惧不安的心理状态。雨水在这里不但是生命失踪的缘由,也成为了寻找和拯救的阻碍。在作品一号《老虎,老虎》中,亦下了一场旷世大雨。雨势之大,一方面导致生活环境更加险恶:“树林里都是土黄色的水,附近的园子都淹了”[19],进而对人物造成生存压力。赖以生存的橡胶无法割,就意味着生活来源被雨水彻底切断。另一方面,暴雨甚至对动物以及人的生命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雨使野猪来到木薯田中找食物,母老虎带着两只小虎也因觅食而出现。这里,雨不再仅仅作为背景、基调、氛围和媒介存在于故事中,也不仅仅是激发作家创作、重返过去生命经验的前提。就故事本身来说,它成了一个关键的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场雨的围困,孩童辛和父母就不会百无聊赖地于家等待,也不会有因食物匮乏来觅食的老虎和山猪,更不会有“也许为了躲雨”朝房子跑来的小虎,直接导致辛的死亡。雨成为了故事发生的前提,也一步步地推动故事进程,甚至最终促成了关键性的情节突转。这篇小说黄锦树是要写出一种死亡的偶然和生命的的不确定性,而雨意象恰成为了这一主题的隐喻。
同时,文学意象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着。它们或由于共同的寄托,或由于相似的形态,被统一于同一意象群之中,达到意义的延伸、融合。从广义上来说,雨是统摄于水意象之下的。它不仅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同时更可以生发出汗水、泪水等多种形态。巴什拉将水视为世界的器官之一,认为水“是泪的躯体”,[20]由此也暗合了雨水自身所蕴含的悲凉、忧伤的抒情特质。生命离不开水,但长久、长期、大量的雨使故事呈现出一种沉没、溺亡的状态。水的沉重、幽深、幻美所激发的想象,使得水与死亡的结合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沉重的眼泪和汗水是生命的苦难,黄锦树在《雨》中,怀着如同诗人般的敏感的心,将这种敏锐的痛苦混同在浪漫、神秘的雨幕组建的画面中,为故事刷上一层迷离的梦幻和抒情的悲伤。在《水窟边》中,昨夜一场大雨过后,辛溺死在父亲亲手挖的井里,“他的泪水像滂沱大雨那样落在儿子的尸体上……然后大雨又来了。日本人也来了”,[21]预示着恐慌、灾难和死亡的来临;在《拿督公》里呈现的父母梦境中,“观音好像在流泪,水一直往下滴”,[22]面对死亡的威胁,连神都变得无能为力,神性同时被苦难和死亡的深重消解。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南洋雨林原始蛮荒的氛围中,一代代割胶人的生命力又是顽强而野蛮的。雨水哺育了橡胶林,雨中如白色巨网般流下的胶汁,也如乳汁般养育着割胶人。在雨天,在调动全部感官的潮湿、封闭的状态中,他们为生存艰难挣扎的汗水和泪水与雨水是混同的,是分辨不清的。生存的困境、劳作的辛酸悲苦、灾难的不期而至,被遮蔽在大雨滂沱之中。雨这个意象把它们都模糊了,从审美角度来说,它将幸福、悲苦的边界都消弭了。他们执着地相信着重生,反而呈现出一种生命的蛮力和美学上的力量。
雨水不断使物质诞生和成长的持续性,象征着生命的代代繁衍。小说中关于性场景的书写总是发生在雨天。割胶人被困家中,欲望和人类的生殖本能成为单调生命的一味调剂。作品六号《沙》是描写这一场景的典型文本:阿土的两个孩子和妻子都相继去世,在和邻居阿根嫂发生关系的整个过程中,雨意象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因素。首先雨为两位赋闲在家的割胶人提供了一个相处一室的契机。随着情节的发展,两人一起收拾房间,“雨大,反正没事,点个灯,让我帮你把屋里打扫打扫吧”。[23]作家细节性地描写了这个过程,历经至亲死亡的二人,在瓢泼大雨中,就像在重建一个家园,因而多了一丝相依为命的意味。外面的灾难与家中的温馨产生强烈对比,阿土同时在这份温馨中想起了逝去的妻子和孩子,进而促发了性与生的渴望,产生了生殖冲动。“看来是很能生小孩的。这么大的雨,大声叫喊也没人听见的”,性欲望得到释放之后,阿土变得“悠哉”,与之前悲惨而枯竭的面貌相比,生命焕发出了活力和温暖。[24]雨在故事中作为一个关键的推进,成为生命的拯救,使其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有延续下去的可能。
雨水在南洋雨林的故事中流逝回还、生生不息,为由生到死再重生的生命轮回模式提供了依托。“水在死亡中是一种被接受的本原”,[25]但同时,水的不朽和绵延以及母性的力量使得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民族都选择以水葬的方式延续对死者的想象性寄托,将其重新交还给源头以求再生。在古希腊神话中的卡翁便是在冥河上渡亡灵去冥府的神,在后来的海洋小说、神话和民间传说中,这种亡灵乘舟渡河的模式也依旧延续下来。“水成为生与死之间的一种柔顺的中介”,[26]由此,故事在大雨中展开各种生死变形。
朱天文以黄锦树的句子“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水獭也许会再度化身为鲸”,[27]来解读《雨》中元素的变形、堆叠、消解,这也是作家结构故事的独特方式。《雨》是短篇小说集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却以相同的元素彼此联系,带有将长篇有意打散的实验性。《雨》作品1-8 号,基本结构皆为四口之家:儿子辛、父亲阿土、母亲阿土嫂、女儿小叶。每一篇总有家庭成员的死亡或失踪,但在下一个故事中又重新出现。黄锦树不着意为人物画像,所有形象在故事中都是面目模糊的象征性存在,人人皆有前世今生,人人皆是隐喻。在释放性冲动时,阿土梦中的潜意识是:“把他们三个都生回来吧,连同可怜的妻”;[28]《龙舟》中提到,母亲深爱着死去的大舅,“所以生下他”,并给他的名字也取作“辛”;[29]《拿督公》中,描绘日军残忍屠杀之后,一句“雨后,大地处处重新长起了杂草”[30]昭示着生命在死亡的残酷中野蛮重生。正如王德威所说:“悼亡的悲怆成了诱惑,与性的亢奋合为一种强大的原欲驱力”,[31]生死轮回,总想要把失踪的、死亡的再生回来。这种轮回的生命状态在磅礴大雨的背景下似乎也有了可信的依据,带有魔幻色彩的生命形态既在不断消解之中,又永远有重生的可能。
正如学者所说,黄锦树是以有限的元素来“孵化他的马华文学的没有”。[32]失踪和死亡,归来和重生,在有无之间他不断地自我解构再重建,无限增殖。于是,在叙事结构的变形之中,作家亦叠加了生命形态的变形,就如《另一边》中,妹妹和辛在大雨淹没家后乘舟逃亡,却因龙舟被侵蚀的孔洞而最终步向死亡。诺亚方舟的故事模式,结局却导向了迥然不同的两极,雨中之舟不再是生命的拯救。面对溺亡,作家多次提到人可幻化为鱼,向着古老的人类祖先归返,雨水为覆灭的生命提供了重生的可能。
四、结语
远离故土的三十年,黄锦树始终对其进行着远距离的回望与审视,将心中早已不复存在的故乡纳入写作之中。他敏锐地捕捉热带典型景观,以丰沛连绵的雨水为主要意象,唤起童年至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创伤经验,并借此探讨时间流逝、历史终将被遗忘的命题。同时,他又将掌控生死的强大力量隐喻于神秘磅礴的雨意象之中,以此寄托真诚的怀念与哀悼。
黄锦树是有着近似于中国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的。在他的作品中,政治与历史的元素总是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说是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即便是在《雨》这样一部以传统抒情意象贯穿的作品之中,对历史的探讨和对华人生命的关怀,依然暗藏在家族叙事之中,只是呈现的面貌获得了诗意的超越。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建立,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焦虑深深影响了黄锦树的创作,他深知作为中国和马来西亚正统文学中的外来者,遭受双重边缘化的马华文学正处于消失的险境,在历史的断裂中求生存毕竟艰难,内外交困。因而,黄锦树在《雨》中延续了他的文化承担,通过一种典型意象,回望过去,也探寻着文学和文化的出路。如同未竟之雨,总是蕴含多重可能。
注释:
[1][31]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第342页。
[2][20][25][26](法)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第20页,第137页,第22页。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1][22][23][24][27][28][29][30][32]黄锦树:《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65 页,第86 页,第260 页,第17 页,第18 页,第11 页,第246 页,第66 页,第159 页,第160页,第76页,第28页,第109页,第250页,第264 页,第141页,第74页,第95~97页,第99页,第148页,第150页,第5页,第151页,第134页,第109页,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