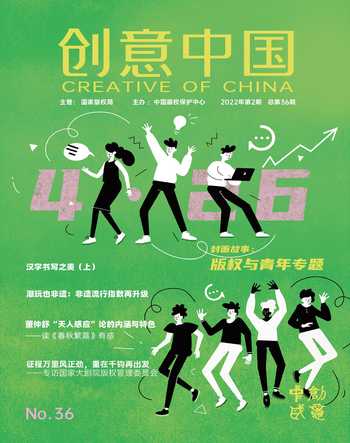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内涵与特色
李承贵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算不算经典不得而知,但如果承认“感应”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将《春秋繁露》视为“经典”也未尝不可。的确,翻开《春秋繁露》,吸引眼球的便是“副类”“副数”等概念,因而我无法不好奇《春秋繁露》中“天人感应”的表现。由于“天人感应”观念在先秦文献中也能偶尔相遇,因而我们赏析董仲舒“天人感应”观念时,会不由自主地拿先秦做比较。不比则已,一比惊人!因为这种对比在我脑海里刻下了两个深刻印象。第一个深刻印象是“焕然一新”。为什么是“焕然一新”?我想大概由于这三个方面表现:
一是系统化。没有疑问,在先秦的几乎所有文献中都能欣赏到“天人感应”现象的描述或记载,比如,《尚书》说:“肃,时寒若。”(《尚书·洪范》)君主施政态度与天气变化存在感应关系;《周易》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彖传》)天地之间存在感应关系,圣人之心与普通人之心也存在感应关系;《礼记》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礼记·乐记》)乐产生于人心与物之间的感应关系;荀子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荀子·乐论》)奸声与逆气、正声与顺气之间存在感应关系。不过,“天人感应”现象或观念在先秦只是或此或彼地零星出现,毫无系统性,更没有为“天人感应”找一个“说法”,使之看上去无懈可击而可信。但在《春秋繁露》中却是另一番景象。董仲舒对“天人感应”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证。董仲舒说:“美事招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以下只注篇名)这是“以类相招”。董仲舒说:“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人副天数》)这是“人副天数”。董仲舒说:“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同类相动》)天之阴雨与人欲睡卧,这是“阴阳相索”。但不管是“类相招”“副天数”,还是“阴阳相索”,董仲舒都将其归为“类”:“天道各以其类动。”(《三代改制质文》)董仲舒的这种略显武断的归纳,不仅将以前出现过的“天人感应”现象统统收罗其中,而且在理论上进行了细致且严密的论证。在这种旁征博引的论证中,有清晰的目的,即以维护统治秩序为目的、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的;有基本的方法,即以类感应、数感应、气感应等为方法;有丰富而特定的内容,即政治、经济、伦理、人性、生活、生死等皆被纳入感应论框架中;从而构造成以天人关系为主轴,以感应为纽带,以阴阳五行等为材料,以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为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的神学目的论体系。
二是普遍化。在先秦,“天人感应”现象和观念虽然亦被“偶遇”,但这种“偶遇”不会让人有触目即是的感觉,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在《春秋繁露》中,无事不感应,无时不感应,无物不感应,无人不感应,“天人感应”现象和观念扑面而来。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物质领域到精神空间,从政治治理到经济建设,从朝代更替到社会改革,“天人感应”穿梭其中。就制度言,新王改制、百官选拔、官衔秩序、礼仪法律、婚嫁殡葬等;就日常生活言,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臣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男女关系、老少关系、亲疏关系等;就精神情感言,好恶、喜怒、哀乐、爱恨、荣辱等;就人之情性言,智愚、善恶、贵贱、尊卑、美丑、正邪、清廉贪腐、君子小人等;就自然现象言,地震、洪水、火灾、干旱、山体滑坡、疾病传染等所有自然灾害。诸如此类,无不在以各种方式表演着自己的“感应”。诚如董仲舒所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人副天数》)由此,《春秋繁露》中的“天人感应”呈现了一个全新而重大的变化,就是日常化、通俗化、普及化。“天人感应”成为叙事的基本模式,成为表达的习惯手段,成为解释的重要方法。物质领域、人文世界、精神空间等所有的事象无不因为“感应”而彼此关联着、彼此惦记着,“感应”犹如天罗地网,无孔不入,没有一种事象可以遗漏,董仲舒说:“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楚庄王》)
三是政治化。先秦时期,“天人感应”观念虽然与政治偶有“暧昧”,时不时地被用来影射政治作为,亦不乏警告意义,但主要用来表达人们对天人间神秘关系的好奇,表达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自然解释,并无明确的服务政治的意图,也没有政治化,更没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反而时常遭受质疑,如子产对“六鹢退飞”的质疑。然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则是自觉地建构一种以长治久安为目标的治政模式。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体系中,政治权力的获得、政治权力的运行、政治秩序的规划、政治得失的评估等,都被置于“天人感应”论体系中,从而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治政模式。何以如此判断?董仲舒认为,帝王的权力来自“天”,帝王只是奉“天”行事,帝王至高无上,所有人必须服务于帝王,因为帝王是“天之子”,董仲舒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为天子。” (《三代改制质文》) 所以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而这正是《春秋》之法:“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那么,拥有权力的帝王如何治理国家?董仲舒说:“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天地之行》)这种以“一”为核心、以“多”为辅助的刚柔并用的治国方式完全仿效于“天”。而对各级官员的考核,董仲舒的方案是:“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四时之副》)这就是说,考核官员依照春夏秋冬四时运行规律即可,当发即发,当处即处,当出即出,顺序而为,因此,对官员的“庆赏罚刑”,不过是“取象于天”。而官职的分工和秩序无不与金木水火土“五行”运行模式对应,董仲舒说:“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五行之义》)此非以“天人感应”为摹本、为依据吗?因而不能不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隐含了极大“野心”的,它从来就没有满足于“为政治服务”,而是已经处心积虑地筹谋了一种特殊的治政模式,并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的“智慧”融入其中,这种模式就叫“天人感应”治政模式,所谓“王道三纲,可求于天”。
那么,第二个深刻印象是什么?“神秘莫测”。如果说“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化、普遍化、政治化等特点皆属于“可感”范围,那么另一些特点则是“不可感”的,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分析方能把握,表现为“神秘莫测”性。似乎也有三个理由可与读者分享:
一是“天人感应”中的“权”。“权”即灵活性。董仲舒虽然对“天人感应”定了个基本规则,那就是“同类感应”。但实际上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则。比如,“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王道通三》)这里的“时则岁美”与“义则世治”“不时岁恶”与“不义则世乱”,完全是“异类”,董仲舒却将这两个有理却“异类”事象通过“感应”连接在一起,以验证他想表达的结论。再如,“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同类相动》)这是说天地阳气与人之阳气感应、天地阴气与人之阴气感应,从而推论求雨可通过“动阴起阴”、止雨可以通过“动阳起阳”达到目的,但事实是,“动阴起阴”并不能实现求雨的心愿,而“动阳起阳”也无法阻止雨水的脚步,也就是没有出现董仲舒所希望的“感应”结果。因此,为了解释、圆融自己想要的结论,董仲舒必须在“天人感应”刚性结论中预备柔性条款,从而自觉地将感应条件放宽,他说:“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实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人副天数》)由于单纯的“类感”可能导致董仲舒陷入困境,因而他机智地、慷慨地对自己提出的“原则”进行调整,不能“副数”则“副类”,不能“副类”则“副数”,既不“副数”亦不“副类”者,则退而求其次,副其他亦未尝不可,无论如何,以满足其解释为至上目标。董仲舒甚至认为,“天人感应”之所以必须有“权”,乃是“天人感应”论内在精神使然,他说:“是故推天地之精,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不肖,在善恶。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阳尊阴卑》)看明白了吧?“权”原本就内在于“天人感应”论中,所以对“感应”中的“权法”无需大惊小怪。这就是所谓“先经而后权”。
二是“天人感应”中的“一”。“一”即一元性。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中 ,所有“感应”都是“二”,所谓“同类感应”。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基义》)这就是说,无物不感应,但相感者是“二”,上下感应,左右感应,前后感应,表里感应,美恶感应,顺逆感应,喜怒感应,寒暑感应,昼夜感应,阴阳感应,夫妻感应,父子感应,君臣感应,四时与四肢感应,等等。既然感应的前提是“类”,“类”用于指称性质或特征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因而感应的“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等性,阴气阳气、此牛彼牛、此人彼人、此男彼女,等等。它们并不先验地存在先后、主次、贵贱之等级关系。但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中,感应“二者”既非对等的,更非平等的,而是有着鲜明森严的主次、贵贱、主辅秩序的,如阴从阳、地从天、女从男、妻从夫、臣从君等,诚如董仲舒所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阴犹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于阳。……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阳尊阴卑》)可见,董仲舒“天人感应”中的“二”必须以“一”为中心,无条件地服从“一”,而这个“一”就是“阳”。因此,董仲舒专门设《天道无二》一章,核心旨趣就是强调“贱二而贵一”“右阳而不右阴”,董仲舒说:“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无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诗云:‘上帝临汝,无二尔心。知天道者之言也!”(《天道无二》)说的清楚明白,“天人感应”之所以必须“贵一”“右阳”,就在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信奉“常一而不灭”理念,就在于合乎“天道”。这就是所谓“贵阳而贱阴”。
三是“天人感应”中的“仁”。“仁”即柔和性。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警醒、威慑帝王,但这种警告蕴含了智慧和慈悲,即要求帝王必须以仁德治国,不能以恶德治国,否则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必遭到“天”的惩罚。董仲舒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智》)这是提醒帝王,自然界较少发生而毫无规律的现象叫做“异”,而“小异”叫灾,一般情况下,如果国家没有治理好,民不聊生,必有“小异”先至以谴告;如果不知悔改,“异”便接踵而至。无疑,通过“灾异”逐次升级的方式对帝王进行谴告,实际上就是给帝王改过自新的机会。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必仁且智》)就是说,在谴告阶段,“天”不会立即轻易地惩罚帝王,而是先给帝王以警告,如果警告后仍不悔改,则施“殃咎”以惩罚,此即“天”仁心之表现。可见,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自觉地融入了儒家“胜残去杀”理念,积极倡导仁治德政,推行礼乐教化。董仲舒说:“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只要帝王依照“天”的教导,颁布新政,任人唯贤,施爱众生,不因喜怒行赏罚,便能获得“天”的支持和庇护。由此不难体味到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中散发出的“柔和”气息,使教化成为治政的主旋律。董仲舒说:“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如果有人为恶,“天”必有所反应,但这种反应并非立即实施严厉惩罚,而是策略的、渐进的、柔和的、慈悲的,尽最大努力从“心”上解决问题,这就是孔子治政理念的再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所倡导、所追求的是儒家的教化观念,而非法家的暴政策略。总之,对董仲舒而言,“天人感应”虽然好灾异之言,但并不意味着以急惩、严惩为事,而是自觉地、巧妙地设置了一个缓冲区,以践行儒家教化理念和仁爱情怀。这就是所谓“天意之仁也”。
至此,读者是否体验到了“天人感应”的神奇所在呢?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还只是本真袒露,那么在《春秋繁露》中便已成精致妆容;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还只是星斗寥落,那么在《春秋繁露》中便是繁星满天;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还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异象,那么在《春秋繁露》中便已成政治生活中的图腾。而在“天人感应”的实际运行中,既有对规则的持守,亦提倡随机应变;既要求两两相感,更主张一阳至上;既推崇德刑并致,又奉行仁教优先。这些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所展示的神奇。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