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的兴趣与汉初学术界动向(一)
马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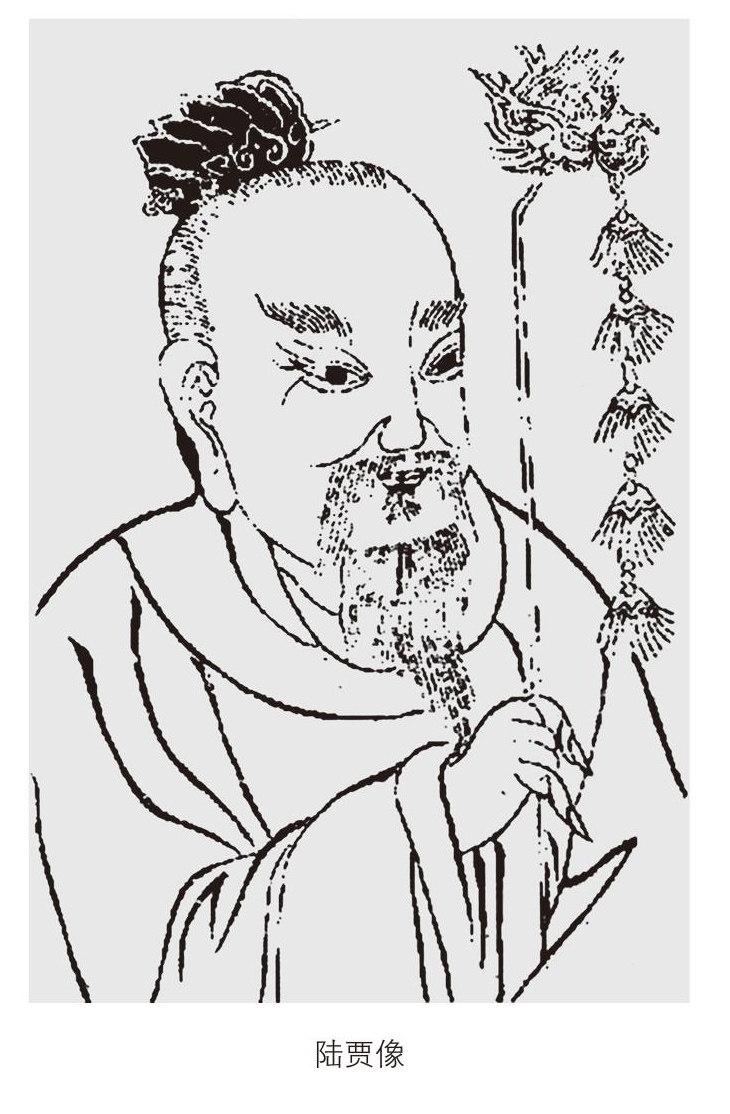
公元前206年十月,沛公刘邦率军至霸上,秦王子婴自知无法抵抗,遂率部投降。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秦帝国—仅仅存在十五年,便已成为历史陈迹。
秦亡之后,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展开了激烈争夺,至公元前202年十月,经垓下一战,项羽自刎乌江,刘邦独得天下。两个月后,刘邦应诸侯王、诸功臣之请即皇帝位。这样,汉朝正式建立。
汉朝的建立,得之于许多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刘邦的胜利带有一种侥幸的意味。因此,得天下之后如何治天下,以刘邦为核心的农民领袖们心中并非完全有数。这些原本以“贩夫走卒”为主体的社会边缘阶层一旦取得了社会中心的地位,实际上也不得不求助于原来的社会中心—知识人,利用知识人的智慧重建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统治。而本文将要研究的陆贾,便是汉初知识人阶层中的最为突出的代表,正是他的理论建树为汉初统治者寻找到一种较为有效的统治方略。
一 诸子的终结
陆贾在汉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他虽然较早即追随刘邦,“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以智慧和雄辩为汉王朝的建立出力甚多,但刘邦给他的报偿并不大,仅拜为中大夫。
不过,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陆贾似乎并不在意世俗地位,位卑言微并不影响他的信仰和他对汉王朝的忠诚。“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关于《新语》的真伪,前人与时贤均有相当多的考辨,笔者认为《新语》或有后人增删,但基本代表陆贾的思想与学术。参《古史辨》第四册关于《新语》的几篇考辨文章及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前言和附录]。
陆贾犯颜直谏的精神不必说了,而他对汉王朝的忠诚似乎也远过于汉初统治集团中的“贩夫走卒”之辈,他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如何重建社会秩序,以使汉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不再出现如秦王朝速亡的现象。这就是陆贾的思维兴趣之所在。
一统天下的长治久安,实在说来并不是汉王朝首先面对的课题。秦王朝建立统一帝国之后,也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秦始皇、李斯所拟定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就其主观意图而言,都是为了帝国统治的稳固与长久。然而,由于秦王朝根本指导思想的失误,遂使其政策、原则的实际结果恰好走到了政策制定者主观愿望的反面。
对于秦王朝的政策性失误,陆贾的看法与秦末汉初的社会共识并无二致,他同样认为:“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第四》。引文据王利器《新语校注》校改,下同)这种见解并无多少新意,早在秦始皇晚年就有人曾明确提出过。(《说苑·反质》篇记载侯生与秦始皇的对话,虽为小说家言,但大体可以反映侯生对秦政策失误的认识。参本书《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一文)
陆贾的贡献不在于对秦王朝政策性失误的现象描述,而在于透过这一现象揭示其思想认识根源,并试图在根本上加以解决。他指出:“故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纤微浩大,下学上达,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道唱而德和,仁立而义兴,王者行之于朝廷,匹夫行之于田,治末者调其本,端其影者正其形,养其根者则枝叶茂,志气调者即道冲。故求远者不可失于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圣而臣忠。或图远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穷。季孙贪颛臾之地,而变起萧墙之内。夫进取者不可不顾难,谋事者不可不尽忠。故刑立则德散,佞用则忠亡。《诗》云式讹尔心,以蓄万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国治,此之谓也。”(《新语·术事第二》)这样,陆贾对秦亡这一现象的分析,便比时人更进了一步,即秦政策性失误并不仅仅是利益冲突和心理因素,而是秦代最高统治者在根本点上—道与德—犯了原则性错误。
道与德,是中国传统统治学说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先秦诸子“易天下”的共同武器。张舜徽说:“吾尝博观周秦诸子,而深疑百家言主术,同归于执本秉要,清虚自守,莫不原于道德之意,万变而未离其宗。”(《新语·术事第二》)此言甚是。先秦诸子基于共同的社会要求,在其思想本质特征上固然有其相通相同之处,但是,诸子之所以为诸子,其根本原因显然在于他们思想特征的相异性,即“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注:“各信其偏见,而不能都举也。”疏:“宇内学人,各滞所执,偏得一术,岂能弘通。”),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庄子·天下篇》)。
犹如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学术对欧洲后来的巨大影响一样,先秦诸子也是中国后世宝贵的智慧资源,包括秦王朝在内的历代统治者,虽然对诸子的思想价值或厚此薄彼,或褒贬不一,但他们无不从先秦诸子中获取思想养料。诚如陆贾所分析的那样,秦王朝的政策性失误不是别的,而是在“道德”的选择与取舍上犯了原则性错误。简言之,即过分倚重法家的结果。
法家是诸子中的重要学派,其基本特征是严而少恩,重刑重诛。正是这些特征促成了秦帝国的建立,然而秦帝国的灭亡也恰恰可以导源于法家学说。稍后的陆贾曾较为系统地总结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设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过秦论》中,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2页)
贾谊的这种分析和推论,是秦末汉初的社会共识。循此原则,新建立的汉帝国要想避免秦朝灭亡的悲剧,就必须彻底抛弃秦王朝所奉行的法家路线而省刑爱民。无疑,陆贾具有同样的认识。他写道:“昔者,晋厉、齐庄、楚灵、宋襄,乘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刻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群臣之怨积于内,而欲建金石之统,继不绝之世,岂不难哉?故宋襄死于泓之战,三君弑于臣之手,皆轻师尚威以至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三君强其威而失其国,急其刑而自贼,斯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新语·至德第八》)
鉴于“去事之戒”而抛弃法家路线,在汉初统治层似乎并没有多大问题。刘邦入关,约法三章,就明确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悉除去秦法。”(《汉书·高帝纪》)这至少在政治层面已明确抛弃秦王朝所奉行的法家路线。
问题在于,汉王朝抛弃法家路线之后,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统治原则,这在当时最高统治层一度引起了激烈争论。
刘邦是没有多少文墨的农民领袖,但他的为人处世倒也潇洒。当他宣布废除秦王朝的统治原则时,似乎在他的心目中并未过多地考虑应该奉行什么路线,一切以实际发生的情形而决定。不过,正是他的潇洒与大度,使得在秦朝一度受到压抑的诸子学得以复兴,各家各派相互竞争,皆欲以其道易天下。在先秦最具影响力的儒、墨、阴阳、道、纵横等家,似乎在汉初统治层都有自己的信奉者和代理人(参《秦汉之际的儒者》,此文对诸子学在汉初的状况有详尽描述与分析,《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卷一)。他们皆欲以自己的学说去填补统治思想的真空。
在汉初复起的诸子中,势力最大的当推儒家。一方面,这些儒学人物基于“外王”致用的传统立场,积极参与汉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工作,如叔孙通毛遂自荐为刘邦“起朝仪”;另一方面,这些儒学人物欲报秦王朝焚书坑儒的一箭之仇,故在汉初有着比其他学派更为强烈的表现欲,他们期望以自己的实践来充分证明“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道理(《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因此可以说,在刘邦平定天下、重建统一之际,最有可能填补统治思想真空的当推儒家。
陆贾无疑也是汉初儒者的杰出代表,他“时时前说称《诗》《书》”虽遭到刘邦戏弄,但最终毕竟有助于儒学势力的扩张,《汉书·艺文志》把他的著作列为儒家类,可证明他对儒学的倾向性。陆贾基于儒学立场,对汉初复起的儒学之外的诸子持一种较为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们的思想虽然具有某些合理性,但都不足以填补统治思想的真空。在现存《新语》中,陆贾没有对诸子学说进行专题评论,然归纳其零散的言论,仍可窥见他对诸子的一般态度。
对名噪一时、在汉初仍甚有影响的纵横家,陆贾虽然本人也极为赞赏并接近于这种思想倾向,但从总体上似乎又持一种否认态度。他写道:“夫举事者或为善而不称善,或不善而称善者何?视之者谬而论之者误也。故行或合于世,言或顺于耳,斯乃阿上之意,从上之旨,操直而乘方,怀曲而合邪,因其刚柔之势,为作纵横之术,故无忤逆之言,无不合之义者。”(《新语·辩惑第五》)平实的叙述语言流露出作者对纵横家人格上的轻蔑。
对于当时甚有影响力的道家,陆贾更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说:“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来,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而非怀道者也。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新语·慎微第六》)显然,这种学说也无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陆贾看来,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足以弥补废除法家路线之后统治思想真空的唯有儒学。他强调:“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夫子……及闵周室之衰微,礼义之不行也,厄挫顿仆,历说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无其立,而世无其主,周流天下,无所合意,大道隐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深授其化,以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逾,科第相序,为万□□□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所立,大义之所行也,岂以□□□威耶?”(《新语·本行第十》)通过对孔子遭遇及历史贡献的描述,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对儒家精神的呼唤以及陆贾的儒学倾向。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陆贾的这种倾向性是否意味着他坚决排斥诸子,或者说他较董仲舒更早就有一种独尊儒术的倾向性呢?回答显然只能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在汉初诸子复起的学术浪潮中,确实已有儒学独尊的思想端倪,叔孙通“儒术不足与进取,可与守成”的说法以及他不惜变通儒学传统以媚世的政治实践,都足以表明儒家学派有一种内在的独尊倾向。不过,对这种倾向,陆贾并不愿意随声附和,他虽然基于儒学的立场对非儒诸子派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似乎也已明显地看到儒学一家独尊所可能导致的恶果。他说:“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今有马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砥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师,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韫匮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功,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新语·术事第二》)似乎可以这样说,陆贾已预见到儒学一家独尊将可能导致思想专制的结果,因而主张诸子并重,主张儒学与诸子并列,择优而取,因社会实践的实际需要重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就此意义而言,陆贾阻止了汉初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边倒”,这不仅对汉初社会的发展功莫大焉,而且其重建统治原则的主张与实践,也势必导致诸子学的终结,使刚刚获得复兴的诸子学失去存在的社会依据,而又不得不将自己的智慧资源无保留地奉献给重建中的新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