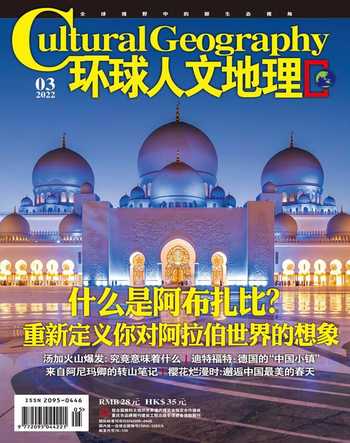一个人,一段路,一座山
周运
转山是什么?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于笔者,是头痛欲裂时看到发着金光的佛像,是沉沉夜色中的孤灯,是被藏獒围堵时绝处逢生的奇遇,是能让人忘记熊和狼的狂风暴雨……



這次转山,转的是阿尼玛卿。
阿尼玛卿,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呈西北至东南走向,主峰玛卿岗日海拔6282米,为黄河流域最高峰。作为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阿尼玛卿是传说中的世界九大创世神之一,主宰着山河大地,在安多地区的藏语中,意为“黄河地区伟大的山神先祖”。
阿尼玛卿是我早就向往的所在。我没料到的是,此行会有如此多的艰难险阻,恰似为我量身打造的“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时至今日,我都无法解释,当时的自己是如何振作起来,一步步完成朝圣之旅的。我是个无神论者,但这一次神奇的经历让我相信,我在冥冥中得到了指引和庇佑。
不是我选择了阿尼玛卿,是阿尼玛卿选择了我。
一切还是从飞机在果洛玛沁机场落地说起。
我带着大堆行李踏上机场大巴时,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乘客的注意。他们好奇的目光,扫过我背上堆砌的大包小包,以及手里的登山杖和帐篷,终于成功地找到了我这个人在哪里。坐定后,隔壁的小伙儿问我:“是来登山的吗?”我喘着气回答:“转山。”小伙儿年轻的脸庞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赞许和羡慕,原来他也很想去转,苦于没时间。小伙儿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经常来回于玛多和玛沁,中途会路过阿尼玛卿,但苦于工作太忙,每次都是擦身而过,这次又要匆匆赶往达日。
司机把我放在离宾馆最近的十字路口,下车后我开始感到不适。毕竟玛沁县城海拔3750米,比拉萨还要高出100米。我坐在公交站的长凳上缓了好久,才敢扛起所有行李走到宾馆。入住后,下楼吃饭顺便晒了会儿太阳,一阵困意袭来,我打算回房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就出发。但没想到这一躺,竟是三天。
傍晚时分,头痛来袭——我意识到自己高反(高原反应)了。因为毫无食欲,便用水壶煮了茶叶,喝了一杯就昏昏睡去,希望明早能够好转。夜里出了很多汗,难受得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于极难受中瞥见外面漫天彩霞——窗口正对着城北的喇日寺,我看到寺庙的屋瓦,还有山坡上那一尊巨大的金佛在阳光下闪耀。但此刻我的意识模糊,身体被头痛、反胃、无力、耳鸣轮番碾压……高反更加严重了。
就这样躺到中午,口渴难耐的我挣扎着爬起来,冲了一杯葡萄糖水,喝下去没多久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呕吐不止。身心交瘁中,理智让我跌跌撞撞地下楼续房。回房后我坐在床角,试图通过冥想和腹式呼吸减轻缺氧症状,可最终还是迷迷糊糊地躺下了。躺下后意识并没有完全得以休息,我听见外面大雨滂沱而过的声音,听见冰雹劈啪作响的声音……渐渐感觉身体化作一滩泥,随着雨水卷进下水道,越陷越深,在黑暗中喊不出声,透不过气。
不知何时,雨似乎停了,鼻子最先被唤醒,那是牛肉汤的味道。睁眼,窗外是热闹的袅袅炊烟。三十小时没有进食的肠胃依旧不适,但似乎可以接受点甜的东西。我吃了少许八宝粥和几个果冻,又吞下两粒盐丸。不敢喝水,微张着干裂的嘴唇维持呼吸。躺到半夜头疼依旧不依不饶,只好又坐起来冥想,试图用专注呼吸来缓解一点痛苦。正襟危坐间,透过窗外黑沉沉的夜,我兀自看到山坡上有一盏孤灯,不知那是诵经阁还是佛像的灯光。这时一个意念跳入脑海——计划应该改变了。我原定走完阿尼玛卿的西侧之后,就放弃东侧,直接前往玉树,去转另一座神山:尕朵觉沃。目前看来,玉树是注定不能成行了。“将阿尼玛卿转完”,一个念头说——如果能撑过当下高反的话。
随即我又陷入昏睡。再次醒来,已是到达后的第三天早上了,身体似乎有所恢复。窗外天气极好,天光云影在绵延起伏的山坡上静静流淌。我望着喇日寺那尊默默陪伴了我许久的巨大金佛,看见下方成片经幡猎猎飞舞,终于感觉到自己又“活了过来”。
到达后的第四天,虽仍有些许不适,但我终于重振信心,收拾好行李出发了。
被高反给了一个下马威的我,终于坐上了从玛沁县开往玛多县的大巴车。班车离开城区,走上德马高速,向西北方向而去。随着路边的风景从楼房街道变成铺满草甸的山丘河谷,此前高反带来的低落情绪和城市的喧嚣一起被抛在身后。
我真的要去转山了,并且无法回头。
车行约一个小时后,驶出雪山二号隧道,司机靠边停住。下车,穿过高速公路,翻过护栏走下路基,钻过一道铁丝网后,我终于看见那两座标志着转山起点的佛塔。察那卡多正是这个路口的名字,渺小到不会出现在任何地图上,却是藏民口中取得“转经钥匙”的重要地点。
两座佛塔都是十多米高,一前一后矗立在路旁,一座是白塔,一座被漆成璀璨的金色,塔基堆放着真言石板。它们旁边有一座方形的祭坛,据说藏民开始转山前,都要在此举行祈福仪式,以求阿尼玛卿保佑自己转经路上一切顺利。我看到祭坛上没有灰烬,地上也没有龙达(画有神像或写有咒语、祈愿的彩色小纸片,祈福时撒向空中)的痕迹,说明这两天并没有人前去转山。我分别绕着两座塔转了三圈,以求得转经钥匙。当然,所谓的“转经钥匙”,并不是实实在在的钥匙,而是象征意义上准许人们踏上转山之路的许可,更像是一种祝福。取得“钥匙”之后,我正式迈出了转山的第一步。


如今在阿尼玛卿东侧已建起高速公路,西侧则是可行车的砂石路。以往步行绕山一圈需要七八天,现在开车一天就可完成——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能用双脚走完西侧。说来神奇,刚才在车上时,我的脑袋还是晕乎乎的,此时背着行李走起来,高反症状反而彻底消失了。感知着脚下的碎石路,行走对我来说似有魔力,构建起我与这片土地的联结,带给我力量。
道路沿着阳柯河谷曲折延伸,路边的山坡上有牦牛在吃草,偶爾能看到几家牧民的房屋,却没有遇到人。大概走了半小时,我远远看到前方的路上有人和马的踪迹,便加快速度赶上去,企盼遇到结伴转山的藏民,没想到遭遇的,却是凶悍的藏獒。
先是远远听到一阵狗叫,寻声望去,声音是从河对岸一户牧民房前传出的。狗叫声越来越近,一只黑色的藏獒正朝着我急速飞奔。它的叫声惊动了另外三条体型较小的狗,同样隔着河对我狂吠。很快,黑色藏獒从桥上过了河,冲到离我只有两米的地方,露出尖锐的獠牙,口水横流,满脸凶相,发出可怕的吠叫。
我被吓得大气不敢出,生怕它扑上来咬我,只得采取回避的策略,强装镇定保持匀速向前走,以求尽快撤出它的领地。藏獒紧随在我身后,丝毫都不放松。与此同时,它的三个朋友也快速跟进,沿着河岸张牙舞爪地追我。正在我数着心跳,丈量着还有多久脱离它们的控制时,前方的道路上突然窜出一条貌似维兹拉犬的土黄色猎狗,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其体型之大,跟藏獒不相上下!那一刹那,我只感觉全身血液似乎瞬间凝固,暗忖这下难以脱险,被迫停下来想要狂奔的步伐,盘算着,只有僵持到有路过的车辆来解救我为止了。肾上腺素急速奔流,全身肌肉在汇报:已做好了搏斗的准备!
此时传来天籁般的人声,牧场的主人出现了,恶犬们立刻偃旗息鼓,剑拔弩张的态势烟消云散。牧场主说他刚才牵着马去对面山坡上放牧,听到狗叫就下来察看。他及时为我解了围,让我不胜感激。
接下来的路程中,我遇到几辆汽车。司机们很热情,都会停下来交谈,给我鼓励的同时,他们也传达了一个信息:前面并没有和我一样的转山者。
天气阴沉下来,在一段爬坡的中途,乌云裹挟着骤雨袭来。四下竟无处遮蔽,我只好拿出一次性雨衣,试图穿上以包住前后的背包和腰上的相机。然而风之狂烈,单薄的雨衣还没等我穿上就被吹烂了。我只好卸下挂在背包上的防潮垫,以便给背包套上防雨罩,再把相机放进背包里。我穿上雨裤,一手抱着防潮垫,一手拿着登山杖,在风雨中向前走。
身上的负重太多,衣物装备、电子设备,加上食物和水,足足有38斤重,每一步都混和着充盈在天地间的密集的雨,压得我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走出这阵雨,一直走到大约在十公里外的一个坡顶,我得到了奖励——阿尼玛卿南端的雪峰,它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尽头。此时,我站立的山坡下开满了橘黄色的野花——大地以大片明艳亮丽的色彩,映衬着山谷那头快速压近的黑云。云层缝隙间的光芒,层次错落地出现,我心里冒出陌生的愉悦,而茫茫天地间,孤独的风仍在猎猎作响。
傍晚时分,眼可见阳柯河的水量增大,泥浆般的冰河水翻卷而下。不多时,大雨便倾盆而下。
我迅速穿过一座水泥桥,只因桥头有几顶长方形的帐篷。快速搜寻,发现其中一顶里面有人,就扎进去避雨。帐篷内有两个人,头裹紫色格纹头巾的妇人坐在火炉前,一侧的床上坐着头戴瓜皮小帽、身披大袄的男人。妇人是藏民,男人是回民。他们热情地邀请我放下东西、坐在火炉边,还给我端来热茶和馍馍。
男人告诉我,他们来自海南州,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到这里挖虫草,一般住50天,今年已经待了一个月。听说我打算独自上山,他黝黑的脸刹时收紧:“山上有很多狼,还有黑熊,要吃人的……我们去挖虫草时,经常在河边看到断掉的手,或是吃剩一截的腿。”他摩挲着自己的腿,心有余悸的样子,“以前转山的人多,挖虫草的也多,还好些。现在进山的人少了,野兽就越来越多。我有一次就差点被吃掉了。”



正在我惊愕之时,门口人影一晃,又进来另一位略胖些的回民,他在另一张床边坐下听我们聊天,妇人则不时提着水壶添茶。摩挲腿的男人抬起头说:“你知道吗,昨天有四五个转山的汉人上去,碰到那么大一只黑熊。”他的双臂伸展开来比划,圆圆的眼睛直盯着我,“还好他们有车,才保住命,逃了回来。”
他的话唬得我心跳加速,我在考虑要不要放弃一个人在山上扎营的计划。这时略胖的回民哈哈笑了起来,他对我说:“你别听他瞎讲。”妇人也开口了:“他在吓唬你呢。”男人见被戳穿,自己也笑了,摆摆手说:“要真是那样,我早就拦着不让你上山了。”他这才正儿八经地告诉我,狼和熊是有的,只是没那么多,这些野兽白天不敢明目张胆袭击人,到了晚上,只要挨着牧民的帐篷扎营,也不会有大碍。
雨停了,一个馍馍和几杯茶下肚也有了力气,表达过谢意后,我背起行囊走出帐篷。男人送我出来,指着前方的河谷说,今天走到垭虎(垭口,藏民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可以继续走两三个小时,快到垭虎的地方还有其他挖虫草的藏民,尽量在他们的帐篷边扎营,晚饭可以去他们帐篷里吃。
我继续沿着河谷向上走,一个个弯道接着一个个爬坡。大约下午6点时,我开始留意路边的帐篷和营地。先是在河谷里的一块草地上,我发现了两顶大门紧锁的帐篷。继续前行,发现山坡上有两座铁皮小屋,仍是铁将军把关。我停下来,认真观察了一下:小屋后紧挨着一道不算陡峭的悬崖,居高临下俯瞰两条河谷在此交汇;屋前有一垛垒得半人高的牛粪墙,下方的石洞中还住着一只肥硕的土拨鼠;二十步开外的地方,有一条清澈的溪流。站在两座小屋中间的草地上,我决定:就在这里扎营。
当我快搭完帐篷时,从山坡的上方走下来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他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身穿一件军绿色夹克,头戴一顶黑色棒球帽,手上戴着棉线手套,握着一把三角形的小铁锹。我以为他是铁皮屋的主人,一聊才知道,原来他住在我刚才路过的帐篷里,是一位挖虫草的藏民。
他告诉我,这两座铁皮屋是牧民的夏季牧屋,一般到七月才会有人住;而他们这些挖虫草的藏民则在四月下旬开始进山,六月上旬就陆续撤离,两者互不干扰。他对我的露营装备非常感兴趣,特别是睡袋,请我拿出来让他仔细瞧瞧。亲眼看见这么小一个玩意儿竟然能迅速膨胀得巨大,他表示非常吃惊。到我跟他说睡袋保暖性非常好,他更是像小孩子一样好奇,不禁伸手进去摸了摸。聊完睡袋,他站起身,邀请我去他的帐篷喝茶。
我背着相机跟他出去,走了几步又回来拿上食物补给包,一是为了喝茶时能与他礼尚往来,不是一味蹭吃蹭喝;二是为了防止那只胖土拨鼠趁我不在,去帐篷偷吃。等我快步赶上,大叔——姑且叫他“蟲草大叔”吧,已经打开门,在河谷帐篷里迎接我了。
一进帐篷,就看到一个火炉,炉子上方一根铁制的烟囱通向篷顶。其他布局倒也简单,右侧是一排通铺,左侧摆放着各种工具,中间一点的地方堆放很多纸箱,里面堆满了食品和杂物。通铺是用砖块和木板架起来的,面上铺着碎花垫子,床头整整齐齐叠着八床棉被,铺侧的墙上挂着一些衣物和帽子。帐篷两侧各有两扇窗户采光,地面已经被踩成了坚实的泥地,通铺下却还长着青草,带着几分野趣。大叔告诉我,他和妻子住在另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给年轻人住的。目前他们都还在山上,要过一会儿才回来。
大叔给我倒了茶,并从纸箱里拿出馍馍——在虫草藏民的帐篷里,茶水和馍馍是招待客人的标配。接着,他从上衣内侧口袋掏出一把黑黢黢的东西,放在床上的小桌板上,咧嘴一笑,对我说:“虫草,今天挖的。”我凑上去端详,一条条沾满泥土的东西,依稀能辨认出虫草的模样。大叔捏起一条大的,说:“这个,能卖六七十块。”又指着其他稍小的说,“这些,只能卖二三十块。”
大叔很是健谈,他告诉我,他们每年都来这里挖虫草。以前收成最好的时候,每人一天能挖上百条。如今虫草越来越难找,每天都要走很远,去很偏僻的地方才能有所收获。话题逐渐离开虫草,作为两个互相感兴趣的人,我俩从各自的工作聊到收入,从婚嫁聊到买房。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阿尼玛卿。从大叔口中得知,这个季节垭口的天气比较稳定,明天如果不下雨的话,早点出发,翻过垭口之后大约两三个小时,就会碰到其他挖虫草的藏民,晚上可以借宿他们的营地。说到野生动物,他劝诫我不要单独扎营,尽量挨着藏民的帐篷:“狼怕人,看到人远远就跑掉了,但熊不怕人,晚上要特别小心。如果不行,就住到我这里来。”


当我表示要走的时候,他立马给我的水壶灌满热水。我投桃报李,拿出火腿肠、卤蛋和蛋糕等零食,他却死活不要,统统塞回了我的背包,最后只接受了我留在床上的一小条香葱饼干。我给他拍了一张照,对他说我要记住他的模样,到了垭口的祭坛,我会为他祈福。
我刚回帐篷没多久,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带着不可抗拒的姿态,密集的雨点像机枪子弹扫过帐篷,一轮比一轮猛烈。雨中夹杂着冰雹,与雷声作伴,震得整个山谷隆隆作响。最可怕的还是风,风吹帐篷时像是四面八方都有一只猛虎,各自拽着帐篷一角拼命撕扯,似在激烈争夺一头猎物。即便拉上了所有风绳,外帐还是被刮得左摇右晃。我在里头睡得提心吊胆,生怕突然整个外帐就没了。此时我开始后悔,扎营的时候没有扎在铁皮小屋的背风面,而是选择了暴露的一面,让可怜的帐篷,直面从两条河谷上游刮来的西北和东北风。然而事已至此,眼下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蜷缩在睡袋里默默祈祷风雨尽快平息。
可怕的暴风雨一直持续到清晨,托它的“福”,我一整夜都没心思去担心什么野生动物的事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