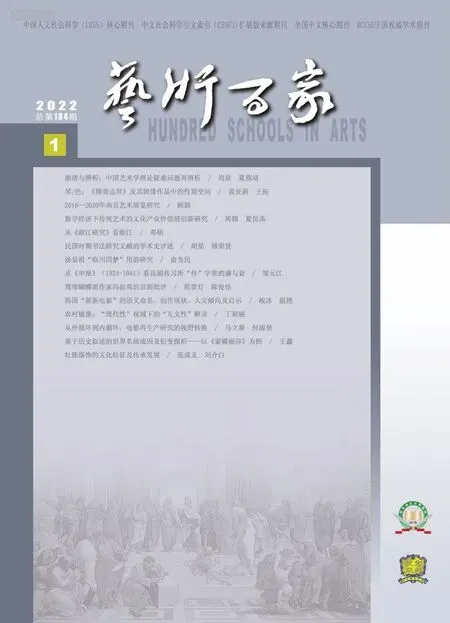鸳鸯蝴蝶派作家冯叔鸾的京剧批评∗
简贵灯,陈俊佳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赣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冯叔鸾(1884—1942),别署“马二”“马二先生”“楼桑”“楼桑村人”,籍贯河北,生于江苏扬州①,是民国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小说界上也得着了非常的荣誉”[1]59。目前学界对冯氏的研究多集中在剧本编剧、小说创作上,鲜少关注其批评实践、批评观念及批评贡献。②事实上,冯叔鸾不仅在剧本编创、小说创作方面成绩斐然,在京剧批评方面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以“戏学”为旨归的批评观念亦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一、冯叔鸾的京剧批评实践
冯叔鸾嗜好京剧,自幼便随其仲兄(按:著名剧评家冯小隐)游走于北京大栅栏一带的戏园中,“寻声按拍,以为笑乐”[2]1。不过,冯叔鸾尝试撰写京剧批评,是在民国元年(1912)初至上海后。冯氏见报端评剧文章不忍卒读,乃以马二先生之名发表评剧文章:
壬子秋来上海,见报端有评剧之文,读之失笑。盖彼辈文自文,剧自剧,能文而不能剧,于是其月旦雌黄,乃无有是处。友人从余曰,何不自为之?曰:诺。遂日书数行,付刊《小春秋》,继而《新繁华》也,《海话》也,《上海小报》也,纷纷托友辈索稿,余亦乐此不疲,无不应命。[2]1-2
当时上海迎贵茶园红极一时的须生杨四立自称谭派,冯叔鸾依据其在北京的看戏经验及积累的戏学知识,在报刊上撰文批评杨四立非谭派正宗。“此类文字连刊数日,当然引起各方面之注意,而群欲探索署名‘马二先生’者为何如人矣。”[3]凭借“见得到,说得出”[4]的批评风格,冯叔鸾很快在上海声名鹊起。
民国二年(1913)春,《大共和日报》总编辑钱芥尘邀请冯叔鸾主持该报笔政。冯叔鸾从此正式开始了卖文为生的生涯。在《大共和日报》的这段时间,冯叔鸾除了撰写小说、发表剧本外,还专门在《大共和日报》附张上开辟了“啸虹轩剧谈”专栏,发表剧谈文章。同年冬天,冯叔鸾出任郑正秋主办的《图画剧报》编剧部主任一职。冯氏回忆说:“忆当癸丑之冬,郑正秋在谋得利创办新民社,余为编演《鸳鸯剑》一节……正秋因《鸳鸯剑》叫座,乃复嘱编红楼戏,续有《风月宝鉴》之作。”[5]作为编辑部主任的冯叔鸾为《图画剧报》厘定体例,分“论著类”“纪述类”“批评类”“杂爼类”四类,以及“戏学思潮”“脚本平议”“梨园掌故”“新剧本事”“舞台消息”“剧场月旦”“伶界阳秋”“戏迷百话”“顾曲指南”九门,其中“批评类”中的“剧场月旦”“伶界阳秋”为冯叔鸾专设的批评专栏。[6]在《图画剧报》任职后,冯叔鸾“遂专力于此,从事《图画剧报》,日为剧论或剧评一二篇”[2]2。
民国三年(1914)四月,冯叔鸾在张丹翁的劝说之下将其散篇剧评定名《啸虹轩剧谈》汇编出版,冯氏在序言中阐述该书的成书经过,“日为剧论或剧评一二篇,汇而集之,已经袞然成册。友人丹翁谓余曰,盖刊而行世,亦是一种文字姻缘。余叹曰:敝帚自珍,人之恒性,文章游戏,刊亦何妨?”[2]2冯叔鸾早期发表在《小春秋》《新繁华》《海话》《图画剧报》等报刊上之剧评大多散佚,《啸虹轩剧谈》保存了冯叔鸾早期的剧评文章,该书“所评论杂剧,则尤能自平其心”[7]。
在《啸虹轩剧谈》出版的同年,冯叔鸾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曲研究刊物之一《俳优杂志》。《俳优杂志》“用作提倡戏剧之先导”[8]2,其体例与《国剧画报》类同,设“论著”“评论”“记载”“杂录”四部。较之《国剧画报》,《俳优杂志》“评论部”门类划分更加科学,分为:(甲)人物评论;(乙)戏本评论;(丙)演艺评论;(丁)剧场杂评。《俳优杂志》主要刊登冯叔鸾的文章,有介绍京剧知识及京剧名伶的《京戏术语》《介绍艺术家》《孙菊仙》;有批评京剧的《啸虹轩观剧闲谭》《孙菊仙兴复不浅》《新民社之义弟武松》等;有研究戏学的《新旧剧根本上之研究》;有介绍戏剧动态的《一年来新剧进行之状况》等。《俳优杂志》仅发行一期便告停刊,冯叔鸾将其重要的文章发表在与其关系密切的《游戏杂志》上。《游戏杂志》的创办者王钝根在《本旬刊作者诸大名家小史,钝根对于读者之介绍辞》中提到两人在“民国三四年间,过从甚密,谈笑唱戏为乐”,并声称“余所编《游戏杂志》,得其投稿甚多”。[9]1《游戏杂志》共收录冯氏的文章18篇,其中包括他的重要理论著作《戏学讲义》。
民国四年(1915)以后,冯叔鸾先后在《亚细亚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华北新闻》、《大公报》(上海版)等报刊任职,主持“啸虹轩剧谈”“楼桑村旧戏新评”“京剧讲座”“俳优新语”等剧评专栏,同时还是《大舞台》《新世界》《晶报》等报刊的重要撰稿人。据不完全统计,冯叔鸾在上述报刊上发表的京剧批评文章不下一千篇。冯氏“识力高人一等”[10],其评剧文字汪洋恣肆,内行折服。[11]
冯叔鸾的京剧批评实践,不止于撰写京剧批评,他还积极参与戏剧论争。冯氏首次参与戏剧论争是在民国二年(1913)。彼时“冯贾党争”缠斗不休。冯叔鸾发表《论剧界之党派》一文,批评党争者“含糊其词,漫为夸大”[2]60的捧角态度,提出“党非剧界中所宜有也”[2]60的观点。冯叔鸾此举引起了冯党领袖柳亚子的不满,两人在报刊上你来我往,进行论争。在冯叔鸾看来,正是因为他的据理力争,“党冯者之焰渐熄矣”[12]。上文所提的《啸虹轩剧谈》的出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冯氏纪念其在“冯贾之争”中战胜了柳亚子:“南社柳亚子以党冯(按:冯春航)之故,讥余不娴雅闻。夫雅闻何于戏?余既窥破此点,乃舍弃所谓雅闻而纵谈戏以攻之,亚子虽不屈,而党冯者之焰渐熄矣,余于是大乐,遂有《啸虹轩剧谈》之刊,所以志成功也。”[12]
《晶报》是冯叔鸾发表剧评、参与论争的重要阵地。民国七年(1918),冯叔鸾声援遭受新青年派围攻的张厚载的文章,如《致豂子书》《评戏杂说》《旧剧之精神》等就发表在《晶报》上。③民国九年(1920),持“跷功当废”观点的冯叔鸾与其胞兄冯小隐围绕“存跷”“废跷”的问题在《晶报》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民国十二年(1923),冯氏兄弟又因为“捧梅”“贬梅”的问题再次在《晶报》上打起了笔墨官司,时人批评:“因伶界前后两大王,一生(鑫培)一旦(兰芳)之故,兄弟互为文章,刊诸《晶报》,各走极端,哗然交哄。”[13]1
民国九年(1920),署名“戏子”之人在10月6日、9日、12日、18日、21日、24日的《晶报》上连载《敬告剧评界》,批评剧评界标准不一、崇古贬今,崇尚空谈、不重实践,收受津贴、自贬身价等种种弊端,[14]引起上海剧评界的强烈反弹。上海剧评名家张肖伧、郑子褒、刘铁仙等人群起攻击戏子,所发表的文章如《驳戏子》(《晶报》1920年10月21日)、《驳戏子》(《晶报》1920年11月3日)、《斥戏子》(《晶报》1920年11月9日)、《辟〈晶报〉戏子之诬谭》(《晶报》1920年11月15、16日)、《记烂污戏子》(《晶报》1920年11月18日)、《斥〈晶报〉戏子之狂吠》(《晶报》1920年11月19日)、《好可怜的戏子》(《大世界》1920年11月25日),对“戏子”极力谩骂,“杂种”“放屁”“下贱”“话匣子”“嚼屎”“狺狺狂吠”“自轻自贱”“狗眼看人低”等污秽之言充斥文章之中。发展到后面,论战的重心偏移到追查“戏子是谁”的问题上。[15]冯叔鸾在这个时候表现出难得的清醒:
“戏子”能用文字在报上发表他的经验,与我们讨论做戏与评戏的道理,无论所说的对与不对,我们都应该容纳、欢迎,希望引起一般“戏子”都来研究研究,庶几可以使中国的戏,有文艺上和艺术上的进步。又何必左一个“评剧家”,右一个“评剧家”,写出那些不相干的话来乱骂、乱猜呢?假使“戏子”的话说对了,固然应该以相当评赞,鼓励他以后对于文字批评的注意,即使他所说的不对,也只能正言指导。何必明讥暗刺,招惹他也明讥暗刺的来,你们又将如何呢?“恶声至必反”,这却怪不得“戏子”,但是这一来,可又都把最初之目的给弄错了,请问彼此乱骂了几次,难道就算是批评戏呢,还是算讨论戏呢?请两方面,“戏子”和“评剧家”,都想一想啊。[16]
冯叔鸾认为评剧家应该客观且包容地对待演员在报上的发声,并给予一定的鼓励和引导,这样才有助于中国戏剧的进步。但他因为理性和包容,反被刘铁仙讥为“戏子的知己”。[17]
值得注意的是,冯叔鸾还以一己之力创办了京剧批评家组织——“戏剧会议”。在“戏剧会议”创办之前,冯叔鸾曾与冯小隐、叶小凤、郑正秋、杨尘因、管义华、周剑云、郑鹧鸪、穆诗樵、刘豁公、恽秋星、姚民哀、尤半狂、陈啸庐等人在民国七年(1918)三月九日一道发起成立上海(南方)首个评剧家社团——上海“评剧俱乐部”。[18]在上海“评剧俱乐部”的成立会上,冯叔鸾与周剑云、郑鹧鸪、郑正秋一道当选干事,主任干事是冯小隐。[19]不过上海“评剧俱乐部”昙花一现,举行几次活动后便杳无音信。不久,冯叔鸾便跟友人前往北京创办《华北新闻》。民国十年(1921),冯叔鸾从北京“倦游归来”后,在上海《晶报》发布《征求戏剧会议的同志》的通告,准备成立剧评家组织“戏剧会议”。《征求戏剧会议的同志》发布短短几天,来函要求加入者有杨雪恨、姚蛰庵、陈艾艾、陈斌如、秦宾赐、王梨花云、吴应生、吴永清、陈富华、梅花吟馆主人、张怡云、少璜、武心南等十八人。[20]截至3月18日,即“戏剧会议”召开的前日,又有数人请求加入。值得注意的是,像陈斌如、吉无咎、陈钱鸣等沪外人士亦要求加入,[20]可见冯叔鸾并没有打算把“戏剧会议”办成上海一地的社团。
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时,“戏剧会议”在久记社票房召开谈话会。到会者仅杭石君、李警民、姚拙盦、杨雪恨、王子臣、梅花吟馆主人、陈富华、王梨云、沈荆香、陈乐民,并冯叔鸾共十一人。冯叔鸾《戏剧会议纪》记载:
余关于剧界之凌乱,评剧者之纷呶,都有所触,发起此会议,浃旬之间,投函响应者二十余众,率皆平素不相谋面者。乃于十九日假久记社开谈话会一次,意图聚晤一番,彼此间可以交换意见,为集合商榷之第一步。到者仅杭石君、李警民、姚拙盦、杨雪恨、王子臣、梅花吟馆主人、陈富华、王梨云、沈荆香、陈乐民,并余共十一人。是日之谈话,除杭石君略有表示外,其余诸子,多抱歉态度,致余未能一一备听教益,至为遗憾。又有请余提出一种具体指计划书,余亦不愿以一己之主张,成为章程式之草案。然是日余之谈话要点,可为一般之同志告也。[21]
从上文可知,这次会议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冯叔鸾原本“意图聚晤一番,彼此间可以交换意见,为集合商榷之第一步”,但是最后却变成冯叔鸾唱独角戏,“是日之谈话,除杭石君略有表示外,其余诸子,多抱歉态度”。19日谈话会后,陆续又有数人要求参加“戏剧会议”。其中周南陔、沈荆香两人专门写信给冯叔鸾发表意见。冯叔鸾再次强调,希望参加者均能发表意见,一起草拟办法,共同讨论。[22]可惜的是,此后《晶报》再无“戏剧会议”的相关消息,冯叔鸾创办“戏剧会议”的尝试最终不了了之。虽然上海“评剧俱乐部”及“戏剧会议”旋生旋灭,但是这段经历是冯叔鸾京剧批评实践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
二、冯叔鸾京剧批评的戏学观念
在丰富的京剧批评实践中,冯叔鸾逐步形成了“戏学”观念,初步奠定了“戏学”的框架和研究路径,继而又将其运用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冯氏批评风格。
(一)冯叔鸾“戏学”的初步建构
初到上海的冯叔鸾,对当时上海京剧批评界颇为不满,他批评道:“文自文,剧自剧,能文而不能剧,于是其月旦雌黄,乃无有是处。”[2]1懂戏、能文的冯叔鸾则能“擅此二长,故成兼美”[2]2。冯叔鸾颇为自负地说:“是时,上海之为剧评者,尚无以内行语入文字者,有之,自余始。”[12]冯叔鸾的确有骄傲的本钱。在京剧批评体系尚在建构的时候,冯叔鸾已经开始了对“戏学”的思考。
早在民国二年(1913)五月,冯叔鸾在主持《大共和日报》时,就在“啸虹轩剧谈”专栏上发表了题名《戏学讲义》的系列文章,这比一般认为的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四年(1915)连载于《游戏杂志》上的《戏学讲义》还要早一年左右。可以说,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戏学”概念的提出,滥觞于冯氏1913年发表在《大共和报》上的《戏学讲义》。
由于《大共和日报》部分缺失,目前在该报“啸虹轩剧谈”专栏上仅见四篇《戏学讲义》。第一篇《戏学讲义》题中有“篇甲:戏学总论”的字样,小标题为“戏之界说第一”“戏之派别第二”;第二、第三篇题中均有“篇甲(续)”的字样,其中第二篇内容为“戏之要素第三”,第三篇内容为“戏之性质第四”;第四篇题中有“篇乙:京戏论”的字样,内容为“京戏之分类第五”,文末标注“未完”。四篇《戏学讲义》下均有“不准转载”的字样,可见冯叔鸾对这几篇文章的重视。
在“戏之界说第一”中,冯叔鸾在《大共和日报》上对“戏”如是界定:
何谓戏?戏有广、狭之义。广义之戏,谓凡人以娱乐之耳目也,如京戏、昆戏、新戏、影戏、马戏、木人戏、落子、滩簧、戏法、像声之类,皆戏也。狭义之戏,则专指扮演古今故事,有声有色,如京戏、昆戏、新戏者皆是,而落子、滩簧、马戏、影戏等不与焉。故王玉峰之三弦,人人乐之口技,朱良壁之大力,林步清之滑稽,五飞图之柔术,虽皆尝陈于舞台,而俱不得目之为戏。故此编亦摈之弗论,以其技艺虽有可观,而皆不合于狭义之戏故也。明乎此,方可与言戏。[23]
上引文章的内容虽然在民国三年(1914)出版的《啸虹轩剧谈》中有所扩充,但其关于“广义之戏”与“狭义之戏”的界说基本没变:
戏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言之,则凡可以娱悦心志之游戏,皆戏也。故有京戏、昆戏、梆子戏、马戏、影戏、木人戏以及变戏法、说书、滩簧、像声、绳戏等,戏之范围乃至广。若就狭义论之,则惟扮演古今事实,有声而有色者,始得谓之戏……戏之界说既定,则其格律自然谨严,而其艺术,亦必缜密不苟也。[2]10-11
其他方面,如“戏之要素”部分,《大共和画报》的“声调”与《啸虹轩剧谈》的表述虽然不同,但意思不变。“姿势”方面,《啸虹轩剧谈》则将《大共和日报》的论述由旧剧扩展到新、旧剧之比较,这可能与作者在春柳剧场的新剧实践有关。而在《大共和日报》的四篇《戏学讲义》之中,理论性最强的“戏之性质”,被收入《啸虹轩剧谈》后基本没有改动。④概而言之,在冯叔鸾看来,戏曲选材要以“美术”(按:即美学)为标准,在“乐本体”的基础上,经过“剪裁”“穿插”“点缀”“演绎”等文学性加工及通俗性改造,以期达到“陶镕性情”的感化目的。由此可见,在《大共和日报》刊载的《戏学讲义》中,冯叔鸾已经进行了关于“戏学”的初步思考。
民国三年(1914)四月,冯叔鸾将其在各报发表的剧评以《啸虹轩剧谈》之名结集出版,《大共和日报》之《戏学讲义》也被收录在卷上“剧论”之中。在《啸虹轩剧谈》出版后的数月,《大共和日报》向该报读者推荐该书,用《戏学讲义》之名来号召:“懂戏者未必能文,能文者未必懂戏,冯君叔鸾(即马二先生),擅此二长,故成兼美。所为剧谈,多鞭辟入里之言,无隔靴搔痒之弊。本报曾揭载其十之二三,已博时誉,不啻一戏学讲义也。”[24]当然,这只是广告之言,冯叔鸾自己则认为《啸虹轩剧谈》“颇多芜杂”[6]。
在冯叔鸾的观念中,“戏也,非学则不足以成家”[25]1。从民国三年(1914)下半年开始,冯叔鸾将对“戏学”的思考,以《戏学讲义》之名连载于《游戏杂志》第9 期至第16 期上。冯氏在第一章“发端”便首先对“何谓戏学”进行界定:“戏学者,研究演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之学科也。”冯叔鸾进而指出“戏学”与“知识”的不同:“今之戏迷家动辄曰某某之‘戏学’如何如何,实则彼辈之所谓‘戏学’者皆知识耳,非学问也。科学家之区分知识与学问,皆以有条理无条理为断。是以老农多识草木,老渔多识鳞介,然不可谓老农、老渔为植物学者、水产学者,诚以其有知识无条理也。知识譬诸原料,而学问则原料之物品也。苟以知识为学问,是不啻指活鸡、生彘为肴馔也,恶乎。”[25]4在他看来,“学问”与“知识”的区别在于“有条理无条理”。⑤在界定厘清“戏学”的概念之后,冯叔鸾以科学之方法,对“戏”之定义、派别、代表人物、文本、演员、表演、舞美、历史、营业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基本搭建起了现代戏剧学的学理框架。相较于同时代的人,冯氏的目光十分超前,他提出的“戏学”概念及进行的“戏学”研究颇具有开创性。冯氏曾非常自信地说:“戏学之成立及戏学名词之成立皆始于我之《戏学讲义》,前此无有也。”[25]3
(二)以“戏学”为旨归的京剧批评
针对“沪上戏界之流行病者何,即不能潜心研究戏之精神,而专爱袭取皮毛”[2]34的毛病,冯叔鸾提出:“有真研究乃敢下真批评,真批评一出,则一般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之批评,皆消匿无效,而戏之价值乃自有定。”[2]38那么,什么是“真批评”呢?按冯氏的意思,“真批评”是建立在“真研究”基础上的。而“真研究”,当然是对“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的研究,即“戏学”研究。换句话说,冯叔鸾心目中的“真批评”是以“戏学”为旨归的戏剧批评。
其一,以戏学为旨归,要求评剧家要具备“戏学的知识”。冯叔鸾评剧的目的是“用文学和美术的眼光,对于现时的戏剧作精密的观察、下正确的评判,以直接或间接促进现时戏剧的改良或进步”[26]。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具备文学、美术(美学)的知识储备,还要具备丰富的戏学知识,所以冯叔鸾认为“评戏最难”,“无戏学的知识者,不足以评剧;无文学的知识者,不足以评剧;看戏不多,不足以评剧;戏情不熟,不足以评剧”。[2]49冯叔鸾进而以某篇批评《琼林宴》的剧评为例:
曩在《民立报》中,见有评贵俊卿之《琼林宴》者,末谓煞神示警涉于迷信,又谓既打死而盛以巨箱弃置郊外,即不应箱中尚有元宝等物,此其说未尝无片面之理,然而独不思事在中古时代迷信岂能除去,现戏剧本是文学中事,若以科学家眼光视之,固为可笑,而以文学家眼光论之,乃为有趣。至于箱中之物,乃是剧中情节之点染,不然,仅一开箱而范仲禹已出,尚有何曲折情趣乎,凡此皆以无戏学的知识,故其评论无有是处也。戏中情节悲欢离合,有起承转合诸法,一如文家之为文。名角唱戏,魄力伟大,转折自然,譬如八大家手笔;寻常伶工,生硬迟涩,譬之酸秀才之咬字,故无文学的知识者不足以评剧也。[2]49
身为凭借“擅此(按:戏学、文学)二长”[24]而迅速在上海滩走红的剧评家,冯叔鸾很明白戏学、文学知识的储备对于评剧家的重要性。虽然戏学、文学知识缺一不可,但是戏学却是关键,“无戏学的知识”,批评家的“评论无有是处”。[2]49
其二,以戏学为旨归,应“以戏学家眼光视之”。对于当时南北报纸上所作的剧评,冯叔鸾认为大多“就目下事实而论,南北各报纸上所作的剧评,不过是用纪叙体的文字,把所看的戏,写了出来,再就个人的眼光,加上几句论断,其优劣只能以文字判别,却不能以眼光判别”,而这些剧评的眼光,也不出以下四种:
1.看过北京十年前的几出戏,便自命为顾曲前辈,开口叫天,闭口德霖,这是一种旧戏迷,顽固的眼光。
2.认识几个名伶,便尽力去颂扬,差不多把古今中外的美,都附会在一个伶人的身上,这是捧角家,浅见的眼光。
3.略知皮黄的皮毛,便时常卖弄他是内行,不管如何,总得写几句行话,这是乡下人,初次开眼的眼光。
4.套着别人的口风,他再附会上一点意思,不管前后的矛盾,这是剽窃家,盲从的眼光。[27]
冯叔鸾认为,带着这四种眼光写出来的剧评,基本溢出了谈戏的范围,“不是嫌某人包银过多,便是骂某人牌子过大,再不然,便说某人当年的戏如何不值钱,再不然,便说某人有何种暧昧的事,差不多把伶人自幼至今,以及饮食起居,戚族朋友,都夹杂写在剧评里面了”[27]。因此,冯叔鸾特意强调,批评戏剧要“以戏学家眼光视之”[2]30。如冯叔鸾《谭叫天之“戏学”》将谭鑫培的出身、师承、演出经历、擅长之处作为“戏学”的一部分展开评论,[28]是其早期以“戏学”作为评剧标准的尝试之作;再如冯叔鸾《余之新旧剧今昔观》“以戏学家眼光视之”评论汪笑侬,认为其“《党人碑》简单不完,《新茶花》支离繁琐”[2]30;又如冯叔鸾“以旧剧家之眼光衡之”冯春航后得出结论:“(春航)演花旦嫌面目太板,躯干太丰,若唱青衣又觉声调全非,稍能见长者,惟苏语流利耳,就此而论,仍不过是一个上中之材,若遽视为天人,真乃措大眼孔小也。”[2]48“戏学”被冯叔鸾反复运用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
其三,以戏学为旨归,应“纯就戏剧之学理上观察”。冯叔鸾在《上海何故无正确之戏评乎》一文中,通过与“友人”问答的方式,揭示其戏剧批评的着力点时说:“余之所批评者纯就戏剧之学理上观察。”[2]48按前述戏学的定义可知,“戏剧之学理”即其“戏学”之理论部分。“戏学”既然为一门“有系统的研究”,那么以“戏学”指导需要精确判断的剧评时,应该“纯就戏剧之学理上观察”。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二十六日,冯叔鸾发表《谈戏的文字》一文,在原来《论评剧》中“不足以评剧”的基础上,提出“不能作(评剧)”的六种情况,将不属于“戏剧之学理”而属于“戏学的知识”的“伶界掌故”剧史、“剧本故事”的戏考、“剧情是非”的剧谈从评剧中剔除,就是因为这些不是“纯就戏剧之学理上观察”。冯叔鸾在《谈戏的文字》中说:
1.不懂戏者,不能作。
2.看剧太少者,不能作。
3.仅懂皮黄腔调板眼,而不明剧本构造者,不能作。
4.仅知伶界掌故,而不明剧理论者,不能作。
5.但注重于剧本故事者,只是剧的考证。
6.但就剧情而论其是非者,与演艺又绝无关系。[29]
要“从戏剧之学理”观察,在批评立场上就要保持客观理性。前述已经谈到冯叔鸾《论评剧》文章中关于客观评剧的表述,在此不再赘述。事实上,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对此冯叔鸾“尤堪自信”:“余之评剧也,学力如何,海上各票友名伶自有公论,至道德一方面,则尤堪自信,不敢以丝毫私心成见置其间。”[2]57他举例说道:
杨四立,余所最恶者也,然彼演《偷鸡》《青石山》等戏,余辄喝彩不已;贾璧云,余所左袒者也,而其扮相太长,余亦不敢为之讳言;八岁红,余所斥为野狐禅者也,而《刺巴杰》一戏之可取处,余每对人言之。凡此皆未尝因一己之所恶,而掩去其所长,亦不敢因一己之所好,而讳言其所短。[2]57
要“从戏剧之学理”观察,在论证过程中就必须讲究理性与逻辑。冯叔鸾对逻辑学有所了解,他曾写过一篇《辩难须知》的文章,专门讲逻辑学的三段论:
凡不明论理学三段法者,不足与人辩难。特演二公式于下,以为好辩难者告。
(甲)大前提:报纸出特刊号者,有类于打吗啡针作兴奋剂;小前提:某报纸之副张,刊席上珍案之特刊号;断定:故某报无异于以席上珍为吗啡针。
(乙)大前提:有譬某附张之席上珍特刊号为打吗啡针者;小前提:凡曾记载席上珍案者,皆可目为吗啡针或戒烟丸;断定:故凡曾刊其任何著作,于任何特刊号之报纸,或杂志,皆为吗啡针或戒烟丸。
能辨别(甲)与(乙)两公式,孰为通,孰为不同,而无误者,始有于他人以文字辩难之起码程度也。[30]
冯叔鸾将理性视为批评之灵魂。他认为“盖今文字辩难者,多富于客气之争执,而不复顾及理性”,“夫辩难而抛却理性,是诚非余孱力所能胜任者矣”。[31]具体落在剧评层面,要求“言之有理,持之有故”[32]。冯叔鸾对逻辑及理性的讲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见得到,说得出”[4]的剧评风格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冯叔鸾受西方影响颇深,如其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分析戏迷群体便是实证。[33]
其四,以戏学为旨归,应“谨守论剧范围”。“谨守论剧范围”这个剧评原则是冯氏与“冯党”(冯春航)健将柳亚子笔战的时候提出的。在“冯贾党争”正酣之际,冯叔鸾发表《论剧界之党派》一文指出:“党非剧界中所宜有也! 剧有好恶,人有抉别,好好恶恶斯已耳,何必言党。党之云者,不顾是非,不分好恶,唯以一心之所崇拜而奉之如神明,曾不敢稍有拂忤,且不许人之稍加贬毁。是故党之好恶,党之是非,必不能公,必不能平。”[2]60冯叔鸾进而批评“冯党”健将柳亚子:“独某君者,拥戴春航,诩为天人,力加匡扶,效死不二,忠于所党,其义可钦。顾忠而不恕,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乃至悍然不许他人于冯党之外另有他党,摇唇鼓舌,俨然老学究之谈道统,不亦可笑之甚哉。”[2]61该文引起柳亚子的反击,冯叔鸾《告柳亚子》辩解他的批评均“谨守论剧范围”。“谨守论剧范围”指批评不能溢出“演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的范围,它是针对捧角党争、人身攻击而言的,所以冯氏才说他的评论“对于亚子未尝有叫骂之言,对于春航、子美亦绝无诋毁之处,评论色艺一本剧学之公”[2]63。
在“谨守论剧范围”的基础上,还要“严格新旧剧之界线”及“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术之分别”。冯叔鸾曾在《啸虹轩剧话叙言》中反思《啸虹轩剧谈》的不足,冯氏认为《啸虹轩剧谈》“颇多芜杂”是因为他在批评实践中混同了新、旧剧,“囊刊谈剧(按:《啸虹轩剧谈》)三卷,颇多芜杂,盖新旧剧固截然两事,未可混同”。在春柳剧场的演剧实践中,他“始能阐明兹义”,于是修正了他的批评观,所有剧评均遵从以下两个准则:
故甲寅以来,所为剧评约有两要点:第一,严格新旧剧之界线。旧者自旧,新者自新,一失本来,便不足观矣! 第二,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术之分别。脚本结构之美恶,是编戏者之责,演员艺术之优劣是演戏者之责,不可不并为一谈,遂张冠李戴也。[34]1
“严格新旧剧之界线”“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术之分别”是“谨守论剧范围”的进一步细分。之所以要“严格新旧剧之界线”,是因为“我国现今之新旧剧界,诸子各挟片面之成见,互相菲薄,此曰新剧不成其为戏,彼曰旧戏不合于情理。舍学理之研究而致全力于诟谇攻击”[8]1。只有根据新、旧剧两者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批评标准,才不会违背初衷。因“新剧应以脚本为要素”[35]2,所以冯叔鸾的剧评主要聚焦新剧的脚本、结构、戏情方面;而在“旧剧”方面,冯叔鸾则将主要精力放在演员及其表演上,这也是冯叔鸾“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术之分别”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冯叔鸾虽要求严守新、旧剧的范围,但其剧评却将新剧和旧剧的相互参照内化于中。
从上可见,冯叔鸾不仅率先提出了“戏学”的概念,尝试为之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将“戏学”作为指导自己京剧批评活动的理论基础。在“戏学”的指导下,冯叔鸾“以戏学家眼光”审视京剧演出,在“谨守论剧范围”的前提下,对京剧“纯就戏剧之学理上观察”。也因为如此,冯叔鸾基本能够避免批评界的陋习,所撰写的剧评也能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冯叔鸾“溷迹于新旧戏场”[23],公暇之余,除了研究“戏学”,就是泚笔谈剧。他深度参与上海剧评活动,实践以“戏学”为旨归的京剧批评观念,在“有例无理”或“理附于各人之例”[36]5的京剧批评界无疑是一股清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京剧批评的近代化转型,他的“剧谈是极有价值的”[1]1。
① 有关冯叔鸾的籍贯,学界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冯叔鸾为河北涿县人,有学者认为冯叔鸾为江苏扬州人。拙作《戏剧家冯叔鸾生卒、籍贯、婚姻考》考证冯叔鸾籍贯为河北涿县,出生地则为江苏扬州,并在扬州接受开蒙教育。参见简贵灯、陈俊佳《戏剧家冯叔鸾生卒、籍贯、婚姻考》,载于《福建艺术》,2020年第9 期。
②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信安娜《亦新亦旧、以中亦西:冯叔鸾剧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赵兴勤、赵韡《冯叔鸾“戏学”的丰富内蕴及文化旨归》(《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4 期),赵海霞《冯叔鸾报刊剧评的理论价值与批评特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1 期),姚赟《冯叔鸾戏剧创作及演出考述》(《戏曲研究》,2017年第99辑)等。
③ 冯叔鸾一一驳斥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人的观点,批评他们“皆似与中国剧绝少研究。既不深悉其内容,辄敢悍然诋訾之,宜其言多失当也”。参见马二先生《评剧杂说》,载于周剑云《鞠部丛刊》,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
④ 详见1913年5月18日《大共和日报》刊载之《戏学讲义》。 该文同时见于冯叔鸾《戏之要素》,选自冯叔鸾著《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年版,第13-15 页。⑤ “有条理无条理”即“有无系统的研究”。冯叔鸾在《怎样研究中国戏学》一文中指出:“凡是称为一种学者,必须其为有系统的研究。”参见马二《怎样研究中国戏学》,载于《大公报》(天津),1928年4月18日第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