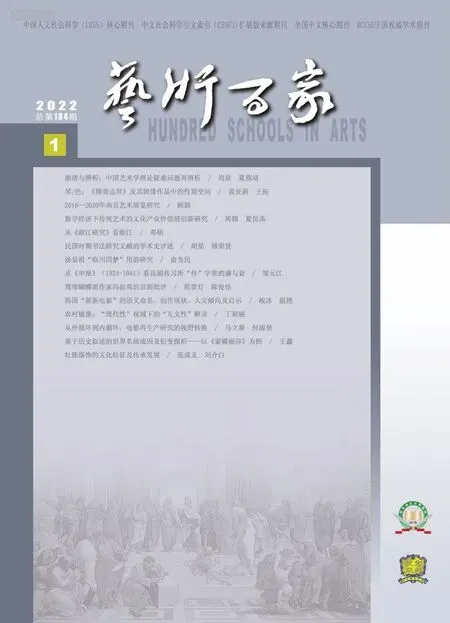图绘跨媒介性:从文学理论到电影研究的知识旅行∗
赵 幸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跨媒介性”(intermediality)是以媒介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文字、图像符号、音乐、符号系统复合体等)的特性为基础,兼具技术和机构平台的特征所形成的传播文化内涵的方式,具有了创作手段、表征特性、科学技术、文化现象、艺术观念、批评方法等层面的多重含义。本文通过比较、分类和关联的方法,跨学科地梳理了英文专著和文集中“跨媒介性”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文学理论、媒介理论、电影理论三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学科意义。选择这三个领域不是随机的——虽然它们并没有涵盖所有涉及跨媒介理论的学科或艺术门类,但对跨媒介性的运用具有时间和逻辑上的先后顺序。
跨媒介的概念在文学理论领域被率先提出,经过近二十年的讨论和运用,从一种对表征特性的描述演进成文学批评方法,并逐渐走出文学理论,被用于反思“大艺术”框架内门类艺术间约定俗成的主导-次要地位(如传统研究视阈下的“语-图”是以“语”为主“图”为辅)。自1983年德国学者阿吉·汉森-罗意威(Aage Ansgar Hansen-Löve)提出“跨媒介”一词并用于批评俄国象征主义作品开始,它首先作为“互文性”的同义词出现在文学理论领域;随着其与互文性和“跨艺术”(interarts)①等词汇的含义逐渐有了各自分野,其运用范围也逐渐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延伸到符号复合体甚至符号体系之间的联系。根据文学理论家沃纳·沃尔夫(Werner Wolf)在大卫·赫曼(David Herman)等人2011年编写的《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中的阐释:“如果‘文(字)’狭义地指代语言文字……那么互文性可以被理解为‘同种媒介’(intramediality)中的嬗变,互文性也就特指语言文字或文字系统之间‘同媒介’(homomedial)关系。与之相反,跨媒介性可以解释广义的、突破媒介边界或不同符号复合体之间的‘异媒介’(hetromedial)关系。”[1]252-256今天,跨媒介理论和批评依然在语-图、语-音作品中运用最广。跨媒介性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发展和运用使得媒介理论学者注意到这一概念,于是在媒介理论领域里,跨媒介性得以脱离文学理论,并作为一个整体的居间的概念具有了其媒介特性,这也使得跨媒介性得以被更加灵活地运用到不同门类艺术的研究中。
媒介理论领域对跨媒介性的讨论成果给一些原先依附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带来新的视角,其中最明显、最活跃的就是电影研究领域。作为复合媒介(composite media)的电影多是被看成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外组合形式(extracompositional form),相关讨论集中在视觉叙述(visual narrative)、图画叙述(pictorial narrative)、图像与叙述(image and narrative)、跨媒介叙述学(intermedial narratology)、超媒介叙事学(transmedial narratology)等方面。在《每一种媒介都会诞生两次》一文中,电影理论家安德烈·戈德罗(André Gaudreault)认为,每一种媒介的诞生首先是技术层面上的,即新科技的产生或几种媒介技术的融合;而后,如果这种新媒介的二次诞生是文化和机制层面上的,那么它将形成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媒介性,并进入特定的社会机构。而电影是最能体现这种二次诞生的媒介和跨媒介艺术形式。[2]104-126也就是说,电影研究的初期是跨媒介文学理论研究,但随着媒介理论提供了跨媒介的媒介特性研究,电影成了可以与其他艺术平行的门类艺术、可以与其他媒介平行的一种媒介。所以,从文学理论,到媒介理论,再到电影研究的视域,一方面追踪了跨媒介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讨论了跨媒介性如何成为突破学科领域屏障的动力,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这种动力也将为新文科消减学科间的屏障提供灵感。
一、文学理论领域的跨媒介
跨媒介性在文学理论领域里的讨论和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文本-图像、文本-音乐;以及三个阶段:定义和区分、分析和批评、扩展和反向思维。这里将主要选取文本-图像在三个研究阶段的发展进行文献挑选和分析,但也涉及少量音乐性文本或文学性音乐。第一个研究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较大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者相比,90年代的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跨媒介性和互文性不可完全地相互替换。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包罗万象的会议论文集,显示出讨论热度,同时也模糊但有效地拓展了跨媒介性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定义和运用范围。进入21世纪,当空泛地讨论定义、集结万花筒式的论文集进入瓶颈期,不少学者开始运用理论成果,进行文学分析或文学批评,由此跨媒介性成为了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约2010年至今,文学理论领域的跨媒介理论有了两个方向的拓展:一是“文本”概念的拓展,二是“跨媒介”不再仅仅作为媒介门类间的互动,而是不同媒介本身特有的研究理论可以被跨媒介地相互运用。
20世纪90年代,英语世界里的跨媒介理论常常和互文性、艺格敷词联系在一起。日耳曼话语语言学创始人亚诺什·裴多菲(János S.Petofi)等学者编撰的《诗歌赏析:文本性、互文性和跨媒介性》(1994)通过符号学等方法,讨论了互文诗中不同媒介对诗歌含义进行的建构,将古希腊诗歌作为口传乐曲文本(musico-verbal text)进行文本以外的再解读。[3]文学学者皮特·瓦格纳(Peter Wagner)编撰的《图像、文本、图像文本:艺格敷词和跨媒介性文选》(1996)讨论了艺格敷词作为将图像转译为文字从而规训视觉的古老修辞手法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定义与转型。首先,瓦格纳认为跨媒介性是互文性的分支,且和沃尔夫一样,瓦格纳认为当图像语言超越文学范畴,进入批评、历史写作等文本时,它依然可以被称为艺格敷词。[4]②这本文集虽然有较大的影响,但实际内容与瓦格纳在引言中的野心并不相符。瓦格纳认为,这将是一部颠覆以往艺格敷词和跨媒介性概念的、具有修正意义的文集。他认为,艺术史研究里的图像-文字关系研究守着传统主义,拒绝后结构主义观点。他提出了广义的艺格敷词,并进一步地将用语言分析艺格敷词的研究本身看作是一种艺格敷词。他提出的革命性创新包括将图像和文字都看作“符号”而不属于某个艺术家的创作——这种观点其实并非瓦格纳首创。瓦格纳尝试重新定义一些术语,但效果比较混淆不清,比如他将图像文本定义为“语言与视觉符号纠缠而生的、依托于文字和图像共同出现的修辞作品。”[4]16这个新定义由一些并不创新的概念以一种拗口的方式再次组合起来,并没有为学界带来实质性突破。而文集所收录的十四篇英文和法文的研究,被分为“艺格敷词和阅读图像表征的相关理论”“图像文本”(主要梳理图像文本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包含两篇文章的“漫画”三部分。这些文章其实并没有很好地契合瓦格纳在引言里的定义和格局。这也体现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不断思考着艺格敷词、图像文本、符号等术语的定义和范围,试图让这些术语对相关研究有更准确、同时又没有束缚感的支持。
此外,文学学者比特·阿勒特(Beate Allert)编撰的《可视性的语言:科学、艺术、政治、文学之间》(1996)[5]、现代语言学者杰夫·莫里森(Jeff Morrison)和德国文学学者佛罗伦·科洛布(Florian Krobb)合编的《文入图,图入文》(1997)[6]也是这一时期讨论文本和图像的跨媒介性的文集。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纳、阿勒特、莫里森等人编著的文集都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包罗万象。主编们则试图从角度迥异的文章中梳理出一些规律,并进行分类。分类方式包括按不同表现或叙述主题、涉及的媒介形式种类、跨媒介过程中的转换方向(如A 媒介进入B 媒介,或B 进入A)、以文本为中心还是以图像为中心等等。《文入图,图入文》作为会议论文集,收录了50 篇精简的论述,从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可视性的语言》是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中发现的较有突破性的一本文集:主编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图像-文字的载体(漫画、插画等),而是将图像-文字的讨论延伸到了更广阔的跨学科领域,特别是社会政治视阈下的媒介科技议题。这本论文集探讨了美学、文化、科技、权力、文字性的视觉、人类的认知科学等等。这种延展为之后跨媒介理论在电影(科技、艺术、权力等)、文化(美学、认知等)等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如此浩瀚而多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也让学者们意识到或许跨媒介作品或事件中有着某种共通的媒介特性,这也为研究跨媒介的媒介特性研究开启了窗口。比如,导演波加娜·莫米洛维奇(Bojana Momirovic)的《广告中的图像和文字:关于口播形象和艺格敷词的跨媒介理论》(2009)关注了广告中让观众自发“阅读”的视觉层面。[7]这里,图像和文字的形式不再是传统的绘本、插图,而是广告中口播产品信息并宣传消费的代言人。莫米洛维奇认为,在这些代言人本身即是物件或现象间跨媒介的通道和平台。
20世纪90年代对跨媒介性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定义、范围等方面的讨论逐渐成熟后,21世纪最初十年出现了多部运用艺格敷词或跨媒介性(再)阐释经典或当代文学作品或文学形象的专著和论文集。这其中包括杰西·托马斯(Jesse Thomas)的《安东尼·伯吉斯小说中的音乐跨媒介性》(2003)[8]、文学学者麦克·高斯(Maik Goth)的《从乔叟的赦免者到莎士比亚的伊阿古:反面角色塑造史中的跨媒介角度》(2009)[9]、安娜·雅各布(Anna Jakob)的《展示不可展示的:迈克尔·翁达杰〈安尼尔的鬼魂〉(2000)和拉吉·卡麦勒·贾〈火中英雄〉(2007)中通过跨媒介产生距离感》(2009)[10]、德语文学学者柏缇娜·库默林-梅巴尔(Bettina Kummerling-Meibauer)和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学者阿斯特丽德·苏麻兹(Astrid Surmatz)合编的《〈长袜子皮皮〉之外: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作品中的跨媒介和跨国界性》(2011)[11]论文集。其中,库默林-梅巴尔和苏麻兹主编的论文集由于其选择了大部分文学理论者都会忽略的、看似浅显的儿童文学,并创新地提出了多种依靠跨媒体形式、跨语言实现的跨媒介性,得到了学界的较广泛关注。《长袜子皮皮》迄今为止已被超过70 种语言翻译,并被改编成广播剧、喜剧、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皮皮的形象也独立出来,被做成人偶或在林格伦主题公园里由工作人员扮演成为常驻角色。像大部分会议论文集一样,这本书被不平均地分为四部分:国际盛誉和当地演化、林格伦作品的电影改编、插图和绘本、音乐雕塑和建筑与作品关系。其中第四部分的讨论最为创新,比如文学学者马格努斯·古斯塔夫森(Magnus Gustafsson)认为,林格伦的文字具有瑞典民谣传统;比约恩·桑德玛(Björn Sundmark)直接将论文题目定为《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声音与乐曲》,他讨论了林格伦作品里的音乐叙事性在作品变成影视后得以释放成真正的音乐和节奏感。
莉莲·卢维尔(Liliane Louvel)在跨媒介理论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她从1998年就开始了相关研究,著作包括《英文文学中的文字与图像》(1998)[12]、《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艺术的双面镜》(2000)[13]、《图像文本的诗性》(2011)[14]等等。卢维尔的《图画的第三种:跨媒介批评论文》(法文原著:2010,英文翻译:2018)是目前为止从方法到观念上都较创新的文学与图像的跨媒介批评。[15]她的方法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出现的比较艺术和符际研究(intersemiotic studies)。全书分五个章节:《语言和图像》《如诗如画,真的》《图画的诗意I》《图画的诗意 II》《躯体回归(转)时图画的第三种术语》。这里,我将以第二章《如诗如画,真的》作为案例梳理作者的方法和观点。[14]55-80原标题中的“l’ut picture poesis”是一句拉丁文,直译为“诗如画”。这里,卢维尔着眼文本里的图画(包括图示、插图、装饰等),将传统的从文字到图像的文学理论顺序进行了反转——她从图像出发,在图像批评的视域下批评文本的文学性。她认为,图画作为阅读体验的一部分,依赖于对不同的愉悦感进行振幅调变。与以往的学者相反,她发现文学和文学批评其实经常借鉴图像理论和视觉创作方式,所以卢维尔认为如果想理解跨媒介批评,人们必须回归最早的写作,比如古罗马诗人贺加斯的《诗艺》。《诗艺》里写道:“诗歌模仿了绘画。一些作品在你靠近时吸引你,另一些在你远离时魅惑。这首诗消解在黑暗里,那首诗想待在阳光下……”[16]400卢维尔让人们意识到插图不仅仅是装饰,而这种融合发生在多变的跨媒介交流过程的居间区域。卢维尔建议诸如“透视”“视觉陷阱”、创作手法(色彩、构图等)这些用于视觉理论的概念和术语可以被挪用到文学批评里。“从画面效果”到“如画的视野”再到“活人静画”(tableau vivant);从“图画描述”到“艺格敷词”,卢维尔用以上两组进阶和对比的术语组举例说明了文学作品中对视觉的挪用程度。最后,在整本书的结语中,卢维尔总结道:两种艺术之间关系不可分割,所以不存在竞争或等级关系,而是一种固有的、扁平的、根茎结构的平面,这个平面消解了盛气凌人的、政治霸权的、甚至性别化了的揣测解读。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不是冲突,而是形成第三种与图画关系的合作。[15]207
文学学者卡拉·刘易斯(Cara L.Lewis)2020年出版的专著《动感的形态:跨媒介性怎样塑造现代主义》,讨论了对文学现代主义产生影响的跨媒介实验性作品或事件。虽然现代主义跨媒介性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刘易斯并没有老生常谈现代主义文学作者参与视觉艺术创作和相关艺术运动的经历,也没有仅仅着眼于艺格敷词,而是讨论了如绘画、雕塑、电影和摄影如何作为一种流动的范式,让现代主义文学“活跃”起来,这种由其他艺术形式的流动范式使得文学作为一种可塑的媒介可以产生史无前例的理论模型。刘易斯通过案例提出了一种新的、从读者出发的跨媒介方式——感觉:“非文字媒介可以在现代主义作者的作品中被感觉到。”[17]3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直到今天,学界对现代主义的研究依然非常重视形式,甚至有现代主义约等于形式主义的说法。而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特别是“读形”(reading for form),恰恰可以为现代主义研究带来跨媒介的维度。卡洛琳·莱文(Caroline Levine)在其著作《形式:整体,节奏,阶级、关系网》(2015)中也强调形式并不是悬浮于深层问题之上的面具,而是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形式批评具有政治可能性。结合莱文的观点,刘易斯反驳了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对现代主义范式关键词“空间形态” 的理解——在弗兰克的观点里,形式是粗劣而固定的,但刘易斯认为形式本身是流动的、变化的、难以预测的。[18]比如在第二章《肉体凡胎:静物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其他挽歌形态》中,刘易斯并没有像以往批评家那样,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的形式结构和她笔下莉莉·布里斯科的静物画一致,而是认为小说揭示了一幅静物画构图的意象隐喻:比如兰姆斯一家桌上精心放置的果盘和贝壳象征着小说热衷于微小、日常事物,并形成一副虚空画(一种象征艺术的静物绘画)——这也再次点明了人生无常的主题。[17]53-92
二、媒介理论领域的跨媒介
21世纪以来,媒体和传播方向的理论研究者们从媒介批评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跨媒介架构和跨媒介创作。领域和视域的改变也给“跨媒介”这个词带来新的含义:在文学理论语境下,跨媒介性是指不同的艺术和媒介形式之间表达方式或美学模式上的交互作用;而新的研究视角则关注跨媒介性的本体论。于是研究转向了梳理跨媒介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持续发展和流变,强调了跨媒介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和媒介性。罗曼语文学专家依琳娜·拉耶夫斯基(Irina Rajewsky)在2005年指出,当前有两种不同的跨媒介性研究的角度:一种延续了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互文性概念,以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写的关于一种媒介如何运用自身的媒介特性激发、升华或者模仿另一种媒介;第二种则是媒介理论的分支,它并没有关注媒介化的作品,而是一种媒介的形成,以及通过展现跨媒介特性形成的媒介转化过程。[19]43-64
文学批评学者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 )2004年的专著《不同媒介的叙事》就符合拉耶夫斯基所说的第二种研究角度。瑞安研究了五种叙述媒介的内在特性是怎样塑造叙述形态、怎样影响叙述表达:面对面叙述、静止图像、移动影像、音乐和数字媒体。瑞安与比较文学学者玛丽娜·格丽莎柯娃(Marina Grishakova)2010年合编的《跨媒介与叙事》在其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更加强调了多模态的建构。[20]编者们之所以会采用“跨媒介”作为标题是因为她们认为跨媒介性覆盖了不同媒介之间所有可发生的关系。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从不同的媒介(记忆研究、图像叙述、电影、广告等等)出发,分别从艺术形式(文字、声音、图像)和技术平台(传播技术,如印刷、电子书)两个方面讨论了跨媒介产生的多模态叙事。最后一篇格丽莎柯娃的文章则提出两种形式的跨媒介表征:“元语言”和“元视觉”。这里,“元语言”指可以激发出图像的文字,而“元视觉”指反思了视觉表征本质上的不足的图像。这本文集用媒介性对作品的叙事进行批评,比如文学理论家扬·贝斯滕(Jan Baetens)和摄影理论家米克·布莱因(Mieke Bleyen)在合著的《摄影叙事、摄影连环画、摄影小说》里指出,摄影小说的媒介特性不足以让猎奇的读者脑海中形成一个具有“彻底的跨媒介叙事性”的故事情节。[21]181此外,这本文集创新地用跨媒介性讨论了多模态对感知、认知、记忆等方面的影响,丰富了媒介理论中接受者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批评。
跨媒介的媒介特性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后,也产生了一些术语。比如2010年前后,“幻景”(imagescape)逐渐成为讨论作品跨媒介性以及跨媒介批评的术语,甚至有时候直接指代跨媒介作品或成为跨媒介性的视觉象征,比如艺术家斯班瑟·塞尔比(Spencer Selby)的《冲刷轮廓:跨媒介性的幻景》(2008)[22]和戏剧学者加布伊勒·里坡勒(Gabriele Rippl)和思想史学者克里斯蒂安·埃姆登(Christian Emden)编撰的《幻景:跨媒介性研究》(2010)[23]。“幻景”一词是迪士尼公司创造的。在图书、周边、影视等超媒介(tranmedial)建构“迪士尼”的元信息下,主题游乐园是“幻想工程师”(imaginer)利用文本、剧场、音乐、影像等艺术形式以不同的跨媒介方式在时空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个让游客沉浸的世界——“幻景” 。表演艺术学者约翰内斯·比林格(Johannes Birringer)在2021年11月出版的专著《流动的氛围:表演与沉浸》中重点讨论了非稳定、偶发、多感知、开放性互动、虚拟实境穿梭的表演场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交互场景中,演员通过放大的声音被嫁接入幻景。他点出了一些以往跨媒介戏剧制作中经常被忽略的关系,比如声音和打光。同时身为研究者和艺术家的比林格从制作人角度出发,思考了在跨媒介表演蕴含的多舞台特性如何通过实体和虚拟的剧场配置来呈现和再现一部作品。[24]
三、电影研究领域的跨媒介
电影领域的跨媒介理论晚于文学和媒介理论,所以不存在定义和术语上的困扰。电影研究的诞生之初是将电影看作一种复合媒介或跨媒介视觉性文本。在电影逐渐发展的过程中,电影完成了从技术到媒介,媒介到艺术,艺术再到文化的格局上的发展。技术、媒介、艺术、文化这四个发展阶段也相应地解释了电影跨媒介理论的演进。电影学者扬·奥尔森(Jan Olsson)和约翰·富勒顿(John Fullerton)合编的论文集《传播的寓言:从移动影像到数码电影的跨媒介思考》(2005)用科技史学者大卫·奈(David E Nye)的名言贯穿各篇论著:“一种科技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机械运作系统,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25]3文集围绕着人与时间、人与空间、人的时空移动展开对电影技术和对电影产生影响的新科技的讨论,而奈提到的“社会整体”则是关注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文集通过讨论从电话、全景摄影到新媒体的科技,覆盖了诸如纪录片、奇观、银幕亲吻等话题,探究了电影表征和银幕世界如何被吸收进入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文化的过程,以及通过从移动全景影像到数码到通过跨媒介表征体现出科技性的戏剧效果。文集包含16 篇论文,分为四部分:“挪移现代性”“再读大潮”“共思与界面”“校准视觉”。第一部分中,电影学者汤姆·冈宁(Tom Gunning)的《弗里茨·朗来电:电话和现代性电路》讨论了电影在与其他具有现代性的传播科技(在这篇文章里是电话)的跨媒介相互作用中,电影风格和影视审美是怎样被其他媒介所塑造、银幕表征——特别是平行剪接——又是如何被影响的。[26]19-39数码中间片(Digital Intermediate,简称DI)工序从21世纪头十年开始流行起来,数码化过程中处理色彩和影像特性所带来了科技、媒介、文化、艺术上的冲击和创作实践灵感。[27]这也使上述电影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电影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在《传播的寓言》论文集的写作年代,电影数码化的成果往往只体现在高解像度色彩调整等技术层面,所以研究对象从数量到种类都不足,限制了研究者的想象。③
跨媒介电影理论学者阿格尼斯·佩索(Ágnes Pethö)提出了重要的概念:电影“居间性”(in-between/ in-betweenness)。她认为跨媒介性的重点在于“跨”,呼吁关注“跨”的过程和过程中的居间性,这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在她诸多的专著中,比如《电影和跨媒介性:对居间性的炽热》(2011)[28]和《陷于居间性:当代东欧和俄罗斯电影中的跨媒介性》(2020)[29],都运用了跨媒介性解读和批评具有地域和时代属性的电影,她认为跨媒介性是一种逃离了分类学,且其定义可以被不断裂变衍生的复杂概念。她关注跨媒介性中的“跨-”(inter-)的含义,以及“跨”这个动作和“跨”的过程对电影的影响。在《电影和跨媒介性:对居间性的炽热》(2011)中,佩索在每个章节里用案例来说明电影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在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居间区域。此外,作者也通过分析个案的范式讨论了电影跨媒介性中的诗学,比如希区柯克电影中绘画作品的魅惑力量,又比如安东尼奥尼电影里时而捕捉时而丢失的触觉意向的独特拍摄手法。从理论角度出发,佩索对跨媒介性的讨论进一步将跨媒介性和互文性切割,对跨媒介关系进行了现象学范畴的定义。另外,一些电影展示了跨媒介性的超介导体验(hypermediated experience)和现实生活的幻觉两者共存,这种共存将影视再现的指代本质和电影特有的意识形态两方面连接起来,让人们得以思考跨媒介性在媒介和艺术中的“政治权术”。
媒介学者金智熏(音,Kim Jihoon)2016年所著的《电影、视频和数字化影像之间:后媒介时代里的混合移动图像》是比较早的、通过“混杂融合”系统性梳理后数字和后媒介时代移动图像技术和观念的研究。[30]当讨论移动图像的媒介特殊性时,作者覆盖了视频博客、影像艺术等经过数位汇流(digital convergence)的作品。毋庸置疑,“混杂融合”和数位汇流都是围绕着跨媒介性和跨媒介特殊性展开的。其中,作者认为跨媒介论文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观念工具”。
2012年开始,爱丁堡大学的“爱丁堡电影与跨媒介性研究”系列由电影批评人马丁·布格内(Martine Beugnet)和电影媒介学者克里斯·拉维托-比亚吉奥利(Kriss Ravetto-Biagioli)主持,迄今为止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题包括电影与其他艺术的跨媒介相互作用(比如《银幕塑像:雕塑与电影》,2019[31])、电影思潮的跨媒介性(如下面要详细讨论的《跨媒介对话:法国新浪潮和其他艺术》,2019)、展演环境造成的电影跨媒介性(《作为电影空间的美术馆:展览中的移动影像》(2021)[32]、《无法被策展的图像:策展后墨西哥电影和媒体艺术》,2016[33])、其他类型艺术家在(类)电影创作中的体现出的跨媒介性(《银幕呈现:电影文化和安迪·沃霍尔、罗伯特·劳申伯格、蒙娜·哈透姆、南·高丁的艺术》,2017[34])等等。这些专著有三个特点:首先,电影本身被作为一种独立的、超越了技术概念的媒介,是一个具有媒介特性并发展出相应的媒介文化体系的整体。其次,这一系列的专著多关注电影与视觉艺术,特别是先锋艺术、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之间的跨媒介相互作用。第三,该系列中的大部分专著都依托于不同门类艺术各自的理论,讨论其与电影理论形成的观念碰撞,通过观念上的跨媒介解释形式上的跨媒介(如嵌入)。这一系列的研究通过当代艺术、文化研究等角度展现了电影作为媒介的可塑性,为讨论跨媒介产物“延展电影”(expanded cinema)的讨论打开了思路。目前,国内关于延展电影的讨论集中在数字艺术(新媒体、移动影像等),但跨媒介性所扩展的不仅是技术,也是媒介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电影媒介与艺术媒介的传播平台和接收形式、艺术媒介与生活媒介的界定等。[35]所以这一系列的专著如得以翻译,将对国内研究拓宽视野具有积极意义。
以往关于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研究多关注风格或内容,而针对电影媒介性的讨论也是将电影解构成文本、视觉、声音等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语言、文字、视觉、听觉跨感知通道的衍生品。所以马里恩·施密德(Marion Schmid )的专著《跨媒介对话:法国新浪潮和其他艺术》(爱丁堡大学的“爱丁堡电影与跨媒介性研究”系列)具有双重的创新意义:施密德将电影看作一种技术、文化和符号复合体层面的媒介,他认为如果要理解新浪潮,就要研究作为媒介的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如文学、音乐)的跨媒介相互作用。[36]比如第二章《以世界为奇观:电影戏剧性》讨论了戏剧对新浪潮的影响。作者首先综述了早期电影如何直接拍摄或模仿戏剧,然后指出在新浪潮重塑电影艺术的同时,荒诞派戏剧也对传统戏剧形式产生着冲击。这两种平行发生的变革也为两种艺术形式提供了跨媒介的平台:比如电影《去年在马伦巴》中植入了一段戏剧,《巴黎属于我们》聚焦于杰拉德排练莎士比亚的《伯里克利》,戈达尔的《中国姑娘》则明显受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叙事戏剧(“辩证戏剧”)的影响。[36]53-83其余章节讨论了文学、绘画、建筑、摄影对新浪潮电影的跨媒介影响。
2021年,由实验电影学者金·诺尔斯(Kim Knowles)和《跨媒介对话》作者施密德合编的《电影的跨媒介性:理论和实践》论文集集合了许多重要的跨媒介学者,可以看作“爱丁堡电影与跨媒介性研究”阶段性成果总结。文集分为四部分:跨媒介的可能性(第一部分:《图绘居间地带》)、跨媒介的实验性(第二部分:《跨媒介的先锋们》)、跨媒介的运作(第三部分:《科技、机制、效果》)、跨媒介的个案研究(第四部分:《跨媒介创作》)。四部分梳理、拓展、探索了电影的跨媒介性,并对相关思潮和作品进行了跨媒介批评。在第一部分中,媒介艺术学者史蒂芬·巴伯(Stephen Barber)、电影视觉学者史蒂文·雅克布(Steven Jacobs)、阿格尼斯·佩索、马丁·布格内(Martine Beugnet)讨论了电影与表演艺术、雕塑、摄影、绘画在艺术、自然、后人类、感知(参见布格内“感觉的电影”理论)语境下的跨媒介居间地带的领域与理论。第二部分里,电影视觉特效大师克里斯托弗·汤森(Christopher Townsend)、移动图像学者露西·雷诺兹(Lucy Reynolds)、实验动画学者巴纳比·迪科(Barnaby Dicker)讨论了处于社会和学术边缘的题材:先锋电影的跨媒介实验性和媒介特性、非电影人在电影创作中自带的跨媒介视野、扩展电影和传统电影的跨媒介关联、扩展电影和艺术的跨媒介纽带。第三部分中,纪录片学者鲍里斯·怀斯曼(Boris Wiseman)、媒介理论学者加百列·尤兹(Gabriele Jutz)、马里恩·施密德追溯了电影的技术起源本身所具有的跨媒介实验性、在拍摄手法方面如何跨媒介地挖掘和挪用其他艺术的媒介特殊性,以及如何跨媒介地运用其他艺术门类表达情绪的方式(如绘画的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带来新的电影感官体验。第四部分包含了导演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创作型演员伊莎贝·若卡莫拉(Isabel Rocamora)、建筑师和导演安娜·瓦索夫(Anna Vasof)、导演萨拉·普西尔(Sarah Pucill)对非主流电影的讨论:舞蹈片中的舞蹈不仅是电影内容和揭示主题的手段,也是两种艺术形式跨媒介嵌入和相互影响的结果;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中的移动图像带来怎样特殊的跨媒介的电影体验;“永动定格动画”(nonstop stop-motion)是目前在短视频网站、当代艺术、动画和电影等不同的媒介领域都广受讨论的动画技术和表现形式;《墨镜》围绕作家、超现实艺术家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un)的摄影作品进行电影创作,通过写作、摄影、电影三种媒介的相互作用形成新的作品。除了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外,这部文集在跨媒介电影艺术批评上还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讨论维度进一步扩大;第二,个案研究的对象包括了最新的作品、趋势和跨媒介表现形式;第三,作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旁观者),也有进行跨媒介实验和创作的导演、艺术家、多栖演员。
四、结语
围绕着跨媒介性的讨论可以创作者的意志和手段为导向,也可以接受者的感知为依据。所以在跨媒介艺术的多个定义中,既有基于作者的创作过程,也有基于观众的接收过程。在以上的讨论中,大部分的定义和范围都是围绕着创作者,而文学-音乐学者丹尼尔·奥尔布赖特(Daniel Albright)在《泛美学:艺术的整体和多样》(2014)一书中,从观众角度定义跨媒介艺术作品。他写道:“一件跨媒介艺术作品是通过两种或以上媒介的相互作用、由观众在自己脑海中凝神将不同媒介中的元素组装起来的复杂而易变的事物……作品的创造者(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引导观众思想,形成一个理想的融合,然而这些引导方式是依据不完整信息的启发,往往毫无用处。”[37]209其实,就如艺术批评家J·赛吉·爱尔威(J Sage Elwell)谈起跨媒介艺术的意义时写道:“我们经常忘记自己本身就是跨媒介存在,我们那些似乎不相交的努力和求索只是人类唯一所求的不同表象:自己与自己和解自洽,我们的物质性与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解交融。”[35]29在学科日渐细化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在生活无限异化和碎片化的现代社会里,创作者们和学者们发现任何语境下的感知、认知和表达都不能用狭隘的、单一的媒介特性去解释,更不能将问题抛给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媒介无限大的定义一切“人类的延伸”,于是跨媒介性在各领域有了富有意义的发展演进。
① “跨艺术”已逐渐被跨媒介性完全取代,只保留在一些院校的跨艺术类学科的专业项目上,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跨艺术门类表演专业(Interarts Performance)。具体参见 Clüver,Claus.“Interarts Studies:An Introduction”[J].Special Issue “Media inter Media,” in Studies in Intermediality Online, vol.3 (January 2009): 497-526.DOI:https://doi.org/10.1163/97890420 28432_027.
② 可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如 Matthias, Voller.Parodistic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in 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Robert Coover and Kathy Acker[M].Marburg:Tectum, 1997.
③ 除此之外,传媒学者克劳斯·米利兹的《生活经验和媒介:宁那·华纳·法斯宾德戏剧、电影、电视作品中的媒介相互作用》(2006)和戏剧导演大卫·芬顿的《〈不稳定表演〉:一个从业者对后戏剧剧场和跨媒介性的诗意的个案研究》(2007)都是同时期关注戏剧和影像跨媒介性的个案研究。Militz, Klaus U.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Media:Media Interplay in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s Work for Theatre, Cinema and Television[M].Bern:Peter Lang, 2006.Fenton, David Raymond.Unstable Acts:A Practitioner's Case Study of the Poetics of Postdramatic Theatre and Intermediality[M].Queenland: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