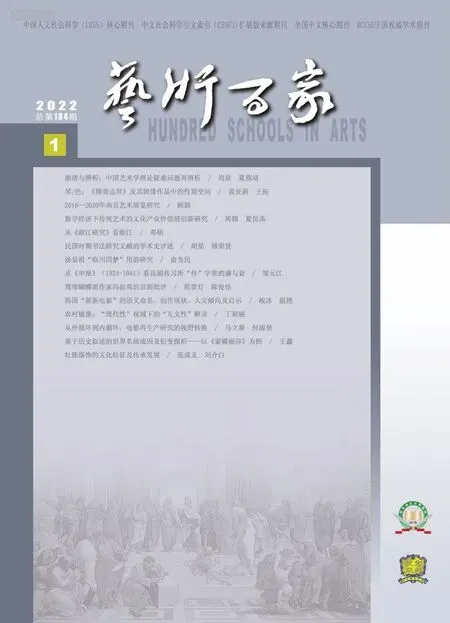民国时期书法研究文献的学术史评述∗
胡笳,傅荣贤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民国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产生了丰富而珍贵的书法文献。因此有人评价:“近代书法史与民国书法史,是一个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绝不逊色的极重要的所在。”[1]134在这个时期,民国书法艺术不但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还因为处于近现代社会转型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环境因素的考验,如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古诗文向语文体的演变、简化字的倡导、硬笔在实用书写上取代毛笔等,都对传统书法形成变革性的冲击。在民国书法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书法理论、书法史、书法评论的观点,既对以前书法发展史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也对当时书法的进步作出了展望,给今人以启迪。本文拟从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家研究与评论以及围绕书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对民国书法文献进行学术史的概述和评论。
一、民国书法文献中的书法演变史
民国书法文献中的书法演变史主要分为文字源流及书体沿革两个部分。
(一)文字源流
民国书法文献重视文字源流,基本上只要是篇幅稍大一些的书法论文及专门书法著作,都会在文字源流上花费一些笔墨,原因在于“书家必通小学,乃免鄙俗之讥。是书先讲文字,次论书法,以此故也”[2]1。而论述书法的各种问题,也确实应从文字而始,因为独特的中国文字才是中国书法的生命基础。若文字没有由来,则书法无从下手。所以在论述文字源流之时,就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字是天生具有艺术之美的,从而为书法的艺术性背书。“世界各国的文字,要算我们中国字为最美术的。别国的字,大都用字母拼合而成,长短大小,很不均齐。只有我们中国的字,个个一样大小,天生成是美术的。”[3]197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字天生不良,没有像西方文字那样演变为符号字体,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遭受西方国家欺凌之际,更是有人直接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归咨于文字之不尽善者矣”[4]44。
(二)书体沿革
民国书法文献对书体沿革有详细的解说,最普遍的是对书体进行大类的区分。如《中国文字与书法》将书体分为古文、大篆、小篆、隶书、章草、楷书、行书、草书等类,《书法心理》将书体分为古文、大篆、小篆、隶书、八分书、真书、草书、行书、杂体书等,《字学及书法》将篆文分为古文、籀文、小篆数种。类似朱师辙的《古文籀文与小篆繁简辨》(《国学(上海)》1926年第1 期)这种对具体书体进行辨析与研究的论文也较多。
麦华三在《汉晋六十简之书法研究》中指出:“我国四千年来文字,向分两大时期。汉以前为古体书时期,用篆体。汉以后为今体书时期,用隶楷行草体。”[9]32虽然论述罗列者很多,但大致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分类,这也与中国书法界对于书体的认知较为一致有关。有些细类的划分也得到了同行的赞同。如《中国美术史》说:“秦代有一种字体,叫做八分,是秦代上谷人王次仲所作,题裁和隶书差不多,自来关于‘隶’和‘分’的辩论文字很多。”[10]117
古人的书体大多沿循旧规,而关于草书的书体分类与风格的争论在民国书法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且持续很久。“草书起于实用。”[11]30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组织了“草书研究社”,1936年,出版了《标准草书千字文》,1941年12月,推出了《草书月刊》,作为国内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更是将这场争论从理论界推到了现实文字的书学应用。长虹的《草书纪年》(《小说月报》1926年第9 期)、荀的《草书谈》(《晏成校刊》1926年第2 期)、杨云史的《行草章法序》(《书法研究》1940年第10 期)、李屋的《草书论》(《光化》1944年第2 期)、建功的《草书在文字学上之新认识》(《辅仁学志》1946年第1-2 期)等文都是这场争论中的一些代表。刘延涛在《草书概论》中对草书的五种起源说进行了总结,对今草、狂草等各种草书做了详细说明,还指出了倡导草书者的见识与误区之处,是当时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他说:“在社会心理与考试制度压迫之下,草书作者,仍能代不乏人,自非世人爱好之深,需要之切,不足以致此;亦非草书虽有缺点,仍有特长,不足以致世之爱好与需要。”[12]116同时兴起的还有对“标准行书”的倡议,很多书法学者认为行书较楷书更适合平时书写,更流畅,更节省时间,也较草书更加清晰易辨识,应该大力提倡。如杨而墨的《行书问题之研究》(《南汇县教育会月刊》1916年第9 期)、易作霖的《行书教授法》(《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7年第7 期)、黄仲明的《标准行书之研究》(《小日报》1936年4月连载)等文是这类论文的缩影。虽然“标准草书”最终没能替代楷书、行书,成为主流书写书体,但这场争论包括对“标准行书”等书体的研究与探索,是民国书法界尝试以书法书体的革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尝试,有其积极价值。
二、民国书法文献中的书法理论
书法理论内涵丰富,民国书法文献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十分庞杂。以书法学本身的一套术语来看,就包括书法典故、学用、鉴藏、考证、款识、椎拓等诸多方面的理论知识。很多书法理论专著如张宗祥的《书法源流论》、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等都有较系统的结构与较广阔的篇幅。1943年,中国书法研究会在于右任、沈尹默、张宗祥、沈子善等人的努力下,于重庆成立,随后创办了《书学》杂志,胡小石、陈公哲、宗白华等很多书法理论家在上面发表过文章,为民国书法文献探索书法理论问题作出贡献。
民国初期,很多清末的遗老遗少还很活跃,如李润清、曾颐、陈宝琛、张謇、罗振玉等人,他们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与对教育文化复古观念的坚持,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他们对传统的坚持,实际上是出于自己学习与使用书法的惯性,坚持以北魏碑刻风格为书法圭臬。康有为作有《广艺舟双楫》,提倡“尊魏卑唐”,就是这种风格的一种体现。并且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顽固地反对任何在书法理论、形式与内容层面的创新。民国初年,这类书法群体及其拥众是书法界的主流,普通民众对于文字革命而带来的文化冲击保持着谨慎而远离的态度,这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书法风格的欣赏态度。虽然早在1917年开始的新美术运动就提出了书法革新与转型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有待时间与理论的积累。直至20世纪30年代,情况方有明显改观。随着清末书法家的逐渐过世,以及随着文字改革、古诗文改革的逐渐推行与深入,新的书法家群体逐渐崛起,其群体中的很多政界达人慢慢掌控了书法理论界的话语权,民国书法界的风格开始更加多元化。如在沈尹默“回归二王”的努力下,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字变革对中国书法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将碑、帖的风格进行了融合,所谓“碑骨帖魂”。这一趋势成为民国书法界的新潮流。如《字学及书法》推崇阮元的北碑南帖论,提到:“历来对于书法的讨论和研究,颇不少名著,但或者陈义过高,不便于初学的研习,或者又拘泥太甚,脱不了一种传统思想的因袭,反使学者深中迷信古人之毒。本编所述,但就容易瞭解而切于普通应用的为主,略采众说,以使初学者得稍窥门径,而有一个扼要的认识。”[6]51
有关书法文献辨伪的研究是中国书法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领域,在民国时期,这一领域也有新的突破。比较突出的人物有余绍宋、唐耕余等人。余绍宋在其《书画书录解题》的卷九,以“伪托”为名,对他所研究出的伪托书法著作30 种进行了介绍,并总结出书法“伪托”的特点,即“技术之书本多依托”“言笔法之书,伪者独多”[13]330-356。唐耕余对《笔阵图》《法书要录》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他如梁启超、顾颉刚等人也对此领域有相应的关注。陈彬和在《中国文字与书法》中提出了书法界长期以来的很多争议,包括对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质疑:“王羲之书名千古,宜无可论,实则碑刻无传。《兰亭集序》聚讼纷纷,阁帖枣木所刻,辗转翻制,面目已非,时至今日,宜有异议矣。”[2]33
在民国书法文献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用传统书法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文论,还可以看到运用近代刚刚开始流行的一些西方艺术理论进行分析的作品,比如运用美学、心理学来研究中国书法理论问题的著作与文章并不在少数。这是民国书法文献在书法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特色与贡献,特别是书法艺术的科学化建构对将书法与西方艺术接轨所做的努力。1927年颂尧发表《书法的科学解释》一文,明确提出书法科学化的旗号,把书法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以科学之方法分析之”。[14]陈公哲在1936年出版的《科学书法》的自序中说:“今日一切学术,皆含有国际性,倘墨守古人成规,不将原有的国粹加以刷新整理,将来要请外国博士讲解中国学术,无他。外人对于研究学术,皆有以为根据,故能缕析条分,阐发无疑。”[15]他在1944年发表的《科学书衡》中,以“直觉方法”和“科学方法”作为区别古今书学研究的标志,通过各三项、十一类的“真书作品给分表”和“行书作品给分表”,进行量化打分。[16]
在笔法理论上,民国书法文献将其作为书法的一个基本功夫加以阐述。徐谦在《笔法探微》中提到:“书法之妙,大要有四。一用笔,二结体,三分布,四用意。”[17]15在《中国文字与书法》中,提到了书法执笔、用笔等注意点。《书法心理》总结了历史上一些名家的用笔方法,包括李斯用笔法、卫夫人用笔法、王右军笔势论、欧阳询八法、李世民笔法诀、智永永字八法、张怀瓘用笔十法、蔡邕的九势为八等。此外还有谭组云的《答鲍梅林草书运笔法》(《文社月刊(上海)》1933年第2 期)等文都是对于书法笔法的专论。
刮耳崖前传令急,霹雳一声千骑入。弓刀匼匝网周遭,罪人黜伏将焉逃?铁笼盛之负以斧,骇汗淋漓写如雨。从征土目凡数千,咸使观睹争骈阗。穴中谁敢萌反复,请视今朝索诺木。远人从此识天威,愿万万古安边陲。[3]65
也有书法学者谈到了中国书法艺术与西方美术艺术的区别与联系。陈彬和说:“西人力求形似,体物状,写风景,均以形似为归,如出一辙。东方人则务在表现个性,似与不似非所计也。书之外包含甚广,书之中其个人之精神寄焉。”[2]76高云塍和韩非木则评价:“我国的美术,无论书画,皆以表现个性为主。”[6]67
三、民国书法文献中的书法家研究
书法是人书写的,书法文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书法家的研究,其中分为对古代书法家与当代书法家的评价。
民国书法文献对古代书法家的评价,主要集中于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等知名书法家,也有一些对二三流古代书法家的评论。沈之善作《王羲之研究》,对王羲之的书法造诣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羲之虽享身后之名,惜余少数书家文士外,一般人士对此伟大美术家之生平与造诣,则未尝瞭解。”[18]5一些人物传记、百科类著作也对古代书法名家有记载与介绍。如《中国名人传》共收录了42 人,其中艺术家8人,书法家则为欧阳询、柳公权。《书法正传》有书家小传。
对于一些古代知名人士的书法作品、风格与成就,也有很多民国书法文献给予了关注。树昌颐写作《王安石评传》,“述安石而及其书法,末事也。相传安石当国时期,其书法颇为并时所尚,甚至花押亦仿安石。”[19]276在这本人物评传中,作者将各种后人对王安石书法的评价进行了罗列,使人印象深刻。还有《人物品藻录》对于李鸿章的书法有详细的展示,仲亮的《泛论书法:辑曾国藩论书法语之一、二》将曾国藩的书法理论进行了总结,以及潘文德的《从“书法学说”论到书圣王右军》(《法治》1949年第2 期)、卢德政的《曾文正公对于书法的指示》(《初杭》1934年第2 期)、《曾文正书法之秘》(《兴华》1934年第25期)、沤盦的《曾国藩的书法论》(《锻炼》1944年第10期)等都是此类作品。
对于当代书法家,民国书法文献的着墨更多。无论是于右任、沈尹默这类民国书法界的活跃人士与书法派别领军人物,还是马一浮、张宗祥、黄宾虹、钱瘦铁、丰子恺、张大千、吕凤子、叶恭绰、溥儒、王福庵等一流书法家,都有很多民国书法文献对他们进行介绍。
在这类论文中,对于右任的介绍尤其丰富,相关论文不下百篇。于右任所倡导的标准草书一度风行民国书法理论界,其人及其书法理论也处于风口浪尖,推崇者有之,揶揄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如道听的《记于右任先生书法》(《上海画报》1931年第749期)、缘岑的《于右任之草书与弈棋子》(《铁报》1936年11月13日第4 版)、葛克雄的《于右任论标准草书》(《现实新闻周报》1947年第5 期)、陆丹林的《于右任氏的“标准草书”》(《雄风》1947年第3 期)等文都是对于右任及其书法理论的评述。
僧道之界也常有书法名家,民国书法文献也没有忽略。以弘一大师为例,有《弘一大师论书法》(《小天地》1944年第5-6 期)、梅瘦的《弘一法师的书法论》(《民国日报》1946年3月21日第3 版)等文。叶圣陶也曾专门写过一篇《弘一法师的书法》(《文协》1944年3月21日第3 版),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沿着书法专业人士的规矩去评价弘一法师的书法造诣,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浪漫的风格去解释自己对弘一法师书法作品的喜爱:“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教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他蕴藉有味,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20]33其实,叶圣陶此论恰恰道出了品鉴书法作品的最高境界,不拘泥于一笔一画、一招一式,而是体会、感受作者人格魅力在作品中的体现,实现了欣赏者与作者的心灵共鸣。对僧道人士书法进行评论的文章还有《海藏楼论清道人书法》(《海报》1942年11月22日第3 版)等。
此外,霜年的《樊云门之书法谈》(《小日报》1931年3月31日)、《当代书家宝瑞臣书法》(《天津商报画刊》1934年第24 期)、笠苑的《陶行知的诗文和书法》(《戏言》1938年第1 期)、《陈含光先生论书法》(《国学通讯》1941年第7 期)、葛康素的《谈陈仲甫先生书法》(《书学》1944年第3 期)这类文章在民国书法文献中都是平常可见的。
一些专业期刊曾经系统地对书法家进行介绍,如上海美术期刊《金石画报》在20世纪20年代每期都有艺术家专栏,介绍了顾青瑶、邓钝铁等人。丰子恺还写过《艺术修养基础》,其中专门对一些重要的楷书大家进行了评价。这种介绍某种群体、某种书体、某种风格的书法家的文论,也是民国书法文献的重要内容。甚至还有对特定宗教群体书法家的介绍,如《介绍回教书法》(《震宗报月刊》1939年第4 期)对谈黄野农先生书法的介绍。其他如对女性、儿童书法家的评价与推介的文论,也不稀奇。《益世报》就发表过介绍儿童书法家张一飞个人书展的广告。
四、围绕书法的一些其他问题
围绕书法这个核心概念,有许多衍生的研究领域,除了以上种种之外,民国书法文献还比较集中的谈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习书法的问题
民国书法界都将书法学习作为一项需要付出巨量时间与体力脑力劳动的事情,在书法学习的重要性问题上,他们的认识十分统一。但在具体的书法学习方法上,却大相径庭。
有人泥古,如《张有为书法之研究》称:“书为六艺之一,从来受人重视,万不可师心自用,自取败道。孟子说:‘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古人的法帖,就是我们规矩准绳。”[21]1313主张学字也应以古帖为根本。“学书如学画一样,没有好的稿本,永远画不成规矩,必须以古人为法,朝夕临摹,渐渐得到个中真味。”[22]1有人专论起初练字字体,《书法概论》说:“不管说法如何,就各名家经验,初学仍宜从楷书入手,此为公论。”[22]28《书法概论》提出先小楷、中小楷、大楷,九宫格、临帖的练字顺序。亦有人说:“初学书法,颜书为宜,此为书家所公认。惟颜书碑帖充斥市肆,学者苟不加以辨别,贸然采用,仍不免误入歧途,是不可以不辨。”[23]10《字学及书法》突出笔的运用,分手法、腕法、指法,字的结构分永字八法等,而练字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大楷、中楷;第二时期为小楷、行书、草书;第三时期为篆书、隶书。还有张天佑的《介绍初学入门之行书备要》(《新闻报》1934年12月20日第15版)等。
有人创新,如虞愚编著的《书法心理》引用西方心理学、神经学说的理论,对书法的学习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解剖。他认为“写字不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乃是感觉与动作两方面的活动。”[24]5书法学习不但是身体的动作,也是脑神经及身体神经系统的协同作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谈书法生理的基础,包括神经系统的联络、书写时各种动作(包括眼动、指动、腕动、肘动、腰动)、书写姿势的正确、临碑帖的方法、时间的长短等,甚至引用了桑戴克、弗里门等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作为解读中国书法学习的例证。
在书法学习工具的选择上,民国书法文献也有很多专论。《书法心理》说:“初学书写,纸质不妨稍劣,但是宁可稍粗涩,不宜光滑,因练习开始,当取其难。先在稍粗劣的纸面,天天练习,将来遇着纯细光泽的,就觉得易写,又不轻率。”[24]71很多此类论述涉及了文房四宝的历史源流、制作工艺、特色及名声等方面,也给书法学习者以很大的启迪。
(二)书法与政治
陈康在《书学概论》中说:“中国书则一面固为生活上应用的一种工具,另一面又可以与绘画、雕刻,并称为一种艺术。”[22]7中国书法虽然是一门艺术,但其所衍生的附加意义早已经超越了艺术范畴,具有更广更高层次的价值,民国书法文献也对此有充分的阐述。
在中国书法研究会的《发起旨趣》中,是这样论述书法与人生、与政治的关系的:“我们站在这个红尘莽莽的人海里,要免掉生活的枯燥与烦闷,应该各就各人的兴趣去找安慰。”“中国书法真可说是世界上特殊的美术,我们生在中国的人,应有发扬光大之必要。”[25]31944年,《书学》刊载了向绍轩的《从书学中窥见中西民族文化异同之一斑》一文,其中谈道:“西国文字教育之识字与习字,在国民教育课程上,不必视为重要科目;而中国文字教育之识字与习字,在国民教育课程上,则当视为基本的重要科目。其所以要视为基本的重要科目,并非如一般人士所谓中国文字繁难,在学校教育课程上,如不特别加重,则收效不易的见解。乃是谓民族本位文化教育,无形中即可于书学课程中间,普遍传述到一般青年学子头脑上去。”[26]66此文坦率地将中国书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联系。事实上,很多民国书法事件背后都或多或少与政治因素有所关联。就以于右任提倡“标准草书”为例,他在《标准草书与建国》一文中,提出“改良文字为建国之先决条件”[28]15。他反对楷书、提倡草书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节省民众书写时间,为政治刷新而服务,所谓:“建国事业至重,时间的争取尤为重要,吾人不可再虚掷无益之时功于楷书之录写。”[28]16张皇在《草书的艺术》中说:“西文有速写法,因此文字的效用格外广多、便利,而文字的价值也更加伟大了。我国有字,比别国早得多,可是,直到最近才经创造速写法,恐怕还不十分健全,实在汉字是太繁多了,也很不容易造成完善的速写法,不得已,我们就把草书认为现成的速写法吧! 那又是一椿何等重大而艰难的工程。”[29]47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则很多民国书法文献的批评就显得鸡同鱼讲了。如琼公在《草书多误》中称:“于右任偏好写草书,且以提倡‘草书学’为己任,其实于氏草书,实不高明,硬欲将章草与孙过庭书谱融合为一,遂致驳而不纯,且多误讹,不足为贵,赏鉴家对之不取焉。”[30]能否理解书法与政治的联系,的确是当时很多书法界人士的分歧所在。但正如丰子恺说的:“我们切不可贪钢笔铅笔的简便而废弃原有的毛笔。须知中国的民族精神,寄托在这支毛笔里头!”[3]198
随着民国时期书法文献的重要性逐渐被学界所认识,对于民国书法文献的研究工作正在不断拓展,只是,“现有的书法文献做了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但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31]52如何透过民国书法文献的林林总总,看到近代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的中国书法人、书法理论与书法作品的转变,看到中国书法的生命力与价值,是民国书法文献研究的更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