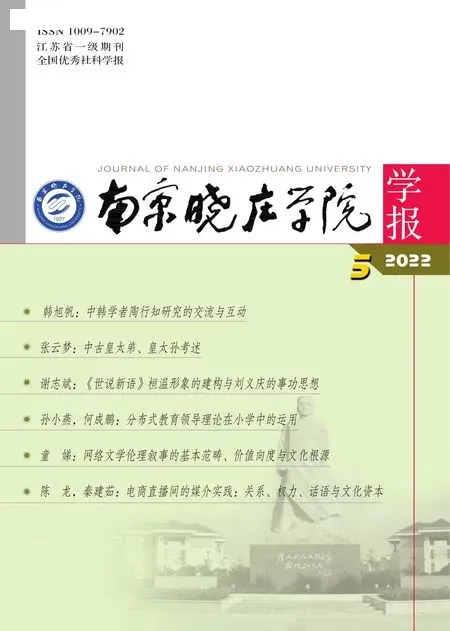《世说新语》桓温形象的建构与刘义庆的事功思想
谢志斌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是中古典型的清谈轶事集,号称“名士生活教科书”。其主旨一般认为是“无为”“务虚”,甚至所谓的“清谈误国”亦以此作为依据。而编撰者刘义庆也往往被视为清谈式的人物。其实,《世说》亦包含着浓厚的经世致用的事功思想,并非完全是“清谈风流”,这一点不断为当今研究者所揭示。例如,江兴祐在《论〈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一文中指出,把《世说》看作“清谈之书”和把刘义庆看作“清谈家”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出儒家的范畴。(1)江兴祐:《论〈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郑学弢认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先事功而后玄谈,是《世说》政治思想的主导方面。(2)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事实上,在《世说》的众多人物中,“事功”的确是一大内容。而刘义庆也通过记述这些事功人物,来表明自己的思想。最典型的是,在东晋中前期虽颇有作为却因觊觎皇权,而被视为“逆臣”的桓温(3)《晋书》将桓温与王敦合传,称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在《世说》中,比较充分展示的是他致力于统一大业,最终因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而功业不成的一个悲剧英雄形象。学界关于桓温、《世说》和刘义庆的相关研究甚多,但很少有学人将此三者结合起来认识。虽然有学人发现《世说》对桓温的风度豪情倍加欣赏,对其尴尬境遇给予理解,对其落寞下场难掩叹息。(4)贾骄阳:《〈世说新语〉对桓温的塑造》,《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但亦未能进一步揭示刘义庆钟爱桓温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分析《世说》所记桓温事迹,探讨刘义庆建构桓温事功形象的深层原因,进而揭示《世说》所包含的事功思想其实是刘义庆本人思想的真切体现。
一、 《世说新语》所见桓温追求功业之心迹及表现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龙亢镇)人。龙亢桓氏本是前朝的刑门之余,桓温之父桓彝为提升家族地位,努力跻身“八达”之列,然他又志在立功,为东晋创立做出了很大贡献。(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这是桓氏成为东晋朝新兴门阀的重要依据。作为新兴门阀的桓氏总体上孤寒势单,不得不依赖事功立足。桓温为了维护门阀地位,与其父一样,努力以功业自立,而当时最大的功业便是稳固江东政权,完成统一大业。《世说》没有叙述桓温直接追求功业的事迹,而是从他的日常行为来展现桓温的功业情怀。
《世说》记载桓温事迹的条文丰富,计有113条,其中大多数都反映桓温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尤悔》第三十三载:“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年版。按,为避繁琐,下引此书一般不再另外出注。有学者据此认为桓温的“历史意识”甚重。(7)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所谓“历史意识”甚重,其实也就是重视历史定位,而这需要事功来支持。《品藻》第九载:“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桓温将管仲作为学习的对象,说明了桓温事功为怀的心迹。(8)施建雄:《试评桓温——兼论东晋前期的政治与军事》,《三明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在东晋门阀政治时代,要想成就一番功业就必须得到士族门阀的认可、支持。作为新兴门阀的桓温,故而极力团结高门大族。《雅量》第六载其对琅邪王氏的团结:“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王珣小桓温将近四十岁,在桓温府中年辈较轻。桓温将其拔擢为一府之望,使之与郗超并称,除了对晚辈的赏识与鼓励外,还有对王珣背后所代表的琅邪王氏的团结。《赏誉》第八“桓宣武《表》云”条及刘注引桓温《平洛表》载其对陈郡谢氏的团结:“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今中州既平,宜时绥定。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神怀挺率,少致人誉,是以入赞百揆,出蕃方司。宜进据洛阳,抚宁黎庶。谓可本官都督司州诸军事。”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平洛之后,上表请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谢尚时任豫州刺史,假若移镇洛阳,将威胁到桓温的北伐领导权。桓温将自己的北伐成果让与谢尚,显是对陈郡谢氏团结的举措。《方正》第五又载其对太原王氏的团结:“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是团结两个家族的一种手段。桓温虽然向王坦之求女不得,且明知是被其父歧视,但也没有因此与太原王氏断交,而是将自己的女儿嫁与坦之之子,由此团结太原王氏。
桓彝在东渡之后便称赞王导为“江左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51页。。盖桓温受其父之影响,积极以参与名士间玄谈的方式称赞不愿与其合作的士族,以谋求当权士族对其的认同。譬如,《容止》第十四称赞谢尚:“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品藻》第九称赞谢安:“桓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容止》第十四称赞王劭及王导:“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凤毛。’”《赏誉》第八称赞王敦:“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赏誉》第八称赞殷浩:“桓公语嘉宾:‘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桓温似乎追慕名士间的玄谈,但其自身之玄谈水平并不高,《言语》第二载:“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余嘉锡先生认为“金华殿之语”就是指“儒生为帝王说书之常谈,非其至也”(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35页。。可见桓温对《礼记》的理解尚停留在儒学水平上,其对事物的审视也衡之以儒家标准。故而刘惔对桓温玄学水平的评价不高。然则桓温为何不惜以浅薄之玄谈水平,参与名士间的玄谈,极力称赞那些高门大族(其中不乏有不与之合作的谢安,有经其废黜的殷浩,还有谋逆作乱的王敦)呢?其原因大概就是为了获得当权士族的认可。
与此同时,桓温注重实务,积极吸纳地方上的人才,提拔寒微子弟。对于地方上的人才,桓温坚持“苟其可用,仇贱必举”的用人原则。《方正》第五载:“刘简作桓宣武别驾,后为东曹参军,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记,简都无言。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宣武亦无怪色。”一般来说,都督府府佐的地位要高于刺史府州吏。(11)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刘简颇因耿直刚烈被桓温一度疏远,但却被桓温由别驾(州吏)调任为东曹参军(府佐),与桓温的关系反而更亲近,可见桓温对于有才能的人是不计前嫌、尽量吸纳的。
凡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桓温都将之纳入自己府中,以备建立功业之需。《任诞》第二十三载:“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悉知山川地形对于行兵作战至关重要,罗友的专长对于桓温的事功建立正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桓温始到荆州便任之为荆州从事。此外,襄阳习凿齿的史学才能非凡,桓温一到襄阳,便重用了习凿齿。(12)吴直雄:《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再考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文学》第四载:“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桓温的表疏写得辞气慷慨,正在于其府中招揽了一批文史人才作为自己的幕佐。(13)林校生:《桓温幕府职能事功剖说》,《北大史学》1997年第4辑。
桓温府内僚佐众多,且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相聚于一府难免会有矛盾,《轻诋》第二十六载:“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士,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袁宏来自著名的文化高族陈郡袁氏,而伏滔门第不高,桓温府中的人经常将袁宏与伏滔并提,由此袁宏便与伏滔产生矛盾。桓温总是想方设法缓和府内矛盾,促成府内的团结。例如,桓温对待幕僚能够宽容爱士,《政事》第三载:“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桓温“以德被江、汉”正是其宽和政治的体现。柯镇昌先生通过分析桓温与幕僚之间的交往,认为桓温与幕僚之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挚友之情,(14)柯镇昌:《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这样的关系自然就使桓氏荆州集团显得和谐融洽。不过,桓温的宽和是以团结为目的的,所以在府内官员欺凌嘲笑其中一位同僚时,桓温不惜将所有嘲笑者一并免官,以促成府中的安定团结。《黜免》第二十八载:“桓公坐有参军椅烝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这样的处罚未免过重,却正向幕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团结互助是桓温府中必须修炼的功课。
总体而言,《世说》中,桓温努力结好高门大族,提携寒门与地方人才,构建团结互助的荆州集团,目的就在于其欲成就青史留名的事功理想。
二、 《世说新语》中桓温的“英雄”悲叹
《世说》中,桓温致力事功却最终不成,英雄落寞,个中原因主要在于受到外在的重重阻碍。
阻力首先来自掌控中央大权的司马昱集团对其北伐的掣肘。司马昱其实是支持北伐的,这从积极经营北伐的庾氏兄弟在康帝死后极力主张立司马昱便可看出。另一方面,由于桓温极力团结士族,司马昱与桓温的关系原本也十分融洽。《言语》第二载:“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正因为与桓温这样亲密的关系,司马昱才在庾翼死后支持以桓温为荆州刺史。然而与此同时,司马昱对桓温的猜忌也逐渐形成,其中关键人物便是刘惔,《晋书》卷七十五《刘惔传》载:“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识鉴》第七注引宋明帝《文章志》与此略同。桓温代替庾翼出刺荆州,朝廷基本没有异议,唯独“居官无官官之事,虑事无事事之心”(15)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五《刘惔传》。的刘惔搅合其中,力阻桓温出镇,破坏司马昱与桓温的团结局面。其后促使司马昱猜忌桓温,搅乱团结局面的,正是这些“永和名士”,而其肇始者便是刘惔。例如,习凿齿原本深受桓温信任,但是见了司马昱之后,立马与桓温反目,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司马昱集团分裂瓦解桓温集团的一场阴谋。《文学》第四载:“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司马昱集团周围的“永和名士”力图破坏内部团结,造成司马昱对桓温的猜忌,其最为严重的便是阻碍桓温北伐。
永和五年(349),石虎病死,后赵大乱,桓温意识到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来临,遂向朝廷上疏北伐。但司马昱却先后派褚裒与殷浩北伐以阻桓温。褚裒和殷浩的北伐相继失败,朝廷才迫于形势将征战之任委与桓温。(16)余世明:《论桓温》,《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尽管如此,司马昱集团也并不是全心支持其北伐,升平三年(359),仍以矜豪傲物的谢万北伐,结果狼狈大败。此外,司马昱集团中的孙绰还阻碍桓温迁都之议,《轻诋》第二十六载:“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永和十二年(356),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经营了几年之后,于隆和元年(362)第三次上疏建议迁都洛阳。其实,迁都可以鼓舞士民人心,给官民以积极进取的心态。桓温频繁地请求朝廷北都洛阳,正反映了桓温欲收复中原、统一华夏的愿望。此前祖逖、庾亮等人汲汲于北伐,所孜孜追求的也正是这一愿望。
其次,来自世族门阀对其政治改革的掣肘。实际上,随着北伐统一事业的推进,对内改革势必要推行。永和年间,随着桓温势力渐大,桓温逐渐受到了来自包括皇帝在内的世家大族越来越强的牵制,并一直持续到桓温去世。《雅量》第六载:“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兴宁二年(364),桓温掌控中央政权之后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一直持续数十年,其中包括并官省职。东晋时期职官众多、机构臃肿的问题已成为人所共识,此前庾亮、王彪之都曾上疏建议并官省职,廷臣对此呼声很高,桓温利用权势强制推行改革,诚为顺应人心之举。(17)胡秋银:《桓温并官省职考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桓温与郗超商议裁撤朝臣,应该就是对这项改革的一次实施。桓温在落实之前,询问了太原王坦之和陈郡谢安的意见,结果遭到两家的反对。而世家大族在桓温执政过程中成为其掣肘,在桓温改革的前几年便已经出现,《赏誉》第八载:“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谢安出任桓温司马,是桓温尽力团结世家大族的结果。然而谢安刚刚出仕,在用人方面便不听从于桓温。其时桓温正准备裁减人事,提高办事效率,却迫于世家大族的压力,只得听任谢安自己安排。
永和二年(346年),桓温“拜表辄行”(18)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页。,出兵伐蜀。其时桓温初临荆州,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19)金仁义:《桓温伐成汉考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言语》第二载桓温在伐蜀途中的感慨:“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面临内有人情异议的牵掣,外有峭壁悬崖的阻碍,其实桓温内心也有一丝如“忠臣孝子难两全”一般的无奈。但为鼓舞军心,虽然叹息,却依旧表现出“要做王尊一样的忠臣直驱成都”的决心。伐蜀最终取得成功,然而,这种成功却为桓温带来更多的羁绊。世家大族及司马昱集团害怕这种“轻易”的成功,联合压制桓温。在这种情况下,桓温三次北伐都没成功,第三次北伐甚至以惨败告终。
世家大族不满于桓温兴宁二年(364)以来主持的一系列改革,故而极力阻碍桓温的北伐。如果说在改革未开始之前进行的两次北伐阻力还不算很大,尚能取得一些成果,那么改革推进之后的第三次北伐,阻力是极其之大的,世族们甚至希望其北伐失败,“以孙盛《阳秋》直书其败观之,则温之败,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之者也。”(20)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60页。桓温大概能感受到来自朝廷内外的阻力,所以在回想自己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北伐事业,不得不有所感慨,《言语》第二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余嘉锡先生考证此条应系于桓温第三次北伐,(2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6页。而此时距桓温为琅玡内史已经三十多年。从金城过淮泗到北方后,桓温再度感慨,《轻诋》第二十六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王衍在西晋末年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不思如何拯救苍生,而只顾保全家门,祖尚玄虚,崇尚清谈,致使国都沦陷,异族践踏中原。桓温登上楼船,眺望中原,想到自己的北伐事业,竟是由于王衍等人清谈亡国所致,于是大发感慨。桓温的感慨不无道理,但西晋灭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必全归咎于王衍。不过袁宏将之归咎于“运自有废兴”,却是一种“天命论”的观点。异族入主中原已经半个多世纪,连袁宏这样随己征战大半生的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事功理想,桓温不得不悲愤以至于发怒。这时的桓温已然是一位内心孤独无知己的迟暮英雄。
三、 《世说新语》重视桓温功业与刘义庆思想的表达
根据张忱石先生《〈世说新语〉人名索引》所统计1630位人物条目,排列前三的分别为谢安125条,桓温113条,王导99条。(2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附录第9-108页。桓温所录条目仅次于谢安,固然与其在东晋朝的军政活跃及其“名气”相关,却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刘义庆对桓温的特别重视。
刘义庆(403—444)是刘道怜次子,早年随诸父征战且历任要职。刘义庆自幼便有很强的事功意识,这是渊源于其家族历史的。其伯父刘裕和叔父刘道规,在东晋末年起兵推翻桓玄的统治,平定各类叛乱,复兴晋室。彭城刘氏在这场恢复晋室的运动中多半立功,刘义庆便诞生于此时。此后十几年间,刘裕对外南征北讨,对内继续土断,逐步稳定了政局,为此后“元嘉之治”奠定基础。(23)朱绍侯:《论刘裕》,《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在这种环境下,刘义庆自幼练习骑马射箭,以期建功立业,收复中原。在其十三岁时,还有幸参加了刘裕一生中最后一次大征讨——北伐后秦。途中留城修庙和彭城大会,文人们歌颂功业,将士们斗志昂扬。这次北伐增强了士族文人现实主义的入世态度,对政治权位的追求和对功业的渴望交织在了一起。(24)陈群:《刘宋建立与士族文人的分化》,《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然而,刘裕死后,刘宋便陷入宗室内斗之中。刘义真由于为刘裕所宠,一度有被立为嗣的可能,加之其文化修养较高,与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相交,共同对抗刘裕顾命集团。(25)王永平:《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景平二年(424),徐羡之等人在宋少帝默许下将刘义真废为庶人。不久,徐羡之等人又废黜少帝,并将少帝和刘义真杀害,迎立刘义隆。刘义隆即位后,非但没有感激辅佐自己上位的辅政大臣,反而在元嘉三年(426),将徐羡之、傅亮诛杀,随即讨杀谢晦。元嘉十三年(436),诛杀最后一位北伐名将檀道济。宋文帝在清除顾命集团之后,起用刘义康执掌朝政。刘义康的执政作风颇为务实,改变了两晋以来的散诞作风。但宋文帝性格猜忌而又多病,且对宗室严加提防。(26)王永平:《刘义康之狱难与元嘉政局之变化》,《学术研究》2014第11期。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覆灭刘义康集团,诛杀刘湛,贬刘义康。表面的元嘉盛世在刘宋宗室内部却暗流汹涌,深藏杀机。
刘义庆为了自保,不得不小心谨慎,寻求机会离开京师,以期有所作为。《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载:“(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在京尹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在京时被宋文帝压制,不敢有太过明显的作为,但是一到荆州,刘义庆便密切关注当时蜀地赵广等人的叛乱和氐王杨难当的叛乱,并且派兵增援。《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二宋文帝元嘉十年及十一年分别载:“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巴东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将二千人救成都。”“临川王义庆遣龙骧将军裴方明将三千人助承之,拔黄金戍而据之。”刘义庆名为都督七州诸军事,实际上对当时蜀和汉中地区的叛乱,并没有总指挥权。此外,刘义庆身边极有可能安排了很多宋文帝的耳目,以监察并分其权。有鉴于此,加之宗室斗争的残酷,刘义庆虽远离京师,雄心壮志,却因功业不成,于是只能“无所作为”。在这种处境下,身在荆州的刘义庆很自然地想到了桓温。桓温处在司马昱集团的猜忌下,仍然有机会进行西征北伐,而自己却被宗室斗争所阻碍。
刘义庆处北府兵逐渐衰微而雍州兵尚未崛起之际,目睹随刘裕起义的北府将领凋零,北伐统一事业连遭挫折。刘裕北伐关中凯旋之后,义熙十三年(417),刘义庆被任命为豫州刺史,镇寿春。寿春为南朝防御北方入侵的军事重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27)宋杰:《寿春在东晋南朝的战略地位》,《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刘义庆以宗室出镇寿春,自然负有重要的防卫边疆及筹备北伐的任务。然而,由于刘裕的猜忌心理,(28)杨恩玉:《刘裕的猜忌心理与用人政策探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在关中安排了王镇恶辅佐刘义真之后,又以沈田子监视王镇恶,导致长安内乱,最终在义熙十四年(418)沦陷。北伐名将王镇恶、沈田子皆死于内难,傅弘之、朱龄石等在抵御赫连勃勃入侵中牺牲。长安收复旋而复失,关中守军和将领死伤殆尽。刘义庆作为前线的主帅,回想起随伐长安时的气势昂扬,对于长安丧败不得不有所感慨和反思。
刘裕代晋之后,刘义庆被征为侍中,参与中央决策。然而景平元年(423),北魏趁刘裕之死掠取河南,攻拔洛阳,刘宋朝廷没有全面的筹备与对策,却陷入与刘义真的宗室内斗之中,以致名将毛德祖在虎牢保卫战中牺牲。北魏的这一次南下,使刘宋欲以河南为根据地向河北挺进的战略从此搁置,此后的北伐仅以收复河南为目标。元嘉三年(426),宋文帝猜忌出镇上游的谢晦,兴兵内战,名将刘粹没有牺牲于北伐战场,却死于此次内战。元嘉七年(430),宋文帝决心收复河南,却又因为猜忌心理,不用檀道济,而派遣无能的到彦之北伐,以致失败,并处决经验丰富的名将竺灵秀。刘义庆作为中央决策集团的一员,虽然对此不负直接责任,但河南的失陷及北伐的惨败,也给其极大震撼与悲愤。然而,元嘉十三年(436),宋文帝因猜忌心理诛杀仅存北府老将檀道济,刘义庆追求的统一大业遭到重挫,《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载:“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名将凋零导致北伐中原的统一事业后继无人,檀道济之死标志着北府兵集团乃至刘宋王朝力量的衰落,此后王玄谟的北伐又以惨败而告终。(29)陈冬冬:《檀道济之死与北府兵集团的衰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而这些名将的凋零又多半与刘宋二帝的猜忌心理有关,刘义庆处凶险无常的元嘉政局之下,除了悲叹于自己的命运,也当对他人的惨烈遭遇有所感慨。在领土渐渐丧失,名将渐渐凋零,统一大业陵替之际,其缅怀桓温,期待一位如桓温一样致力于统一大业、领导北伐收复失地的将领乃是当然之心理。
众所周知,刘裕造宋代晋,不仅是一般的王朝更替,而且意味着寒门武人集团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30)王永平:《刘裕诛戮士族豪族与晋宋社会变革》,《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以武力事功崛起的士族一扫东晋玄谈散诞的风气,逐渐转向务实的作风。在这种风气之下,一些高门士族出身的文人都热衷于建立事功,例如,谢晦、谢灵运等人摒弃“素退”的祖训,积极参与刘宋政权。谢灵运在遭贬斥之际,依旧写成《劝伐河北书》上书宋文帝,以表达对统一大业的向往。刘义庆也向往事功,向往统一大业,但由于元嘉政局的波诡云谲,于是将功业热情转向文史,《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载:“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周一良先生已经指出“世路艰难”暗指元嘉的政治环境恶劣,而“跨马”又是有政治野心的暗语。(3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22页。然则刘氏在政治上失意后,只能将兴趣转向文学,用“立言”的形式来建立自己的事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既然立德与立功对刘义庆来说都难以实现,便退而求其次,以立言的方式造就不朽。《世说》的编撰动机正在于此,而刘义庆瞩目桓温功业的原因也可由此得窥一二。
其实,刘义庆的际遇与桓温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刘义庆与桓温的门第相接近,都不是文化高门;桓温继承了桓彝开创的崇尚事功之家风,(32)金仁义:《桓温伐成汉考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1期。刘义庆也受家族家风的影响,事功观念比较强烈;桓温在追求统一大业的过程中非常努力,却处处掣肘,刘义庆也一样,欲建事功,却生怕被猜忌,只能目睹曾经收复的旧壤寸寸沦陷。元嘉之际,刘义庆以荆州刺史居于上流,目睹桓温旧迹,当无限怀念这位已逝之人。
四、 结语
刘宋正是一个对魏晋以来清谈玄学做总结的时代。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征当时的大儒豫章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并立儒、玄、史、文四学,重新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刘义庆自幼便有对事功的追求,元嘉之际玄学的式微及儒学的重振,给予其一丝功业可成的希望。而宗室内斗相残之极为惨烈,使刘义庆为明哲保身,不得不放弃对现世功业的追求,转而以立言的形式建设自己的事功。刘义庆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这样一部清谈之书。(3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26页。《世说》中的“桓温”毕其一生之精力,稳固江东政权,追求统一大业,然而遭到当时世家大族及司马昱集团的阻碍,最终悲叹功业难成,泣柳金城。这种经历让刘义庆产生共鸣,在刘宋宗室斗争惨烈,收复的旧壤相继失陷,统一大业陵替之际,刘义庆缅怀这位迟暮的北伐英雄,其实是对自身命运艰难、功业难建的悲叹。最终在编撰《世说》的过程中,刘义庆瞩目桓温的功业,似在不经意间造就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英雄形象,而这正是刘义庆期望建功立业、统一中原的反映。因此,表面看来是一部清谈集的《世说》,内中正暗含了刘义庆的事功思想。
(本文系在陈金凤老师指导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