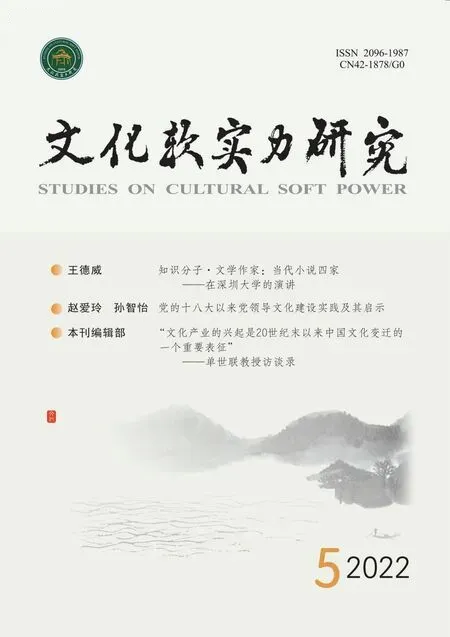“五四”前后学人的佛教观与文化自信问题
姚彬彬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2)
一、“五四”前后学人佛教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所谓“中国近代佛学复兴”这一文化思潮,肇始于晚清,“清代之季,物极而变,识微之士,张皇幼眇,咸以群治之弗整,由于教旨之弗昌……十年以来,手梵文,口大乘者蜂起,彬彬雅雅,不懈益奋,盖学术风气又将一变矣”[1]。其发生契机,是中国学人面临西学东渐之大势,努力开掘传统思想资源,期以维系固有的文化自信。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言,彼时“打破了二千年来儒教独尊的诸子学、佛教乃至其他东西一齐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这正是以堂皇的阵容和传统自负的中国之‘学’,在攻进来的欧洲学术、思想面前不愿屈服,动员和集结了所有能够动员的‘学术’部队,试图进行的彻底抵抗和最后决战,实乃一个壮观而豪华场面”[2]。当时所谓“佛学复兴”,其主要特征是士林逐渐开始重视大乘佛教的哲学义理部分,后来逐渐集中于已成“绝学”的由唐代玄奘系统输入的唯识学及相关的知识论系统因明学上。葛兆光指出,“晚清好佛学的人,几乎都是趋新之士大夫”,他们发现,“要理解西洋思想,原来看上去不大好懂的梵典佛经,倒是一个很好的中介,用已经理解的佛学来理解尚未理解的西学,的确也是一个好办法。比如西洋那种复杂繁琐的逻辑,可以用同样复杂繁琐的因明学来比拟,比如西洋对于人类心理的精细分析,可以用同样分析人类意识的唯识学来理解”[3]。被学界称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平生学术旨趣“行在弥陀,教尊贤首”,但晚年亦逐渐对唯识学发生兴趣,其学术继承人欧阳竟无于1922年在南京开办支那内学院,隐然成为斯学之重镇。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文化思想界的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呼吁“德先生” “赛先生”的思潮蔚然成为潮流,当时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等思想,都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持负面评价。在内学院开办的同一年,由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拟定于4月4日借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年会,于是在3月9日,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通电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呼吁支持。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予支持。3月21日,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位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提出:“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百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4]同年6月,非宗教同盟出版罗章龙编辑的《非宗教论》一书,该书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人撰写的31篇批判宗教的文章。事实上,在1921年前后,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已开始重视和强调反思批判宗教,其会刊《少年中国》在1921年春出版三期“宗教问题号”,其所刊文多数对宗教持负面意见。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在一系列演讲中批判宗教并赞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说:“中国的运气真好”,因为中国远离欧洲,避免了宗教战争的影响;有史以来没有产生过“和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5],希望中国能保持这种没有宗教的文化传统。由少年中国学会所发起的关于宗教的争论,引发广泛社会影响。《新青年》《觉悟》《学衡》《新潮》等一批报刊纷纷载文,形成颇具规模的批判宗教热潮。
由这一背景出发,我们就可理解欧阳竟无何以于1923年10月在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上发表《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其中谓“凡宗教家类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宗教式之信仰为何?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评者是也。佛法异此。无上圣智要由自证得来,是故依自力而不纯仗他力。依人说话,三世佛冤,盲从迷信,是乃不可度者”[6]3云云。另一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佛教僧侣太虚则在1924年因回应“科玄论战”,撰写了《人生观的科学》一文,他认为佛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玄学、哲学或科学,谓“佛教的唯一大事,只是从人的生活渐渐增进以发达人生至其究竟,即是由人乘直接佛乘的一条大乘路”,故认定其为一种“人生观的科学”[7]。这些表明,当时的佛教领袖们试图极力将佛教与“宗教”定义拉开距离。但是,这一努力在当时颇占主流的学人看来,当然只能持一定保留意见,因为佛教无论是其经典还是社会实际存在状态,都客观上包含了一些强调仪式信仰、敬拜神佛和神秘主义的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那套讲“解脱”和“空性”之类的哲理。因此,1938年汤用彤为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作之跋语中所言“佛法,亦宗教,亦哲学”[8]之语,应代表了当时对佛教持中立立场的学人的一般看法。
总之,“五四”前后学人的佛教观,与晚清时士林以“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9]这种认识状况相比,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像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等仍对佛教持有“温情之敬意”,但多数研究佛教的教外学者,都能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并不能简单说他们是在“肯定佛教”还是“否定佛教”。王颂先生近期发表的《五四学人论佛教与中国文化传统》,以“佛教本位”为视角,认定“五四”以降“几位代表学人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胡适、张岱年、任继愈的否定派和陈寅恪、钱穆、汤用彤的肯定派”[10]。王君所论,自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是否可如此简单且非此即彼地划为两条阵线,当可见仁见智。笔者自无意对王君之说提出全面商榷,倒是觉得可借助这一疑问,略阐己见。
二、支那内学院的印度佛教基要主义倾向与学界相关回应
由唐代玄奘自印度亲习并将之系统传入中国的唯识学,在晚清时期,已得到许多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关注,但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此学在中土未得到系统传承,大量经典亡佚,杨仁山晚年通过日本友人南条文雄等人的关系,将玄奘弟子窥基的《因明大疏》《成唯识论述记》,圆测疏解的《解深密经》,遁伦的《瑜伽师地论记》等唯识学早期重要著作,均于日本一一寻回,陆续付梓。到了他的弟子欧阳竟无这里,则彻底将佛学研究的方向转向于此学,欧阳的学生吕澂评价其学:“师之佛学,由杨老居士出。《楞严》、《起信》,伪说流毒千年,老居士料简未纯,至师始毅然屏绝。”[11]欧阳在一开始就基于玄奘所传唯识思想,认定“中国化”佛教宗派华严、天台所据以建立的经典《大乘起信论》有问题,他在1922年撰写的《唯识抉择谈》中认为:“真如缘起之说出于《起信论》。《起信》作者马鸣学出小宗,首宏大乘;过渡时论,义不两牵,谁能信会,故立说粗疏远逊后世,时为之也。”[12]认为《起信》是一部“立说粗疏”的“未了义”佛学典籍。后来他了解到部分日本学者已断定《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伪造之说后,则更加明确了“自天台、贤首等宗兴盛而后,佛法之光愈晦”这一看法,乃至把这种“恶果”归诿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缺陷上:“中国人之思想非常儱侗,对于各种学问皆欠精密之观察;谈及佛法,更多疏漏。在教理上既未曾用过苦功,即凭一己之私见妄事创作。极其究也,著述愈多,错误愈大,比之西方佛、菩萨所说之法,其真伪相去诚不可以道里计也。”[6]36-37自此,他们这一派佛学彻底否定了中国化佛教的合法性,在佛学上走向了唯印度佛教唯识学原教旨是尊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径路。
由于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本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后来的宋明儒学虽然“辟佛”,但实质上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他们的不少影响,因此,内学院佛学里面显然隐含了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即后世与他们认定是“伪学”相关的儒家思想,那自然更加一钱不值了。欧阳竟无在《<尊闻居士集>叙》中未加掩饰地表达这一看法,其谓:“率天下之人,幽锢户牖,终古无见天日之期者,不仁哉,讲学家也!生也,而不知不生;乐也,而终不免有著;一贯也,而终不知两端;中庸也,而不知高明;仁者人也,而不能知天;道其所道,非孔子之道也。吾不敢谤孔,称心而谈:《周易》、《中庸》语焉不详;三藏十二部,曲畅其致。”[13]其所谓“讲学家”即宋明诸儒,更以中土儒门经典较之佛典相差远甚。他的弟子吕澂则在1943年时与熊十力论辩时明确说,宋儒所成立的“本体”等观念,皆“俗见本不足为学”[14]24。
就此而论,内学院的佛学态度,不仅涉及了佛教教内的义理是非之争,他们的结论也间接影响到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价值这一敏感问题。对此,当时倾向“中国文化本位”的学者,其中包括后人所说的“新儒家”学术共同体,及“《学衡》派”同人等,当然注定不可能接受他们的这一判断。就王颂文中提到的那几位先生而言,如汤用彤说:
外来和本地文化的接触,其结果是双方。……因为文化本来有顽固性,所以发生冲突。因为外来文化也须和固有文化适合,故必须双方调和。所以文化思想的移植,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经过以后,外来思想乃在本地生了根,而可发挥很大的作用。……一国的文化思想固然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但是外来文化思想的本身也经过改变,乃能发挥作用。……所以佛教到中国来,经过很大的改变,成为中国的佛教,乃得中国人广泛的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相同相合的能继续发展,而和中国不同不和的则往往昙花一现。比方说中国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等等。天台、华严二宗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故势力较大。法相宗是印度道地货色,虽然有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上,也不能流行很长久。[15]
汤先生的意思无非是说,因为佛教于中国开展,首先要适合中国文化的环境土壤,故而必须出现自发的迁变,才出现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思想学说在传播过程中,注定是不可能永远不生变化地保持其“原教旨”状态的。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则更直接地说:
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足归于消沉竭蹶。近虽有人,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势不得不然也。[16]
“欲然其死灰”者,显然指的正是支那内学院一系的学者,陈寅恪在此直接表达了他不以为然的态度。而王颂文中对陈寅恪此文仅引用了“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一段,就论定陈先生“肯定了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10]。虽然这并未说错,但因为佛教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如果不具体剖析陈寅恪(及其他学者)肯定或否定的是佛教中的哪种学说,就难免有些将问题大而化之了。
当时对内学院冲击最大的一个事件,便是本追随欧阳竟无在内学院学习唯识学的熊十力,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忽一日尽毁其学而“弃佛入儒”了。从1919年到1922年间,熊十力在内学院终日沉潜于佛教经卷研习唯识学法门,欲“追寻玄奘、窥基宣扬之业,从护法诸师上索无著、世亲,悉其渊源,通其脉络”[17]。 后经梁漱溟介绍,熊先生赴北大任教,1923年,北大印行他的《唯识学概论》讲义,分“唯识、诸识、能变、四分、功能、四缘、境识、转识”等八章,约九万余言,基本上依据玄奘所传之本义,忠实于内学院所学。但于是年,他忽盛疑旧学,渐对传统唯识学体系发生不满而欲以修正之,故毁弃前稿,开始发心草创《新唯识论》。此后十年间,熊十力在当时较为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中,与友人林宰平、马一浮、梁漱溟、张东荪、汤用彤、钱穆、蒙文通、张申府诸先生反复切磋、辩难,相互启发。1932年10月,熊著《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在杭州出版。在《新唯识论》中,熊十力反复辨析和反思佛家唯识学的名相与体系,并出己见,揭其理论的诸多两难与不足,返身而归本儒门易理,开阐“体用不二”“翕辟成变”之学说。内学院同人,包括欧阳竟无本人,对于熊十力这一“叛教”之举,当然是十分愤怒的,熊亦由此结下了与内学院学者的恩怨,此后内学院的刘定权、吕澂等,都曾与熊发生过激烈论战。
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虽然自此与内学院学者各趋异路,但一些于佛教保持中立态度的学人倒是对其甚表肯定,蔡元培、马一浮为《新唯识论》作序皆高度评价其哲学造诣,即使专门研究佛学的汤用彤,也与熊十力成了较好的朋友。汤用彤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涉及对鸠摩罗什赠慧远的一首偈颂的诠释,汤著对此全文征引熊十力的解读。据王元化回忆说:“在十力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中,还是以佛学为胜。他可以算得上是‘五四’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和汤用彤先生交谊颇厚,两人都以佛学名家。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引十力先生就鸠摩罗什赠慧远偈所作的诠释。我不知道此文见于十力先生何书,曾请问过他。据他说,这段文字不是引自他的著作,而是应汤先生所请托,为汤先生所写的。从这件事来看,可见汤先生对他的佛学造诣是很器重的。”[14]4但是,王颂在其文《五四学人论佛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却认为:“他对好友熊十力任意阐释佛教义理甚至不惜大肆歪曲的做法也并不赞同。据钱穆回忆,三十年代初他在北大任教时与熊十力、汤用彤和蒙文通交往密切。熊十力当时刚刚发表《新唯识论》,批评乃师欧阳竟无,蒙文通不以为然,一见面就予以驳难。汤用彤当时在北大讲授佛学,‘最称得上是专家’,他却‘独默不语’,只好由钱穆予以缓冲。众所周知,汤用彤曾经接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对印度、西洋、中国的古代哲学都有深厚造诣,但他对熊十力的高谈阔论却不赞一词,其实已经无意间表露了自己的态度。”[10]显然王君认为,汤用彤对熊十力的佛学看法不以为然,但了解汤先生平生为人者显然应该可以看出,这只是他一贯的行事方式,有“口不臧否人物”的晋人之风,故“独默不语”而已。事实上,汤用彤先生在学术思想取向上属“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他们至始至终强调本国固有之传统文化的优长,故汤用彤对于佛教哲学的看法,显然应与熊十力更接近,不可能更倾向于内学院的基本立场。
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后来对内学院佛学有不失中肯的批评意见:
欧阳竟无先生说藏密、禅、净、天台、华严,绝口不谈;又说自台、贤宗兴,佛法之光益晦。藏密、净土,不谈可以。天台、华严、禅,如何可不谈?若谓人力有限,不能全谈,则可。若有贬视,则不可。台、贤宗兴,如何便使佛法之光益晦?而吕秋逸写信给熊先生竟谓天台、华严、禅是俗学。此皆是宗派作祟,不能见中国吸收佛教发展之全程矣。他们说这是力复印度原有之旧。然而佛之教义岂只停于印度原有之唯识宗耶?此亦是浅心狭地之过也。[18]
这一论述,实可视作“后五四”时期“文化本位派”学者对内学院“基要主义”立场的代表性看法。
三、钱穆、冯友兰对“中国化佛教”宗派思想的肯定
钱穆先生的自我定位虽非“新儒家”而为史家,但他“文化本位”的思想立场还是颇为明显的,对于中国化佛教诸宗义理,在其著述中有颇多肯认,尤于禅宗思想再三致意。钱穆曾指出,禅宗之出现,诚中国佛教由出世之观念返于入世之一大思想史转捩,宋明儒学之复兴,最先的契机实始于此[19]160。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慧能《坛经》之要领便是佛教之自性化与人间化,他说:
慧能讲佛法,主要是两句话,即“人性”与“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屏弃一切事。所以他说:“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所以他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说:“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又说:“自性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又生何国?”又说:“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这些却成为佛门中极革命的意见。慧能讲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屏弃世俗,只求心性尘埃不惹,又何碍在人生俗务上再讲些孝弟仁义齐家治国。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20]
钱穆正面表述佛教在中国思想发展脉络中的作用,王颂先生说:“佛教摆脱印度原有的厌世的、神秘的、宗教的色彩,回归入世的、人文的情怀,是钱穆对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定位。”[10]这是比较公允的看法。但是还应该注意到,钱穆平生对于唯识学基本没什么兴趣,他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于南北朝隋唐佛学部分,仅仅论列竺道生与惠能两个专节,他“所以特举此两人者,因其特与佛学之中国化有关”[19]140。由此可见,说钱穆是佛教的“肯定派”虽然是不错的,但“肯定”的部分限于佛教的“中国化”思想。
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与钱穆相当类似,从他最为通行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就可以看到,他对“在中国的佛学”与“中国的佛学”作了明确区分:
“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二者所指的不一定是一回事,即不一定是同义语。因为佛教中有些宗派,规定自己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不发生接触。相宗,又称唯识宗,就是一个例子。……像相宗这样的宗派,都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它们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起作用。“中国的佛学”则不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21]
冯友兰重点考察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哲学传统发生相互影响、能融入中国哲学精神中的中国化佛教。其亦以禅宗为典范,说:“往后我们将会看到,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21]由此可见,冯先生对禅宗这种“中国的佛学”给予相当肯定,而对像唯识学这种“在中国的佛学”显然持保留意见。
四、胡适、张岱年、任继愈论禅宗思想的历史价值
胡适先生平生对禅宗史的研究堪称筚路蓝缕,在敦煌文献、域外文献中开掘新材料,虽然在不少具体问题的结论上未必尽当,但其原创性贡献是学界公认的。当然,他研究禅宗史的初衷,确有揭穿后世僧侣建构“伪史”的动机,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断非认定禅宗思想一无是处。比如他在1934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国禅学的发展》中总结禅宗的方法,归纳为五种:(1)“不说破。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问;要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槃菩提可证”;(2)“疑。其用意在使人自已去想,去体会”;(3)“禅机。普通以为禅机含有神秘性,其实,真正的禅机,不过给你一点暗示。因为不说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已去想”;(4)“行脚。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一顿棒,有时候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5)“悟。从‘不说破’起,到‘桶底脱了’,完全觉悟贯通”[22]59-61。胡适认为以上方法,“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是超越了偶像崇拜信仰的,其中体现独尊自心的理性精神,故总结说:
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绍,崇拜,研究,选择,以致“得意忘象,得鱼忘筌”;最后,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菩提达摩是骗子,十二部经也只能拿来做揩粪纸;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家的禅宗。所以这四百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22]62
这种方法和精神脉络,影响于后世儒家,故“宋明理学的昌明,正是禅学的改进,也可以说是中国古时代宗教的余波”。他还常引用朱熹的诗句为证,认为禅悟境界无非“就是朱熹在吟味下面的诗句时所领略的风光”: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并感叹道:“这样的禅,是不合逻辑、违反理性、超越吾人知性理解的吗?”[22]127——胡适曾言及他与罗素之间的一个公案,足见他对禅宗思想的亲切体认:
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中国,北京有一般学生组织了一个“罗素学术研究会”,请罗素莅会指导。但罗素回来对我说:“今天很失望!”问何以故?他说:“一般青年问我许多问题,如‘George Elior是什么?’‘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几句话作可能的应付。”我说:假如您听过我讲禅学,您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以作回答。罗素先生颇以为然。[22]60-61
胡适先生平生确实对印度的一切思想学说并无好感,也确实认为这些东西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不好的作用,对唯识学也是如此,他曾明确批评过这类学说:
玄奘不满意于中国僧徒的闭门虚造,故舍命留学印度十多年,要想在佛教的发源地去寻出佛教的真意义。不料他到印度的时候,正是印度佛教的烦琐哲学最盛的时候。这时候的新烦琐哲学便是“唯识”的心理学和“因明”的论理学。心理的分析可分到六百六十法,说来头头是道,又有因明学做护身符,和种种无意义的陀罗尼作引诱,于是这种印度烦琐哲学便成了世界思想史上最细密的一大系统。伟大的玄奘投入了这个大蛛网里,逃不出来,便成了唯识宗的信徒与传教士。于是七世纪的中国便成了印度烦琐哲学的大殖民地了。[22]439
他之所以对禅宗思想的历史价值有一定肯认,盖以“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成分最多”[22]16,认为这是彻底中国化了的学说。就此而论,胡适对佛教的基本认识,与倾向“文化本位主义”的陈寅恪、汤用彤、钱穆、冯友兰等,谈不上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只是他的表述方式有时显得有些极端,对于“尊佛”之人,听起来不那么顺耳罢了。
张岱年先生在其青年时代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国哲学大纲》于1935年开始撰写,1937年完成初稿,1943年曾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为讲义,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张岱年著中将宋明儒有关宇宙本根问题探讨的思想脉络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即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其中理气论上承先秦道家之道气二元论,由北宋二程开其先,并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唯心论即“主观唯心论”,张岱年认为其在中国的正式形成当与佛教的“万法唯识”的观念的输入有关,在儒家中由南宋陆九渊及其弟子杨简开其端绪,并由明代王守仁集其大成。显然,虽然他认定佛教“只是中国哲学中的‘客流’”[23]41,但并不是未在中国哲学史上发生过作用。而且,在1980年此书再版时,他在再版序言中也明确承认了:“书中没有讲中国佛学的思想,又基本上以戴震为结束,近代存而不论,也是明显的缺陷。”[23]2而在后来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哲学史”条目时,已补足了这一“缺陷”,他述及禅宗时说:
禅宗的创始人慧能以心净自悟为立论的哲学基础,说:“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若识本心,即是解脱”。这就是见性成佛的顿悟说。慧能提倡成佛的简易法门,使佛教禅宗在唐代后期广泛流行起来。佛教的学说对于宋明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有重要影响。
张先生作为一位信念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哲学中“气论”思想一直比较认同,他所寄望的中国哲学的未来方向,即延续气学传统的唯物论的发展,更具体地说,实指马克思唯物主义(张岱年称之“新唯物论”)于中国的植根和生长。他在青年时代便认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而“唯物与理想之综合,可以说实开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24]。因此,他自然不可能对倾向“唯心”的佛学有过高的评价,但绝非对佛学没有研究,把他简单定性为佛教的“否定派”恐怕也是有些过当的,他的学生方立天先生曾回忆说:
佛教哲学是宗教哲学,有着与一般哲学不同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对它进行内在的、深透的心性体会。这里强调心性体会的重要,也肯定心性体会的可能。我以为这对教外的研究者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记得吾师张岱年先生也曾点化过我:“你研究佛教,可要进去啊。”只有设身处地,虚心体察,深契冥觉,体会贯通,才能理解佛教哲学的真谛和精义。[25]
显然,张岱年对佛教是存在一定“了解之同情”的,我们何以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也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张岱年先生也同样给予“了解之同情”?
任继愈先生早年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曾经较为认同儒学,但在1956年前后,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开始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向熊十力坦陈,熊先生不仅不以为忤,还赞许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26]。他后来所撰写的一系列佛教研究文章,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称之为“凤毛麟角”。
必须注意到,即使是在当年的那种环境下完成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任继愈论及禅宗,虽然出于众所周知的特殊语境,偶尔也有些不失为正面的评价,诸如:
禅宗力图把佛性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每个人的内心,把依靠佛教的经典转向引导人们相信个人的顿悟(内心的神秘启示),把拜佛转向呵佛骂祖,这就埋藏下了毁灭他自己的炸弹。遇到一定的条件,遇到革命的阶级或革命的集团,或者这一武器拿到不满意现实剥削制度人们的手上,它将会沿着另一个方向——佛教教义所反对的方向前进。[27]159
任先生这里所说的“佛教教义所反对的方向”,无非是那种传统的、基要主义式的“教义”。他还指出:
在古代,宗教神学势力笼罩着思想界的条件下,泛神论经常是宗教神学内部的破坏力量。它把神融化于自然界中,否认有所谓超自然的本源西方的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思想家,如布鲁诺、斯宾诺莎都是通过泛神论从宗教神学的迷雾中自己解放出来的。中国的禅宗时代比他们早得多,它不是以新兴的资本主义作为内部推动力量,而是在佛教内部反对贵族僧侣阶级的斗争中出现的,这一派是以世俗地主阶级中不当权派的中小地主阶级作为它的社会基础的,它的主要锋芒指向当权派的豪门贵族、特权阶级。[27]162
在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家中接见任继愈,肯定了他在宗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绩,任继愈对这次谈话作了记录,毛泽东谈到许多对宗教问题的看法,也谈到:“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28]显然,毛主席的那段著名论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9]也是任继愈先生研究佛教的基本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五、结语
研究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就佛教研究而言,若站在“佛教本位”,自然会觉得某些学者的个别论述听起来比较刺耳,某些学者的论述则听起来更容易接受一些,从而会简单划分为对佛教的“肯定派”和“否定派”。但若以更为客观的历史主义视角,充分了解和剖析这些学者的历史语境,以及“佛教”学说本身的复杂多元性,则会发现,问题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往往“肯定”中亦有扬弃的部分,“否定”中也未必没有对其中某些具体内容的肯认。“五四”以降不同学派的学人对佛教的研究显然正是如此。其中,除了内学院一系的印度佛教基要主义者们,其余学人基本上都对禅宗等“中国化佛教”思想表达出一定的肯定态度。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无非与内学院和当代日本“批判佛教”的学人一样,只能不承认汤用彤、冯友兰所说的“中国的佛教”(或“中国的佛学”)的合法性,一切以印度佛教的某种学说为准,恐怕也在无意中陷入了“基要主义”的理论误区中了。
就此而论,汤用彤与胡适在1937年1月18日那次“有趣的对话”也就容易理解了:
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他又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我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我们都大笑。[30]
当然,胡适先生说“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难免确有偏颇,只能看做是一个特殊语境的笑谈,而汤用彤先生所说“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其中表达的是一种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高度自信态度,这不仅透露出对那种“基要主义”者的委婉否定,也是“五四”以降包括文化本位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在内的一切对本国文化(包括“中国化佛教”)富有一定“温情之敬意”学人之思想共识。坚持文化自信,不妄自菲薄、不挟洋自重,更不能陷入基要主义式的非此即彼观念,才是吾人今日研究和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应持有的正确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