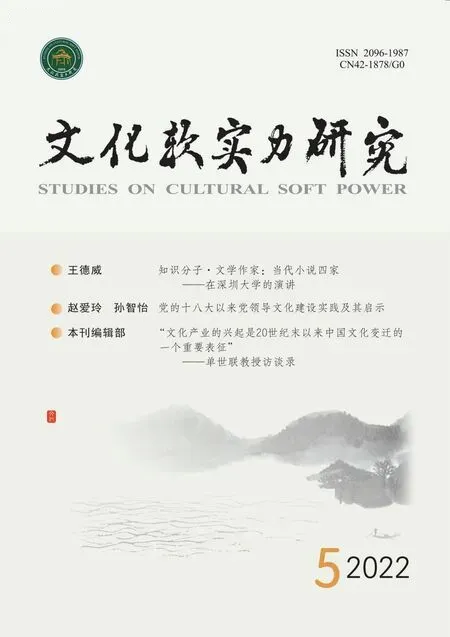知识分子·文学作家:当代小说四家*
——在深圳大学的演讲
王德威
(哈佛大学 1.东亚系;2.比较文学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02138,美国)
本次讲座以四个故事来叩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文学作家?文学如何思想?
这四位当代中文以及华语世界的小说作者融合了个人的生命历练、小说创作以及历史思考,写下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作品有虚构成分,然而更多的是个人生命的记载。在这四位作家中,首先介绍王小波先生(1952—1997),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和思想界最重要的代表人之一。在他1995年过世之后,一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其次是郭松棻先生(1938—2005)。他出身台湾大学外文系,1966年到美国加州大学深造。1970年,在海外发生了“保卫钓鱼岛运动”,这是一个左翼的政治运动。而来自于台湾的郭松棻加入了这个运动,并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
第三位是陈映真先生(1937—2016)。他应该是台湾从1949年到2016年(即陈映真过世的时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左翼思想者、社会活动家及作家。他的生命大起大落,他个人的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未必受到广泛认同。但他对政治献身的热情,以及他把这样的热情导向40年文学创作的漫长历练,使他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学代言者之一。
最后一位最为特别,是黄锦树先生(1967—)。黄锦树是生长在马来西亚的一位华语作家。20世纪80年代末期,黄锦树决定到台湾留学。之后长住台湾,且成为了一位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但是,他写作的冲动以及他对故乡——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的持续关注,直到今天一如既往。
2018年4月,黄锦树获得了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这个奖项,每两年颁赠给两位作家。一位是中国大陆作家,一位是华语世界作家。第一届的获奖者,一位是大家所熟悉的贾平凹先生,另外一位就是黄锦树。
这四位作家有非常不一样的背景,但殊途同归。他们在写作的过程里都不断叩问: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知识?
在我们这个时代,创作或阅读文学的渠道早已多样化、分众化。但这几位作家用最纯粹、最严肃的方式来回应以上问题。在介绍这四位作家之前,我以最简约的方式介绍我的理念架构及进入问题的方法。
首先介绍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他不但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创作者。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萨特面对整个西方(尤其是欧洲)战后破败的社会和人文废墟有感而发。他不满政治的现实,写出了《什么是文学》(WhatIsLiterature? 1947)。萨特问到,在战后百业凋零、民生颓唐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为什么要文学?文学难道还有什么用吗?他的回答是积极的。他认为,文学当然是有用的,文学和政治息息相关。他甚至认为,作者写作文学的构思、过程与目的就是要与自己、与世界沟通,进而引起行动,把思想付诸于历史实践。萨特把文学的定义扩充到一人间境况里,我们思维与行动的契机。
其次介绍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他是上个世纪末英美学界影响力最大的批评家。在他林林总总的贡献中,最为人知的有两方面。第一,他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念。批判西方的思想界从十七八世纪以来虚拟或想象出了一个“东方”,然后把“东方”作为一个研究的学问。“东方学”代表了西方对于“东方”(包括中国、印度、中亚等西方以东的广袤地带)产生的一个大的学问体系。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代表西方殖民、帝国时代的文化霸权心态。尤其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后裔,他对这样的文化霸权感同身受。第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在千禧年之交引起学界极大反响。他问道,“什么是知识分子?”对萨义德来讲:“知识分子是一个流放者,局外人,业余者,也是一位面向权威、运用语言说出真话的作者。而他说出真话的方法是爬梳另类资源,打捞湮没的文件,复原被遗忘或被抛弃的历史。”延伸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可以这么说,知识分子运用文字、想象力,把自己不随俗的、反省的、批判的声音付诸于文学表现,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行动。
第三位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他是一位法国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对他来讲,文学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休闲和消费的文化活动而已。文学本身的阅读、生产、流通的场域,已经充满了政治的动力和张力。一个伟大的文学就是“最民主的文学”。在文学的世界里,生命最大的或最渺小的事情,最无法想象的或最实证的,全都被作家放在同一个文字平台上平等对待。从这个观点来看,比如《红楼梦》就可以是一个朗西埃定义的“民主的文学”。这部作品里的神话与历史、陷溺与度脱、兴盛与衰亡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下,支撑一个信念,那就是——文字,可以包容、调动、思考人生现象。文学,对于朗西埃来讲,是一种“感性的配置”。文学作者能够将生命喜怒哀乐、穿衣吃饭等等不同的感性的资源重新排列组合,以文字展现结果。对于朗西埃来讲,这里有政治的动因,文与政的互动总以最实在的感性方式进行。
最后一位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犹太裔的美国学者,也是一位当代重要的女性学者。阿伦特的体系与上述范例又有不同。对阿伦特来讲,语言不是一个透明的沟通工具而已;语言是人之所以为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里讲得非常非常重。我们处在“后现代”的时代。各种资讯似乎不断地告诉我们,语言其实只是流动的符号而已,一个虚拟的东西。阿伦特提醒我们,语言其实是人对于自己尊严的一个认识和肯定。对她来讲,语言的叙述能量,即你怎么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叙述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叙述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把这个事讲清楚、讲好呢?它是如何安顿我们自己的——“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在历史里担负的责任是什么?” 阿伦特的这个观点,已经和中国传统的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立言”思维相近。言说不是后现代的游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我们对自己负责的开始,就是把自己的言说好好的掌握。
以上都是比较枯燥的理论背景,以下介绍故事。从故事的讲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理解这四位知识分子是怎么以文学来印证他们对生命问题的思考或辩证。
一
首先我介绍大家熟悉的王小波。王小波是20世纪90年代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他逝世前后,大学生对王小波的追捧曾是一个奇妙的现象。王小波1952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曾经短期在北大教书。1980年代后期,他决定要做一个专业的自由写作的作家。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妻子李银河,是中国性学研究的先驱之一。1984年至1988年间,王小波和李银河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深造。当时,他有机会跟从一位名师——许倬云(海外20世纪70—80年代最重要的历史学者之一)。回国后,王小波虽然在经济领域教书,却对文学跃跃欲试。他总是希望写出一点东西。他觉得只有通过“书写”,才可以辩证生命中各种矛盾和遭遇。他选择小说虚构的形式。与此同时,他也写作了许多的杂文和散文,非常有“鲁迅风”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王小波体”,用俚俗轻佻的方式,写着很严肃的东西。王小波在《怀疑三部曲》中写到:“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对于我们这样以正统是尚的文化,突然有一个作家说,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有趣在混沌中存在,当然是惊世骇俗的。
这里看看1992年让王小波成为一个现象的作品——《黄金时代》。王小波在1972年下放时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到1992年发表,整整写了20年。这样的一部作品,想必是惊天动地的传世之书?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其实不然,这部作品其实有浓重的情色成分。故事讲的是一个叫王二的年轻人,下放到农场,遇到一个被污蔑为“破鞋”的女医生。两人被控有了奸情,既然无法证明自己无辜,只好证明自己的“不无辜”。他们将错就错,以人人挞伐却又心向往之的性爱作为对抗压迫的方法,他们放浪形骸、胡天胡地,每次被斗后交出一份又一份的“性爱”报告,然后在众人批判中继续“堕落”,才有更多可供下次批评的材料。受害者和加害者成为了不可思议的同谋:每一次批判和忏悔都比上次更露骨,更刺激,更不可告人,但却更撩人遐思。这正处于“文革”的最高潮。这是那个最狂乱、最荒凉的时代,却也变成了最不可思议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写作了“文革经验”的最特别的一种寓言。他称之为“黄金时代”(当然带有讽刺意味的),也是一个“色情”时代。一切的欲望,一切各种政治的动机,真的假的,都“赤裸裸”晒在太阳底下,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抑的、欲望的群体游戏。在这个定义上,这部作品其实又是本非常荒凉的作品,讲述了人和人之间被剥夺了一切之后,一种无可奈何的“创造性”。
再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例。在“文革”中,王小波最羡慕的是一只个性古怪、充满斗志的猪。猪,本来就是被养来要被杀的被吃的。在被宰之前,这只猪常常做出很多惊人的事情。给它不好的,它不吃;它心情不快乐,就自己爬到房顶上去溜达,独处一段时间。这是一只不合群的猪。王小波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刻意地用色情的语言来反证一个时代的狂躁和虚无。1992—1997年的五年中,他又写作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1997年突然心脏病发作逝世,年仅45岁。王小波成为那一代年轻大学生的偶像,是身后才开始的。他冲破了当时很多思想与生活的禁区,来表达朗西埃所说的——那个时代的生存者的感性以及七情六欲,他们的妄想或是希望,并通过重新的配置与重新的运用文学虚构的方式来见证那个时代的躁动和不安。
二
现在我们再介绍陈映真的故事。陈映真1937年出生在台湾的北部山区三芝乡,来自于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在20世纪50—6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时期(即所谓的白色恐怖时期),陈映真开始对左派革命主义发生兴趣。那时候,西方的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介绍到台湾,他必然也受到影响。同时,他对鲁迅以及左翼的文化开始展开探索。陈映真的作品充满深沉的象征的意味,他描述一个小城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彷徨,白色恐怖氛围下的社会性麻木,充满没有出路的叹息。他早期的作品充满伤感、颓废的元素。1968年,他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因蒋介石过世而特赦。
陈映真归来后对第三世界和阶级问题日益关怀。他认为一个作家的本职不只以写作来取悦读者。一个作家应该是通过写作来挑衅读者,教育读者,甚至鼓动读者。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却给陈映真带来了很多的震撼。曾经,他想象“文革”可能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现代化契机。但“文革”的结束和后果却让他作为一个左翼信仰者,产生何去何从的惶惑。
陈映真1983年的一个故事——《山路》——有着动人的表述。这部作品讲述了四五十年代台湾共产党的一群青年男女艰辛奋斗的过程。这群在右翼势力控制下从事左翼革命工作的青年男女,注定要面对生命中最严酷的考验。故事女主人公蔡千惠出身良好,但因未婚夫向往革命,随之加入地下党。地下党的领导(党小组长),英勇帅气,蔡千惠有了仰慕的感情。在一连串的国民党逮捕左翼革命分子的过程中,蔡千惠的未婚夫和党小组长同时被捕。告密者是蔡千惠的弟弟。蔡千惠的未婚夫被判了终身监禁,而小组长被枪毙。
这时蔡千惠做出一个决定。她伪装成小组长的未婚妻,来到他贫困的老家,以忏悔救赎的心立意帮助这个家庭度过难关。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传奇:一个少女,伪装成另一个人的未婚妻,自我牺牲,协助小组长家庭走向小康,最后成为中产阶级。这个家庭的子弟们长大了,对这个“大嫂”也都很孝顺。故事的高潮是,已经老去了的蔡千惠,有一天很舒服地坐在台北的位于高级地段的家中,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个叫黄贞柏的政治犯终于被假释出狱了。这个叫黄贞柏的政治犯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她真正以身相许的未婚夫。
故事的女主角蔡千惠产生了难以自拔的罪疚感。她觉得自己有罪,背叛了自己的未婚夫。而她认为自己更大的背叛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的生命里,让李家(小组长的家)从一穷二白,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中产阶级,被所谓的资本主义所驯化。她不但背叛了她所爱之人,甚至也背叛了她所愿意相信的革命理想。但这个革命理想原来就是由一个浪漫的寄托——蔡千惠对小组长的暗恋——所转嫁产生的一个理想。
故事的最高潮,蔡千惠看到未婚夫出狱消息后,不知道为什么,失去生存意志。她茶饭不思,被送到医院里,一点一点地萎缩而死。弥留时,她写了一封信给多年未见的未婚夫。她叙述自己一生为革命理想(转嫁的革命理想)的牺牲,最后幽幽问到:“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不,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更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试想,1983年的台湾,居然有一个叫做陈映真的作者,用女性的口吻来回顾台湾共产党所来之路,叩问自己所坚信的革命如何在后革命的现实下遭到严酷考验;还有革命的成败所带来的后果及困惑。这是一个非常真诚而且大胆的作品。这就是所谓的《山路》三部曲的一部。这部作品在大陆受到很多批评家的讨论。陈映真的左翼思想要何去何从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也正因如此,我以为陈映真可以视为当代左翼文学创作者中最诚恳、最真实的一位作家。他不惧怕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挑战,坚持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2006年,陈映真选择了永远地回到中国大陆。2016年,逝世于北京。
今天在台湾,陈映真是一个完全被抹消的名字。但不论立场,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陈映真写作、思考的方式,都深深让我们感动:原来文学还可以这样写,还可以强烈带出一种阅读和思考的冲动,让你不断地去询问他为什么是这样的。还有(陈映真)做出自己决定后,仍然一步一步走向个人的历史选择,死而后已。
三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郭松棻的故事。郭松棻也是台湾人。他来自于台湾台北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家族。他的父亲是郭雪湖,曾经是日据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郭松棻出生于1938年,1958年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后转外文系。他热爱文学与思想,喜欢萨特存在主义,典型的上个世纪中的台湾“文青型”学生。郭松棻大学期间参与很多实验电影、剧场活动,也是台湾最早介绍并批判萨特思想的作者。1966年郭松棻赴美深造比较文学。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顺利进入博士班,完全可以循规蹈矩,获得学位,留在美国,安居乐业。
但郭松棻有一颗躁动的心。1970年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在台湾和美国华裔留学生圈内爆发。当时美国主张将钓鱼岛归予日本,引起海内外知识青年抗议。钓鱼岛虽然面积不大,但因历代版图归属和海底油藏等多种原因,引起东亚地缘政治震动。“保卫钓鱼岛运动”牵涉许多留美菁英分子,伯克利又是美国校园“民主圣地”,时逢越战风潮,各种抗议此起彼落。当时台湾留学生中有许多在离台前已经受到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启发,对国民党不满,向往更民主、更自由的解放。因此,钓鱼岛成为海外青年知识分子爱国运动的引信,一旦爆发,迅速蔓延北美。就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郭松棻、刘大任等一大群当时台湾和香港留美学生(尤其是人文方面最顶尖的一群学生),突然完全向“左”转。原因当然是国家民族主义。为了爱国,刘大任、郭松棻甚至放弃学业,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展开了全美大串连。当时,郭松棻等在美国参与了各种精彩的活动。
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在政治狂热最高潮的时候,这群爱国学生决定效人民公社精神。穿衣吃饭甚至生孩子与否都成为“群众”一起决定的事。当然,台湾国民党政权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认为这些人已经是“叛国者”。美国也把他们放在了黑名单上。1974年,这群学生应邀访中国大陆,这次的访问却让他们无比震撼。这些人充满浪漫情怀,来到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所思所见却让他们的革命梦想迅速瓦解。
“保卫钓鱼岛事件”后,部分核心分子无家可归,被安排进入联合国充当翻译。曾经要改天换地的热血青年,现在在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都——纽约——的联合国里,每人每天从事周而复始的文件翻译工作。这几乎已经有卡夫卡寓言意义了。
但是,对郭松棻这样有思想张力的学者作家,难道革命就这样完了吗?答案不是这么简单。在从中国回到美国之后的那些年,郭松棻进入联合国,韬光养晦,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写下大量文章,持续思考: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左翼……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作品日后都逐渐出土,我们这才了解,真正的左翼,一如既往。
郭松棻其实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哲学思辨、思想上的左派的坚持,而这样的一种坚持,最后导向他对“什么是文学”的重新定义。也许,文学不能带来革命,而革命也未必带来最理想的后果。但是,文学确实砥砺了一个有政治信仰、有思想坚持的作家,继续打磨他的生命目的。这里的文学是要求心血绝对奉献,而又绝不保证成功的。用比较夸张的话说,这样的文学是“嗜血”的,一定要求你的“献身”。这种文学(政治)信念某种程度上像是现代主义美学极致推衍,但任何知道郭松棻政治背景的读者都会理解,他每一部作品都深深埋藏着前半生政治风险和政治奉献的点点滴滴。所以他的作品,像《月印》《月嚎》等,都不容易看,因为有如密码,需要不断拆解。
郭松棻的现象,就像是陈映真的现象一样,它代表了台湾以思想为导向的文学政治的两种极端。陈映真从文学开始,最后走向了为政治的活动,他最后甚至觉得如果不回到中国的土地上,他无以完成一生的志业。而郭松棻经历早年政治狂飙,最后选择自我流放在海外,闭关在他那个狭小的联合国办公室里、家中的书斋里,一个字一个字地不断地去书写,并“重写”(他重写的功夫是非常惊人的),一生魂牵梦萦的革命理想和问题。他用文字的方式再思考,再辩证,再书写。政治在这里不是表面的你是哪一个党派哪一个信仰,政治就是书写行为的本身。在这里,他似乎完全地和世界断绝关系。但在另外一方面,他内心澎湃的血脉,却是无比的汹涌。2005年,他因为中风脑溢血突然去世。
四
最后是黄锦树的故事。黄锦树来自于马来西亚,是移居到东南亚的第三代华人。过去一百五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已经成为传奇。他们漂洋过海来到马来半岛,什么都可以放弃,不能够放弃的是自己的文字,不能放弃的是自己在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向往和执着。所以想象中的中国也许不是政治地理的那个中国,但却是一个宗族的中国,文化的中国。
黄锦树也是充满了纠结的一个作家。一方面,他已经是一个外国人——他是马来西亚人(现在已在台湾定居)。马来西亚是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华裔,不能再说他是法理上的中国人,而是华人。但另一方面,这些华人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执着,可能比你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到吉隆坡,尤其到槟城,我们会见证到非常特别的一个族群文化的生态。
马来半岛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成为英属殖民地,二战的时候被日本人所占领。战后,英国人希望重新拿回这个地方。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殖民势力在全球退潮,1958年马来亚联邦宣告独立。居住在马来半岛的华人到今天约有700多万,占目前马来西亚人口的1/4;而在二战以前比例更高。面对英国殖民势力,面对当地土著的不友善,华人曾经向往成立以华人为主的政治群体。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任总督,为了防堵当时正在萌芽的“马共”活动(“马共”里有大量的华人),实行了新村政策。新村是什么呢?就是英国殖民势力强制大批华人迁徙居住在特定区域,用篱笆、铁栏杆围着,防止他们和“马共”分子接触。现在很少有人再提到20世纪50—60年代“马共”的活动。对于黄锦树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已。因为,曾经有一个时代,拥有大量华人的“马共”有他们的革命梦想。时过境迁,马来西亚华人要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黄锦树的《鱼骸》写于1996年,是华语世界最脍炙人口的名作之一。故事发生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求学,最后留在台湾生活。这位年轻教师专长甲骨文,行动孤独而诡秘,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也不回家。到了深更半夜,这个老师鬼鬼祟祟地来到台大校园里的醉月湖边。他不是赏月,而是抓了湖畔乌龟,带回办公室,宰杀乌龟,处理内脏,然后将龟壳洗净,放在小酒精炉上慢慢烧烤,直到听到“扑”的声音。3000年前,巫师用龟壳占卜时,就是在火上烧烤龟壳,待龟壳裂开以后,按照裂缝来卜算命运吉凶。原来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台大中文系年轻甲骨文教师,每晚上就在办公室里执行三千年以前的占卜仪式。
你正觉得这个故事恐怖、荒谬的时候,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原来这个故事有另外一层情节:年轻的男教师曾有一个哥哥。哥哥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厉行“新村”运动时,参加了“马共”,退入丛林,最后失踪了。多少年后,这个弟弟都在想着:当年如果随着我的哥哥进入了丛林,我今天到哪里去了呢?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哥哥。他好几次回到马来西亚的丛林里,想要找寻失踪的哥哥。有一天,泅泳一处湖泊深处(也就是曾经发生大规模“剿共”的地点),他居然摸到了一个骸骨。那是鱼的骸骨?还是人的骸骨?就在此时,年轻教师似乎了解(也愿意相信),那是亡兄最后的命运。几十年后,兄弟在这里相遇了。他把骸骨的一块带回台湾,朝夕摩挲。每当有学生来问起,老师淡淡回答:“那不过只是鱼的骨头而已”。
“鱼骸”的“鱼”字是有双义的,始是鱼的骨头,也是剩余的残骸。一切俱往矣,到了20世纪末,一个漂流在台湾的“马华”青年,仍然做着半个世纪以前的残梦。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也明确点出一代海外华人,在政治、历史与个人生命的抉择之间,不断选择出路,最后难以为继的僵局。而这个僵局,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找到另外一个想象的、虚构的、跳跃的出路。所以,我用这个故事作为我今天讲座的结束。
五
结束讲座,我要提出什么是我心目中的文学?我们现在谈文学太多时候都是局限在一个专业科目的定义下的文学,而这种文学不过就是诗歌、戏曲、小说、散文等文类?而今天当文学老师、学者在哀叹着文学越来越衰时,我却要说,“文”学在中国的整个广义的传统里,其实不应该被局限在这样一个狭隘的学科定义里。
1902年,慈禧太后号召京师大学堂作出学制改革。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所熟悉的“文学”这个词,其实是1902年以后的发明,也不过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以前的“文”,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含义,请容我在这里做个说明。这个“文”,最开始是指大自然(包括生物、动物、人,运动留下来的各种痕迹),像鸟走路的脚走在地上所留下的痕迹,或斑斓的兽皮鸟羽形成的印记,人为制作所留下的装饰图样……从痕迹、印记,到后来变成装饰(所有装饰的行为的总称)。“文艺”这个观点,是在汉代才真正的出现。那么用“文”来作为一种美的写作的方式,其实出现的时间已经是到了汉代。到了汉代和六朝的时候,“文”逐渐成为“知识”的代名词,延伸到文化、文明。天文地理,天文、地文、人文……而“文”化而广之,也成为所谓气质教育、气质培养的代名词。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谈文学,必须要把对“文”的看法放大,才能了解“文学”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它不再是狭隘的审美的文学而已。
最后,我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说明知识分子进入“文学”的三种不同的路径。
第一个是梁启超(1873—1927)。“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他认为,文学完全可以充分地展现他的政治力量。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世道人心。这样的“文”鼓舞民心士气。它充分的展现了“文”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相互连带的互动的正面的关系。
第二个是刘鹗(1857—1909),即《老残游记》的作者。他认为,“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这里的“文”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启发民心民智的一个启蒙的工具,“文”也是一个抒情、明志的方法,“文”可能是一种可泣可笑的形式,用来表达我们对于一个时代各种各样感怀的一种方法。所以相对于第一个启蒙,这可能是一种抒情的、用情感性的方式来说明的文学的观点。
第三个,我认为还有一种文学的姿态,那就是鲁迅(1881—1936)的姿态。“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夜颂》)一个真正的文人,他不只是看到光亮的、清楚的、启蒙的世界上的文明。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家不再只是简单地表达个人对时代的感怀、情绪而已。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家应该有强烈的辨别、批判能力,有洞察明暗的审视各种各样“文”的能力。这是一种鉴赏力,一种判断力,也是一种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当一切看起来黝黑的时候,“文”似乎隐而不显,在黑暗里,你怎么能看到“文”呢?鲁迅教导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真正有批判力和洞识力的知识分子作家“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有这样的一种洞识和洞察的眼光,看到了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黑暗,然后做出他个人分辨是非的能力,这是一种知识分子作家的传承,以此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