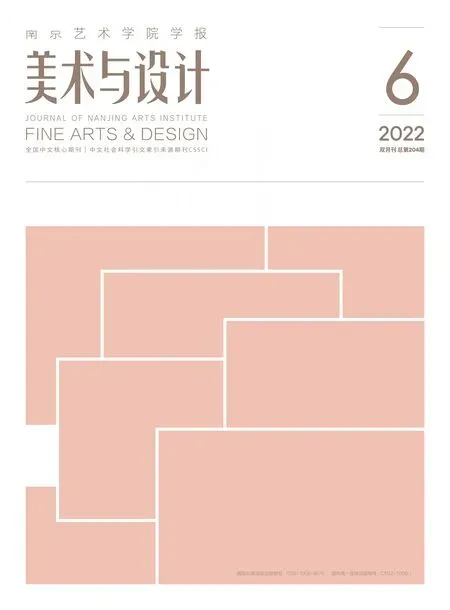书画著录的发端与早期文献考略①
丁薇薇(上海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234)
作为中国特有的书画典籍之一——著录,是书学、画学文献的重要组成,其发端久已不可确考。关于最早的书画著录,近代以来诸家持论不一,仍须穷其原委,系统梳理。兹就管见所及,对多家观点加以考辨廓清,并就早期书画著录的编撰特点作出探讨。
一、书画著录的缘起
关于“录”,《广雅·释诂三》释为:“录,记之具也。”颜师古曾注《汉书·董仲舒传》:“录,谓存视也。”有记载、抄录,登记以便查存之意;也指记载物的名称,记载言行或事物的簿籍、书册等意。“目”有指要目、条目、目录之意,“目录”则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书名、篇名及其叙录。“著”有撰述、写书之意,“著录”泛指记录、记载,亦指以书名列入目录,登记在簿籍上。
书画著录的形成和发展与目录学的研究与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典籍卷帙浩繁,目录学著作对于了解历代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功用显著。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是中国目录分类的萌芽阶段,两汉时期创立了具体使用的文献目录体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各类官私书目数量甚多,至隋唐出现了许多文献目录重要的分类原则与方法。历代公私藏家亦将书画整理次第,编次目录,使其有所归属。传统书画著录则特指以文字记录书画、碑帖等原迹,根据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编制文献目录,成为提供作品信息的目录性书籍。
我国书画虽肇始甚早,但开始兴盛要到秦汉之时。六朝时期北方政权林立、战争频仍,社会遭受严重破坏,而相对安定的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书画艺术领域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有关于绘画源流与兴废的记载,记叙了秦汉以来书画、图书、古物之聚散过程。历代帝王接收前朝所遗书画,并以内府征收为主要途径,蓄积珍图秘玩。书画作品往往汇聚于皇室和雅好书画人家,或颁赐给贵戚。然到艰难之世,又经沉浮散失,王朝的兴起与没落是影响内府书画收藏的重要因素。
书画目录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图书典藏工作的时代背景分不开,“论其先后,仅次于文章志及佛经录”,[1]故书画目录发生较早。每一时代,御府将所藏众多法书名画进行清理,检点、核定藏品数量、名目,为之编目。书画经过审定编第,以便于帝王索阅披览,也成为彰显帝王文治功业的见证。皇室鼎盛,统治者着力于充实和保护皇家藏品,编纂著录正是典藏的重要手段,成为反映法书名画基本信息的最好工具,是对历代名迹收集、鉴别和保存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六朝时期书画著录溯源
1.图目的肇始
书画著录见诸文字记载缘起于何时,可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晋明帝司马绍作传得知,所注曰:“彦远曾见晋帝《毛诗图》,旧目云:羊欣题字。验其迹,乃子敬也。”[2]又据《唐朝名画录》记载:“以晋明帝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之像,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意采掇。”[3]毛诗,指两汉时鲁国人毛亨和赵国人毛苌对《诗》的辑注,即《诗经》。相传卫协画有《毛诗图》系列,唐文宗太和年间,皇帝李昂好古重道,召程修己再次创作《毛诗图》。以《诗经》入画作为宣传儒家礼教的载体,成为辅佐教化、人伦的重要绘画题材而受到推崇。魏晋以来,画本虽少见流传,但历来多有依此进行的绘画创作。
今人谢巍据张彦远所述考证出东晋明帝司马绍有《毛诗图旧目》,其称“旧目”,是与唐文宗时新编《毛诗图目》相区别。他说:“图目非晋明帝亲编,盖于其在位时敕臣下编制。据书名称‘图目’,至少应著录图名、秩卷、绘者姓名三项,又有王献之(或羊欣)题字,可说画录大要已备。”[4]13盖司马绍《毛诗图目》据《毛诗》三百篇分别由其本人和卫协等多人写绘之后予以编目而成,惜已散佚。东晋时编目法已较前完善,《毛诗图目》以目录性方式编写而成,可知图目之书在东晋已开端绪。
2.南朝书目、画目推考
关于著录的源头,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著录类文献中列入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视为现存最早的法书著录。[5]192《论书表》见存于张彦远辑录的《法书要录》卷二,虞龢奉诏命参与共同搜访东晋“二王”书迹,并对内府秘藏法书作品进行系统整理,工作完成之时,即泰始六年(470)写了奏章《论书表》上呈宋明帝以作汇报。《论书表》全篇评论了“二王”的书法造诣和遗闻雅事;论及东晋以及宋宗室的收藏与遗失;记录了伪造“二王”书迹的手段;品题宫中古今秘藏,以及奉命寻访、征集到的法书妙迹,并记录了“二王”等各家书作的材质、卷数、装潢等,且分以品级;对明帝诏令改进御用文房用具也有介绍,涉及书迹品评、收藏、作伪与鉴定。“表”即“奏表”,又称表文,是古代臣属向君王上书陈情言事的奏折或书信,语言往往谦恭而情恳意切。其基本特征与以条目、要目作为篇目次序的书画目录有所不同,故《论书表》不宜视为著录体裁。
宋明帝命令臣下整理宫廷收藏,虞龢作为主持人,在《论书表》中道明共同参与鉴定工作的其余三位分别是前将军巢尚之、徐爰子司徒参军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孙奉伯。他又向明帝表明撰写有书目:“今新装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又羊欣书目六卷,钟、张等书目一卷,文字之部备矣。”[6]从中抉出所编书目,有“二王”《镇书定目》《羊欣书目》《钟、张等书目》,很有可能是由参与内府收藏整理的几位鉴定家共同编著而成。因奉诏之故,未加以署名。另据《旧唐书》卷四十六·志第二十六,虞龢有《法书目录》六卷。以上各篇从书名来看,应属法书著录书。惜书目内容均已佚,难以考稽。
宋高祖刘裕所夺东晋桓玄藏画最终落入齐高帝萧道成之手,萧道成将宋内府所藏之画亲加鉴定。张彦远记述:“南齐高帝科其尤精者,录古来名手,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共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馀,旦夕披玩。”[7]可知齐高帝尝命侍臣择古画之精美者辑录自古以来名家,并撰品评文字。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诸家文字》中首列南齐高帝撰《名画集》篇名,殆及此书,说明沿至北宋郭若虚或尚得见,但未详注其内容。《名画集》自此之后似无有传载,直至清代王毓贤《绘事备考》中提及宋僧辨、褚灵石、范惟贤“三人咸工绘事,见于齐高帝《名画集》”。[8]关于《名画集》,今人温肇桐认为是最早的著录,[9]然谢巍考《名画集》为画品著作,而将南朝齐初《名手画录》一卷视为《名画集》之初编画目,最后由萧道成定夺去取,为画录书之较早者。[4]25-26《隋书》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亦著录《名手画录》一卷,未知撰人。《名手画录》与《名画集》二书不同,惜今不存,俟续考。
梁朝继承了自吴、东晋、刘宋、南齐四朝以来所藏弆流传之书籍及书画,梁武帝萧衍能书,雅好图画,其子孙中也多能画,故文物之盛、数量之多,自东吴以来无一王朝能胜过。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诸家文字》征引书目,尚有梁武帝萧衍《昭公录》、亡名氏《僧繇录》等。《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昭公录》“盖画品录之类也”,[10]谢巍考证当为著录所得秘图珍画之名称的画录,“或有曩时之题评,或录有旧日之题赞”,编撰时间大概在萧衍登帝位之前的齐和帝中兴年间(501-502)。[4]31关于《僧繇录》,谢巍又考其为梁武帝长子萧统专记张僧繇画之书,“或有品评,或有论说”。[4]35以上二书循名责实,当为梁时画录书。郭若虚也很可能未寓目原书,仅见前人书目引录。为免失著录,姑列之,以备参考。
另据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其内容列举古画名目,并将所录画目与梁《太清目》进行比较,间分注是梁《太清目》所有,或所不载,有的则标明是为异名,或有作画者记载出入。稽裴氏所据,因知梁武帝太清年间官库藏画撰有图画目录。虽未见《太清目》原文,亦可推断此书为一部画录书,应是萧衍下诏编制,贞观时期尚存。今人徐邦达认为最早的著录见于南朝梁代《太清楼书画目》,[11]此书名未见著录,应有误,其所指与《太清目》疑为一书。考隋以前古画,《太清目》颇可借资。且从《贞观公私画录》可推测《太清目》所载既有真迹,也有摹本。《太清目》自裴孝源之后皆不见著录,盖已佚失。据胡璩《谭宾录》云:“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令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12]推测是书为梁武帝时善丹青的朝臣编纂,著录与品评二体兼备,成为画品录。
关于法书著录,《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齐梁间“为法书目录者不止一家”。[13]检索史料可知大概,如官员殷钧曾校订秘书阁四部书,重新编排目录,《梁书》中称其“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14]即另外编定法书类别和目录,惜不知篇名。又如,据唐人窦臮《述书赋·下》所注,得知傅昭撰《法书目录》。
梁朝亡后,虽其所藏法书名画有被梁元帝焚烧者,馀者为西魏掠夺,亦不乏散落于民间之书画,至陈文帝肆意搜求,秘阁中仍蓄有名品。据《隋书》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有《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一卷。此书名不似后世通用“名画”与“法书”并称,而将“图书”与“法书”并列。是书不见宋以来诸家书目著录,似已佚失。
三、隋唐五代书画著录考析
1.隋、唐法书著录
隋代在建朝之初便着手收集书画,内府所蓄图画书籍除继承北周收藏以外,隋文帝杨坚平陈之后又得其图籍。据《隋书》所记:“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谴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①《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作 “宝迹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7.藏古画。”[15]隋朝历史虽短,但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且隋炀帝杨广善属文,工丹青,能草书,“二台”所蓄法书名画可供其赏鉴。隋朝所聚既多,必有目录,然所载不详。窦臮《述书赋·下》有载:“隋蜀王府司马姚最撰《名书录》。”[16]姚最其人,梁元帝时期曾受命整理画卷,撰有《续画品》。《名书录》很可能是其入隋后奉敕整理书迹而为,但未见流传。
隋亡后,内府藏品散佚于外。唐高祖李渊所获前朝书画藏品一律收入御府,为皇家收藏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雅好文艺,尤偏好书法,登基不久发动宫廷内外搜集整理王羲之和其他魏晋名家真迹。太宗内府及其后帝王在书画收藏、鉴识与管理上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其一,内府收藏承继了前代真迹与伪作,虞世南、魏征、褚遂良等鉴识人负责书迹真伪鉴定。其二,唐太宗昭令搨书人摹拓王羲之书作可靠者,临写、钩摹众多内府法书,用来保存或赏赐皇族和近侍大臣,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其三,使用帝王年号作为内府藏品递藏和鉴赏印鉴,历朝跋尾押署也有所变化,不同时代不断改进内府贮藏法书名画的方法,确立褾装制度。
经过大量搜求与系统整理,唐内府收藏得以充实,法书尤为富藏。唐代的法书著录则藉由张彦远《法书要录》保留于世。张彦远为唐僖宗乾符前后人,出身宰相世家,官左仆射补阙、祠部员外郎、大理寺卿,由于家学渊源而致力于书画研究,其编撰《法书要录》作为丛纂体例,辑录了从东汉至唐元和年间的书法理论著述三十九种,采辑书目颇丰。
《法书要录》卷三中载有《右军书目》,是褚遂良为内府编纂的官方目录。此目录以书体为基本分类,分别著录了王羲之正书五卷四十帖、行书五十八卷书目,书目每卷标题书作篇目、行数,或每帖首尾句和所书与的对象等,其中如《乐毅论》《黄庭经》,以及《东方朔赞》因单篇内容较多而自成一卷;较为简短的尺牍等则数帖合为一卷。其大致内容如:“正书都五卷(共四十帖)第一,乐毅论。(四十四行,书付官奴)。第二,黄庭经。(六十行,与山阴道士)。……行书都五十八卷 第一,永和九年。(二十八行,《兰亭序》)。缠利害。(二十二行)。”[17]88-89此书目录于贞观年间,为“临写之际便录出”,[17]99与唐初史目相类,也证实了褚遂良摹写内府收藏王羲之法书确有其事。褚遂良作为负责甄别内库法书真伪之人,书迹的编目工作由他完成也在情理之中。从体例上看,《右军书目》为传世王羲之法书目录最早者,也是保存至今最早的官方法书目录。
《法书要录》卷三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武平一唐中宗时官修文馆学士,记载了有机会见到的贞观内府收藏,记“二王”书帖之聚散颇详,内容应是以鉴藏为主,兼有著录。从其中所记“豫州刺史东海徐公峤之季子浩,并有献之之妙,待诏金门,家多法书,见诧斯题,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后”[18]116来看,徐氏私家法书目录虽未见载,此篇很可能是武平一为徐氏家藏法书编目作序。《法书要录》卷四有韦述《叙书录》一文,叙录开元时“二王”“二张”法书真迹事。《法书要录》卷四收录张怀瓘于唐肃宗乾元三年(760)所撰《二王等书录》,亦记“二王”书迹之聚散,并及梁元帝毁图书。《法书要录》卷三又收入徐浩建中四年(783)所撰《古迹记》,述唐太宗时收罗“二王”法书之盛及武后时之散失,继述唐玄宗以后再聚再散情形。文中自称臣,是本为表进之文。《法书要录》卷四卢元卿《法书录》,自叙于元和三年(808)整理内府收藏法书,记王廙、齐高帝、王羲之法书装裱印记及跋尾。
上文诸篇皆唐时人,而所记若一,当属可信,亦可检阅“二王”法书流传概况。在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六中,将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古迹记》、张怀瓘《二王书录》、②《法书要录》卷四作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唐)张彦远.法书要录[G].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146.韦述《叙书录》、卢玄卿③《法书要录》卷四作 “卢元卿”。(唐)张彦远.法书要录[G].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167.《法书录》,以及南朝宋虞龢《论书表》,共6篇,均划分归为“记事”著录。[5]192-193可以发现,这些书作体例系用记事的文体,涉及书法品评、书迹搜访、名迹流传、书法作伪、鉴藏品式、装裱等,具有叙事意义和夹叙夹议的特色。这些法书论著是具有记传性质的书学史籍,旨在记叙史事,文体上兼有传记、记录、品第的性质,与一般之书名目录、画名目录相区别。因此,余绍宋将之归类为著录的观点仍值得进一步商榷。
此外,《法书要录》卷十为《右军书记》 《大令书语》,为张彦远本人录王羲之、王献之书作文字内容,并作了较为细致的诠注,二书应属法书著录性质。《右军书记》录王羲之法帖释文如《十七帖》《兰亭序》等四百六十多帖,可资对王羲之书迹流传及其事迹的考稽,也可见唐太宗大力倡导王羲之书法,一时蔚然成风;但《大令书语》仅录王献之书语二十条不到,贬抑显而易见。此时,晋宋人更重王献之的时代审美情趣产生了转向。
从留存于世的唐人书画文献来看,唐贞观年间鉴藏风气鼎盛,内府收集的法书名画在武则天和中宗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开始向外流散。之后唐玄宗李隆基设置的集贤院负责搜访“二王”法书和摹制事宜。至安史之乱,内库法书皆散失。唐肃宗李亨以后内府收藏数量寥寥,遂任命徐浩为搜访书画使收集“二王”法书,又任命御史集贤直学士史惟则奉使访求书画。到唐德宗李适、唐宪宗李纯时代,皇家内府收藏已远不及贞观、开元之盛期。褚遂良《右军书目》、张彦远《右军书记》《大令书语》作为法书著录,可与虞龢《论书表》、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徐浩《古迹记》等文献互为参证,可知唐时“二王”书迹之显晦存亡。
2.唐代存世与散佚画录
贞观时御府所藏书画甚多,唐太宗遂命臣下编纂著录,以见其文治之绩。就目前所存的著录来看,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绘画著录。余绍宋认为“是编为著录名画之祖”“考隋以前古画名目者莫古于是。是亦鉴赏家之祖本矣”,[5]256-257并总结道:“著录之事肇自李唐,褚氏《书目》、裴氏《画史》,其滥觞也。”[19]美术史学者大都采其说,然著录书画目录之书,非始于唐,早于唐代的书录、画录不止一二,惜未传世。
裴孝源,初唐贞观时期人,活动于唐太宗、高宗时期,曾官中书舍人,其生卒和生平事迹不详。所著《贞观公私画录》一称《贞观公私画史》,①是书题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卷三夹注中云“裴孝源《画录》”,《图画见闻志》《益州名画录》等作“《公私画录》”,《宋史》作“《贞观公私画录》”。明清以来,《国史经籍志》《弇州四部丛稿》《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四库全书》等众多典籍中将 “录”改为 “史”,《贞观公私画史》题名沿用至今。从卷首贞观十三年(639)八月自序来看,唐太宗之弟汉王李元昌命其辑录,记录亲眼所见唐太宗一朝公私所藏,著录了自魏少帝曹髦至贞观十三年(639)秘府官本和搜访于私家所蓄画作逾二百九十卷,并录佛寺画壁47处。所谓“又集新录官库画”,[20]指在内府藏画目录的基础上,加上所收集的流散于私家和佛寺画目。参看徐浩《古迹记》中所述:“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后。”[18]119此外,张怀瓘《二王等书录》等文献中也有关于贞观十三年(639)内府鉴藏相关记载。可知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发动了大型的宫廷典藏活动,着力于内府书画的搜购、点校与汇编,此年是唐内府书画编目的一个重要时间。或可推测,褚遂良临写之际编录的《右军书目》与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成书时间也相距不远。
裴孝源因了解公私收藏与寺庙壁画,故能著成此书。《贞观公私画录》所录卷轴作品,前列画名,偶记出处、作品尺寸,后列卷数、画家、有无题跋印记、真迹或摹本等,并标注有否为梁《太清目》所载。记录作品不依时代为序,而按品格高下列为先后,画家始于陆探微、魏少帝、卫协、晋明帝,终于杨契丹、展子虔、孙尚子、王廙,并有无名画作。所录诸迹俱称卷,唐以前藏品的装裱品式似为横式卷轴。书中虽文字扼要,仍是了解、掌握贞观年间御府和私家所蓄古画迹状况及存画数量的参照,也是现存考古画名目的祖本。
谢巍据元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著录唐代高士廉等奉诏纂修《贞观御府书画谱》,认为此著录或称《贞观御府书画录》,成书时间早于《贞观公私画录》,为秘府所编者,即贞观十三年前之“旧录”。《贞观公私画录》则为新录,亦收佛寺及私家所蓄,“其目的则为传播,故其书得以传世。而《贞观御府书画谱》收入《文思博要》,是为御览之秘籍,后世散出,方知一二”。[4]49《贞观御府书画谱》未见唐、宋诸家书目著录,已罕见流传人间,于元代突然出现,却是史籍中关于贞观内府书画的又一记载,惜已难窥是书内容。此前书画目录内容皆系单独法书之目录与图画之目录,《贞观御府书画谱》可谓第一部官藏书画合编目录。
唐代的画录还有《齐梁画目录》一卷,著录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又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九·经籍考五十六,互为参证,可知此篇为窦蒙之子窦泉所录。因全文不详,有俟旁证。另据《太平御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明书》等征引书目,尚有佚名《古今名画录》,盖记录自晋以来传世之名画及前朝的摹本与仿作等,也包括了盛唐时诸名家所绘。再据南宋郑樵《通志》卷六十九·艺文略第七,著录有张又新《画总载》一卷,张又新约活动于唐宪宗元和前后,曾任秘书监秘书郎,盖执掌图籍之时编成此书,惜后世未有传载。《新唐书》列有唐御府所藏自初唐至太和初之诸家画目,《佩文斋书画谱》中将之列为《唐画目》,画目数量已远不到百件。相比之下,唐前期内府文化盛况到唐中后期因战争和社会动荡使内府收藏渐趋衰落。在内府收藏流散的过程中,私家收藏对保存法书名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南唐内府画目
五代十国时期偏安于江南的南唐王朝,远离北方的兵乱,虽国运短暂,但在中原艺术趋于沉寂之时,南唐却是书画艺术发达的地区。南唐文风鼎盛,皇室对于文物、文房四宝极为推崇,重视图书和法书名画的收集。南唐三代帝王有着较好的艺术修养,烈祖李昪曾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21]中祖李璟亦广泛搜求,至后主李煜,雅尚图书,据《江南别录》记载:“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22]南唐有专门的内府文房机构及专职人员负责书画整理和鉴定,授以文房副使、文房检点、文房官检校、文房押司官等官职,也有专门的皇室收藏玺印用于内府收藏书画的钤盖。[23]跋尾押署由御府文房机构鉴定人员参与,李后主亦亲题画人姓名,或押字,或题写诗词。南唐从皇室到朝臣、文人士大夫中不乏善品评、精鉴赏者,内府有收藏书画的目录也在情理之中。
唐末五代书画典籍无多,现知有关绘画的著述有《江南画录》《江南画录拾遗》《广画新集》等,惜原书遗佚。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诸家文字》列有亡名氏《梁朝画目》,谢巍据明朱寿镛《画法大成》卷一《画史》篇著录,考出《梁朝画目》作者为南唐后主李煜,所记为南唐内府所藏,惜今不详。[4]98-99另据北宋邵博《闻见后录》记述:“予收南唐李侯《閤中集》第九十一卷画目。”[24]通过行文可知《閤中集》除画题、作者外,又分上品九十五种、中品三十三种、下品一百三十九种三个等级来品评画作,推测《閤中集》很可能是南唐内府收藏画目清单,收藏规格与画目编纂体例可见一斑。《閤中集》至北宋仅存一卷,后有李公麟跋,其中所录名品多流散于士大夫家,故于北宋时期加注有藏处。其余各卷不知详情,第九十一卷今尚未见全文,从体例来看,应为画品与画目的结合。
四、早期书画著录的特征
1.书画著录体裁初具雏形
中国早期画学文献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谢赫《画品》、庾肩吾《书品》、姚最《续画品》旨在评定书家、画家,兼论及作品。从魏晋至唐五代,除书论、画论之作外,书画品评风气十分盛行。之后逐渐兴起中国画学中的“史传”之书,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是一部评论唐代画家及其作品的断代画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虽有关于古代名作的品目、鉴识、收藏,其中如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为记录古来重要绘画目录的专篇,但从画史撰述来看,《历代名画记》的写作往往结合着绘画品评、画家传略和作品著录,是以记史为中心的体例结构,画史、画论、画评三者一体,兼具著录性质。考此期的书学、画学著作,带有序、传、赞、记、录、品之篇名较为流行,也代表了不同的体裁与各自独特的写作体例。但历来有一些题名为“画录”“书录”之书,如彦悰《后画录》、窦蒙《画拾遗录》、佚名《唐朝叙书录》、辛显《益州画录》、佚名《江南画录》等,在内容上为画史、画品或书史、书品性质,与著录书并无关联。
考画编有目录,综合多家之说,以谢巍所考较为可取,著录专书的形成时间可推至东晋,晋明帝司马绍《毛诗图目》为肇始,当为著录之祖,比之南齐《名手画录》和梁《太清目》这两篇已佚失的文献时间更早。南朝一百多年风云,宋、齐、梁、陈四朝更迭,出现了多种书画著录书。南齐虞龢等人所编《法书目录》《二王镇定书目》《羊欣书目》《钟、张等书目》,以及南梁傅昭《法书目录》为较早的书迹著录。自此以后,历代多有书录、画录之作。梁王朝的书画典藏活动较为频繁,如梁武帝及其子分别编有《昭公录》《僧繇录》,从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亦可知梁《太清目》大概,循书名责之以实,《太清目》为早于《贞观公私画录》的绘画著录。南陈时期则记载有《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陈隋之际有姚最《名书录》。以上诸种画目、书目是我国书画著录书之较早者,也是唐代书画著录文本的来源,惜今已不存,无从考见编目体例。
唐代书画文献不仅总结了内府法书名画聚散的历史,也记录了内府收藏的制度,以及私家收藏的经验,如藏品的真伪鉴别、用印、押署、装裱,成为中国书画鉴藏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其中唐五代书画著录的撰写反映了对内府收藏进行甄别、分类、编目等管理工作,是了解内府收藏的重要依据。唐人高士廉等《贞观御府书画谱》、窦泉《齐梁画目录》、佚名《古今名画录》、唐文宗时期《毛诗图目》、张又新《画总载》,以及五代李煜《梁朝画目》《閤中集》等著录亦不传,今已难究其实。早期的绘画著录传者以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为最早,是唐代以著录画迹为重要特点的画学著作。唐代存世专录所见所藏之法书者有褚遂良《右军书目》、张彦远《右军书记》《大令书语》,均是可考的有明确记载的著录。
对现代以来诸家考辨意见加以考索,最早的图画著录始于东晋,其后,南朝、隋、唐、南唐时期书画整理的重要成果就是编制了各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单书目录,这说明每一个朝代对于书画典藏的重视,在整理书画目录方面付出了劳力,也为后世著录的编纂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例。
2.官库书画目录体系初建
目录之作,古皆官书。六朝时始有专类书画目录,内容主要基于内府书画清理、编目与管理,以著录官库书画为主。虽“有从来蓄聚之家,自号图书之府”,[25]但早期有所记载的书画目录多为官纂著录。内府书画编目自晋以来不绝如缕,国泰民安之时,内府收藏占据主体,富而精者多为帝王家之物,远非当时私家所能具备。
历代帝王庋藏法书名画甚为丰赡,但无闲暇亲躬择选,往往委臣下近侍劳之。因而,执掌图籍、广揽帝王府库图书之官员往往肩负此任。故早期的书目、画目等古代帝王著作,虽有自撰者,但大多敕臣编纂,而书名常以帝王之名署之,如司马昭《毛诗图目》、萧衍《昭公录》等。这些书画著录大多系奉敕编撰,或编纂者非一人,故也有不署作者姓氏之情形,因此阙名,如《太清目》。早期书画著录编纂者主体为善鉴藏的臣子,私家收藏中的高手如虞龢、裴孝源、褚遂良、窦蒙、韦述、徐浩、张彦远等因书画技艺或累世收藏,获得了丰富的鉴藏知识,网罗于内府之中从事书画鉴定,他们作为官库书画的鉴识人,有赖于所擅长的专业知识进行编目、鉴别等工作,内府珍藏法书名画才得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保护和管理。
书画著录所言宜可征信,其本质在于实录。在内容上包含了皇室收藏与归纳、卷帙整理、装裱等管理书画的重要史料与信息,是掌握书画基本状况、了解其源流、考辨真伪的门径、依据和辅助。不同的美术史文本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关于美术家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作为画史的撰作与传世,其书写的历史是由写作者个体来完成,个人的美术史观与价值判断是主要因素。而早期的书画著录,是见证人据以客观实录,需确凿可依,其撰述方式较少主观发挥与个人情感因素。
在书画著录发端时期,著录之书几为散失,仅能就书名或留存数篇加以评论。据当时官修目录编制体例,书画著录体裁上多以目录进行编写组织。此时采摭编次书作画作目录篇幅有限,未能具体,可谓书画著录体例的雏形。唐五代及以前的书画著录除著录书目、画目外,组织内容的方式或包括卷帙、作者姓名,或署有时代,或有人物小传、品题,亦未可知。早期书画著录的体裁多书、画分开,不似后世书画同列;著录的内容往往兼有鉴藏,论及装裱皆称卷,应是古人书写、创作和阅览的习惯,由右及左,形式一致;流传的古法书名画,真迹数量渐趋寥寥,也不乏临摹或伪作,这些均彰显出传统书画著录体系初建阶段早期书画著录的特征。
结语
书画著录历史悠久,东晋至隋唐五代时期是著录发展史上的重要开始,惜大多已经散佚,记载缺略。从早期书画著录中可目睹官方收藏之盛衰,令人起今昔之想。对著录之体裁,存其目者据以考证,形成了以作品为中心的体例,奠定了后世书画著录书的撰写观念与方式。书画著录的发展历宋元明清,尚复不少,而内容体例日渐完备。对存世早期书画著录文献进行整理校勘,包括拘以与其他传世法帖名画的互校工作,对于正确征引和了解唐五代以前的书画史、书画鉴藏颇可借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