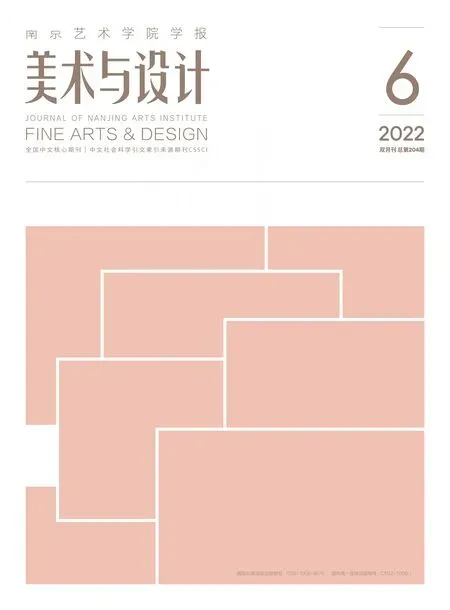贝尔特·莫里索的人体画研究
于 婕(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翁乙超(南京书画院 金陵美术馆,江苏 南京 210006)
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在《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一文中,提及艺术史上的确没有像米开朗琪罗、伦勃朗、毕加索等一样伟大的女艺术家。那什么是伟大的艺术?诺克林认为:创作艺术品包含着自我一致的形式语言,或多或少依赖或不依赖于世俗的习俗、修辞或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必须通过学习和研究,或者通过教学或学徒,或一个长期的个人经验形成。[1]18想要在艺术上取得成就,那么教育是第一位的,以及权威的机构的认可,但19世纪,法国女性实际上无法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与权益,女性学习艺术只能是资产阶级女性的业余爱好。
贝尔特·莫里索是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8次印象派画展,她参加了7次。她也是19世纪法国为数不多的女性画家。19世纪大部分资产阶级女性仍处于依恋阶级给她们带来特权和物质生活的阶段,接受传统的“男权”观念的束缚。莫里索将绘画视作一份职业与社会格格不入时,印象主义给莫里索提供了一种契机。印象派艺术家大胆探索,对学院派所有原则提出了质疑。印象派画展缓和了莫里索的女性社会角色和职业生涯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19世纪以前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莫里索所处的环境和她的性格给了她比大多数女性更多的表达可能。她的家族属于资产阶级,因此在莫里索成为一个社会怪人时,阶级特权也将保护她免受太多的公开批评。莫里索不像19世纪其他同样水平的女性艺术家妥协她们的艺术或者牺牲她们的社会地位来迎合传统,在莫里索的职业生涯的每一个时刻,她都在社会需求和艺术需求之间走过一条狭窄的道路。然而,她在尝试男性化的主题——人体画时,技法表现和性别问题以及价值观念使之又陷入新的矛盾中。莫里索在这主题中只能借用镜子和表现手法来缓和女性在人体主题表现上的窘迫与不安,但与时代的主流审美相比仍是失败的。
一、贝尔特·莫里索的绘画环境
在19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男性优于女性,女性一直被大众定义为男性的附庸品,其职责是繁衍与照顾家庭。19世纪的个人主义在共和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艺术表现中确保了一种自主的男性自我,莫里索这个时代的女性认可“自我”的含义是男性的自我,她们对男性的依赖,也深深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的女性虽然可以学习绘画、音乐等艺术,但不会作为一种职业。自1648年法国皇家美术学院建立以来,很少接纳女性学员,后来甚至宣称女性不能成为学院成员。社会习俗只允许上流社会未婚女孩通过私底下习得业余的音乐和绘画的技巧作为一种装饰,从而在家庭社交活动中能够向男性充分展示自己,取悦他人,同时也能愉悦自己。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人体研究是每一个艺术家训练的基础,学院把人体画置于绘画等级制度的顶端。80年代艺术院校完全剥夺了女性艺术家用任何性别的人体模特的权利,即使到了19世纪末以后,女性艺术家可以参加人体写生课,模特也必须部分着衣。整个欧洲都将女性排斥在以文艺复兴传统为基础的学院人体课之外,也使女性无法复制男性艺术家的成功。
1880年在莫里索艺术生涯的后半段,她已经完成了女性社会责任中两件重要事情,结婚和生育缓和了她的社会舆论,这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早期的印象派画展为她的艺术声誉奠定了基础。因此,莫里索可以少关注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尝试人体绘画。莫里索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她将女性形象的主题与自己对立起来,通过有意识地区分不同的符号来强调女性的形象。莫里索的人体绘画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私密空间里的女性形体和人体女性。
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中讨论了男人的风度基于他身上的潜在力量,是一种对别人产生影响的力量;女人的风度在于表达她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界定别人对待她的分寸。[2]61这就是被动的女性的世界,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完成她们自己的价值,形成属于她们的女性气质。女性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以男性的视角来对自我观察,既是自我观察,又是他人的“被观察者”,成为一种特殊的视觉对象。画家、观众、收藏家通常都是男性,艺术作品中的人体对象通常是女性。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女性这些形象展露身体的正面,直白或隐喻的是性爱的对象,是属于看画者的。以及女性在梳洗打扮时,那一刻被男性凝视,都表明她是男性实际或者潜在的性对象。“一个自重的年轻女子,在梳妆间除非见她的丈夫,不能见任何人……此时此刻见其他男人的女人,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拒绝得了。”[3]109莫里索是上流社会的淑女,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她承认这些女性身体的暴露是不合礼的,但她在表现这类主题时拒绝提供观众所期待的色情内容,她将内容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场面,尽可能地描绘成她所期待的迷人画面。就像印象主义用感官数据来构思每一个表现对象,放弃题材中的所谓情节或者故事,把表现的主题都当作“风景”和“静物写生”来处理,为了色调而不是为了题材。莫里索将她这类绘画进行的一系列缩减和组合,始终把表现元素限制在视觉范围内并且排除一切不属于视觉范畴或者无法转换成视觉范畴的东西。
对于莫里索来说,19世纪欧洲的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定义和高雅艺术的概念之间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定义也迫使女性不可能成为所处时代重要的艺术家。莫里索如同大多数想成为画家的女性最终做的那样,将自己限制在“镜前”肖像画。杰尼琼·拉贝尔(Jenijoy LaBelle)汇编了一本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文学中女性对镜子的痴迷的书,[4]这个时代的女性痴迷于自己的镜像,镜子被认为是女性生存的重要工具,她们总是要看自己,因为她们的生活依赖于自身外表。就像那个时期的文集中所说“女人从男人那里得到一切;男人给予女人是因为他们爱女人;他们喜欢她们,因为他们觉得她们很美。”[5]在各种视觉的评论下,女性内化自己的状态,镜子也成为她们审视自己的象征。
二、对镜梳妆的女性
1876年之前,莫里索和其他一些保守的画家以及印象派画家都在创作人物肖像画,描绘时尚的巴黎女人。莫里索以一种知性和正式的绘画风格画了朋友、母亲和姐妹,表现了现代女性的气质。在1876年至1880年,在这些肖像画之后,莫里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描绘女性的身体,她一直在与女性气质作斗争,从而使她失去了很多的设想。莫里索在创作这些画时,始终逃离不了社会和文化制度给予她的影响,她的画是代表了男性审视下的女性的自我形象。但莫里索这类梳妆打扮画已经偏离了女性业余绘画的安全领域,莫里索在资产阶级的体面、色情和绘画野心之间左右为难。旧的观念很难改变,这是性别文化无法解决的冲突,莫里索的尝试和妥协始终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变。但它们代表了莫里索为扩大她的工作范围所做的努力。在她的梳妆画中,莫里索将衣着单薄的女性安置在两种观看模式之间:在窗户的边缘,和刚好碰到镜框。此外,白色的衣裙和浅色调的窗帘透过镜子、窗户反射出亮光都有吸引观众视觉的效果。她们在镜子前梳妆打扮,观众和画家则一起关注着画中的女子,观看者在观看画作和认知她们的过程中,这些女子也通过镜子看向自己。法国精神学家拉康(Lacan)认为镜子是主体自我形象得以确立的重要依据,也是辅助观看者主体性生成的重要工具。[6]80主体关于自我的观念建构起来,然后以此形象再去认识自我,修正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许多诗人和艺术家都曾将自我意识的觉醒描述为在人的生命中一种强大的、令人震惊的体验。莫里索作为女性去描绘女性对镜的过程既是描绘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自我审视和自我认知的过程,又是女性对制度标准的反思和女性意识的思考,她们在对镜凝视这过程中设计出社会需求的女性形象,实现对自我的认证。
《穿衣镜》(The psyché,1876)(图1)中的女子站在镜子和窗户之间,镜子里明显地展现出女子的镜像,女子侧身站在镜前,注视着自己的衣着与身形,她被为观众所做的装扮的镜像所吸引。镶着缎带的拖鞋羞怯地露出脚踝和小腿,靠近我们这边肩膀不小心地露在外面。卡拉·戈特利布(Carla Gottlieb)在《毕加索的“镜前的女孩”》一文中提及此幅作品,[7]509这种长形镜子在19世纪开始流行,“psyché”这个希腊单词在《大拉鲁斯百科全书》(Grand Larousse Encyclopèdique)中译为“灵魂”,莫里索作品中的镜像面向观众,女性从一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也是在凝视自己的灵魂。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和一个虚拟的形象,一个代表现实,一个代表内心。观众的视觉也从现实女子身上转移到了虚拟的镜像人物中。《梳妆打扮》(The Toilette,1876)(图2)中人物裸露着半个肩膀,脸前的白色光斑和镜子的反射将视点吸引过去,衣服与裸露的皮肤使用大面积的浅色颜料,笔触零散抽象,无法让观众分辨清楚身体与衣裙的具体位置。在《擦粉的女子》(Young Woman Powdering Herself,1877)(图3)女子坐在一面镜子前,墙上挂着相框,我们的注意力被明亮但杂乱的墙壁和梳妆台上聚集的物体分散了。在《穿袜子的年轻女人》 (Young Woman Putting On Her Stocking,1880)(图4)中,女子坐在窗边,背景的窗户和窗帘透着强烈的白光。莫里索用抽象的技法转移观众对性感的女性身体的关注。画面颜料快速划过,凝结、堆积在画布上,大面积的白色调如同镜子的反光吸引观众的视线。

图1 穿衣镜

图2 梳妆打扮

图3 在擦粉的女子

图4 穿袜子的年轻女人
镜子、窗户这种多重视觉的运用,鼓励我们去思考如何看待女性,或者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女性行为规范中要求:女子不能目不转睛地直视对方的眼睛,说话时要目光向下并时不时抬眼看,这是良好的教育绝对可靠的标志。[8]57莫里索将这种行为有意或者无意地用在了画面中,这些在私密空间里的女性都一致地将目光转移,不与观众对视。在两种观察方式之间最不自在的人就是莫里索自己。莫里索在矛盾的心理中将画面的视点分散来缓解自己的窘迫。在这类相当传统的主题中,镜子的作用是让观众的视觉愉悦翻倍,同时也表明了女性对视觉愉悦的渴望。莫里索这段时间里共创作了7幅梳妆作品,几乎都没有突出展示女性的身体。无论我们如何期待性,莫里索都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镜像里的想象是父权文化观念中所期待的形象并非真实的女性本身,女性通过镜子开拓自我的视觉空间,在现实空间外确立真正的主体意识,实现真实的自我。
三、女性人体
19世纪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女性画家被描写为有熟练的业余水平,并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丈夫和家庭上。在莫里索的年代不管她画什么,她的选择都不容易,也不安全,因为女人根本就不应该选绘画作为职业。莫里索在大胆地尝试梳妆女性形体画后,仍然不满意自己对女性身体的表现。
在1885年之后她思考了她同时代人的绘画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并且尝试画了一些局部裸露的女子形象,如《裸肩女孩》(Girl with Bare Shoulders,1885)以及《后视裸体》(Nude from Behind,1885)(图5)。莫里索都只画了裸体背部,在描绘胸部时,以急速的笔触带过或是用光斑处理。1886年在参观雷诺阿的画室后,莫里索在笔记上写道:“我觉得两幅在水中的女人画和安格尔的画一样让人着迷。他说人体画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之一。”[9]她不仅仅是欣赏它们,她觉得这些画迷住了她。受雷诺阿的启发,莫里索重新审视了18世纪的艺术,她被说服了,认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是可以融合的。莫里索认同男性画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对女性人体的定义。她所画的是裸体女性,也是在画自己身体的一种反映和自己身体的另一个版本,同时完全呈现给男性观众。在她认同男性的观点后,要将欲望转化为被欲望,这便形成看的人和被看的人一种矛盾心理。

图5 后视裸体
莫里索在转化这种意识时,她将人体当成静物来描绘,让情感变得空洞,描绘的人体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自己也介于两性之间。但人体艺术是性欲投射到性对象上的一种主动的表现,女性长久的社会观念固化的意识又怎么将其完全否定呢?莫里索在1890年前后多次尝试,一直寻找解决这种矛盾的心理的方法。1887年,莫里索《休息的模特》(Model at Rest,1887)(图6)这幅画虽然描绘的是一个正面的裸体模特休息时的状态,但展现出来的却是一个紧张的模特,抓着胸前的布为自己遮盖,画面的笔触模糊,只能辨别模特的腿手臂是裸露的,模糊的胸腹,不清晰的手用土红色线条简单勾勒出来,整幅画都体现了画家紧张急迫的状态。之后,莫里索又创作了《在镜前》(Before the Mirror,1890)(图7),这是莫里索最大的、准备得最充分、也是画的最华丽的一幅人体画了。对比前面两幅素描,镜像中的女性越来越清晰,在卧室的镜子前,一个裸体的女人用双手梳理头发和素描稿的构图一样,一件宽松的衣裙从一个肩膀滑落下来,在镜子里可以看到她的脸和身体的前面,以镜像呈现给观众,但镜像的身体正面仍是模糊了所有的性特征,同时也被衣服适度的覆盖。莫里索这幅画用了多种视觉焦点,其中的画中画是不是莫里索用来伪装自己的人体画的一种手段?镜子的反射能力质疑了画的准确性,而画的解释能力则削弱了镜子的可信度。但最终她还是没有解决人体绘画的心理矛盾问题,女性被社会文化灌输了这样的表达是不得体的。就如同最初她参观完雷诺阿的画室后在笔记上的记录:“昨天,在圣日耳曼郊区的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了一幅布彻的版画,虽然极其不得体,但却非常优美。”

图6 休息的模特

图7 在镜前
莫里索承认人体是不可缺少的,她赞美男性艺术家所描绘的人体画是多么迷人,但最终她都以镜像的形式呈现出来。莫里索将情感赋予所描绘的人体画中,镜子是莫里索将自己作为旁观者的借口,无论她如何尝试,都没有找到解决她困境的办法,她在笔迹中也提到:“欲望和渴望并不是不存在,但是一切接近现实的东西都很有可能压倒情绪,而物质的现实永远只是一种堕落,即使在它快乐的时刻也是如此。”她渴望实现她的欲望,但是实现又会湮灭一种感情。
结语
女性的作品存在于女性的形象中,最常出现在女性眼中的画面就是镜子反射给她们的画面。[10]但在莫里索的画面中的镜子所反射出来的图像都不能很好地反映任何东西,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女性艺术家无法在描绘女性身体这类主题中走得很远,因为这是男性艺术家和女性的身体之间不可避免的生理和心理的矛盾。社会文化、制度以及学院艺术教育的限制等,也使女性不能像男性一样系统学习人体画。技法的不成熟和创作条件的局限导致她们的艺术实践只能局限在静物画、肖像画和风景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