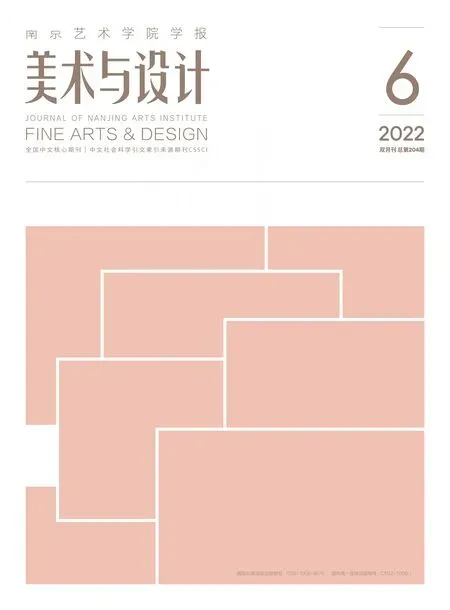关于穆里略①
文/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译/吴京颖(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 浙江 杭州 310018)
李 颖(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馆,江苏 南京 210013)
在德国艺术史文集中,布克哈特的部分我选择了一篇在他完成大学学习后所写的短文,这篇文章只在一份杂志上“发表”过,而且是在少数朋友手中以手写本传阅。这篇文章直到最近在德国也很难读到。可以确信的是布克哈特这位内心保守的学者,很快从他的这个圈子及其激进的领袖戈特弗里德·金吉尔(Gottfried Kinkel)脱离了这个圈子。在之后的几年他甚至宣称他对于杂志的贡献如同“垃圾”,并声称会“一直”反对他们出版这些作品。他关于《穆里略》的一些笔记展示了他探究艺术与历史的成熟方法。提供这些例子让人们了解一位天才的心灵是怎样完美形成的,甚至是在他开始创作之前。
布克哈特在首段嘲讽西班牙思想开放的摄政王埃斯帕特罗时已然隐约显露了政治斗争,埃斯帕特罗是对抗卡洛斯集权主义的领袖。布克哈特的思想被塞维利亚所吸引,因为正是在塞维利亚,穆里略找到了他心目中完美的模特,其艺术品质触动着他,模特的美丽使他的内心充斥着情欲。激发布克哈特长远认识的很可能不是穆里略《完美灵魂》[Immaculada Soult]的圣母加冕,而是一幅可能出自18世纪早期的模仿者的绘画作品,这幅作品归于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ippe)名下,是他在卢浮宫藏品中的一部分。
布克哈特对穆里略的人物刻画(可能会使读者想起海因斯对鲁本斯的描述),已经成为他对历史阐释的主导母题。穆里略是个(Gewaltmensch)——这在英语中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在此我们可不甚理想地解释为“自然之力”。这意味着在人类的灵魂、思想与身体的超能发展。没有智力束缚、宗教狂热、罪恶感与恐惧心理;有自制力,掌握自己的理性与感性,因此能够掌握与享受生活。这是对于新人性的描述,根据布克哈特所说,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生成。他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中的王子、雇佣军、人文主义者和女史。用上述这些词语,布克哈特为后世几代人界定了用文艺复兴的概念界定了几代人。
布克哈特撰写穆里略;但是他的思考涉及了杨凡·艾克与巴洛克风格之间艺术发展的整个图景轮廓,使他那个时代的艺术受到争议。在北方国家,通过范·艾克发现了现实,绘画与可感知的当代生活融合在一起,代价是失去老艺术流派中的奇妙天真的理想主义。在南方,现实主义的觉醒在一世纪后发生,但这与古物的发现密不可分。因此在“梅迪奇时代”,意大利艺术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互相渗透到达顶峰(布克哈特认为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中具体呈现了这一点),而在北方,宗教改革阻碍了人们对新精神的彻底接受。在短暂的无与伦比的繁盛时期,意大利艺术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沦为“无望的平淡无奇的唯心主义”,而威尼斯的感性艺术则在提香的晚期作品中经历了现实主义的逐步发展,然后与卡拉瓦乔和他的分支那不勒斯派一起“大步发展”,穆里略的艺术之源。
布克哈特被穆里略的《完美灵魂》中体现出来的地道的、扎实的美感深深感动,必然会接受他艺术中理想主义的缺乏。他解释说西班牙人的阴郁风景是他所需要的孤独的效果。但是他发现穆里略每次绘制理想的基督形象时都不成功,穆里略将他所有的热情都投注在了文雅的圣母、狂喜的圣徒、回头的浪子与乞讨的男孩身上——这种发现需要一个超个体的解释。布克哈特当时正在收集材料,去完成反宗教改革的历史研究项目,因此他在那个时期的精神环境中找到了解释。在反宗教改革艺术中,表达的重点从崇拜转向了崇拜主体,从圣人转向了殉道者、狂喜的牺牲者与受苦于信仰的受难者。这些复杂的概念重新出现在布克哈特的作品中。例如:为其老师弗朗兹·库格勒艺术史手册(1847—1848)的修订本中,他自己的反宗教改革的讲座(1863—1864)中,以及在他身后出版的《鲁本斯纪事集》(1898)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即艺术的蓬勃发展不受经济衰退与政治腐败的影响,再次预示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对地中海的热爱,其感官享受与美丽。他认为世界史表述的,应该是“每个时代的样子”。他在东方与墨西哥艺术中看到了“理想主义”(令人想起青年歌德对原始艺术品的辩护)。最后,他看到了鲁本斯和伦勃朗的绘画精神中的灵性。基于这些认识,他反对拿撒勒人试图复兴中世纪敬神艺术的尝试。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撰写时“伴随着现代人的恒定眼光”。
因此,他对穆里略的随笔读起来像是他之后作品的前奏。布克哈特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作为艺术史家,他想在不过度强调国家流派的情况下描述形式与风格的独立发展与变化。作为文化史家,他在人类精神发展方面也有同样的希望。《康斯坦丁大帝时代》(1853)描绘了那个时代的智性史(相当灰暗),这一时期艺术-历史复兴被科洛夫(Kolloff)最早预见。《艺术指南》(1855)是具有灵性的、讲述了古代至18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品欣赏指南”,包含自传、地理、历史与美学信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叙述的可塑性极为卓越。而作为其续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实际上是文艺复兴建筑的历史。它尤为关注建筑形式(及其用途)的自主发展,沃尔夫林、维克霍夫与李格尔都在很多方面对其产生影响。
这是布克哈特身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布克哈特曾将追求名望视作文艺复兴时期个性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而此时他却摆脱了这种追求,余生专注于以在巴塞尔大学任教而生活,这种摆脱使得他获得了个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此外,在最后的三十年中,他发表了大约170场关于西方文化各个方面的公开演讲。他身后才发表了这些重要成果。其中包括《鲁本斯纪事录》,其构成分析(compositional analyses)的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他的《希腊文化史》,通过强调城邦中的残酷和不民主阶级结构,强调希腊的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以及悲剧元素在希腊神话与历史的主导地位,彻底摧毁了温克尔曼那希腊性格中的“和谐”观念。然而,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同样缺乏幻想,他更加强调艺术的救赎能力。
——格特·席夫(Gert Schiff)一次又一次的,我被不可抗拒之力指引至西班牙博物馆(Musee espagnol)大厅。在这儿,我每天都可以见到我的太阳——穆里略的《玛利亚》( 图1)。我对自己说:曾经在2个世纪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女孩生活在塞维利亚!现在,或许是因为“乌尔冒”(Urmau)①格特福莱德·金吉尔(1815-1882),艺术史家与革命者,成人教育先驱。“乌尔冒”是金吉尔的绰号,意为Maikaferbund(May Bug Association),是波恩学生协会(1841-1847)的智囊,这个协会布克哈特也曾经参与。时常捍卫统治者,这座城市毁于一旦。

图1 《关于穆里略》雅各布·布克哈特巴黎,1843年8月初
穆里略依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之一。这儿展示着他的自画像。这幅画也是他所有作品的关键。我们将其与唐·菲利普四世宫廷中所有俊美的骑士作比较,这些画显然是委拉斯贵兹草作完成的,耀眼于各个墙面上,你将会明白穆里略是如何超越他的时代的——这是自然之力仍在运用物质与智力的力量,而在他的周围,他那崇高的祖国与高贵的人民则越来越堕落。
看看这漂亮的,微微撅着的嘴唇!它们透露着这个男人的行为!这些略微缩回的鼻孔,闪动的眼睛,怒气冲冲的拱眉,整张脸庞,难道不像是激情的军火库吗?然而,在其之上仍是傲慢的、专横的前额,它使一切变得高贵,可控制,精神化。在它两侧,流淌着最美丽的黑头发。被这个男人爱着的女人多么幸福!我相信这张嘴唇已被亲吻了很多次。
巴特洛姆·埃斯特班·穆里略1617年出生于塞维利亚。他是胡安·德·卡斯蒂略和委拉斯贵兹的学生,自1645年以来一直生活在塞维利亚,直至1682年去世。这些是(上帝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所有记录在案之事。然而,在他的画作中,他的伟大灵魂伴随着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为世人所见证。
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唐·菲利普二世统治之后,严重的经济弊病侵蚀了西班牙生存的精髓。在他的第二任继任者的领导下,第一场惨败发生了。西班牙人被迫承认葡萄牙的自治,并承认自己被克伦威尔(Cromwell)打败。在贫困潦倒的人民心中,一种忧思的恐惧蔓延开来,认为更糟糕的时代即将到来。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的智性运动还是一如既往的新鲜与活跃。卡尔德隆(Calderon)的全盛时代恰逢穆里略的青年时期。然而这个国家却被沉重的锁链束缚着,因为前文所提的致命冲击系统地控制或误导了它的外交活动。再加上朝贡的政府亲信的压力和外国捏造之词的压力——这些压力比任何其他国家要承受的压力都更荒谬、更可怕。据历史学家所说,整个家族都开始过上乞讨的生活,无法再过正当的生活。因此,现在不是进行战争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穆里略无法形成一种历史风格。他的风俗画手法甚至进入了他最崇高的创作之中,这也适用于他稍年长一些的同代人苏巴朗(Zurbaran)身上。同样,构图是他最薄弱的环节。他视情况将自己的人物放在画中,在这方面,即便是瓦萨里时代的罗马画派的拙劣画家也比他优秀,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都能像一件纯粹的手工艺品(a mere handicraft)一样具备某种确切的构图才能。
但是,穆里略的乞讨男孩,他的一群孩子,是慕尼黑美术馆最重要的财富之一,流露出深受压迫的百姓的情感。这些都是他无声的哀叹,违背了多明我会的审查制度(Dominican censorship),我们只有现在才明白,因为我们对西班牙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同情之心。这些衣衫褴褛的、漂亮的、结实的孩子们,靠在杂草丛生的树篱上,靠在破旧的墙上,他们难道不是这个国家的形象吗,依旧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力量,仅仅只是暂时的在回顾四周那过去遗留的残垣断壁。任何想要完全理解这些图像的神圣诗意的人都应该阅读古兹曼·德·阿尔法拉切的历险记。①《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是流浪汉小说的一部经典著作。流浪汉小说是一种虚构的体裁,形成于西班牙,名字取自西班牙词语picaro,意为 “无赖”或 “恶棍”。比起供娱乐消遣的小说而言,《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具有更多的说教意味,它具备流浪汉小说的所有特点。该书的作者是马特奥·阿莱曼(Mateo Alemán,1547 年生于塞维利亚,约1615年卒于墨西哥),他开创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他所效仿的流浪汉名著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 y de sus fortunas y adversidades(《小癞子》)截然不同。《小癞子》出版于1554年,作者不详。在这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作者使用小故事、娱乐活动和趣闻轶事对故事情节进行了补充,反映出正义、荣誉和宽恕等主题,尽管这些补充打断了古斯曼这一叙事主线,仍然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古斯曼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物,他多次实施欺诈并设下阴谋陷阱。故事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情怀,能把读者带到16世纪西班牙和意大利复杂的真实世界中,并反映出那时正在进行的反宗教改革的精神。第一部分于1599年在马德里出版,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第二部分则于1604年出版。该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很快便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此版本收藏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印刷于1681年。他也是这样一个乞讨的孩子,却能够放弃意大利所有的奇观,只因向往家乡塞维利亚的美丽。
但在我开始漫谈之前,应先阐释穆里略的外在特点。首先要赞扬的是其色彩,具有火一般的通透,还伴有明暗对比法,直接沿袭了伦勃朗与科雷乔的血统。再加上一些西班牙画家本土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画面中的人物与观者之间的氛围层次(l'ambiente)获得了精湛的表现。看多大量作品的观者都知道,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诗性,如果杜塞尔多夫学派的艺术家知道这种成就的秘密,如果他们的色彩不是这么硬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流派之一。另一方面,但凡看一眼伦勃朗的作品,就能知道即使是最粗俗的人物形象,只要通过光线与空气,也能让其具备精神气质。穆里略的作品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在他的理想人物形象身上,这让我看到了他艺术特征的核心。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写实主义者,除了少数情况外,他压根不想成为其他的角色。他的《帕尔多的圣安东尼》是一个真实的乞讨修士,而非一个虚拟人物。他的《井边的雅各布》是一个西班牙牧羊人,和真实的几乎一模一样——但想想艺术家有什么优点!他没有让工人变成残废的样子,而是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民族,一个没有因乞讨而憔悴,也没有因贫穷而悲惨的民族,而是通过赋闲时的沉思,获得了对自身美的认识!毕竟,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人常常如此惊人的美丽的原因。他们只是将美作为一个要点,而不带任何北方的矫揉造作。他们的动作尽管非常生动,却像狮子和老鹰一样简单而宏大。
对于穆里略来说,美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无数镜子的映像。通常我不喜欢比较,但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拉斐尔。在拉斐尔的圣母中,尤其是《西斯廷圣母》,你能感觉到一种(无论多么无意识的)映像。的确,他在著名的信中对其的描述只不过是“遵循了一个特定的想法”。但是谁能否认《西斯廷圣母像》[Modonna di San Sisto]、《福利尼奥圣母像》[Modonna di Foligno]、《花园中的圣母》[La Belle Jardiniere](其后者存于卢浮宫)已经超越了最美模特的所有可能性呢?这和路德(Luther)的奇迹理论是一样的:奇迹是提炼而成的,不是自然之外的,而是自然之上的。(Miracula non fiunt praeter naturam, sed supra naturam)
相反,穆里略在塞维利亚寻找最美丽、最虔诚、最聪明的女孩,通过仰望她,获得创作圣母必需的热情。她会虔诚地生下弥赛亚,但不论她洁白透明的皮肤下跳动的血液有多么的纯正,她永远不能成为圣徒、天使的女王。所以,神奇的女人,从画布上下来,看着我,这使得我余生都充满了了快乐。
好吧,你可以笑啦!我是得不到《西斯廷圣母》的青睐的,因为在她面前我必须垂下眼睛,她如此认真地凝视着观众的脸!然而,来自塞维利亚的女孩却虔诚地将双手交叉在她跳动的心脏上,不停地凝视着高高的天堂,在金色的云彩中,无数天使露着脑袋互相亲吻。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站在地球上,压碎了蛇的脑袋——她并不知道,神圣的光芒正流淌进她的双眼,现在她知道自己会生下救世主,我希望她活生生地存在着。
好吧,我觉得你可以笑。人们在这张作品前会失了心智,因为这是一幅如此完美的画像。
他对耶稣基督的形象则是另外一回事。不幸的是在此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尽可能地接近人们所熟知的《基督像》[Vera Icon]这种遍布欧洲的古老基督肖像。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样一幅充满明暗对比和空气透视的写实画的古代类型,效果非常不好,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可怕和毫无特色的形象。(请注意,现在只有极少数画家能够画出这样的肖像。我只是以穆里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
尽管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穆里略确实有勇气按照他的标准去画上帝的母亲。但在画上帝时,他却违背了内心,竭尽全力地依赖传统。我认为,至少可以部分的,用以下方式解释这一点:穆里略对意大利与西班牙画派的往昔历史有着宝贵的认识。他知道有多少画家冒着风险摔了一大跤。他知道有多少艺术家至少前进了一段路,却在离沟渠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然而,我想不出有哪位画家会断然放弃再现艺术性的、不受束缚的上帝形象。他曾无数次将其描绘成一个极为美丽的孩子!我相信他的美丽妻子一定为他生了一个非常漂亮活泼的男孩,否则他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男孩形象。
1843年8月9日
穆里略真的是一个古里古怪的人!他的绘画形象闪耀着最美丽、最欢快的情欲。一次又一次,即是画中最神圣的场景,也会爆发出恶作剧般的笑声,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最昏暗阴沉的背景前!例如,最可爱的小耶稣站在一个圣方济会修士前,充满了质朴的虔诚与修士般谦卑忠诚,小耶稣打开了他的旅行袋,将一条面包塞了进去。一切都沐浴在美丽的夜光或是宁静的夕阳余晖中,而不损害画面的人物效果。然而大师穆里略将他的场景布置在有着乌云的黑暗荒野中——没有比挪威环境更阴沉的地方了。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厄斯》,和他大部分大型作品都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他选择了一个普通的灰褐色背景。
我想首先,艺术家需要将前文所提作品中天使们的光晕进行比较。但是这些作品周围都是他亲手创作的不同的历史画,画作展示的是同一种背景,同一片阴暗、雷鸣般的天空,没有天使与光晕。当我发现穆里略的两幅风景画时,我更是大吃一惊,这两幅作品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要阴郁。萨尔瓦多·罗莎(Salvator Rosa)或里贝拉(Ribera)(历史画)和其他那不勒斯人的耀眼的光芒、黑漆漆的阴影,都不适合他。不,他用的是一种忧郁的,相对统一的灰色。他表现的不是愤怒与绝望,而是阴郁。举一个例子,一条蜿蜒的小路穿过崎岖的山丘,山丘上覆盖着少得可怜的小乔木与小灌木,同样被闷热邪恶的云团所笼罩。他画这幅画是相当粗心,多半是当作一种研究。因为这幅画缺乏必要的目的与个性,无法创造出真正险恶(sinister)的印象。
我想通过这些观察来证明的是:他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眼中的自然,而不是风景中或人造建筑中的自然。当我说,他用悲伤的眼光看待他的国家,但却用快乐和充满希望的眼光看待他的同胞,我的理论是不是有些离谱了?
这个问题变得越引人注目,我们思考它的时间就越长。克劳德·洛兰创作热那亚那美丽、闪耀的日落以及海岸边闪闪发光的宫殿的时间与这幅风景的创作时间相当,都是在同一个十年里画的。它属于一个我们习惯性认为南方太阳最喜欢的孩子的国家,植被丰富,天空蔚蓝,一点也不亚于希腊。小心些!这幅画甚至不是马德里画派之作,因为没有比荒凉的新卡斯蒂亚荒野更好的题材了。不,这位塞维利亚人之子,安达卢西亚人穆里略,曾经画过。
让我继续我的推测。我想我在几位伟大的画家作品中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那就是米开朗琪罗(前提是《维纳斯》真的依照他的草图,在他的监督下由庞多尔莫绘制出来)和鲁本斯。这一级别的人物画家偶尔会全然忽视风景与背景,将这部分绘画视作微不足道(en bagatelle),随意地描绘光影,让人物最终从强烈的效果中脱颖而出。但是没有其他艺术家像穆里略一样,如此明显和刻意地践踏他祖国的美丽风景。甚至在16世纪人们对于风景的意识还未唤醒之时,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创作,而在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加斯帕罗·普桑(Gasparo Poussin)和阿尔伯特·凡·埃弗丁根(Albert van Everdingen)生活的时代才出现。在我看来,与埃弗丁根这位被誉为北方最后一位最严肃的风景画家相比尤为引人注目。埃弗丁根的所有画作中仍然包括蓝天、粗壮的冷杉树、浪漫的城堡和瀑布。即便是拥有“宏大而阴沉的头脑”的雅各布·雷因斯达尔(Jacob Ruysdael) (正如艾森多夫(Eichendorff)在谈到他的维克托伯爵(Count Victor)时所说)甚至在他最阴暗的峡谷和沼泽中,也描绘出一片茂盛的橡树。只有穆里略能够忍受最贫瘠的灌木丛——他每天都能看到塞维利亚卡尔特修道院(Carthusian monastery)的柠檬树、棕榈树和芦荟。
但这也许是一个伟大心灵所固有的,他时不时地为自己内心的快乐创造一个相反的极点——一种阴郁的孤独,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这是天才的神圣悲哀,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具备这种特质。努马去了埃格里亚的源头,穆罕默德退居山洞,基督回到沙漠。在这里,心灵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独居之地,一个比实际情况更加黑暗的夜晚;借此,以快乐为中心的自我会更加灿烂地散发出它最强大、最内在的光芒。“并充斥自己好听的声音。”(Und die Fülle des eigenen Wohllauts.)
1843年08月12日
我摆脱不了穆里略,他太吸引人了。今天我再次非常仔细研究了他的性格和他奇妙的理想主义,得出以下结论:
他塑造的基督形象,除了清晰可见地对《基督像》的追忆之外,还带有强烈的西班牙元素。诚然,在穆里略的诸多圣母像和乞讨的孩子们的这些人物身上,没有一丝内在的力量和活力。他原本如此有力的手在画布上徘徊,胆怯且犹豫。但是如果他不能将基督塑造成神,至少他将基督绘制成一个血统纯正的西班牙人。基督的外表是如此细腻、白皙。他那高贵专注的目光可以在委拉斯贵兹笔下一些骑士身上看见,但在穆里略其他作品中几乎未曾出现。
基于这一点,可以建立以下特性描述标准:在穆里略基督之后,紧随着的是他的《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一个依旧微不足道、理想化的人物,这一人物形象可能源于一时心血来潮,与穆里略其他的基督形象非常相似。他的身后是一个跪着的抹大拉,这个形象虽不是罗马画派的理想形象,但也与穆里略的一般的形象不同,更像是提香理念下的模特形象(提香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称自己为写实主义者)。然后我只能说《圣彼得头像》[Head of St.Peter]虽然比穆里略其他的形象更具概括性,但却代表了一种相当粗犷的西班牙风格。神妙的《福音传道者圣约翰》[St.John the Evangelist]具有独立、全然真实的风格特征。将他从《施洗约翰》那儿分离出来。紧随其后的是《玛利亚》和所有其他的奇迹图像,甚至《浪子悔改》[Repentance of the Prodigal Son]与乞讨男孩也包括在内。
那么,穆里略是宗教画家吗?鲁本斯在创作神圣主题时是宗教画家吗?这个问题涉及艺术哲学中最深奥的一部分。奥弗贝克(Johann Friedrich Overbeck)会否认,他甚至认为拉斐尔的作品不属于宗教画。
如果一个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切都会变得简单,甚至不必认同海涅(Heine)这个极端左派,他认为画天使比画呕吐的农民要容易得多(攻击)。
17世纪是反宗教改革的时代,难道不和安吉利科(Fra Angelico da Fiesole)、布赫纳(Stephan Lochner)时代一样的虔诚甚至更加虔诚吗?鲁本斯不是把他的一生献给了弗兰德斯和布拉班特吗?它们是反对荷兰的前线城市,也是真正的教会激进分子。穆里略难道不属于那个全然忠诚于天主教的国家吗?另一方面,佛罗伦萨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比安吉利科时代更无聊而且教会大分裂的时代。此外,我们至少明白鲁本斯是一个极好的天主教徒,毫无疑问,穆里略也是。因此,如果奥弗贝克在他愚蠢的狂热中谈到了艺术的背叛(postasy of the art),尤其是把拉斐尔拿出来当替罪羊时,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种所谓的背叛是非常自然的发展,画家们的信念丝毫未受到影响。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我区分了两个要素:15世纪末艺术方法的突然改进与增多,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材料增多与世俗主题突然加入竞争。
秘密就在这里——在于宗教改革之前艺术奇迹般的发展,而不是所谓可怜画家的背叛。不是拉斐尔,而是莱奥纳多·达·芬奇标志着这一演变的高潮。因为当时莱奥纳多已经创作出他最伟大的作品了,而佩鲁吉诺画派还在原地踏步。而拉斐尔,我们都知道,当他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就被深深地震撼了。
然而,一个被证明的事实是,只要艺术手段不完善,一个初步的理想主义(idealism)就可以发展。只有孩子才会期待有一天他能实现所有的愿望,一驾马车或是一个皇冠。最开始,画家对人物只有非常粗浅的认识,因此他的人物形象多多少少都是类似的。他还不能赋予他的人物鲜活的形象,正是因为这种局限,促使他收集他所拥有的无论是诗集还是圣物上的人物面庞。但是,这并没有使早期艺术与艺术家比艺术全盛时期的艺术与艺术家更加虔诚与优秀。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只要他们的目光还未投向现实,那理想主义就是一种自然和必要的形式。是的,即使是东方国家,蒙古人和犹太人,以及同等程度(甚至更高)的墨西哥人,都还停留在不完美的理想主义里,拥有四至十二只胳膊的梵天(brahma)就是力量的理想化象征。如果西方世界的人民在这方面更加机敏,只能证明他们属于这个世界上的智性贵族。
然而,在文化史提供的所有利于人类精神的证据中,有一个观点总是以它的美而突出:艺术的初期同样也拥有幼儿般甜蜜的梦想、健康的身体、天真的理想主义。在它手法不完善的同时,其意图表现出了极大的深度与美丽。它的意图是清晰与开放的,还未被普遍的艺术手法分散与混淆。
最奇特的是艺术向现实主义探索的方式。南方的发展与北方不同,它几乎比北方晚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日耳曼北部,文化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14世纪末,现实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当时理想主义盛行于弗莱芒画派中,而凡艾克兄弟突然就点醒了同代人对现实及其绘画方法的认识。他们不仅重新塑造人物形象,还赋予人物背景——风景、街道或是房间,这些都源于现实。他们也无法忘记狭窄小巷中的狗,窗台上的猫,李子,烟囱上的玻璃瓶。无论其形式多么朴素和枯燥,这种现实主义仍然有巨大的感染力,因为它直接表现了人们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南方,非常幸运的是,15世纪末现实主义的觉醒与对古物的最新研究正齐头并进。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由于意大利人与外部连接的关系更紧密,因此与北方人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艺术品,此外,意大利是教宗所在地,处处都有最高级的精神较量,因此他们对艺术品的争夺要比北方更加激烈。教宗所在地,以及政治的堕落,为造型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德国醉心于未来,而它的艺术至此将要排在意大利的后面。
1500年前后,意大利已全然生活与享受人生。艺术真正的繁荣持续了不到4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拉斐尔的一生。意大利为此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
在梅迪奇时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渗透进南方艺术。《西斯廷圣母》(1517)或许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之作。在拉斐尔之后,这两种主义的结合只存在于威尼斯,而且即便是威尼斯,现实主义也是在提香的晚期作品中开始盛行。罗马—佛罗伦萨画派堕落为一种无可救药的、乏味的、一边倒的理想主义,而卡拉瓦乔和那不勒斯画派等更为强劲的人物,使现实主义一跃而变。无论是什么,在现实主义的裂变与波伦亚画派的反思结合之后,现代艺术进入了新的篇章。因为艺术成为一种意识的产物,而不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穆里略和塞维利亚画派是现实主义那不勒斯画派的一个分支,或者至少后者对穆里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毕竟,我在这里所描述的都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些过程决定了艺术的永恒进程;奥弗贝克(Overbeck)说一个画派放弃了另一个画派。但那也意味着要用公正的眼光(警察的尺度)来衡量艺术作品及其精神。没有艺术家能够约束自己,让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不超过自己的老师。但别再说了!今天每一个理性之人都知道精神的最重要品质是它的运动/变化以及无限发展的能力。
如今大家都知道,反宗教改革时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时期。大规模破坏被极为努力的重建所抵消。不论德国有多少作品被烧毁,意大利所制作的艺术品数量还是与之相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徒甚至设法从新教徒手中夺回了无数的教堂。它们立刻被装饰一新,其华丽程度令人震惊。
让我们回到主线上来,虔诚的理想主义从反宗教改革的艺术中几乎完全消失。我们不想否认这个事实。但在安吉利科时期,这些艺术品也同样虔诚,这也是事实。这种虔诚只是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出路。
现在圣母已经远离了她往日的神圣、纯净与贞洁。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所画的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提香同样也是。在意大利绘画作品中,基督变得更加次要,平庸甚至令人厌恶。在这两个伟大的主题中,有一个因为过于频繁的描绘而耗尽了人们的心血。另一个则是人们几乎难以用双手,有价值的去绘画展现,除非是几个幸运时刻。然而即便是幸运时刻,也是全凭直觉而作。然而,艺术,只要是真实存在着,总会意图去创作一些真正“新”的东西,如果艺术家创作了新的、史无前例的事物,那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内心的需求。
因此,放弃对神圣人物的理想化演绎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一些真正的自然(nature)力量,例如圭多·雷尼和穆里略,通过描绘现实成功重新获得他们的理想主义。然而,他们的成就与安杰利科的古老神秘相差甚远。
弥补这一差距的可能是:
艺术家越难以描绘出可爱(adorable)的人物,就越能成功描绘出受人崇拜敬重(adoring)的人物。反宗教改革的艺术已经为我们增添了许多人类虔诚与基督之爱的表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也许是所有艺术中最动人的作品。因此,反宗教改革艺术并不是旧的理想主义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补充。安吉利科最擅长画《得胜的教会》[ecclesia triumphans]、基督、圣母和圣徒。在另一方面,穆里略描绘的是教会的民兵(ecclesia militans)、殉道者、妇女祈祷像(orantes)、受难者。这已不是天堂荣耀之时。现在,尘世的苦难,尘世的朝圣之旅,终于结束了。然而,像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与苏巴朗(Zurbaran)能够成功创造出《圣方济各祈祷像》[St.Francis in Prayer],就像乔托能够创作出圣母像那样,需要一颗虔诚的心。我记得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安特卫普学院的鲁本斯的《基督受难》[Christ a la paille]。死去的基督靠在石凳上,他的亲人支撑着他。画中的圣母像是鲁本斯笔下一个苍白的普通女人,很难说她是神圣的。但她的脸上弥漫着深深的、无限的悲伤,赋予她神圣的虔诚形象。类似的画面时常可见于凡·戴克的作品中,但是我在这里谨慎地引用了名声不佳的鲁本斯。
兰克很好地描述了这个世纪的“狂喜”(ecstatic)艺术。没有哪个时代的宗教信仰像现在这样深厚与广泛。在这方面,穆里略再次成为大师中的大师。他的《受胎告知》[Immaculate Conception]与《帕特摩斯岛的圣约翰》[Saint John on Patmos]或许通过绘画具体表现了最伟大与最纯粹的奉献。在这一点上,安吉利科,甚至拉斐尔都不能充分证明。
让我们承认每个时代的价值!没有一个时代缺乏神圣精神之作,只是,我们不应向无花果树要葡萄。
我们的时代,从温克尔曼开始算起,代表了一个与梅迪奇时代同样重要的发展时代,因为艺术史研究对艺术家产生了影响,就像魔术一样。一些独立学校已经从一开始的烦琐和困惑的折中主义中脱颖而出,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
穆里略的伟大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引起一场骚动。他的作品已经被热切地研究过了。六位画家同时忙于效仿他的《受胎告知》。让我们希望,这位天才的所有美好与伟大可以激发和感染那些奋斗着的天才的年轻心灵!
我真想再和奥弗贝克(Overbeck)说一说关于背教的事!我会告诉他我认为是背教的事,也就是说,不是博洛尼亚画派与安特卫普画派的诚实与激励人心的努力,而是他个人的艺术虔信主义,促使他竟敢以此为由去诋毁拉斐尔。他不羞于从那些由鲁本斯、范戴克、穆里略、大卫等人耗费巨大努力安全建立起来的艺术手法中,懒洋洋与怯懦地抽象出来。好像他仿佛不需要一般的艺术教育、扎实的绘画技巧、真实以及可信的色彩,只需要“简单和虔诚”。在我看来,如今模仿安吉利科的艺术家,就像是试图用中世纪编年史的风格来描述法国大革命的人。那么,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时间投入到那每一条分支都饱满的遍性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