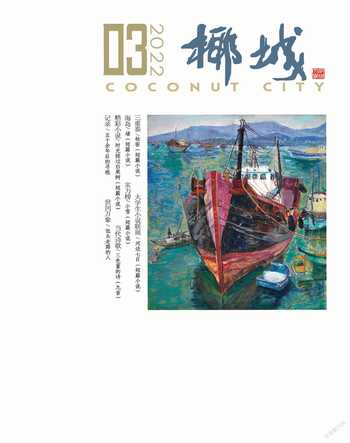时光掠过白果树

作者简介:张艳玲,教师,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散见于《四川文学》《龙门阵》等刊物。
那时候的早上,真早啊!
那是个星期一,鸡叫三遍的时候,郑前准时醒来,伸着懒腰,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股冷风从墙缝中钻进来,郑前打了个寒战,赶紧借着蒙蒙的天光,手忙脚乱地穿衣服。这时,厨房里也照例响起母亲拉风箱的声音,呼哧呼哧,时长时短。还有隔壁,也照例传来林家妈叫唤林富强起床的声音,还有风箱的喘息声。
“郑佳,弟弟起床了,把煤油灯端进去给他照亮!”母亲停下风箱,给姐姐郑佳安排例行功课。
郑前知道,当风箱不再喘气的时候,红苕饭就要熟了。
风箱是川中地区那时候生火做饭的必用工具,助燃。一只手呼哧呼哧地拉着,一只手往灶堂里喂柴草,左右开弓,不亦乐乎。要是不熟练,即便手忙脚乱,也未必煮得出饭来。比如郑前就不行,姐姐郑佳也只能算半个熟手。
姐弟俩的名字是父亲取的。郑佳、郑前,即为“挣家”“挣钱”之意,生活的愿望,从字里行间呼之欲出。郑前的父亲,是白马公社中心学校教语文的民办教师,母亲是白马公社白果树村小的民办教师。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是知识分子啊,至少是文化人,却给姐弟俩取出这样的名字,真俗气。可那时候穷啊!白马公社处于四川盆地的最底部,属于川中丘陵。这里,冬天总是大雾弥漫,寒风呼啸,湿气逼人。阳光,总是被盆地四周的山脉遮挡着,只有晌午时分,太阳磨磨蹭蹭到了顶,才吝啬地洒下一点阳光。有歌中是这样唱的“雨露滋润禾苗壮”,这至少不全对吧。没有充足的阳光,那些禾苗就像那时的孩子一样,营养不良。所以,那时的白马公社,就是穷乡僻壤的代名词。当然,其他公社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那时候,郑前见识有限,对穷富没有比较,更不知道有“俗气”这个词儿。直到上了初中,郑前才自作主张将名字改為“郑谦”,声母韵母都一样的,算是照顾了父亲的面子。父亲笑了笑,并没有反对。其实,那时候的农村人给子女取名,口味都比较统一,都寄托着“露骨的理想”。比如“有财”“富贵”“建设”什么的。比如同桌的李建设,还有既是隔壁又是同学的林富强。只是郑前家姓郑,用了谐音,到底还是文化一些。
姐姐郑佳给郑前端来煤油灯,然后匆匆出去了。她比郑前早半个时辰起床,每天除了早读之外,还要帮母亲煮猪食。郑前起床后,除了读父亲给他的《少儿唐诗》,还要做家务:扫地和喂鸡。父亲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母亲说,母鸡下了蛋,郑前吃了蛋,身体强壮,头脑清醒,才能像李白那样写诗。只是,父亲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震着了郑前,银河真会从天上落下来吗?但他又想,说不定那李白还真是天上的神仙呢。神仙是不会看错的。所以,郑前认为,读诗、扫地和喂鸡这三件事,一定是人生的大事,少一件都不行。可惜,鸡并不多,就一只公鸡,两只母鸡。公鸡不下蛋,只会打鸣。
吃过早饭,郑前背起书包去叫林富强,他们都是母亲那个班的学生。每天,母亲都会早他们半个时辰到学校。姐姐在父亲的乡级中心校读书,距离更远,也早早地走了。
郑前和林富强走出一里地了,老是感觉哪里不对。浓重的雾气裹满全身,水田里结的冰反射着白光,好像刺着他的屁股。林富强取了一块田里的冰,对着冰块吹了一口气,瞬间冰块上有了一个洞。郑前扯了一根茅草给林富强穿在冰块上。林富强嘻嘻地甩着冰块玩,嘴里吟诵着郑前昨天教给他的诗句“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铮”。郑前打了个哆嗦,不由得紧了紧旧棉衣,感觉那冷气正从单薄的裤裆里嗖嗖地钻进来。他歪着头看了看林富强的屁股后面,才惊恐地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忘记带上了:草垫子。这样的天气,坐在那几块石头垒起的凳子上面,犹如坐在冰窖上。那滋味,那后果……
郑前刚上学的那个冬天,还没养成带草垫子的习惯,就经常挨冻,甚至有一天上课时,他拼了命也没憋住,一泡尿悄悄地涌了出来。这可不是“飞流直下”。他不敢告诉严厉的母亲老师。就读于母亲所教班级,不知是别扭感还是另类感,郑前不知道该喊“母亲”还是“老师”,最后竟自出心裁,这样联合称呼了。他也不敢让邻座发现异样,更不敢离开座位。因为一离开座位,那石块上面就会留下显而易见的“罪证”,他就会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林富强就遇到一次,至今还被同学们叫着“屙尿狗”。郑前后来才想到,那时候寒冷都是一样的,石头凳子也是一样的,忘记带草垫子的同学也是有的,那为啥他们就不涌出尿来,成为“屙尿狗”呢?说不定也像我一样,拼命忍住的吧?其实,郑前的猜想是极有道理的。放到今天来看,那时候,这些孩子为什么憋不住尿呢?为这问题,郑前默默思索了很多年,终于想明白了:主要是生活太差,平时少见油荤,加上那冰冷的石头凳子的刺激,自身体质不好的话,绝对撑不到下课,绝对尿!
总之,郑前决定誓死守住这个秘密。他寸步不离,就那样在石块板凳上端坐着。偏偏天公不作美,一阵狂风过后,窗外飘起了小雨,还夹着川中地区难见的雪花,不疾不徐却密密匝匝,在昏黄的天空中旋转飞舞,并穿过木格窗飘进教室里来。郑前就和着雪花,还有尿裤子,在石凳子上冷了一个上午,也瑟瑟地抖了一个上午。他的尿裤子由湿到干,嘴皮由红到白,再到紫。回家后,裤子上是一圈又一圈的“花白地图”。更要命的是,屁股上长出了大大小小的紫红色冻疮。
这冻疮又痛又痒,陪伴了郑前整个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天。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这冻疮也像他读诗、扫地和喂鸡一样,锲而不舍,毫不懈怠,在以后的每一个冬天,都会如期而至,回到他的屁股上。到次年的仲春,冻疮才开始陆续自愈。其间屁股会奇痒难耐,他就开始用手一遍一遍地抓挠,抓啊抓,挠啊挠。但他又不能在同学们面前挠,会被误认为是干疙痨(疥疮)。这干疙痨的特征就是奇痒,还传染性极强。常常是一人染上,全家乃至亲朋都得遭殃。晚上,染上干疙痨的那家人,围在桌旁吃饭,突然男女老少总动员,齐齐地抓耳挠腮,场面盛大而滑稽。不知者,还以为他家在集体演练猴戏呢。所以,干疙痨是很讨厌的,像瘟神一样,人人避之唯恐不及。gzslib202204051307然而,谁又能避得开时代呢。
至少在川中,那是一个干疙痨盛行的年代,甚至虱子也是乡下孩子身上的常客。现在的孩子对虱子的概念绝对只能去百度了。其产生的根源么,和“屙尿狗”是异曲同工的。想想吧,一件衣服,尤其是内衣,一穿就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所谓勤换衣服,那最起码你要有换的啊。
郑前怕当瘟神,但又忍受不了冻疮的痒痒,要挠呢,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只能偷偷摸摸的。有时,他把手伸到课桌下,装着捡东西,乘机挠上一把;或者故意玩铅笔,用笔尖使劲刺上几下;又或者假装调整坐姿,用力把屁股在石凳子上来回蹭上几下。但这些动作,也只是隔靴搔痒,甚至有时还变本加厉地痒起来。等到下课铃声一响,郑前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然后躲进某一个角落,把手伸进裤子里,一阵狂挠。总算暂时舒服了。一进教室,郑前便焦头烂额,苦不堪言。心里默默对母亲老师说:如果我成绩下降了,你可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什么呢?他一直也想不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秘密就是用来暴露的,尤其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过了不久,郑前就暴露了,全班哗然。郑前哭着央求母亲老师帮忙解释,说这不是干疙痨,只是冻疮。当然,同学们是相信老师的,再说了,生冻疮的也不只郑前一个人。但郑前的抓挠是有目共睹的啊,于是,得了个绰号“郑抓抓”。
那时候,取绰号,编(唱)顺口溜,一向是同学们重要的也是富有创意的娱乐活动。比如,学校旁边的大路上,偶尔会看到自行车,多半是凤凰牌的,那钢圈轮子还有中间那个啥,白晃晃地耀眼。那时候,人们叫它“洋马儿”。当然,能骑“洋马儿”的人,也是很“洋盘”的。于是,一些捣蛋鬼就会追着唱“洋马儿,白肚皮,老汉儿买来儿子骑”。仿佛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开心地大笑。直到新来的刘老师也骑了“洋马儿”到学校来,才没人敢唱了。愣是少了一项娱乐活动。
扯远了。郑前痛定思痛,丢下林富强,转身就往家跑。宁可迟到挨批评,他也得回去拿他的草垫子。
草垫子到底是啥玩意呢?这对若干年后的孩子,甚至对很多城里人来说,恐怕和宇宙飞船差不多吧,只能想象。其实,它就是一种简易的坐垫。今天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坐垫:粗布的、绒布的、真皮的,或方形的、圆形的、卡通的。软硬厚薄,花样百出。但那时候乡下的郑前们就只有一种坐垫——稻草的。现在描述起它的制作工艺来,都有些绕:用一捆稻草,将中间扎紧,然后从扎紧处的两边,依次搂起一缕,绕着整捆稻草,一圈一圈地像辫辫子似的编,就编成一个圆圆的有点像寺庙磕头用的蒲团。用的稻草大捆一点,编出的垫子就厚一点,如是一小捆稻草,就很薄。编到最后的那一缕稻草,就束成一个小尾巴吊在边上,以便手提。不知别处是不是这样,反正到了秋冬季节,郑前他们白果树村小学的孩子们人手一个,可谓标配。早晨带去学校,放学带回家,不然会丢的。如此,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
话说郑前提着自己的草垫子沿着田埂飞奔进学校,已经上课了。进了教室,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凳子了。说是凳子,其实就几块烂石头重叠在一起,最上面一块稍微平一点罢了。课桌也大抵是这样的。郑前有点蒙,发现烂石块不见了,变成了一截四四方方的石条立在泥地上。桌子也是整块的石板,还泛着青光。他再看泥地,也平平整整。以前教室的泥地可是坑坑洼洼的,即便老师组织同学们用土填起来,过不了多久,又原形毕露了。高一脚低一脚走在上面,一不留神就摔跟头。老师摔倒后,学生就在下面捂着嘴吃吃地笑。有胆大聪明的孩子会赶紧把老师扶起来。老师尴尬地“咳咳”两声,拍掉泥土,顾不得手肘、膝盖的疼痛,捧起书本又继续上课。同学们已习以为常。
但是,摔跤摔出了深度和影响力的,就只有刘老师了。那天,郑前的母亲老师要赶在暴雨来临之前抢收地里的油菜籽,请了半天假。顺便说一句,民办教师在本质上还是农民,没有编制,没有粮食供应,要一边上课一边务农,工资也很少。而且,由于主要精力在学校,地里的庄稼往往是全村里最差的,产量最低。这天,母亲老师请假以后,郑前他们的课由新来的小刘老师代上。刘老师二十多岁,穿着刚刚流行的喇叭裤和尖头皮鞋。那堂课,刘老师不止摔了一次,两次,而是三次。一次比一次有深度。別的地方看不见,只说膝盖。第一次把膝盖处的喇叭裤摔了一个破洞。第二次把破洞里的膝盖摔了一条小口,渗出了丝丝猩红的血。第三次把摔出小口的地方,又加深了一层,那血就把破洞两边染红了,像一朵红艳艳的花。刘老师摔第一次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摔第二次,没人笑了。摔第三次,很多同学都哭了。因为刘老师除了龇牙咧嘴,他并没有发脾气,更没有摔书,而是跛着腿,继续上课。只说,同学们哪,我们确实很落后,但大家说,我们愿意这样一直落后吗?同学们抹着泪眼使劲地摇头。刘老师说,对了,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就是要改变这落后……
放学以后,郑前走到刘老师面前,嗫嚅道,刘老师,对不起,我妈今天如果不请假……刘老师摸摸他的头,笑着,不要这样说,你妈也不容易,又要上课又要种庄稼,怪我,没走习惯。
那时候真苦,但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真简单哪。
曾经有个同学叫夏春花,被摔得跛了半个多月,是由班里的大个子同学轮流搀扶着、背着上下学的。夏春花很过意不去,一次,从家里“偷”出一捧花生要分给大家。人人都盯着花生,但都摆手不接。夏春花说,不要我甩田里了哦,扬手欲甩。结果大家欢叫一声,一涌而上……在那个还不知零食为何物的年代,又香又脆的花生可是了不得的。那时候的孩子没那么娇贵,他们像田埂上的铁线草一样,默默地、顽强地生长着。给点阳光,他们就心满意足。而学校、老师和书,还有同学之间单纯的友谊,就是他们的阳光。
当然,那时候的家长也比较马虎,孩子摔伤以后,愣是不见有人冲到学校气势汹汹地讨说法。他们都忙着包产地,夜以继日地要从贫瘠的土地中多刨粮食。他们也许并不懂什么知识改变命运,但他们知道,学校和老师是不会害学生的。而且,有不少民办教师比他们还难。曾经有一个住校的年轻女老师,因房间漏雨,把煮饭的柴草全淋湿了,饿着肚子,一个人坐在门口哭得一抽一抽的。后被一个路过的家长看见了,晓得了情况,马上回去联络了几家人,组织了三担大柴捆子送到学校来……gzslib202204051307郑前看到教室里的桌凳和地面,非常恍惚,难道是自己跑快了,被大雾迷了眼?再一看,周围的同学好像也不认识了,有人捂着脸,有人坏坏地看着他,有人笑出了眼泪。郑前想,肯定是走错教室了,趁老师没发现赶紧溜。于是,他弓着腰向教室门口蹭去。“郑前!你往哪里去?”郑前站住了,这分明是我母亲老师的声音啊!他挠着头:“我、我以为走错了。”哈哈哈……教室里终于憋不住了。
“回到你的位置吧。”母亲指了指。同桌李建设挤眉弄眼向他招手:“郑抓抓,看这里!”
母亲老师清了清嗓子:“孩子们,以前,你们用的是烂石块砌的课桌、板凳,我们的支书和队长一直觉得这事愧对你们!他们经过一年的筹备,组织村里的男劳动力,到山坡上去开石头。他们一锤一锤地敲,也不知磨破了多少双手,用坏了多少把錾锤,才为咱们錾出了这些方正的石桌子、石凳子。”母亲老师的眼里闪着泪光:“为了给我们一个惊喜,昨天是星期天,他们组织了很多劳动力加班加点,全给我们换上了,把泥地也平整了。全校四个班,我们被排在第一批。现在,你们高不高兴啊?”同学们拍着桌子:“高——兴!”虽然桌凳仍是石头的,但总算平整了、踏实了。再也不用担心哪块石头冷不丁掉下来,砸着小脚丫子了。郑前瞟了一眼脚背还包着布条的李建设。
郑前稳稳地坐在石凳上,一双手在光滑的石桌子上摩挲,屁股下又有草垫子。他一时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这下写字就更工整了,听课就更专心了,成绩嘛,必须超过班长周有财!
这天,母亲老师给他们讲了很多新鲜的东西。不但有高级公路,还有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能通到每一个家门口,还有乡村别墅。不但家家户户用电灯,还可以看电视,全世界发生的事都知道。以后的课桌凳啊都是木质的,散发着香气。同学们昂着头,眼睛迷离,如听故事。郑前心大,暗暗说,我就要成为故事里的人!末了,母亲老师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是艰苦一点,但只要我们不断努力,永不放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时,我们这里随处都可以看到外国人那样嘟嘟的小汽车……
郑前不知道外国是啥样,但他见过外国人造的小汽车。夏天的时候,姐姐考上了重点初中,父母亲兑现了承诺,带姐弟俩来到县城游玩。在公园口的广场里,刚好停下一辆锃亮的小汽车。车屁股上贴着英文字母。郑前大着胆子上前问那个戴着墨镜的叔叔,这是啥车呢?墨镜看了看郑前,不认识吧,嘿嘿,外国车。郑前想去摸一下那闪光的玻窗,又不太敢。就想,要是我们教室的窗户也安上这明亮的玻璃,就不怕那些冷风和暴雨钻进来了。那天,他们一家子还去参观了县城最好的一所中学。郑前见到了传说中涂着乌红油漆的木质课桌椅。是不是有香气,他倒没闻出来。课桌下还有一个“大肚皮”,里面可以放好多的书。穿着雪白连衣裙的小姐姐可真好看。郑前一脸神往,他想,要是自己能马上进去和他们并排坐着才好哦。但又马上掐灭了这个念头,就无师自通地涌出一首刚背熟的诗“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回来以后,郑前首先就近地向同桌李建设“传达”了县城的见闻,并说,我不想做诗人了,我要做一名设计师,一定要为白果树村小学设计一座高楼,比白果树还高。门窗全是玻璃,不怕风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也是他刚知道的成语)。课桌和凳子都是木制的,涂上乌红油漆,放着光,散发出香气。
李建设偏着头说,好是好,只是你设计出来了,哪个来建呢?这么高的楼,怕是要很多钱吧?
郑前怔了一下,好像没想到这一点。但马上指着李建设,你来建啊,你不是叫李建设吗?……还有那么多同学。李建设将手一阵乱摇说,我……我不行的,完不成,我家这么穷。
郑前很生气,说,你听明白没有,我说了是现在吗?
李建设说,以后……那行吧。
两人还拉了钩。
一晃,可怕的冬天又早早地来了。
是不是在缺乏阳光的季节,大人小孩都容易受伤呢?郑前抠破小脑壳想。因为林富强的二伯也受伤了,是林富强的爸干的。
原来,林富强家有一块地与他二伯家的一塊地相邻,都在白安河边,属于滩涂,薄薄的沙地上浮着硬硬的乱石。那天,两兄弟都在锄地,准备种油菜。然后就为他二伯把地的边界挖多了,侵占了林富强家的面积,两人由争吵到动手,由动手到动武器。林富强他爸用锄头挖了他二伯肩头一锄,他二伯当时就倒在白安河边,血水流入了白安河。
这下,白安河就不白了吧?郑前想。
林富强家一下就空了。他爸挖伤了人,看着他二伯满身是血,吓得丢下锄头就跑了。可是他妈跑不了啊!还得顶着。郑前听父母说,幸好没伤着骨头,但在区医院住个十天半月是肯定的。林富强他妈卖掉了从娘家陪嫁过来的两个柜子、一个大圆桌,甚至还抵上了一头就快出栏的肥猪,一并赔给他二伯作医疗费,才暂时了结。但是,他二伯家要求林富强他妈必须去医院护理,不然就要去派出所报案。林富强他妈急出了眼泪,我……我的庄稼呢?又指着林富强说,他呢?我儿子咋办?
这时,郑前他妈站出来说,富强他妈,你去吧,富强就交给我们。林富强他妈说,这……这……郑前他妈说,没事的,我们不单是邻居,更主要的是,富强是我的学生,晓得不?
郑前当然很高兴。并且自从林富强在他们家吃饭以后,一日三餐的红苕糊糊(红苕煮熟以后,加少许玉米面搅拌而成)都变得稠了一些,有时在泡菜里还加了几颗油辣子。这可是意外的收获。
只是,林富强从此变得沉默了。每天晚饭后就跑到村口的大白果树下,一屁股坐在枯树叶上发呆,不知想些什么。
那棵白果树真大啊!郑前他们试过,要十个小伙伴手拉手才能围上一圈。白果树村,就是因这树命名的。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吟诵一首歌谣:
村口有棵白果树,屋后有片翠竹林。竹林采来一枝竹,白果树上打白果。手中翠竹轻轻摇,白果树下遍地金。
村口有棵摇钱树,屋后有片聚宝林。翠竹编成大竹框,白果树下装笑声。手中竹筐沉甸甸,白果树下喜盈盈。gzslib202204051307郑前问过父亲,父亲说,这白果树又名银杏树,还叫“公孙树”,意思是爷爷种树孙子才能吃到果子。郑前就想,咋这么慢呢,不是说只争朝夕吗?要是我们白果树村的變化也这么慢,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从此,在郑前的小脑瓜中,对白果树就不是很尊敬了。
很多时候,郑前就陪着林富强坐在大白果树下。树上的叶子还有少许未落,黄灿灿地挂在树梢,被瑟瑟的寒风吹着,上下翻动,发出簌簌的声音,似在窃窃私语,嘲笑着树下这两个小家伙。只一眨眼工夫,黄叶就被吹落,飘飘乎乎晃荡在他俩眼前。林富强就会抓住一片,双手使劲地撕扯着。郑前就说,别扯了,这叶子这么好看。林富强瓮声瓮气地说,好看能当饭吃吗?
两个九岁的孩子,常这样在寒风中默默坐上一两个时辰。直到郑前的屁股又痒得不行了,两人才回家。
有一天,林富强突然大声喊出一句:我不想穷!
郑前愣了一下,然后使劲地点头说:嗯哪,我也是!
夜晚,月亮升起来,挂在白果树枝头,倒映在白安河上。白安河还是白的。月亮被雾气笼罩着,时明时暗,像随时都要藏起来的样子。郑前躺在床上,就想,城里的月光是不是这样的呢?很久睡不着,突然听到堂屋里母亲和父亲小声的对话。
父亲问:哪里还痛,我再给你揉揉?母亲有腰疾,那是长年累月上课和干农活积淀下的。
母亲说,不用了,你上课也累,每天十多个小时。
顿了顿,父亲说,自从学校都换上了整齐的石桌凳,地面也平整了,就再没有人摔伤了吧?
母亲叹口气说,学校倒是没人受伤了,只是难为支书、队长他们了,那些石头都是山坡上、庄稼地里埋着的,要开采出来,就得毁掉一些庄稼,还有土地。一些人就稀罕那点田边土坎,当时……
父亲说,这情况你早说过的,当时你就发现支书和队长脸上有乌青,推测不是被村民打的,就是劝架误伤的。
母亲说,我说过了吗?
父亲说:嗯哪,早说过了。接着也叹了口气:唉,怪就怪太穷了吧,那点土地就是村民的命根子。
母亲说:只是,可怜这些孩子哦,这样的成长环境。
这一晚,郑前做了很多奇怪的梦。但都非常破碎,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他梦见了阿拉丁神灯,好像是从白安河边的滩涂上,用锄头“叮当”一声挖出来的。好像是林富强他爸,又好像不是。那灯在空中飞舞,后来又变成了煤油灯。很多人跑过去跪着许愿。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其实,以上这些是差不多二十年以后,白果树村小的四个同学,坐在一处残垣断壁上共同絮叨、回忆的一段旧时光。
他们是:郑前,不,是郑谦,某大学建筑设计学院副教授。林富强,县城打工,做房屋装修。郑前的同桌李建设,白马镇街上一个废品收购站小老板。还有一个女同学夏春花,是白马镇初级中学语文教师。
林富强抓了块断砖,不停地杵着地面说,看吧,错过了就错过了,现在连补救都没得意义了。
李建设说,不怕你们笑,那年我回到这里,没见一个人影,我从破门窗里钻进去,还特别收购了一件东西,你们猜是啥?
大家都望着他。
李建设比划着:一根斑竹做的教鞭!
郑谦的心怦了一下,殷切地说,给……给我可以吗?也许正是……我妈用过的。郑谦他妈如今老年痴呆了,每天就会说两句话:我是民师,我在白果树村小教书。
三个人都愣了一下,一齐说,肯定的,肯定的。
郑谦摇着头,唉,都怪我,说大话,其实很无能。
林富强伸出粗糙的手抹了一把脸,苦笑了一下说,你再能,你能挡得住那些年轻人陆陆续续外出打工吗?然后是中年人,然后是妇女,再然后孩子们要么去镇上读书了,要么随父母去了外地。
夏春花接过话,然后村小就几乎没有生源了,只得关门。才过两三年,原本就破旧的教室……呜呜……就……就全垮塌了,成了现在这一堆堆……呜呜……夏春花哭得梨花带雨。
然后,三个男人都流下泪来。
林富强站起来指着四周,喷着唾沫星子。当年,为了争那点田边地角,亲兄弟都打得头破血流。再看现在,这些好田好土,长的啥呢?野草啊!
郑谦向林富强伸出手,说,把图纸拿出来吧。
林富强从背上取下一个圆筒,茶碗大小,差不多有一米长,泛着幽蓝的光。这是一个装图纸的专业工具,应该叫收纳筒或别的什么。里面的图纸还是好几年前郑谦亲自设计的:教学楼、办公室、图书室,连厨房、厕所、操场、绿化带都清清楚楚,漂漂亮亮。教学楼尽管没有白果树高,但应该更切合实际。图纸一直被林富强收着,很多同学都看过。
郑谦取出图纸,展开摩挲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一边,拿出打火机,咔嚓点燃了。其余三人几乎惊叫起来。林富强要过来夺,被夏春花挡住了。
郑谦喃喃道:这叫“化”,就让它和这里彻底融为一体吧。如果非要建点什么,也只能是别的了。
盯着那火苗,夏春花又涌出泪来,还能怎样呢,各地的村小几乎都没有了,就连民师这个称谓也远去了。突然说:你们猜,此刻我脑海中冒出个啥词儿?——挽歌。
林富强和李建设同时问:啥……啥晚歌?
郑谦当然听明白了。他的心痛了一下。
好在,白果树还在。他轻声吟起了那首歌谣:
村口有棵白果树,屋后有片翠竹林。竹林采来一枝竹,白果树上打白果。手中翠竹轻轻摇,白果树下遍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