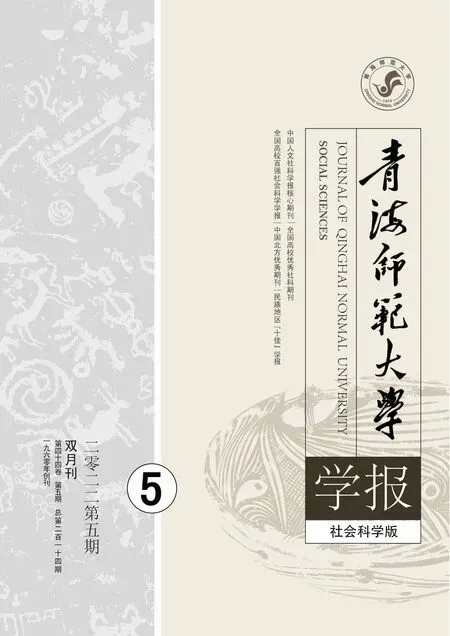从“西伯利亚大驿路”到“红色国际大通道”:在西伯利亚“发生”东方革命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西伯利亚(Сибирь) 自古以来因其极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一直居欧亚大陆之要冲,始终为多元民族与文化之汇聚地区,持续成为多种势力与霸权之争夺场所。在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ВКП(б)](1)1925年12月前为俄共(布)[РКП(б)],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联共(布)”,强调作用时使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转向”(Eastern Revolutionary Turn)(2)布里亚特裔美国籍学者达基亚娜·林霍耶娃(Tatiana Linkhoeva)使用了“革命向东”(Revolution Goes East)这个词汇。参见:《革命向东:日本帝国和苏维埃共产主义》(Revolution Goes East:Imperial Japan and Soviet Commun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20)背景之下,“世界革命”的战略重心转向东方国家,重点在中国及外蒙古、朝鲜、日本和印度支那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共产主义运动。西伯利亚这一占据苏联版图70%的广袤地区,时空交汇并且风云际会,变成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的策源地,成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前哨”(форпост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3)КурасЛ.В.Иркутск-форпост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20-1922 гг.) //Известия Ирк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2017. Т. 21.
在苏联和俄罗斯史学中,对20世纪20年代西伯利亚历史的研究屡见不鲜,(4)如:柯尔马科夫主编的《伊尔库茨克编年:1661-1940年》(Колмаков Ю. П.Иркут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1661-1940 гг. Иркутск : Оттиск, 2004.);白卫军中将萨哈罗夫撰写的《白色西伯利亚(1919-1920年内战)》(Сахаров К.В.Белая Сибирь(внутренная война(1919-1920гг).Мюнхен,1923.);库拉斯的《伊尔库茨克在共产国际的远东政策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1920-1922)》(Курас Л. В.Место и роль Иркутска 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минтерна (1920-1922 гг.) //Известия Ирк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2016. Т. 16.)和《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前哨》(Иркутск - форпост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20-1922 гг.) //Известия Ирк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2017. Т. 21. );日加洛夫的《苏联远东政策的性质和目标(1920-1924)(Жигалов Б.С.О характере и целях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1920-1924гг//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2010.№4(12))。梁宾科夫的《伊尔库茨克:革命西伯利亚的首都》(Рябиков В.В.Иркутск-Cтолиц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Сибири.Ирку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57.)。以上著述基本以内战和西伯利亚地区革命为主要研究对象。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索特尼科娃(И.Н.Сотникова)在2015年出版的《共产国际中国局:组织结构、干部和经费政策(1919-1943)》(Китайский сектор Коминтерна: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кадровая ифинанс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19-1943 гг. Москва,Наука -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5),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玛玛耶娃(Н.Л.Мамаева)在2019年发表的《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进程》(Коминтерн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в Китае 1920-х гг.//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о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4 2019.),2021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曼诺夫(Н. Г.Романов)和奥尔洛夫(К. В.Орлов)主编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东方:纪念共产国际一百周年》(Коминтерн и Восток: к 100-летию Коминтерна :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 Москва,ИВ РАН, 2021.);上述著述直接以共产国际与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主题,在研究题材和文献方面都有所突破。有关这一时期西伯利亚档案文献出版也颇为常见(5)由新西伯利亚州国立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的专家马雷舍娃(М.П.Малышева)等主编的《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文献集》(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1920-1922гг).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ибирского бюро ЦК РКП(б) и Сибир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Новосибирск,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索特尼科娃和维尔琴科(А.Л. Верченко)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编辑出版的《1920-1927年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1920-1927. 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 2021.),但是重点和焦点基本放在苏俄的国内战争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革命之上,即局限于其国内历史的范畴之内。欧美史学界的相关研(6)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安娜·别洛戈洛娃(Anna Belogurova)的《南洋革命:共产国际和东南亚的中国网络(1890-1957》(The Nanyang Revolution: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1890-195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著名俄裔美国籍中国问题专家潘佐夫人(А.В.Панцов)在2019年发表的《张太雷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Чжан Тайлэй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зма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4, 2019 г.),美国学者达基亚娜·林霍耶娃的《革命向东:日本帝国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等等。,在视野和角度上略有突破,但重点仍然落实在苏俄内战之上。中国学界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主题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囿于俄文文献所限,主要关注的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国内的政策实施和作用影响(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自1996年翻译并出版了21卷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012年),内包括了大量中共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关系的档案文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但是,具体涉及中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三者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关系的专题尚未发现,仅部分论文略有涉及。如:张秋实:《1929-1931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之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4期;王占仁、尚金州:《1935-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新论》《东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白拉都格其:《略谈共产国际与内蒙古革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等。,对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发生的中共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合作关系,以及中共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革命活动涉及极为有限。
西伯利亚地区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东方国家(地区)共产党关系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重要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唯一的)红色交通线,还是众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的关键发生地,是各国共产党领袖和重要人物的重要活动地,因此有巨量的档案文献遗留和保存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各类档案馆中,这些档案文献的研究为上述曾经被历史湮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事实上,西伯利亚在20世纪20年代,扮演了东方革命策源地的关键角色。这包括:第一,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指导下,朝鲜、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共产党在西伯利亚成立,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的成立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组织支持。第二,西伯利亚不仅是联共(布)与共产国际与东方国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力量的组织关系的重要发生地,也是东方国家和民族共产党之间交流与互助的重要地点。第三,以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为中心,东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西到托博尔斯克(Тобольск)—鄂木斯克(Омс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南到上乌丁斯克(Верхнеудинск)(8)1934年7月24日更名为乌兰乌德(Улан-Удэ)。—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再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铁路,穿越满洲里—绥芬河—哈尔滨—大连,构成了一个跨越欧亚,辐射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红色国际大通道。在这条半隐半现的国际大通道及其支线上,往来的不仅有大量的人员、物资和经费,还有看不见的命令、信息和情报。以上诸点,正是本文努力从宏观方面尝试研究的方向。
一、时间与空间交汇下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9)在俄文文献中最早出现“西伯利亚”的时间是1407年。(参见:МиллерГ.Ф.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Москва-Лениград,издат.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1937.Т.1.C.5)。关于“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在俄国最早撰写《西伯利亚史》(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的日耳曼人米勒尔(Г.Ф.Миллер)否定了来自鞑靼人的自我称呼сабыр的说法,认为名称来自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的别尔马科人(Пермяки)和泽梁人(Зыряне)语言中的сибэр和чибэр(意为“美丽的”)。(МиллерГ.Ф.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Т.1.C.195)。中国学者包尔汉、冯家升认为“西伯利亚”名称来自于长期活动在鄂毕河中游、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的鲜卑人,俄语转译“鲜卑”即为“西比尔”(сибир)。另一说:“西比尔”是鲜卑人崇拜的一种瑞兽。(参见:包尔汉、冯家升:《“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还有来自蒙古语“шибир”(意为“沼泽地带”)和曾在西伯利亚地区短暂活动的中国少数民族“锡伯”(sibe)之说,不一而足。最初是专指位于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之间的西伯利亚汗国(Сиби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1460-1598)。随后,在沙皇政府的政策鼓励和俄国富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Строгановы)的财力支持下,各类哥萨克远征军从16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挺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时期,是将哥萨克的扩张和殖民活动视为开拓之功而大加赞扬的,例如“叶尔马克的远征开辟了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光辉的地理大发现时期”。[1]早在1563年,伊凡四世就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随着哥萨克的攻城掠地,西伯利亚的区域也随之迅速扩大,“西伯利亚的主要居民是鞑靼人,他们居住在托博尔河、伊尔德什河、鄂毕河、托米河、叶尼塞河的南部,以及这些河流之间的草原地带”。[2]俄国扩张势力再度越过西西伯利亚和中西伯利亚的界河——叶尼塞河,到17世纪中叶已经到达太平洋西岸,到18世纪中叶最后占领楚科奇和勘察加两半岛,到18世纪末,俄国扩张势力越过白令海峡,抵达太平洋东岸的阿拉斯加。“俄国也将西伯利亚的概念从原来窄小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俄国的东部边疆。这种地理概念和包括的地域范围逐渐为西方所了解并加以确认。发展到今天,西伯利亚则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名称。”[3]沙皇政府在1822年的行政区划中,将西伯利亚划分为以鄂木斯克为行政中心的西西伯利亚总督辖区(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和以伊尔库茨克为行政中心的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190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Больш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中指出西伯利亚是指俄罗斯帝国在亚洲北部的全部领土,它北濒北冰洋,东临太平洋,西至乌拉尔山,南至蒙古、中国边界。[4]
在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区划再次被重新划分,即沿太平洋分水岭山脉、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合流处到外兴安岭为界,东部为远东地区,西部为东西伯利亚(10)西西伯利亚(西起乌拉尔山,东至叶尼塞河) ,东西伯利亚(西起叶尼塞河,东至太平洋分水岭山脉)。有时在自然地理上又划分出中西伯利亚(西起叶尼塞河,东至勒拿河)。。《苏联大百科全书》(Советская больш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第三版(1976年)标示:“西伯利亚占有北亚大部分领土,西起乌拉尔山,东至太平洋分水岭山脉,北起北冰洋沿岸,南至哈萨克共和国岗峦起伏的草原和中国、蒙古边界。”[5]“西伯利亚的东界开始于赤塔省的东部,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合流处的附近。它把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地区分隔开来。这条界线差不多也是到处沿着山脉走的: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朱格朱尔山脉和通常在地图统称为科里马山脉的那些高耸的山塊。这些山脉形成了一面流向太平洋,一面流向北冰洋的那些河流的分水岭。它们把赤塔省和雅库特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领土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阿穆尔省和马加丹省的领土分隔开来。”[6]因此,“有时人们往往把整个亚洲北部叫做西伯利亚,将苏联的远东地区也包括在内。这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苏联的远东由于地处海滨,在自然条件上与地处内陆的西伯利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从自然地理的观点来说,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完全独立的地区”[7]。
在帝俄和苏联时期,西伯利亚面积分别为1 300万和1 000万平方公里。在苏联时期,雅库特共和国(Якутская АССР)、楚科奇自治区(Чукот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赤塔州(Чит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阿穆尔州(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和马加丹州(Магад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被划出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自18世纪初开始向西伯利亚大量迁移俄罗斯族和其他的欧俄地区的民族,为其殖民政策服务。据1701年的统计资料,西西伯利亚有俄罗斯移民12 000户,东西伯利亚有7 000户[8]。西伯利亚远离俄国政治中心,因此沙皇政府无法对其采取在其他殖民地所惯用的统治方式,只能在西伯利亚建立几个殖民统治中心,由军事、行政、司法和经济权力合一的地方总督(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行使权力。所谓“西伯利亚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存在;它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有约束力的民族身份。它的现代历史与俄罗斯的现代历史密不可分。容易征服的乌拉尔山脉与其说是一个地理边界,不如说是一个欧式俄国的虚构性、政治性界线,在这个界线之外,坐落着一个巨大的亚洲殖民地和一个广阔的刑罚场所。西伯利亚既是俄国的黑暗之心,也是一个满是机遇和繁华的世界”[9]。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西伯利亚为“罗荒野”,意指广袤和荒芜之地。在俄罗斯文献中则称西伯利亚为“无底的袋子”(бездонный мешок),是指它无穷无尽的资源和对于冒险者的机会;也称其为“罪孽的袋子”(мешок грехов),因为此地区是沙皇政府和农奴主惩罚犯人和农奴的流放地。美国著名旅行家和记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先后四次来俄罗斯游历,多次赴西伯利亚实地考察。他在《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andtheExileSystem)中写道:“流放制度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个省的总督昨天直白地告诉我,托木斯克监狱的状况很糟糕,但他无能为力……我先前对政治犯的待遇所写和所说的那些,看上去大体还是准确和真实的——至少就西伯利亚而言是这样。”[10]在各种民族的文字中,西伯利亚基本上都是“外省”“遥远”“荒凉”“寒冷”“苦难”的代名词。1906年莫斯科出版的《教育通报》(Вестник воспитания)上的一篇文章中推测:如果在俄罗斯境内的居民中普及识字的话,欧俄地区至少需要120年,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地区至少需要430年[11]。英国旅行家基克松(Francis Hixson)于19世纪末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道:“神奇冰封的外贝加尔──是一个与世界隔绝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这里,似乎任何时期都遇不到欧洲文化,这里没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也没有普希金。”[12]沙皇政府在1915年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表明,截至1914年1月1日,托博克斯克省、托木斯克省、叶尼塞斯克省、伊尔库茨克省,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滨海省、谢米巴拉金斯克、雅库特、勘察加、阿克莫林斯克和图尔加州居民人数为12783千人。[13]
然而,西伯利亚蕴藏的无尽资源和未来发展空间引发了各国学者、旅行家和冒险家的关注。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亲手所建的彼得堡科学院的首位俄罗斯籍院士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就曾经评价:“俄国的强大将来由于西伯利亚而增长。”[14]而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历史教授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则评价:“在欧洲共和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交叠发展的历史中,西伯利亚成了一个孤寂的集结待命地区……西伯利亚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革命和流放实验室。”[15]早在1905年革命中,西伯利亚地区就同步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起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工人和士兵在武装起义胜利后,在1905年12月6日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为孟什维克梅里尼科夫( А. А.Мельников),布尔什维克沃罗采夫(И. Н. Воронцов)为副主席,布尔什维克罗戈夫(А. А.Рогов)、库兹涅佐夫(К. В.Кузнецов)被选为委员。工兵代表苏维埃正式宣布解除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正式接管城市,组成人民法庭,出版报纸《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工人》(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рабочий)。这一政权被称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共和国”(Красноя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一直存在到1906年1月3日,最终被沙皇政府镇压。[16]
在1917年发生的推翻沙皇政权和颠覆俄罗斯帝国的二月革命,在西伯利亚延迟爆发并产生重大影响,具有时间差和空间差的明显特点。
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也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且在政治实力对比方面显现了升降浮沉的复杂局面。
由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任命和派驻的官员迅速接管了帝俄时代的行政、军队、警察、司法、财政、教育等国家和地方权力机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了伊尔库茨克城市杜马。这些具有“国家”性质的权力机构立即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相邻的周边国家的承认。
但是另一个“政权”——直接来自民间的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和影响明显地展现出势不可挡的上升趋势,并且作为地方自治机构获得了实际的自我管理职能。到1917年7月,西伯利亚地区共有各类苏维埃150多个,其中工兵代表苏维埃45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8个、工人代表苏维埃47个、士兵代表苏维埃20个、农民代表苏维埃34个。[17]
在旨在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月革命发生后,正是因为地区差和时间差的原因,各种反苏反共势力得以聚焦在西伯利亚地区,使得整个地区面临非常复杂的政治局势。
二月革命后,时任海军中将、黑海舰队司令的高尔察克(А.В.Колчак)宣誓效忠临时政府政权。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自命被推翻的临时政府代表,参加了在乌法(后迁至鄂木斯克)建立的内阁执政(C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被任命为军事部长。1918年11月18日,由社会革命党人主要控制的内阁执政被拥护高尔察克军事独裁的军官推翻,高尔察克被拥戴为最高执政(Верхо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同时被邓尼金(А.И.Деникин)、尤登尼奇(Н.Н.Юденич)等将领尊奉为白卫军最高指挥官(Верховн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高尔察克获得了英国的军事援助,在鄂木斯克成立了军事独裁政府。在短时间内,高尔察克就组建起一支15万人的军队,并在1919年春天展开了由东向西的全面进攻,前锋直指伏尔加河一线的地域,迫使托洛茨基(Л.Д. Троцкий)乘坐铁甲列车亲临前线督战,从而扭转战局。1919年11月,鄂木斯克被红军攻占。高尔察克率部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东退却,希望逃往太平洋沿岸,在那里寻求日本的支持,以求东山再起。
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联合实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的浪潮中,日本是积极的参与者。1918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成立西伯利亚计划委员会,图谋以武装干涉将西伯利亚分离出去,成为日俄之间的缓冲国。日本最终派出多达7万人的庞大部队,从海参崴登陆,几个月内就到达贝加尔湖和布里亚特一带。日本一直支持着高尔察克,直到1920年其战败被俘;同时还给另一位白军领袖谢苗诺夫(Г.М.Семёнов)以援助。时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Коминтерн)代表在伊尔库茨克工作的达林(С.А.Далин)回忆当时危急的形势,“日本依靠白匪的力量,到1921年底实际上掌握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巴罗夫斯克这一带地方。这样,当时日本的统治就扩展到了朝鲜、台湾、整个满洲、蒙古和俄国远东,形成了一个地域广袤的帝国,它威胁着苏俄和中国。这就是1921年的远东形势。”[18]
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反苏反共势力的巨大挑战,在1918年2月23日至28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第二次全西伯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西伯利亚红军。在这次会议上选举出新的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Центросибирь),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司法、教育和军事委员部,正式行使国家政权职能。1919年7月红军越过乌拉尔山,1920年3月红军完全控制贝加尔湖周边地区。俄共(布)在鄂木斯克、托木斯克、阿尔泰、伊尔库茨克、叶尼塞斯克、雅库特建立了军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与欧俄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不同,革命委员会成员由俄共(布)中央任命,其权力高度集中,具有军事共产主义(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的特点,适应了西伯利亚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亟待恢复经济的要求。
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形势的陡然变化,俄共(布)中央于1918年12月17日决定建立俄共(布)西伯利亚局[Сибирское бюро ЦК РКП (б)],领导这一地区的军事斗争。“在伊尔库茨克取得了镇压反革命胜利之后,中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苏维埃的大力帮助下,积极在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巩固苏维埃政权。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和东西伯利亚苏维埃边疆局(Окружное бюро советов B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统一归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在那段时间里,伊尔库茨克恢复了电报和电话联系,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的工作完全恢复,食品部门的供应能力大大增强。”[20]1922年底苏联成立,西伯利亚地区虽然彻底消灭了白军,但并没有立刻恢复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而是仍然保持了战争期间的革命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持续工作到1925年12月,随后才陆续恢复了苏维埃政权。
1920年,日军开始从伊尔库茨克撤离。1922年6月24日,日本宣布撤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1922年10月25日,红军解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现在从白海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这一片广袤地域上,到处红旗飘扬。困难的年代,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现在,在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结束以后,国家和人民能够轻快、舒畅地喘一口气了。”[21]1930年,按照苏联行政区域,西伯利亚被划分为东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和远东三个边疆区。
广袤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因其历史上长期与蒙古、朝鲜、中国、日本往来的原因,来自上述民族或国家的移民、宗教和文化等因素长期在该地区留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西伯利亚的革命也是东方革命的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库拉斯(Л. В.Курас)在题为《伊尔库茨克在共产国际的远东政策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评价:“革命西伯利亚的首都在世界革命的输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当时这座城市在远东存在的短暂时间内,变成了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前哨。”[22]
二、“红色国际大通道”的形成与东方革命“司令部”的建立
西伯利亚虽然地处遥远、寒冷荒凉,但自帝俄时代至苏联时期都设想打通欧俄地区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联系,建立一个东达太平洋西岸,南至中亚、蒙古、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或政治经济空间。帝俄时代的学者和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早在18世纪中期就说过:“如果将沿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沿岸的陆路与海上路线汇合的话,它将使俄国的实力在东方自由地加强和扩展。”[23]
为此,在哥萨克军队大踏步地向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扩张的同时,沙皇政府在 1725年至1730年授权已经归化俄国的丹麦探险家白令(Vitus Jonassen Bering)组织对西伯利亚的全面科学考察。1733年,枢密院发布了建立从莫斯科到鄂霍次克的西伯利亚驿路的命令,下令每月在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之间发两班驿车,从托博尔斯克到伊尔库次克和雅库次克之间每月发一班驿车,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和堪察加之间每2个月发一班驿车。这一命令被认为是西伯利亚驿路建立的伊始,开创了西伯利亚陆路交通发展的新阶段。直到18世纪末,西伯利亚驿路才最终形成,并正式获得了“西伯利亚大驿路(Великий Сибирский Путь)”的称号。莫斯科—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是自西至东的主干线,还有鄂木斯克—奥伦堡—阿克莫林斯克—谢米巴拉金斯克向南支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米努辛斯克的向北支线,彼尔姆—托博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西部支线,托木斯克—巴尔瑙尔的向南支线,伊尔库茨克—上乌丁斯克(乌兰乌德)—恰克图向东南支线。
1893年时任交通大臣维特(С.Ю.Витте)给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Ⅱ)上奏折,认为造成“俄国劳工的生产率很低”的原因,除了俄国寒冷的气候外,更主要的“交通不便是减低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24]。西起车里雅宾斯克东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是在他的交通大臣任期内开工的。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沙皇政府加快了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步伐,并且在1896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联合御日条约》,获得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从而使帝俄势力全面进入中国东北,获得了从欧俄地区调兵直达中国东北旅顺港口的便利,使横跨欧洲的西伯利亚大通道再度向南延伸,邻近朝鲜半岛,直逼中国中原地带。这是西伯利亚作为欧亚大通道(Транссибирская Mагистраль)的第二次大发展。
1915年沙皇政府开工修筑从西伯利亚大铁路重要枢纽城市新西伯利亚至哈萨克斯坦塞米伊的阿尔泰铁路(Алтай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苏俄时期铁路继续修筑,1921年铁路修到塔拉兹,1924年铁路修到达比什凯克,1931年铁路修到里海海岸的土库曼巴希,全线总长度2 351公里。这条铁路将西伯利亚与中亚连接到了一起,被命名为土西铁路(Туркестано-Сибирская Mагистраль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又名西伯利亚中亚铁路(Турксиб)。
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西伯利亚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联络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共产主义力量、致力于发动东方革命的“红色国际大通道”,也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东方国家和周边地区的共产党进行人员、资金、技术、情报交流的“红色国际大通道”,更是上述国家和地区共产党之间交往互助的“红色国际交通线”。
早在1917年10月29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了第一次全西伯利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就有来自中国哈尔滨、满洲里、大连的代表参与。[25]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汇报:“现在打算(一旦共产国际较好地解决东方民族处的改组问题和经费间题)派出负责工作人员的考察团,到中国工作和了解情况,同中国来往的路线是:1.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取道蒙古(经恰克图、乌尔嘎(11)现名称为乌兰巴托(Улан-Батор)。)是12至 16天的路程;2.直接路线(伊尔库茨克—满洲里—哈尔滨—北京)是8至10天的路程;3.伊尔库茨克—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上海;4.伊尔库茨克—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哈尔滨或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26]利用以上的国际大通道,共产国际从1920年春在中国开始了系统的组织宣传工作,共产国际革命局(Ревбюро)在上海收购了一家印刷厂,用以印刷马克思主义文献,并且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向哈尔滨和上海运来资料。共产国际参与了1920年11月起在上海出版《共产党》杂志的工作,杨明斋在上海建立华俄通讯社(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采用塔斯社和其他欧洲新闻通讯社的报道,翻译成为中文并宣传出版,该通讯社在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都设有分社。因此,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马耶娃(Н.Л.Мамаева)认为:“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若干关键领域为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提供的财政援助:出版业、组织信息和宣传工作,组织翻译俄文党纲、俄罗斯联邦宪法、劳动法典,在上海开设俄语学校的活动(1920年),共产国际建立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的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27]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乌索夫(В.М.Усов)则从军事情报和秘密战线的角度评价连接中国与苏联的西伯利亚国际大通道的特殊意义:“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苏联各种情报机关赋予满洲和哈尔滨特殊的意义。哈尔滨和满洲同时被用作各种货物的‘转运站’和跨越苏中边境的‘走廊’——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员派往苏联学习、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例如1928年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利用这个‘走廊’,秘密越境)和返回中国时利用;另一方面是苏联公民到中国做地下工作时利用。”[28]
东方革命是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即定的革命目标,但是在与欧俄地区革命形势有着明显的时间差和地区差的背景下,在复杂环境和政治背景之下,各类派驻西伯利亚的党政军民机构之间出现了职能叠加,效率低下的现象。苏俄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共和国外交部、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红军总部第四局(情报局)、红军第五军情报局、共产国际以及西伯利亚远东的地方政权和党组织都以不同方式介入对华事务,参与在华人华侨中的政治宣传与鼓动。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副主席布尔斯泰因(М.Бурштейн)在给俄共(布)中央的信中抱怨:“东方民族部的工作因遇到以下一些很大的障碍曾停顿过,有时处干完全瘫痪的状态:1.同远东局关系不正常。寄给东方民族部的所有邮件、报告、通报、报纸等都被压在上乌丁斯克,或来得很晚,或根本就送不到目的地。不让来往民族部的信使和代表通过……”[29]
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决定将组织和发动东方革命,在东方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职能归口赋与共产国际。1921年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远东书记处,将1920 年 6 月设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职能转交远东书记处,舒米亚茨基(Б.З.Шумяцкий)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首任负责人。长期与舒米亚茨基共事的张国焘称“那时施玛斯基(舒米亚茨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30]。舒米亚茨基在 1921 年 2 月 12 日的第1号命令中宣布:“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 月 15 日的决定,以及 1 月 5 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代表处以书记处的形式获得批准。”[31]原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下属的东方民族部和苏俄人民委员会西伯利亚外交使团的大多数工作人员进入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机构。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Китайская секция)、日本部(Японская секция)、朝鲜部(Крейская секция)、蒙藏部(Монголо-Тибетская секция)和军事部(военный отдел)。中国部由阿勃拉姆松(М. М.Абрамсон)临时主持,后由张太雷和张国焘接任,下设两个科,第一科负责做西伯利亚华人和伊尔库茨克华人营红军士兵的工作,第二科负责在中国的工作;日本部由田口(Тагучи)主持;朝鲜部最大,由韩满申、金满根(俄文名谢列勃里亚科夫Сереболяков)和太洪主持;蒙藏支部由舒米亚茨基、萨赫扬诺娃(М.М.Сахянова)(12)布里亚特人,专门研究蒙古问题,曾在上海负责联系朝鲜共产党人。主持。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出版了铅印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Народ Дольного Востока)。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杂志,经常刊登有关日本、中国、朝鲜、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等国经济方面的文章,以及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及革命运动的资料。书记处情报部工作人员斯列帕克、佩尔林、考夫曼、拉依戈罗茨基专门为这个杂志准备材料。《远东人民》第一期上,刊登了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向中国、朝鲜和日本青年团发出的呼吁书,吁请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于1920 年 9 月 1 日至 7 日在巴库召开了第一次东方人民代表大会,来自30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抵达参加大会工作。这次大会的口号是“各国无产者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32]。而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原计划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即1921年11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11月12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目的就是揭露美国和日本在远东地区侵略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阴谋,呼吁中国、朝鲜、蒙古放弃对美国的幻想。但是来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未能在会议召开之前悉数到达,一些国家的代表甚至在12月初仍然在辗转赴俄的路上。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会议举办地址迁到莫斯科,1922年1月21日大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名称也由原来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Съезд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改为“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Первый съезд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时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干部的达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认为:“这一名称更符合大会的特点与与会者的成份。”[33]参会代表150人,来自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布里亚特和荷属印度尼西亚的30个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其中,朝鲜54人,日本16人,中国44人(张国焘、张秋白〈孙中山的代表〉、黄凌霜、黄璧魂、王东平、邓培、邓恩铭、高君宇、梁鹏万、贺衷寒、朱枕薪等)。蒙古14人。其他代表来自布里亚特、卡尔梅克、雅库特,以及来自印度的罗易(M.N.Roy)。因此,所有这些组织的活动都是直接针对中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东亚的中国(包括西藏、蒙古)、朝鲜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他们设法与蒙古、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对他们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并接收对苏联军事情报具有重要价值的作战信息,他们为唤醒东方革命的工作做出了贡献。”[34]季诺维耶夫(Г.Е.Зиновьев)和萨法罗夫(Г.И.Сафаров)致开幕词;列宁(В.И.Ленин)、托洛茨基(Л.Д.Толоций)、季诺维也夫、片山潜(Сэн Катаяма)和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担任名誉主席。
由于缺少通晓东方国家语言和国情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决定从东方国家大量调回工作人员,充实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干部队伍。1921年春,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Т.В.Кузнецова)和萨赫扬诺娃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
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同时,还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Восточной отдел Исполком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олодежи),达林自1921年就在这两个部门工作,曾在1922年、1924年、1926-1927年三次被派到中国工作。
1922年1月4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撤销。同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东方局(Бюро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Коминтерн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成立。该局帮助远东国家共产党出版宣传文献,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国际间联系渠道。
因此,从托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再到海参崴,从伊尔库茨克到上乌丁斯克再到乌尔噶,从西伯利亚到中亚,西伯利亚实际上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致力东方革命的“基地”和“司令部”。
三、在西伯利亚“发生”东方革命
“世界革命”的主张源自列宁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和对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的发展。他在1915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35],但这一胜利是以“全欧洲的革命”为基本条件的,因此“唤起国际革命”和从“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被列宁定位为“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36]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形势很快陷入低潮,列宁在1919年12月承认,“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37],强调将世界革命的重点转向“唤醒的东方”,因为东方各民族“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要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38]。
1921年10月21日,全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开设的“东方训练班”基础上建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简称东方大学)(13)1923年起更名为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им. И. В. Сталина)。。从1922年起,陆续在塔什干、巴库和伊尔库茨克设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分校。1925年11月7日,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ени Сунь Ятсена,简称中山大学)(14)1928年12月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1926年在莫斯科建立了国际列宁学校(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ленинская школа)。上述学校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服务于其“世界革命”和“东方革命”的战略,专门招收来自东方国家的学员,目标是“直接和积极地研究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经验,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国家的共产党的经验,研究当前紧迫工作”[39]。
共产国际对我国西藏的兴趣是由苏俄和英国的意识形态对抗引起的。由于西藏靠近英属印度,因此将西藏视为英国的利益范围,俄共(布)试图阻止其在亚洲的扩张,尽管他们自己也试图利用西藏作为渗透印度的基地。俄共(布)还担心英国通过西藏地方宗教领袖对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施加影响。由仁钦诺(Э.Д. Ринчино)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蒙藏部在这方面是主管机构。早在 1920 年 8 月 17 日,蒙古代表团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副负责人加蓬(Ф. И. Гапон)领导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西伯利亚代表团、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секции восточ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ского бюро ЦК РКП(б))与蒙古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举行三方会议,最后达成向蒙古提供武器、经费和军事教官的协议。[40]仁钦诺在伊尔库茨克会见了著名的蒙古七人代表团(15)成员有鲍道(Догсомын Бодоо)、丹赞(Солийн Данзан)、道格索木(Дансранбилэгийн Догсом)、劳索勒(Даржавын Лосол)、苏赫-巴托尔(Дамдины Сухэ-Батор)、查格达尔扎布(Дамбын Чагдаржав)和乔巴山(Хорлогийн Чойболсан)。,与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阿旺·德尔智(Агввн Лобсан Доржиев)讨论了布里亚特和蒙古问题。
1920年8月29日,尚在伊尔库茨克的蒙古代表团就近期蒙古人民党的任务向蒙藏部提出建议。其中:“1.苏俄可以扩大对人民革命党的公开和秘密援助,并协助恢复外蒙古自治。…… 4.派常驻党员到各中心点,鼓动组织党部、党支部。 5.在乌尔嘎建立党的中央机关,下设以下分支机构:1)宣传和出版; 2) 军事; 3) 信息和联系部,选派专门的军事和政治教官候选人到伊尔库茨克接受培训。 6.与苏维埃建立专门的互助机构。俄罗斯通过蒙藏部与有关组织沟通,向俄罗斯运送牲畜和原材料,俄罗斯为人民革命党在蒙古建立大小型工厂,生产日常生活必需品。”[41]
1920年9月19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蒙藏部开会决定苏联军队进入蒙古和组建蒙古自治临时政府。[42]1920年11月17日,蒙藏部决定为蒙古人开设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在第一批学生中有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1920年11 月底,苏俄政府将 150 吨白银和 10 万美元,以及武器、食品、制服移交给蒙藏部,用于目前在蒙古的工作。[43]1921年3月1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在恰克图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党,同时还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军。3月13日在恰克图召开蒙古劳动者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蒙古临时政府。蒙古临时政府致电舒米亚茨基,请求苏俄红军进入外蒙。舒米亚茨基从伊尔库茨克给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发去电报:“履行为与温琴(Р.Ф.Унгерн)作战的蒙古人民党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派遣教官的义务。”[44]1921 年 4 月 3 日,驻扎在伊尔库茨克的红军第五军接到命令,组建单独的蒙古布里亚特骑兵师与盘踞在乌尔嘎的温琴男爵指挥的白卫军的斗争。
1921年 7 月至 8 月期间,舒米亚茨基从伊尔库茨给齐切林发出了数封电报,汇报了解放乌尔嘎之后的蒙古形势,提出建立蒙古军队的方案,提出建立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蒙古代表处和派遣教官在蒙古组织军事、行政和经济工作的必要性。他还提交了报告《论在蒙古打败温琴的军事和政治结果》(О военн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тогах поражения Унгерн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45]。 建立于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第五军在1922年11月16日改名为“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народ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арм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设在伊尔库茨克、赤塔和海参崴,直接参与蒙古政权的建立和保卫。
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在19世纪中期后亦成为朝鲜人的移居地。苏联和当代俄罗斯著名的东方学和朝鲜学专家、莫斯科大学功勋教授米哈伊尔·朴(М.Н.пак)认为西伯利亚远东是朝鲜共产主义革命的发源地。[46]
1919年 11 月 22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东方民族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1920年6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处成立了朝鲜科(Корейская секци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上乌丁斯克的俄共(布)党组织都建立了朝鲜科。同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了全俄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коре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当时16个朝鲜党组织拥有成员和积极分子2305人。[47]1921 年初,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舒米亚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东方局(восточное бюро Коминтерна),其中就包括了朝鲜民族委员会代表。在朝鲜共产主义者内部,出现了“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伊尔库茨克派”认为朝鲜共产党首要任务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上海派”则认为朝鲜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朝鲜的自身民族革命。
1921年3月23日伊尔库茨克出版的《劳动的权力报》(Власть труда)报道:“3月19日举行了大型活动,伴随着音乐和隆重的仪式,伊尔库茨克火车站迎接了来自朝鲜、中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各个城市的参加朝鲜共产党首次成立大会的70名代表。”[48]1921年5月4日在伊尔库茨克隆重召开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来自 26 个组织的 85 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正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工作的张太雷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组委会主席李盛(Ли Шенг)提议将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蔡特金、舒米亚茨基选为大会名誉主席。舒米亚茨基在大会第二个发言,他代表共产国际祝贺朝鲜共产党的成立。他强调:“第三国际要求其成员成为积极而坚定战士。这是它与黄色(第二)国际的区别,这个国际不向其成员提出纪律要求,这个国际缺乏团结和严格一致的行动计划……俄罗斯无产阶级万岁!你们的朝鲜共产党将在好客的国家里建立。”[49]来自汉城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化名“茨”(“Ц”)同志用韩文致答谢辞:“我找不出任何话来感谢来自不同党组织的代表们。并且还自然地在心中产生了一个疑惑:我们能完成建立朝鲜共产党的任务吗?但是我相信,俄国同志会来帮助我们。在朝鲜无产阶级身处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时,只能有兄弟般的俄国共产党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希望成为斗争的胜利者,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建立自由的朝鲜。我希望我们很快地在第三国际所处的城市里遇到最亲近的朋友。因此,我们是无产阶级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奔走相告:各民族兄弟情谊万岁!”[50]
在1921年5月5日朝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舒米亚茨基作为大会主席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报告《朝鲜的国际地位和我们的关键任务》(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ореи и наши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政策正在摧毁朝鲜经济,在朝鲜民族、国家和社会中制造了诸多的不和谐和矛盾。5月11日,朝鲜的“茨”同志作报告《日本无产阶级和朝鲜贫民》(Япон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и корейская беднота)和《论在朝鲜的苏联式建设》(О советск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в Корее)。5月12日大会以59票通过了《朝鲜共产党党纲》(Устав компартии Кореи )。5月14日选举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南满忠(Нам Манчхун)、韩明世(Хан Мен Се)、德洪(Те Хун)、崔高丽(Чхве Горё,俄文名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Николай Максимович),金(А.А. Ким)等人,南满忠和韩明世受命派驻共产国际。5月15日,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闭幕。但是朝鲜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并未停止,它反映在伊尔库茨克的朝鲜人中,也反映在上海和朝鲜本土的朝鲜人中。1922年12月共产国际解散了朝鲜共产党的上海派与伊尔库茨克派。1923 年 2月,在海参崴设置“共产国际远东局高丽组”(Корейское бюро при дольневостчном отделе Коминтерна),推进建立朝鲜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
1920年夏,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设立了日本科,但是长期无法开展工作。同年11月从伊尔库茨克向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日本科还没有行使其职能,因为缺乏合适的党的革命干部”[51]。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很少,并且很多人与白卫军或日本政府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因此不得不从在美国的日本人中寻找可以信赖的人员。1921年10月1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库恩(Kun Bela)写信给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И.Н.Смирнов)谈及计划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远东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任命了三个人到代表大会组委会工作……委员会成员以下同志:吉原太郎(Таро Иосифара),朴和罗易,我将其描述如下:吉原太郎是著名的日本人,他来自美国……据美国同志说,他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了解工人运动,是一个可靠的同志。他还不是美国共产党的党员……在我们这里缺少最好的同志。‘聊胜于无嘛!’大家都这么说。”[52]在 1922 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了“远东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有 16 名日本人参加。有6人来自日本,他们是高濑恭司(Кнёси Такасэ)、德田奎伊特(Кюитн Токуда)、吉田羽子茂(Хазимо Ёсида)、田健虎(Книторо Вада)、北原荣一(Эйити Китамара)和小林信次郎(Сипдзиро Кобаясин)。[53]他们从日本来莫斯科路途极其艰难,要经过中国、苏俄远东地区,要穿越西伯利亚,一路上要躲避日本警察和军队。
1922年5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日本远征军中的宣传工作及其特点的问题》(Об агнтработе и ее характере в японо-экспедиционных войсках в Сибири)。主席团批准初步执委会特别委员会的决定:“指示片山潜马上出发去赤塔。”[54]1922年8月片山潜在赤塔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在外贝加尔的日本军队进行反战宣传,随后片山潜返回莫斯科。日本社会党党员、印刷商人北浦清太郎(Китаура Сэитаро)开始在日本军队进行反战宣传。1922年10月,日军从海参崴撤军。
鉴于西伯利亚外国干涉军撤离,以高尔察克、恩琴、谢米诺夫为首的白卫军被红军击溃,以及中国、日本、朝鲜共产党和蒙古人民党成立。1922年2月,共产国际宣布撤销远东书记处,上述国家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直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55]1923年1月,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在海参崴设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 бюро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ИККИ Коминтер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为在日本、朝鲜和中国开展运动的需要,建立由片山潜、马林和维经斯基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56]由于片山潜和马林实际上并没有到海参崴接受任命,维经斯基就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实际领导人,这一机构主要针对中国、日本、朝鲜共产党的工作,以及在上述国家收集情报和向上述国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转运经费。
中国与西伯利亚陆地相连,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党际关系,对于三者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入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助于正确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和苏联历史。俄罗斯学者马马耶娃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贯穿了20世纪20-40年代的漫长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 在此期间,目标、任务、互动形式都发生了变化。 然而,尽管双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误,尽管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矛盾,这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无益的。但是共产国际与俄罗斯和中国共产党方面,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仍然保持了稳定的相互关系”[57]。
1926年2-3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决定对共产国际作彻底的改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自1926年4月撤销。决定成立 11个地区书记处,维经斯基被任命为新的远东书记处负责人,书记处的成员还有谢马温 (В.Е.Семавин)、蔡和森、杨诺夫斯基(М.И.Янвоский)、金(А.А. Ким)、德洪和卡斯帕罗娃(В.Д.Каспарова)等人。为加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根据远东书记处1926年 4月27日决定,在中国上海迅速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1926年夏,维经斯基一行抵达上海,远东局随即开始工作。远东局的核心是俄国代表团,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拉菲斯(М. Г. Рафис)担任党的中央出版机构的编委,格列尔(Л.Н. Грен)研究工会问题,而福京(Н.А. Фодин)从事情报、宣传和青年工作,陈独秀和瞿秋白参加其工作。为了保密和人身安全,远东局的工作人员都使用了化名∶“谢尔盖”是维经斯基,“教授”是格列尔,“马克思”是拉菲斯,“年轻人”是福京,“老头”是陈独秀、“文学家”是瞿秋白。[58]远东局下设地区科,除同中、日、朝各国党进行联系外,还从事党建工作和帮助解决工会和青年问题。在远东局的成立会议上,讨论了远东局的工作性质,通过了它的基本工作准则,即吸收各国党的代表参加讨论党的问题,对于中国,“仅限于根据中共中央报告进行一般的指导,而不去取代中央,不去破坏党的正常发展”[59]。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远东局的工作并不满意,1927年初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被中止。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维经斯基和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在中国的最高代表机构,一直活动到1927年6-7月间,而鲍罗廷在其中拥有决定权。
结 语
中国第一本《西伯利亚史》的作者、著名的俄国史专家徐景学强调了研究西伯利亚史的重要意义,“由于西伯利亚同亚洲毗邻,所以它同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便是同这些国家交往。这种几百年间复杂的交往,既有和平,也有战争,有欢声笑语,也有血和泪。对西伯利亚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应放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分清是非,排解许多疑团。”[60]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东方革命中,与欧俄地区存在自然的地区差和时间差的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的“革命空间”和输出革命的策源地。从俄共(布)到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工作机构的变迁,可以清晰反映出苏联对中国等东亚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可以体察其东方革命战略的实质和特点。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角度看,该地区是其了解东北亚各国动向的窗口,是推行世界革命和在亚洲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东亚各国抗日而确保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桥头堡。对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东亚共产主义力量来说,该地区是寻求苏联指导、人员培训和物资援助的大后方,同时在20世纪20-40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以及东亚各国共产党之间是在这一广袤地区进行交流互动的。西伯利亚作为东方革命的“基地”和“司令部”,实际上发挥了“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前哨”的特殊作用(16)1969年伊尔库茨克州苏维埃为了纪念共产国际成立50周年,在伊尔库茨克市中心设立“共产国际大街”(yлица Коминтерн)。此外,在伊尔库茨克还有“列宁大街”(yлица Ленина)、“苏赫-巴托尔大街”(yлица Сухэ-Батора)、“特里谢尔大街”(yлица Трилиссера)和“工农红军第五军大街”(yлица 5-ой армии),在南萨哈林斯克设有片山潜大街(yлица Сэн Катаям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