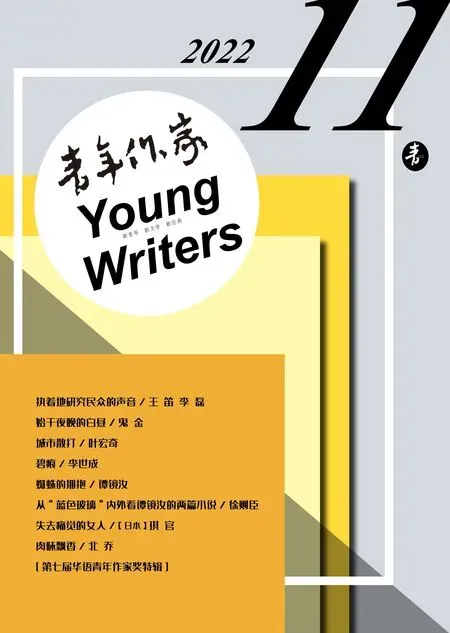克澜湾
天 野
安然下了手术台,倍感轻松。退休前最后一次做手术,将告别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妇产科。拧开水龙头洗手,不用看表,也知道过十一点了。换完衣服,拎包走出医院大门,街道只有她一个人。
直行二百多米,右转进入永丰巷,走五百米就是自家小区。肚子早饿过站了。喉咙干得要爆炸,加快脚步想快一点到家。一天五台手术,双腿像绑了沙袋,不听使唤,怎么都走不快。
永丰巷口容得下两个人。一个人很宽松。走进去几十米,安然总觉得有人跟着自己,心里一紧,似乎还听到不紧不慢的脚步声。路灯是新换的,比过去亮许多。回头却不见人。
敏感多疑,有点神经质。丈夫受不了安然这毛病。两年前单位满三十年工龄可以退休,办完手续去加拿大陪女儿。分开,我们会过得更好。丈夫临走前的话。
安然回到房间,坐在藤椅上打起盹来。恍惚间,觉得脚趾缝发痒,又觉什么东西从脚趾缝里爬出来,她歪着脑袋动了一下脚,半睁半闭,想看是什么东西。芝麻样的黑点,一点点从脚趾缝里滚出来,在脚背慢慢散开,感觉不到它们的温度,但能觉察行进的路线是向心窝而来。再瞧,那黑点变成一只只蚂蚁,成群结队,颇为壮观。再细瞅,它们长着蚂蚁身子、婴儿头。耳畔隐隐传来啼哭声。她一脚蹬开木凳,抖落双腿,人像鱼一样抽动,无法直起。耳鼓被什么东西击中,雷鸣般的脚踏声,不绝于耳。
安然知道有的事情终究无法逃避,或者说是绕不开,时至今日,只能自己去面对。
重回克澜湾?没人明白安然心中忐忑多于欣喜。安然从挎包里取出一本发黄的《赤脚医生手册》,目光停留几秒。一支黑杆钢笔同《赤脚医生手册》一并塞进挎包。草绿色挎包有些年头了,包盖上隐约可见“为人民服务”字样。
安然盯着包,克澜湾的清风和阳光在她眼里闪过。马鹿、黄羊、棕熊、灰狼、红狐、獾猪从她身边穿过,没有袭击冒犯她的意思。自顾自地走向密林深处。一只成年白肩雕从贝加尔湖飞来,盘旋在她的头顶,久久不肯离去。不远处高耸的雪峰张开双臂要拥抱她。平静的水面,陡然间浪花如巨掌拍向她。脚下的路炸裂开,涌出一条宝蓝色河流。她挥舞胳膊呼救。一个低沉的声音挤进她的耳鼓,胆小鬼。白肩雕叼住她的衣领,在空中飞翔几圈。眼里是阔大的克澜湾,光亮刺眼。再睁眼,河流的位置出现一座石头垒砌的墓地。
晕车,吐得一塌糊涂。到县城吃午饭,其他人吃得欢实,安然只喝了半碗温开水。接着,从县城去萨尔曼草原的克拉镇,车速慢,安然坐副驾驶位置。路是砂石路,小坑套大坑,能把心肝肺颠簸出来,抵达克拉镇时已是晚饭时间。
安然在宿舍整整躺了一天,才缓过劲来。心里嘟囔,这鬼地方,这辈子不想再来。
牧区缺医。原本对于已是学校学生的安然而言,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临来克澜湾时,突然接到通知,应届毕业生统一到牧区实习,于是,安然仓促中拿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欣然领命下基层了。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克澜湾,是安然骑马去艾德力家。艾德力是林区护林员。之前见过一面,这次在医务室遇见艾德力。他明显手足无措。艾德力的妻子孜热娜快要生了,妻子痛得嗷嗷叫,艾德力一个大男人根本帮不上忙,急慌慌跑来求救。乡卫生院的医生外出去巡诊,只有安然这个实习医生留守,怎么办?虽然在省城实习期间,也做过助产士,可让安然独当一面帮孕妇接生,心里还是没底。总不能置之不理吧?无奈,只能惴惴不安地赶往艾德力家中。
体形瘦小的孜热娜,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束在消瘦的脑后。若不是隆起的肚子,误当她是学生,稚气未退的脸上一双羞涩的眼睛,不敢多看安然一眼。一问才知,比安然大一岁。
安然轻轻抚摸孜热娜圆鼓鼓的肚子,胎儿臀位,顺产需要调整姿势。于是,安然镇定地指导孜热娜用力。她小心翼翼慢慢调整,费好大劲,差不多半小时后,孩子生下来,一个肥嘟嘟的男孩。艾德力欢喜不已。安然额头的汗珠顺颈滑入前胸。她顾不得擦拭,孜热娜的胎盘没下来,再伸手进去时,发现还有一个胎儿,横位。安然身子一紧,停顿几秒,果断调整胎位,大声鼓励孜热娜说,加油!使劲!使劲!
孜热娜筋疲力尽,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哪有劲顾得上胎位不正的第二胎?
安然拿毛巾擦几下孜热娜脸上的汗水,柔声说,孩子不能长时间待在肚子里,再努力一下。孜热娜眼皮微微张开一下,无力地又合上。身子软得似面团,一点劲都使不上,急得安然满头大汗,不停地按压孜热娜的肚子。一个小时后,孩子在安然的辅助下,终于生出来了。谢天谢地,孜热娜的命保下来了,婴儿因窒息而夭折。安然双手托着婴儿,觉得这是块千斤巨石,能压垮自己。艾德力急忙接了过去。
安然无法控制自己,转身抬起右胳膊,用衣袖擦拭模糊的眼睛。疾步迈出屋门。站在屋角浑身发抖,不停抽泣。
安然使劲打自己。如果自己早点发现,如果自己手法更娴熟,如果……
愧疚不安如蛆虫爬满全身。
一切都是天意。艾德力安抚完妻子,又安慰安然。安然收拾完东西,背着棕红色药箱,左肩挎着草绿色帆布包。人如树叶,一股风都能吹跑。沮丧无力地摇摇头,长叹一口气,叮嘱艾德力照顾妻子,转而走向拴马桩。
一个月后,艾德力携带一面锦旗来到镇医务室,憨厚淳朴的艾德力并没有因为难产而夭亡的婴儿责怪安然。孜热娜康复了,新生儿阿尔多斯的笑声感染全家人。夫妻俩没什么不满意,而且,此番艾德力除了用一面锦旗致谢,还带来了妻子孜热娜的小小心愿,请求安然做阿尔多斯的“脐带妈妈”。
小小的医务室热闹起来,镇卫生院院长王国忠是名有经验的医生,听了艾德力惊心动魄的叙述后,一边欣喜,一边暗自夸赞安然的冷静和胆量。心想,莫说是在牧区,就是县医院,但凡遇到难产,医生都是小心翼翼征求家属意见,保大人,还是保小孩?于是便热情地劝导涨红脸的安然:认下阿尔多斯。安然自己还没有结婚,不知道说什么好。望着艾德力真诚的目光,羞涩地点点头。如此,安然成了阿尔多斯的“脐带妈妈”。
安然接到返城消息,第一时间骑马去向艾德力一家告别。一岁多的阿尔多斯见安然把马拴在自家屋前的树桩时咧开嘴笑着,扭扭歪歪向安然迎上去。
安然抱起阿尔多斯,在小脸上左边亲一口、右边亲一口。艾德力说,我们的家跟你的家一样,欢迎你常来。安然脸颊挂着两行湿漉漉的泪珠,阿尔多斯的小脸贴在泪珠上。
安然返城进入省人民医院。工作一年,公派去省医科大学进修四年。回来后,在省人民医院妇产科坐诊。面对一个个生命降临的喜悦,也要面对一个个夭折生命的悲伤。
有一阵子,安然被派往偏远的库拉县医院,帮助县医院提高妇产科水平。百姓听说省医院的医生坐诊,蜂拥而至,没有休息日,只有接待不完的孕妇,做不完的手术。当然也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不肯引产的女人,歇斯底里吼叫谩骂,不过瘾还会拳打脚踢。有一名生了五个孩子不肯带环的女人,脱下带泥巴的鞋子扔到她脸上,砸出鼻血。一名产妇生出兔唇男孩,无厘头地对她叫嚷说,你干过什么孽障的事?
每当夜深人静,安然会陷入深深的不安与自责中。每每这时,她吃不下饭,哪怕肚子叫个不停,也没有一点食欲。与一个个不眠之夜斗争无果后,她不得不借助安眠药入睡。面色暗沉,眼圈青紫,目光无神。谁都不会想到她是一名年轻的妇产科大夫。
她没有告诉丈夫自己所经历的这些事。只是夜里被噩梦惊醒。梦里总有黑影挥之不去。
幸好,县医院要升级,安然回到了省人民医院。
安然言语日渐寡淡。丈夫板着脸埋怨,回到家,跟块石头一样,死气沉沉。
不只在家里,在科室,非必要,安然极少说话。更难见脸上有笑容。私下里同事们也小声议论,安大夫怕是有什么秘密,不然怎么不合群。嗨,生性孤僻的人,没什么奇怪。不管怎么说,总觉得不对劲。八成是更年期综合征。
安然偶尔也会听到同事窃窃私语,回应的方式是默不作声。这下,更无法猜透她的心思了。她成为同事眼里的冰山,谁也不知山里藏着什么。科室里的人渐渐对她敬而远之。
一天,护士冲里屋的安然说:安大夫电话。安然接过电话得知对方是艾德力的儿子阿尔多斯,他考上省警察学校,父亲叮嘱他,一定来看看安妈妈。
安然心里一阵慌张,像是听到逮捕令。半晌才平复心绪。她说自己有手术,让他安心学习。但他执意要送点东西过来。她说让护士去门卫室拿。
安然站在医生办公室,透过宽大的玻璃,见到高大帅气的阿尔多斯。阿尔多斯将一个手提袋交给护士。望着阿尔多斯离去的背影,安然脚粘在地上,挪不动。
安然想起那个夭亡的婴儿,心一沉,手提袋掉在地上。
晚上,安然做完手术从医院回到家,已是凌晨一点多,闭着眼睛,恍惚间,又到克澜湾,回到艾德力家,这一次,安然清晰地在男婴脸上看到眼角渗出的泪珠。哇!一声尖叫。安然从床上弹坐起来。丈夫忙按亮台灯,惊讶地问,怎么了?
安然脸色煞白,望着一脸惊恐的丈夫说,没事,一个梦,睡吧!丈夫端过床头柜的保温杯递给她说,喝口水。她摇摇头,缓缓躺下。
此后,阿尔多斯每个学期返校都带着东西来看安然,她总以各种理由拒绝见面,东西留在值班室让护士去拿。
安然并没有将阿尔多斯的土特产拿回家,而是分别送给了同事。为什么这么做,安然自己说不清楚,似乎这样是最好的方式。后来,安然让科里的护士长给阿尔多斯送过一些高能钙、螺旋藻、西洋参、蛋白粉等东西,并捎话过去,祝愿他母亲孜热娜身体健康。
非典那年,阿尔多斯毕业了,因为疫情,没有来向安然道别。他在电话里对安然说,有机会,一定带安妈妈回克澜湾住一阵。她在电话这头说,晕车,哪里都去不了。
那一天肯定会到来的。阿尔多斯语气坚定地说。
回到家,安然一脸疲惫,丢下包,一坨泥似的堆在靠窗藤椅上。扯过搭在藤椅上的毛巾,擦了擦脸颊,木然地望着窗外的槐花想,要是一朵槐花多好,没有这些闹心的事。
一晃五年,槐花再次开时,安然从省里抱回来一个“三八红旗手”荣誉证书。她顺手搁在书柜里。洗过水,倒一杯开水。她从克澜湾回来就习惯了喝开水,虽然家里各种茶叶放过期了,也不会打开冲泡一杯。家里的水有股子漂白粉的味,实在难咽,但习惯形成就不好改变。喝水时,眼前会闪过蓝莹莹的克澜湾。
牧民们眼里克澜湾的水很神奇,被虫子叮咬,或者不小心蹭破点皮,不用抹药膏,提一桶克澜湾的水,太阳底下暴晒一天,用水冲洗,很快就好了。安然起初听来不可信,但去山上挖椒蒿时不慎划破脚踝,冲洗两次,很快结痂了。
安然不止一次梦想能喝到克澜湾的水,可这样的想法停留不到三秒,立刻被另一个奇怪的庞然大物碾碎。
安然尝试着跟本院精神科大夫交流,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想自己是医生,又何必再求助其他人。找来相关书籍翻看。看了几个月,疑虑加重,甚至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是荒野里的一只狐狸,转世才如此多疑。难道仅仅是多疑?似乎不全是。那还有什么恶魔蛰伏在心里呢。想来想去,还是没想明白。
省电视台开了一档公益健康讲座,请安然去做嘉宾,节目录制中,安然对着镜头坦然地说,如今育龄妇女幸福多了,医院各种先进的检测仪器,帮助医生提早筛查出疾病,争取了治疗时间,挽救了不少生命。过去不敢想,许多妇女,尤其是农牧区育龄妇女吃了这方面的亏,检查不及时,或者没有条件检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自己没保住性命,有的腹中胎儿也没保住。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的恩赐。我们都要好好善待。说到这里,安然眼眶里汪着泪花,声音有点哽咽。
讲到这,安然心慌耳热面烫,有种负罪感,总觉得对不起一些产妇和生产中夭折的婴儿。这种感觉像一把无形的剑,一次次刺伤她的心房。后来体检查出她有房颤,她一直觉得与这种心理有直接关系。
在其他妇产科大夫看来,是手术总有风险,医生不是神仙,万无一失,各种不确定性必然存在,个人是无法掌控的。不能看清这一点,就无法当一名医生。
说服别人容易,说服自己难上加难,甚至一辈子都说服不了。
一天夜里,安然值班,来了一个急诊。产妇有心脏病,羊水破了,急需手术。安然从护士手里接过单子扫一眼,在家属一栏看到阿尔多斯几个字时,心里咯噔一下,是重名,还是曾经接生过的男孩阿尔多斯?当家庭住址一栏写着萨尔曼大阪克拉镇时,她确定是艾德力的儿子阿尔多斯没错。
此时,安然才想起来,自从自己换了手机号,再没有接过阿尔多斯的电话,细算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他们的音讯了。眼下手术是大事。
安然越发感觉不如从前,反应慢不说,手也不利索。幸亏有助手协助,真不知全程手术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想着,安然收紧身子,头歪向左侧。她右耳的听力不如左耳。这样护士说话也许能听清楚些。
出了手术室,安然在医院过道见一个面庞黑红的男人,没错,这就是阿尔多斯,只是人胖了一圈、黑了一层。安然摘下口罩说,女孩,4.2 公斤,母女平安。阿尔多斯拉着安然的手一个劲道谢。直到护士喊安然时,才松手。
那一夜,安然记得入睡前吃了安眠药,可半夜醒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安然不再看自己。人不借助参照物看不到自己。镜子、玻璃、不锈钢一切可以照到自己的物体统统从家里拆除或者更换。
安然习惯早起,坐在藤椅上,窗户不是全部打开,只开中间两扇。这样一来,窗外院里槐树直挺挺地守候在那儿,像在等候吩咐的仆人。
膝盖摊着报纸,是好几年前的旧报纸。安然举起报纸,同一段话读了七八遍,文字开始旋转,像是飘在空中带翅膀的蚂蚁。
用力拍打。飞舞的蚂蚁不见了,报纸破了。
有那么一次,安然梦里回到了克澜湾,她没去看望艾德力,而是去找阿尔多斯同胞弟弟,当然是那个夭折孩子的墓,找了一天一夜,怎么都找不见。安然绝望地哭泣,引来了喜鹊、金翅雀、红嘴鸥、戴胜、伯劳、巨嘴沙雀、老鹰,甚至还有白肩雕。不同的鸣叫声淹没了安然的哭声。
砰的一声,惊醒了安然。风挤进窗户,推倒窗台上的玻璃水杯,滚落下来,碎了一地。
安然浑身无力,起不来床,只好请假在家休息一天。
咚咚咚。有人敲门。这声音太稀罕了。安然身子蓦然有了劲,努力从地上爬起来,整理一下衣服,缓步向房门走去。
安妈妈好,我是阿尔多斯。安然愣住,眼前身材壮实面膛黑红的男人是那个略带羞涩单薄的阿尔多斯,是那个生下来又黑又瘦的孩子?
定睛再看,眉眼间跟艾德力一个样。
阿尔多斯的到来,令安然意外。已是萨尔曼林区派出所所长的阿尔多斯,握着安然的手说,安妈妈,回去后忙工作忙孩子忙大大小小事,跟您联络少了。阿尔多斯“机关枪”似的一通话,安然的思绪一时跟不上。脑际出现最多的画面是他刚出生时的样子。一想到这,安然身子不由哆嗦两下。
看,这是新采的羊肚菌,增加免疫力。阿尔多斯将牛皮纸袋递给安然。她接过来闻到新鲜羊肚菌特有的香气。
说什么好呢?这些年都记得我,不时捎来东西,都不知道拿什么谢你们一家。安然将纸袋放在茶几上。
喝点茶。安然问。
安妈妈,不喝了,我还要去办点事。你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来接您。从省城到萨尔曼修通了高速公路,一小时就到。
阿尔多斯要走,安然忙从角柜拿出一盒安化黑茶塞给他说,捎给家里人,心意。
安然将阿尔多斯一直送到小区门口,看着他上了出租车,才转身返回。
进家门,脱去外套,坐在藤椅上,从兴奋到平静,持续一个中午。啥也没干。藤椅怕是累了,吱吱作响。她双手搭在藤椅扶手上,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似乎受到莫大委屈,越哭越伤心。这种无端袭来的心绪一直折磨着她。
安然患有眩晕症,坐车坐船坐飞机超过半小时,头晕恶心。各种眩晕药无济于事。安然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的日子,时光变慢了。
那是夏日最热的几天,空气像是被玻璃一样耀眼的阳光炙烤得癫狂。她穿件绵绸短袖衣裙,手里拿两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充当扇子,不时扇动几下。一个人的生活简单。一天两顿饭,做一次吃一天。更多时间交给藤椅,交给发呆。
恍惚间,觉得脚趾缝发痒,又觉什么东西从脚趾缝里爬出来,她歪头动一下脚,眼睛半睁半闭,想看一眼是什么东西。芝麻样的黑点,一点点从脚趾缝里滚出来,在脚面慢慢散开,感觉不到它们的温度,能觉察到行进的路线是不断向小腿上方前行。耳鼓被什么东西击中,雷鸣般的脚踏声,不绝于耳。一只拳头飞过来砸在她的头上,她嘴巴张得老大,没叫出声,人晕倒过去。
醒来时,窗外漆黑,没有月亮的夜晚。萨尔曼大阪像时光老人一样走进她的记忆。
安然不敢再想,几十年间,经历太多无法忘记的瞬间,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妇产科大夫,见得最多的是婴儿。他们一个个长大,融入人海。有的还没有开始生活,便悄然离开。像一粒灰尘,无影无踪。每次想到这时,那个幽灵抓一下她,怎么驱赶都无法撵走。
克澜湾该回去看看。至少给那地方一个交代,毕竟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人。太久没有离开屋子。安然鼓足勇气拨通了阿尔多斯的电话。
阿尔多斯家的牧场在克澜湾。过去这里是集体所有,后来分给牧民,他家有八百亩草场。距克澜湾不远处的山坡上有间老屋,过去艾德力放牧时用来休息的地方。如今闲置,简单收拾一下住人没问题。细心的阿尔多斯拿来多功能LED 灯,一部能随时跟他保持联系的对讲机,灌满热水的保温桶,一个野外用的酒精炉,储满电的暖宝,以及奶酪、馕、包尔萨克、干果、黄油、果酱和盐等。
跟艾德力一样细致周到。安然说。看着桌上的物品,由衷感激阿尔多斯的照顾。
您,我们跟前,妈妈一样的人。住得好,我高兴。阿尔多斯说。顺手把一只玻璃瓶放在炕桌上。这个花可以插一下。
点头微笑。安然心窝滚烫。
推门见山见水,安然很满意。夏天像蜜一样稠的阳光从木格窗户中流淌进来,洒在绚烂的花毯上。满屋子都是花香的感觉。
您一个人住这里可以吗?阿尔多斯的目光从鼻侧漏过来探寻地看着安然。
习惯了独居。安然说。慈祥的目光落在阿尔多斯黑红的脸上。不用担心。
中午在阿尔多斯家里吃了一顿清炖羊肉,胃满满当当。下午不想吃什么东西。安然从包里掏出披肩,披在肩上。把吊床搭在胳膊上。这个年纪爬山是奢望的事,四处走走没问题。累了在吊床上歇息一会儿。这是女儿嘱咐她的。她不是母亲,像是孩子,听从女儿的指令。
雪山和呼尔河在牧民眼里都是神灵。常有牧民来这里祈福和忏悔。过去,安然对此半信半疑。她不相信岩石构造的山,能体察人复杂的情感。也不能理解,一条峡谷中的河能通晓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不知不觉,安然走到克澜湾畔,那里有一个自己。意料之中的事。她在克澜湾灌了一杯水,痛快地喝下。浑身轻松许多。她渐渐明白,许多事,你想抗拒、想忘记、想抛弃、想挽留,却无能为力。
安然的记忆被激活,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模糊的身影,都接受她的检阅。不知是山给她壮了胆,还是河给了她底气,没有抽泣,连平日不请自来的恐惧、不安和焦虑,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夜幕降临,安然借着月光在草地上漫步,听不到脚步声,四周安静得有点失真。夜风伸出婴儿般的手,牵引着她向一处幽暗的山湾走去。
月光下,山湾开阔地有几处石头堆。一处体积最小的石头射出绿宝石般的光芒,照亮安然全身。安然突然意识到风把她带到了墓地。她想再往前一步,风死死拽住她的胳膊,身子抖动几下,站在原地。抖动中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暖瓶打碎了,又像是击穿了玻璃墙,抑或是锃亮的铠甲被甩出去的声音。
此时,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阿尔多斯。问她怎么样。安然说,感觉好极了。
需要什么帮助么?阿尔多斯问。
安然说,帮我联系一下镇卫生院,我想以后每个周末来卫生院志愿服务,趁着自己还能动,为牧民多做点事。
现任镇卫生院院长是老院长王国忠的女儿王珊珊,省医学院毕业的。阿尔多斯说。
女承父业,太好了,带我去看看。安然说。
阿尔多斯说:夜晚山里凉,早点休息,明天早晨去接您。
安然抬头望向星空,明月正静默地注视着她,不觉耳际滑过一串冰凉的串珠,无声无息跌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