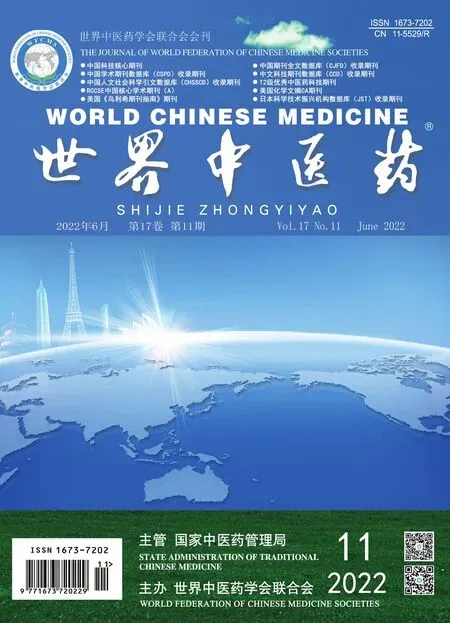疏肝健脾法在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中的应用
陶丽芬 彭卓嵛 李桂贤 蔡林坤 蓝斯莹
(1 广西中医药大学,南宁,530001; 2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南宁,530023)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属中医“痢疾”“久痢”“泄泻”及“肠澼”等范畴,临床以黏液脓血便或血性腹泻、里急后重为主要表现[1]。关于该病病因病机,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言:“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必先以怒挟食,致伤脾胃……此肝脾二脏之病也,盖以肝木克土,脾气受伤而然。”《医方考》中亦有“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肝责之实,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之论。可见UC虽病位在大肠,但肝脾功能的失调在UC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肝郁脾虚是临床上UC发生的关键病机之一,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肝郁脾虚证在UC中的多发性[2]。因此疏肝健脾法的研究对于中医治疗UC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肝郁脾虚是UC发生发展的重要病机
1.1 肝脾在生理上相互为用,维持正常消化功能 肝主疏泄,喜调达而恶抑郁,脾主运化,宜健运而恶壅滞,肝疏脾运是维持正常消化功能的重要基础,两脏生理功能上相互影响、密不可分。首先,脾的运化有赖于肝的疏泄。《血证论》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可见木能疏土而脾滞以行,土得木而达。脾得肝之疏泄、分泌胆汁才能升降相宜、运化功能健旺,从而为脾胃受纳腐熟、运化水谷、通利三焦气机升降提供保障。其次,肝的疏泄有赖于脾的滋荣,《医宗金鉴》曰:“肝为木气,全赖土以滋培。”脾胃健运、升降有序则水谷精微输布有序于肝,肝木得阴血滋濡则刚柔相济,肝气冲和条达、疏泄有常,即土旺木荣之意。由此可知,肝脾两脏在生理上相互为用、相得益彰,共同维持着水谷精微的消化吸收,诚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言:“肝脾者,相助为理之脏也。”
1.2 肝郁脾虚发为UC,影响疾病预后及转归 正常情况下机体内肝木脾土的关系以承平为度,承乃制,“肝木疏土,脾土营木,土得木而达之,木赖土以培之”。肝疏脾运协同作用,以维持体内水谷精微消化、吸收、输布功能的正常,是保证机体气血津液平衡的重要环节,但当木太过或土不及,这种平衡就会遭到破坏。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思虑过度、焦躁紧张等精神心理因素普遍存在,不良情绪刺激易导致肝失疏泄之职,气机失调、肝气郁结为患。因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且肝脾两脏为疏泄与运化相互为用的关系,肝木一郁,疏泄不及,则先克脾胃之土,导致脾土阴凝板滞,久壅不运而成虚,形成肝郁脾虚之证。肝脾同损则气血生化不足,引起肠络黏膜失养,肠黏膜屏障功能下降而易受湿、热、瘀、毒等病理因素侵袭。此外,木壅土虚、运化失常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湿滞壅滞肠间,日久湿从热化,湿热熏蒸,搏结气血,肠道传导失司,脂络受损,气凝血滞,腐败成疡,化为赤白脓血而下。加之肝气郁结阻滞,血气凝滞、腑气不通,故UC患者常有腹痛、里急后重频发。并且UC具有缠绵难愈、病程漫长的特点,临床UC患者多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情志不舒症状,使得气滞郁结,木壅土滞,脾虚更甚,脾虚难复,可见肝郁脾虚因素始终贯穿在UC整个病理过程之中,是关系到疾病发作和愈合的关键环节。现代研究发现,肝主疏泄与调节下丘脑-垂体轴有关,脾主运化主要与胃肠功能有关[3]。肝气郁结后出现的焦虑、抑郁等症状可直接作用于支配胃肠运动的迷走神经,使胆碱能神经兴奋性减弱,从而抑制胃肠运动功能,胃肠道动力不足而引起分泌、消化、吸收障碍[4-5],导致出现纳差、腹痛、腹胀、腹泻等UC相关胃肠道症状。此外,肝郁、脾虚均可对胃肠道黏膜屏障具有一定的损害作用。肝郁可通过改变胃肠黏膜的局部微循环、免疫微环境,以及黏膜上皮细胞增殖与凋亡等来影响炎症的发展和溃疡的愈合[6]。另有研究表明,焦虑、抑郁通过影响神经内分泌介质的主要效应物如乙酰胆碱、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促使抗炎反应失衡,可能是UC复发、转化的潜在机制[7]。脾虚引起肠黏膜损伤的机制可能与胃肠运动的异常、胃电节律的紊乱、胃肠黏膜细胞的凋亡、胃肠激素分泌的异常等有关[8-9]。这些研究思路和成果从现代分子生物学角度支持了肝郁脾虚病机从心理、神经、免疫系统等交互作用,影响着UC的发生发展及预后转归,为中医临床从肝郁脾虚论治UC和疏肝健脾法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2 疏肝健脾法在UC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肝郁脾虚是UC发生、发展的关键病机,临床上亦发现UC患者普遍存在身心症状[10-11]。契合该病肝郁脾虚的病机特点,治疗当以调和肝脾为切入点,正如叶天士所言:“治痢之大法,不过通塞二义,肝脾并重。”UC治疗当以疏肝健脾为治疗要旨,疏肝理气、调畅气机为先,益气健脾、扶正祛邪并重。使肝气调达则情志得舒,胸胁胀满窜痛自消,脾胃健运、统摄有常则胀除食复,气化湿去,黏液脓血便自止,腹痛后重可除。
临床上已有不少医家采用疏肝健脾法取得了较好疗效,所用方剂从柴芍六君子、痛泻要方、逍遥散等经方到各种自创方,涉面较广。如吴春江和赵双梅[12]认为本病多与情志失调有关,辨证多为肝郁脾虚,以痛泻要方加减治疗,总有效率为94%,而宋小莉[13]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痛泻要方的有效性。全国名老中医李桂贤教授认为UC为本虚标实之疾,以肝郁脾虚为本,湿热内蕴为标,临证运用经验方加味柴芍六君子汤治疗肝郁脾虚型的UC患者,疗效颇好[14]。李帅军等[15]认为UC病机基础为肝气郁滞,横逆犯脾,脾胃运化失常,并给予痛泻要方化裁而成的肠舒颗粒治疗肝郁脾虚证患者,结果显示肠舒颗粒可显著减轻患者临床症状,改善肠黏膜病变,并且下调患者血清一氧化氮水平及白细胞介素-8、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的水平。彭志红等.[16]、杨桦和邓金凤[17]认为本病与肝郁脾虚关系密切,将肝郁脾虚型UC患者随机分为2组,分别予以逍遥散化裁方、柳氮磺胺吡啶治疗,结果显示逍遥散化裁方在治疗本病上具有疗效显著、复发率低的优点。陈旭[18]认为肝郁脾虚证是UC临床常见证型,并采用疏肝健脾颗粒治疗29例肝郁脾虚证型UC患者,以柳氮磺吡啶肠溶片作对照,结果表明疏肝健脾颗粒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柳氮磺吡啶肠溶片组。李淑英等[19]认为UC主要病机为情志因素致肝气郁结,横犯脾胃,脾运失常,传导失司,日久湿浊内蕴,气血凝滞,肠络失和,血败肉腐成疡。并将142例患者分为观察组(柳氮磺吡啶片+健脾疏肝煎)和对照组(柳氮磺吡啶片+中药安慰剂)进行干预观察,结果表明健脾疏肝煎可显著减轻肝郁脾虚型UC患者的临床症状并改善肠黏膜病变。
现代医学认为UC的发病机制涉及免疫、肠黏膜屏障、肠道微生态、凝血等多种因素,中医药对本病的干预作用机制相应地也多从以上几个方面研究[20-21]。目前疏肝理脾法治疗UC的机制研究报道不少,但研究尚未深入全面,大多集中于神经-内分泌-免疫、胃肠道免疫、肠黏膜屏障、肠道微生态机制的研究。如秦震声和张燕生[22]研究发现,疏肝理脾法可能是通过作用于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促进抗炎因子的产生而发挥治疗作用的。顾立刚等[23]的研究结果表明,疏肝健脾方药可使结肠黏膜组织一氧化氮含量和髓过氧化物酶活性下降,从而减少肠黏膜组织炎症细胞浸润,促进炎症修复。肖永峰[24]、蒋志滨等[25]的研究结果显示,痛泻要方可通过调控肝脏硬脂酰辅酶A去饱和酶1与肠道5-羟色胺的平衡,下调肿瘤坏死因子-α等炎症介质途径,或通过提高结肠黏膜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基因和蛋白表达途径,调节肠黏膜免疫抗炎机制而对肝郁脾虚型UC大鼠起到治疗效果。李哮天等[26]的研究证实加味柴芍六君子汤可能是通过调整肠道菌群,以及促使体内炎症介质如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10的分泌增加,抑制抗炎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和γ干扰素等水平的下降而有效治疗UC。牛跃辉[27]的研究也表明了加味柴芍颗粒可通过降低UC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和C反应蛋白等水平改善UC患者炎症状态,改善病情。这些临床观察及实验药理学研究成果为疏肝健脾法治疗UC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也为中医药治疗UC的机制和靶点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3 研究不足和展望
但是,中医对UC的研究多侧重于临床观察,且临证用方繁杂不一,疗效评价机制尚未完善,也存在着研究样本量较小,可重复性差的不足。对于实验研究方面的研究,仅提示了疏肝解郁方治疗前后某些指标的变化,并且特异度灵敏度高的检测指标尚未确定,目前的实验研究也尚未能充分反映UC慢性病理过程中相关指标的复杂性、动态性变化。此外,实验研究多集中于免疫机制研究,对于其他如肠道微生态、神经-免疫-内分泌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因此,未来的研究方向:1)在临床研究中应增大样本量,完善疗效评价机制。2)实验研究上应深入全面探究疏肝健脾治法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内在联系,并加强特异度灵敏度高指标的研究;结合中医整体观,从遗传基因、通路等多角度、多机制研究疏肝健脾法治疗UC的作用机制和靶点,为基于此治法研发出治疗UC更有效的药方提供依据。
4 小结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证医学体系的核心,而治法上贯理、下统方药,在辨证论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治法的研究是中医取效的关键环节之一。肝郁脾虚证是UC临床多见的证型,针对肝郁脾虚的病因病机所确立的疏肝健脾法在UC治疗中的应用已日趋成熟。并且证实基于疏肝健脾法选用的疏肝健脾方对于缓解患者症状、改善黏膜损伤等确有疗效,在实验学指标如血清炎症指标、肠道菌群的调节方面也有一定的效果,不良反应少,远期疗效可观,与西医治疗比较,确有其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