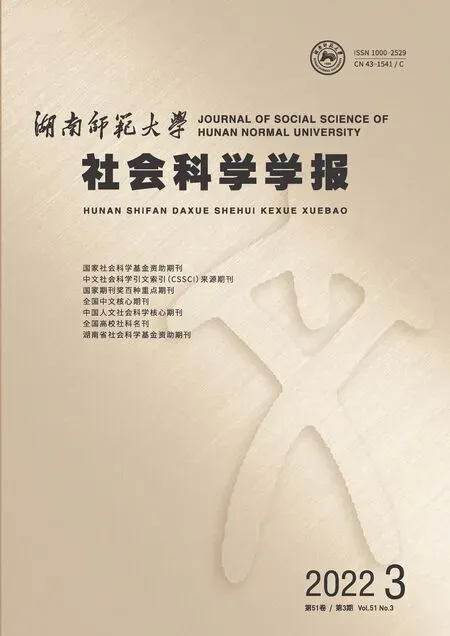国际投资仲裁反腐实践中的文化挑战及其法治因应
银红武
文化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它却能让具体个人或组织的身份得以归类与明确。有学者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群体以及该群体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组织所共享的价值和规范”[1],娜奥米·梅齐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文化”定义,即“任何一套共享的、标志性的行为——通过此种行为,意义得以产生、得到执行或遭受质疑,甚或遭致转化”。在解释这一点时,她补充道:“文化的不同作用往往源于年龄、性别、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的差异”[2]。埃德加·H.沙因则将组织文化定义为“一个群体为着解决其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问题而共同掌握的一种基本假设模式,该种模式运作得很好以致被认为是有效的。因而,这一模式被当作感知、思考和感受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并用以教导新成员”[3]。不难发现文化的定义和文化本身一样具有多样性,但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与行为、信念、经验、理解与价值紧密相关。
关于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康奈尔大学奥卢菲姆·泰沃教授认为:“法律制度的胜利是一种完全包含其影响的生活方式的部分胜利。因此,法律制度有其社会组织根源,现实就是法律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指导或惩戒……关于法律制度的基本假设就是它既与生活的其他领域共生,又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共同遵守。”[4]劳伦斯·M.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定义为“在社会中人们对法律与法律体系及其组成部分所持的态度、价值和观念”[5]。在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的广义定义的基础上,汤姆·金斯伯格进一步指出,法律文化是“一般文化中使得社会力量朝向或偏离法律的有关习俗、观点、行为与思想方式部分”[6]。
一、国际投资仲裁活动的文化属性
与国内司法机制通常根植于它所服务的社会的文化不同,国际仲裁并没有单一的文化根源,因为后者是试图取得竞争主导地位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不完美的融合实践[7]。近些年来,国际仲裁的理论和文化虽已历经了显著变化,但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仲裁文化的重心已经压倒性地向“西方”下沉[8]。这绝非一个令人感到无比困惑的现象,因为它只是很自然地顺应并客观反映出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军事、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真实发展状况以及存在于南北国家间的层级差距。即便是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国际仲裁语境下,简·保尔森描述了两个主导法律传统(即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间的文化差异。譬如,一名美国律师习惯性地在仲裁开始前向一名中东仲裁员递交一份“裁决书草案”。不难预见,一位受过民法法系培训的仲裁员极有可能将美国律师的举止视为完全陌生甚至是不恰当的行为[7]。于是有学者总结道,国际仲裁“完全植根于普通法系或民法法系传统……受精英律师圈主导,后者将‘美国中心’或‘欧洲中心’概念进行糅合并付诸仲裁法的实践”[9]。
具体到国际投资仲裁,无论其被视为一套系统①还是仅被认为一个框架②,它显然是一种程式化的活动,是一种文化实践。事实上,国际投资仲裁的程式化特征自争端方第一次递交仲裁申请书、答辩状或接收仲裁通知与程序令(或其他具有此类命名的文件)即可明显感觉出。广泛地看,国际仲裁程式的区分性特征包括具体种类的学术出版物、会谈、规范规则、行为建议、召集性电话会议、时间表、书状的交换(包括申请书、辩诉状与反驳书状)、听证会仪式和证据提交程序,以及终局裁决书的组织结构与公布等。所有的这些活动细节无论是否协调以及它们是否受某些传统的主导,伴随着国际仲裁实践的发展,它们往往会产生变化,从而形成了自身的亚文化。多年来随着国际仲裁程序的程式化发展,具体到仲裁员的选任与对律师的指导这些事项,最基本的考虑必然是落脚于仲裁程序的熟悉这一点上,而这亦可被称为文化能力。国际投资仲裁活动的文化属性与程式化特征概莫能外。
在国际仲裁中,基本正义最好是通过独立、中立、具有代表性和享有知情权的决策活动来实现。文化理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来自东京地区法院的一位日本法官绝非裁判关于美国华盛顿州卢米印第安人保留区域内一桩儿童监护权案件的最合适候选人。同样的问题随之而来,发生于欧洲公司和非洲国家间,或中国公司与非洲国家间的争端,哪些人将是最合适的潜在仲裁员?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同一班人马不可能是裁决后两桩案件的最合适人选。然而现实情况是,鉴于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员“圈子”太小,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事实上也很可能是)这两个实体案件将由同一班仲裁员进行裁判。如此一来,仲裁效果正如苏珊·布莱恩特所说的,“文化差异常常导致我们将同一组事实赋予不同的含义”,而且“不准确的定性会导致律师在代表客户时犯下重大错误”。对此,布莱恩特的结论是,文化误解有时看不见,但可能会以根本的方式影响案件的结果[10]。
在国际投资仲裁语境下,特别是仲裁庭在应对争端方所提出的腐败抗辩时,文化理解与文化挑战已变为仲裁程序无法回避的争论议题。因此,对部分涉腐国际投资仲裁案(特别是World Duty Freev.Kenya与Methanexv.United States两个典型案件)的文化层面的解构将有助于了解在解决涉及腐败问题的国际投资争端过程中,文化问题是如何站上争端解决工作的“舞台”中央的。
二、国际投资仲裁反腐实践中的文化挑战
逐利是商业资本的天性。当逐利行为突破法律与道德界限时,商事腐败现象随之产生。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与大背景下,商业腐败行为的跨国性特征与日凸显。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自然伴生与道德异化现象,国际投资法语境下的腐败活动渐变为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在内的司法实践的防控与规制对象——SPPv.Egypt(1992)案据称是涉腐国际投资仲裁第一案。此后,投资争端方(包括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在仲裁程序中提起跨国投资腐败抗辩的仲裁案件时有发生。数据表明,在28个国际投资仲裁案中,腐败问题或被暗指,或被明确用以抗辩[11]。
(一)World Duty Free v. Kenya案的文化挑战问题
World Duty Freev.Kenya案围绕肯尼亚第二任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于1978-2002年执政肯尼亚24年)的涉嫌腐败问题,仲裁庭根据英国法律和道德标准直接予以裁判。但该案引发的文化挑战议题不容小觑。
1.当事人、仲裁庭成员和代理人的文化代表性质疑
本案申请人——世界免税公司是一家马恩岛公司。该公司于2000年6月16日根据投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递交诉肯尼亚的索赔申请。申请方任命德高望重的王室法律顾问安德鲁·罗杰斯(澳大利亚人)为仲裁员。被诉方最初也任命了另一名澳大利亚人,即詹姆斯·克劳福德为仲裁员。两名澳大利亚仲裁员共同推选了吉尔伯特·纪尧姆(法国人)为首席仲裁员。克劳福德后来因担心冲突而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同为王室法律顾问的英国人维德。
申请方的代理人为御用大律师杰弗里·罗伯逊和奥利维奥·霍尔兹沃斯(两人均为英国公民),以及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彼得·布西米和来自肯尼亚内罗毕的保罗·缪特。被诉方的代表是来自新菲尔德巴黎办公室的简·保尔森、君斯坦丁·帕塔斯德斯和米特什·科特查。
鉴于保罗·缪特是唯一的非西方法律文化代表,故整个专业对话可以说是基本发生于当今世界的西方法律传统人士之间。虽然仲裁适用法是肯尼亚法律,但其一般被视为与英国法律相同,故肯尼亚共和国在该案中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提供了用作审议的事实模本。
2.私人捐赠性质认定的文化冲突:外交礼仪抑或贿赂官员
World Duty Freev.Kenya案是外国投资者基于合同(而非条约)主张对东道国的索赔案件。索赔方主张,具体结合政府官员与东道国相互关联的腐败行动和不作为,肯尼亚共和国实际上对申请方处于内罗毕和蒙巴萨机场的免税商店的投资予以了征收。申请方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众多政府部门提出大量的事实指控,控诉其如何“摧毁了公司建立免税连锁店的计划”,并造成大约相当于5亿美元的损失。
东道国一开始试图对每项违约指控予以回应,但后来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一个单一事件(该事件虽发生于合同签订之前,但其定性却能最终决定裁决结果):根据申请方自己的说法,当初出于获得合同的目的,公司赠送了肯尼亚时任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50万美元的礼物。申请方的大股东兼首席执行官纳西尔·易卜拉欣·阿里为此提供了证词。裁决书中引用的有关事实陈述部分如下:
17.我受到了名为Joshua Kulei(JK)的人的接待,他介绍自己是总统的私人助理。萨贾德和我得到了总统的接见,而我亦向其表达了我的投资建议并予以了解释。我意识到萨贾德实际上与HEDAM(总统)关系非常密切。我指的是正如证据5(a)所列出的那张照片所示,在今年10月14日举行的一次重要政治会议上,萨贾德正坐在HEDAM(总统)的左后方。
18.我知道萨贾德在1989年2月16日收到了信用证中所列明的价值5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他安排将其兑换成肯尼亚先令(KSh)。他把这些现金装进一个棕色公文包带到我和HEDAM(总统)的会面地点。当我们进入总统接待我们的房间时,他把公文包放在墙边并留在那儿。等会面结束后,我们从先前放公文包的地方将公文包取走。在返程途中,我打开公文包看了下,发现里面的钱已经被换成新鲜的玉米了。
于是基于申请方的这份承认证词,仲裁庭裁判投资合同是通过行贿而获得的,但合同因有悖于公共政策而无效,从而政府有权撤销合同。对于申请方提出的征收索赔诉请,仲裁庭则避而不答。
可以说,该份裁决书的形成真正称得上是深受西方法律文化影响的结果。首先,如上所述,几乎所有的关键参与者(包括仲裁庭成员和当事人的代表)均来自占主导地位的两大西方法律传统。其次,合同本身虽选择肯尼亚法律(法庭认为与英国法律相同)作为适用法,但是适用于仲裁条款的法律却直接是英国法律。最后,仲裁庭所援引的法律依据基本(除了一位肯尼亚社会学家的专家声明)是英文著述,其中包括马斯蒂尔勋爵的观点、《奇蒂论合同法》以及一些英国法院判例和其他仲裁裁决。
在World Duty Freev.Kenya案裁判过程中,虽然申请方明确提出了文化方面的主张,却被仲裁庭随意驳回。肯尼亚社会学家Pius Mutie在其关于文化层面的专家声明中提及两个重要观点:第一,“私人捐赠是受到习惯做法的认可的,亦被肯尼亚人民认为是一个外交礼仪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关于私人捐赠的公共使用事项,第二点集中在“哈拉姆比”(Harambee)的文化实践上,即出于公共目的而通过私人捐赠来调动资源。
但遗憾的是,仲裁庭拒绝接受这些文化观点并坚持认为:
本庭可以肯定的是,由阿里先生本人代表“香水宫”公司(世界免税公司以前使用的名称)伙同萨贾德先生对莫伊总统所实施的偷偷摸摸的举动(利用棕色公文包以钱换新鲜玉米)不能被看作是为着公共目的的私人捐赠。支付这些款项不仅是为了会见莫伊总统(正如申请方所提交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会见期间获得总统关于预期投资的许可。本庭认为,这些款项必须被视作是为着获得1989年合同的签署而作的贿赂。
于是在对合同是通过贿赂而获得的这点上做出事实认定后,仲裁庭依据国际公共秩序概念以及肯尼亚和英国的公共政策原则裁决合同无效。
3.“受审”的非洲东道国文化
在World Duty Freev.Kenya案中,仲裁庭的裁决完全基于阿里关于“私人捐赠”的证词。可以公平地假设,如果仲裁庭接受阿里关于捐赠的证词为可信,它也必须接受他关于莫伊24年任期内在肯尼亚国内是如何办事情的一个更广泛的声明。阿里的声明描绘出一幅景象:没有莫伊的许可(该项许可是在个人进行捐赠后才被批准的),在肯尼亚任何事情都干不了。如果该项声明被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在莫伊任期内签署的所有投资合同都是非法的或都可被撤销。如此广泛的一个结论将无异于置肯尼亚的国家文化于接受审判的地步。假若事实如此,那就得要求仲裁庭进行比它实际所为的更深入的审查。
关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社会学家Pius Mutie表示:
在肯尼亚国内的许多非洲社区,在众多文化场景下(这些礼物)是作为表达“你好”或认可领导人权威的方式被送出的。当人们去拜访朋友或亲戚时,他既不会“空手”而去,也不会“空手”而归。无论礼物的价值如何,互相交换礼物都是被传统认可的;相反,不遵守这些习惯做法只能表明当事人要么极度贫穷、吝啬或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抗。[8]
作为在其证人证词中主动披露有关礼物信息的阿里(他大概被认为是一个可信的证人)也表示,“他向莫伊总统支付了一笔他认为是合法的钱。当时,在肯尼亚做生意之前进行这种捐款是常规做法;该做法有其文化根源,并为‘哈拉姆比’制度所支持,该制度出于公共目的而通过私人捐赠调动社会资源”。
对这些关乎文化的观点,仲裁庭均予以驳回:不仅因为它怀疑该文化的存在,还因为它认为这一文化实践的本身已经被腐化与滥用。
最后,当然也是更重要的,仲裁庭做出结论道,“在本案中,我们应该承认申请方据以主张其所实施的贿赂行为有效的任何当地习俗是有悖于构成英国法律组成部分的国际公共秩序与英国公共政策的”。这是考虑到英国的公共政策与肯尼亚的公共政策是相同的,因为适用法的相似性。仲裁庭还指出:“本庭认为,重要的是在英国历史上普通法历来对行贿国家官员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并将该罪排列于叛国这一重罪之后。”③
不难发现,World Duty Freev.Kenya案仲裁庭的整个分析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英国法律、国际公共政策和肯尼亚法律是相同的,并且它们共同作用于争议的解决。虽然这在技术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仲裁庭只运用了一条较为笼统的规范试图解决本案事实的文化复杂性,至少可以说是过于简单了。仲裁庭犯了一个错误,即不能因为法律可从其他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复制过来,从而断定特定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包括文化基础和道德标准)也会以与法律文本相同的方式得以复制。
(二)Methanex v. United States案的文化冲突问题
Methanex是一家拥有众多生产、运输与销售甲醇的美国子公司的加拿大公司。作为MBTE关键原料的甲醇主要用于提升无铅汽油的性能。1999年3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Gray Davis签发行政命令,禁止在2002年底后使用MBTE。鉴于Methanex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甲醇生产商,因此一旦加利福尼亚州行政命令生效,其业务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Methanex公司于1999年12月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发起仲裁,指控加利福尼亚州的行政命令相当于对Methanex投资的征收,构成了对国民待遇和最低待遇标准义务的违反,从而主张约9.7亿美元的损害赔偿。
1.政治竞选捐款性质认定的文化冲突:违反外国投资者待遇标准的腐败行为抑或正当合法的文化行为
申请方Methanex公司的主要论点是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Gray Davis之所以决定签发MBTE禁令,其背后的真正动因是腐败——作为Methanex公司强劲对手的ADM公司(美国主要的乙醇生产商)捐资26万美元给时任副州长Gray Davis用于州长竞选活动,以此换取后者做出使Methanex公司投资处于不利地位而对捐资者有利的行政决定。
在仲裁程序中就腐败证据而言,仲裁庭接受了Methanex公司所建议的“点连”法(“尽管单个证据片段在孤立情形下对其进行审视可能会显得毫无意义,但假若所有的证据结合起来看的话,它们会对真实事件的发生提供最具说服力的可能解释……”)④。但遗憾的是,Methanex公司在利用这一方法佐证自己论点方面并未能如愿以偿。而庭审中作为被诉当事方的美国则辩称,加利福尼亚州的MBTE禁令是出于合法的公共健康目的,因为该种物质正在对当地饮用水产生污染。在阐明非法腐败行为与对公共决策予以合法(但往往是不道德的)影响行为之间的微妙界限基础上,最终仲裁庭考虑到在美国并不认为竞选捐款为非法行为,而有关行政禁令的立法程序透明且正当并历经了平行审查,于是裁决Methanex公司所声称的腐败站不住脚,做出了对Methanex公司不利的裁定:认定仲裁庭对部分诉请无管辖权,对于其拥有管辖权的申请方其他诉请则基于事实而予以驳回⑤。
2.美国文化背景下“可容忍”的政治游说与竞选捐款行为
即便在当今社会人们利用个人关系来确保获得别人没法得到的某些优势实际上还是大行其道,而这使得腐败的认定工作变得更具复杂性。所有社会内的文化规范都在不同程度上放任或至少容忍那些除了内在事实之外的理由而意在影响公职人员决策结果的做法。为着让官员在履行公务时能有所通融而向其进行的货币或非货币支付应被归入贿赂范畴还是仅被视为允许存在的普遍社会规范或社区操作规范,这无疑取决于行为评估人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在这方面一个较好的例子就是拿美国所谓的“游说”活动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进行比较[11]。
美国文化语境下的“游说”一词意在正式描述一些人对特定领域(立法的潜在主题)最关切的相关信息是如何传达至立法者的这一过程。“尽管(游说)行为往往会导致对政治平等机会和政府神话的偏离,但因其社会影响不大故人们对其采取常规容忍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指“游说”活动)可能已成为美国政治体系的不可或缺部分”[12]。允许从前的民选官员通过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因而可以接近他们)进行“游说”活动,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其他社会(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类似行为可能会被视为无法容忍的“影响力交易”。在美国,对许多游说人士而言,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自己可能会涉嫌非法腐败这一点;非正式的讨论和交流,再加上通过给付小费以示“礼貌”,所有这些都构成整个游说行当的日常惯行“生态图”[12]。
在美国文化背景下政治竞选捐款行为同样具有“可容忍性”。可以理解的是,在如今的商业形势下具有财务利益的公司出于确保获得有利的立法或合同目的,往往倾向于投入相当多的财务资源以实现其预定目标:主要方式就是支持他们认为将极有可能认同这些目标的政府官员的竞选活动。美国最高法院甚至认为,这种用金钱说服政府官员的能力是言论自由的固有内容⑥。尽管其他国家的观点要保守得多——有些国家甚至完全不允许私人捐款(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不论其意图如何,外国人从事过的竞选捐款都被视为非法行为),认为利用公共资金进行竞选活动更好,但是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内,假若有人进行过类似的海外支付,通常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
当然,政治游说和竞选捐款只是美国公共决策行为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内受到通常提早做出的私人馈赠影响的众多方式中的两种。这些物资馈赠一般仅被商人视为做生意需开支的部分成本,即便是最挑剔的美国公司也不会将其看成是腐败。正如赖斯曼所指出的,“我们的法律体系通过创设合法的经营费用这一工具来实现对这些做法的容忍和便利化:业务交易时不是仅参考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而且要看本质上与此不相关的个人喜好”[12]。
三、国际投资仲裁反腐进程中关于文化挑战的法治因应
鉴于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在反腐实践中不断遭遇到来自各当事方关于文化的挑战,可以说这些文化冲突的解决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国际投资仲裁反腐事业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是故关于文化挑战的法治因应问题就变为国际投资仲裁反腐进程中一道必须作答的现实应用题。主要地讲,国际投资仲裁反腐语境下应对文化挑战的“良法善治”路径构建可着力于仲裁程序中文化代表性的地域平衡与非西方法律传统仲裁员的能力建设、腐败认定的法律标准确定化以及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与内国国家机关间反腐协作机制的创设等工作。
(一)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文化代表性的地域平衡与非西方法律传统仲裁员的能力建设
国际仲裁实践中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应属仲裁员的文化背景。在现实中,非洲国家官员会称一个完全由西欧人组成的仲裁庭为“外国仲裁庭”,个中缘由不难理解。可以想象的是,同一官员不可能会用这一词语去称呼一个包含有两名非洲人的三人仲裁庭。撇开政治正当性不谈,仲裁庭至少在文化理解的必要性问题上满足了仲裁员的地域代表性均衡要求。在国际投资仲裁反腐实践中文化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显得不可逾越,但其中的解决方法之一可能也出奇的简单:确保裁判者文化的多样化。当然,在解决一个涉及非洲因素的投资争端时完全寄希望于在三人仲裁庭中任命两名来自非洲的仲裁员有点不太现实,毕竟在单个案件中试图通过仲裁员的任命管理来确保文化微观层面的适当代表性和多样性有一定的现实难度。
以非洲国家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主要是ICSID实践)为例。尽管非洲成员国称得上是对ICSID机制的创建起着“催化剂”作用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是国际投资法法理的践行者与反哺者,亦是推动外国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SDS)机制改革的“量身定制者”[13],但非洲国家的ICSID参与实践主要限于作为案件的重要来源地提供辅助性帮助(最近数据显示在递交至ICSID解决的全部案件中大约22%具有非洲因素),其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仲裁实践中真正扮演决策者(即担任仲裁员)的比例仅为4%。而像西欧和北美这些地区虽然与其相关的案件数加起来占总数不到12%的比例,但来自该地区的、起着决策作用的仲裁员数量却占了总数的70%以上。从数字上看,自ICSID成立以来,非洲人士担任仲裁员约90人次,而来自西欧和北美的仲裁员却高达1 416人次。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仲裁庭占非洲仲裁员多数[14]。
ICSID仲裁现实表明,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寻求重塑一种更具实质公正意义、能挑选多样裁判者群体以确保仲裁员地域代表性均衡的国际投资仲裁秩序。在当前,这将意味着需对常设性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程序规制以及联合国贸发会的临时仲裁规则进行修订,以此加强具体案件下对仲裁员文化多样性和适当地域代表多元化的考虑。文化多样性将成为仲裁规则适用中的一个强制性要求事项[15]。
无疑,在提议确保国际投资仲裁员的地域代表性均衡的同时,一个不能忽视的实际情况就是非西方法律传统仲裁员的能力建设问题。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应借鉴国际法院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成功经验,后两者通过创建资金援助信托基金作为各成员国分享经验与进行技术援助的平台,以此来保障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至于影响其有效参与机制的能力。因此,在国际投资仲裁语境下逐步实现裁判者的地域代表性均衡的建议还应该包含对来自非西方法律传统的潜在裁判者与参加者提供技术援助,并帮助其进行能力建设的具体内容,从而确保非西方法律传统国家能从这一建议的实施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就非洲国家而言,有学者乐观展望:通过在非洲大陆建立可信任与能胜任的司法和仲裁机构,从而把关涉非洲的投资争端案件吸引到非洲裁判,亦不失为一种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8]。
(二)国际投资仲裁语境下腐败判定的严格法律标准
国际投资仲裁反腐法治指的是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基于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仲裁合意对直接与跨国投资有关的腐败行为依法进行调查与证实,并做出有法律拘束力的惩治腐败行为的裁决结果[16]。正因为腐败的认定与文化维度相关,所以国际投资仲裁反腐法治应在遵从文化的基础上遵守腐败责任法定原则。
1.文化遵从基础上的腐败责任法定原则:被禁止的腐败违法行为v.文化许可的合法物质激励
当然,将旨在确保官员偏离公共职务而做出的货币或非货币支付行为定性为贿赂还是视作在主流社会规范下获允许可的行为或者看成一个社区的操作规范,这些完全取决于对具体行为进行评估的人所采纳的判断标准[11]。《纽约时报》曾刊载文章曝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部分劣迹。包括美国AT&T公司、瑞士制药商诺华和 Squire Patton Boggs律师事务所在内的众多企业巨擘总共支付了科恩逾200万美元向他咨询如何在特朗普治下的华盛顿政府多变的外交手段影响下顺利开展国际经营的应对建议。此外,科恩还操刀了特朗普与美国演员斯蒂芬妮·克利福德“不伦”恋情的“封口费”事件。
关于美国白宫的礼物事件,《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曾披露沙特阿拉伯国王于2015年向奥巴马及其家人捐赠了价值130万美元的礼物。虽然根据美国法律,总统及其家人应该把这些礼物移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但是“就美国政府议定书而言,当不接受礼物会给捐赠者和美国造成尴尬时,他们必须接受这些礼物”[17]。议定书显然关注到文化层面的东西,并对具体情况予以微妙处理。
诚然,欲将科恩的“交易”和奥巴马的礼物与“新鲜玉米换现金”的行为区别开来的话,这就需要对这些支付进行事实模式的预测分析——尽管这些事例都很好地展示了世界运行方式的复杂性。当裁决涉腐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时,仲裁员应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对案件的文化维度保持敏感来维护正义。一方面仲裁员应秉承文化理解精神,对具体文化背景下为社会所容忍的物质激励采取遵从态度;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对本质为被禁止的腐败行为予以识别,通过促使腐败行为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方式,确保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与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得以维持。
2.腐败判定的严格法律标准
对World Duty Freev.Kenya案与Methanexv.United States案的裁决,除了遭受文化因素的质疑外,仲裁庭很快判定自身除了无管辖权似乎也没有太多法定理由(即便是依据当今西方的腐败标准)。在应对此类存在较强文化影响的涉腐投资仲裁案件时,仲裁庭很有必要根据相应的适用法为国际投资法语境下的腐败认定确定一个区分度高且较为严格的法律标准。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腐败可细分为广义腐败与狭义腐败。关于广义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全面列举了11种腐败行为(第15条至25条)。狭义腐败主要指贪污贿赂。以狭义腐败为例,大法官罗伯茨2014年在McCutcheon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案中曾表示:“我们已经说过,政府方面的监管不应针对譬如候选人对其支持者或盟友所表达的一般性感谢,或者为获得可能的政治性会见而提供的支持。讨好和会见……并非腐败”。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唯一应被禁止的腐败是一种被称为“维持交换条件”(quid pro quo)的腐败(也即基于“直接用职权行为交换金钱理念”的政治交易)。腐败的标志是金钱性的“维持交换条件”:用美元换取政治好处⑦。
World Duty Freev.Kenya案中阿里详细介绍了众多肯尼亚政府官员如何要求自己给他们送礼物,包括为官员家人提供从手表到相机不等的礼物,以及他是如何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官员们的要求可谓各式各样,而这一现象在肯尼亚很是普遍。阿里的证词并没有表明每种情况下确切的交换条件,以及他用现金从总统那里换回的各种政治性或其他利益——这些好处中有多少是源自总统对其公权力的运用,又有多少是总统通过个人能力争取而来的。换言之,要想对本案进行全面考虑和适当处理就需要更深入了解案情事实。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仲裁庭对本案事实的文化层面内容拒绝“深究”调查,从而错失了揭示文化在投资仲裁中所起作用的大好机会。
阿洛伊修斯·拉姆松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问题》一书中表示:“所有社会的文化规范应在不同程度上宽恕或至少容忍那些并非纯粹属于直接交换条件,亦并非出于歪曲案件原本事实的理由、只是意在影响公共官员决策结果的那些做法。”[11]鉴于国际投资仲裁庭在反腐调查取证的职权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国际投资仲裁语境下腐败的认定应严格把握且应限于“维持交换条件”的法律标准。事实上,Methanexv.United States案仲裁庭亦坚持认为,假若真实存在捐款者利用竞选捐款换取对己有利的政府行为的“维持交换条件”的话,那么即便支付是通过表面合法的竞选捐款形式得以实现的,也会导致判定腐败的发生⑧。
(三)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与内国国家机关间反腐协作机制的创设
关于仲裁庭是否在理论上享有充分的职权对腐败指控进行调查的问题,现阶段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答案基本都是肯定的。但是,诸如2007年Siemens AG仲裁案裁决⑨,事后被证实为错误裁判事件的发生从侧面鲜活地揭示了投资仲裁庭缺乏足够的手段与工具用于腐败刑事调查的无奈现实[18]。World Duty Freev.Kenya案仲裁庭所发布的第一个免责声明就是对这一事实的承认:
必须注意的是,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一开始并不是这些仲裁程序的当事方之一,在程序中也没有被依法代表。他没有以证人身份参加庭审。仲裁庭对前总统没有管辖权。最终,仲裁庭是根据本案当事方所引证的证据与提交的陈辞对争议作出裁决。⑩
国际投资仲裁庭在反腐实践中似乎苦于腐败证据的举证与印证等问题,而这也确实令人一筹莫展:他们不具备内国刑事调查机构所拥有的广泛调查资源与手段;同样地,他们亦不具备强制有关当事方到庭的职权,当然也不能像内国法院那样命令第三方参与到仲裁程序中来。关于仲裁庭在治理腐败时所面临的此种“尴尬”境遇可从以下事件窥见一斑:世界免税公司继在ICSID递交World Duty Freev.Kenya案后,又向其他仲裁机构另行提起了一项仲裁,并赢得了获赔5 000万美元的裁决。但是这一裁决后来却被肯尼亚高等法院撤销,理由是仲裁庭不能主动(sua sponte)考虑腐败事项,因为政府部门(肯尼亚机场管理局)并未提及腐败问题[19]。
尽管仲裁庭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客观存在,但这并非意味着以ICSID为首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在反腐法治语境下不应该或不能有所作为,毕竟仲裁庭对最终公平公正地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涉腐投资争端是拥有空间与杠杆的。就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的文化挑战而言,鉴于内国机关执法人员深受本土文化熏陶,是本土文化的深谙者与践行者,因而构建内国执法机关与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反腐协作机制无异于在两者间架起了一座文化了解与沟通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况且,在ICSID与内国执法机关间还存在反腐职能的重叠(尽管前者存在先天缺憾),若能成功创设两者间的反腐法治合作机制,那么就能更好地确保国际投资法框架下反腐功效的实现,切实保护国际投资活动的全球公共利益,并最终实现国际投资可持续发展共同体构建的目标[20]。
1.投资争端方成功主张腐败抗辩的前提条件设置
假若腐败抗辩由东道国提出,则国际投资仲裁庭在采纳腐败抗辩时需向东道国确认:跨国投资腐败是否涉及本国官员的共同腐败行为。如果回答是肯定,那么东道国须向仲裁庭证明其已对涉腐官员启动了内国反腐法治程序或在其法律框架内已按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贯彻实施了反腐败标准,或者向投资仲裁机构承诺其将启动针对涉腐官员的内国反腐法治程序。就前两种情形而言,内国反腐机关有义务向投资仲裁庭提供外国投资者的腐败证据以及相对应的反腐处罚信息。在后一种情形中,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依照约定有权对内国反腐法治结果进行问询以示监督。内国反腐机关必须向国际投资仲裁机构通报涉腐官员的处理结果,以履行其对后者所作的反腐承诺,不得无理拒绝。
在外国投资者提起腐败抗辩的情况下,投资者必须向投资仲裁庭如实披露其是否已经启动了控诉东道国官员腐败的内国反腐法治程序。以作为申请方的外国投资者向投资仲裁庭提出腐败抗辩情形为例:根据我国《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第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党组织、党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纪违法的行为。”该《规定》第三条进一步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对如实检举、控告的,应给予支持、鼓励”。如此,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将身处中国境内的外国投资者是否已经做出了检举、控告中国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举动作为决定该投资者能否成功主张腐败抗辩的前提条件,与我国《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
2.ICSID与内国国家机关间反腐法治协作机制的具体构建:以中国的实践为例
联合国打击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国际反腐论坛”框架内所建议的仲裁机制强调,仲裁员的管辖权仅适用于合同的商事影响部分。刑事定罪仍将维持在内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职权范围内[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参照本法规定”为我国国家机关与如ICSID之类具有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共同创建反腐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提供了明文内国法依据。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六章“反腐败国际合作”第五十条与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的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反腐败国际条约实施工作以及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在反腐败执法、司法协助和信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这两条中的“国际组织”可解释为包括ICSID在内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ICSID与中国国家机关间进行国际反腐刑事司法协助
鉴于ICSID在跨国投资腐败调查职权与工具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参照本法规定”的条文,包括ICSID在内的国际组织可依法与中国国家机关开展国际反腐刑事司法协助工作。考虑到有些国际组织(比如ICSID)与我国政府并未缔结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些国际组织(比如ICSID)与中国国家机关可按照平等互惠原则,通过外交途径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我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是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审查处理对外联系机关转递的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承担其他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相关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中相互提供协助,包括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以及其他协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包括ICSID在内的国际组织可参照上述有关“外国”的规定“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或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中相互提供协助”。
(2)ICSID与中国国家机关在投资争端财政义务方面的相互承认与抵扣执行
参照ICSID公约第54条第1款,我国应承认ICSID依照公约做出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并在中国领土内履行该ICSID裁决所加的财政义务,正如该裁决是中国法院的最后判决一样。另外,假若ICSID仲裁庭已做出了对外国投资者不利的裁决,而此后内国的反腐国家机关又启动了跨国投资腐败调查程序,那么内国反腐国家机关的最终罚金能否用ICSID仲裁中投资者所遭致的经济损失来抵扣呢?对此,有学者持肯定态度。其观点认为,罚金抵扣的数额可相当于在东道国提请腐败抗辩情形下外国投资者未能获得支持的ICSID诉请金额。该项建议的可取之处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寻求实现减缓外国投资者所遭受的腐败成本的目的,从而促使内国反腐国家机关和东道国腐败抗辩的共同作用不至于构成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输入的障碍[22]。
反过来,针对在ICSID裁决做出前就已审结的内国反腐司法或行政执法案件,基于公平法律原则与“一事不再罚”行政法一般原理,内国国家机关的财政处罚结果不能重复适用于ICSID裁决的财政义务部分。如“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外国投资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贿赂他人的,由监督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外国投资者依照该条已被执行的罚款,可得到ICSID裁决的财政义务抵扣。同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法》关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修改规定,外国投资者犯行贿罪被中国司法机关施以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其已被执行的财政处罚可用于抵扣ICSID裁决中关于财政方面的不利结果。
结语
包括投资仲裁在内的国际仲裁程序就其结果而言是一种文化互动行为,但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容易为那些真正拥有决策权的裁判者所忽视。正如World Duty Freev.Kenya案与Methanexv.United States案所揭示的,文化是大多数人希望避免触碰的、非决定性与不方便考量的因素。这一表述甚至被视为带有恶意,特别是从以下角度来看:它似乎在提醒决策人士,你们错过了你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就像无意识的偏见一样。当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和从属地位的群体提出文化质疑时,这一问题就愈发显得带有政治、经济和权力层面的意味,事态发展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遭受文化误解的群体自是不应感到气馁,反倒应大力争取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得到满足。
毋庸置疑,充分考虑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文化代表性的地域平衡与非西方法律传统仲裁员的能力建设,为国际投资仲裁语境下的腐败判定设置严格法律标准,以及创设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与内国国家机关间的反腐协作机制,不仅是为了确保涉腐国际投资仲裁的法治正当性,更是为了提升这一程序结果的公正性与有效性。
注释:
① 虽然法律专业文献大都将国际投资仲裁视为一套系统,但人们却长期困扰于这套系统在裁判法理方面的非连贯性。有学者表示,“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虽谈不上观点完全相一致,但也堪称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一致”。参见Jan Paulsson.Denial of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1。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尽管非连贯性是当前国际投资仲裁面临的一个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实践活动将会出现更多的一致性结果,参见Charles N Brower, Stephan W Schill.Is Arbitration a Threat or a Boon to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J].Chi J Intl L, 2009(9): 471-498。
② 框架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大卫·卡隆认为:“任何关于ICSID系统内一致性的讨论都必须首先注意到,问题的根源已经深深嵌入仲裁本身的结构之中。一般来说,仲裁(特别是国际商事仲裁)实际上不是一种系统,而是一个在其内彼此分立抑或结果难以预测的仲裁员个人行为得以做出的框架。”参见David D Caron.Investor State Arbitration: Strategic and Tactical Perspectives on Legitimacy[J].Suffolk Transnatl L Rev, 2009(32): 513-524。
③ 参见World Duty Free Companyv.Republic of Kenya, ICSID Case No ARB/00/7, Award(4 October 2006), paras.110, 136, 138-174,172, 173。
④ 参见Methanex Corporation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nal Award, Part Ⅲ, Ch.B, para.2。
⑤ 参见Methanex Corporation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FTA/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Final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merits dated 3 August 2005。
⑥ 参见Citizens United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8(2010)。
⑦ 参见McCutcheon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72 US(2014); 134 SCt 1434, 1436(2014), quoting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n, 558 US 310, 360(2010)。
⑧ 参见Methanex Corporation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nal Award, Part Ⅲ, Ch.B, para.37。
⑨ 参见Siemens AG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2/8, Award,(Feb.6, 2007)。
⑩ 参见World Duty Free Companyv.Republic of Kenya, ICSID Case No ARB/00/7, Award(4 October 2006), para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