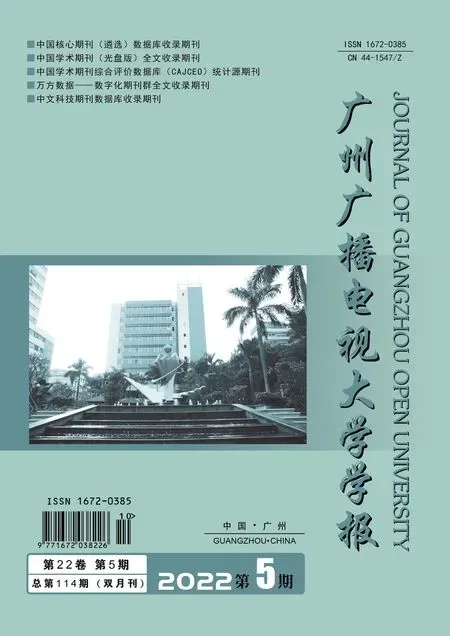《北京人》人性焦虑的书写特色
薛诗艺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焦虑(anxiety)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angh”,与“狭窄”“受束缚”有关,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学现象,它几乎反映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对象、程度不同而已。[1]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曹禺产生了强烈的人性焦虑。这种对人性的焦虑促使他不断进行自我发问,反问的痛苦构成了曹禺创作的灵感来源。《北京人》的文本变形浓缩了曹禺过往的人生经历,几乎动用了他从童年到抗战时期的全部见闻和生活储存。其中,人性焦虑的书写随处可见,这种焦虑通过铺设残酷环境、叙述诗意语调、创造反抗意象一步步推进到对人性的发问,进而以发问推动深入思考,架构出潜藏的富有生命力的意象,呐喊出释放人的自然天性的迫切之声。
一、人性焦虑的成因
正如曹禺自己所说:“那是非常奇怪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些童年的记忆就闯入我的构思之中”[2],《北京人》是他从前过半人生经历的一个变形浓缩,戏中的人物在生活中差不多都有影子。因此,探究《北京人》中人性焦虑的来源,就要从曹禺的创作素材,即人生经历入手。
曹禺的身世具有特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长发育,形成了内向、寂寞、忧郁而又敏感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决定了曹禺诉诸文本的倾诉方式。曹禺拥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和孤寂的童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他开口倾诉的欲望。在他生下三天后,生母就去世了,父亲是个脾气暴躁、带有典型封建大家长特质的男人,继母虽尽可能待曹禺如亲子一般,但她却同曹禺的父亲和哥哥一般染上了烟瘾,性情大变。同时,照顾曹禺长大的姆妈则在潜移默化中浸透给他人生悲苦的情绪。姆妈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深受封建社会的束缚,她既有值得人同情的悲惨遭遇,却又有令人憎恶的“小市民”恶习。她热衷于倾吐自己的不幸,擅长挑拨离间。在曹禺儿时,她就曾因向继母要求涨工资遭拒,转而到曹禺面前编排继母坏话,挑拨他和继母的关系。也是从她口中,曹禺第一次知道继母并非自己的生母。曹禺本就对这个大家庭充满失望,自然对此更加敏感,由此更加疏远了自己的亲人。姆妈还喜欢向曹禺讲述她的悲惨家事,这进一步加深了曹禺对这个世界的厌弃和对人类存活的困惑。家中颓废堕落的环境令他深感孤独、苦闷却又无能为力,他只能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在一个人的空间中与自己对话。而随着外出求学,跟着父亲到任职地,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世道的黑暗与残酷。他亲眼目睹了衙役残忍用刑拷问犯人的血淋淋画面,看到了年轻军官们在舞会上人模人样,却到大街上欺凌百姓、当街招妓的丑陋嘴脸。而在这个时期,他的父亲又因中风早逝,从此家道败落,紧接着便是姐姐惨死、哥哥去世的手足分离。可以说,家庭的败落让曹禺切切实实尝到了世道的凉薄和人情的冷漠,而那短短几年的数场生死离别则加深了他对生死的恐慌。当耳闻目睹的世道的悲惨真正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对生存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体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人为什么活着”的追问和困惑。
身世的特殊性加深了曹禺对风雨飘摇时代的深切关注,对自身的追问上升到了对整个时代人性的追问。曹禺写作《北京人》时正处于抗战的后期,旧的社会形态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形态似乎正在形成,但在现实中,处处都显露出了政治颓败、民生凋敝、内乱不断、社会失序的乱象,外来的敌人大剌剌地占领着中国的领土,封建礼教的幽灵依然飘荡在中国的上空。此时,中华民族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将何去何从的命题盘旋在曹禺的脑海中。其实,自五四运动开始,这种对民族未来的担忧和个人命运的彷徨就已经在知识分子身上有所体现,对世道黑暗的憎恨深化为了对人性的憎恨,但偏偏心中留存着点滴希望,渴望有人能带领这个悲苦的民族走出深渊,这种渴望又引申出了对人性的焦虑。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的焦虑,焦虑不为,又焦虑无所为,这种焦虑就像是一场放逐,就像在无助的荒芜空间里,无人伸手援助,只剩下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正是基于对现实的感触,对这个不道德的世界的失望,曹禺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对人性的焦虑。这种焦虑近乎达到变态的程度,可以称为一种自我的折磨,即在显而易见的绝境中不停地发问、挖掘,誓死执着地要找出一丝生的气息。
写作《北京人》期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加剧了曹禺对自身觉知的敏感性,点燃了他对人性的追问。他和夫人郑秀共同养育了两个女儿,却在生活的琐碎中磨灭了当初相爱的激情。在这个时期,方瑞的出现给曹禺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的色彩,他麻木的感官再次生动起来,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再次跳动起来。对方瑞的一见钟情让曹禺对自身的觉知更加敏锐,他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方瑞的陪伴。可是,要说他对郑秀一丝感情也无却也不然。在协议离婚的裁决书宣告后,想到二人当年月下定情、南京订婚和八年离乱中共同经历的艰难岁月,曹禺和郑秀都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这恰恰就是人性复杂、矛盾的表现,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人性与生活。
正是基于对自身感知的清晰认识,他更加产生了对人性的焦虑和对人性问题的迫切追问。人是自由的,恋爱也是自由的,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爱上了方瑞。可是,夫妻间数年的感情同样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他生养孩子的这个女人曾经也是他最爱的女人。两个相爱的人缘何走到离婚的地步,爱上另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地斩断前缘吗?曹禺作出决定很迅速,他选择遵从人性本能,但内心的挣扎却是长久的,包括晚年,曹禺回忆起他与郑秀之间并不美满的婚姻,也还在感慨:“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3]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困惑使得曹禺对人性焦虑的追问深入到了更深的层面。
二、人性焦虑的书写方式
(一)铺设残酷环境
焦虑是恐惧的基础,恐惧伴随着焦虑,焦虑之中又含有恐惧。人性焦虑源于对某种特质的恐惧,恐惧感促使曹禺对剧本进行残酷的架构,而残酷的文本环境又恰恰是一切焦虑进行的背景,二者相辅相成,推进了文本表达。
从表面来看,《北京人》的剧本人物处于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整幕剧在曾家内部并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也没有如《雷雨》一般所有戏剧人物的矛盾都在同一幕爆发的火爆场面。但是,这种平静下却藏着如黑洞般能把人吞噬的残酷,蕴藏着摧毁人灵魂的刀剑,这是一个极其冷酷而黑暗的王国。
一开幕,曹禺着力展现曾家客厅和花厅的布置,文本称花厅是“曾家最后的一座堡垒。纵然花园的草木早已荒芜,屋内的柱梁亦有些褪色,墙壁的灰砌也大半剥蚀,但即便处处都像这样显出奄奄一息的样子,而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勉强挣扎、抵御的。”[4]一针见血地布设了整部剧环境的基调——将死未死的残酷。由近及远的镜头推开来,慢慢渲染出曾家大宅院原有建筑的轩豁宽敞、金碧辉煌以及如今的荒凉破败,曾家就似一片黑色浮雕的地下空城,无声无息地守着旧章旧制。随着镜头拉远,临院小巷的吆喝声仿佛给这幅黑色油画添了一丝气息,画面由令人压抑得喘不过气到使人揪着空得以浮出水面换口气,却又带着一丝古城冲淡古朴的悠远孤独。有意渲染的曾家小花厅,是一抹静的布景,犹如一幅色彩阴暗浓重的油彩画,给剧作增添了浓烈的阴郁沉重之感。当再有意识地设置与静景相对的流动的声音背景,不失时机地突出人物的语言、行动的心境,更使全剧在这种凄冷的背景中呈现出一种残酷、冷清的气氛。有声、有活气的小巷和无声、压抑的宅院形成鲜明对比,人们还未来得及细细回想二者留在心中的震撼,下一秒,镜头再次拉近,人们再次俯头下水,跟着又回到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宅院。剧作结束时,曾家的土墙塌了,棺材抬走抵债了,曾家也残酷地吞噬了自己。无声的寂静比起有声的争吵更令人胆寒发颤,曾家就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所在,也是残酷的杀人不见血的地方,又是一个不露声色地摧毁人生欲望和灵魂力量的魔窟。正是这种郁闷窒息的环境将主观对象具象化,剧中主人公都在被这个残酷的黑洞一点一点吞噬。
(二)叙述诗意语调
残酷的环境代表着快的节奏,在大环境急促的前进背景乐中,曹禺加入代表着慢的诗意语调。浓重、急切的底色,佐以截然相反的叙述风格,却能引起更激烈的对比色彩,给人带来更直观的冲击,自然而然地将作者的焦虑感慢慢渗透进来,引起心灵的震动。
《北京人》就像一首为封建大家族送葬的委婉抒情诗,整部剧笼罩在诗一样的氛围之中,充满诗的情调,具有诗一样深远的意境。它揭示曾公馆的衰亡景象,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这里没有多少激烈的表面冲突,一切在渐渐走向坟墓,悄然死去。而该生的,悄然出走,走向新生。曹禺将矛盾冲突安置在背景铺设中,在日常叙述语调中,则着力描写生活中细碎的家庭琐事,在生活化的景物、对话、动作中推进对人性的叩问。
剧本寓情于景,情景相生,声色结合,充满诗意,充分吸收了古诗的诗意表达,巧妙地将自然环境的描摹与人物情感世界的刻画和诗意的抒情融为一体,使自然景物、自然景象也能为塑造性格和刻画人物心灵发挥作用。在描绘曾家客厅古色古香的陈设时,伴随着蓝天白云间交织着的冷冷鸽哨声、独轮车发出的“孜妞妞”的响声、深夜深巷中算命瞎子悠缓的铜钲声和深夜长街传来的凄清苍凉的叫卖声、更夫更锣的木梆声,以及在暮色苍茫中远处城墙上荡漾的未归营的号手吹奏的单调的号角声,夹杂着淅沥的雨声和飒飒的风声。这正是通过声色结合的描写手法营造悲凉的牧歌情调,放慢了大家族的衰败史,却让人能够更细致地观察到衰败的细节。在诗意、缓慢的叙述语调中,烘托出特定情境气氛中文本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波澜,呈现人物心理的变化发展,从而强化看客的视觉和听觉感知,哀婉的迟暮感点点深入人心。这些背景声和人物长叹、低语、嗫嚅、絮絮叨叨、嘤嘤饮泣的情态语言,共同汇成了《北京人》既生活化又诗意化的戏剧情境,伴随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哀伤的抒情诗意情绪,焦虑感衍生出了无力感、沉重感,从单纯的焦虑到了沉痛的思索,走入了对人性的叩问。
(三)创造反抗意象
曹禺用这种充满音乐美和抒情性的诗歌语言娓娓道来秋日家族衰败的故事,一步步地叠加上棺材、耗子、鸽子、风筝、火车等象征性的物象,在对人性的焦虑中,一层一层思考当时世俗人性存在的问题,抽丝剥茧地引出对人性问题的思考。
棺材隐喻剥削阶级的命运,暗示封建文化和腐朽制度的必然灭亡,这是曹禺所坚定的价值信念。耗子则是曾家子孙的象征,他们毫无作为、毫无思想、毫无能力,显示了封建士大夫文化对主体生命力和内在气血的损害。历史的创造者成了生命的空壳、无用的废物,导致了生命的彻底浪费,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彻底丧失,进一步危及民族的存亡。这是曹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人们人性思考的映射,有知识的文化分子要如何做才能改变这些偷食生的气息的“耗子”?为什么活生生的人会变成祸害社会的“耗子”?火车蕴含着一种理想与希望,隐喻新文明和一种前进的方向。曹禺思考的结果是,只有新式文明才能拯救陷入泥潭而疯魔的人们,要用现代的科学来拯救这个社会。
实际上,文本还创造了一个潜藏的重要人物——“猩猩似的野东西”的北京人,这个意象最能代表曹禺对人性焦虑的思考结果。他虽然没有出现在文本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却一直存在于幕后,从一开始就表达出了创作者的态度。“北京人”既是人类祖先的象征,又是人类希望的象征。他是现实的“北京人”的对照物,他“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5],富有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和野性。这是对现实的“北京人”的讽刺与鞭笞,隐喻着现代人希望回归自然、反抗文明束缚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也是现代哲学思考的一个明显悖论,即野蛮与文明、人文与科学、自然与理性等等之间的冲突。曾皓、曾思懿、曾文清、愫方等中老年一代更多地承担着文明的负累,而在曾霆、瑞贞等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则显现出更多自然野性的生命基因。曾家之外的“北京人”、袁任敢、袁圆等,无拘无束,他们自然、快乐,没有繁文缛节的约束。相比之下,曾家的子孙们就成了囚笼里圈养的文明动物。事实上,这种悖论正反映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独特的荒谬现实。
但曹禺并非单纯崇拜凶蛮与粗野,他的人类理想也并非要回归原始。他深感此时生存在这个社会的人们,不是如曾文清一般的“活死人”,就是如曾皓一般的“死活人”。曹禺看透并恨透了封建势力压抑人性的罪恶,主张激发人的活力。因此,他创造了这个具有反抗意味的潜藏意象,借此阐述自己探索出的解决之道,将关注点从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深入到了陈腐、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上来。剧中袁任敢所说的“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其实就借由剧中人物道出了曹禺的心声和期盼。
三、结语
人性的本质在于尊严,而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灵魂。由于有了灵魂,人才比其他所有生物都要高尚得多,珍贵得多,神圣得多。人性焦虑是一种负面情绪,然而,曹禺通过急促的发问敦促了人们对人性的思考,这种由单纯焦虑转入深刻思考的文本表达,正是剧作的价值所在。在超越焦虑之外,曹禺体现出了更为积极、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对人性的存在充满矛盾的认识中表现出了宽广的悲悯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