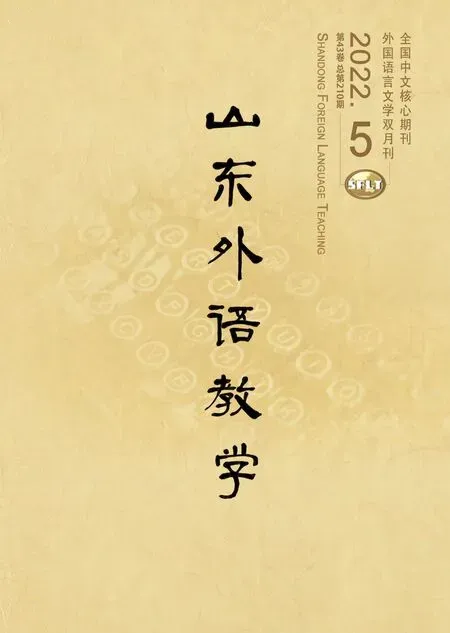苏格兰的神话:伊恩·麦克莱伦小说中的乡村共同体
王卫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1.引言
哈特(Francis Russell Hart)在《苏格兰小说》一书中将历史、共同体和人物归纳为苏格兰小说的三大母题,而在这三大母题当中,他尤其强调了共同体的主导地位。哈特认为,苏格兰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共同体的道德主导性,共同体的信念是“个人价值的基础和救赎的条件”(1978:401)。同样,《企鹅苏格兰文学史》的作者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也一再重申共同体的重要性,他认为苏格兰小说中共同体书写的开山鼻祖是19世纪初期的作家高尔特(John Galt, 1779-1839),高尔特笔下的乡村共同体是“微缩版的民族”(2007:530)。和同时代的作家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不同,高尔特的小说淡化了个体,他着力书写苏格兰西部小镇的共同体。但是,放在整个苏格兰小说史的全局之中,高尔特书写的乡村共同体也只能算作雏形,真正如诗如画地书写了苏格兰乡村共同体的当属菜园派小说,而菜园派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麦克莱伦(Ian Maclaren, 1850-1907)莫属。麦克莱伦在《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BesideBonnieBrierBush, 1894)和《旧日好时光》(TheDaysofAuldLangsyne, 1895)等小说中建构了一种理想化的苏格兰共同体,那是一种以乡村牧师兼教师为核心、崇尚平等主义教育的共同体。在物质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心甘情愿地为牧师发现的“可塑之才”(lad o’ pairts)①尽微薄之力,资助可塑之才完成大学学业。而作为回报,可塑之才学成之后会选择回到乡村做牧师,不会像城里长大的孩子那样“在商业世界寻找一个宣泄自己特殊才能的出口”(Anderson, 1983:158)。在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和可塑之才、和平等主义教育绑定的共同体是一种苏格兰性的体现,借用英国社会学家麦克罗恩(David McCrone)的话说,对乡村教区学校的理想化是“一种神话,它可以被视作苏格兰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正在遭受英格兰化的侵袭”(1992:94)。
2. 可塑之才、平等主义教育与共同体形塑
贝克(Timothy Baker)在《乔治·麦凯·布朗与共同体哲学》中归纳了共同体的四个特点:“它所指的是一个地方的、以地理区划为基础构建的区域;它具有可以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它具有可以共享的道德和伦理方式;它能够创设人际关系和呈现个体自我的语境”(2009:5)。就共同体理论建构而言,在日益强调共同体跨民族性和跨区域性的当下语境中,贝克的理论显得有些武断,因为可以共享的目标往往是需要跨区域和跨民族的。但就文学研究而言,贝克的理论并未过时。由于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书写往往有一种怀旧情怀,所以,“将共同体与外界区分开来的小天地”依然可以被视作文学作品中共同体形塑的首要因素(Keller, 2003:35)。
从某种意义上讲,苏格兰菜园派的代表人物麦克莱伦创作的小说简直就是贝克共同体理论的生动范本。麦克莱伦在苏格兰的珀斯、斯特灵以及爱丁堡接受教育,并在珀斯郡做自由教堂的牧师。作为牧师,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给苏格兰民众。作为作家,他一生致力于书写他自认为纯正的苏格兰风情。麦克莱伦的首部作品《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在英美国家影响巨大,维多利亚女王、格莱斯顿首相都十分喜爱这部作品,出身苏格兰的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也成了他的忠实粉丝。虚构的苏格兰乡村小镇德拉姆托奇蒂随着《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而闻名,麦克莱伦以此背景相继创作了《旧日好时光》《后来和其他故事》(AfterwardsandOtherStories, 1899)《拉比·桑德森》(RabbiSaunderson, 1899)等一系列极具苏格兰特色的小说。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最能体现菜园派特色的还是他最先创作的两部小说:《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和《旧日好时光》。
纳什(Andrew Nash)在《菜园派与苏格兰文学》一书中认为,麦克莱伦小说集中体现了菜园派小说的特色,“最主要的特点是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体价值的礼赞”(2007:135)。对共同体价值的礼赞不是菜园派小说的专利,但是在苏格兰小说发展史中,没有那个流派比菜园派更善于凸显共同体价值。作为苏格兰菜园派的代表人物,麦克莱伦笔下的共同体不但凸显了区域性和民族性特征,而且还为呈现个体自我提供了广阔空间。他笔下的共同体是一个崇尚平等主义教育、不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共同体最崇高的目标是培养可塑之才,因为培养苏格兰的可塑之才其实是“为整个英联邦增添财富”(Maclaren, 1894:17)。
卡梅伦(Ewen A. Cameron)在《1880年以来的苏格兰》一书中指出,以麦克莱伦等人为代表的菜园派小说展现的是“未受铁路、贫富两极分化和政治争端等现代性标志所侵袭的、感伤的和性别化的苏格兰小镇和乡村图景”(2010:9)。此话可谓是一语中的。麦克莱伦虚构的德拉姆托奇蒂就是一个未受现代性侵袭、感伤的苏格兰乡村范本。德拉姆托奇蒂的居民并不富裕,但他们上下一心,互帮互助,塑造了一个美好而祥和的家园,构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最为集中地展现菜园派小说共同体价值观的是《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的第一个故事《多姆西》(“Domsie”),它用如诗如画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充满感伤情调的可塑之才的故事。
《多姆西》中被牧师兼教师选为可塑之才的男生是乔治·豪尔,他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慧。在以德拉姆休为首的当地民众的资助下,他有幸进入爱丁堡大学,不负乡亲们的厚望,为他们捧回了一大堆奖品和奖章。然而没等衣锦还乡回报乡亲,年仅21岁的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奖章成为豪尔生前的荣誉,蔷薇成为他坟墓的点缀。德拉姆托奇蒂为豪尔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在豪尔的墓碑上,除了他的名字、年龄以及过世的时间(1869年9月22日),还特别镌刻了他的学位(文学硕士)以及一句让人震撼的墓志铭:“他们将把整个民族的荣光和荣誉都敬献给它”(Maclaren, 1894:55)。
《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的最成功之处,就是让可塑之才这个颇具苏格兰色彩的词汇得以流传。安德森(Robert Anderson)通过历史考据发现,可塑之才的说法在1894年之前的教育文献中并不存在,“苏格兰版的‘可塑之才’的频繁使用似乎就是来源于华生(麦克莱伦的真名)的乡村故事”(1985:91)。可塑之才的文化传统得益于苏格兰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教育思想。自1850年起,平等主义教育成为苏格兰杂志上热议的话题,苏格兰的大学向穷人敞开大门,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和有钱人子女一样到大学去深造。对平等主义教育高度的概括是“贵族与农民”(peer and peasant)以及“地主与耕夫”(laird and ploughman)理念,诚如《苏格兰教育》的作者吉布森所言,“地主的儿子,牧师的儿子,农民的儿子,都可以坐在同样的板凳上,学同样的课程,用同样的皮鞭规训”(qtd. in Anderson, 1985: 82)。平等主义教育使得豪尔脱颖而出,从乡村走向城市,成为爱丁堡大学的优等生。可塑之才无需经过入学考试,牧师兼教师的实名推荐即可帮助他们圆大学之梦。《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的主人公多姆西天生就有伯乐的慧眼,“他能够在萌芽之时发现一个学者,从一个看上去只适合做牛倌的男孩那里预言出学拉丁文的品性”(Maclaren, 1894:9)。如果没有平等主义教育体制,没有慧眼识珠的牧师,豪尔这个可塑之才也就只能被埋没在偏远的苏格兰小镇。
乔治·布莱克对菜园派小说的感伤情调给予了无情的嘲讽,他认为菜园派小说家“是一群聪明而又感伤的苏格兰人,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感伤情调”(qtd. in Bold, 1983:107),其实不然。麦克莱伦笔下的可塑之才豪尔之所以英年早逝,是因为他只享受了苏格兰平等主义教育的一个方面(开放竞争),而与另一个方面(奖学金)无缘。豪尔能读大学全靠家人的节衣缩食以及当地民众的乐善好施。他品学兼优,从爱丁堡大学获得了一大堆荣誉,但就是没有拿到奖学金。如果有奖学金,豪尔或许就不会积劳成疾,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从这种意义上讲,豪尔是个可怜的可塑之才,他没有来得及走完可塑之才的最后一步:完成学业回到乡村做牧师。但是,豪尔同时又是个可敬的可塑之才,在他弥留之际,他仍然不忘一个未来牧师的职责,他成功地劝解一位同乡的纨绔子弟弃恶从善。
需要强调的是,麦克莱伦笔下可塑之才故事的核心不是个体,而是一个崇尚平等主义教育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商业成功并不值得夸赞。在列举多姆西的教育成果时,商人被放在最不显眼的位置:“多姆西时代学校送出去的英才中有七个牧师,四个校长,四个医生,一个教授,三个公务员,还有许多‘将自己献身于商业追求的人’”(MacLaren, 1894:9)。平等主义教育体制最看重的是拉丁文和希腊语教育,而商业教育、“科学特别是技术教育被给予很低的地位”(Paterson, 2011:97)。平等主义教育对于共同体形塑的作用不言而喻,诚如1837年《皇家委员会关于苏格兰大学的报告》中所言,不问贫富、任人唯贤的苏格兰平等主义教育“对共同体整体而言产生了诸多好处。它通过大学教育这个更友善、也许更强大的纽带,将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联系在一起”(qtd. in Anderson, 1985:85)。
3.乡村共同体的核心与“良心”
凯勒(Suzanne Keller)在《共同体:追寻梦想,实现现实》一书中强调了领导者对共同体的作用,她认为,共同体的成功有赖于“每个人的参与以及有效的领导者,堕落的领导者会给共同体带来灾难”(2003:21)。麦克莱伦小说中的共同体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牧师兼教师”(dominie)的引领。安德森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与机会》一书中将教区学校、乡村牧师兼教师、可塑之才视作菜园派小说的三大核心(Anderson 1983:26)。在三大核心中,教区学校提供了场所,可塑之才和牧师兼教师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千里马和伯乐,没有伯乐,再好的千里马也只能在边远的苏格兰乡村壮志难酬。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在三大核心中找出最重要的因素,那应该是牧师兼教师。
非常有趣的是,就个人发展而言,麦克莱伦笔下的牧师兼教师不是成功的牧师,而是失败的牧师。国外学界借用菜园派小说家克罗齐特(S. R. Crockett)的作品名称,将此类人物命名为“stickit minister”,《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中的多姆西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多姆西上大学时是优等生,有很好的学位与前程,大概是因为爱情受挫(小说叙述者在多姆西临终时佩戴的盒式项链坠里看到了一张傲慢而美丽的女人头像),否则他或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德拉姆托奇蒂这块穷乡僻壤度过余生。多姆西服从命运的安排,把所有的爱和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学生身上。是他发现了豪尔这个可塑之才,他游说乡亲们慷慨解囊,才使豪尔得以圆大学之梦。他牺牲了自己却成就了共同体,在他执教期间,德拉姆托奇蒂是“一个以它送往大学的孩子而闻名的地方”(MacLaren, 1894:4)。
在麦克莱伦的小说中,牧师兼教师绝不仅仅是善于发现可塑之才的伯乐,他是共同体中最具凝聚力的核心人物,是共同体的基石。凯勒指出,对共同体构成威胁的最主要因素是“宗派纷争以及关于土地、财产和目标的纠纷”(Keller, 2003:35)。一旦出现宗派纷争以及土地纷争,牧师兼教师就立刻挺身而出,成为维护农民利益、维系共同体价值的纠纷调解人。麦克莱伦在《旧日好时光》中一则名为《为了良心》(“For Conscience Sake”)的短篇小说中,以生动的笔触书写了德拉姆托奇蒂小镇上的宗教冲突和土地纠纷。在这则故事中,小镇上的代理人(factor)试图强迫伯恩伯雷改变宗教信仰,如果他不同意,代理人就会毁弃土地租约,让伯恩伯雷失去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伯恩伯雷为了心目中的良心和所信奉的教义,决定放弃个人利益听从上帝召唤,宁肯失去土地也决不放弃信仰。在这种宗教意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的老伴儿坚定地支持他。最后,在牧师的协调之下,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地主也站在了农民一边,代理人成了孤家寡人被迫让步,伯恩伯雷终于幸免于难。小说中的教派纷争是指自由教堂(free church,苏格兰地区称为free kirk)和圣公会(established church)之间的争斗,在代理人的眼里,两个教派之间的纷争简直不可理喻。代理人质问那些为了“良心”而不惜舍弃自己土地的乡民:“难道自由教堂用一种方式唱赞美诗,而圣公会用另一种方式吗?”(Maclaren, 2008:33)在他看来,为了所谓的良心与时代对抗,不过是苏格兰人特有的执拗罢了。代理人的质问不无道理,在苏格兰历史上,由于自由教堂成立之初并没有专门的教堂可以做礼拜,自由教堂和圣公会的会众轮流使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司空见惯。但在农民们眼中,自由教堂和圣公会还是水火不容。在宗教纷争迭起的时候,麦克莱伦笔下的牧师总是站在农民的一边,为自由教堂辩护,为共同体的维系而出面调停。
作为一名苏格兰自由教堂的牧师,麦克莱伦对宗教冲突问题了如指掌。从1843年开始,苏格兰自由教堂在许多地区确立了自己的朝拜仪式,由于一时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场所,在一些较小的城镇和乡村,自由教堂和圣公会轮流举行宗教集会,已然成为双方默许的事实。从这种意义上讲,《旧日好时光》书写的是苏格兰乡村的真实图景。两大教派相互独立,各自笼络着自己的牧师和教徒,在德拉姆托奇蒂小镇这样的小地方,宗教纷争竟然也如此波澜壮阔。代理人是商业社会的缩影,他试图以商业手段干预乡民的信仰,在德拉姆托奇蒂这样一个到处都是“为了良心”的信徒的地方,他注定要失败。本来可以和他站在一道的牧师,为了“良心”倒向了农民的一边,连地主也为农民的坚定信仰所感动。所以代表着商业文明的代理人,就必然会在眷恋着农业文明的苏格兰小镇里栽跟头。
就总的基调而言,共同体理论的建构者大多是礼赞乡村而贬抑城市。斯达德特(D. Studdert)在《共同体的概念:在政体与个体之间》一书中就认为,“城市生活代表着乡村传统的衰微以及社会化文明状况的崛起,城市中的和平和商业是通过相互之间潜在的恐惧以及社会规约来维持的”(2005:22)。在《旧日好时光》中,麦克莱伦借叙述者之口,对乡村共同体给予了礼赞,而对城里人的无根性则进行了无情鞭挞:“对于一个城里人来说,他可能在一个城市出生,在第二个城市受教育,在第三个城市结婚成家,在第四个城市工作”(Maclaren, 2008:30)。城市人的家就像旅馆,住了之后就忘了。城市人没有根,是地球上的流浪汉。而农村人则截然相反,从出生、成长、成家、劳作乃至死亡,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老年看到的风景和孩提时代看到的并无二致。农村人的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你要是把他和土地分开,他的心就会枯萎,就会死亡”(同上:30-31)。
《旧日好时光》中一则题为《婢女》(“Servant Lass”)的故事最生动地阐释了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女主人公莉莉离开家乡奔赴伦敦务工,村民像欢送可塑之才一样慷慨解囊,深深祝愿,盼望莉莉能在伦敦有更好的前程。人们都想去看看伦敦塔,看看西敏寺,“那是一个许多大人物安眠的地方”(Maclaren:2008:159)。然而莉莉在伦敦并不快乐,苏格兰的孩子们中爆发了猩红热,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家照顾家人。然而没等她回归故里就已经奄奄一息,她临终时最大的愿望是“和妈妈、奶奶躺在德拉姆托奇蒂的墓地里”(同上:169)。同乡的好人杰米承诺要把她带回家乡安葬,乡亲们坚持认为,莉莉留在乡村就会安然无恙,是伦敦这个大都市“杀死了她”(同上:161)。
如果我们认同安德森的说法,将教区学校、乡村牧师兼教师、可塑之才视作菜园派小说的三大核心,那么,这三大核心中的核心应当是牧师兼教师,教区学校是牧师兼教师和可塑之才共享的场地,而乡村则是菜园派笔下苏格兰共同体的依托。只有在乡村的背景之下,自由教堂和圣公会之间的宗派纷争才能得以和解,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情结才能得以维系,为可塑之才慷慨解囊、为了良心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壮观场面才能够出现。一旦离开了乡村的依托只身赶往城市,就会和《旧日好时光》中的莉莉一样无根无助,在孤单寂寥之中枯萎死亡。虽然莉莉在临行前带了一大袋家乡蔷薇的干叶子来回忆故乡的清香,但这种象征性的东西抵挡不住城市的冷酷无情。
4.美丽而“真实”的苏格兰
以麦克莱伦为代表的菜园派小说,用生动的笔触书写了一个到处是田园风光、感伤情调、互帮互助、和谐的乡村共同体,这种理想化的共同体书写被批评家们称为神话(myth)。当代英国作家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2005)在《魔法师》(TheMagus)中用一句话概括了神话中美丽与真实的悖论,他说神话世界到处充斥着“美丽但不真实的岛屿,不真实但美丽的公主”(1977:552)。在福尔斯的眼里,文学世界的美丽和真实,就好比中国古人常说的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菜园派小说的研究者将教区学校、可塑之才、平等主义教育等称之为神话,言外之意似乎就是在批评菜园派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美丽但不真实。菜园派研究的领军人物谢泼德(Gillian Shepherd)就认为,菜园派是在“用一种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冷酷、越来越不真实的方式”书写苏格兰共同体中的苏格兰人(qtd. in Brown, 2000:150)。
谢泼德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以麦克莱伦为代表的菜园派小说中以可塑之才和平等主义教育为轴心、以牧师兼教师为核心、强调共同体中个体“良心”的写法其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麦克莱伦小说中的美丽和真实并不矛盾。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可塑之才在苏格兰不是神话,而是事实。安德森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与机会》一书中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包括著名的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以及苏格兰著名希伯来语教授缪里(Alexander Murray, 1775-1813)。卡莱尔13岁步行到爱丁堡“开始他作为贫困学生的古典生活之旅”(Anderson 1983:6);缪里小时候是牧童,在当地牧师的举荐下,他最终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奖学金才圆了大学之梦。和菜园派小说中最经典的可塑之才一样,毕业后他做了乡村教区牧师,多年以后才成为希伯来语教授。根据佩特森(Lindsay Paterson)的考据,在20世纪的前20年,苏格兰教育部门(SED)依然在倡导平等主义教育体制,希望整个苏格兰都能发现可塑之才,并通过实名推荐将他们送入大学,而这种体制其实是19世纪“可塑之才神话传统的现代化”(2011:96)。
此外,麦克莱伦笔下的失败牧师形象也和历史记述相吻合。布朗(Callum G.Brown)在《重读菜园派》一文的开头讲述了一个饱受磨难的牧师的故事:1711年3月1日,约翰·莫里森牧师被派到加尔洛克做长老会教区牧师,当地人开始并不欢迎他,把他关在满是牲畜和粪便的农舍里足足三天。六个月后,当他在马里湖东岸旅行时,又被当地居民脱光衣服绑在树上任凭蠓虫叮咬。最终,他的善行感化了当地的一个女人,她出于同情将其释放(2000:138)。麦克莱伦笔下的牧师多姆西虽然没有上述故事中的磨难,但他在大学爱情受挫,在游说德拉姆休为可塑之才捐款之初也被推三阻四。他一反常态地发了火儿,慷慨陈词,对德拉姆休讲了一大通培养可塑之才是为英联邦增添财富的大道理,德拉姆休深为感动,才最终答应出一大笔钱资助可塑之才。
对于颇受人诟病的感伤情调问题,麦克莱伦有着自己的解释。麦克莱伦认为,他小说中频繁出现死亡的场景其实和自己作为牧师的身份有关:
“作为牧师,我们很少看到生活光明的一面。我承认,婚礼上也能迁就我们,但我们更熟悉的是葬礼。人们不会让牧师去分享他们家庭的节庆。他最通常听到的是痛苦的话语,每天都和死亡面对面。这很容易使得他的头脑变得严肃起来。”(qtd. in Nicoll, 1908:170)
麦克莱伦小说中的死亡场景确实令人倍感伤怀,尤其是《多姆西》中乔治·豪尔的葬礼的那一段,读者忍不住要为这位品学兼优的可塑之才的英年早逝而潸然泪下。但这种死亡场景绝不是为了赚取读者的眼泪。麦克莱伦是一位牧师出身的作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位熟悉葬礼而不熟悉婚礼的牧师去书写欢天喜地的场面,而对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令人感伤的场景不闻不问。
其实,无论麦克莱伦笔下的苏格兰真实与否,他对于苏格兰文学的贡献都不可低估。他对苏格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出神入化地书写了苏格兰乡村共同体的生活,美丽的苏格兰也使他成名于世。作为一名作家,他希望自己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完美的苏格兰。在1894年5月28日致史蒂芬·威廉森的书信中,麦克莱伦写道:“如果呈现苏格兰生活的努力让您愉悦,那正是我的一点希望”(qtd. in Nicoll, 1908:162)。麦克莱伦的小说特别适合这样的读者群,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机会来亲自参观想象中山谷里的乡村”(Campbell, 2008:xiii),所以,真实与否并非问题之所在,是否具有典型性才是关键。人们可以怀疑麦克莱伦笔下的苏格兰乡村共同体是否真实,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麦克莱伦笔下的苏格兰就是读者心目中的苏格兰。
福尔赛斯·哈代(Forsyth Hardy)在《电影中的苏格兰》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在制作电影《南海天堂》(Brigadoon, 1954)时,制片人找到正在《苏格兰人》报社做记者的他,说想在苏格兰为电影取景,取景之地最好是苏格兰高地保持着百年前旧貌的乡村。哈代带他去了卡尔洛斯、丹凯尔德、康姆莱伊、因弗沃瑞,制片人摇头叹息。当他返回好莱坞的时候,他深感失望地对同事说:“我去了苏格兰,但没有见到任何看起来像苏格兰的东西”(1990:1)。制片人的这句话颇有深意,有意无意地道出了外人眼里的苏格兰形象,那就是百年不变的苏格兰乡村。一旦乡村被城市商业化和工业化侵扰甚至吞没,那么人们心目中的苏格兰也就不复存在了。布朗在《重读菜园派》一文中这样概括苏格兰的特点:“这个地区主要是乡村,按西欧的标准经济上相对落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体,到处是山、沼泽,有700多个岛屿。交通不畅,地方特色很强”(Brown, 2000:139)。其实布朗的话可以归结为一句,那就是苏格兰最主要的特色其实就是乡村。
和英格兰相比,或许苏格兰小说中的共同体和乡村的绑定关系更紧密一些,但乡村共同体书写并非苏格兰小说的专利。真正把苏格兰和英格兰共同体书写方式区分开来的恰恰是麦克莱伦笔下以可塑之才为轴心的平等主义教育神话。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把以可塑之才为轴心的平等主义教育理想视为苏格兰性(Scottishness)的体现。社会学家麦克罗恩认为,平等主义教育是“可以界定苏格兰民族的特点之一”(McCrone, 1992:100),它已然成为了苏格兰民族的文化资本。教育学家安德森引证苏格兰教育史料,认为苏格兰平等主义教育反映了苏格兰生活的基本民主属性,是一种内在的平等,这是“把苏格兰和她的南方邻居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Anderson, 1985:83)。
5.结语
殷企平在《共同体》一文中描述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冲动,他认为,工业革命之后的共同体冲动其实是人们“群起为遭遇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冲击而濒于瓦解的传统共同体寻求出路,并描绘出理想的共同体愿景”(2016:78)。共同体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怀旧。在当下语境中阅读麦克莱伦的菜园派小说,会有许多新的关于共同体的启示。首先,麦克莱伦书写的以可塑之才和平等主义教育为轴心、以牧师兼教师为核心的苏格兰乡村共同体并非纯然虚构,它和苏格兰的历史记述有诸多吻合。其次,麦克莱伦笔下的苏格兰共同体与乡村有着一种绑定关系:一旦离开了苏格兰乡村,共同体就不复为共同体。一旦共同体风雨飘摇,苏格兰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的苏格兰。最后,麦克莱伦笔下的可塑之才神话体现着一种苏格兰性,乡村共同体书写不是苏格兰的专利,牧师兼教师的角色也并非苏格兰小说的专利,但是,以可塑之才为轴心的平等主义教育却是苏格兰民族的文化资本,是与英格兰相区分的重要标志。虽然可塑之才神话已经成为过去,但以麦克莱伦为代表的菜园派小说中铸造的可塑之才之魂并没有成为过去。
注释:
①关于“可塑之才”的具体释义,参见王卫新《〈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中的苏格兰商业“美德”》,载《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第135页。
——与姚大志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