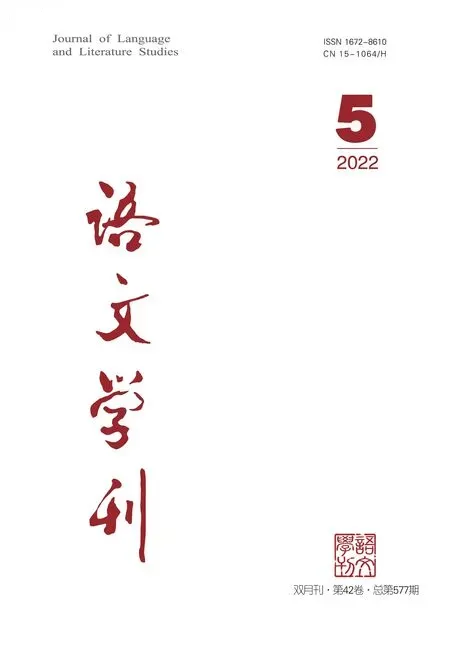传统与时间的对话
——艾略特传统观中的历史意识与诗学实践
○ 李敬巍 喻名希 牛煜琛
(1.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2.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艾略特是20世纪重要的作家、批评家之一,也是“英美新批评”的思想先驱,他的“感受的统一”“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等理论无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他的种种理论之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他的“传统”观。艾略特早年在法国求学时曾系统学习过柏格森的哲学理论,受柏格森“绵延”观念的影响,艾略特建构起了自己的“传统”观。本文将从艾略特传统观中的历史意识出发,探讨其对于柏格森的具体借鉴以及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实践。
一、艾略特文论体系中的“传统”
“传统”(tradition)是艾略特文论体系中的核心观念,也是艾略特的文论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在艾略特的文学批评中,与“传统”有关的理论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整体性、传统观的历史意识、语言、神话、民俗在内的等理论都与之相关。本文中的“传统”主要指艾略特与“个人”相对应的“传统”观。不同于以往考古学的“传统”,艾略特认为“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1]2。在艾略特的“传统”观念中,并没有将“过去”(past)孤立看待,而是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认为“传统”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与批判的有机结构。艾略特认为“传统”含有历史的意识,这要求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1]2,并达到永久和暂时的统一。
除了“历史意识”之外,艾略特认为“欧洲文学和英国文学自有其格局”[1]3。他将传统视为一个“理想的秩序(order)”,它是需要不断自我批评与修正以发展自身的有机结构。“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1]2,由现有的经典所构成的传统的秩序本身是完整的,但如果要在传统中加入新作品后使其继续保持完整,整个传统所形成的“秩序”必须为之改变,构成传统的每个作品的价值关系比例都会随之重新调整,这就是“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1]3。
虽然这种“秩序”很容易让人视作一种理想化的、终极的秩序,但艾略特认识到“传统”也涉及批判和变革,“它不是既定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僵硬地摆在那里并由静观来发现的东西,它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存,更多表现为一种可能性”[1]4。这种批判性的观点不仅针对眼前的过去,通常也描述了诗人与过去所有成就之间的关系: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到主要的潮流,而主要的潮流未必都经过那些声名最著的作家。真正要做到“创新”,必须深刻意识到不断变化的“欧洲思想”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与欧洲诗歌的整体建立有机联系。
(二)柏格森的“绵延”
1911年前后,艾略特在法国学习期间接受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哲学基础。柏格森的直觉理论所给予他的最大支持,莫过于唤醒了艾略特的时间意识,助其完成对“传统”的“历史意识”的认识。
柏格森的理论以源初事实为依据和出发点,他在寻找意识材料的源初性时排除掉了意识领域中一切附属于空间属性的东西,从而余下真正的性质的多样性——一种持续着的“绵延”(Duration)。柏格森将时间与绵延等同看待,区别于科学研究中可以测量的时间,纯粹绵延是“性质变化的连续体,这些变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并与数目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纯粹绵延是纯粹的异质性(l’hétérogénéité pure)”[2]99。柏格森还将存在的范围从意识领域扩大到了整个宇宙:他认为宇宙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绵延,一个创造着的绵延。他引入物象(image)的概念,认为世界是一个物象的世界,在世界的绵延中将宇宙本身看作一个未完成的巨大的东西,它永远倾向于成为一个个体,却又永远无法达到,只能永远处于完成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它永远处在流动之中,永远活在它自身的永无终结的不断完善之中。
而在人类的绵延上,柏格森认为,“记忆”对人类来说是时间的本体论层次上的核心,可以说,记忆就是人类的绵延。柏格森用“人格”(la personnalité)一词来代替真正的自我(深层自我),他认为,我们直接“看到”的人格是 “灵魂状态在时间的路途上前进,它随着绵延的累积不断地自我扩张,可以这样说,它是在带着自身滚雪球”[2]157。我们就这样带着自己过去所有的记忆,像滚雪球一样在时间中前进。“我们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性格?我们无非是从出生以来,甚至是出生之前的历史的凝缩,因为我们全都带着先天的禀赋。”[2]157这种人格带着所有过去的记忆,而且它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个加入到过去所有瞬间的新瞬间”[2]157。
(三)历史意识
“传统”观是艾略特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传统”中的“历史意识”也是他构建自身诗学体系的基点,这里的“历史意识”即是“传统”观中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性理解。这是一种在当下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识,也是接近和成为“传统”所必不可少的意识。
在艾略特的传统观中,“传统”不能被直接继承,要达到“传统”必须具有历史意识(the historical sense)。这种历史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1]2,它使得传统“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1]2,这需要诗人在写作时对“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文学”[1]2进行批判性把握,并将这种文学结构视作“同时的存在”。他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认为,过去一直都是与当前共存着的,在“现在”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说,过去恰恰就是一种现在。
在这种“历史意识”的观照下,“传统”是一个过去与现在同时存在的,不断完善更新的开放体系,正如柏格森认为宇宙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绵延,一个创造着的绵延,它永远倾向于成为一个个体,却又永远无法达到,只能永远处于完成的过程之中。艾略特的“传统”可以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解读,“过去的过去性”可以从“共时”角度进行横向的理解,而“过去的现存性”则可以从“历时”角度看待——在“传统”历时沿袭的过程中,“传统”中的“过去”并没有成为积灰的古董,而是以一种积极的互动来进入当下“传统”的构成中来,使得“传统”成为一个未完成的自我批判自我发展的开放体系,使得它自身永远处在流动之中,永远活在它自身的永无终结的不断完善之中。
“过去”的作品和思想可以给“现在”以引导和互动,“现在”同样可以赋予“过去”当下阐释和现实价值。人们可以时时运用这种历史意识去关照“过去”的文学作品,用“现在”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标准去重新阐释它们,使得它们获得与以往不同的、对标当下现实意义的文学理解,获得对以往自身认识的超越。这种历史意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使得“传统”包括了一定时空内的整个的文学,同时也让作家意识到自己在这一“传统”中的地位以及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对艾略特来说,历史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1]2。通过“历史意识”,传统不再只是“过去”的东西的集合,“传统”中的“现存性”连接了过去和现在,并通向未来,成为柏格森哲学观点中的一种“绵延”。
艾略特认为哲学应该看到理智(intellect)和直觉(intuition)的同一性,而不是将它们割裂。他在早期的论文集中有过“柏格森主义本身是一种理智建构(Bergsonism itself is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3]41的表述。柏格森用“直觉理论”解释世界,并通过它将直觉观点融入理智观点中,因此,艾略特赋予了“永久的意识和暂时的意识”一种理智维度,它与包含着历史记忆的秩序或直觉有关。艾略特将集体历史心理无意识(the collective-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unconscious)与诗歌写作相结合,他借鉴了柏格森的“记忆”,即从永恒绵延的概念演变而来的个人无意识(the personal unconscious),根据柏格森的说法,记忆就是人类的绵延。“我们无非是从出生以来,甚至是出生之前的历史的凝缩,因为我们全都带着先天的禀赋。”[2]157正如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总结的,“任何民族维护其文学创造力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广义的传统——所谓在过去文学中实现了的集体个性——和目前这一代人的创新性之间保持一种无意识的平衡”[1]193。这也正是艾略特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进行实践的,通过拾捡起普遍的和非个人的过往记忆的碎片,使自身不断接近“传统”,直到汇入其中成为新的部分。
二、历史意识的诗学实践
(一)追忆:接近和成为“传统”的过程
“非个性化理论”(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是艾略特标志性的文学理论之一,也是艾略特的“传统”观中的历史意识投射到诗歌创作上的产物。艾略特认为,“诗人,任何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1]2。“传统”的共性超越了任何特定的私人意识或狭隘的群体意识,一个诗人必须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必须明白什么是文学史上的主要潮流,因而这种客观上跨越个人声音的理论就此被提出:诗歌不是个人情感的溢出,一个诗人必须学会在诗歌中牺牲自己的个性和情感,才能置身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潮流。“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的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
非个性化理论主张诗歌所表达的艺术情感不同于“简单、粗糙或者乏味”[1]13的个人情感,而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而艾略特认为,“艺术情感成为统一的感受的途径是通过个体感受的客观化”[1]13,这就是艾略特1921年在他的批评文章《哈姆雷特》中提出的著名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理论。在对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批评文章中,艾略特为主人公“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延宕做出了如此解释:“艺术上的‘不可避免性’在于外界事物和情感之间的完全对应,而《哈姆雷特》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对应。”[1]13他认为艺术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就是为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或某种实物,或某处场景,一旦“客观对应物”所牵连的现实与意象的对应关系失误,例如,当亲情的承载体——“母亲”超出其原本对应的情感范畴,成为哈姆雷特厌恶和复仇的对象时,其所引起的情感效果势必走向困惑和延宕。相反,若意象与艺术效果的对应关系能够客观地得到确认,那么只通过呈现意象就足以引发相应的感觉经验。“非个性化”理论和“客观对应物”都是艾略特诗学主张中的组成部分,而它们理论构建的基点在于“传统”观中的历史意识,即对“传统”的时间性理解。这在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体现为寻找合适的“客观对应物”使“个人”和“传统”的感觉相连,从而向“传统”学习并使自身接近和成为“传统”,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之为“追忆”。在这里引入“追忆”的概念,它原本是宇文所安在讨论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西方文学的区别时提出的,他将西方文学归结为“换喻”的典范,即指代艺术与感性世界之间,一种摹仿、复现而泾渭分明的关系,其核心是意涵与形式的逻辑协调;至于中国古典文学,则被视为“举隅法”的土壤,旨在说明“记忆”与“传统”在古典诗歌中的特殊表达——在“追忆”发生时,记忆与被记忆者处于同一纬度,“过去的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4]3。虽彼此所追溯的“过往”不同、“传统”各异,但从实际创作来看,艾略特的诗学实践承担了与之相近的艺术效果。
在“非个性”理论中,“传统”被看作与一种“个人”对立的、应当被正视和追忆的存在:“传统的意义实在要广大得多。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就必须用很大的劳动。第一,它含有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1]2这一论述同样可以作为艾略特“历史意识”的佐证,我们所追忆的“传统”并非仅是个人化的记忆与生活体验,而是更为辽远层面的概念,所以他称“这些经验不是‘回忆出来的’”,而是需要向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过去学习、拾捡。如艾略特所述,“对于诗人来说,只有斗争才有生命——斗争的目的就是把个人的、私自的痛苦转化成为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和非个人的东西”[5]164。由此生发的“追忆”随之成为对社会和文化整体经验及“传统”的回溯,它注定宏大而破碎,故绝难囿于个人的、具体的现实。实际上,在对“传统”的认识上,后来的学者亦有所声张——“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说是自我折射的建构”[6]35,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无根无源的文学作品。“传统”在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亦从未被轻视,而艾略特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改变了对“传统”的态度和接近它的方式,即一种作为过程的“追忆”。
艾略特之前,欧洲文学传统的继承一般表现为对方法论的学习。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时代起,经常能够得到承认的“传统”是“摹仿”(Mimesis),艺术,或细致到文学,无论是作为对柏拉图“理式”世界的摹仿,或是对自然现实、感性存在的摹绘,又或者黑格尔所主张的绝对精神的代言,在“摹仿”的嬗递中,人们只将其当作创作上的某种启示或指导,对待前人的态度往往仅限于风格和艺术价值的批评,各种文学作品、流派途经这一“传统”,各自选择反映时代现实的方式,终抵各自的目的地,“传统”于此成为一种路径般的存在。
艾略特则将“传统”视作一个完整且日益衍化的本体,视作一个“宝库”,甚至“终点”,“摹仿”不过其中一隅。而诗人通过拾捡起过往记忆的碎片,一次次地追忆“传统”,使自身不断接近那里,直到汇入其中成为新的部分。此外,对过去的认识规定了我们必须站在当下,而当新的内容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时,能够认识和追溯它的位置又变成了将来,这也意味着,“追忆”的行为并非一时一地,而是于每个时代都会存在的一种发展的方式,换言之,“追忆”是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
(二)荒原:历史意识与“追忆”行为的具象化
《荒原》(TheWasteLand)是艾略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反映其文学“传统”观的代表作品。“荒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缩影,也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熔炉。全诗一共434行,诗中共使用了7种语言,引用了一百余个典故,从而将遥远的古代与现代连接起来,将欧洲与亚洲、美洲、非洲关联起来。烦琐的典故、变幻的时空、不断被破坏的人物形象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荒原》为表达思想,否定与毁灭了诗中的自我个性。艾略特在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和现实生活中捡拾起种种意象,这些破碎的意象都经历过这种“毁灭”,它们不是诗人有意创造的,而是一种经过变幻的“对应物”,读者能够通过它们的情绪、心灵和内心世界的物象,感受到它们对应着的整个欧洲,甚至是移植了印度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世界“传统”,这使得荒原成为一个包罗着整个欧洲文学甚至世界文化的失落之地。
《荒原》由不同的片段构成,每个片段都有一连串体现着深广历史文化传统的情境,这些情境并置重叠,形成了这样一个欧洲文明的失落之所。在这里,艾略特混合了过去与现在,将古老神话与真实事件、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相交融,从而将现代西方世界紊乱的社会面貌和荒凉的精神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艾略特拒绝给诗歌加以结构的束缚,拒绝依赖线性的时间习惯进行联想,他的创作同时又表现出包举宇内、超越某一特定文化背景的宏大意图。为此,他找到了最可能实现的方式:纯粹依靠感觉和经验,从跨国界、跨民族的宽阔知识和历史中拾捡起文化的“碎片”,借此将典故所代表的“传统”和实际意象所指涉的“现实”一并与读者的情感对应起来。于是,曾经的时间被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还原到一起,形成了一处时空杂陈的“荒原”——既是“对应物”的聚合,本身也作为欧洲文明现代困境的“客观对应物”而呈现,我们因而得以回想起诗人和我们自身关于过往的“记忆”。
具体至文本,通过《荒原》中意象的组合,其所唤起的“追忆”的对象常以神话原型的形态出现,整体来看,统摄整个“荒原”的神话原型,即“荒原”本体精神的源头,在于韦斯顿《从祭仪式到传奇》和弗雷泽《金枝》中的“圣杯传说”——一则关于“荒原”的统治者,“渔王”的神话。《从祭仪式到传奇》第九章中提到,“渔王”是“一位半神,站在他的人民与土地,以及控制他们的命运的不可见力量之间”。而根据艾略特的注释,他特别引用了《金枝》中“关于阿童尼斯、阿蒂斯、奥西斯那两卷”[7]127,从而组成了“圣杯传说”的基本设定:“伊希塔是伟大的母亲女神,是自然生殖力的化身”[8]526,人们相信她每年为寻自己的伴侣神祇,要到黄泉走一趟,她不在时,人间一切生命都受到灭绝的威胁,而当其用“生命之水”回到阳世,“自然界的一切就复苏了”[8]526。“渔王”的形象于是与之相洽,“渔王”——其本体即多元文化背景下同构的神话原型,亦即繁殖神的形象,他失去了性能力,曾经的王国随之变成“荒原”——繁殖神的繁殖能力与土地的生命力联系在了一起。
当论及“原型”,很容易使人相信“渔王”的形象正是荣格所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选择,是作为艺术灵感源泉的“原始意象”,但令人生疑之处依然存在——一来对“渔王”的追忆确实通向共同的“传统”,符合“非个性原则”的生效,但从个人的角度,这同样也是一种背离,即诗人是在个体记忆和经验的指引下,有意识地追求“无意识”的原型;再者,“渔王”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原型”,对于我们在现实中产生的荒芜感而言,他并不具备“补偿性”,相反,他更像是揭露我们正处在何种困境中的一幅投影。不止“渔王”如此,《荒原》中隐现的其他“原型”,在我们“追忆”他们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如第二诗节的《弈棋》,前半部分的“追忆”发生在两个时空的对话与对弈之间:先是坐在辉煌堂厅中寂寞无言的贵妇,其后墙上的刻画昭示出更加遥远但是与其同质的时空——弥尔顿笔下的另一处失落之所“失乐园”。然后“原型”就此登场,“仿佛是一扇眺望林木葱郁的窗子/挂着菲罗墨拉变形的画图/她被野蛮的国王/那么粗暴地强行非礼/但夜莺曾在那儿/用她那不可亵渎的歌声充塞了整个荒漠”[7]106。这里化用了奥维德《变形记》中菲洛墨拉的悲剧,同样讲述一位国王因性欲而犯下的罪愆。此后,一场对话使“我”所处的时空现身,“你在想什么?想什么?是什么呀?/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想看/我想咱们是住在耗子的洞穴里/死人连他们的尸骨都丢失了”[7]106。“耗子的洞穴”原文为“rats’ alley”,实际指索姆河附近的一条战壕,从“耗子的洞穴”一路回忆至“铺满尸骸的战壕”,诗人自己也已察觉到,无论诗歌还是现实,基于自己记忆所建构的到处是无法完成的形象和场域,因此他只能进行,而无法结束“追忆”这一过程,只能不断“追忆”那些可以加入并成为诗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所构成的破碎、荒凉的感觉,却绝无终点。
在第三节《火诫》中,“原型”激发“追忆”的功用更为昭彰。诗的后半节讲述了一位都市小职员与其情人间淡漠的性生活,其奇异之处却在于,以神话原型的视角涉入了平庸无序的现代生活叙事。
在暮霭渐浓的时刻,这时眼睛和背脊
从办公桌上抬起,这时人类的发动机
像突突地震动着等待开动的出租车那样等待着,
我,泰瑞西士,虽然双目失明,跳动在两个性别之间,
长着皱巴巴女性乳房的老头儿,却能看见[7]113
“泰瑞西士”,又译作“忒瑞西阿斯”,在本节中,他与作为“现代对应物”的商贩形象,即“尤金尼德斯先生”,构成彼此观照的一组形象,而艾略特格外强调这个人物的重要性:“泰瑞西士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是戏中的‘角色’,却是本诗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贯穿所有其他人物……事实上,泰瑞西士所见到的,也就是本诗的内容实质。”[7]132因此,我们很难忽略对此形象的分析,按照诗人的解释,诗中所有的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同理,男性角色也并无不同,然而,“泰瑞西士”是唯一的例外——他源于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一则神话,相传他在看见两条蛇交合时,将它们击打,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女人,7年之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击打蛇,遂又变成了男人。当朱庇特与朱诺问及他哪个性别从性爱中获得了更多快乐,他称女性获得的快乐远胜男性,朱诺于是使其失去了视力,而朱庇特则给了他预言的天赋。“预言”和“两性同体”,或许正是诗人看重这一形象的原因。神话里的人物穿越到了现代,然而身负的职责并未改变,在一个时代里,这个形象本身就成为其他时代遗落,或间入于此的“记忆碎片”,甚至是全诗最重要的一处路口。诗歌借一个古典而超现实的人物之眼,去审视现代都市里失去本真的贫瘠生活与“爱”。除了“目睹”,他同样发挥了自己神予的职责,“预见”,或者说“想象”——从“我,泰瑞西士,长着皱巴巴乳房的老头/看到这番景象,就能预知其余”,到“我,泰瑞西士早先已经经受过/在这同一张长沙发或床上演出的一切”[7]114-115。诗人戴上泰瑞西士的面具,引领我们站在一处交界,通过追忆,进入迷宫般的荒原,我们则通过“泰瑞西士”的眼看到都市里习以为常的意象,同时预见到剩下的一切,由此追忆起神话中的性爱,想象着“荒原”还未荒凉前的那个繁盛蓬勃的王国。
“追忆”注定是个无法产生结果的过程,但这一行径本身却极富意味。在追溯遥远的意象,和自觉呼应以往的“传统”时,它产生了为这片荒原开疆拓土的愿望,同时怀抱一种期待:今天的“追忆”正预示着,如稀矿般蕴于自身的碎片意象,终也会在将来某一天被后人重新拾捡起来,并帮助他们回忆起那时已经作古的“今天”。
三、结 语
“传统”观念中的历史意识可以被看作是艾略特文学批评体系构建的一个基点,它是在柏格森“绵延”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历史意识”的观照下,“传统”是一个过去与现在同时存在的,不断完善更新的开放体系。“传统”观中的历史意识要求诗人不断接近和成为“传统”,这就必须牺牲诗人自己的个性和情感,“非个性化理论”由此提出。而诗人牺牲掉个性,表现普遍的共性则需要通过“客观对应物”来实现。诗人必须寻找合适的“客观对应物”使“个人”和“传统”的感觉相连,从而向“传统”学习并使自身接近和成为“传统”,“追忆”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接近和成为“传统”的过程。艾略特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改变了对“传统”的态度和接近它的方式,即一种作为过程的“追忆”。在艾略特的诗歌创作《荒原》中,“追忆”行为具象化为从跨国界、跨民族的宽阔知识和历史中拾捡起文化的“碎片”,借此将典故所代表的“传统”和实际意象所指涉的“现实”一并与读者的情感对应起来,是艾略特历史意识的伟大诗学实践。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