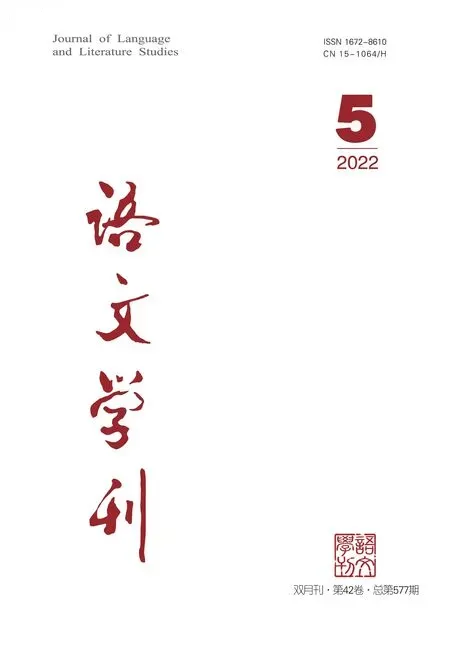基于语义指向理论的动结式分析
○ 杨朋飞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动结式是由动词和表示结果的谓词组合成的结构体,属于汉语的特色句式,形式标记为“V+C”,如“听懂”“哭湿”“喝醉”等。赵琪指出,动结式意义可以表述为:一个实体因受所处语言结构中动词所指代的动作的影响而发生了状态的改变[1]。近年来学界对动结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是探讨致事类型,如陆俭明[2]、梅立崇[3]、马真、陆俭明[4]、施春宏[5]45-57[6]21-39等。二是分析配价及论元提升,如郭锐[7][8]169-186、袁毓林[9]399-410、施春宏[5]45-57等。同时也有学者对具体动结式进行研究,如沈家煊[10]、帅志嵩[11]、崔婷[12]等。由于动结式中“C”的语义类型丰富,语义指向不同,难以全面概括其特点,因而本文基于语义指向理论对动结式进行分析。
一、“C”的语义指向
动结式是表示状态形成过程的事件类型,典型的动结式表示致使关系,实际代表一个复合事件,事件的核心是动词和补语代表的语义构成。施春宏指出,动结式所代表的一个完整的致使事件就包括这样四个语义要素:致事(致使者)和致使方式、役事(受使者)和致使结果[6]22。因此,“C”的语义可以指向三个方面,分别是“致事”“致使方式”“役事”。但是在句法层面上,“致事”和“主语”、“役事”和“宾语”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一)C指向主语
(1)我听懂了他的话 → 我听他的话+我懂了
(2)他喝醉了酒 → 他喝酒+他醉了
(3)他长高了 → 他长了+他高了
(4)花长高了 → 花长了+花高了
在以上例子中,主语即致事,从“C”的语义特征来看,“懂”“醉”“高”的语义指向为发出行为动作的主体,即施事,但是在内部语义特征方面存在细微差异,“懂”的语义特征为[+自主][-可控],“醉”的语义特征为[+自主][+可控],“高”的语义特征为[-自主][-可控]。这说明“C”在指向主语时受到语义特征的影响,当“C”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时,指向的主语必须为人,当“C”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时,指向的主语可以为物。从主语的成分来看,主语不但可以由动作行为的核心论元施事、受事充当,也可以由非核心论元充当,如工具、材料、方式、目的、角色、处所、范围等,还可以由动词性成分充当,如:
(5)黄瓜切细了 (受事)
(6)树坑挖深了 (受事)
(7)美人计害惨了我们(工具)
(8)米泔水浇死了花 (材料)
(9)踢足球踢肿了腿 (动词)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主语不属于致事,当主语为动词的受事时,动结式后面不允许再出现核心论元。“C”的语义前指受事,当主语为动词的非核心论元时,述结式后面必须出现核心论元,但是“C”的语义只能后指核心论元,不可前指非核心论元,如 “惨”后指“我们”,“死”后指“花”,“肿”后指“腿”。通过对“C”语义指向的分析,可以断定,无论何种成分作主语,“C”只能指向句式中的核心论元。
(二)C指向谓语
这类补语指向动作行为进行的过程、状态和实现结果等。
(10)我教完了这学期的钢琴课 → 终点
(11)你等久了 → 过程
(12)这首歌你唱快了 → 伴随
(13)老师抓住了他 → 状态
在以上例子中,“完”指向动词“教”,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束,对应动作线条上的终点,“久”指向动词“等”,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对应动作的整段线条,“快”指向动词“唱”,表示动作的伴随情态,对应动作线条的任一点,“住”指向动词“抓”,表示动作完成的状态,不对应动作线条表层,而是对动作线条深层的状态实现。
(三)C指向宾语
(14)写歪了字 → 我写字+字歪了
(15)说错了话 → 我说话+话错了
(16)摔碎了杯子 → 摔杯子+杯子碎
(17)裁好了衣服 → 裁衣服+衣服好
(18)擦湿了袖子 → 擦袖子+袖子湿
在以上例子中,“歪”“错”“摔”“好”“湿”分别指向“字”“话”“杯子”“衣服”“袖子”,虽然是同指宾语,但“C”和“N”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从(14)和(15)来看,“字”对应客观存在的可见实物,表现形式为“歪”,指向是客观的,而“话”是非客观存在的抽象体,没有表现形式,指向是主观的。从(17)和(18)来看,“C”对受事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好”是衣服存在的前提,而“湿”只是袖子性状的变化。从(14)和(16)来看,“字”与“歪”同时存在,即“字”的出现过程伴随着“歪”这一状态,“歪”指向动作结束时的受事,而“杯子”与“碎”异时存在,即“杯子”在“碎”发生后,就不再是“杯子”了。同时,动词“摔”“裁”“擦”的对象都是客观存在的“杯子”“衣服”“袖子”,但是,当“C”表示的状态出现时,三者的实际指向出现差异,“杯子”是消失物,“衣服”是生成物,而“袖子”不变。
(四)C指向假宾语
假宾语是指动词和宾语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语义关系,即宾语不能够作为动词的论元出现。在上述(三)中,动词和名词都是典型的“动作—受事”关系,属于真宾语,语义关系与下列例句具有明显差异。
(19)砍断了斧子 → 斧子砍+斧子断 唱哑了嗓子 → 嗓子唱+嗓子哑
(20)笑疼了肚子 → ~笑+肚子疼 累弯了腰 → ~累+腰弯
(21)累病了工人 → 工人累+工人病 看哭了观众 → 观众看+观众哭
(22)跑遍了全城 → ~跑+全城遍 开满了山峰 → ~开+山峰满
(23)跑了一身汗 → ~跑+一身汗 摸了一手油 → ~摸+一手油
以上例子的“C”都指向假宾语,但是依据内部语义关系的差异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例(19)类是工具宾语,例(20)类领属宾语,例(21)类是施事宾语,例(22)类是处所宾语,例(23)类是状态宾语。例(19)类宾语是指动作行为进行时凭借的工具,如“砍断了斧子”是指“用斧子砍→斧子断”,“唱哑了嗓子”是指“用嗓子唱→嗓子哑”。不同的是,“砍断”可以存在真宾语形式,如“砍断了树枝”,“树枝”不能作为动词“砍”的工具,只能作为受事宾语,而“唱哑了歌曲”不存在真宾语形式,即“唱哑了歌曲”不能成立。郭锐和孙天琦从论元提升和抑制的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砍断了树枝”中,“砍”的客体论元和补语“断”的主体论元两者同指,而在“唱哑了歌曲”中,“唱”的客体论元受到抑制,因而不能成立[13]461。例(20)类宾语是指动作的发出者和补语谓词的实际指向之间具有领属关系,致事者与动词是主谓关系,如“~笑”“~累”,宾语和补语谓词是主谓关系,如“肚子疼”“腰弯”。例(21)类宾语是指动作的发出者和补语谓词的指向为同一关系,如“看哭了观众”中“看”和“哭”同时指向观众。在这类宾语中,动结式的致事可以从“V”的客体论元或间接的非核心论元中提升,如“这部电影看哭了许多观众”“这批活儿累病了俩工人”,“这部电影”是动词“看”的客体论元,“这批活儿”是动词“累”的原因,属于动词的非核心论元。例(22)类宾语是指补语谓词的语义指向是动作行为进行的处所,“C”表示一种周遍义,是对动作行为空间范围的说明。例(23)类动结式是“隐性述结式”[13]460,即可以看作是隐含补语谓词的动结式,“一身汗”和“一手油”是对致事者的状态描述,语义关系式为“由于V致使N存在某种状态”,状态宾语具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必须要与数量短语共现,如“跑了汗”“摸了油”不能成立;一方面是语义具有双指性,“跑了一身汗”可以是“~跑+~一身汗”,可以是“~跑+一身汗(V)”,前者是状态,后者是受事。
二、语义指向基础上的动结配价
关于动结式的配价问题,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从理论上说,可以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自上而下,即将动结式看成一个整体,遵循动词的配价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即将动结式看成由述语动词和补语动词整合而成的结构式,进而根据两个底层动词的配价及其论元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动结式的配价[5]46。学界普遍运用自下而上的配价分析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符合动结式的实际情况。在对动结式配价问题上,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主要是通过从动结式中“V”和“C”的论元提升规则角度分析动结式的配价,代表学者如袁毓林[9]405-409、郭锐[8]169-186、施春宏[5]45-57,都提出了一套分析动结式配价的规则和公式。由于动结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一方面动词和补语不属于固定结构,无法稳定配价,另一方面动结式内部各成分之间具有随语境搭配的随意性,因而无法用一个公式涵盖所有情况。宋文辉认为从动词和补语的配价得出的计算规则必然有特设性,必然有例外[14]。因此,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动结式的配价进行分析,即只关注动词和补语实际指向的论元情况,认为动结式的最高价为二价①,黄锦章也指出,如果L2②中变元的逻辑和大于2,那么,V-R的配价为2(即小于变元的逻辑和)[15],即如果动结式的配价大于2,动结式的配价则为2。在本节中,我们不把论元提升作为讨论的重点(下文详述),而主要从“V”和“C”的语义指向来分析动结式的配价问题。王红旗曾以补语的语义指向数目来计算动结式配价,认为动结式配价=1+X(补语的语义指向数量,与动词同指时为0)[16],但此公式存在局限性,比如无法解释部分受事作主语时的配价情况,如“这部电影看哭了许多观众”。
在上文我们提到,典型的动结式表示一种致使关系,因此,从致使关系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当“VC”具有同指关系时,根据“C”的及物性分为两类,一类如a“站累”“洗累”,语义关系为“A站致使A累”“A洗致使A累”。值得一提的是,施春宏将两种情况分别讨论,认为“站累”主体同指,没有客体,是不用拷贝动词提升论元的动结式类型,“洗累”主体同指,客主异指,是用拷贝动词提升V的客体论元的动结式类型[5]54-55,而现实语言中,“站累”同样具有“洗累”的特点,如“我们站军姿站累了”,因此,我们不分别讨论。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许多学者认为是动结式例外的句式,如“我吃饱了饭”“他喝醉了酒”,依据上面的分析和学者提出的界限原则[17]143,“吃饱”“喝醉”应该为一价,但是实际上却是二价,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是特例。我们认为这不应该算作特例,如“追累”“喝醉”“吃饱”等都可以提升动词的客体论元,这可以从概念结构角度解释。以“我喝醉了酒”为例,事件结构为:[我FMOVE INTO 醉G]主事件+[我F喝酒G]副事件[10]9,主事件和副事件之间存在足够的联系,因此可以提升动词的客体论元。同时,“吃饱饭”“喝醉酒”的动结式,是一种逻辑上的蕴涵关系[17]144,两者在语义理解上具有相互性,“饱”一般关涉对象“饭”,“醉”一般关涉对象“酒”,因此两者共现时可接受程度高。另一类如b“听懂”“学会”,语义关系为“B听致使B懂了N”“B学致使B会了N”。在a类中,“C”是不及物动词,因此我们将a类看作是只有施事论元的一价动词,虽然存在二价情况,但数量少不够典型。在b类中,“C”是及物动词,因此我们将b类看作是具有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的二价动词。二是当VC不具有同指关系时,如“哭湿”“唱哑”“教会”“教完”等,语义关系为“A哭致使B湿”“A唱致使B哑”“A教致使B会”“A教致使V完”。从“C”的性质来看,“C”既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非及物动词,这一点与“VC”同指时具有差异,这是由于“VC”不同指,“V”的致使义要求必然出现宾语实现动结式语义的完整。换句话说,“站累”完整式为“A站累了A1”,“哭湿”的完整式为“A哭湿了B”,由于“A1”的同指性,即使省略也不影响语义的完整度。
在现实的语言运用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情况,当“VC”同指且“C”为不及物动词时,“VC”可以具有二价性质,如“这部电影看哭了许多观众”“这批活累病了俩工人”,这可以运用语义的具体性来进行解释。所谓的语义具体性是指在一个致使结构中,使因成分越具体,就越容易产生显著的结果,从而提升为致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6]29。下面通过列举例子进行对比说明:
(24)这部电影看哭了许多观众 → 电影看哭了许多观众 → 电影看哭了观众
(25)这批活儿累病了俩工人 → 活儿累病了俩工人 → 活儿累病了工人
通过分析以上2例,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自左向右,句子的可接受程度越来越小;二是自左向右,句子的具体性越来越低。如“这部电影”是实指,“电影”是泛指,“这批活儿”是实指,“活儿”是泛指。
同时,我们认为,“VC”的特殊搭配还和“C”的语义程度有关系,具体来说,当“C”的语义程度越深,“VC”的特殊用法可接受度越高,语义程度浅,可接受程度低,我们通过举例说明:
(26)这件衣服把我洗累了 → 这件衣服把我洗废了
(27)这个姿势把我站累了 → 这个姿势把我站废了
以上2例在现实的语言环境中都可以出现,但两者相比,一般情况下,右边句子的出现频率和可接受度高于左边的句子,这也体现了说话者的心理,即通常用非常规的句法搭配形式表达语义的夸张。
三、动结式的论元提升
关于动结式的句式生成问题,一直是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同时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郭锐、袁毓林和施春宏的研究成果,都提出了各自的论元提升规则。
袁毓林用论元优先等级概括了动结式的论元准入规则:(1)述结式允准述语动词和补语动词至少各放入一个论元参与论元提升;(2)述结式优先选择述语动词的主体格,并把它提升为述结式的主体格;(3)述结式优先选择补语动词的客体格,并把它提升为述结式的客体格;(4)如果补语动词没有客体格,那么把其主体格提升为述结式的客体格,消价、共价的情况除外;(5)如果补语动词的主体格跟述语动词的主体格共价,或者跟述语动词消价,那么述语动词的客体格可以提升为述结式的客体格[9]409。
我们认为袁毓林的规则存在不完善之处,如(1),在“我吃饱了饭③”中,补语动词并没有论元参与提升;如(4),补语动词没有客体格,说明本身是不及物的,因此语义只能指向致事和动词,指向致事时则为共价,指向动词时,则为消价,因此这个规则并不具有实际的应用性;如(5),在“观众看哭了电影”中,补语动词“哭”的主体格和述语动词“看”的主体格共价,但是述语动词的客体格并不能提升为述结式的客体格。综上可见,这些规则并不能全面解释动结式的生成问题。
郭锐针对动结式的生成提出了一套新的规则[8]169-186。施春宏在《动结式的配价层级及其歧价现象》指出了郭文的不明确之处,同时提出动结式在论元结构整合过程中对底层论元的提升是在“元”和“结”两个层面上进行的[5]53。但也存在问题,一方面是太依赖于语境,如“教会”可以是五系动结式,一方面是在确立“元”时,即配价的最小确定值,存在两可性,如施文认为“听懂”“点亮”为二元,实际上可以为一价,如“故事看懂了”“灯点亮了”。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动结式论元提升的规则,都不能很好地概括动结式的情况,所以我们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对动结式进行简要分析。
上文提到,动结式是具有致使义的事件类型,因此,语义关系式可表述为“A通过V致使B→C”,如“我砍断了树枝”,语义式为“我通过砍致使树枝断了”,“C”指向“树枝”。如“我站累了”,语义式为“我通过站致使我累了”,“累”指向“我”。因此,我们从“C”的语义指向来分析动结式的论元提升情况。
根据“C”的语义指向,我们将动结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C”前指主语,一种是“C”后指宾语。
(一)“C”前指主语
①“VC”二价同指。如:
听懂=A听B,A懂B=A听B致使A懂B=A听懂B
学会=A学B,A会B=A学B致使A会B=A学会B
当“V”和“C”具有二价属性时,两者的语义指向相同。施春宏认为,凡是论元同指的,就必须先叠合再提升到动结式上来,而不能先提升后叠合[17]93,因此两个事件在融合过程中,首先论元完全重合,进行提升,然后动词依次排列,成为一个事件结构。这符合戴浩一提出的时间顺序原则,即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
②“VC”差价同指。如:
看哭=A看B,A哭=A看B致使A哭=A看哭B
踢累=A踢B,A累=A踢B致使A累=A踢累B
“VC”差价同指是指“V”是二价动词,“C”是一价动词,两者的配价数不同,但语义指向存在重合。在上面的两例中,“A看哭B”和“A踢累B”不是合法的句子,这是由于在两个事件融合过程中,致事合并进而导致动词依次排列,形式上“哭”和“B”紧靠,但实际上两者是跨界结构,没有语义关系。但动结式的致使义要求“B”“C”形成事件结构,同时由于“VC”两个事件具有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只能将处于平行关系上的主宾语移位,形成“B看哭A”结构。
③“VC”一价同指。如:
累病=A累,A病=A累致使A病=A累病
当“V”“C”具有一价属性时,两者的论元可以完全重合,动词依次排列。
需要指出的是,在③中,依然存在②中的情况,如“这批活(N)累病我了”,但两者存在差异。在②中,“N”是作为动词的语义指向出现,与动词存在论元关系。在③中,“VC”的语义都不指向“N”,因而两者不存在论元关系。同时我们指出,“N”必须具有具体性,对应现实的语境,因此我们把“N”看作是话题成分。
(二)“C”后指宾语
④“VC”差价同指。如:
写错=A写B,B错=A写B致使B错=A写B错→A写错B
打碎=A打B,B碎=A打B致使B碎=A打B碎→A打碎B
“VC”差价同指是指“V”“C”的配价数不同,但是两者的语义指向部分相同,即“C”的主体论元与“V”的客体论元相同,在两个事件的融合过程中,两者的共同论元“B”重合,其他部分依据时间顺序形成的事件结构为“A写B错”,即“VOC”格式。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式主要出现在中古时期,在宋代,“VOC”逐渐变为了“VCO”。
⑤“VC”差价异指。如:
唱哑=A唱B,D哑=A唱B致使D哑=A唱哑D
砍断=A砍B,D断=A砍B致使D断=A砍断D
“VC”差价异指是指“V”“C”的配价数不同,两者的语义指向也不同,不存在共同论元,所以在事件的融合过程中,作为事件核心的动词首先靠拢融合,形成“A唱哑BD”“A砍断BD”。由于事件的致使义要求“C”和受事形成事件结构,所以“哑”“断”优先选择与之具有语义关系的“D”,从而形成“A唱哑D”“A砍断D”,在这类动结式中,“D”表示动作进行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在④和⑤中,存在一种同形的动结式,即动结式的形式相同,但是提升的论元存在不同,如“砍断”,既可以是“我砍断了树枝”,也可以是“我砍断了斧子”。孙天琦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砍”的客体论元并未提升,提升的是补语“断”的主体论元,只是两者同指而已。但是他并没有分析“断”的论元优先提升的原因。从事件结构出发,事件可表述为“用斧子砍树枝”,事件的参与者具有同质性,都能与补语形成新事件,动结式具有事件的可选择性,因此,两者的论元可以同时提升。
四、不及物动词的语义指向问题
蒋绍愚指出,动补结构产生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因为动补结构还可以分几类,各类产生的时代并不相同[18]。在对动补结构产生年代的问题上,学者意见差别很大,石毓智指出,这主要是由所考察的类别不同于鉴别的标准互异造成的[19]55。即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补语的语义特征,但是由于动结式表达的是一个具有致使义的事件过程,所以补语的语义指向对句法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节试图从语义指向角度对动结式的产生进行分析。
关于动结式的产生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分析,如王力指出,大约在汉代,使成式已经产生了,及物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和及物动词带不及物动词的使成式大量出现。前者如“引近定陶王”(《汉书·元后传》),后者如“射伤郗克”(《史记·齐太公世家》)[20]。再如梅祖麟认为“杀”是及物动词,“死”是不及物动词,在先秦两汉,“V杀”可带受事宾语,“V死”则不能,这种现象说明它们都是并列结构[21],“V死”到了唐代才可以接宾语。通过比较两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伤”和“死”同样是不及物动词,为何在汉代可以出现“V伤+宾语”,而到了唐代才可以“V死+宾语”?单从及物性角度来看,无法解释上述现象。同时,由于古汉语词类活用比较普遍,因此在确定词语的及物性方面存在分歧,如:
(28)楚子燮灭蓼。
(《左传·文公五年》)
(29)郑人大败戎师。
(《左传·隐公九年》)
李佐丰认为“灭”“败”是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22],而蒋绍愚认为应该将这两个词看作是及物动词[23]。事实上,“灭”和“败”的及物性问题对分析动补式产生时间具有重要影响。这说明,从及物性角度分析动结式形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石毓智指出,动补结构都是从连动或连谓结构发展而来的[19]54,同时在汉语史上,也的确存在过多动共宾的语言事实,如“尽斩杀降下之”(《史记·匈奴列传》)、“邀击破走之”(《三国志·魏书十》)。因此可断定“V伤”和“V死”两者在最初时是并列的结构。同时,两者的语义都指向后面的宾语,分析为“AV+B伤”,“AV+B死”。但是“伤”和“死”在单独使用时,具有不同的语义指向,如:
(30)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
(《礼记·礼运》)
(31)请为王入齐,天下不能伤齐。
(《战国策·东周》)
(32)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
(《国语·晋语》)
(33)今之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史记·陈涉世家》)
通过上例可以看出,在例(30)中,“之”是指“周道”,在例(32)中,“之”是指“奚齐”,“之”的语义指向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伤之”是指“伤周道”,“伤齐”是指“使齐伤”。“死之”是指“为之死”,“死国”是指“为国死”。因此当“V 伤”“V 死”还是并列结构时,“V伤”语义同时后指,不存在指向的歧义性。而“V死”语义可以异指,存在指向的歧义性,所以,虽然“伤”“死”同为不及物动词,但是在形成动结式中存在时间差异。梅祖麟认为,“V伤+宾语”出现在汉代,而“V死+宾语”一直到唐代才出现[21]。石毓智指出,在中古时期只有语义指向为宾语而且是及物性质的补语才可用于VCO格式[19]60,这也反映了语义指向对动结式的影响。梁银峰指出,从语义指向上可以将动补结构④分为三类:(1)V2的语义指向受事,来源于古代汉语的使动句式。(2)V2的语义指向施事,来源于古代汉语的自动句式。(3)V2的语义指向V1,是汉语动词虚化的自然结果[24]。这说明“C”的语义指向和动结式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根据古汉语的实际情况,当“C”的语义指向为宾语时,在中古时期出现过“VOC”格式,这既符合上文我们分析的致使事件的融合过程,也体现了语义指向对动结式的影响。
【注 释】
①存在三价的动结式,如“老师教会了我们舞蹈”,但由于特征明显,数量少,本文暂不分析。
②L2表示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件p导致事件q)。
③有的学者认为“吃饱”“喝醉”是例外,但这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加以讨论。
④作者在绪论中明确指出即动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