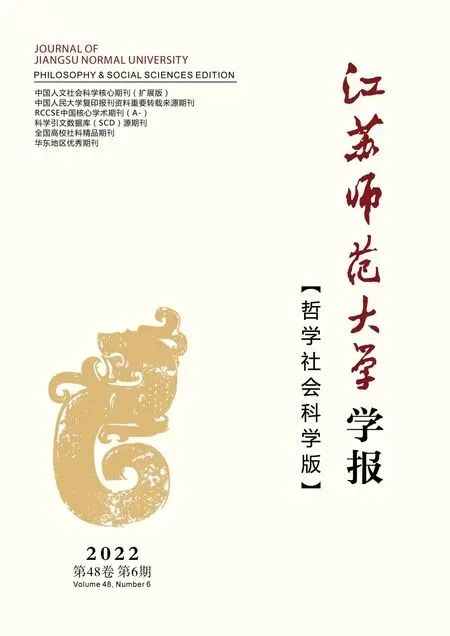沈璟《博笑记》戏曲本事及其他
张文德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明代著名戏剧家、曲学大师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词隐,江苏吴江人。以他为首的“吴江派”是明代最大的一个戏曲流派,阵容庞大、影响深远。沈璟不仅长于戏曲理论建树,而且在戏曲创作方面也成就斐然,著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其晚年所著《博笑记》久富盛名,现存明天启三年(1623)刻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徐朔方《沈璟集》校点刊行。
《博笑记》是沈璟最后一部传奇作品,凡28出,约完成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关于其戏曲本事,“吴江派”重要人物吕天成的《曲品·博笑记》曾云,“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多令人绝倒。先生游戏之笔,至此神化极矣”(1)吴书荫:《曲品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8页。。因此,学者皆从《耳谈》中考索其故事来源,致使戏曲本事蔽而不彰。客观而言,《博笑记》传奇虽然取材于王同轨《耳谈》的故事不少,但仍不到全剧10目12则故事的一半,其他则另有所本,并非出自《耳谈》。
郭英德、金宁芬等先生对《博笑记》戏曲本事,均有考订和探究,颇多创获。尤以金宁芬先生的《明代戏曲史》为著:
(博笑记)10个故事大多据明人王同轨《耳谈》所载改编。如其中《某孝廉》《句容氏》《刘尚贤》《优诈》为《巫举人痴心得妾》《恶少年误鬻妻室》《穿窬人隐德辨冤》《诸荡子计赚金钱》所本,《僧诈》《巫诈》《大别狐妖》《杞县疑狱》等篇中的部分情节为《起复官遘难身全》《卖脸客擒妖得妇》《英雄将出猎行权》所取。张弼《张东海集》卷四《睡丞记》所记之嘉兴丞则显然是《乜县丞竟日昏眠》中乜县丞的原型。(2)金宁芬:《明代戏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其中,《句容氏》现存各本皆作“句容民”,或为笔误,当正;张弼《张东海集》卷四,应为张弼《东海集》卷三;所谓《僧诈》《巫诈》《大别狐妖》《杞县疑狱》等,谓为戏曲《起复官》《卖脸客》《英雄将》所取,征之事实颇不合,当另有所本,不予采信。如此可知,金宁芬先生集前贤诸说,参以己见,将《博笑记》戏曲本事,已考订5则故事出处,即:《耳谈》中的《某孝廉》《句容民》《刘尚贤》《优诈》4个和《东海集》中的《睡丞记》1个。即便是这5个故事的出处,尚有可议之处,而其他又皆“存疑待考”,实失考。现就学者已考和未考的戏曲本事及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第1目《巫举人痴心得妾》(巫举人2-4出)剧叙扬州举人巫嗣真赴北京会试,“三场得意,春闱拾芥可期”(3)(明)沈璟著,徐朔方辑校:《沈璟集·博笑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页。以下曲文皆出此书,不再出注。,在京等候发榜,相约同年好友南京庄举人、扬州贾举人,出外郊游。巫举人见一淡妆美妇祭墓归,惊为天仙。便离群赁驴追赶,至其家,其夫谎称美妇新寡,正辞墓待嫁,巫举人愿以百五十金聘娶。合卺之夜,妇告以扎囤实情,相偕逃躲友人处。其夫带“众光棍”前来“打诈”,遍寻不着,便“撞死四牌耧上”。学者已知本事出王同轨的《耳谈》卷1《某孝廉》,但未予论述:
乙未有某孝廉群饮于郊,见一妇哭墓归,素笄艳妆,绝美;妇乘蹇。因弃众驱蹇从之,及门,妇入,莫为计。忽自内一人出,孝廉与语。其人曰:“此妇新寡,辞其夫墓归,将适人耳,吾为某执伐来也。”孝廉曰:“幸甚!为我媒,当厚报公。”其人曰:“然。”因以为期。至邸舍,仅出廉值,盟已成。其夜妇至,下舆。谛视之,果逢者,大喜。花烛觞散,且就寝。妇曰:“君第先寝。”孝廉即先寝。逾时,妇不寝。孝廉起问曰:“汝何不寝?”妇语如前。孝廉又先寝。妇见孝廉韶秀,又饶橐装,屡寝皆如己言,知无他肠。……孝廉即如其言迁去。未明,夫果拥众至,见是空室,以询邸主人。邸主人曰:“相公夜装归矣。”即群崩去追之,不知所往。(4)(明)王同轨:《耳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戏曲《博笑记》“巫举人”本此而作。“巫嗣真”名系撰出;结尾“其夫撞死”,巫嗣真与同乡贾、庄二举人皆中进士,亦为增饰。此种“轧火囤”诈财骗局,历代多有,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补卷第八”收录《吴约知县》《临安武职》《郑主簿》《王朝议》等,皆属此类。《耳谈》则是“妇身是赚具,反为妇卖,机中之机,亦何矫捷”,事鲜见而新奇。沈词隐《博笑记》藉此敷衍,以阐发“掘坑者自陷”“骗人者终自害”的道理。凌濛初拟话本小说《拍案惊奇》卷16《张溜儿熟布迷魂阵,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头回”和“正话”,皆本于《耳谈·某孝廉》敷衍,不关涉戏曲情节;原“某孝廉”小说改为“浙江嘉兴沈灿若”(5)(明)凌濛初:《拍案惊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页。。学者多言之,不赘。
第2目《乜县佐竟日昏眠》(乜县丞,5-6出)剧叙崇明县乜县丞自夸“耳又聪来眼又明”,却将“张鈇”读成“长铁”;把“将敬”认作“蒋敬”,喜怒无常,昏愦嗜睡。有乡宦贺其新任,前来拜访;县丞手下回报,“大人”正瞌睡打盹,不见客,改日回拜。次日,乜县丞专程到乡宦府上造访,结果是两人相互打盹对睡,竟日未得晤谈。天晚,县丞回衙时,订约下次再访。剧中曲唱点明主旨:“古和今不曾闻,他这一对。对面沉沉睡,睡着不得醒,醒了还如醉。醉人呵怎如他昏到底。”
此事学者已知出自张东海《睡丞记》,但多据晚明浮白主人《雅谑》转引,未查考原文。现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原文如下:
嘉兴丞某善睡,尝访一乡贤,坐俟其出,辄睡。主人出,恐觉之,相对默坐,亦睡。丞觉,不欲妨主人睡,坐待亦睡。主人既觉,丞犹睡,不欲觉之,又睡以待。丞觉,晚矣;主睡方酣,遂不及相叙而去。噫,岂特睡丞哉!吾闻诸工部主事过大朴云。大朴,嘉兴人。(6)(明)张弼著:《东海文集》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64页。
作者张弼(1425-1487),字汝弼,号东海,明成化二年二甲进士,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官南安知府,治绩卓异,时人目为“神仙太守”,见明徐复祚《花当阁委谈》卷5《神仙太守》、褚人获《坚瓠集》卷3《神仙太守》等;著有《鹤城稿》《东海集》等。而《五杂俎》卷7言“华亭县丞”(7)(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古今谭概·癖嗜部》卷9亦是“华亭丞谒乡绅”,皆言出自“张东海作《睡丞记》”(8)(明)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8页。。事实则是原文作“嘉兴丞”,讲述人也是“嘉兴人过大朴”,系嘲笑家乡县丞昏庸嗜睡之事。因华亭张弼载入文集,后人遂讹为“华亭丞”,沈词隐则戏改为苏州府“崇明县(今上海市崇明区)丞”。
第5目《恶少年误鬻妻室》(卖嫂,12-14出)剧叙有兄弟三人,长兄出外经商,5年不归;老二、老三设计,让人谎报兄丧,并以50两银价,将大嫂卖于远方客商。约好晚上抢人,以白髻为记认。老三因得钱太少,不满二哥所为,便将此事预先告知大嫂。大嫂往见老二媳妇,表示愿嫁富商,但嫁衣仓促难办,己之守孝白髻,喜事不宜,遂与其互换髻饰。傍晚,客商前来娶亲,一见“白髻”妇人便抢,误劫走老二媳妇,开船远去。而大哥返乡,一家团聚;老二妻离子啼,无以自存。此剧,学者已知出于《耳谈》卷7《句容民》,而疏于故事流变的相关论述: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贩木,五载不归。仲以嫂美,令人诈称兄死,嫂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无嫁意,乃私受河上贾人金鬻之。乃绐贾人曰:“嫂性好嫁,而多矫饰,若好语则费日,汝可率徒众猝至,见素笄妇拥而登舆,但云:明日讲话。登舟为汝妇矣。”计定,其夜率徒众至,仲季皆避去。而不知季嗔兄分己金少也,潜以语嫂,独仲妇不知。嫂亦不嗔,但泣告仲妇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饰妆。今是吉礼,而素笄往可乎?幸以汝缁冠相易片时,其安矣。”仲妇授缁冠,自着素笄毕,嫂即匿去。仲妇出答,客众见素笄,拥而登舆去如飞,而乘风舟发矣。夜深仲归,始诧失妇;不省而追之不及,惟乱数日不得。乃次朝,伯氏肩其重橐归,夫妇宴婉聚,庐里皆来劳远人。仲亦归,闻其二稚啼索母,伶仃,盖仲妇所弃儿也。肠为寸裂。里人有知者,无不掩袖卢胡。(9)(明)王同轨:《耳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174页。
此故事颇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博笑记》据之敷衍,甚少增饰。在弄巧成拙、欲卖嫂反丧自家妻的笑声中,映现出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实图景。同胞兄弟竟蔑兄卖嫂,利欲熏心,公然宣称“兄弟如手足,钱财是性命”;嗜财如命,置伦理亲情于不顾,终堕入妻离子散的窘境:“所欲害人者,还著于本人”。此事传播甚广,明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卷5《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传奇《赚青衫》有取于此。又见清人徐岳的《见闻录》卷2《卖妹妻》;清代李百川《绿野仙踪》第23回、清佚名《换嫁衣》、石成金《雨花香·自害自》等通俗小说皆本此而作;清代《卖嫂丧妻宝卷》亦据此敷衍(10)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第6目《诸荡子计赚金钱》(假妇人,15-17出)剧叙苏州城内有老孛相、小火囤、能尽情,获悉阊门外无名观道人有钱财,便去寻一个极标致的串戏小旦,假扮妇人迷路,至道观投宿以骗财。临睡时,老孛相与小火囤二人冲进观中捉奸,敲诈道士120两银子;能尽情又勒索道士告状,亦诈得一笔钱财。长洲县令捕获这伙奸徒,予以严惩。学者已知事本《耳谈》卷14《优诈》,但二者颇有异同,应予论述:
姑苏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妇人至,曰:“与良人反目,怒归母家。忽迷失道,身无所依,愿得假宿。”僧始拒却,已而心动,曰:“汝但随我影行。”至一庵,盖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闼入,缚僧曰:“贼秃,安得诱良家妇!”至此,僧不能辩,但乞求。旁一人曰:“可尽汝有得释。”僧曰:“有面近百秉,皆出于乞化,愿以谢过。”面既尽,始罢。后始知妇是狡童,夫与群不逞皆优。尝入寺,垂涎其面而佐此。王元祯寓吴所见。(11)(明)王同轨:《耳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
《博笑记》主体架构虽承自《耳谈》,而细节颇多不同,结局更大异其趣。剧改“山塘寺僧人”为“无名观道士”,改“面粉”为“钱财”。结尾增出“道士索告”及长洲县令破案事,使奸恶棍徒终罹法网,受到惩处。如此增改,意在杜绝奸宄,淳化民风。此事亦见王兆云(元祯)《白醉琐言》卷上“假妇胁僧”,文字略异,刊行则晚于《耳谈》。而其源实出于唐代王仁裕《玉堂闲话》,《太平广记》卷238引署《大安寺》(1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42页。;又见于《智囊全集》卷27《大安寺奸民》(13)(明)冯梦龙:《智囊全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92页。。叙唐懿宗时常微服私游寺观,民间奸猾不逞之徒,访知大安寺有江淮进奏官所寄吴绫千匹在院,便假扮皇上游寺,骗得吴绫千匹。寺僧久而方知是奸人之谋。《耳谈》事多同此,吴优盖师其故智。
第8目《穿窬人隐德辨冤》(贼救人,22-23出)此目用两事串合一剧,学者误执一事而立论,故言人人殊,歧见纷出。有言“本事出《耳谈》卷3《墙间妇》条”,有说剧作本于《耳谈·刘尚贤》。 事实上,此一剧中含括两则小故事,而以“偷儿”绾合。
其一,叙一赌徒,因赌倾家,妻谏不听。一日,赌徒赢得40两银子,妻欲用此赎回衣衫首饰,丈夫则主张用此翻赌本,二人斗口,夫殴妻。妻含忿归房。适有偷儿觇知赌徒赢钱,穿窬入室,见“鬼持绳圈上”、赌徒妻自缢,便大呼救人。家人惊起,妇人获救。赌徒与偷儿相互劝勉,戒赌戒偷,改过迁善。此事,郭英德先生认为事出《耳谈·墙间妇》(14)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似有扞格:
一妇嗔其夫博,反唇,而夫殴之,夫出,自缢。忽一妇青袄红裙,自墙出为解练,得不死。先是有偷儿入,伏梁上。亡何,夫至,见偷儿。偷儿不为动,问何以不动?曰:“我本偷儿,今见墙间妇出,解练如此,恐吓足软故耳,非不畏死也。”问妇,妇曰:“果然!”是人竟缚偷儿送御史台。(15)(明)王同轨:《耳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此中,女鬼是救人者,而《博笑记》中“鬼”是诱妇自缢的害人者;小说中“偷儿”见女鬼出墙间,恐惧口噤足软;而戏曲“偷儿”则是见义勇为、大声呼叫救人,缢妇获救得活。两者仅事件起因相同,皆是妻嗔夫赌博,夫殴妻,妻忿自缢;其他迥异。《墙间妇》是“义鬼救人获贼”,而非“贼救人”,与戏曲显有不合。击鬼救人事,早见于刘义庆的《幽明录》: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从京还,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广屋中。雨止月朗,遥见一女子,来至屋檐下。便有悲叹之音,乃解腰中卷绳,悬屋角自绞;又觉屋檐上如有人牵绳绞。此人密以刀斫卷绳,又斫屋上,见一鬼西走。向曙,女气方苏,能语,家在前,持此人将归,向女父母说其事。(16)鲁迅:《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84页。
此中救人者是过路客人,而非小偷。明代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6《义盗》,叙京师富人钱洪六疑妻与人私,酷虐之,妻不胜忿,遂自缢。盗入室行窃,适遇之,大声疾呼:“堂中有人缢死!”呼至再三,洪六方惊起,解其悬而活之(17)周光培:《明代笔记小说》第11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贼救妇人”尚见于清代小说《警寤钟》第6回《发婆心驱鬼却妻》侠盗云里手击缢鬼救妇人。张潮《虞初新志》卷13《记缢鬼》“偷儿救张氏妇”事亦同此。
其二,剧叙赛范张与胜管鲍为结义兄弟,雇用前“偷儿”为挑夫。一日,发现了窖藏金银,二人皆欲独吞。“一人将毒酒饮对方”,一人趁药发之际,持刀砍死对方。挑夫报案,官府查明:只为那些“没影的银钞”,朋友相杀“刺的先死了,药毒后来发”。此事本于《耳谈·刘尚贤》,且有更早之源:
孝感县民刘尚贤、张民时二人,比党为友,实以利合。醉则拍肩矢日,愿同生死。常谓我等无钱把撮,不见交谊,异日倘富贵勿相忘。偶夜行,见火燐燐,识其地,掘之,果是银根,矗起如笋。二人大喜,谓宜具牲醴祭祷,而后掘取。尚贤已置毒盏中,令明时服之。明时亦置斧腰际,乘醉击尚贤死;而不知毒发身亦死。盖二人豕腹,俱欲独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复往掘银根,几遍亩地,濯濯无迹。二人盖空死,而其为义何义焉!此万历乙未年六月事。里人游其地,所亲见焉。(18)(明)王同轨:《耳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王同轨说:此为乙未年(万历二十三年)之实事,亦系传闻,未必属实。《博笑记》据之敷衍,而增出“偷儿”目击,删去“二家妻子”访掘银根事。意在讽喻:清酒红人面,黄金黑世心。所谓的世俗结义,无非是利来利往,各怀私心,虚伪可笑;为独吞虚幻的金银财宝,竟至毒手相加、以命相搏。此事早见于三国吴康僧会所译佛经《旧杂譬喻经》卷上《展转相煞喻》:有三人“见道边有聚金”,相约共取。一人买饭“取毒着饭中”:二人死,己可独得金;“二人复生意”见其回共杀之,食毒饭而二人亦俱死(19)(三国)康僧会等著,孙昌武、李赓扬译注:《杂譬喻经四种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页。。佛经故事虽然简约,但主要情节相同,当是《耳谈》故事前源。戏曲所本,更近于《耳谈·刘尚贤》而非佛经故事。“刘尚贤”事亦见于《古今谭概·死友》(20)(明)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页。,略简。此剧用正反两事以阐明:盗贼虽为人不齿,但能见义勇为、有救人之心;交情密厚的结义兄弟,却见利忘义、互相残杀。藉此一“偷儿”串合两故事,以讽喻现实,惩创人心。若仅以“穿窬人隐德辨冤”戏目而言,既“却鬼”又“辨冤”的,唯徐复祚《花当阁·义盗》可以当之。
二
第3目《邪心妇开门遇虎》(虎叩门,7-8出)剧叙南京近郊龙潭村有婆媳两人,皆寡居。婆婆去女儿家,次日回。当天晚上,儿媳已睡下,金陵人常循理返城不及,到此借宿。妇人说自己寡妇一人,男子不便留宿,让常循理院内草堆边权宿一夜。夜间虎来叩门,妇人认是客人“立心不端”而敲门,拒绝开门。虎又再三叩门甚急。妇人情动意转,以为 “那人”对己真实有意,便“动心”急去开门。虎入,衔咬妇人而去。学者对其本事皆失考,实见于明代吴大震的《广艳异编》卷28《金陵人》:
金陵有人晚行出龙潭村,借宿于孀妇家,妇拒之曰:“我家无他男女,独吾一人守舍,不可相容。”哀请之,乃许宿于庭中草堆。且感且惧,夜不交睫。中夜,有虎至,以爪扣内门。妇以其人有淫心也,叱曰:“怜汝孤客,好心相留,何立心不善如此!”虎乃止;俄而又扣数声,妇又曰:“毋放肆,明日我姑归,决不但已!”虎又止;俄复扣数声,妇颇情动,笑言曰:“郎毕竟有情吾耶?”虎始连扣不已。妇曰:“多情郎,何性急如此!”速起开门,其虎突入,衔妇而去。其人不敢喘息。明发,奔告邻里,共踪血迹,觅至古墓前,而妇唯余半体矣。(21)(明)吴大震:《广艳异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9页。
剧情全出稗史小说,二者甚少相异。均为金陵人到京郊“龙潭村”出行,天晚借宿村庄寡妇家,目睹“虎咬妇人”事。惟添出金陵人名字“常循理”,其他则据实展演。剧作讽喻“守节”妇人,言行不一,自诩“立志高,愿守坚贞操”,“媳妇是不带网巾的男子汉,谁敢近门来觑一觑儿”。一旦真正面对“诱惑”,竟忘却“虎患”而“动心”开门,未能始终坚守贞节初心,终遭虎吞而丧命。
第4目《起复官遘难身全》(假活佛,9-11出)剧叙南方某官员丁忧起复,带着两个仆人,“将近京都”,天晚借宿“空空寺”。寺僧见其生得肥胖“宛似一躯弥勒尊佛”,便杀了官员的两个随从,用麻药酒将官员灌倒、剃光头发,每日不予水喝,只以“肉汁解他的渴”, 使其“如痴似哑,再难明悟”。养得“面貌如玉,手脚如绵”,“只说天上降下来的活佛,多哄人些钱财”。空空寺有活佛下降,轰动四方,烧香拜佛者不远千里而至。本州太守闻知,命人将“活佛”抬进府衙瞻仰。一日,太守见“活佛”手指能动、欲喝水、会写字,便拘来僧人审问,方知是寺僧将其下药,哑而不饥,诈称活佛下降,以欺世牟利。太守严惩寺僧。
此剧,学者皆从《耳谈》中索考本事,牵合附会,难以信从。明代公案小说“假佛上天”之事,颇为常见。明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卷下《威逼类·雷守道辨僧烧人》“四川成都升仙寺” ,每年二月“送佛上天”,分巡道雷继焕见其垂泪,下令停止火化,命人抬入府衙中供养,三五日后渐能言语,始知是会试举人游寺,被僧加害,捕僧严拷,供明其罪(22)刘世德等:《古本小说丛刊》第28辑《廉明公案》,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14页。。万历三十三年(1605)序刻本《郭青螺新民公案》卷4《净寺救秀才》:绍兴秀才徐俊携妻詹氏入寺求子,僧见徐妻美,设计谋夺。中秋时将徐俊头发削去,置于干柴上,“饮一盏迷魂麻药汤”,谎称送佛上天;郭子章见疑,审明捕僧,救出徐俊夫妇(23)刘世德等:《古本小说丛刊》第3辑《新民公案》,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83页。。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僧之自焚者,多由徒众诳人舍施,愿欲既厌,然后诱一愚劣沙弥,饮以瘖药,缚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当烟焰涨合之际,万众喧阗,虽挣扎称冤不闻也”:
宋某人为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许之。至期亲往验视,见僧两眼凝泪不动,问之不答,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纸笔。乃自言某处游僧,至此寺,众欺其愚弱,诳言惑众,厚得钱帛,至期药而缚之耳。遂按诸僧,毁其寺。(24)(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清代许奉恩《里乘》卷7《活佛》与《博笑记》“假活佛”故事最为相似,当与戏曲同源。江南某生游佛寺,发现寺藏妇人之秘,众僧欲杀人灭口,密议“将来活佛上天,我辈可藉此渔利,较为得计”:
遂将生发剃净,幽诸密室。饮以喑药,日给淡食,不入粒盐。百日,肌肤肥白如匏,且腰脚柔软,不能行立。乃于郊外架木为高台,谓某日活佛肉身,趺坐台上,涅槃示寂,藉火化以生天。举国男妇闻之,扶老携幼,不远而来。皆香花顶礼,瞻拜祈祷,一唱百和,舞蹈若狂。
邑令某公,见“活佛”面白皙如满月、泪下如雨,觉事可疑,下令停止火化,命人将活佛抬至内衙,“在邑署暂住一夜,藉使署中细弱,得遂瞻拜”。邑令审问,生不能言,以写字述其经过。邑令大怒,乃拘捕主僧及助虐者,一火焚之。(25)(清)许奉恩:《里乘》,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28-230页。
第7目《安处善临危祸免》(义虎事,18-21出)此目实含两则故事,学者不明其本事出处,实皆可考。其一,叙池州建德县农夫安处善,贷谷奉母,归途遇虎,惊惧倒地,虎只舔其身,并不咬吃。安处善向虎哀告:家有老母倚门悬盼,煮粥奉亲之后即来送死,决不失信。虎听后摇尾而去。次日,安处善如期践约赴死,虎见其是志诚守信的仁孝君子,不仅不吃他,反赠其银以奉母。此剧本事,见于明宋凤翔《秋泾笔乘》:
万历十七年,建德山中一农夫贷谷回,卒与虎遇。农告虎曰:“某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谷度命,容送谷到家,供母晨昏,来此就死,不敢失信。”虎遂曳尾而去。农至家为母言之。母止之曰:“幸脱虎口,奈何送死!”农曰:“人为虎食,命也。今纵不往,终亦难逃。况昨已许之,安可失信!”母泣送之。农至其地,虎已先衔一人,而不食,见农至,惟以爪爪死人而去。农不测何意,及解衣,包中得银数十两。因取归以奉母,而葬此人。(26)周光培:《明代笔记小说》第6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页。
戏曲全据此而作,细节亦同。“孝子告虎”事,早见于宋洪迈《夷坚乙志》卷12《章惠仲告虎》:成都章惠仲,日黑行路,马仆坠崖下,虎来衔章发。章谓虎曰:“汝灵物,当听吾语。吾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婿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独吾一身存,将窃升斗禄养母。汝食我,奈老母何?”虎闻,遽舍之(27)(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2页。。
明万历间王稚登的《虎苑·孝感第二》、陈继儒的《虎荟》卷4皆据《夷坚志》收录《章惠仲告虎》。而“建德农夫遇虎”不仅见于《博笑记》,还见于清初话本小说《警世选言》 第2回《慈航渡朱生救功畜》入话,学者多不明所自(28)刘世德等:《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实出于宋翔凤的《秋泾笔乘》,话本小说将其改为虎放走奉母的孝子、咬死杀生的猎人,则与戏曲略有不同。
其二,剧叙铜陵县某人家贫,携妻乘船往建德县投靠亲友。船家见贫人妻美,顿生恶意,哄骗贫人与己上岸寻找住处,留下其妻守船。山间僻处,船家打死贫人,回船谎称其夫被虎咬死,威逼贫妇嫁给他。贫妇言:须见夫骨方嫁。船家只好与贫妇回去寻找,山中遇虎冲出,将恶船家咬死衔走。妇人始信其夫或真遇虎死,大哭于途。一老汉问询,并言:适过县衙,见一铜陵男子,告船家将其打死后复生。妇至,果然是其丈夫。虎咬恶船家谋妇事,学者多失考,实本于明代沈周的《石田杂记》:
(成化)十九年,宜兴一人因无产有役,与其妻逃历阳,遇行船因问往去向,长年遂答曰:“我正往历阳地方。”其人搭去。长年悦其妻,至历阳,诱其人曰:“我于此地最多识熟,你妻可留船中,我与你去觅舍者。”长年同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船绐其妻曰:“汝夫已落虎口矣。”妻哭,长年曰:“无苦,我自与汝成配!”其妻疑曰:“虎其能尽食吾夫,若得见遗肉一脔,亦愿足,然后与尔为配。”长年不得已,领其妻往寻。不意一虎,竟搏长年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真死矣!”路人闻之,诘其所由,妻以实告。路人云:“适从县前,见有一人被船夫打死,复活来告。岂汝夫耶?”其妇诣寻之,果其夫复活云。(29)(明)沈周:《石田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3页。
明人祝允明《前闻记·义虎传》和都穆《都公谈纂》卷下《义虎》大致相同,而王稚登的《虎苑·殛暴第六》和陈继儒的《虎荟》卷6亦载录,文字略异。此剧用两个“义虎”故事串合而成,地名“宜兴”剧改“铜陵”,改“历阳”为“建德”亦是据前则“建德农夫遇虎”之事而来;“船家”身上的“二十六两银子”,也是据前则“包中得银数十两,因取归以奉母”而生发,原船夫故事本无此事。戏曲从正反两个方面形象地说明:志诚孝义之人,虎不侵;奸诈凶恶之人,遭虎吞。虎能明辨善恶、洞察正邪。剧中明言“虎有仁义,人不如兽”,故称“义虎”。
第9目《卖脸客擒妖得妇》(卖脸客,24-25出)剧叙财主古吾言有女被妖怪缠其身,无奈。张榜招贤,能驱除妖祟者,以女嫁之。一日傍晚,大雨骤降,有卖面具青年,遇雨求宿。老汉为女儿事心烦,不允所请。卖面具青年只好权栖门外,借火烘烤沾湿的面具,膝盖、双手、头脸全戴上面具。妖怪见此人多脸,惊惧不敢上前。青年审妖,妖实诉:自己是黑鱼精,在庄前水塘居住。青年命其不得再来缠扰,妖遂感谢而去,小姐病愈。古老汉请青年下池塘斩杀黑鱼精,将女儿嫁之。
庄一拂等先生皆谓此剧与《初刻拍案惊奇》卷12《蒋震卿片言得妇》事略似(30)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47页。。乃辗转沿袭,未中肯綮。“片言得妇”是“误约私奔”主题,此戏是“妖魅惑女”故事,迥不相侔。此剧“卖脸客”实本于王兆云的笔记小说《湖海搜奇》卷下,其目录有《柳鸾英》《面具治黑鱼精》等,但今存明万历刻本已残佚,有目无文。现据《坚瓠集·面具治怪》移录:
《湖海搜奇》:金陵有人担面具出售,即俗所谓鬼脸子者。行至中途,遇雨沾湿,借宿大姓庄居。庄丁不纳,权卧门檐下。中夜不寐,面具经雨将坏,乃拾薪爇火而熯,首戴一枚,两手及两膝各冒其一以近燎。三更许,见一黑汉,且前且却。某大声叱之,黑汉前跪曰:“我黑鱼精也。家在此里许水塘中,与主人女有情,每夕来往。不意有犯尊神,恕责。”其人叱之速去。明旦告主人以所见。某小女果病祟不安,遂竭塘渔之,得乌鲤重百余斤,乃腌而担之归。(31)(清)褚人获:《坚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9页。
此事又见于明人冯梦龙《古今谭概·妖异部》“鬼畏面具”和《古今笑》等。戏曲全本小说。剧中卖脸客治生乏术,靠卖面具糊口,唱道:“这脸子呵是一家一计,若还毁却,将何充口食。”烘烤面具“头戴一个,两手各撑两个,两膝各戴一个,蹲地烘介”。此比小说5个面具还多出两个,所以“黑衣黑面怪”见后大惊:“何方显神,身生七面嘴。我时衰矣”。青年见其畏惧退缩,大声一唬,黑衣怪连忙跪倒,自诉是“黑鱼精魅”“谢得尊神放我归”,再不敢将女迷。剧中招贤医女帖子与卖脸客“得女为配”事,不见本事,则为沈词隐《博笑记》所增饰。面具可以降妖除怪,固然可笑,而旨在讽谕:术士之符咒驱邪亦如面具吓鬼,多出于偶然的机缘巧合,未必真有法术神通。
第10目《英雄将出猎行权》(26-28出)剧叙有二强盗深夜入室抢劫,掠掳一少女,而杀死其父母。天将明,携女子行路不便,二盗将少女暂置于路旁枯井中,用大石掩井口,拟于晚上同来携归。少年将军祁遇出猎居延,行至此处,闻井中有呼救声。将军救出少女,询知事情原委。打猎归来,便将生擒的两只豺狼置于前枯井中,仍用旧石封好井口;将少女带回府中。晚间,二盗如期前来取井中少女,刚移开井石,二豺狼冲出,咬死两个强盗;少女与将军缔结良姻,以大团圆终场。学者对其本事皆失考。实见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2《语资》:
宁王尝猎于户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动婉含嚬,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乘。时慕荦者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户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哔膊有声。店户人怪其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云:“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32)(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115页。
此事又见于《太平广记》卷238《宁王》《僧尼孽海·户县僧》和《广艳异编·宁王》《贤奕编·柜熊治盗》等,皆承自《酉阳杂俎》,文字略简。而刘元卿《贤奕编》卷3《柜熊治盗》,有明万历二十一年序刻本,或为《博笑记》直接所本。其中“柜子”,剧改为“枯井”;“一熊”改为“二豺狼”;宁王李宪将莫氏送入宫,唐玄宗封其为“莫才人”;剧改为将军“祁遇”自娶为“小夫人”。其他大体相同。此外,王元寿《玉扼臂》传奇,祁彪佳评曰:“取汪昌朝所传《韦将军闻歌纳妓》剧,而杂以虎易美姝事”(33)(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明祁骏佳亦有杂剧《鸳鸯锦》(南北4折),祁彪佳评曰:“新歌初转,艳色欲飞。以虎易美姝,沈词隐曾采之《博笑》内,较不若此剧之豪畅。”(34)(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8页。显然,《玉扼臂》传奇、《鸳鸯锦》杂剧均是据“杂俎”而改编的剧作,只是将原故事中的“熊”改为“虎”,即“虎易美姝”;有别于《博笑记》的“豺狼易美姝”之事。学者多不知其本事出处,却云:“虎易美姝事,见《太平广记》引《原化记·天宝选人》”(35)齐森华等:《中国曲学大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实误。故特为拈出。
三
明代吕天成《曲品》评《博笑记》有云:词隐先生“杂取《耳谈》中事谱之,多令人绝倒”。学者囿于成说,无不从《耳谈》中钩辑考索《博笑记》戏曲本事。诚然,王同轨的《耳谈》的确是沈词隐创作《博笑记》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但却不是唯一的来源。也就是说,《博笑记》本事不全出于《耳谈》,作者沈璟本人在第一出“开宗明义”中,已道出:“昭代名家野史,于今百种犹饶。正言庄语敢相嘲,却爱诙谐不少。”声称他是在泛览了明代流行的百余种 “名家野史”之后,才采撷若干“诙谐”嘲谑的故事,谱出《博笑记》的。由上文亦可知,《博笑记》取材广泛,尤以明人刊行的“野史”故事为多。《耳谈》只是其中之一,而非全部。
《博笑记》虽然历来多被视为“传奇”,但却与明代昆曲传奇既有的体制规范颇为不同。其最大差异是: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全剧以“博笑”为主旨,串联诸多短剧。第一出“开场”中作者已明确列出10个剧目名称,剧由10目短剧缀合而成,自无可疑。至于10目短剧,含括故事的数量, 说法各异。一般认为:10目即 10个故事;也有说11个故事的(36)刘召明:《沈璟〈博笑记〉的艺术成就及其戏剧史意义》,《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经过辨析,我们认为,10目短剧实含有12个故事。《博笑记》之第7目“义虎事”,第8目“贼救人”,均各有正反两例,两目共4事,而非一事一目剧;其他8目则一事一剧;共计10目12则故事。故事的多少,关乎戏曲本事的考证和戏剧体制特征的认知,亦非细事,不可不辨。
《博笑记》由10目短剧缀合而成的结构特点,打破了传奇的既有规范,显得颇为与众不同,既有传奇的体制形态,也有短杂剧集合的特征,模糊了传奇与杂剧的界限分野。所以,多数学者仍将其归入传奇类,也有不少学者视其为杂剧集。如徐子方先生即认为:“《博笑记》为一本包含十个作品的短剧集”,“事实上乃一南杂剧集”,并且“准确地讲应称之为昆曲杂剧”(37)徐子方:《明杂剧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00页。。
学者们对于《博笑记》的传奇与杂剧之争,见仁见智,各有其立论的依据,难以划一。《博笑记》短剧缀合的性质,无疑具有了某些杂剧合集的特征。单独析出一目,视作短杂剧予以论述,亦未尝不可。但若从《博笑记》整体观照,命名为“南杂剧集”或“昆曲杂剧”,则有违沈璟创作本意,也不符合古今人们长期的既有认知事实。如果一定要为这种“特创新体”正名的话,可称之为“剧体传奇”,是杂剧与传奇的融合体,而以长篇传奇为其本质属性。
吕天成的《曲品》只品评新旧传奇,不涉杂剧;却对《博笑记》有详细评述,视之为“似剧体”新传奇。祁彪佳对杂剧、传奇分别评述:传奇入“曲品”,杂剧入“剧品”。而《博笑记》恰被列入《远山堂曲品》之“逸品”。显然,祁氏视《博笑记》为传奇而非杂剧。他写给沈泰的信中还说:“如许时泉之《太和》、沈词隐之《博笑》、叶桐柏之《四艳》、车柅斋之《四梦》,彼已汇成全记,似不宜仍作散剧。”(38)(明)祁彪佳:《远山堂尺牍·乙巳年》,南京图书馆藏,明末抄本。可知《博笑记》是“全记”体传奇而非“散剧” 体杂剧。明代茗柯生(凌义渠)《刻博笑记题词》亦云:“今世填词度曲者,业无不奉先生所制为律令。若此记则又特创新体,多采异闻,每一事为几出,合数事为一记。既不若杂剧之拘于四折,又不若传奇之强为穿插。能使观者靡不仰面绝缨,掀髯抚掌,而似讥似讽,可叹可悲之意,又未始不悉寓其间。”(39)(明)沈璟著,徐朔方辑校:《沈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92-793页。
揆沈氏“特创新体”之意,旨在融合杂剧传奇之优长,更好地为其表达主题服务,仅取一事不足以见出孝道或笑料的多面性和深广度。上下古今,人生百态,一斑不足窥豹,便广搜博取以证之,以阐释“孝”与“笑”的广泛性和普适性。这正如鲁迅先生论《儒林外史》所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4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应该说,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在结构体制方面,深得沈氏传奇“创体”之精髓。既然《儒林外史》是公认的长篇通俗小说,而非短篇小说集;《博笑记》亦应作如是观,是长篇传奇而非短杂剧集。
从《博笑记》文本内证来看,其戏剧排场显然是按照昆曲传奇的惯例,结构篇章,安排场次的。如第一出“副末开场”阐明创作动机与剧情,终场是生旦大团圆结局;连续出数长达28出,分上下卷,中间第14出后有“小收煞”——“戏文暂歇。下卷又有假妇人事登场”;而且目与目之间,有钩连、有过脉相衔接,如“巫孝廉事演过,乜县丞登场”等。如此,皆是传奇的固有规范和排场布局,杂剧从无此例。也就是说,《博笑记》的整体结构形态特征,显示其为长篇传奇体制,而不是杂剧集。
《博笑记》第16出,苏州小旦报出串戏演过的戏文名:《杀狗记》《白兔记》《荆钗记》《拜月亭记》《琵琶记》《牧羊记》《金印记》《双忠记》《八义记》《精忠记》《卧冰记》等,一色全是戏文传奇。下接:
[众]都是妙的。却怎么没有新戏文呢?[小旦]新戏文好的虽多,都容易串。我只在戏房里看一出,就上一出。数不得许多。[众]《博笑记》倒有兴。[小旦]还不曾见。[丑]你也迟货宝器了。
可见,沈璟把自己的剧作《博笑记》与元明传奇戏文并列而论,视为一体,明白无误地说是“新戏文”昆曲传奇,而不认为是杂剧。但《博笑记》确实又有短剧缀合“似剧体”的一面。据其“两栖”的特点,比较可行的办法,可酌用吕天成的说法,称之为“剧体传奇”,即《博笑记》以传奇体为其本质属性,而兼有一些杂剧的特征。这也是历来众多的文学史、戏曲史、文化史均将《博笑记》列入“传奇”类的原因之所在。
总之,沈璟《博笑记》用缀合10目12个故事的“特创新体”——剧体传奇,演绎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生百态,为市井细民写心。热肠骂世,冷板敲人;藉诙谐笑谑之笔,发抒胸中之牢骚愤郁,直写曲摹,庄语戏喻,皆臻奇妙。同时,沈璟身为“词林之哲匠,后学之师模”的一代宗师,其可贵的平民化立场,以及对通俗本色、可演可传之剧场性的追求与坚守,对于扭转当时文人剧的案头化倾向,使之向民间性、娱乐性本体复归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