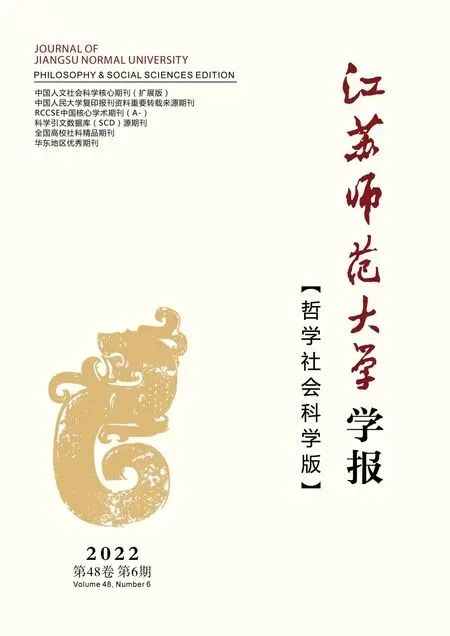关于《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几个问题
臧公秀
(苏州大学 金螳螂建筑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学界一般认为,先秦城市规划有两种类型:一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述“礼制型”城市,一是《管子·乘马》等篇所述的“有机型”城市。所谓“礼制型”城市以西周城市建设制度为基础,是原生型城市的规划体现,“有机型”城市则是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次生型城市的规划体现。学者对二者规划思想的具体内容研究,因为《周礼》是儒家核心经典,对后世制度建设影响深远,其“营国制度”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基本规范和指导思想,是后世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至于《管子》城市规划与建设思想,因为该书出自多人之手,相关内容分散于各篇之中,学者除了谓《乘马》篇的城市规划思想为有机型城市之外,对分散于其他篇章的规划与建设思想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既不符合《管子》一书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应有地位,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事实也存在着距离:既要对《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系统性予以重新认识,更要重新认识其历史基础问题。笔者以为,所谓有机型城市并非次生型城市的理论总结,而是原生型历史实践的理论概括,而《管子》城乡一体化、人地相称的规划思想则历史地揭示了古代国家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一、《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基础
鉴于学界对《周礼》礼制型城市规划的普遍理解,在讨论《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基础时,首先要对《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作简要叙述,以资比较。《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云: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下同),第927页。
这段文字虽然简略,但内容丰富,概括而言,可分为三项:一是王城面积和城内空间结构,即“方九里,旁三门”。周制六尺为步(周制一尺约合现在23.1厘米)(2)周代度制,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38页。,三百步为里(415.8米),“方九里”即边长九里(3742.2米)的正方形,每面城墙开三个城门,共有城门12座。城内空间分割是“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就是纵横各九条道路,每条路的宽度是“九轨”(“轨”是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二是城内建筑布局以宫寝为中心,“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即宫寝位于城的中心,西侧是祭祀社稷之神的社,东侧是祭祀祖先的宗庙,北面是物资交易场所——“市”,南面是群臣处理政务的办公区——“朝”(3)关于“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的空间布局和具体建筑尺寸,以及祖、社与宫寝的空间关系,古今学者有过各种讨论。从实践层面考察,均存在着不同问题。本文出于分析《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实践基础需要而综述“匠人营国”内容,不拟就学者之间的分歧做出详细辨析。关于“匠人营国”空间结构分析,以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为代表,见该书第二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三是“市、朝”的面积规定。“夫”指井田制下的百亩之地,一步宽、一百步长为一亩,一百个长条亩合并在一起为百亩,是一个农夫即一户的授田面积,“夫”指户主,代指一百亩土地。“市、朝一夫”即“市”和“朝”的用地面积各为“一夫”之田即一百亩。按西周制度,“方里为井”即一井九百亩,有九“夫”耕种,王城的空间规划以“夫”为基本单位,方九里之城,就是八十一井的空间面积。西周是宗法等级社会,城邑面积因身份而异,面积和名称有别,天子之城曰“国”,诸侯之城曰“都”,卿大夫之城曰“邑”,都、邑面积和城内建筑规模较“国”均依次递减,城的形制和城内空间结构则相同。对上述内容的具体理解,学者之间存在某些分歧,但对其历史真实性的总体认识则基本一致,认为是西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论总结,尽管可能有后世学者理论总结和设想的成分,但其基本内容是真实的,是西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制度规定,其中也包括了商朝城市建设的某些制度。
但是,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地理环境是城市兴建的前提,无论是人类社会文明初期聚邑的自然形成,还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有目的有计划的城市建设,地理环境都是先决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中国古代城市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按照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一般理论范式,城市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第一次是农业和牧业的分离,第二次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第三次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城市就是在这次分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产物,特别是工商业活动。但是,这只是逻辑的抽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具体路径有着个性特征,决定于具体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的演进形态,中国城市形成和发展当然有着自身特征。现代史学研究表明,中国文明有着自身特点,不存在从低到高三次大分工的依次演进问题。中国早期城邑称为聚、邑,就是聚集而居的居民点,逐步发展为人们理解的“城市”。史学家曾将西周时代的国家形态和希腊进行过比较,结论是西周和希腊国家形态在外部形式上都是城市国家,都属于城邦,但与希腊以社会分工、工商业发展、地缘关系为基础不同。西周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划分居民身份,手工业、商业由官府直接控制,生产目的是官府消费,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身份、职业世袭,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其国家形态是宗族城邦,其社会形态是宗族奴隶制社会(4)西周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由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最早提出,后逐渐被史学界所接受和补充论证。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9-194页。。西周时代,不同阶级、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聚居在同一个城市中,并不存在后人所理解的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也不存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区别。从经济形态看,西周是农业社会,西周的城邦是有围墙的农村,城内居民主体是农民,城市经济主体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国民经济影响轻微,不存在现代学者认为的“商品经济”问题,是地地道道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因而无论是城市选址,还是城内建设,必须考虑到地理条件问题,固然要满足城市安全条件,更要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地理环境、土地质量、水源问题必须首先要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其次才是满足手工业生产需求。但上述“匠人营国”对地理环境问题却没有涉及,仅仅把规划内容聚焦于城市等级、宫寝衙署、道路交通等空间布局。这显然不符合先秦社会发展和国家形态的历史实际。学者有鉴于此,只能将其概括为“礼制型”城市。笔者以为,概括为“礼制型”城市是正确的,但是这是就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空间表达,而不能作为原生型城市。
笔者以为,管子的城市规划理论是真正的原生型城市理论概括,因为《管子》理论符合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是齐国历史实践的总结。《管子·乘马》云: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5)梁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1《乘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04年版(下同),第83页。
《乘马》认为地理环境是建城的前提,城址要选择依山傍水的地带,近山者要避免受旱,近水者要避免受涝,要充分利用水资源,凭借地势,兴修水利,抗旱排洪。无论是城垣走向、高低、宽窄,还是城内交通网络、沟渠布局,以及城内衙署、市场、作坊、民宅等建筑,都不必要按照“规矩”“准绳”。这“规矩”“准绳”就是建城立邑的各项规定,建城立邑不是削足适履地一定要依据什么规矩、准绳,而是应根据地形地貌如山川河流、土质肥瘠、人口多寡,因地制宜,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这说明,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着建城立邑的系统规定,而《管子》主张突破这些规定,一切以城市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准。《管子·度地》托名管仲和齐桓公对话,论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的具体内容,云:
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事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6)《管子校注》卷18《度地》,第1050-1051页。
其中“不倾之地”的内涵,一是安全,二是旱涝保收的肥美之地。其具体要求,一是以山为依托,二是以水为保障。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谈得上城市规划和建设。其基本内容为:一是城郭系统,由内城外郭和城、郭之间的土地和郭外之“土阆”以及护城河构成多重防护体系。“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是就护城河而言,地势低者筑堤抬高水位,地势高者开渠引水,以保障足够的水流。二是城内有系统水利设施,和城外水道形成网络,以保障日常生活、农业灌溉和手工业生产用水,既抗旱又排涝。 考古资料说明,《管子》的这段论述不是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对现实城市建筑的理论总结和指导,齐国都城临淄的城址选择,城垣走向、水利系统、交通系统、生产区域、生活区域分割等等,与《管子》所述几乎相同。这些众所周知,笔者曾有过叙述分析,本文不再赘述(7)臧公秀:《〈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实践性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6期;《城市规划视角下〈考工记〉的国别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6期。。
明白《管子》和《匠人营国》的规划差异,现在可以分析二者的关系问题。出于《匠人营国》是西周制度,《管子》是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者的论文汇编,只能反映战国情况的既定认识,学者们一致认为《管子》的城市规划思想是西周礼崩乐坏之后的产物,也就是所谓有机型城市和礼制型城市是接续关系。西周礼乐有序,城市规划和建设也尊卑有等,天子之城、诸侯之城、卿大夫之城及其内部空间结构,均依礼而建。春秋以降,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统一王朝演变为列国纷争,社会等级混乱,各国建城立邑不守礼制,僭越成为普遍现象,《管子》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就是这一大变动时代的体现,不再以突出天子权威、维护天子权威为旨归,而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春秋战国确实是旧的社会结构解体、新的社会结构确立时期,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当然有着新的时代特征。但是,如果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又不难发现,这一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从西周是同一王朝、礼制是普天之下共同遵守的刚性规定的既定认识出发得出的结论,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当代城市史和城市规划史研究中,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特点,不约而同地认为三代以来就是统一王朝,体现在城市建设上自然有着统一的制度和规划,西周礼乐秩序下的城市规划当然是全天下的城建总纲。不过,这只是人们受后世大一统观念影响下的主观判断,将西周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后世中央集权统一王朝混为一谈的结果。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中华文化发展道路是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在其早期阶段,“多元”特色突出,不同区域文化有着不同的空间特性,体现在城市发展上而有着区域特色。所谓“一体”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统一”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处于不断丰富过程之中。西周时代虽然有着大一统观念,但和后世的统一王朝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史学研究表明,西周并非传统认识的统一王朝,而是宗族城邦联合体,周天子和诸侯国的关系并非后世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周王号称天子,施行分封制,分封的对象有宗室、功臣、归附的商朝贵族、先贤之后,同时也承认那些自古已经存在的部落领袖的诸侯地位,而分为不同等级。这众多的诸侯,有的是周初新建的,有的则是和周邦同样悠久的国家,甚至比周人的建国史还要长。无论是分封的诸侯国,还是夏商之后,或者原始邦国,他们建城立邑都不可能按照什么礼制等级。因为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结构不同,文化传统也不同,不可能按照什么统一的礼制建城立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王室也难以要求普天之下遵守统一的制度,所谓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并不具有制度上的强制意义。在分封制下,无论是什么等级的诸侯均具有治国的全权,周王不过问诸侯国内政,所谓的共主不过是盟主而已。原来早已存在的先贤古国固然保留其独立传统,就连新封诸侯在建国之初也自行其是,齐国就是一个典型。《史记·齐太公世家》谓“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8)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第1480页。营丘与莱夷为邻,姜尚受封时不了解封地情况,以为自己封邑安全无虞,一路优哉游哉地逶迤东行,“道宿行迟”,有“逆旅之人”提醒说“时难得而易失”之后,才昼夜兼程于黎明时分到达营丘,正逢“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经过一番征战,才击退莱夷,控制营丘。当时的齐国封地只有营丘一个点,也就是后来的临淄,经过长期征战,才发展为东方大国。值得注意的是姜尚的立国指导方针:一是“因其俗,简其礼”,即不按照周人礼俗,而是顺应原居民的风俗;二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因为营丘附近特别是东部地区多丘陵,地邻海,农业受限而物产多样,故因地制宜地发展手工业、土特产贸易和渔盐业,使齐国迅速致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9)《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0页。。这体现在城市建设上,当然不存在遵守什么礼制要求问题,即使有规定,对于齐国而言,也行不通。所以,我们有理由说,《管子》城市规划思想正是齐从立国以来历史实践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而不是春秋以后生产力发展、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
二、“人地相称”的规划主张
上文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固然与社会分工密不可分,更主要的是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就城邑性质而言,则是有围墙的农村。城市首先是作为军事堡垒,而后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有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传说古代圣王舜治理天下有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0)《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34页。。这“一年”“二年”“三年”是形容用语,表明舜统治天下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赢得人心,天下之人自觉归附,使其人口迅速增多,由聚而邑,由邑而“都”,聚是最初的居民点,人数有限,邑是较大的居民点,“都”的人口又多于邑,空间规模相应扩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的记载,“都”是诸侯国都城,都、邑和周天子之“国”即王城构成当时城的三级体系。司马迁笔下的“三年成都”的“都”仅仅是比喻舜治下人口增加迅速,并无《左传》所说的等级含义。这聚、邑、都以人口多少为依据,而不是以空间大小为前提,聚、邑、都均包括所有居民在内,而以农业人口也就是后来人常说的农民为主体。这聚、邑、都不是舜有意规划建设的结果,而是人口增加、自然生成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漫画。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早期城邑选址无一例外地或者依山,或者傍水,大都在二级台地上,说明《管子》的“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的选址原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军事上为了安全,经济上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早期的城邑中根本不存在现在人们理解的工商业问题,也不存在现代学者认为的城乡之别。
在古代社会,地广人稀,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人口多少是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所以人口聚集的速度与规模决定着城市生成与发展以及国力盛衰,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招徕人口,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才成为后世榜样。战国时代,城市发展迅速,富国强兵是各国共同追求,城市规划和建设自然以人为核心,齐国则走在了历史的前列。《管子·小匡》托名管子和齐桓公讨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子提出“三其国而伍其鄙”的主张,云:
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1)《管子校注》卷8《小匡》,第400页。
这一段话也见于《国语·齐语》,二者文字有微小差异,基本内容相同。《国语》被史学界看作《左传》的补充,是春秋主要国家君臣之间讨论军国事务的言论集,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小匡》的这段文字应是转录《国语》。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其规划的意义尤其值得重视。上述文字表明,在空间上,国土分为“国”“鄙”两部分。国即国君直接控制的都城,鄙是都城周边地区,相当于郊区,是“郭”的附属空间。无论是国还是鄙,规划均以人为核心,根据人数多寡,规划国土资源,所有居民,都以“五家为轨”作为基本户籍编制,国内居民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共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手工业者和商贾编制为六个乡,士和农夫编为十五个乡。这二十一个乡分别由国君和高氏、国氏率领,其中“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叫做三其国。国中经济资源由农田、池沼、山林组成,根据需要,三个乡设立一个市以满足物资交流(先秦时“三”多为虚指,“市立三乡”之“三”不一定是三个乡),分别设立专职官员负责手工业、渔猎、养殖业生产,即“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鄙的人口少于国,有十五个乡,分为五属。按照职业,士农工商分区居住,“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士”是下层贵族,是国家主人,参与国家祭祀、谋划政务、当兵打仗,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从事具体生产活动,故“处士必于闲燕”。“农”是农业生产者,是居民主体,故要“处农必就田野”。这里的“田野”是城外、近郊和城内土地的统称,“农”要居住在方便农耕的区域,靠近耕地,这个“就田野”即集中居住在城墙附近,既可以统一耕种城内农田,也方便出城耕作。“工商”是官手工作坊和店铺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当时工商食官,手工业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官府需求,调剂不同行业之间的物资余缺,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四民”地位不同,身份、职业世袭,分区居住,分别管理,既保持身份地位的差别,也使他们能心无旁骛地司其职、专其业,保证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这些下文还要述及,此处从略。
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建城立邑是难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使之能够正常地生产,才是根本前提。而《小匡》只有士农工商的户数,没有提到农民的土地来源问题,仅仅把农民编制在一起,农民如何生存?迄今为止,没有学者注意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原因在于当时土地国有,农夫土地由国家分配,手工业所需生产资料来源以及商贾所通之土特产,也由国家分配,或者由国家掌控的山川林泽之出产来满足,所谓虞、衡就是专门管理山川林泽特产的官员总称。农夫土地按户平均分配,每户百亩良田(所谓井田制下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是指良田),山川林泽也根据工商人数决定。所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就是为了满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需求。地势有高低,土质有肥瘠,山林池沼物产也各不相同,必须把不同质量的土地折合成百亩良田再分配给农民。《乘马》云: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纆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汎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12)《管子校注》卷1《乘马》,第89页。
这“百而当一”“十而当一”“九而当一”之“一”是指一个土地分配单位,指一百亩。土地质量差,产出少,就增加分配数量,以土地授予数量调节质量差异,处良田者按标准授予,处劣地者则增加受田数量,根据土地情况,九倍、十倍以至百倍地授予,从而使农民收益平均,这就是“地均”之法。《乘马》云:
“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13)《管子校注》卷1《乘马》,第104页。
土地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人地关系因土地质量有别,不同质量土地所满足的人口数量不同。同样是“万室”即万户之民,因土地质量不同分别需要方八十里、百里、百二十里之土。在不同自然条件下,人户相同,实际土地面积不同,所以不能机械地规定城邑面积,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根据地理条件、土地质量、物产构成,在人均百亩良田的前提下,因地而异,保证人地相称,从而使地尽其用,人尽其力,既能保证城邑安全,又能保证国家的统治需求。《八观》云:
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14)《管子校注》卷5《八观》,第259页。
人多地少或者质量贫瘠,百姓生存没有保障;人少地多,城邑再大也难以守住。城内各种建筑用地和规模要保有适当比例,如“宫营”即环绕宫廷建筑的庭院,“室”是各种房屋总称,“囷仓”即粮仓,“台榭”即贵族用来享用的亭台楼阁。概括而言即宫廷建筑、官府衙署、娱乐园囿等等,用地要有统一规划,在满足统治集团需求的同时避免浪费。庭院营地多,房屋用地少,则住房不足;住房过多,则房屋空置而形成浪费;若仓储少而亭台楼阁多,则难以满足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建城立邑,必须考虑土地资源和人口数量关系,农业用地如此,建筑用地也是如此。
《管子》的人地相称、人地合一的规划思想,并非思想家的主观想象,而是有着普遍的社会基础。以往人们认为战国是土地私有制时代,地主拥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只占有很少的土地,所以士人们才把五口之家、百亩之地作为王者之政的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出土资料和现代史学研究已经证明,战国是土地国有制时代,施行普遍授田制,耕地和住宅均由国家分配,国家在分配耕地和住宅的同时,对生产内容也作出明确规定,房前屋后要种植经济作物、饲养家禽家畜,作为家庭生活的经济补充。商鞅之法,“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15)《商君书·境内》,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益”指增加,意思是按军功授予爵位和田宅,每斩一个有爵位的敌人就增加一级爵位、一百亩土地、九亩住宅。这“益宅九亩”是以普通农民授予九亩住宅用地为前提的。孟子仁政主张的核心内容就是五口之家、百亩之地,外加五亩之宅,指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16)《孟子·梁惠王》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66页。。这“树之以桑”云云,并非书生呓语,而是有现实制度基础的。农民住宅如此,官僚贵族住宅也是如此。为发挥住宅用地的经济效益,故而作出上述规划,以保证“养”的需要。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地相称、城乡一体式资源规划。
三、城市建设与社会控制
《管子》的城市规划思想并非如现代理解的为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是为了有效实现社会控制,将社会各阶层的生产生活控制在国家需要的秩序范围内,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力量总动员。体现在城市建设上,就是把居民分隔在固定的空间之内,不仅有城有郭以分别内外,居民也被墙垣分隔在各自的乡、州、里的空间之内,居民“日常”均处于官府的严密监视之下。《八观》云: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17)《管子校注》卷5《八观》,第256页。
无论是外郭内城,还是城内里居及每家每户的墙垣都要符合要求。城、郭要完整,除了规定的城门之外不得有其他孔道和外界相连,里与里、户与户之间,以墙垣隔开。吏民统一从里门出入,彼此之间不得相通,里门按时开闭,由专人负责。《立政》云:
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18)《管子校注》卷1《立政》,第65页。
“闾”是里门,“闾有司”是里监门即里的看门人,居民按照规定时间从规定大门出入,“闾有司”逐一观察里民的出入举止以及居家日常,若不按时出入、衣服着装违背身份、言谈不符合规定,一经发现,立即向上级汇报。那些有不法行为的人若是“长家子弟臣妾役属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则再宥,三则不赦”,以示对长家子弟臣妾役属宾客的优待。“凡孝梯忠信、贤良俊才,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役属、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19)《管子校注》卷1《立政》,第65页。,逐级上报,不得越级,以示里尉、游宗、什伍之长及长家的教化功劳。每三个月要将监视情况上报里尉,里尉六个月则上报给乡,一年进行一次总结,赏善不独及个人,罚恶也不止于一身,州长、里尉、游宗、什长、伍长都有份,本质上这是相互监督的连坐制度。出土秦汉法律史料说明了这一思想的真实性。云梦睡虎地秦律《法律答问》云:
越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垣为“完(院)”不为?巷相直为“院”;宇相直者不为“完(院)”。(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232页。
“垣”即墙垣。律文明确,里与里之间的墙称为垣,家与家之间的隔墙则称为院。作为里与里之间界限的垣若处于两巷相对的位置就是院,否则就不算作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襍律》关于里中墙垣的叙述比较详细,云:
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 。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捕罪人及以县官事征召人,所征召、捕越邑里、官市院垣,追捕征者得随迹出入。(21)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33页。
《二年律令》是汉初法律,内容较多地沿袭秦律。律文规定了私自翻越邑里和官市墙垣、偷开里门等违法行为的具体量刑标准:“皆赎黥”。损坏的墙垣没有达到五尺高度,属于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只有在抓捕罪犯和为公家征调人员时,为了抓捕的需要,才可以沿着罪犯或者逃亡者的踪迹越墙追捕。这“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说明“邑里、官市院垣”有高度标准,道路宽窄当然也有其要求。里门钥匙由里典、田典统一保管。《二年律令·户律》规定:
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22)《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1页。
里门钥匙有田典、里典轮流掌管,每天按时开门和关门。在“伏日”则全天关闭里门,禁止里民出入耕作,也禁止行人通行。如果在“伏日”有诏令为老人献酒、官府人员公务需要,以及使节出行,或者发生火灾、追捕盗贼,则开门放行。否则,违背规定,罚金二两。城门和里门,有专人昼夜值守,称之为“里监门”。“里监门”是最低级的公职人员,没有俸禄,按天领取口粮,所以在历史上被看做卑贱的职业。里门如此,县邑城门也是如此。《二年律令·户律》规定:
募民欲守县邑门者,令以时开闭门、及止畜产放出者,令民共(供)食之,月二户
□□□□令不更以下更宿门。(23)《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1页。
县邑门多事杂,看门人手不够,要募人看守。职责是按照法令,在规定时间内开门关门,防止城内禽畜逃出。应募守门人的伙食由县邑内居民轮流供应,一家十五天。凡是不更以下的所有居民都要轮流在县邑大门值夜班。明白《管子》的城市规划思想,不难发现,这些并非秦汉首创,起码在《管子》书中可以发现其源头。
之所以把军民固定于各自空间之内,处于官吏的严格监督之下,就是为了将民户置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保证社会秩序最优化,满足国家统治需要。《管子》对此有充分的论述。《小匡》对四民分立的必要性有充分论述:
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24)《管子校注》卷8《小匡》,第401-402页。
四民分居是出于职业化考虑,便于官府组织生产和劳动群体的经验交流及技术传承,避免见异思迁,保证职业世袭。“令夫农,群萃而州处”,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的各个环节,依时而行,邻里之间,相互提醒,统一行动;儿童少年,耳濡目染,收到少习天成的效果,“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令夫工,群萃而州处”,是为了“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也就是可以更好地选择原料,计算用料多少,提高产品质量。“令夫商,群萃而州处”,是为了“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即判断年成好坏,把握国家需求变化和一年四季货源、需求和价格,准确计算运输费用,贵买贱卖,调有余,补不足,使四方特产,周流天下。父传子,子传孙,“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
所谓组织生产、保证技术传承,只是一个方面,并非主要目的。控制人户、相互连坐,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兵役和徭役来源。民户登记在册,固定在乡里之中,男女老幼,哪些人达到生产要求,哪些人达到从军标准,一一登记在官,平时耕作之余,给官府、贵族提供劳役,战时从军。这就是兵农合一的控制体制,当时名称为“作内政而寓军令”,其具体制度,《小匡》云:
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25)《管子校注》卷8《小匡》,第413页。
“五人为伍”以“五家为轨”为基础,家家户户,每户有一人当兵。战国时代,步兵为主,五人是一个基本的作战单位,军事和行政合一,户籍编制是为了军事编制的需要,故而“五人为伍”是当时普遍的制度。从理论上看,兵农合一体制下,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军事训练,邻里之间,彼此熟悉,休戚与共,战场上自然同生共死,从而实现“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的目的。这反映了人地合一、城乡一体规划的本质: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战国是以战争为轴心的时代,也是我国古代城市大发展时期,形成了系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制度,《周礼》的《匠人营国》和《管子》是其代表,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充分的论述,而分别命名为“礼制型”城市和“有机型”城市。但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共同点均以“国家控制社会”为前提和归宿。《匠人营国》以君权为本位,突出君权无上性,将王权作为大一统的最高代表,体现的是分封制下的王权与诸侯权力的尊卑等级,王权通过诸侯控制社会。《管子》所体现的是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尽管还保留着分封制的残余,贵族依然分割君权,但主体内容则是国家直接控制社会,国家权力渗透到每家每户;体现在城市规划领域,无论是城址选择,还是城邑的空间生产,国家权力是直接的主导力量。这是中国古代与近代城市规划的根本区别,也是古代中国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城市规划的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