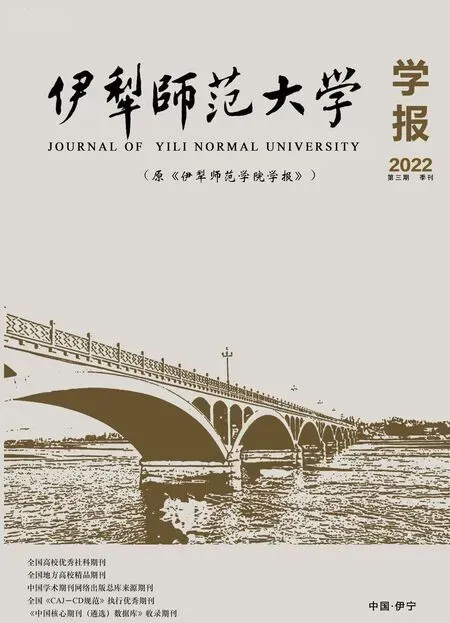新疆散文的经验书写与叙述主体的形象建构
郭鹏舒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新时期以来,新疆当代文学进入了新的时代环境,获得了新的文化语境,“在与中心主流文学不断地交流与渐进式融合中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因其特有的边地书写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同样影响着新疆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情感表达。就新疆散文来说,可以发现周涛、刘亮程、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王族、沈苇、李娟、南子等作家的创作与当代文坛不断涌现的文化散文、西部散文、非虚构写作等散文流变的对话与融合。除了理解新疆散文和当代散文的互动关系,还需辨析同处新疆的不同作家在情感倾向、创作风格及叙述方式上的不同。与小说相比,散文与作者的联系更加紧密,不过“越来越多的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意识到:散文一方面要描写个人的亲身经历,表现个体对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散文应允许想象和虚构,应敢于打破‘个人经历’和‘个体经验’的限制。”[2]换言之,散文不仅强调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悟,还应允许作者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进行虚构想象和情境叙述。对应当前的散文创作,可以看到不同文本中叙述情形的差异。在第一人称的自叙类散文里,作者似乎“现身说法”,在作品中表露心迹、表现个人经历。然而,在以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为主要感知视角的散文中,作者与叙述者①、叙述主体的间离感便比较明显,作者往往借助文字、通过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展现情感和完成表达行为,“作者只能在文本的外部进行叙事,而能在文本内部叙事的则是叙述者。”[3]在这里作者是现实层面的创作者,叙述者和叙述主体则属于文本层面,叙述主体便是体现作者主体意识的叙述者。从叙述主体的文本层面对新疆作家的散文创作进行考察,根据具体作品来研究作者与叙述者、叙述主体的彼此关系,由而理解作家在地域经验、创作内容和叙述方式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散文中主体意识和形象建构的多维呈现。
一、“在路上”的漫游者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中,学者多将新疆当代文学纳入“西部文学”的研究范畴进行分析,可是随着新疆当代文学体量的不断扩大,“西部文学”的研究内容与新疆当代文学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厘清与界定。肖云儒曾提出,“西部文学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群落性现象,它由作品和理论两部分构成实体,但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体现。”[4]在肖云儒的研究中,西部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更多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周涛、杨牧、章德益等的“新边塞诗”,王蒙、陆天明、赵光鸣、董立勃等描绘新疆社会生活的边疆风情小说,均表现出西部文学的共性特征和美学风貌。韩子勇在《西部:边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中将陆天明、周涛、赵光鸣、董立勃等作家放在西部作家群体中来把握,分析作品中蕴含的中国西部文学的抒情传统、“天边外·在路上”的叙述模式等,对周涛散文的古典深韵和社会关怀、陆天明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历史书写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丁帆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提及“西部”更多的“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呈内涵上的交叉”[5]。该著作将新疆作家纳入现代以来西部文学的演进历程,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分析新疆各民族作家的文学实践。在重新修订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中则增加了对新世纪以来新疆作家的创作论述,其中包括王族、沈苇、李娟、南子等汉语创作者,以及艾克拜尔·米吉提、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等少数民族双语作家,特别提到“新疆新散文群落”的现象及这一群落中作家个性有别的创作特点[6]。
当代学者是从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美学特征、精神内涵等多个角度对西部文学进行阐释与概括的,就西部文学所体现的精神内涵来说,有苦难意识、生态意识、历史意识、生命意识、主体意识等,其中“游牧”“漂泊”“行走”“迁徙”则涉及身份认知和主体意识的问题。新疆作家身处祖国西部边陲,作品的文化意蕴和精神特质与其他西部作家有相通之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包括了“游牧”“行走”的主体意识和“在路上”的叙述模式。“也许是新疆过于辽阔和多样,而相比之下的文学表达过于稀薄,以文学方式的穿越、行走、探险、揭秘,成了一种选择。很多情况下,‘在路上’或‘文学的游牧’既是一种写作动机,也成为作品的结构方式。”[7]在这些作家笔下,“在路上”的散文叙述不只是一种行文方式,还体现作家的精神诉求和创作需求。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游走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怀念着牧民生活中留存的游牧精魂(《永生羊》)。遥远的达坂城、火洲吐鲁番、艰难前行的博格达,行旅途中,王族一边拍摄一边记录新疆的独特景观(《从天山到阿尔泰》)。南子跟随农民走在北疆的田野上,体验着人与大地相交织的命运,巴里坤日复一日的生活、卡尔塔村一望无际的哈密瓜田,一切都和谐共生(《蜂蜜猎人》)。在古今对谈、时空交错、位置转换中,在游历壮美山河、探寻人文古迹的过程中,作家们获得了行走在路上的精神愉悦和生命体验,从而对自我、对新疆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也变得越发敏锐。正是这种内在渴求推动着他们找寻灵魂的安顿之所,“行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历、散步,也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一种“漫游”。
细读作家周涛以往的多数作品,可以发现其散文中的叙述主体是思想者、探险家、漫游者的融合。在《巩乃斯的马》《沙场秋点兵》《伊犁秋天的札记》《大雪飘,饺子包》等作品中,作者以“我”作为叙述主体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我”是这些过往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散文文本的叙述者,具有“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双重体悟。“我”描述在新疆生活的诸多感受,既回溯与牧民交往的美好记忆,又叙述了日常的温暖细节和军营的火热训练,所具有的立场和观念体现了作者本人的主体意识,也表达出散文作品的内在意蕴。这种以“我”的见闻和思索为中心的散文创作,还强化了作者自叙式散文情感和内容的真实性。《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红嘴鸦及其结局》《猛禽》《凝视片刻》《行者》等作品,既有仰躺在草坡上感受草原幻觉、获得精神解脱的“他”;也有不安于庸常生活、渴望摆脱世俗束缚的“行者”,固执而艰辛地寻找生命和精神的家园;还有假借动物的视野来表达作者对自由精神和高贵品质的向往,在这些以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为主要感知视角的散文中,作者并不执着于叙述人物和情景的细节,而是借助叙述者来完成抒发感悟的表达行为,进行有限度的艺术想象和虚构,表现这些人与事中凝结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周涛的散文不但在西部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漫游,而且作者也把这种借助散文创作精神的漫游,作为自己融入西部,与西部的历史文化自然人文融为一体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8]在驰骋古今的谈论中,作家周涛融入了自我对生命、文化的理解,作家以审视的眼光看待周遭世界的一切,贯穿其中的是对自由精神、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向往。
与周涛散文中凝神思索的漫游者有所不同,作家刘亮程散文《一个人的村庄》的叙述主体是毫无目的、无所事事、终日游荡的“闲人”,全书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但“我”并不等同于作者。“我”在黄沙梁经历的事情、所看到的景象,是作者对自身经验进行想象和虚构后所呈现出来的文本内容,“黄沙梁”是作者用文字构建的“一个人的村庄”,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精神原乡。叙述主体“我”是脱离世俗生活和伦理束缚的“闲人”,喜欢扛着铁锨在荒野上转悠,没有生存压力和物质欲望的折磨,不需要为了生计在土地上刨食,也不会为了改建家园、添置农具衣物而忙碌,只会改变野草和树的长势、改变牛羊未来的命运。在黄沙梁田地里,只有“我”不忙农活而在思考时间、感悟生命,在与狗、驴、马、鸟、蚂蚁共同生活的环境中,在与那些忙忙碌碌却一无所获的农民一起生活的村庄里,“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感觉时光在身上慢了下来。这里所谓的“闲”不是闲来无事,而是精神上的一种清逸与悠闲。“我”是村庄唯一的旁观者,随意游走于黄沙梁任何一寸土地上,观察村庄里的常与变,“守着这一村人种完一辈子的地”,看着“最后的收成——一村庄人一生的盈利和亏损”[9]26。
相比于周涛、刘亮程散文中叙述主体的漫游、行走、游荡,李娟笔下的叙述主体少了精神的闲适,多了生活的紧迫,她不是为了欣赏自然风景而走进牧场,多数情况下是迫于生计而进行的“迁徙”。散文集《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主要记述了李娟在阿克哈拉、沙依横布拉克等地的亲历见闻和真切感受,在这些自述式的散文中,“作者”“叙述者”“叙述主体”三者合一,作者饱含情感却又不失理性地看待自身与牧民所经受的一切,记录着他们悠久的游牧生活样态。“我”虽不是牧民,却像游牧者一样不断迁徙,跟随着母亲经营的“半流动”杂货铺和裁缝店进入阿勒泰深山牧场。为了生计,一家人“吃在山野”“穿在山野”“行在山野”“住在山野”,用肢体语言和简单的日常用语与哈萨克族牧民进行交流,牧民们“也就模模糊糊地理解,反正最后生意总会做成的”[10]。本来简单的事情可能会因为语言不通而变复杂,却因为大家都简单地表达、简单地活着,便少了许多麻烦。在消息闭塞、生存艰难的茫茫山野,阿勒泰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象与深山孤寂单调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欢乐、赞叹、心酸、寂寞各种情绪融汇笔端,这种“半流动”的生活让“我”深深体会到普通人生存和转场的艰辛,以及这片贫瘠、辽阔的大地上一切生命的坚韧与豁达。
在新疆散文的创作实践中,作家们所表现出来的“行走”“漂泊”的创作姿态,“在路上”的叙述方式和“孤独”的心灵体验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新疆经验书写的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散文中漫游者的形象特征也存在差别。周涛对游牧文化和自由精神的体悟,寄予在思想者、探险家、漫游者合而为一的主体形象中,作家在人文关怀、文化批评的格局中进行书写,散发着文化散文特有的美学魅力和思想深度。刘亮程营造出一个时空静止的村庄,叙述主体以“闲人”的方式漫游于村庄的每个角落,旨在找寻新疆边远乡村生活中恒定不变的内在。李娟散文中“作者”“叙述者”的距离更为接近,作家记录了与哈萨克族牧民一起转场的“半流动”生活,书写着牧场上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和生活日常。作家们虽都把“新疆”作为共同的叙写对象和地域范畴来关注,但散文中叙述者走“在路上”的姿态却各具千秋,这种差别体现出作家感悟生命、表达方式、情感倾向的独特性。
二、诗意想象的抒情者
在“寻根”文化之大背景下,一些作家开始反思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精神危机、信仰缺失问题,不断寻找能够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当城市现代文明与物欲横流造成人的灵魂的挤压感,当东部日渐失去了‘孤村芳草远’的自然空间,西部则显示出自然净土的家园意味,给予人类诗意存在的可能。”[11]面对西部神秘壮观的边地风景和亟待发掘的人文景观,以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境况,作家选用文字传送对西部的认知、寻求诗意表达的可能,“西部”已成为激发他们审美感受、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西部散文”的创作热潮便显示出作家构建家园净土的尝试与努力。范培松将“西部散文”称作“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12],在他看来,“西部散文”虽以地域存在而命名,但除了自然地理的客观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西部散文”内含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审美的价值取向。这些描写西部生活样态的散文,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精神、边缘文化的思考,作品呈现的美学特质、风格特征也受到西部的民俗风尚和人文历史的滋养。
“西部叙事与抒情的历史和西部生活的性质及人文境况密切相关,而自然地理又是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13]受到自然环境、历史情境、文化传统的影响,“一种浪漫的、悲剧的、神秘的、偏重感性、偏重生命意志、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流溢出来”[13]。就新疆文学的发展来说,抒情始终是这片大地上最为重要的文学传统。“新疆是诗与散文的自治区。”[7]就诗歌而言,出现了“新边塞诗人”周涛、杨牧、章德益,随后兴起的诗人北野、沈苇、刘亮程等接续“新边塞诗”的西部精神,展现出更加开放、更显个性的创作风格及文学样貌。对比诗歌,新疆散文创作同样出色,除了周涛、刘亮程、李娟引发学界讨论和广泛关注的作品外,还有叶尔克西、沈苇、卢一萍、王族、南子等人创作的表现新疆风俗人情、生命样态、自然景物的散文作品。“新疆是感性的,生命的冲力与蓬勃的野性仿佛重现人类的青春期。这深沉的感性,易于歌咏而拙于陈述,长于抒情而乏于叙事。”[7]面对充满野性生命和深沉感性的新疆大地,作家们往往选择诗歌、散文来抒发情感。周涛、刘亮程、沈苇均是以诗歌起步,而后不断开阔创作领域向散文迈进;李娟虽以散文成名,但诗集《火车快开》则是作家文体实践的一次尝试。诗歌的语言锻造方式和表达技巧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创作,而散文本质的自由和内容的宽泛也是作家们选择这一文体的重要原因。在这些饱含生命哲思、人生态度的作品里,往往由一个诗意想象的“抒情者”发出感叹,不过,作家笔下叙述主体抒发情感的方式和内容却不相同,还需依据文本内容分析作家塑造了怎样的抒情主体,以及抒情主体是如何表现作家创作诉求的。
从周涛诗歌与散文的文本内容来看,作家笔下的抒情主体形象是一致的,都有洒脱不羁的人格特征和不甘平庸的精神追求。周涛对新疆的诗意想象带有英雄主义的豪情,作者的主观感受和爱憎情感投射在叙述主体上,使散文里的人、景、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过河》里那位枯瘦衰老的哈萨克族老太太,虽然年岁已高、行走不便,可一旦上马,便牢牢掌控马前行的方向。《伊犁秋天的札记》里有高超骑马技术的通信员,骑着骏马奔驰于农场和师部之间,散发着英雄豪情和人格魅力。在巩乃斯草原的夏日暴雨中,“我”曾看到奔腾跳跃的马群在嘶叫、冲锋,“雄浑的马蹄声”和雷声雨声一起组成草原的生命交响曲,在“我”看来,巩乃斯的马“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14],它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自由驰骋,释放野性的生命力。周涛散文里的牧人形象和自然生灵无一不浸透着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叙述主体“我”不时发出赞叹和议论,抒发对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的歌颂,“我”既是散文的叙述者,又是体现作者精神意志的抒情主体,作家并不过分注重遣词造句,而是在行云流水的自然倾泻中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在诗的语言节奏和想象逻辑中塑造精力充沛的叙述主体。
与周涛背负自由精神和启蒙意识的“抒情者”相比,刘亮程散文更多是徘徊在乡村与城市间抒发乡愁的叙述主体,在表达着对村庄里事物与时空的感受。作家对乡村的诗意想象是个人式的独语,他对故乡空间“黄沙梁”的不断提及,是为了留住即将消失的乡村经验和乡土记忆,也是为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留下一片清净的园地。刘亮程的诗歌、散文、小说的内在本质是相同的,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正午田野》《库车行》《在新疆》及小说《虚空》,都是作家为留住乡村文化精神的种种尝试,“一个人的村庄”便是作家跳脱出现实乡村的诗意想象,也是他借由文字逐渐构成的人文意象。作家以诗意的笔法描绘记忆和想象中的田园村庄,在“遥远的黄沙梁”里,“家也是土地的一部分/人也是庄稼的一种”[15]11,人在天际与田野之间,守着麦子成熟、盖好房子住下,用铁锨、犁头耕种自己的生活。在刘亮程的诗歌和散文中,有一个不断离去又归来的叙述主体。为了逃离农村艰苦、贫穷的日常,去寻找梦里渴望的远方,“我”选择离开故土,但终究还是返回故地寻找迷失的“名字”与自我。“没有名字的人还将无休无止地埋身劳动。没有名字的人像草一样,一个季节一个季节地荒凉下去。”[9]69“我的名字离开村庄/去了很多地方/人们忘记它的时候/我就去那些荒凉的路上/找我的名字回家”[15]37,“我”既希望挣脱乡村的束缚在城市“扎根”,又无法抛却牵绊只能返回家乡“寻根”,在乡村与城市间游走不能找到真正的归处。字里行间涌动着作者浓浓的乡愁,情感最终指向了新疆边远农村的那宅小院,院子里、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作者久久回望的所在。
写作是李娟感受生活、抒发情感的方式,她曾说“我的写作只与我的个人生活有关。”[16]或许李娟不会像周涛去纵横古今、谈论社会与文化,也不会像刘亮程凝练情感、表达乡村哲思,但李娟的独特价值在于她发现了日常生活中别人忽略的诗意和生命最本真的欢愉。即使作家所处的生存境遇很艰难,她的文字都充盈着抚慰心灵的力量。李娟习惯从大地和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滋养,从生活本身寻找未来幸福的方向,《遥远的向日葵地》书写了“关于大地的,关于万物的,关于消失和永不消失的,尤其关于人的——人的意愿与人的豪情,人的无辜和人的贪心。”[17]作家曾与亲人生活在乌伦古河南岸的高地上,见证干涸辽阔的荒野长出金光灿烂的向日葵,看着成熟的向日葵被收割、装袋、拉走,等到曾经似乎喧闹过的土地再次归于沉寂。在回首这段经历时,作家写下收获的喜悦、无限的等待和漫长的孤寂,文字的底色仍然是暖色调的。这片向日葵地满足了作家对土地、耕种的想象,文中大地和向日葵的自然意象,以及陪伴母亲和外婆度过漫长岁月的丑丑、赛虎、兔子、稻草人,都成为作家抒发诗意与情感的重要载体。在《走夜路请放声歌唱》《记一忘二三》里,李娟表达的情感更丰富,一些欢欣和快意的背后还有其他未被发现和记录的生活面孔,有长时间辛劳却无法得到充足休息的心酸,还有无法弥补的青春遗憾和到处漂泊的伤感,以及无法排解的孤独和无助软弱带来的恐惧,正是这些情绪的反差让生命的调色板上有了更多的颜色。李娟的散文不曾预设视角,就是在无数的记忆碎片里,作者选取最鲜明的生活片段进行叙述,让读者切身感受到“我”的思绪跳跃和情感波动,以闲话式的方式向读者倾诉“我”所经历的生活、所看到的景象。
从对自然地理、文化内涵的书写到对乡土记忆、日常生活的表述,新疆作家逐渐跳出原有西部散文、新疆散文的抒情模式,发掘生活中的诗意内涵进行艺术想象。无论是刘亮程的乡土散文,还是李娟的日常叙事散文,其艺术风格既有浪漫抒情写意也有对现实生活细节的叙述描写,一些凝注作家生命哲思的意象则体现了他们对散文艺术和表达空间的深入掘进。
三、生活“在场”的记录者
“在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术语,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对“在场”的定义指向了西方哲学史中对观念、本质、存在的认知。“在场”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后,在内涵和外延上出现了转移和扩大。周闻道等人发表的《散文:在场主义宣言》提出了“在场主义散文”的概念,随后推出一系列切合“在场主义”旨要的作品。“在场主义散文”强调“‘介入’与散文的‘在场性’”[18],要求作者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真实而真诚地展示人生百态和社会现状,认为散文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与现实精神,不能失去“散文性”“介入性”“当下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散文创作提出的相应理论、形成的散文类别可谓壮观,出现了文化散文、西部散文、学者散文、女性散文、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写作等分类和命名。在复杂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对“在场”“介入”“非虚构”的强调,显示出读者、研究者、创作者、文化消费市场对散文表现社会现状、直面人生的要求,以及新世纪以来散文创作的“叙事转向”②。抒情是新疆散文最为主要的文学传统,但整体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内生规律也在影响着新疆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表达方式,原以抒情为主的新疆散文开始转向以叙事为主,叙述主体由诗意想象的抒情者变为生活“在场”的记录者,这种转变在李娟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李娟散文中对哈萨克族生活的描写来说,《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记述了“我”在杂货铺、裁缝店和牧民的日常交往,仍以“我”为主体而发出感叹。但在《羊道》系列和《冬牧场》中,李娟不再肆意表达自我对牧民和游牧生活的观感,而是尽量克制情感选择客观记录。牧民家庭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成为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我”是一个既参与其中、又无法完全融入的记录者,这样的变化与李娟所参与的《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不无关系。李娟与牧民一起赶牛羊、背冰雪、绣花毡,涓涓细流般的日常细节就是她写作的原生材料,作家无意去高谈阔论、肆意评判他们的行为习惯,而是希望牧民能接纳并允许自己去记录这些生活。即便如此,李娟还在反思这种体验到底有没有价值、是不是在走马观花,“我在这里,无论做什么,无论怎么努力,都感觉远远不够。无论想说什么,似乎都难以合乎实情或心意。”[19]在作家看来,文字、照片、摄影只能留下一些记忆碎片,她虽然努力走进牧民的内心世界、认真体会他们的生活细节,但记录生活与本真的生活状态还隔着很远的距离。
或许,文字和文学只能无限靠近真实和现场,却永远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描述、抵达真实和真理的彼岸,但这种对生活“在场”的记录、努力融入牧民生活的行为本身就富有价值。随着大规模的转场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牧民选择定居,这种古老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也被现代进程和社会发展所改变,正是因为作家用文字记录了这里的生产生活,才使得这种生命形态得以保存更长久的时间。在散文集《永生羊》《蓝雪莲之淼》《草原火母》中,叶尔克西深情回望北塔山的儿时记忆,表达着对游牧生活和草原文化的怀念;在《转场的消息》《大雪的挽留》里,王族记录了那仁牧场的牧民冬日的艰苦生活,也看到牧民接受、忍耐背后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游牧者的归途》是南子行走边疆地区时的所思所感,作家关注边疆游牧民族的生存现状,感怀游牧日常生活里的居住习惯与民俗礼仪,见证了草原里游牧文化到绿洲文化的变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情感十分浓烈而炙热,相比之下,李娟在《羊道》系列和《冬牧场》里更多是融入和克制。“我”跟随扎克拜妈妈一家转场春牧场、夏牧场,又和居麻一家转到冬窝子过冬,在“我”和两家人的相互理解和照顾中,生命和关怀的意义再次获得印证,并不相同的文字和语言是彼此交往、沟通的绊脚石,但情谊和理解却是建立信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作家以自身真实体验为基础,以近乎还原的文字记录着即将消失的游牧生活。
与作家李娟相似,刘亮程也在关注新疆大地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散文集《库车行》《天边尘土》《在新疆》写到念念不忘的南疆之行,老城里因长期居住而变得破旧的土房子和每家屋户上升起的袅袅炊烟,那些被大片沙漠环绕的田地和在田头游走耕作的农人们,都是作家梦中多次靠近的景象。作家熟悉库车土街土巷里留存的古老旧址和传统农耕的生活方式,当看到“那个坐在街边打盹的老人”,“我”便想和老人一起坐着,感受时光的打磨、见证世事变迁,等到和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变成库车老城的一部分(《暮世旧城》)。在“我”看来,接受岁月淘洗的事物和延承下来的生活习俗并不需要过程,熟悉新生的技艺和习惯反而更需耗费心力。“我”更愿意参加库车每周一次的巴扎,挑选摊位上摆着的手工农具和铜器,品尝街边维吾尔族妇女烤制的麦黄圆馕,而不是急急忙忙奔向不确定的未来,“我不一定会喜欢未来,我渴望在一种人们过旧的年月里安置心灵和身体。”[20]绵延久远的事物和习惯契合了“我”对理想生活的认识,那些淳朴的民风民俗更能获得“我”的关注和倾心。作家就是在文字构造的场景中一次次地回望库车老城,记录着久居老城的普通人的生活日常,表达彼此之间相通的情感体验与表达。
面对社会快速发展中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人文意识淡薄的情形,周涛怀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进行散文创作,叙述主体也由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形象转变为关注现实的批判者和介入生活的在场者,鞭辟入里的观点统合了作者的主观情感与社会意识,叙述主体寄予着作者真挚的家国情怀和理想的文化理念。长篇散文《游牧长城》是对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两种形态的思考,“我”认为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理解民族历史是非常必要的,“找一找,梳理一下更深刻的脉络,也许一些突然的现象就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了,也许一种整体的、历史的认识和把握就不再是空谈,而成为清醒的自觉。”[21]当沿着长城脉络旅行甘肃、山西、陕北时,作家接触到不同于新疆的文化语境、风俗风景,与新疆的短暂分离,让他跳脱出原有的思维阈限,进而为现代人的文化寻根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文化的发展需要在不同文明形态的碰撞中寻找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因子。散文《读〈古诗源〉记》是一次与传统文化、古典诗词的对话,笔记式的散文融入了作者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认同,“我是反对那种以菲薄和轻浮的态度讥笑古代文化的,尤其不能同意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22]“我”从现代人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古典诗词,在评点诗词的过程中,作家审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主体力量也在不断加强。周涛立足文化传统反观现代文明,散文中对文化现象的辨析和对现代人文精神衰落的批判,均可看作他介入现实生活的直言。
新疆的地域景观和文学传统使得作家长于抒情,但阅读新世纪前后的新疆散文,可以看到作家们的叙述重心发生了变化,散文的思辨性、叙事性在不断加强。周涛对文明形态、人文精神的关注,刘亮程、王族、南子、李娟对城市、乡村、旷野的思考与认识,体现出作家们关切现实生活、彰显主体精神的创作倾向。当然,无法忽略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写作等文学现象对作家的影响,当散文写作变得格式化、形式化,对散文文体和写作内容的审视和反思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散文作者、叙述者、叙述主体的讨论,涉及散文中“真实与虚构”的问题③,周涛、刘亮程、李娟等作家对新疆经验的倾力书写是将个人经历和生活原生状态进行整合和想象,散文当中的叙述者、叙述主体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再者,作者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带来了时空上的间离、记忆和情感的不完全性,使得散文变成有限制的真实和有限度的虚构,因此探讨作家不同阶段散文作品中的主体形象成为一种必要和可能。通过对作家抒情、叙事的方式进行辨析,明确“谁在叙述”“谁是叙述主体”,分析他们对社会文化、自然风物的情感指向和精神思索,明晰不同作家的创作追求和文体风格。同时,在对当代散文、新疆散文的发展脉络梳理中,理解周涛、刘亮程、李娟、王族、南子等人新疆经验书写和主体形象建构的共性特征和个性表达。一定程度上,这些散文创作是立足于新疆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的地域书写,但他们又跨越了个体经历和地理位置的局限,把握与时代、社会的对话机会,表达着对文化、生命、家园、自我的感悟,既接续了中国散文绵远流长的抒情传统,又为新世纪以来散文的创作转向提供了叙事篇章。
注释:
①这里主要采用了申丹在《也谈“叙事”还是“叙述”》中对“叙述者”的定义,她认为“叙述”强调表达行为,而“叙述者”是文本中作为表达工具的讲述或记载故事的人。
②在《思潮弱化与叙事转向:新世纪散文的基本面向》一文中,刘军从新散文、在场主义两个散文思潮及散文内部整体性的叙事转向,来论述新世纪以来20年的散文变化。
③陈剑晖在《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一文中提出“有限制虚构”的观点,探讨了散文“真实与虚构”的问题,认为散文创作应当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经验整合和有限度的艺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