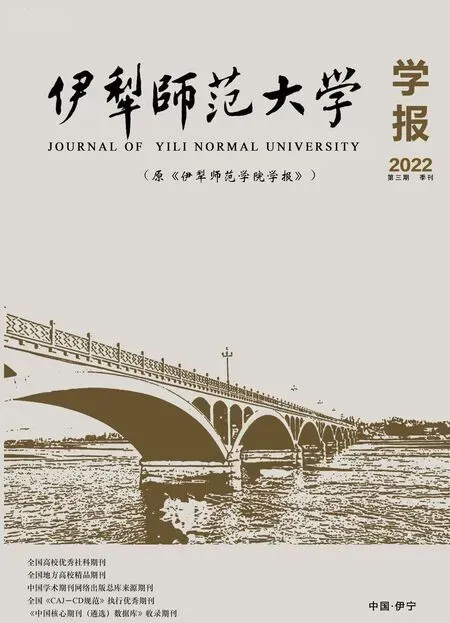上古汉语“有+S”结构中“有”的焦点标记功能探析
刘 微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上古汉语中有许多“有+S”的结构,从测查的文献来看①,这种结构在《诗经》中就十分常见,例如:
(1)摽有梅。(《诗经·召南·摽有梅》)
(2)有敦瓜苦。(《诗经·豳风·东山》)
(3)发彼有的。(《诗经·小雅·宾之初筵》)
(4)明星有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
针对“有+S”结构中的“有”究竟是何成分、作何解释这一问题,从清代的王引之开始一直到当代的研究者,均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但目前为止,学界仍没有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
一、关于上古汉语“有+S”结构的讨论
围绕上古汉语“有+S”结构的讨论主要是从上古汉语“有+N”结构的角度着手的。
(一)语助说(词缀说)
《经传释词》中将“有+S”结构中的“有”解释为:“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1]言下之意,即“有+S”结构下的“有”没有实际含义,是名词的前缀。
但这种解释明显有不合理的地方。王引之所说的“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说的是当一个字不能成词时,那么就需要加上“有”来构成一个词。而王氏列举的“邦曰有邦”“家曰有家”乃至“梅曰有梅”,在上古汉语中,“邦”“家”“梅”均是可以独立成词的,并不需要加上前缀才能单独使用。并且,以上词在上古的文献典籍中,加上所谓的前缀“有”成词只是少数,不加“有”才是常态。因此,“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的说法不符合上古汉语的语言使用习惯。
王力在《古代汉语》中将“有+S”结构中的“有”解释为名词的词头,是对王引之“语助说”的一个延续,认为“有”作为词头本身没有词汇意义,只表示词性,但王力先生自己也指出:“有些词头也不专门表示一种词性,在那种情况下,就是真正的有音无义了。”[2]467这种矛盾关系的存在,实际上也证明了“有”在“有+S”结构中不是表示词性的。
(二)音节助词说
王金芳与杨和鸣(2018)[3]则将“有+S”结构中的“有”不再当成一个词内部的语素进行分析,而是把“有”当成一个音节助词。因此在“有+S”结构中,“有”的本质还是一个词,但作为一种助加单位,不能成为句子成分。这样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法解释“有+S”结构中的“S”是可以独立成词的这一问题。
邢福义(2018)[4]对汉语助词作了如下定义,认为助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附着在某个语法单位上起助加作用,可以附着于词上,二是绝大多数的助词居于后位,只有少量类似于“第”的助词可以处于前位。
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有”作音节助词的说法也不能解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无法满足助词帮助某个语法单位起附加语法意义作用这一条件。在“有+S”结构中,“S”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独立运用的名词,如果说“有”在此结构中是帮助“S”附加名词的语法意义,是说不通的。二是不满足绝大多数的助词都处于后位这一条件,且在常见的助词分类中,并没有音节助词这一小类,也找不到与之相近的助词分类。也就是说,在助词的范畴里,我们无法为“有+S”结构中的“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三)谓词说与名词说
黄奇逸(1981)[5]认为,“有”就是动词,表示存在,与“无”相对。“周”是“肥沃的土地”,那“有周”就是指一个有肥沃的土地的国家。“有熊”就是一个有很多熊的国家。黄永堂(1984)[6]则认为“有”应该训为“大”,且是从“有无”之“有”的含义中引申而来。同时还指出,“有”可以训为“多”,从《诗经》到《史记》,都存在“大”和“多”互训的情况,因此“有”就是“大”。
“有”字在“有+S”结构中作名词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秦建明、张懋镕(1985)[7]提出的,“有”同“或”“域”,而这两字又是“国”的古字形。例如,《诗经·商颂·玄鸟》有“奄有九有”一句,《韩诗》中写作“九域”。郑玄注中也有:“域,有也”。这种解释主要是针对古国名,但对古族名没有办法解释,于是蔡英杰(1997)[8]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法,即把“有+S”结构中的“有”解释为“州域”。这种解释法是将“有+S”结构中的“S”看成了形容词,并认为上古时期的定语后置是常见的现象。
但无论是谓词说还是名词说,都只能解释在古国名和古族名前的“有”,不能够解释其他名词前的“有”。而国名、族名都是属于名词中的具体类别,能放在国名和族名前的“有”必然与放在其他名词前的“有”存在联系,如果不能解释这种联系,那么这种说法显然还是有欠缺之处的。
(四)指示代词说
既然不能将“有+S”结构中的“有”归为助词,也不能用谓词或者名词去解释“有”字,学界便将目光投向了代词,试图为“有”找到更合适的解释。李宇明(1982)[9]认为“有+S”结构中的“有”应该理解为指示代词,附加在普通名词之前,可以使普通名词转变为专有名词,当这个专有名词的概念固化之后,“有”就被逐渐去掉了。
李宇明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何有些名词之前可以加“有”,而有些名词前不可以加“有”,主要是由“有”字后面名词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是特指名词就必须加“有”,如果是泛指名词就不能加“有”。但李宇明本人也指出,“有”可以表特指义的原因尚不明确,且同样一个名词,什么时候作专有名词,什么时候作普通名词,这个定义过于主观。例如“摽有梅”,“梅”就是一个常见的普通名词,没有什么专有名词用法。如果说在《诗经·召南·摽有梅》中,“梅”象征的是女子,那也只是修辞赋予的临时含义,不能说是“梅”的特指义。
“有”的指示代词说不但可以解释“有+S”结构中的“S”作国名、族名的现象,还可以解释“S”作其他名词的现象,因而代词说更符合上古汉语的语言事实。但李宇明认为“有”附加在名词前可以使普通名词专名化的观点仍然有无法解释的特例。
总而言之,“代词说”尽管解决了当“有”后的词干为名词时“有”字的性质,但对于“有+S”中“S”为其他词性时,“代词说”便无法成立了。例如在《诗经·邶风·泉水》“女子有行”一句中,“行”在此句中作动词,指“女子出嫁”,那么“行”前面的“有”若作代词解释,显然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并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有+S”结构中的“S”是名词还是动词或者形容词,在“有+S”结构下,若“有”作代词解释,则无法解释“S”和“有+S”之间在语义功能上究竟有何具体的区别,也无法解释在语法功能上,“有+S”中的“有”为何能出现在除名词以外的其他词前。因此,“有”的含义及功能与其后的“S”并无直接联系。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有”在“有+S”结构中作焦点标记更符合实际情况。
二、焦点标记“有”的判断标准及其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汉语中的焦点问题。但此时“焦点”的概念并不明确,学界对“焦点”的理解也不统一。对此,刘丹青、徐烈炯(1998)[10]指出,所谓的“焦点”,本质上是一个语用性的话语功能的概念。所以,焦点不受语法的制约,可以存在于句子的任何部位,不是句法结构成分。同时,刘徐二人给出了“焦点”最简明直白的定义:“焦点是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10]这一观点得到了徐杰(2018)[11]等学者的赞同。
徐烈炯(2001)[12]以焦点的表现形式为分类标准,将焦点分为零形手段、重音、语序和焦点标记四种。对焦点标记的判定,方梅(1995)[13]认为,一个句子的焦点是语义中心的所在,但方梅的焦点标记判断是基于现代汉语口语的,因此重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标准。在古代汉语的研究视域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当时的口语重音情况,因此,我们根据徐烈炯、刘丹青(1998)[14]的观点,将使用强调手段(如形态、虚词、语序、韵律等)对某一语言加以突出,使听话人特别注意到这部分信息有表强调特征的成分,视为具有焦点标记的功能。
何元健(2010)[15]提到焦点与话题的区别,认为话题是出现在句首的,而焦点却不一定出现在句首,它作为新信息的标志是强化有关成分的语义。焦点可以通过焦点结构来获得,也能通过语音、形式方式来获得。
换言之,当“有”在句子中,没有实在的意义,也不充当句法成分,去掉“有”字,句子依然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有”在此句中为焦点标记。例如前面提及的例(1)至例(4),在这四个例子中,“有”后的“S”词性并不完全一致,例(1)中的“S”是名词“梅”。例(2)中的“S”是形容词“敦”,“敦”的含义是圆。例(3)中的“S”是名词“的”,“的”的含义是靶心。例(4)中的“S”是形容词“烂”,“烂”的含义是灿烂。但不管“S”的词性如何,这个结构的整体意义就等于“S”,“有”字的存在和缺失均不影响句义。“有梅”就等于“梅”;“有敦”就等于“敦”;“有的”就等于“的”;“有烂”就等于“烂”。与助词等虚词不同,虽然虚词没有实在的意义,但其具有不可或缺的语法意义,缺少虚词的存在,句义就会发生改变甚至不成立。以古汉语中常见的结构助词“之”为例:
(5)在河之洲。(《诗经·周南·关雎》)
(6)葛之覃兮。(《诗经·周南·葛覃》)
(7)麟之趾。(《诗经·周南·麟之趾》)
(8)扬之水。(《诗经·唐风·扬之水》)
(9)扬之水。(《诗经·王风·扬之水》)
以上的“之”与后面的名词同样构成“之+S”结构,但“之”在句中均表示明确的修饰关系,以例(8)和例(9)尤为突出,“扬之水”去掉“之”则整个句子的结构都会发生改变,语义从“激扬的流水”变为“扬起水”。
当“之”字后面的“S”不是名词时,这种差别则更加明显了:
(10)天之牖民,如埙如篪。(《诗经·大雅·板》)
(11)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12)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诗经·大雅·绵》)
(13)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
严格意义来说,从例(10)到例(13),“之”字后面的词与前面的“之”字联系并不紧密,“之”与后面的词仅仅是位置上的前后关系,不能构成一个“之+S”的结构。
通过对比“有+S”结构与“之+S”结构,我们可以发现焦点标记“有”与常见的古汉语虚词“之”的差异。从整体特征来说,“有”附着在其后的“S”上,具有强调突出的作用,标记其后成分的焦点身份,让其后的焦点成分成为全句的信息焦点。这种“有+S”结构中的焦点标记“有”并不是仅存在于《诗经》中,在上古汉语的文献资料中比比皆是,例如:
(14)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周书·召诰》)
(15)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尚书·周书·召诰》)
(16)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尚书·商书·汤誓》)
(17)有王虽小,元子哉!(《尚书·周书·召诰》)
(18)既搢必盥,虽有执于朝,弗有盥矣。(《礼记·玉藻》)
(19)殆有甚焉。(《孟子·梁惠王篇》)
例(14)与例(15)中的焦点标记“有”后的名词均在国名、族名之前,例(16)与例(17)的焦点标记“有”均在普通名词前,但“有夏”“有殷”“有周”与“夏”“殷”“周”的意思毫无差别,“有众”“有王”与“众”“王”也没有差别。例(18)与例(19)中的“S”从名词换成了动词和副词,“有盥”依然等于“盥”,“有甚”依然等于“甚”。尽管“有”在结构中并没有起到意义上的帮助作用,但加上焦点标记“有”后,使得“有”后的“S”得到了强调。
正如徐烈炯、刘丹青所提到的那样,焦点本质上是一个语言性的语用功能的概念,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焦点可以存在于句子的任何部位,因此不是一个句法结构成分。但是焦点存在也会有其固定的位置,这使得焦点和句法也有了一定的关系,此时焦点这一语用概念就会进入句法层面,从而具有了语法形式特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古汉语“有+S”结构中的“有”从“词缀说”“谓词说”“名词说”均能够找一定的例子进行佐证,但总有特例无法解释的现象。即便是“代词说”可以解释名词前的“有”在形式语法层面的功能,却无法合理地解释“有”字意义。同时,不管是以上任何一种解释,都只将目光局限于“S”为名词的情况,当“S”为其他词性时,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有”究竟有何功用。
三、焦点标记“有”与其他古汉语焦点标记的对比
古代汉语中常见的焦点标记有“是”“之”“所”。“是”“之”“所”在古汉语中作焦点标记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讨论。
何乐士(1990)[16]认为,焦点标记“是”的用法到5世纪时彻底成熟,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了今日。而古汉语中的焦点标记“是”是由复指代词“是”发展而来的。
王力(2001)[2]253-365指出,“是”“之”“所”均是古汉语中常见的复指代词。有关“是”“之”“所”从复指代词转化为焦点标记的现象,最早为徐杰、李英哲(1993)[17]所关注。徐李二人认为,先秦汉语中,宾语的前置现象实际是突出焦点的手段。石毓智、李讷(2001)认为:“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判断词会自然地向焦点标记演化。汉语的判断词‘是’也不例外,它在演变成判断词的同时,很快也发展出了焦点标记的用法。”[18]29
最后,石毓智、李讷对先秦代词作焦点标记的现象进行了如下总结:“在先秦汉语里,焦点化的附着成分(受事代词)必须居于句子的第二位置——动词之前和主语之后。”[18]41
但石李二人认为“是”在上古汉语中还不算真正意义的焦点标记,对此,刘丹青(2004)提出了不同意见:“先秦汉语名宾前置式主要是唯O 是V 式,其名宾前置主要是语用因素决定的,没有什么句法条件规定某个名宾必须前置,选择前置是表达焦点的需要。”[19]因此,路广(2004)[20]对古汉语复指代词和焦点标记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梳理,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还指出,焦点现象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能存在于疑问句和否定句中,就也能存在于肯定句中,且焦点的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焦点标记词这一种手段,还可以采用重音语序等变化手段。刘志刚(2008)[21]将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是”“之”与现代汉语“是……的”等结构进行对比,进一步肯定了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是”“之”确为焦点标记。
徐江胜(2017)[22]也认为“是”“之”在古汉语中有明确的焦点标记功能,还指出“所”也具有将宾语提前,以达到强调宾语的作用,并且分析得出,“所”由施动关系标记虚化成了焦点标记。自此,古汉语中“是”“之”“所”可作焦点标记的论证已十分充分。
因此,我们可以对比“是”“之”“所”作焦点标记的情况:
(20)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21)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其爱鼎?(《左传·昭公十二年》)
(22)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庄子·大宗师》)
(23)三国之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战国策·齐策三》)
(24)唯命所听。然先言子所病之正。(《列子·仲尼》)
(25)造父曰:“唯命所从。”(《列子·汤问》)
例(20)和例(21)中的焦点标记“是”附着在名词后,构成“S+是”结构,去掉“是”并不影响句义,因为焦点标记“是”的含义完全等同于前面的名词。焦点标记“之”则有两种结构类型,例(22)和例(23)中的“之”与前面的名词构成“S+之”结构,“之”的含义也完全等同于前面的名词。例(24)和例(25)中的“所”则同样与前面的名词构成“S+所”结构,“所”的含义依旧完全等同于前面的名词。
在这里,我们将三个焦点标记“是”“之”“所”记为“F(focus)”,故以上三个焦点标记与其前的名词构成的结构是“S+F”。通常情况,“F”应该与其后的动词构成“F+S”。但根据语义,以上五例的焦点“F”与其前的名词明显是对等的指代关系,和其后面的动词反而没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S+F”结构更为合理。
从以上三个常见的古汉语焦点标记可以看出,焦点标记是句法层面和语义层面上看起来相对多余的部分,删掉完全不影响表意,这在功能层面上,与“有+S”的情况是一致的。但焦点标记“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有”作为焦点标记,它通常是出现在“S”前而不是“S”后,那么,这影不影响它成为一个典型的焦点标记呢?
根据徐烈炯、刘丹青的定义,焦点标记理论上可以存在于句子的任何位置,因此,焦点标记出现在“S”之前或者“S”之后,都不影响焦点标记的强调性质。故焦点标记的位置并不影响其作为焦点标记的特性。
前文已经提到,焦点标记可以出现在句子中的任何位置,因此焦点标记前后的词性都没有必然的限制。根据Gundel(2018)[23]在其《论焦点的不同类型》中的观点,将焦点标记分为心理焦点、语义焦点和对比焦点三种,其中语义焦点和对比焦点才能算得上是语言学范畴下的“焦点”。语义焦点重在突出信息之新,而对比焦点重在突出信息之必要。除此以外,多个焦点标记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且不同的焦点标记之间有强弱主次之分。只有满足了以上几个特征,才能证明“有”在“有+S”结构中作为焦点标记的典型性。
通过对“有+S”结构中焦点标记“有”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并确认焦点标记“有”的三大语法功能特点:第一,焦点标记“有”其后的“S”没有词性上的限制,“有”可以出现在名词、形容词、动词或者副词等词性前,但焦点标记“有”最常见的还是出现在名词或者形容词前。第二,从焦点标记的类别看,“有”属于对比焦点,通过添加焦点标记“有”来突出强调的内容。第三,“有”存在的句子中还可以出现其他的强调形式。当句中出现其他焦点标记时,则“有”属于强调程度较低的焦点标记。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作焦点标记时与其他焦点标记同时出现的例子:
(26)有芃者狐。(《诗经·小雅·何草不黄》)
(27)有卷者阿。(《诗经·大雅·卷阿》)
(28)其于观东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进擅退,不使群臣虞其意。(《韩非子・八奸》)
(29)有所达则物弗能惑。(《吕氏春秋・知分》)
(30)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商君书・农战》)
(31)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随怒事情,辄有所发。(《老子想尔注》)
袁毓林(1997)[24]对古汉语焦点标记“者”进行分析后,认为“者”作焦点标记时,通常附加在名词性成分之后,构成“NP+者”结构,“者”通过将宾语话题化和加“所”作标记两种手段,从而具有了提取宾语的句法功能,因此“者”也是古汉语常见的焦点标记之一。
例(26)到例(27),“有”与“者”作为焦点标记同时出现在句子中,以例(26)为例,“有芃者”与“狐”互为同位语,焦点标记“者”将“有芃”这一形容词性的词组化为名词性词组,且突出了“狐”的性质是“有芃”,因此,“者”是该句中强调程度最高的焦点标记,而“有”仅仅强调“芃”,故“有”作为焦点标记,其强调程度低于“者”。例(27)中的“有”同样强调程度低于“者”,此处不再赘述。
从例(28)到例(31),“有”与“所”作为焦点标记同时出现在句子中,以例(28)为例,“必令之有所出”与“必令之出”在语义上并无明显不同,因此“有”和“所”在此句子中都可以随意去掉。但对比“必令之有出”与“必令之所出”,我们可以发现,“有”具有一定的动词性质,表示存在,所以“必令之有出”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合格的句子,而“必令之所出”则不再完整。由此可见,“有”的焦点化程度不如“所”高。接下来的例(29)到例(31)也是同样的情况,故不再赘述。
四、结语
古汉语“有+S”结构中的“有”究竟在结构中作何成分、有何功用、出现在不同的词性之前有何不同,这历来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以往的讨论着眼于语法层面,倾向于将“有+S”结构中的“S”按照词性的不同,把“有+S”结构拆分为“有+N”“有+V”“有+Adj”等几种不同的形式去讨论,且多数讨论都集中在对“有+N”结构的讨论上,不但将讨论本身复杂化了,还使得“有+S”结构的共性被忽略了。
此次探讨试图抛开词性对结构本身的干扰,将“有+N”“有+V”“有+Adj”合并为“有+S”结构,从而将研究的核心集中于结构中的“有”上,从语用的角度分析,得出“有+S”结构中的“有”是一个焦点标记,并将焦点标记“有”与古汉语中其他常见的焦点标记进行对比,从而总结出焦点标记“有”具有以下三大语法功能特点:第一,焦点标记“有”其后的“S”没有词性上的限制,“有”可以出现在名词、形容词、动词或者副词等词性前,但焦点标记“有”最常见的还是出现在名词或者形容词前。第二,从焦点标记的类别看,“有”属于对比焦点,通过添加焦点标记“有”来突出强调的内容。第三,“有”存在的句子中还可以出现其他的强调形式。当句中出现其他焦点标记时,则“有”属于强调程度较低的焦点标记。
注释:
①本文测查的文献有:《诗经》《周书》《商书》《礼记》《孟子》《左传》《庄子》《战国策》《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商君书》《老子想尔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