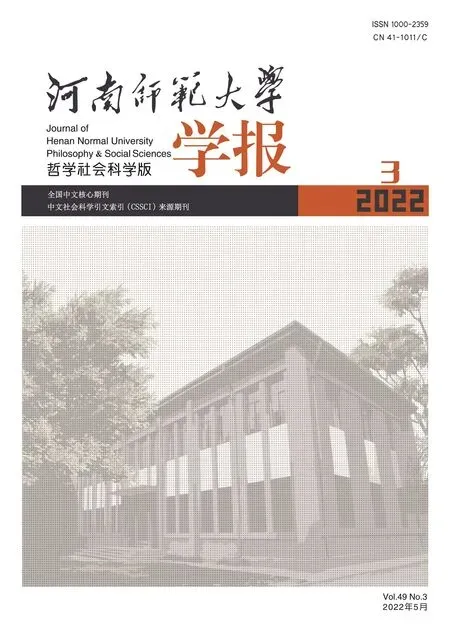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考论
刘志伟,胡姝梦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他少年成材,其文学成就,特别是骈文创作,称得上是南北朝时期的翘楚。关于庾信早年事迹,史传中记载颇为笼统简略,而北周滕王宇文逌《庾信集序》一文则曾有言及,说是庾信“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1)许逸民:《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55页。。据清倪璠《庾子山年谱》,庾信十五岁当梁武帝大通元年(527)(2)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3页。,其时入主东宫的,是年在二十七岁的昭明太子萧统。如此看来,宇文逌所要表达的是少年庾信曾在昭明太子手下任职,与东宫文士曾有过交集。
但是,近世有部分学者对宇文逌的说法颇有怀疑,主要理由大致有二:(1)年十五出任萧统东宫讲读,年纪过于少小,似不能胜任,亦无此先例;(2)其时昭明太子二十七岁,早已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和作家,还有必要请一位少年郎来指导他学经读书吗?(3)鲁同群《庾信年谱汇考》指出,“可知侍太子读一职颇为尊重,非十五岁童子所可胜任。……故笔者不从滕序而从《周书》”,详参范子烨:《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卷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645页;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庾信小传》认为“十五岁的侍读对于二十七岁的太子来说是不合适的”“有年少人当侍读是稀罕的”,故将“侍梁东宫讲读”解作“庾信列席太子开设的讲义,射策席间所提出的问题”(详参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08页)。另外,也有不少学者肯定了宇文逌的说法,认为庾信任萧统伴读属实(4)刘文忠《鲍照和庾信》一书指出,“庾信十五岁便进入东宫(太子宫),为昭明太子萧统的讲读(伴读)。萧统喜爱文学,又有丰富藏书,庾信作为他的伴读,自然有了更好的读书条件”(刘文忠:《鲍照和庾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1页);张翥,曹萌《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文学》中说,“庾信为太子讲读约五年有余”“在这一段时间里,庾信的主要工作是给昭明太子侍读。昭明太子为人甚是谦和,又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庾信同他在一起,既有者共同对于儒典、史籍的兴趣,又有着彼此间的切磋和讨论”(详参张翥,曹萌:《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4页);林怡《庾信研究》指出,“我们认为庾信初仕时间当在梁大通元年(527)十五岁时,起家官为一班或二班‘不言秩’的东宫清职‘侍东宫讲读’,这年昭明太子二十七岁,庾信‘弱龄参顾问’就是充任萧统的伴读书童”(详参林怡:《庾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2页);吉定《庾信研究》一书提出,“(庾信)伴读对象是昭明太子萧统”(详参吉定:《庾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页)。以上诸家之说,均将萧统作为庾信的讲读对象,并予以阐发。。为了准确解读宇文逌序文的这一文句,也为了有助于全面了解庾信生平中的早慧事实,笔者觉得有必要就上述问题加以辨析,以供读者深入讨论。
一
想辨明这些问题,先要考察《庾信集序》的记载是否属实。既然史传未载庾信侍东宫讲读一事,想要全面了解此事的可信性,就应从作者宇文逌与庾信的关系、序文的创作背景,以及庾信作品的生平自述中寻找答案。
首先,宇文逌是庾信入侍北周以后结识的宗室成员,从诸种文献记载看二人交游颇为密切。宇文逌,字尔固突,北周文帝宇文泰之子。《周书》本传载其“少好经史,解属文”(5)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第206页。,正是由于宇文逌少年时代对学术和文章的用心,为其日后与庾信的文学往来埋下了伏笔。据倪璠《庾子山年谱》,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以南梁使者的身份来到西魏,适逢江陵沦陷,遂仕于北地(6)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23页。。庾信在西魏北周任官期间,深受北周明帝宇文毓和武帝宇文邕的赏识,也因此与宇文氏诸王产生较多的交集。诸王之中,滕王宇文逌与庾信的交游最为款密。《周书·庾信传》载:“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7)令狐德棻:《周书》,第734页。宇文逌在《庾信集序》里也说:“余与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缟紵,契比金兰。”(8)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66页。另外,庾信诗文中有《谢滕王集序启》《谢滕王赉巾启》《谢滕王赉马启》《谢滕王赉猪启》,这些文献材料表明了二人在生活与文学上的交谊深厚,由此推知,宇文逌有较多的机会了解到庾信早年的人生经历。
其次,参看宇文逌《庾信集序》与庾信《谢滕王集序启》,可知宇文逌受庾信之托为《庾信集》作序,序文完成后,又曾交与庾信阅览。《庾信集序》末尾道:“欲予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9)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66页。直接表明此序是受庾信之托而作。后庾信为答谢宇文逌制序,特作《谢滕王集序启》,开篇点出“伏览制垂赐集序”(10)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552页。,说明他曾详细阅览《庾信集序》。从二人一系列相关的文章互动中看出宇文逌不存在杜撰庾信生平的可能性。况且宇文逌从庾信早年生平经历中精心择选十五岁入侍东宫一事,予以盛赞:“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虽桓麟十四之岁,答宿客之诗,鲁连十二之年,杜坚离之辨,匪或斯尚同日语哉!”(11)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55页。桓麟、鲁连二人皆以早慧闻名,据《后汉书》本传记载桓麟“早有才惠”(1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0页。,另《鲁仲连子》记载“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1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459页。。可见宇文逌以此二人的早慧事迹来与庾信相比,意在凸显庾信十五岁入侍东宫更加难能可贵。倘若庾信此事不实,宇文逌何必如此费力着墨呢?
再者,庾信《哀江南赋》中的生平自述,可作为印证宇文逌序文的关键材料。《哀江南赋》有云:“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14)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8页。“王子滨洛”二句袭用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盖同王子洛滨之岁,实惟辟彊内侍之年”(15)《文选》卷五九载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此二句下吕向注,“王子晋初游洛滨,年十五。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李善注引《周书》,“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与之言,五称而三穷。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不能与言’”,又引《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雒之间”(详参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64页)。,“王子滨洛”正指十五岁时的周太子晋,也是后来传说中在伊洛地区成仙的王子乔。“兰成射策”一句中,兰成,即庾信小字(16)倪璠注引陆龟蒙《小名录》,“兰成,信小字也”(详参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9页)。,射策,指朝廷组织选拔官员的策试(17)射策,即对策,古代考试官员的一种方式,《汉书·萧望之传》载,“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详参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2页)。,此句与宇文逌序文中记载“玉墀射策,高等甲科”(18)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55页。为同一事。由此可知,庾信十五岁射策高中甲科,是与他入侍东宫同年发生的事。
再看《哀江南赋》下二句“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19)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8页。,笔者认为当指庾信年十五射策高中甲科后,入尚书省任尚书郎(20)“含香”,任尚书郎之典,“建礼”,即建礼门,指尚书郎执勤处,倪璠注,“桓帝时,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后尚书郎含鸡舍香,始于此”,“尚书郎昼夜更直于建礼门”(详参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9页)。,仍在东宫兼任侍讲侍读(21)“仍矫翼于崇贤”,崇贤,即太子门。由宇文逌序文“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玉墀射策,高等甲科”的表述顺序,知庾信十五岁,先侍东宫讲读,后射策高中甲科。射策高中后,得以入尚书省充任尚书郎,此后继续于昭明太子东宫侍从讲读,昭明太子薨逝后,又入萧纲东宫任抄撰学士,故用一“仍”字。。这也就是说,庾信的自序恰好印证了宇文逌序文“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一事。倪璠将《哀江南赋》此句解作庾信任尚书度支郎中,寻转东宫学士(22)倪璠注:“按滕王逌序:‘信解褐授安南府行参军,寻转尚书度支郎’故云是矣。”可知倪璠认为此处庾信所说进入尚书省是指任尚书度支郎(详参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9页)。,恐误。原因在于:庾信生平自序理应按时间先后历述,庾信任尚书度支郎中在二十五岁前后(23)参宇文逌序“解褐授安南府行参军。尺木未阶,高衢方骋。寻转尚书度支郎中”,可知庾信任安南府行参军与转任尚书度支郎中之间间隔时间较短。关于庾信任安南府行参军的时间,可参看《梁书》的相关记载。《梁书》载梁武帝授安南将军者共计四人:天监三年(504),任命扶南国王恔陈如阁耶跋摩为安南将军;天监四年(505)至天监六年(506)间,任命柳惔为安南将军;天监七年(507),任命曹景宗为安南将军;大同元年(535),任命萧续为安南将军。在上述记载中,仅有萧续任安南将军的时间与庾信的生平节点相吻合。《梁书·武帝本纪》载“(大同元年)以安北将军庐陵王续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大同三年)以安南将军庐陵王续为中卫将军、护军将军” ,表明萧续担任安南将军在大同元年(535)至大同三年(537)间。因此,庾信任安南府行参军也应在此时间范围。大同元年(535)至大同三年(537)年之间,庾信二十三至二十五岁。此后不久庾信转任尚书度支郎中,可推知当在二十五岁左右。,而后文“游洊雷之讲肆,齿明离之胄筵”(24)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8页。,当指庾信十九岁在萧纲东宫担任抄撰学士时期(25)关于庾信任东宫抄撰学士的时间判定,可将《梁书·庾肩吾传》“(萧纲)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东海鲍至等充其选” 与《周书·庾信传》“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 相参,知庾信在中大通三年(531),萧纲入主东宫后,随即担任该职。此外,由《周书·庾信传》载,“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可知庾信自序所言“游洊雷之讲肆,齿明离之胄筵”。当是追忆了这段追随萧纲,参与讲筵,备受恩礼的经历。,如此一来,显然出现了时间顺序的颠倒,因此,“始含香于建礼”不应指庾信二十五岁之事。依据梁武帝天监四年(505)下诏:“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26)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第662页。又自汉代以降,多有射策高中甲科,充任郎官之例(27)据《汉书》载,匡衡、翟方进、何武、王嘉等人皆“以射策甲科为郎”。《汉旧仪》云,“太常博士弟子试射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参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89页),梁代史料中亦有王训、张绾、王承等人射策甲科,授郎官的记载。,可知射策高中甲科后,庾信是有资格充任尚书郎一职的。对照宇文逌序文,正好补充了他入侍昭明太子东宫的主要活动是侍从讲读。至此可知,庾信年十五入侍昭明太子东宫的文献记载是信而有征的。
二
前文仔细论证了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一事具备充分的材料支撑,搞清楚了这一点,接下来就有必要探讨庾信在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得以入侍昭明东宫的各种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有机统一,促成了庾信一步走进了梁代的文化核心圈中。
庾信入侍东宫的前一年,也就是普通七年(526),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外部因素,致使庾信于次年入京。第一个是普通七年(526)夏四月,梁武帝下诏令群臣荐举人才,《梁书·武帝本纪》载:“诏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荐闻,州年举二人,大郡一人。”(28)姚思廉:《梁书》,第70页。庾信之所以参加策试,与这通诏书密切相关,庾信凭借家族出身及出众的才德进入推举之列,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推举之后还需经过朝廷考试合格,方能任官,这就是所谓“射策”,应是明年即大通元年(527)的事了,此时庾信正十五岁。这一外部因素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梁武帝注重文教,广求贤才的大环境下,积极培养并延揽人才是一种常态。首先,梁武帝尚学尚才的顶层设计,由发展文教、广立学馆而始,《梁书·武帝本纪》称其:“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29)姚思廉:《梁书》,第96页。另外,《陈书·儒林传序》也记载他留心培育人才,概称:“(梁武帝)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30)姚思廉:《梁书》,第433页。其次,在努力培养人才的前提下,梁武帝在天监至年间对选士制度也予以相应的调整。天监四年(505),梁武帝下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31)姚思廉:《梁书》,第41页。明确选官以才学为重,突破年龄限制。接着,天监七年(508),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32)姚思廉:《梁书》,第47页。又于天监八年(509),下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33)姚思廉:《梁书》,第49页。强调了不限门第,随才试吏的选官思路,这些诏令在稳固文化统御,弥合士族、寒门矛盾的同时,无疑申明了上层政权求才若渴的整体态度和选拔人才的多项准则。在普通七年(526),直接关涉庾信入京的诏令下达之前,普通三年(522)五月,梁武帝也曾下诏:“公卿百僚各上封事,连率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34)姚思廉:《梁书》,第66页。可见举荐人才的风气之盛。如此风气之下,普通七年(526)下达这通诏书显然不是偶然之举。
第二个外部因素是萧统、萧纲生母丁贵嫔于普通七年(526)十一月逝世。据《梁书·武帝本纪》载:“(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是日,丁贵嫔薨。”(35)姚思廉:《梁书》,第70页。其时晋安王萧纲在襄阳任雍州刺史,他一得噩耗自必急速返回京城,奔赴母丧。依照《礼记·丧礼》记载的丧礼程序:“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若未得行,则成服而后行。”(36)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335页。萧纲在外闻母丧,必然从速而归。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庾信的父亲庾肩吾是晋安王萧纲的腹心近侍之臣,《南史·庾肩吾传》记载:“(晋安)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37)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246页。因此,当萧纲返京奔丧之际,庾肩吾陪侍其左右应是肯定的事实。又据古代官场情况,职事官员往往携带家属赴任,于是,萧纲奔丧,庾信随其父陪侍萧纲赴京也就顺理成章了。按《梁书·简文帝本纪》记载:“七年,权进都督荆、益、南梁三州诸军事。是岁,丁所生穆贵嫔丧,上表陈解,诏还摄本任。”(38)姚思廉:《梁书》,第104页。萧纲此时仍任雍州刺史,进京奔丧后便返回雍州,而庾信射策高中甲科,留于京城。由于朝廷策试官吏,加上丁贵嫔病亡这两个因素,促成了庾信就职东宫,这也成为他人生道路早年的一个节点。
接下来,就庾信其人的综合情况来看,是否能满足十五岁入侍东宫的条件。庾信的家族出身是符合入侍东宫条件的。庾氏家族在梁朝虽非世家大族(39)《梁书·庾于陵传》载,“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此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姚思廉:《梁书》,第689页)。由此可知,梁代选拔东宫属官本重门第出身,庾氏家族并不在甲族范围,不过庾于陵凭借自身才学,使梁武帝提出用人不限甲族之论。,但庾信的上代多因才学受到王室成员的垂青。萧绎在《中书令庾肩吾墓志》中赞誉庾氏家族:“掌庾命族,世济琳琅,遂昌开国,蝉联冠冕。”(4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6109页。庾信的八世祖庾滔追随晋室南渡。祖父庾易史书有传,称其“志性恬静,不交外物”“建武三年,诏征为司空主簿,不就”(41)李延寿:《南史》,第1245页。,颇有清名。庾信的父亲庾肩吾被萧纲赞为“杞梓之材”(4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6110页。,曾入侍萧纲东宫,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中庶子。庾信的两位伯父庾黔娄和庾于陵,前者曾任太子萧统侍读,颇受器重,后者博学有才思,入侍萧纲东宫,官拜太子洗马。庾氏家族受到梁王室礼遇,这也为庾信进入梁帝王择选入侍东宫者之列提供了有利的出身环境。
早慧成材,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是少年庾信入侍东宫的重要资本。宇文逌序文盛赞庾信的早慧,称其“少而聪敏,绮年而播华誉,龆岁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43)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53页。,与《周书》本传记载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44)令狐德棻:《周书》,第733页。相一致。结合庾信《哀江南赋》中“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和《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其八》里“弱龄参顾问”(45)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336页。的自述不难看到,庾信早年已拥有了出色的多方面才能,其中以博学为首要特征,对经义尤为熟通。另在德行方面,也具备儒家理想人格要素。这些为学为人的优异之处,为庾信入侍东宫创造了有利的个人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萧统本人颇爱才士,这也为庾信进入东宫创造了有利因素。《梁书》本传记载: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46)姚思廉:《梁书》,第167页。这条材料一则表明萧统爱才,二则展现了萧统与周围学士的主要学术活动,三则叙述了东宫藏书之盛。由此看来,梁武帝大通元年(527),恰居于京师的庾信,凭借家族出身和才学入侍东宫,后射策高中甲科,备受萧统的赏识,继续留侍东宫,也合于萧统的揽才之心。而庾信入侍东宫,有机会与东宫诸文士产生交集,并获得查阅典籍之便,对自身的文化成长也有诸多助益。
三
如上所述,庾信年十五入侍梁昭明太子东宫应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他侍讲读的对象究竟是谁呢?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昭明太子本人,笔者对此抱有怀疑,认为此说是难以成立的。
先就萧统的人生经历来看。此时他二十七岁,几近“而立”之年,像这样的年纪,还需要一位少年郎来为其讲读,岂非咄咄怪事?此外,萧统是一位“生而聪睿”的早慧者,幼年曾得庾黔娄、殷钧、到洽及明山宾等名士为其讲经读书,五岁遍读《五经》,九岁于寿安殿讲《孝经》(47)姚思廉:《梁书》,第165页。。事实上,庾信入侍东宫之时,萧统已经是学养深厚、文章繁富的学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庾信来担任其讲读是不可思议的。
再就相关史传材料来看,侍讲读者大多是成年成名的人物。而且,有梁一代,侍讲读者通常是在王室成员尚未成年之时,承担着启蒙教育的责任。例如,天监八年(509),萧纲领石头戍军事,时年七岁,由徐摛为其侍读。庾黔娄任萧统侍读时,萧统三岁,殷芸任萧统侍读时,萧统十三岁(48)分别见《梁书·庾黔娄传》,“东宫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详参姚思廉:《梁书》,第651页),《梁书·殷芸传》,“(天监)十年,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详参姚思廉:《梁书》,第596页)。。侍讲读者主要参与王室成员讲授经义的活动,如《梁书·徐勉传》记载:“(萧统)尝于殿内讲《孝经》,临川靖惠王、尚书令沈约备二傅,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王瑩、张稷、柳憕、王暕为侍讲。”(49)姚思廉:《梁书》,第378页。又《许懋传》云:“文惠太子闻而召之,侍讲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50)姚思廉:《梁书》,第575页。这些侍讲读者均已成年成名,且侍讲读者明显较侍读对象年长。当然,纵览魏晋南朝文献,也有少数未及成年便因才学出众担任王室侍讲、侍读的,但讲读对象均处于幼年阶段。《晋书·司马骏传》记载司马骏任曹芳侍讲,“齐王芳立,骏年八岁,为散骑常侍侍讲焉”(51)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4页。,齐王曹芳与司马骏同岁。《梁书·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另据《南史·宜都王铿传》记载:齐高祖萧道成第十六子萧铿,“年七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52)姚思廉:《梁书》,第742页。。陶弘景虽未及成年而为诸王侍读,但萧道成诸子也尚处幼年。这些记载说明十五岁的庾信为二十七岁的萧统讲读是无前例可循的。
那种认为庾信为萧统讲读的见解实际上是误解了宇文逌序文的原意。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是:庾信在昭明太子东宫的讲读对象究竟是谁?东宫人员不仅包括太子及东宫属官,还应包括太子诸位子嗣。以庾信的年龄和侍讲侍读制度的规律看,这位早慧才子应当是给未及成年的王室子弟讲经读书的。俞绍初先生在《昭明太子年谱》提出:“信得以入侍东宫,为昭明诸子讲读矣。”(53)俞绍初:《昭明太子萧统年谱》,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这一观点既肯定了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的事实,也为他的主要活动划定了合理界限。下面笔者就庾信为萧统诸子讲读的合理性做进一步说明。
首先,就昭明诸子年岁而言,他们在大通元年(527)多处于早期教育的关键时期,的确需要有伴读者来加以引导。萧统膝下五子,史书有确切生年记载者是第三子萧詧,按《北史·萧詧传》所说:“八年二月,詧终于前殿,时年四十四。是岁,周保定二年也。”(54)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088页。由此推知萧詧生于梁天监十八年(519),较庾信小六岁。萧统长子萧欢为蔡氏所生,蔡氏于天监七年(508)四月已被纳为太子妃,以此推之,萧欢的年纪当小于庾信,且可能比较接近。大通元年(527),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时,萧统长子萧欢、次子萧誉当在十岁至十五岁之间,三子萧詧此时九岁,兄弟数人均处于接受早期教育的重要年龄段,由早慧成材且年龄稍长的庾信来为他们讲经读书是合适的。
其次,看这一年萧统的境况。萧统生母于普通七年(526)十一月去世,南朝沿袭晋代心丧三年之礼,刘宋元嘉年间,议定心丧以二十五月为期,梁代采用郑玄二十七月之论(55)见《魏书·李业兴传》,“业兴曰:‘此之一事,亦不专从。若卿此间用王义,除禫应用二十五月,何以王俭《丧礼》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详参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63页)。此事发生在东魏天平四年,时值梁朝梁武帝大同年间,萧衍遣散骑常侍朱异接待东魏李业兴、李谐、卢元明三人,故有此对话。,而大通元年(527),萧统正处于心丧期。他为人至孝,正如《梁书》本传所说在丁贵嫔出殡之时,“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56)姚思廉:《梁书》,第167页。。除生母过世外,这一两年间,萧统周围的文士如陆倕、明山宾、到洽等也相继辞世。《梁书·到洽传》记载萧统在与萧纲书中感叹:“明北兗、到长史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己已。去岁陆太常殂殁,今兹二贤长谢。……比人物零落,特可伤惋。”(57)姚思廉:《梁书》,第404页。足以见出他悲伤哀痛的心情。处于这样的境地,萧统亲自参与诸王子教育的精力会相对减少,但他深知对诸王子的教育不可废弛,于是引进年轻文士庾信为诸子讲经读书,这应该也是庾信进入东宫侍从讲读的一个成因。
再次,梁王室普遍重视对子孙的早期教育,因此留心引进优秀的人才充任侍读侍讲的人选。有关这一点,我们从梁武帝为幼年时期的萧纲选择侍读者的言论可窥一斑。《梁书·徐摛传》记载:
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行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58)姚思廉:《梁书》,第446—447页。
晋安王萧纲七岁时,领石头戍军事。梁武帝萧衍颇为关心萧纲的教育问题,希望求得才干与德行兼备之人陪侍萧纲左右。于是周舍举荐徐摛,称徐摛虽身形矮小瘦弱,但可以胜任。梁武帝强调选人需有真才实学,而不看重其容貌,于是选徐摛为侍读。南朝时期,文士早年为王室讲经读书,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江淹少时好学,以文章显,《自序》中有“弱冠,以五经授宋始安王刘子真,略传大义”(59)李长路,赵威:《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378页。。又《梁书·王暕传》记载:“弱冠,选尚淮南长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员外散骑侍郎,不拜,改授晋安王文学。”(60)姚思廉:《梁书》,第321—322页。王暕年少有成人之度,二十岁担任晋安王文学。由此可见,选择德才兼备者为王室子弟讲经读书或伴游,是梁王室一贯的做法,这也正好说明选择庾信入侍东宫为萧统诸子讲读一事绝非偶然。
四
明白了庾信入侍东宫的主要讲读对象之后,再来看宇文逌序文里“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所传达的信息,显然指庾信在昭明太子东宫的主要活动,而不是官职。这一点,从下文记载庾信“解褐授安南府行参军”(61)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56页。,明确说出他的起家官就可以看出来。若“侍梁东宫讲读”指庾信的起家官,那么序文内容就自相矛盾了。
再者,“侍讲读”应当是宇文逌经过自身用语习惯加工而成的表述,因为在北朝语言表述中,多有使用“侍讲读”“讲读”的习惯。如《魏书·高谧传》记载:“显祖之御宁光宫也,谧恒侍讲读,拜兰台御史。”(62)魏收:《魏书》,第752页。又《刘芳传》记载:“(刘芳)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恒侍坐讲读。”(63)魏收:《魏书》,第1220页。此外,《北齐书·张雕传》中也记载:张雕“魏末,以明经召入霸府,高祖令与诸子讲读。”(64)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594页这些材料共同证明了在北朝语境当中,“侍讲读”或“讲读”用以传达侍从皇室讲经读书的经历,显然并非指官职。
另外,由侍讲侍读的制度来看,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侍讲读多数也仅为称号,没有官职(65)仅在北朝后期,侍读成为正式官职,如《隋书》记载北周时期,长孙平解褐卫王侍读、杨汪解褐冀王侍读、柳裘累迁太子侍读等。,从这个层面讲,侍东宫讲读也不能作为庾信的起家官。南朝史料中多见侍讲读由本官兼任的记载,加上《宋书·百官志》《南齐书·百官志》《通典·职官典》中均未记载侍讲读的官品,可以表明在当时侍讲侍读不是固定的官职。例如,《梁书·庾黔娄传》记载:“东宫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中舍人到洽、国子博士明山宾等,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66)姚思廉:《梁书》,第651页。明确反映出庾黔娄是以本官兼任萧统侍读的。又,《明山宾传》记载:“(明山宾)迁北中郎咨询参军,侍皇太子读。”(67)姚思廉:《梁书》,第405页。以及《贺革传》记载:“(贺革)起家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68)姚思廉:《梁书》,第673页。共同反映出南朝侍讲侍读由本官兼任的情况。可以说,无论就宇文逌序文的上下文关联,还是侍讲侍读的制度来看,“侍梁东宫讲读”均不指涉庾信的官职,而应理解作庾信入侍东宫后的主要活动。
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的这段经历长达五年。庾信在为萧统诸子讲经读书期间,不排除有机会参与到萧统所组织的学术创作与文学讨论当中。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的时间,恰值《文选》成书的最后阶段(69)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3982页。,庾信作为东宫之中的早慧才士,也有可能参与了《文选》的修订和增补。中大通三年(531)四月,萧统薨逝,七月,萧纲被立为太子,萧统诸子各被封以大郡,于是,庾信结束了这段侍读生活。不久,庾信便入侍萧纲东宫,担任抄撰学士之职。早年两度入侍东宫,为庾信日后居于梁代主流文学创作团体之中创造了优势。据倪璠《庾子山年谱》记载,太清二年(548),庾信再度入侍萧纲东宫,担任东宫学士(70)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8页。。从庾信前期诗文创作可以看到,《奉和同泰寺浮图》透露了他与梁皇室的文学交游,此作与萧统《同泰僧正讲诗》、萧纲《望同泰寺浮图》、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以及王训《奉和同泰寺浮图》,均以梁武帝所建同泰寺为创作对象,属同主题创作,这些创作主体均是梁皇室和核心文士集团成员。
庾信从十五岁起,数度入侍梁东宫的经历,使其能深入地参与到梁代的文化核心圈中,从而建构起自身的文学理论主张和文坛盛名。在细致考察庾信早年生平经历的基础上,自然也更能理解庾信对梁王室真挚的情感体认,以及梁亡后所遭受的文化幻灭感。以庾信诗歌为证,《拟咏怀·其六》云:“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倪璠注:“言梁代以国士遇我,有知己之感,不能报也。”(71)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232页。正是他在梁代备受恩遇的真实写照。而《拟连珠》所云:“是以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72)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622—623页。则是梁亡以后,庾信已无所归依的幻灭感、漂泊感与乡关之思。
五
庾信年十五入侍昭明太子东宫,为萧统诸子讲经读书,可称颇具代表性的才子早慧事迹。在庾信早慧事迹的背后,是文化士族密切关注子弟早期教育的时代文化环境。
庾信少时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73)令狐德棻:《周书》,第733页。,除自身颖悟外,自然与家族教育的引导密不可分。当时文化士族对子弟的教育形成了一个有章可循的系统化过程。《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记载:“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7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第143页。可见士族家庭普遍注重教导幼年子弟,令其广泛积累才学根底,随着子弟年岁的增加,对有志者循循善诱,使其具备传承先世之业的能力。翻检梁代史料,王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75)姚思廉:《梁书》,第469页。,陆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76)姚思廉:《梁书》,第724页。,伏挺“七岁通《孝经》《论语》”(77)姚思廉:《梁书》,第719页。等,皆印证了颜之推的言论,反映出如庾信一般天资颖悟者在普遍重视早期教育的氛围中多有涌现。
再就庾氏家族的具体情况来看,庾信的上代均为早慧才士,可见家族尤为重视对子弟的早期培养。父亲庾肩吾八岁能赋诗,两位伯父庾黔娄和庾于陵,前者“少好学,多讲诵《孝经》,未尝失色于人”(78)姚思廉:《梁书》,第650页。,后者七岁能言玄理。由此推知,庾信早年在耳濡目染之间,对家族长辈的思想观念和处世态度定多有学习,也有更多的机会博览典籍、请益学问。少年庾信作为俊迈聪敏的“有志尚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身的理想诉求和文化自信。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所言,“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和“文词高于甲观,楷模生于漳滨”(79)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6页。,分别代表了庾信为人和为文的理想诉求。“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80)许逸民:《庾子山集注》,第104页。,则是他对家族传承与文化自信的双重溯源,这些足以砥砺少年时代的庾信不断前行,并围绕梁代政权上层构筑起个体的价值认知。
庾信年十五入侍东宫的早慧事迹也被后世文人所接纳,使得“庾郎年最少”成为经典的文学意象。李商隐《春游》“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8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第39页。,以及梅尧臣《苏幕遮·草》“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82)周义敢,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第78页。中,“庾郎”当指庾信,之所以称庾信“年最少”,就在于他年仅十五岁已然成名,是历史上早慧才子的典范。由后世文人的接纳来看,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一事的确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要之,本文从宇文逌的序文入手,结合相关的史料以及文学作品,对庾信年十五入侍东宫的材料依据、综合因素以及讲读对象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通过相关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十五岁的庾信凭借出众的才学和良好的德行入侍昭明太子东宫,主要是为萧统诸子讲经读书的。东宫是梁代主流文学的渊源之地,少年时期入侍梁东宫的经历,既造就了庾信的早期文学观念,也为他在梁代文坛的声名传播奠定了基础,更成为他入北后深切追念并反思梁代文化的重要缘由。
在推崇早慧文化的传统社会风气中,历朝历代多见早慧才子的事迹。这些早慧才子中,有善著文章者,有熟诵诗书者,亦有能言善辩者。翻览他们的早年经历,可为传承早慧文化提供启示。庾信十五岁侍梁东宫讲读之事,不仅对庾信的一生影响至深,也恰恰展现了梁王室早期教育的重要形式。择选早慧者为幼年的王室子弟讲读,便于他们建立起“情兼师友”的密切联系,进而稳固文化核心圈的主流力量。如此一来,这种教育形式在帮助幼年子弟增进自身学养的同时,也历练了早慧者的综合能力,形成了良性的文化增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