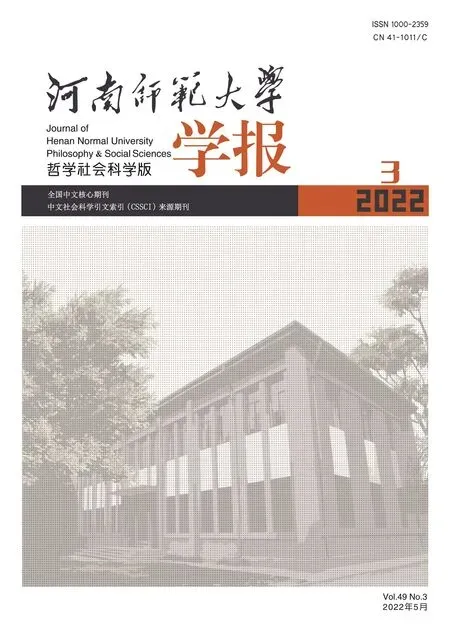“双减”背景下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理念转型与制度优化
张海鹏,张新民
(西南大学 法学院/教育立法研究基地,重庆 400715)
自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规范意见》)以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2021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再次强调,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当前,中央和地方层面的监管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引起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热议。在此背景下,科学厘清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职责,系统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长效机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检视校外培训机构政府监管当前现状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善治理念和清单管理模式就校外培训监管的理念转型与制度优化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培训教育的长效治理有所助益。
一、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考察:以政策文本为中心
我国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且主要以政策文件为依据开展活动。由于地方层面的培训机构治理文件主要系中央政策文件的细化落实,在特色性、创新性等方面尚不明显(1)丁亚东,杨涛:《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特征、问题与展望:基于21个省市政策文本的分析》,《教育与经济》,2019年第6期。,以下分析主要围绕中央层面的政策文件展开。
(一)历史沿革: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三个阶段
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可以发现,我国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以2014年发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及2018年出台《规范意见》为节点,可分为前监管、弱监管及强监管三个阶段。
2014年以前,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有关的政策文件主要围绕学生校内减负、学校有偿补课及学校违规收费展开,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较少。虽有《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的通知》(教基一厅函〔2014〕13号)等文件提及加强培训机构管理、推动培训机构行业自律,并无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具体措施。
2014年开始,在继续规范学校违规补课和乱收费的基础上,学校教师的有偿补课行为成为治理重点,并先后发布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2014〕1号)、《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教师〔2015〕5号)等规范文件。通过切断中小学校和在职教师与校外培训机构的利益牵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招生行为和师资队伍,促使其真正发挥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功能。但该阶段主要以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为监管重点,未能全面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制度体系。基于市场的快速兴起及监管的相对缺位,校外培训机构在此期间迎来了爆炸式增长,随之引发了学生课业压力居高不下、家长经济负担不断增加、学校主流教育遭受干扰、教育均衡公平受到冲击等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以2018年国务院出台《规范意见》为标志,校外培训机构正式进入强监管阶段。与前两阶段相比,该阶段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门政策文件大幅增多(当前主要监管政策文件见表1)。内容层面,围绕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条件、运营要求、配套举措、监管机制等方面建立了全面的制度规范。实践层面,以政策为指引的大规模、高强度专项治理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论从监管文件数量还是监管执法强度来看,2018年《规范意见》尤其是2021年《双减意见》发布以来,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表1 当前主要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政策文件
(二)效果评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分析
总体而言,随着《双减意见》的出台及各地治理行动的大力开展,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从监管思路看,确立了学科培训和非学科培训分类管理的思路,并与校内教育改革协同推进。从监管主体看,成立了专门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并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稳定的监管组织。从监管内容看,围绕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准入、教学内容及日常管理等多个维度制定了全面的政策规范。从监管实效看,各地持续展开的专项治理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大量不合格机构被取缔关闭、中小学教师兼职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与行为不断优化改善。
但另一方面,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仍有完善空间。监管方式上,当前仍主要通过专项治理行动进行集中整治,呈现出运动式、阶段化和选择性特点。监管举措上,当前主要通过设置更高的准入门槛、更细的运营标准、关闭不合格机构等来促使培训机构合规经营,总体上属于以防堵为主的管控模式(2)孙伯龙:《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转型:理论与路径》,《教育学报》,2018年第4期。。监管主体上,仍属于以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的一元治理模式,缺乏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监管制度上,仍存在不具体、不合理、不完备之处(3)李曼,刘熙:《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治理困境与政策应对》,《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7期。。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现代化,应以“双减”政策的发布与实施为背景进一步优化理念与制度,建立统一性、长效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校外培训监管机制(4)薛二勇,李健,张志萍:《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形势、挑战与路径》,《中国电化教育》,2021年第8期。。
二、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理念转型:以善治理念为指引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是否正确认识校外培训教育的功能作用,并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进而在校外培训治理中实现善治。“善治的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页。,其内涵的法治、参与、回应和公正四项要素(6)张镭:《迈向共生型的社会规则交往:善治理念与当代中国社会规则交往模式的更新》,《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3期。可为当前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理念转型提供指引,进一步具体落实到监管依据、监管机制、监管方式及监管重点四个层面。
(一)监管依据:从政策干预到法律主治
当前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立法尚显薄弱。从规范数量看,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密切相关的立法仅有《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三部。这三部立法中涉及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条文为数不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例如,《民办教育促进法》仅在第12条和第26条涉及培训机构的准入审批和培训证书。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则仅在第33、38和41条分别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学校、幼儿园不得与培训机构合作为未成年人提供有偿辅导课程,校外培训机构应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于规范内容言,涉及校外培训监管的立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缺乏明确性与可操作性。例如,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5条将“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纳入民办学校,但《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均主要围绕学历教育民办学校展开,并无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的具体操作性规定。从实践层面看,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主要是依据政策文件开展大规模的专项治理行动。
虽然政策与法律相比更加灵活、高效,但其在科学性、稳定性上难以保证,也缺乏明确的实施保障和评估机制(7)邢会强:《财政政策与财政法》,《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域外实践表明,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日本自1949年颁布《社会教育法》起,便开始将校外培训纳入立法规制范围。培训机构在日本被视为特定的服务性产业由经济产业省负责,通过《特定商业交易法》《地方公务员法》等分散立法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更进一步,分别出台了《私立教育机构设立、经营及课外辅导法》及《补习及进修教育法》,就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立、运营及监管等进行了详细规定。我国校外培训治理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实,尽管依据政策文件的“专项治理”可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但它无法持续、全面、根本地解决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问题(8)周翠萍:《论校外培训机构的特点、问题及定位监管》,《教育科学研究》,2019年第10期。。无论基于法律治理相较于政策治理的比较优势,还是校外培训治理的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均应从政策干预迈向法律主治,形成稳定、持续的常态化监管(9)马佳宏,覃菁:《基于供需偏差分析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探寻》,《现代教育管理》,2018年第11期。。
(二)监管机制:从行政管理到合作治理
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此种行政管制型的监管模式存在成本昂贵、程序繁杂、过于依赖政府部门、难以实现监管创新等局限(10)Richard Stewart. A New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1(1).,不仅面临高额的行政成本,而且难以取得理想的规制效果。因此,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实践中,各国越来越重视充分发挥学校、家长、行业协会等主体的治理功能,力图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合作治理。例如,日本建立了成熟的行业自律机制,由行业协会负责准入审批、培训机构认定、教师资格认定、教学标准设置等重要事项,使其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中扮演重要角色。欧美国家则重视发挥学生及家长的治理作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来实现校外培训行业的市场化调节。
善治的参与要素提倡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不应只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而应是各个监管主体的合力治理,即将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及某些个体融入治理网络中,形成多维互动的监管网络。具体而言,校外培训机构的合作治理既要求各个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还要求政府部门与学校、家长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建立广泛协作关系(11)Mark Bray,Ora Kwo.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for Public Good: Policy Options for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Asia, The Central Printing Press Ltd, 2014,pp.51-62.。政府层面,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涉及课程内容、广告价格、财务税收等多个方面,需要教育、商务、税收等各个部门沟通协作,建立起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学校层面,各级学校可通过提高课程质量、增加课后服务、管理教师兼职等来参与校外培训治理。家长层面,家长通过理性选择培训课程和积极维护自身权益而发挥培训机构治理功能(12)Percy Lai Yin Kwok. Demand Intensity, Market Parameters and Policy Responses towards Demand and Supply of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n China,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2010(1).。社会层面,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还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合作治理模式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在信息搜集、作出决策及行政执法等环节的巨额投入,而且政府的干预更具谦抑性,能在最大限度尊重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维系公共价值(13)Dennis D.Hirsch.The Law and Policy of Online Privacy: Regulation, Self-regulation, or Co-regul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2011(2).,是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必然选择。
(三)监管方式:从管控为主到堵疏结合
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突出审批作用,体现出提高准入门槛、加大惩罚力度等特征,总体上属于以限制和管控为主的模式。但此种以管控为主的监管方式无论在法理依据还是实施效果层面均有局限。一方面,管控为主的监管模式不利于充分发挥培训教育的正面价值。培训教育不仅具有存在的历史和法理基础(14)祁占勇,答喆:《论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当代教育论坛》,2021年第3期。,而且在集聚教育资源、完善教育结构、构建学习型社会、形成人力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5)高博:《民办非学历教育与社区教育合作基础及模式》,《民办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过于严格的管控举措将对培训教育的灵活性、积极性及创造性造成不利影响,阻碍培训教育正面价值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以管控防堵为主的监管方式也难以实现监管的核心目的。当前对培训教育机构进行大力整治的主要动因在于,通过对培训乱象的整治来实现课外补习的“退热”。但“补习热”现象的产生具有来自家长、培训机构、学校及政府等众多主体的多重原因(16)贺武华,娄莹莹:《中国式“影子教育”及其规范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学校教育中工具理性的教育追求、崇尚竞争的教育机制及“考试为主”的教育评价等(17)蒋军营,刘济良:《个体生命卓越性视域下的教育及其建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也是其重要的驱动因素。对培训机构的严格管控并不会影响需求端的补习热情。相反,在课外补习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培训教育机构的减少将可能促使形成以卖方为主导的课外补习市场,反而增加课外补习成本。
善治的回应性要素倡导保持开放的价值理念。(18)周延东:《回应性监管视野下的国际物流安全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2期。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而言,开放就是理性认识校外培训的正面功能与负面效应,实现堵疏结合。日本和韩国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均经历了以管控为主到堵疏结合的发展历程。两国长期的治理实践表明,校外培训的政府监管不应停留于硬性禁止或片面防御层面,而是应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还原其应然价值和本来面目,从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构建良好教育生态(19)周霖,周常稳:《韩国影子教育治理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外国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在对培训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改进偏远地区、困难儿童的学习状况,从而充分发挥校外培训机构的正面功能。我国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也应正视校外培训的双重效应,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四)监管重点:从主体管制到行为规制
当前的校外培训监管呈现出较强的主体管制特性。在准入资格上,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在法人性质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法人,不允许营利性培训机构参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在市场机会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可参与学校的课后服务,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参与。在资本运营上,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引入外资或进行资本运营。
公正是善治的基本要素,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及机会的均等(20)俞可平:《公正与善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主体管制模式侧重于基于主体身份或资格不同,而给予差别化的法律待遇。至于主体的实际行为如何,则不在重点考虑范围。从公正的视角观察,主体管制模式意味着对某类主体赋予特权,并对其余主体限制发展,从而背离自治与平等原则;同时,给予不同身份主体不同的市场进入机会将减少竞争者数量、产生垄断,进而造成消费者损失、背离分配的合理性。因此,符合善治之公正要求的当属于行为规制模式。在此模式下,法律所调整和关注的是主体的具体行为,而非主体的特定身份。事实上,行为规制模式已在域外校外培训监管实践中获得普遍运用。无论日本、韩国还是欧美各国,对校外培训机构准入环节的主体性限制均相对较少,培训教育的公共性主要通过运营环节的监管体系来予以保障。我国的校外培训监管也应实现从主体限制到行为规制的转变,在平等对待各类培训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基于行为内容的动态监管体系。
三、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制度优化:以清单管理为核心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确立政府与市场、社会、学校等主体间的权责边界。在构建政府权责边界的常用制度性工具中,清单管理模式因其权威、直观、简便等特征而备受重视(21)陈向芳:《基于清单管理模式的政府权责边界构建问题研究》,《理论导刊》,2017年第1期。。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明确强调,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在校外培训监管领域引入清单管理,对于明确监管边界、优化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相关立法,建立“制度清单”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清单制度的前提和基础(22)陈升,李兆洋,唐雲:《清单治理的创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4期。。应以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政策为基础,通过政策的法律化程序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构建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制度清单”。一方面,尽快制定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立法。在立法模式上,校外培训机构立法有专项立法和分散立法之分。专项立法模式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通过制定统一的单行法就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立、运营及退出等事项进行明确规定。日本和多数欧美国家则采取分散立法模式,通过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分别予以规制。于我国大陆而言,专项立法模式更为可取。这是因为,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涉及税收、教育、经营、财务诸多方面,专项立法可以克服分散立法的“碎片化”局限,在明确主体职责的基础上统一推进实施。而且,现行政策文件体系可提供良好的规范基础,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制定专项立法具有现实可行性。在立法内容上,可围绕商业和教育两个维度展开。商业层面主要涉及培训机构的行政审批、设立登记、场地安全、广告宣传、信息公开、财务管理等;教育层面主要包括班级人数限制、教师资格要求、教学材料审核等。另一方面,在制定专项立法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其他相关立法。基于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立法的性质与层级,其无法涵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全部规范,而是需要其他相关立法提供配套支持。例如,在《教师法》修订时,应对中小学教师兼职问题予以回应,从而为专项立法中的师资要求提供上位法依据。此外,在公布《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基础上,还应通过规范性文件就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的必须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予以明确,从而强化消费者的权利保障,避免相应纠纷。
(二)厘清监管权限,明确“权责清单”
在完善规范体系、建立制度清单的基础上,应梳理出校外培训监管的“权责清单”。“权力清单”是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精神,梳理出法律赋予的权力事项;而“责任清单”是依据“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精神,梳理出法律要求的责任事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权责清单不仅应包括事项目录,还应该包括与之相对应的事项详单,完整涵盖事项名称、权责主体、权责依据、具体程序、负责机构、业务电话、投诉电话等内容。
厘清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权限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展开。横向层面,应厘清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如前所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涉及课程内容、广告价格、财务税收等多个方面,应首先厘清教育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各个行政部门的具体职责。例如,根据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教育行政机关是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审批机关,主要负责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但无论学科类还是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其均系从事教育服务活动,当其产生纠纷时社会公众也通常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回应。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对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也应具有一定监管权限。纵向层面,应厘清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主要由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负责具体政策的落地实施。但我国地域广阔,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等不同地区校外培训的发展状况不尽一致,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也存在差异。因此,地方政府不应只是国家监管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而是应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上享有一定自主权限,从而在中央与地方监管权限划分上维持一种动态平衡(23)潘冬冬,李佳丽:《教育分权与两岸四地课外补习管理:一个比较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三)降低准入门槛,实行“负面清单”
合理的准入标准对于保障培训教育质量、保护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24)胡天佑:《我国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与治理》,《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但对市场准入予以过度限制,不仅不会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反而导致教育培训产业中产生行业垄断、地区性行政垄断,营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抹杀市场主体的创造力。(25)孙伯龙:《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转型:理论与路径》,《教育学报》,2018年第4期。因此,有必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适度放开、降低准入门槛,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是指仅列举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对于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事项,都属于法律允许的事项”(26)王利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其首先发端于外商投资领域,对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可在总结和吸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校外培训行业健康发展的准入负面清单,并通过法定程序将负面清单纳入法治化轨道。
降低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可从如下方面展开:首先,适当放开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限制。如前所述,当前的校外培训准入政策有限制过度之嫌,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既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法人等。从理论上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人类型与其公益属性并非全然对应,即使是营利性的校外培训机构,其合法经营行为同样具有补充学校教育的功能。保障其公益性的核心不在于设立环节的法人类型选择,而在于实际运营环节的有效规范。(27)张海鹏:《非营利民办学校法人类型再造》,《复旦教育论坛》,2019年第6期。从实践上看,此种模式不一定符合社会的现实需求。例如,一些偏远地区原本并无校外培训机构,一刀切地不审批新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将使这些地方的学生无从获得补充性教育资源。其次,适当降低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要求。开办资金、场所面积等门槛不仅不会令大量的小型培训机构及个体培训老师随之消失,反而可能促使其转入地下经营,使监管变得更加困难(28)Julian Dierkes.Teaching in the Shadow: Operators of Small Shadow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Japan.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2010(11).。因此,在满足日常经营、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可适当降低开办资金和场地面积等准入标准。再次,适度放宽分支机构的审批要求。《规范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在同一县内设立培训点或分支机构必须经过批准。但大型培训机构的教职员工通常在各个教学点灵活调配,让所有教学点都满足统一的准入条件并无必要。为将所有培训机构(含教学点)纳入监管范围,可要求在审批区域外增设教学点必须经过批准,而在审批区域内增设只需备案即可。
(四)健全运营要求,完善“底线清单”
在准入环节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宽进严管”是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必然选择。因此,有必要从招生、收费、教学等方面梳理出校外培训机构在运营环节的行为底线,为其提供明确指引。
域外的校外培训机构立法主要围绕教师资质、场地设施、日常运营等方面建立培训机构行为的“底线清单”(29)Mark Bray,Ora Kwo.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for Public Good: Policy Options for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Asia, The Central Printing Press Ltd, 2014: 35-45.。从内容上看,我国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政策已经涵盖各个方面,但从明确行为底线的角度而言,现行政策仍有完善空间。一方面,现行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不足。例如,实践中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30)孙汝铭:《校外培训机构人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明显增加》,《中国青年报》,2019年8月9日。,但现行政策中缺乏培训教师消极资格的明确规定。有必要贯彻预防式立法理念,建立校外培训教师的行业禁入制度并强化培训机构的入职审核义务(31)孟凡壮,刘玥:《韩国课外辅导机构法律规制探析》,《全球教育展望》,2019年第2期。。又如,现行政策中关于校外培训机构主要人员、收费退费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应进一步充实完善。另一方面,部分现行政策要求过高,具有监管过度之嫌。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不得明显高于当地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线上培训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等政策规定,无论从必要性与可行性上看,均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以现行政策为基础构建法律体系时,应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进一步梳理现行规范,制定出清晰的“底线清单”,使其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又能确保公益底线。换言之,校外培训机构行为底线的设置应在确保公益性基本要求的同时保留一定弹性,从而避免“去监管→危机→严监管”的恶性循环。
四、结语
校外培训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发挥补充学校教育、提供学习机会等正面功能的同时,还带来加重学习负担、侵扰学校教育、损及教育公平等巨大风险,构建有效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刻不容缓。随着《双减意见》及其配套政策的发布实施,我国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在厘清监管思路、建立监管组织、完善监管制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在构建长效的法治化体系方面仍任重道远。有效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必须在理性认识其双重效应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监管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妥当平衡。一方面,应以善治理念为指引,贯彻法治、参与、回应及公正的基本要求,完成迈向追求法律主治、强化合作治理、采取堵疏结合、侧重行为规制的理念转型。另一方面,应引入清单管理模式,借助制度、权责、负面及底线四张清单,通过加强相关立法、厘清监管权限、降低准入门槛、健全运营要求进行制度优化。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长效监管,促进校外培训与学校教育良性共生,保护广大中小学生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