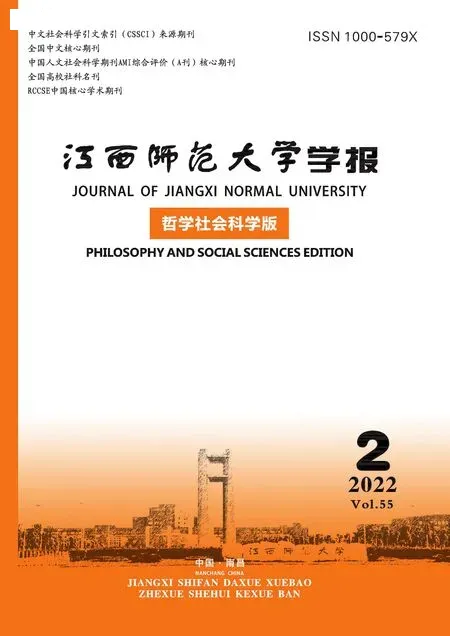述论恽代英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周利生, 周琰培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革命实践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p23)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恽代英以其较高的理论水平,在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学术界普遍认为,恽代英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1)学术界关于恽代英对中国革命理论贡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曾银慧《恽代英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陆巧玲,王智《恽代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及贡献》(《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陶厚勇《恽代英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探析》(《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20年第4期);李孝君《论恽代英早期思想的发展、特点及实践》(《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杨海兰《恽代英的国民革命观》(《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李正兴《恽代英“国民革命”观略述》(《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等等。。本文拟从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革命领导权、革命动力等四个角度论述恽代英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一、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初步阐明“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步入近代社会。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等著作中,抨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指出“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2](p612)。不过,由于时代所限,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作出明确判断。1912年7月,列宁从布鲁塞尔《人民报》阅读到孙中山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后,发表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该文评析孙中山民粹主义思想的同时,指出中国是“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3](p429)。1915年7、8月间,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指明英、俄、法、德、日、美等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瓜分情形,并将中国同土耳其、波斯列入“半殖民地”国家[4](p326)。这里,列宁提出了中国“半殖民地”的概念,但没有具体展开分析,其主要意指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毛泽东曾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p633)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既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明确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界定社会性质,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例如,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中明确认定,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6](p147-148)。随后,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使用“半封建”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土地制度,指出中国享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7](p75)。于此前后,陈独秀于1922年8月在《东方杂志》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分析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现状,认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8](p267);蔡和森于1922年5月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认为,中国政治局面为“半封建的武人政治”[9](p88),后于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10](p795)的国家。这说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逐步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来初步表述中国社会性质。
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认知和思考,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分析。1922年5月,恽代英在泸州商会的演讲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军阀走狗、一切傀儡,统治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使中国变为半殖民地”[11](p201)。这是恽代英第一次使用“半殖民地”的概念。1924年5月,恽代英在一次关于“五九”国耻的演讲中,痛陈中国被西方列强控制的程度,使用“半亡国”指称“半殖民地”。“诸种公营事业,如海关,邮政,铁路等事业之委权于外人的手里”,“中国不啻成为一处半殖民地。也可说是一个半亡国”[12](p361)。针对源于五四运动的反对日本的浪潮,恽代英提醒人们,不仅要“记得日本的二十一条”,还要记得鸦片战争以来受到西方列强威胁“所缔结的各种不公平的片面的条约”,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不仅仅雪了日本所加于我们的耻就算了事,我们也要雪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任何一国所加于我们的耻”[12](p361)。
恽代英通过对封建军阀“卖国式的外交的失策”[12](p358)、“脱离中国统治权的不可思议的外人所建设的国家”[12](p360)、“中国领土权的丧失”[12](p361)、“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底存在”[12](p361)以及“所缔结的各种不公平的片面的条约”[12](p361)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阐释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社会状态。恽代英还发表《华洋贸易册中可注意的事》《庚子赔款与最近政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资产阶级自己供认的剥削成绩——上海社会局发表的纺织业工资统计表》等文章,列举数据和事实,揭示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真实原因及社会现状。例如,恽代英通过对比分析1922年华洋贸易“出入口各种货物”,发现“我们衣食日用之所需,如此仰赖外国”,由此得出结论:“在经济上最剥削我们的,是英美日本三国,而英国为最厉害,最可怕。”[13](p123-125)恽代英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命脉所赖的“海关权完全操在外人手里,自己一些也做不来主”[12](p423)。他在夏令讲演会讲演时悲愤地指出,“香港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枢纽”[14](p249),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等租借地“主权仍属中国不过一句空话而已”[14](p252),这些地方通通“已为外人僭权越法”[14](p256)。此类分析和论断,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对提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二元社会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5](p93)。
除了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之外,恽代英还曾使用“次殖民地”这一术语描述中国社会性质。“次殖民地”的概念来自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1924年2月3日,孙中山在演讲民族主义时提出,中国受到列强人口问题、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重压迫,尤其在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下,“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其国际社会地位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低,其实是一个“次殖民地”国家[16](p345)。恽代英在宣传三民主义时多次使用“次殖民地”,并对“次殖民地”的形成原因进行探析。1925年12月,恽代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批评了戴季陶关于帝国主义由于“人口问题”侵略中国的观点,指出帝国主义“陷中国于次殖民地”的根源是“由于经济问题”[14](p367)。1926年9月,恽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讲义《政治学概论》的第一讲中提出问题“何以说中国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17](p179)?恽代英分析道:“租界、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关税权,以及公使团之威权,都证明中国是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所以说是半殖民地。因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无怜惜地宰割之下,其地位比专做一国的殖民地还不如,故总理又称之为次殖民地。”[17](p181)对于中国“次殖民地”的社会地位及其给予中国民众的迫害,恽代英的认识是清晰的。1926年12月,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别训练班的讲话中指出,“处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不论何阶级,都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其中要以农工们所受的痛苦为最”,农民每至青黄不接时,“总是没有饭吃,易于流为盗匪”,工人“生活上时时发生恐慌”,商人“破产的不知许多”,学生“中途辍学的亦多得很”,因此,农工商学这四种人生活上都是痛苦的,“除革命亦是别无生路可走的”[17](p385-386)。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认为,在中国有的地方如上海,“外人势力的膨胀,我国人事事之无能为力,可说是已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12](p361)。
二、分析中国革命的任务,提出“打倒国内军阀、解除帝国主义的侵掠”
革命任务与社会性质、社会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建党之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两大仇敌。陈独秀提出帝国主义是“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如若“此物不僵”则民无宁日[18](p84);军阀祸国殃民,应“抛弃军国主义”[18](p348)。李大钊称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强盗世界”,是“我们的仇敌”,提出要“改造强盗世界”[19](p459);称皇帝、贵族及军阀等为“历史上残余的东西”,提出“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19](p367)。这些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共二大在分析中国社会状况时指出,“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是加给中国人民的最大痛苦[6](p132),并制定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20](p62),即党的最低纲领。
然而,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在当时遭遇到了“好人政府”“联省自治”“废督裁兵”“制宪救国”等各种论调的反对和攻击。比如,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直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极力鼓吹“武力统一”,而各省地方军阀为自身利益强烈要求“联省自治”;一些改良主义者以为无须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改变国家的现状只需要建立所谓的“好人”政府。胡适就将反对帝国主义称之为“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声称“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21],“尽可以不必去做哪怕国际侵略的噩梦”[21]。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以〔与〕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22](p539-540)。
恽代英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发表文章对此类错误论调予以批判。他指出,废督裁兵论如同“向老虎作揖,请他宁忍着饿肚子,莫要吃人”一样没有研究价值,制定国宪省宪因“没有威权为后盾”也必将陷入失败,以和平之法办新村的努力“绝没有圆满成功的希冀”,主张好人政府但没有“各方面的威权为后盾”终只能是纸上谈兵[13](p38-39)。恽代英坚定认为,在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存群雄争长的局面下,这些都是“不切实的言论”,中国的出路在于“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13](p37-43)。恽代英指出,“我们要打倒这一切”,“要扑灭武人的专政”[13](p126);“我们一定要拥护革命的势力,建设人民的政府”,“中国的各种危险与紊乱,才可以得着他的救济”[12](p270)。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恽代英就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理念。针对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恽代英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他起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并发表于《大汉报》,宣言书指出,“公理既未昌明,杀机总未可免,宁得罪此假托人道的诸强”,“勇猛力争,毫无所用其畏怯者也”[23](p16)。1919年10月8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这打破军阀的功夫,亦是有了奋斗的决心”[23](p314)。恽代英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行径极为愤恨,具有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救国之志。
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后,恽代英以多种方式大力宣扬。1923年10月14日,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制定的九条纲领中提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军阀肃清政局”[13](p97-98)。1924年6月底,恽代英向民众演讲时指出,我们挽救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打倒国内军阀,(二)解除帝国主义的侵掠。”[12](p429)《国民革命》一书是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的政治讲义。恽代英在这本讲义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四大压迫中国民众势力的可恶面目,提出:“我们应当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同时并要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得着解放。”[17](p212)恽代英始终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即便面临国民党右派的诬蔑和打击,他仍宣称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17](p20)。
三、分析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阐明“中国无产阶级站在领导革命的地位”
无产阶级领导权指的是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针对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尚未取得彻底的胜利时就希望“赶快结束革命”的状况,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24](p199)。俄国革命时期,孟什维克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对此,列宁批评道,“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25](p81),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担负着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的积极的任务”[26](p367)。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立场,但是并没有深入到“如何领导”的具体问题之中。[27](p53)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中共三大一方面认定国民党存在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革命和忽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两个错误的观念”,另一方面又认为国民党应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并立在领袖地位[6](p276-277)。1924年8月,陈独秀发表文章仍然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28](p112)。直到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提出,中国革命发生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革命性质既是“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7](p222),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无产阶级参加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胜利[7](p219)。不过,中共四大前后,党内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天然领导权”观点。彭述之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认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29](p184-187)。这一观点在肯定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同时,没有认清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严重事实,实际等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恽代英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领导作用非常重视。1923年6月,党在酝酿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恽代英在一封书信中就明确提出,未来的民主联合战线中“须完全注意于为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13](p83)。中共四大前夕,恽代英以“代英”“但一”等笔名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苏俄与世界革命》《苏俄与中国革命运动》等文章,高度评价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建设中伟力,批评国民党“不愿有许多农工群众来拥护”,号召中国青年应该向俄国革命学习[12](p569)。
中共四大结束以后,恽代英重视贯彻落实党的决议,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也更加清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大通过的决议,接受了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的观点,指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不妥协地站在第一道火线上面,为他们自己,而且为全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奋斗”[7](p276)。对此,恽代英表示高度赞赏,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丝毫不摇动的与帝国主义为彻底的战斗”[14](p18),且“只有越是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有把握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14](p18)。其后,恽代英多次提到并阐释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1925年3月,恽代英发表文章称:“我们知道中国的民族革命,只有新式产业下的无产阶级有领导他的力量。”[14](p55)1927年2月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时,恽代英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说明‘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上的地位,证明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力量。”[30](p39)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恽代英一方面肯定“中国无产阶级站在领导革命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30](p171),“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17](p11);另一方面认识到必须争夺领导权,而根本办法是解决好劳动群众的利益问题,无产阶级政党要“站在工人农民本身利益的立脚点上,领导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7](p56),广大的共产党员“要能够到各种有群众的机关中间去组织一个核心,注意本机关中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宣传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起来奋斗,而且自己站在前线上面领导他们奋斗”[17](p348)!这些思想无疑是非常宝贵的。
革命领导权需要争夺才能获得,中国共产党人对反动思潮必须进行批驳,这正是恽代英理论水平的优势所在。针对国民党右派散布的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目的是促进国民革命,“帮助国民党,督促国民党,早些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12](p456)。针对国家主义派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恽代英指出:“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14](p89)针对戴季陶提出“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2)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58068部队印刷所,1982年,第195页。,反对阶级斗争,并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寄生政策,“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31](p816),恽代英发表文章《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指出:“有人说阶级争斗是人们提倡起来的,以为是马克思发明出来的,实则阶级斗争是几千年来的事实,马克思不过将他说明罢了。”[17](p135)
四、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提出“我们的势力根基在工农身上”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列宁曾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32](p151)1922年6月,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发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明确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提出,改造旧社会既不能单靠个人的力量,也不能靠贵族、资本家及武人的力量,“群众的集合”才是改造旧社会“唯一的武器”,“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13](p25-30)。具体到国民革命的动力,恽代英分析指出,“国民革命是靠全体国民,特别是靠那些穷苦被压迫的民众”[12](p508),“只有组织群众才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实力,而且果能组织群众,亦一定可以打倒帝国主义”[14](p222)。而且恽代英将这些认识上升到唯物史观的高度,提出:“我们应研究唯物史观的道理,唤起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厉害的群众,并唤起最能对他们表同情的人,使他们联合起来,向掠夺阶级战斗。”[13](p31)因而,他号召青年“研究唯物史观,以发现历史进化必要的条件”[13](p32)。恽代英的这些论述,“一方面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另一方面也表明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杠杆的思想”[33](p103)。
恽代英革命活动的早期,主要与青年学生打交道。他认为,“只有青年学生,是纯洁而勇敢的反抗恶势力的生力军”,学生活动是“改造社会的先锋队”和“改造社会的生力军”[13](p49-51)。随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舞台上作用的进一步彰显,恽代英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日益成熟,对革命基本动力的分析也日趋准确,认识到学生“易趋向革命,但浪漫而摇动”[17](p479),提出“中国不会是我们几个学生所能救治的,我们必须农工平民大家都站起来”[12](p304)。恽代英认为,农民“生活极苦,故稍加宣传即易加入革命战线”,工人“因生活苦而所受压迫直接易见,故易加入革命战线”,因此“我们的势力根基在工农身上”[17](p479-480)。1924年4月,恽代英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分析了各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他指出:智识阶级“虽然有时候特别肯为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努力”,但“他们自己没有经济上的地位”;“虽然他们在恶劣的政治经济中间,亦要受许多窘迫,然而他们并不一定与统治阶级的利害相冲突”,因此,智识阶级是“不能倚赖”的[12](p256)。至于商人阶级,他们的“利益已经与外国势力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不感觉革命的需要”,显然是“不可倚赖”的[12](p257)。“没有革命的力量”的俸给阶级“不敢有任何异志”,“靠他们革命,是不会有希望的事”[12](p257)。绅士阶级则是“军阀官僚的鹰犬爪牙”,“想靠他们为民众努力以反抗军阀官僚,这又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痴想”[12](p257)。工人和农民深受“赔款的横索,外债的滥借,国帑的浪费中饱”等毒害,“濒于破产危殆之境,他们没有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妥协调和的余地”[12](p258),因此,“我们须先把革命势力,建筑在工人农人身上,或者建筑在确愿献身为工人农人利益而奋斗的兵匪游民身上”[12](p262)。
将“兵匪游民”作为革命动力,是恽代英独特的理论思考。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都曾分析过游民的问题,认为游民是兵匪的来源。但是,他们对游民的“革命性”的一面认识不足,甚至认为游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群众上不甚重要”[29](p191)。恽代英则认为,游民产生的根源是受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解决游民问题的方法是“使他们与农工结合,而且使他们将来有化为农工的机会”[12](p262),因此游民可以成为“革命的大力量”[12](p125)。为了发动游民起来参加革命,必须要解决他们生存问题,满足其利益,制定“切实为农工游民等谋利益的主张与计划”,同时“能用合当的宣传方法,使他们信服而谅解”[12](p125)。因此,“革命政府必须侧重农工游民乃至其他方面的利益”,“以唤起多数国民的参加革命行动”[12](p126)。恽代英甚至提出了通过“拨款经营移殖开垦事业”以及“经营大工商业”等具体措施[12](p127),安置游民,解决其生产生活问题。这些观点为党的四大所认同,中共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20](p333)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34](p1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的一员,以丰富的社会实践和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动力的探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这些认识既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展示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