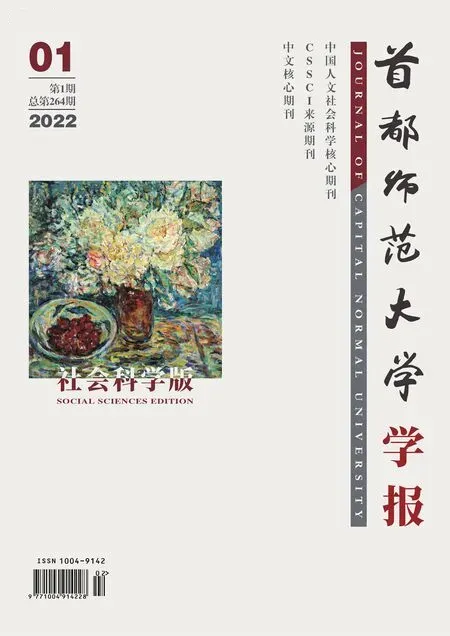追赠恩荣:汉魏晋南北朝丧葬仪制吉凶相参的历史演变
王 铭
在中国古代的礼制传统中,从礼经到礼典,丧葬礼是一项具有规范人伦亲疏意义的根本性礼仪。在吉、凶、军、嘉、宾五礼体系中,凶礼亦首重丧礼。凶礼包括几种不同的礼仪,按《周礼·春官·大宗伯》所云:“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①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春官·大宗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759页上栏—下栏。处理死亡之事的丧葬礼被归属于凶礼,并且往往被视为大凶之礼,无疑属于凶礼之中最为重要者,在整个五礼体系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近二十年来,中古礼制研究成为学界一大热点领域,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渐次出现。梁满仓细致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礼制的“五礼制度化”进程,凶礼即是一个重要的着眼点①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八章《魏晋南北朝的凶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662页。。专就中古时期的丧葬礼研究而论,成果最丰者当数吴丽娱,她以唐代礼典与唐《丧葬令》为重心,系统讨论了中古丧葬礼令制度的变化,提供了综合性的理解与细致的分析②吴丽娱关于中古丧葬礼制的一系列研究论文,集于氏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上、下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吴丽娱注意到西晋及陈朝关于丧葬礼吉凶问题的争论与唐代的《大唐元陵仪注》之间的渊源关系③吴丽娱:《再造“国恤”——试论〈大唐元陵仪注〉的礼仪来源》,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3页。,只是未及讨论丧葬吉凶问题在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演变、内容及其意义。漥添庆文已注意到汉代葬礼“吉凶卤簿”中容车、柩车分别作为吉驾、凶驾的区分④窪添慶文:《中国の喪葬儀礼——汉代の皇帝の儀礼を中心に》,《東アジアにおナる儀礼と国家》,東京學生社1982年版,第89-90页。。刘可维根据郑玄、孔颖达等汉唐经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注疏,认为将葬仪中的车舆划分为吉、凶两类的礼制基础源于《礼记》《仪礼》所载理想化儒家凶礼中的用车制度,汉代以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礼仪继承吉凶车驾、卤簿制度,唐代从皇帝至一般官员的送葬礼仪中均明确规定吉凶车驾、卤簿等使用⑤刘可维:《汉唐间皇帝葬仪中所见吉凶仪式初探》,《第四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论文集》,上海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7月,第438-454页。。刘可维还从葬仪“殊礼”的角度,讨论了汉魏晋南北朝葬礼中的吉凶卤簿相关仪制,勾勒甚为细致⑥刘可维:《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殊礼”的形成与变迁》,《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笔者亦曾初步讨论中古丧葬车舆的等级性和下移问题,以及居于丧葬礼吉卤簿中心的魂车问题⑦拙文《辇舆威仪:唐宋葬礼车舆仪制的等级性与世俗化》,《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魂衣与魂车》,《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从《礼记》等儒家经典规范来说,礼经中有着鲜明的“吉凶不相干”的原则⑧《礼记·丧服四制》云:“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唐代孔颖达正义:“吉凶异道者,言吉凶各异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3《丧服四制》,《十三经注疏》,第1694页下栏—1695上栏。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丧服》:“凶服不敢入公门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门’。”见《白虎通德论》卷10《丧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下栏。《礼记·杂记下》“麻者不绅,执玉不麻,麻不加于采”一句,郑玄注云:“吉凶不相干也。”见《礼记正义》卷43《杂记下》,《十三经注疏》,第1566页上栏—中栏。在东汉班固、郑玄以来诸学者的描述中,即将《礼记·丧服》所说的“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的礼经原则简化为“吉凶不相干”之语,成为后世经学家在辩驳吉凶礼制时反复征引的一条基本原则。关于中古丧葬礼吉凶问题的经学思想观念及其变化,笔者另文详论。。虽然丧葬礼在“五礼”中归属于凶礼,但中古丧葬礼在操作性的具体仪制上,如丧葬仪制中的卤簿、车舆、旌旗、仪服等“物化礼乐”方面⑨杨英在讨论“仪注”时,将车舆、冕服、雅乐等仪制视为“物化礼乐”。见杨英:《北魏仪注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9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8-181页。,却能发现诸多属吉的仪制成分。丧葬中的“吉凶卤簿”即是包含吉驾、凶驾在内的分别体现吉与凶两重属性的仪仗器物,同时出现在重臣勋戚的葬礼仪制中。在中古丧葬礼这样的大凶之礼中却兼采吉、凶两类完全不同属性的卤簿形式,那么我们希望追问的是,其间的仪制吉凶相参是如何在礼经原则之外渐次在礼仪实践中扩展的?这一问题饶为有趣,值得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亦涉及到中古丧葬礼在象征观念中使居于丧葬礼核心位置的亡魂完成由凶到吉的转化的关键性仪制,因而对于研究中古丧葬信仰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拟从丧葬仪制所包含的吉、凶两种属性的物化礼乐角度出发,针对中古时期丧葬礼的吉凶相参仪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加以考察,并阐释其背后的丧葬亡魂观念与社会影响过程。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作为“汉魏故事”的葬礼吉卤簿
在秦汉时期,车舆已成为天子卤簿中的主体部分①关于秦汉时期的车舆制度,可参见张仲立:《关于卤簿制度的几点研究——兼论周五路乘舆制度特点》,《文博》1994年第6期;李润桃:《〈史记〉车舆类名物词与秦汉车制》,《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后汉书·舆服志》载:“汉承秦制,御为乘舆。”②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29《舆服志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43页。秦汉相沿的制度中的乘舆,特指的是天子车驾,如《新书·等齐》即云:“天子车曰乘舆。”③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1《等齐》,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页。乘舆原为天子所乘之车辂,后为表示对天子的敬畏,直接以乘舆借代天子④蔡邕《独断》卷上:“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页。,因此其仪制等级至高无上,具有垄断性。天子乘舆还进一步从车驾扩展到配套仪制,东汉蔡邕《独断》云:“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⑤《独断》卷上,第1页。可见东汉之时,乘舆之制已不仅包括天子车舆,还可以包括为天子出行而准备的一系列配套仪制如衣服、器械、百物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配套仪制在后来的丧葬卤簿中同样渐次出现,并被吉、凶两重属性所渗透,形成中古葬礼中的吉卤簿与凶卤簿。可以说,车舆仪制是中古葬礼吉凶卤簿的首要来源。
自西汉开始,一部分天子乘舆之制被赐用于重臣勋戚葬礼,其中车舆与凶卤簿的结合在相关丧葬仪制中出现最早。史籍所见最早的先例是霍光与孔光。《汉书·霍光传》记载勋戚霍光的丧葬仪制:“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⑥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48页。《汉书·孔光传》记载重臣孔光的丧葬仪制:“载以乘舆辒辌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余两,道路皆举音以过丧。”⑦《汉书》卷81《孔光传》,第3364页。西汉朝廷以象征天子仪制的东园秘器、辒辌车、黄屋左纛等乘舆仪制给霍光、孔光送葬,以示哀荣优抚,道路上亦放声喧呼。从汉代开始,在极少数拥有特殊地位的贵臣或诸侯王死后,皇帝赐以多种形式的“殊礼”,超越了一般“臣”的礼制规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准皇帝”的礼仪标准⑧刘可维:《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殊礼”的形成与变迁》,《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其具体仪制虽不如后来繁复多样,却是以乘舆卤簿赠予官员葬礼的历史先声,成为此后中古时期重要官员葬礼吉卤簿可以追溯的最早成例。
礼经的“吉凶不相干”原则,在东汉礼制皇帝大丧中也得到了强调。《后汉书·舆服志》载:“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既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皆不得入城门。当用,太仆考工乃内饰治,礼吉凶不相干也。”⑨《后汉书》志第29《舆服志上》,第3651页。这正是处理皇帝大丧的大行礼中所使用的相关车舆,同样强调“吉凶不相干”原则,并已被落实到了朝廷礼制之中。此时的丧葬相关车舆还只是装饰较为低调的凶驾,故未及触发对于葬礼吉凶相干的议论。
到东汉的丧葬礼中,其他的吉卤簿与鼓吹开始出现。东汉明帝以后,卤簿驾仪已非“天子”专属,已正式用于皇后、太后这一级别的“大丧”,而次一等的“法驾卤簿”在汉灵帝时已用于大臣杨赐之丧,可见卤簿车驾仪制已经彻底松绑⑩陈惠玲:《两晋荒礼礼情之观察》,《台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07年第3期。。《后汉书·杨赐传》载中平二年(185)杨震之孙杨赐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赠东园梓器禭服……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公卿已下会葬”[11]《后汉书》卷54《杨赐传》,第1785页。。可见鼓吹在东汉后期的重臣葬礼中出现,且有前后部鼓吹与法驾伴行,与东园秘器等御用凶驾一起送丧。陈惠玲认为,东汉凡“太皇太后、太后、皇后、诸侯王”都有法驾卤簿,并且丧葬亦比照办理,史不书常例,唯殊礼尊崇之特例载之;“列侯”虽没有卤簿,但可申请,以备威仪。凡有卤簿者,生事用之称“吉事卤簿”,如用于婚仪或出行;丧事用之称“凶事卤簿”,用于送葬,卤簿有吉凶乃依“事死犹生”之理①陈惠玲:《两晋荒礼礼情之观察》,《台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07年第3期。。也就是说,原来作为吉礼场合出现的代表等级身份的卤簿被借用到凶礼丧葬情境之中,并产生了专门的葬礼吉卤簿之称,与之相对的则是凶卤簿,两者合称为“吉凶卤簿”。吉卤簿在重臣丧葬礼中的优抚借用,与凶卤簿同时出现,实际在礼仪操作实践中与丧葬礼“吉凶不相干”原则呈现不同的面貌,正是此后中古丧葬仪制同时参用吉凶卤簿的源头。
到了汉魏之际,吉凶卤簿与鼓吹用于诸王重臣丧葬礼。曹魏文帝为任城王曹彰举办葬礼,“至葬,赐銮辂、龙旂,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②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19《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6页。。在晋代礼仪文献的回溯中,将葬礼殊礼的成例称为“汉魏故事”。《晋书·礼志》“凶礼”条载:“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以鼓吹。”③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0《礼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26页。“故事”即旧事,是本朝或先王的已行之事,汉、魏、晋三朝遇有重大之事时多援引故事以寻求经典依据,晋时将典型故事修定汇编与律令并行,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④吕丽:《汉魏晋“故事”辩析》,《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魏晋南北朝时“故事”的来源甚广,经典、先代本朝制度、方针政策、君臣理事、少数民族首领割据之事、旧俗等均可成为故事⑤李秀芳:《魏晋南北朝“故事”考述》,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丧葬礼方面的“故事”尤其如此。殊礼本身意味着超越了一般制度的礼遇,因此殊礼的标准并非依据既定的礼仪或法律,而是以“故事”即前代人物的事例为准⑥刘可维:《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殊礼”的形成与变迁》,《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因此,这种“故事”实际上是对于重臣勋戚的一种优遇与恩荣,成为一种特别的成例。故事学成为晋唐间礼制建设的重要范畴,中古礼因故事之学的加入而在礼义层面呈现出不同于先秦礼文化的一面,并对后者有所补充⑦闫宁:《中古礼制建设概论:仪注学、故事学与礼官系统》,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在东汉、曹魏、西晋接连“禅代”的政治话语环境中⑧汉魏禅代“故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以较小的社会动荡代价重建一个合法政权,奠定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模式,中古各朝纷纷效仿。参见杨英:《曹操“魏公”之封与汉魏禅代“故事”——兼论汉魏封爵制度之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汉魏故事”在礼仪方面更是具备了政治文化上的合法性意义,故而丧葬吉凶卤簿鼓吹成为朝廷着意优抚重臣、收揽人心的有效政治举措,亦成为对重臣身后尊荣的一种超规格展示。
二、晋代重臣葬礼吉卤簿鼓吹的除与复
西晋时期在礼制上基本确立了丧葬礼作为凶礼的地位。《晋书·礼志》云:“五礼之别,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则养,死则哀,故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者也。”⑨《晋书》卷20《礼志中》,第613页。魏晋之际,五礼制度化进程大大推进,丧葬礼作为大凶之礼的地位日益奠定。把治丧、丧葬、丧服等仪统称为凶礼,这也是五礼制度确立并实践的标志⑩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在西晋时期,可以看到更多史料,诸臣对丧葬礼仪进行细节关注与原则议定。
由于作为大凶之礼的丧葬礼实际运作中往往掺杂着诸多属吉的成分,西晋时期对于丧葬礼中是否应该加入相关吉卤簿有了不同的理解。《晋书·礼志》载:“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11]《晋书》卷19《礼志上》,第581页。萧子显撰《南齐书》卷9《礼志上》称之为《晋礼》,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17页。西晋初期荀顗制定《新礼》,一个重要的思路是按照礼经的丧礼皆尽从凶的观念,将吉驾卤簿、凶服鼓吹从丧葬礼制中废除不用,此即《通典·礼典》所引的“按礼,天子七月葬。新议曰:‘礼无吉驾象生之饰,四海遏密八音,岂有释其缞绖以服玄黄黼黻哉!虽于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称矣。辄除鼓吹吉驾卤簿。’”①杜佑:《通典》卷79《凶礼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43页;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67《孙毓》“驳卞搉武帝丧礼议”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848页下栏。荀顗试图让丧葬礼完全归之于凶礼,改变曹魏礼仪吉凶相干的面貌,故而去除掉丧葬礼中所有属吉的仪制。此时五礼制度尚不成熟,这虽然是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可由于矫枉过正和不符实际需要,在实行过程中并不顺利②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页。。
到了西晋中期,挚虞重议西晋初期荀顗制定的《新礼》,对其作出了损益,并将“汉魏故事”的葬礼设吉凶卤簿以朝廷诏令形式予以批准实行。这是西晋朝廷对之前葬礼吉凶相参的实际情况加以正式认可,并以修订新礼的形式固定下来。此详见于《晋书·礼志》“凶礼”条载:
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以鼓吹。新礼以礼无吉驾导从之文,臣子不宜释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驾卤簿。又,凶事无乐,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挚虞以为:“葬有祥车旷左,则今之容车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还。《春秋传》,郑大夫公孙虿卒,天子追赐大路,使以行。《士丧礼》,葬有稾车乘车,以载生之服。此皆不唯载柩,兼有吉驾之明文也。既设吉驾,则宜有导从,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义。臣子衰麻不得为身而释,以为君父则无不可。《顾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礼设吉服导从如旧,其凶服鼓吹宜除。”诏从之。③《晋书》卷20《礼志中》,第626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8《乐二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97页下栏。
《通典·礼典》所引此条史料记载,其上并有孙毓的意见称:“《尚书·顾命》,(周)成王新崩,传遗命,文物权用吉礼。又礼,卜家占宅朝服。推此无不吉服也。又巾车饰遣车,及葬,执盖从,方相玄衣朱裳,此卤簿所依出也。今之吉驾,亦象生之义,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设而不作。”④《通典》卷79《凶礼一》,第2143页。可见孙毓认为葬礼中亦可用吉服。虽说鼓吹宜除,但所除者只是限于凶服鼓吹,而鼓吹吉服可以设而不作,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将鼓吹除去,仍然在丧葬队伍象生的吉驾卤簿之中保留了吉服鼓吹,当然,由于鼓吹属吉,故在凶礼中不宜发出乐音。孙毓将大丧使用吉服的旧例追溯到了《尚书》所记载的周成王时代,这不无托古之嫌,不过他认为葬礼中的华盖簇拥导从、方相引导开路都可以视为丧葬卤簿的来源,这一点则基本不误,实际上都可以认为是物化礼乐的内容⑤关于中古丧葬礼出殡时导夫先路的方相仪制,参见拙文《开路神君:中国古代葬仪方相的形制与角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拙文《中古丧葬方相、魌头礼制等级考论》,《中国中古史研究》第11期,兰台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187页。。这条材料在北宋初年的《太平御览》中引录为:“挚虞《新礼仪志》曰:‘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鼓吹。新礼以礼吉事无凶,(凶)事无乐,宜除吉卤簿、凶服鼓吹。虞按:礼,葬有客车郎,吉驾之明文也。’”⑥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567《乐部五》“鼓吹乐”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版,第2563页上栏。其中的“客车郎”当为“容车郎”之讹,意指为容车(即魂车)服务的导从人员⑦关于容车或魂车的讨论,参见拙文《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魂衣与魂车》,《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漥添庆文认为,这里所说的“吉凶卤簿”即指以容车和柩车为中心构成的送葬仪式,其中容车为吉驾,柩车为凶驾⑧窪添慶文:《中国の喪葬儀礼——汉代の皇帝の儀礼を中心に》,《東アジアにおナる儀礼と国家》,第89-90页。。挚虞所谓“此皆不唯载柩,兼有吉驾之明文也”,可见丧葬队伍中有载尸的柩车之外,亦有导从的吉驾,两者正是在车舆仪制上凶、吉二分,实际上柩车是凶卤簿的中心车舆,而容车(魂车)是吉卤簿的中心车舆。吉凶卤簿与鼓吹在此时的丧葬仪制中充分展现出来。
可见,西晋时期往复争议的是吉卤簿鼓吹是否应该参入丧葬礼,并给予相应的解释。挚虞所谓“新礼以礼吉事无凶,(凶)事无乐”,仍是出于礼经所说的“吉凶不相干”原则,故而认为不应在丧葬礼中加入属吉成分的音乐鼓吹,因此宜除吉卤簿、凶服鼓吹。西晋初期荀顗新礼“以礼无吉驾导从之文,臣子不宜释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凶服之鼓吹”,而西晋中期挚虞以为“宜定新礼设吉服导从如旧,其凶服鼓吹宜除”,说明挚虞改定新礼中的丧葬仪制,将其中吉驾卤簿、吉服导从归复到汉魏旧制,只是凶服鼓吹按照荀顗新礼除去,但吉服鼓吹仍予保留,在葬礼吉驾中设而不作。
西晋两次修礼对待丧葬鼓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西晋朝廷礼仪改革的思路变化有关。从西晋初期荀顗主持修订的《新礼》实行了二十七年,直到西晋中期挚虞再次修改新礼,自此后按此新礼实行①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57页。。挚虞修订五礼制度所集新礼亦被称为《新礼仪志》②挚虞此书已佚,《太平御览》卷567所引称之为“挚虞《新礼仪志》”,第2563页上栏。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卷90《礼仪部十一》所引称之为“挚虞《新礼仪》”。四库全书本第8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页下栏。,在此问题上是又向更旧的礼制回归,认为基于葬礼中的容车(魂车)是吉驾,那么亦应配置吉仗卤簿作为相应的导从。故挚虞改革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思路,仍是将属吉的卤簿仪制复参入丧葬礼之中。挚虞在此问题上向“汉魏故事”复归,重新恢复了一度被荀顗建议废置的葬礼吉卤簿并将之规范化,且将之与容车吉驾的观念联系起来,成为后世葬礼吉凶卤簿制度的一个基本原点,后来一直没有被动摇过。在挚虞的改革中,葬礼吉卤簿是由吉服人员导从的,而这一条又成为后来陈朝时争议的一个关键点,下文将作详论。不过,对于凶服鼓吹这个问题的处理,挚虞仍是同意了荀顗的意见,认为应该坚持凶事无乐的原则,将八音都从丧葬礼中除去。但是,因吉驾卤薄中包含有鼓吹乐,所以挚虞对五礼的修订确定了鼓吹乐在凶礼中的使用③刘斌:《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上)》,《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7年第1期。,吉服鼓吹仍在葬礼吉驾卤簿中得到了保留,成为后来南朝依据的殊礼定例。
东晋初年,晋元帝之子琅邪悼王司马焕年方二岁即薨,“帝悼念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琅邪国右常侍孙霄上疏谏曰:“棺椁舆服旒翣之属,礼典旧制,不可废阙。”④《晋书》卷64《元四王传》,第1729页。其中所备的物化礼乐即有吉、凶卤簿,除凶门柏历、棺椁属凶之外,吉驾车舆、吉仪服、旌旒、扇翣均为葬礼中属吉的仪制,已被认为是在殊礼丧葬中不可或缺,可见成例的影响之深。
三、南北朝重臣葬礼吉卤簿的扩大化与规范化
南北朝葬礼中的吉卤簿,进一步融入了纷繁复杂的车舆、旌旗、伞盖、仪服、羽葆鼓吹等诸多仪制于一体,成为朝廷旌表死者身后崇高地位的常例。其中尤以鸾辂、凶旒、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等为此一时代卤簿的典型特点。
随着五礼制度化的日益推进,南朝包括黄屋左纛、鸾辂九旒、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等天子卤簿亦常被赐给皇室、诸侯王送葬,以彰显身后哀荣,并形成新的“故事”。《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载,刘宋大明六年(462),宣贵妃“葬给辒辌车,虎贲、班剑,銮辂九旒,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上自临南掖门,临过丧车,悲不自胜,左右莫不感动”⑤沈约:《宋书》卷80《孝武十四王·始平孝敬王子鸾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63页。。辒辌车、黄屋左纛、銮(鸾)辂、九旒原是天子车舆、旌旗,赐给皇妃葬礼,形成标识皇家规格的“故事”。辒辌车自西汉以降是一种运送皇帝棺椁的四轮柩车,而鸾辂实际是一辆用作准皇帝制度的容车,即与柩车相对的吉驾⑥刘可维:《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殊礼”的形成与变迁》,《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九旒作为旌旗仪制亦被纳入葬礼吉卤簿序列之中,说明了葬礼吉卤簿仪制的进一步扩大。羽葆是一种以鸟羽聚于柄头如盖的仪制,常与鼓吹组合形成最高等级的仪制,即为“羽葆鼓吹”。《南齐书·海陵王纪》载南齐建武元年(494)十一月海陵王殒,“给温明秘器,衣一袭,敛以衮冕之服。大鸿胪监护丧事。葬给辒辌车,九旒大辂,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东海王故事”①《南齐书》卷5《海陵王纪》,第80页。。可见亦是沿用“故事”成例。《陈书·衡阳献王昌传》载:陈朝天嘉元年(560)“四月庚寅,丧柩至京师,上亲出临哭。……给东园温明秘器,九旒銮辂,黄屋左纛,武(虎)贲班剑百人,辒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葬送之仪,一依汉东平宪王、齐豫章文献王故事”②姚思廉:《陈书》卷14《衡阳献王昌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09页。。这些仪制所依据者仍为前朝诸王“故事”,相沿成例而渐成一套较复杂的葬礼吉凶卤簿仪制。
南北朝时期亦有重臣生前享有羽葆鼓吹,在其死后又追赐羽葆鼓吹、班剑等仪仗。梁满仓指出,南朝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军礼鼓吹制度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将领死后被赠武职和鼓吹屡见不鲜,这是对死者生前军功的表彰,并通过表彰死者来激励生者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南齐王俭殁后,朝廷“追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斑剑为六十人”。张铣注:“羽葆、斑剑,并葬之仪卫。”④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46任昉《王文宪集序》,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1987年版,第879页下栏—第880页上栏。可见原来专属于天子的卤簿仪制羽葆鼓吹、班剑,常在高级贵族葬礼中赐用,分别指代卤簿伞盖、鼓吹、仪卫。班剑成为高等级葬礼吉卤簿中具有鲜明仪卫性质的仪制,使葬礼更具威严感和震慑力。《梁书·太祖五王传》载南朝梁始兴忠武王萧憺“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时年四十五。追赠侍中、司徒、骠骑将军。给班剑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⑤姚思廉:《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55页。。临川靖惠王萧宏于普通七年(526)四月薨,朝廷“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剑为六十人。给温明秘器,敛以衮服”⑥《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第341页。。北魏孝文帝礼制改革,丧葬制度亦多吸收汉魏西晋“故事”,融合南朝丧制⑦金爱秀:《北魏丧葬制度探讨》,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如太和十七年(493)重臣尉元薨,朝廷“葬以殊礼,给羽葆鼓吹、假黄钺、班剑四十人,赐帛一千匹”⑧魏收:《魏书》卷50《尉元传》,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30页。。
从葬礼吉卤簿的发展脉络来看,西汉时期的重臣丧事中所设吉凶卤簿还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只是辒辌车、黄屋左纛与道路举音。而汉魏之际以来鼓吹在丧葬礼中广泛应用,虽是设而不作,仍说明了吉仗仪制在丧葬凶礼中的进一步渗透。降至南北朝,葬仪中所用“殊礼”主要包括有辒辌车、黄屋左纛、鸾辂、龙旂九旒、虎贲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等车舆仪仗,这些“殊礼”的下赐均溯源自西汉霍光以及东汉诸侯王的葬礼故事,但经过了西晋朝的整理与改造,又为东晋南北朝所继承⑨刘可维:《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殊礼”的形成与变迁》,《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实际上,丧葬吉卤簿的渗透参入也是从这些方面着手的,可见卤簿制度演变与丧葬礼仪之间的特殊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丧葬礼变成了皇家诸侯王、勋戚重臣可以使用吉卤簿的最为重要的场合,故而其结合极为密切。
自西晋中期归复并重新确立丧葬仪制凶中掺吉的规定之后,这种丧葬吉凶相参现象到南朝进一步扩大,葬礼九旒的使用说明吉卤簿进一步渗透到了旗帜,使之具有了“凶旒”的性质。丧葬礼中吉凶旗帜的混用,在南齐时期已经比较严重了。南齐仆射王俭由于不满于本作为吉仗的旒旐使用于丧葬凶礼,因此将丧葬礼中的凶旒取消,从而确立了铭旌作为引魂旗幡的礼制地位。王俭对刘宋的五礼制度进行了改革,总体继承了两晋的五礼制度,并在原有基础上有因有革,这是五礼制度由发育到成熟的过渡时期⑩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62页。。深谙士族礼法的王俭出自高门琅琊王氏,素习自晋以来江东朝章国故,著名当时。王俭制定南齐新礼,其主要改革的仪制在于舆辂(车舆)、旗常(旗帜)两方面,而这些仪制正属于在中古丧葬礼中鲜明渗透的吉仗卤簿。《南齐书·礼志》载此前四年即南齐建元二年(480),皇太子妃薨,仆射王俭上书奏议:“旒(斿)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斿)。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旂)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①《南齐书》卷10《礼志下》,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58页。《通典》卷84《凶礼六·丧制之二》“设铭”条所引此条史料“旒”作异体字“斿”,无“伍”字,“桁”作“旂”。 第2274页。 《通典》“桁”作“旂”,于文意更合。诏从其议。此处王俭奏议中所谓“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正是公卿以下平时不用吉旒而仅在丧葬时赠用,说明了当时朝廷重臣丧葬仪制中实际上已较普遍渗透了吉仗旗帜,使其性质转变为一种凶旒。其所说吉部伍自有旂辂,凶部别有铭旌,正是将当时丧葬礼中吉凶卤簿中的不同旗帜根据其或吉或凶的属性分别加以归类区隔,分为“吉部伍”与“凶部伍”,实际上就是吉卤簿与凶卤簿两个队列。凶部有旗帜铭旌,吉部的“旂辂”包括了旗帜(吉旐)与车舆(吉驾),都已被纳入了当时的丧葬礼典之中。而王俭所谓“旒(斿)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实际上是说作为朝廷命服的旒是属于吉仗,出于“吉凶不相干”的礼制原则,吉旒不应该用于凶礼场合而成为“凶旒”。王俭称葬仪所用的旒旐为“凶旒”,其实是旧例以皇室成员与公卿达官卤簿中的旌旗之制来直接充当葬仪引魂的旗幡,只不过以往官员平时不备吉仗旗帜,仅在丧葬时立之以引导亡魂。这一做法遭到了熟悉礼典的王俭的批评。吴丽娱认为,王俭反对公卿大夫为显示等级而别建于凶礼的旌旗之上的做法,认为凶旒与铭旌不能两置,后隋代《开皇礼》、唐代《开元礼》中无旒,说明参考王俭的意见取消了②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下册,第457页。。朝廷下诏将葬仪中的凶仗铭旌与吉仗之旒区分开来,凶卤簿中以铭旌作为引导的旗幡,亦成为丧葬礼中的代表性旗帜被定型下来。
四、南朝后期丧葬凶礼仪服从吉的争议
葬礼所服衣服(仪服)吉凶之制的问题已见于上文所述西晋中期挚虞的新礼改革中,葬礼吉卤簿由吉服人员导从。在北朝,北魏皇帝丧葬仪制亦是吉凶相参,葬礼队伍中即兼有凶服、吉服人员。《魏书·礼志》载太和十四年(490)文明太后崩,十月既葬,东阳王元丕曰:“伏惟远祖重光世袭,至有大讳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见。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窃闻所传,无异前式。”③《魏书》卷108《礼志之三》,第3032页;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37“南齐武帝永明八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297页。元丕所论北魏“四祖三宗”皇帝大行之礼,其葬礼队伍中围绕着梓宫(棺柩)的侍送人员成服为凶服,而其他左右的仪服从吉,为吉服。可见吉、凶仪服已同时出现于北魏皇帝丧葬礼中。
但丧葬凶礼中的仪服从吉现象在南朝后期发生强烈争议,礼官朝臣引用了当时很多丧葬礼的仪注文献展开激烈辩驳。《陈书·刘师知传》记载了陈武帝陈霸先(庙号高祖)驾崩之时(559),朝堂诸臣围绕着陈高祖山陵礼所使用吉凶卤簿和成服吉凶的问题所辩论的往复意见,原文较长,此处摘录如下:
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服。
(刘)师知议云:“既称成服,本备丧礼,灵筵服物,皆悉缟素。今虽无大行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侠侍之官,悉著缞斩,唯著铠不异,此即可拟。愚谓六日成服,侠灵座须服缞绖。”中书舍人蔡景历亦云:“虽不悉准,按山陵有凶吉羽仪,成服唯凶无吉,文武侠御,不容独鸣玉珥貂,情礼二三,理宜缞斩。”中书舍人江德藻、谢岐等并同师知议。
文阿重议云:“检晋、宋《山陵仪》:‘灵舆梓宫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仪》称:‘灵舆梓宫容侠御官及香橙。’又检《灵舆梓宫进止仪》称:‘直灵侠御吉服,在吉卤簿中。’又云:‘梓宫侠御缞服,在凶卤簿中。’是则在殿吉凶两侠御也。”时以二议不同,乃启取左丞徐陵决断。陵云:“梓宫祔山陵,灵筵祔宗庙,有此分判,便验吉凶。按《山陵卤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爰及武(虎)贲、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岂容侠御独为缞绖邪?断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并服缞苴,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衽绖而奉华盖,缞衣而升玉辂邪?同博士议。”(下略)①《陈书》卷16《刘师知传》,第229-230页。
这段材料涉及对葬礼吉凶问题的争论,对于判断葬礼中的吉凶的具体成分及其区分原则颇为重要。细研之,可以读出如下三方面重要信息:
第一,葬礼历来具有吉凶相参的特征。刘师知所谓“銮舆兼设,吉凶之仪,由来本备”②《陈书》卷16《刘师知传》,第230页。,谢岐所谓“山陵卤簿,备有吉凶……爰至士礼,悉同此制”③《陈书》卷16《刘师知传》,第231页。,都说明天子山陵礼乃至士丧礼同时备有吉、凶两种卤簿羽仪,不管双方争论如何,都没有质疑葬礼卤簿之制中的吉卤簿的合法性。这已是朝堂上诸礼官的一个共识,双方都将此当作成服是否服吉问题的讨论起点。葬礼“吉凶之仪”的包含仪制范围在其“由来本备”、“悉同此制”的新原则基础上不断明晰化、扩大化。
第二,葬礼吉凶二分所依据的原则。魏晋南北朝丧礼之学有诸多文献,并发生了诸多礼议④高二旺:《魏晋南北朝丧礼学的兴盛及其实践》,《江汉论坛》2010年第9期。,只是双方所引用的晋宋时期的礼学文献今已无存。但从《陈书》记载辩驳的文字摘录来看,《灵舆梓宫进止仪》称“直灵侠御吉服,在吉卤簿中”,又云“梓宫侠御缞服,在凶卤簿中”,可见“吉卤簿”、“凶卤簿”的名称已明确无疑正式出现在当时的仪注文献《灵舆梓宫进止仪》中,记载皇帝山陵礼的仪注文献《山陵卤簿》中也有“吉部伍”之说,实际上也是“吉卤簿”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梓宫部伍”即是以梓宫(棺柩)为中心的凶部伍或称凶卤簿。吉、凶卤簿二部并立,与灵车相关的在吉卤簿中,而与棺柩相关的则在凶卤簿中,这等于是明确了丧葬所用卤簿的吉凶相参特征并以仪注形式固定下来了。徐陵提出的“梓宫祔山陵,灵筵祔宗庙,有此分判,便验吉凶”,说明葬礼中的吉、凶之别关键在于灵、柩的区别,也就是说灵魂及其灵筵、魂车是要归之于宗庙的,将来要过渡为祖先,所以属吉;而遗体所在的棺柩是要埋葬于山陵墓室,所以属凶。这点也得到了所有礼官朝臣的认同,成为争论的第二个基本起点共识。
争论的焦点还在于第三个问题,即山陵礼之前的吉凶卤簿人员成服的吉凶问题。葬礼队伍中吉仗与凶仗的区分,导致相关人员所服也与其吉凶属性有关。徐陵所谓“《山陵卤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爰及武(虎)贲、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说明围绕着魂车的吉部伍(包括车驾舆辂、羽葆鼓吹、虎贲班剑、伞盖扇翣等仪制)中的各种侍送人员是着吉服,并已以仪注的形式确定下来。争议双方的意见是,一派以博士沈文阿为代表,得到了左丞徐陵的支持,认为成服之时应同山陵之时,“文物并吉”,则不合“司事者凶”,即认为吉仗中的相关人员都应该照常服吉,而凶仗中的人员则改服凶服,并引当时已有的山陵仪注、成服仪注为据。另一派以中书舍人刘师知为代表,得到了蔡景历、江德藻、谢岐等人的支持,认为“山陵自有吉凶二议,成服凶而不吉”⑤《陈书》卷16《刘师知传》,第231页。,即不管吉凶卤簿是否有吉,只要是山陵之前的成服问题,都应该从凶服而不从吉服。谢岐也认为“从灵舆者仪服无变,从梓宫者皆服苴缞”⑥《陈书》卷16《刘师知传》,第231页。,则吉仗人员所服相对比凶仗人员要轻,但是不能服吉是大前提。因此,双方意见冲突的关键在于,在吉凶卤簿人员的仪服问题上,是应以葬礼本身的大凶属性为基本前提,还是以葬礼中吉凶卤簿各自的吉凶属性为参照。
陈朝这场争议的结果,八座审议及陈文帝最终均支持刘师知的意见,认为“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犹从吉礼”①《陈书》卷16《刘师知传》,第231页。。这说明朝廷对待大行皇帝山陵礼的大凶问题上,对于凶礼的本质性的坚持盖过了对葬礼吉仗的显示性的要求。这是朝臣众议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嗣皇帝在天下百姓面前所必须表现出来的孝心,同时也体现了南朝五礼制度化的历史大趋势下凶礼地位的确立。葬礼仪服所造成的丧葬吉凶相参的问题在历史的进程中延续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就丧葬仪制与亡魂观念的关系而言,此时之所以产生朝议纠纷的关键之处,在于葬礼车舆卤簿仪仗中,灵车(魂车)与柩车构成了葬礼卤簿吉、凶二仗的两个基本中心,从两个不同方面代表了亡者的所在位置,即前者代表灵魂,后者代表遗体。中古葬礼仪式中这种灵魂、遗体二分的出发点,当是源于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并流行于汉代的魂魄二分观念②参见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3、94-101页;余英时:《“魂兮归来!”——论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收入氏著《东汉生死观》,侯旭东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53页。。山陵礼所用卤簿是吉凶相参,“葬礼分吉”说明在卤簿仪仗的参与下,丧葬已并不完全只有凶礼的成分,而是出于显示政治权势地位的需要,不可避免添入属吉的成分,由此葬礼成为“哀荣”并重的场合。江德藻所议“祖葬之辰,始终永毕,达官有追赠,须表恩荣,有吉卤簿,恐由此义,私家放敩,因以成俗”③《陈书》卷16《刘师知传》,第231页。,正点出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私家士庶,上行下效,相习成俗的状况,吉卤簿在丧葬仪制中的作用被凸显为对亡者的“追赠”与“恩荣”。这条材料虽为陈朝的情况,但山陵礼、官僚丧葬礼混用吉凶卤簿的情况此后一直沿袭,到唐代进一步制度化。
五、余论:中古丧葬礼制原则与礼制实践的张力
陈寅恪曾探讨隋唐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指出有三个来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页。。陈戍国提出此外隋朝礼仪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南北朝之前的古礼(汉晋礼仪与先秦礼制)⑤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阎步克参酌此说另作“隋唐制度五源说”,提出包括北周、南朝、北齐、汉晋、古礼这五个来源⑥阎步克:《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从丧葬礼制的情况来看,南朝、北朝因素的合流导致了隋唐丧葬卤簿制度的发展。而单就唐代丧葬礼吉凶卤簿制度的来源回溯,则可发现南朝因素更为直接,开启了唐代山陵礼与官僚葬礼仪制凶中参吉的制度化特征。而再往前追溯其源头,则是来自汉魏的“故事”与西晋全面铺开的五礼制度化进程,丧葬仪制吉凶相参的礼制新面貌于此开始展现,此亦与陈戍国、阎步克诸先生所说的汉晋来源大致相合。
在“三礼”经义中有着鲜明的“吉凶不相干”的礼制原则。而丧葬礼“吉凶相参”的成例,发端于汉魏时期朝廷对于重臣勋戚的优遇。东汉时期开始,出现丧葬礼“吉凶相干”的新局面,对“三礼”原始精神造成冲击。西晋时一度撤销但却无法坚持,中古丧葬礼基本上仍按照“吉凶相参”的方向发展,愈演愈烈。从西晋一直到南北朝后期,历二百多年的时间,官方对于丧葬礼中吉凶卤簿相参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分别着眼于吉驾卤簿、葬给鼓吹、吉凶旗帜、吉凶仪服等问题,说明丧葬吉凶相参的仪制范围仍在逐渐扩大,这奠定了中古丧葬礼制的基本吉凶属性。经过一系列朝议与诏令,官方希望从礼制上将丧葬礼吉凶混杂的问题确定下来。
中古时期,虽然礼经确定的“丧重哀戚”与“吉凶不相干”原则被礼官反复提及,但在丧葬凶礼的实践中却陆续掺入了越来越多属吉的仪制,呈现出“吉凶相参”的局面,吉卤簿在现实中更凸显了朝廷对重臣达官身后的“追赠”与“恩荣”,由此可以体会经典诠释与礼制实践之间的张力在逐渐拉大。考之中古时期的五礼制度化进程,作为凶礼的丧葬礼之中却不断融入属吉的成分,造成了丧葬礼的各种物化礼乐的仪制出现吉凶相参的普遍状况,虽经部分反复,总体上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以礼制“故事”、“殊礼”与成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汉魏到两晋,以吉卤簿用于天子、皇家大丧,转而下移至追赠给重臣、诸侯王送丧,进而使南北朝时期吉卤簿成为优抚官员身后荣耀的重要仪制,在凶礼重哀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重排场、重恩荣的情绪,从而此后进一步延及士庶,渐渐导致了流俗的效仿。这实际上也奠定了此后唐代将丧葬吉凶卤簿纳入国家礼令的制度前奏,也启发了降至五代、宋代丧葬礼愈趋世俗化、娱人化的民俗基因。正是在汉魏南北朝以来丧葬礼逐渐吉凶相参的仪制基础上,唐宋时期吉凶卤簿与丧葬礼进一步紧密结合成为国家制度形态,造成了葬礼仪制的全面车舆化,并进一步从皇家和官僚系统蔓延开来,上行而下效,影响波及一般百姓,导致此风在社会上广泛盛行,形成厚葬的习俗①拙文《辇舆威仪:唐宋葬礼车舆仪制的等级性与世俗化》,《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
在吉凶卤簿的衬托下,中古丧葬礼的精神在“哀”的原则之外鲜明渗透了“荣”的成分,而“荣”的强化正需要一定规格与规模的仪仗来高调呈现的,这就为吉卤簿渗透参入作为大凶之礼的丧葬礼奠定了历史条件。在中古葬礼实践中,围绕着搭载亡者遗体的柩车为中心,设置一系列属凶的凶卤簿正是礼经丧礼重哀戚的精神体现;而围绕着搭载亡者灵魂的容车(魂车)为中心,具有吉的属性而掺入凶礼之中的吉卤簿成为出丧队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②拙文《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魂衣与魂车》,《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其目的则是要烘托和凸显亡者灵魂的显贵地位,这也是朝廷礼制所赋予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哀”的本质也好,“荣”的强化也好,都是生者尤其是官方、社会所想象中的亡魂的身后感受,同时很大程度上亦是昭示给活着的生者与旁观的世人看的。“吉凶不相干”原则处理主哀戚的凶礼丧葬礼,却渐渐在历史的演进中被“吉凶相参”的新观念所代替,于是从“哀”到“荣”的倾向也愈加明显。这与吉凶卤簿制度在丧葬礼中的渗透关系密切,从而亦使中古丧葬礼的各种仪制日趋呈现出吉凶相参的特征。丧葬吉凶仪制上的争议,形式上是礼经规范意义上的吉凶观念之争,实际上又反映了权力的特许恩荣机制。从“哀”到“荣”的原则争议与实践强化,可见中古时期权力加持的追赠恩荣观念的彰显,也体现了经典性规范与等级性礼制背后的五礼制度化进程与权力恩遇机制的渗透。
(本文得到台湾淡江大学古怡青老师以及三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