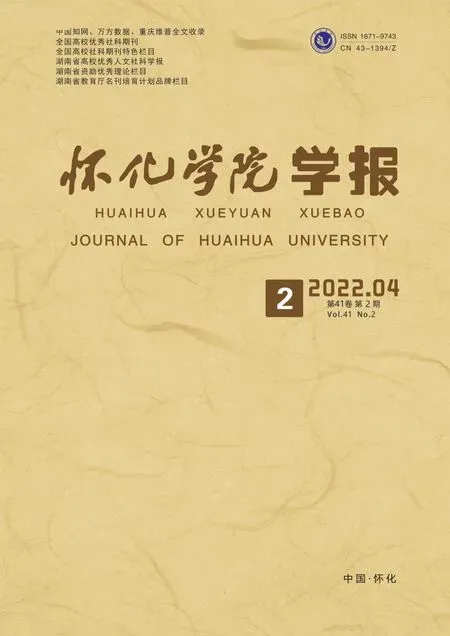1556 年关中大地震灾民心理的历史考察
唐 晓, 罗康隆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嘉靖三十四年处在嘉靖帝统治的后期,也是大明王朝的末期。经过了“嘉靖中兴”,社会继续平稳发展,虽北有鞑靼、南有倭寇,早先还有旱情,但总言之这一年本应该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它并不平淡——震亡人数高达83 万,号称世界死亡人数之最的地震。该地震波及范围广、破坏程度高,给灾民造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影响。本文在厘清关中大地震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重现震灾中灾民的心理状态并分析此种心理出现的历史原因,在政府及社会各界乃至灾民自身的救灾活动中总结、归纳出针对心理创伤的内容,由此也说明心理重建并非近现代的新鲜事物而是古来有之。
一、关中大地震的史实
学术界对关中大地震的震级测评、受灾情况、救灾赈灾等诸多方面均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 关中大地震的发生
关中大地震的统计数据在三个版本①的《中国地震目录》 (以下简称《目录》) 中均有详细记载,本文基本上以最早的李善邦版为准。关中大地震发生时间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夜,即公元1556 年1 月23 日,震中为陕西华县(北纬34.5°,东经109.7°),震级8 级,范围“延及千里”,极震区为华县、渭南和华阴。受灾县达101 个,分布于5 个省约28 万平方千米,震感范围更是达到了227个县。近年来学界对于地震名称、震中和震级均有争议。关于震级有三种观点:8 级的说法被普遍接受,《目录》亦持此观点;谢毓寿认为华县、渭南烈度已至Ⅻ,震级应取8.5;而地震学界用81/4级较多。震中位置又有华县和蒲州两说,华县说较普遍,李世勋等人认为地震震中是在北纬34°44',东经110°16',也就是在蒲州、朝邑、潼关、华阴之间,非华县。至于极震区范围,不仅在近代有多种说法,古籍记载更是五花八门,记载以太原、蒲州、夏县等山陕两省辖地方志为多。不过这些结论对本文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关中大地震”的名称,以免引起争议。
(二) 关中大地震的影响
有“人”才成“灾”,灾害的影响按对象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次生灾害,前者如“地裂泉涌”“平地突成山阜”,地下水泛滥上涌等。而破碎的地震区岩石发生崩塌,加之暴雨或洪水就会形成水石流,地震区河流含沙量增加使洪水险情更频繁。关中大地震之所以引人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其高达83 万的死亡人数,此数据最早源于《明史·世宗本纪》“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地大震……死者八十万有奇”。多数研究者认同此数据,不过另有宋立胜的45 万、单修政的70 余万和王汝雕的53 万三种观点②。单认为少了的十几万只是官方统计错讹,王认为所谓83 万是包括了次生灾害受灾者和逃亡、迁移的人口。按照西方对于饥荒的定义,关中大地震的“荒”应是属于并非完全的匮乏,而是叠加上震前旱灾导致的大面积歉收,政府又不作为而导致的大量贫困阶级的死亡③。灾后的社会相当混乱:政治上,灾民生存环境艰难,官方赈灾措施不到位便会发生官民相斗、“民蜂起掠食”等现象,政府与中央威信随之下降。其次产生了大量往周边,特别是向省城迁徙避祸的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大因素。经济上地震造成田地荒芜、劳力损失、粮价飞涨,给社会以沉重的打击。文化上,文献史书陷入土中、金石碑刻断裂脱落,学舍损毁严重,对此后关陕教育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可以说直接切断了关陕儒生的入仕之途。个别文豪大儒的遇难也使晚明陕西的文学暗淡下去。
灾害的发生会使人的观念和行为都发生变化,心理的调节更是必然。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使生境发生变化,灾民的心绪自然不同以往。
二、灾民对地震灾害的认识
地震灾害具有其特殊性,在同等时间内震灾的致死率和破坏率远非其他灾害可比,因此它对灾民的冲击也是最大的,震时死亡率可达到每分钟上万人,“地裂泉涌”“树摇目眩乱”,“民惊溃,起者、卧者皆失措”,震后“千门万户半作鬼,广厦高宫尽成土”[1]25,更让人仰天长叹。地震刚开始时,灾民“初疑盗,继疑妖祟”[2]383,实际上体现了自然地理知识的匮乏。《目录》记载16 世纪这100 年内,53/4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09 次,实不该不知地震,但其又确是不知,以致把地震归于灾祥妖祟,这就来源于传统认知中的人地关系。
(一) 归因天谴:“人事乖乎下,灾异见于上”
早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中就有此端倪,《春秋繁露》记载:“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这也是古代中国最为流行的一种灾异观——“天谴论”,即所谓“人事乖乎下,灾异见于上”[3]61。虽然随着自然科学的逐渐发展,地动仪等测量仪器也早已出现,但在对地震的认识上,天人感应的思想仍占绝对主流:下至贫民上至帝王,有天灾降临必纠责上层。百姓责怪官吏腐败;皇帝检讨自己言行;文武大臣自相反省。不过也有记载从汉元帝开始,地震便不再纠天子之过而全怪朝臣、后妃和外戚了。当中央收到灾情后,立即“请如例修省,九卿科道许极言时政得失”。后嘉靖又强调“内外臣工其痛加修省”。除此例行公事之外并未发现天子自省和把天灾异象卷入首辅之争的记载[4],从1553 年地震的“上谕礼部曰:‘灾异屡作,仰荷天心仁爱,朕躬叩玄恩以祈消弭。文武群臣其实加修省,各条陈时政得失以闻’”[5]6179可以看出嘉靖并非对国难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从1563 年徐阶麾下御史邹应龙以水旱灾害抨击严嵩一党也推得出争端热烈的严嵩与徐阶不会放过如此良机。另外徐学谟[6]621《世庙识余录》也载“兵部尚书杨博之父亦被压死,上闻之,谕严嵩,此博不忠所致,博怀疑,畏不敢为父祈恤,后夺情起复蓟辽总督,始敢陈情给祭葬”。综上所述,此次地震的真实情况很大可能并未达上听。报灾和勘灾都是很重要的环节,永乐时更严惩匿灾官员,但因为“天人感应”思想的根深蒂固,天灾必是人祸而起,官吏恐被皇帝责罚,因此不敢上报实情[7]。
在这个前提下,灾区与朝廷掌握的信息失衡。灾区等不来中央的救助,只能向神明祈求圣上的关注,《地震叹》中“我欲托巫咸,上奏通明殿,飞章彻蕋陛”[8]98正是灾民心声的表达。而嘉靖帝在收到报灾之后便派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兵备副使汪来和都指挥使王玉前往灾区祭祀山神,以表达“圣心之恻”和虔诚地请求神灵莫降灾祸。
(二) 夸大凶兆:“黑气盈日,数有蜺珥”
在惊恐情绪支配之下的灾民把几乎所有异象都夸大,如《赵浚谷文集》描述震后“黑气盈日,数有蜺珥”[9]26-27中的黑气或许只是烟尘,蜺珥也就是霓虹的光晕,在灰尘中透照到地上,形成了瑰丽的景象。《华州志》记载“忽又见西南天裂,闪闪有光,忽又合之……震之夕,星殒如雨”[2]396,很明显是夸张了,因为根据志书记载,震时并无流星雨发生。《国朝汇典》记载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光忽暗,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数十相摩,视久则百千飞盪满天,向西北散。易卦验云:愚智同位,日月无光”[10]1456,而史书中也并没有日食的相关记载,所以这里也同样是夸大了天象以强调地震带来的凶象。
除在描述灾后异象方面显现出夸张的倾向外,也出现了灾前所谓“预兆”的记载,张翰在《松窗梦语》 中言:“余闻先期居民梦天庭发榜,首湘阳王,次韩司马,次杨尚书、王祭酒、刘参知,共数万人,后皆压死,是兆端已先见矣。又云:黑夜居民家关云长骑赤兔马大呼:‘急随我行!’有随之向东行者,得免。岂西北之奉事惟谨,而云长亦为之效灵耶?”[11]100灾前有人梦到王维桢等后来在地震中丧生众人皆在天庭榜上,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预言梦形式,即预言榜中人此后会为天庭效力,作为在凡间的他们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接着下文由关羽带路躲避灾难的说法也符合了关中地区对关羽这一特殊神祇的民间信仰情况。
三、灾民心理创伤的体现形式
灾害对人的伤害是立体的,在灾害造成的多方位影响下,“灾民意识”逐渐产生,总结为以下四种具体表现形式。
(一) 对灾害本身的恐惧
首先对灾害的恐惧可分为对灾害本身的畏惧和对灾厄随时会降临的不安。在上文论述中提到灾民“妖魔化”地震的倾向,对天神的敬畏让灾民们发觉自己的渺小。主事王尧弼记,“民之死于变者不可胜纪,闻有生者,亦废不能兴”[2]396;《地震叹》 言,“数月地时动,露宿股恒颤”[8]98;《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载,“人心惶惶,夜皆露宿,不敢进庐舍”;《祈禳地震文》也记,“苍赤惊怖,祍席不安”[3]61。这表明在地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灾民都处在一个害怕余震的高度紧张之中,即使建屋也不敢“安业”。于是便兴起了类似于现代板房一样的安置房:“有力之家,多用木板合厢四壁,上起暗楼;公衙之内,则置板屋,士庶人家亦多有之,以防祸也。”这种板屋总体轻巧,成本较低,最重要的是若在余震中倒塌也不会压死里面的人,还可以原地重建。
(二) 失去亲人的悲痛
极震区的灾民几乎都经历着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还有全家全族无一生还的极端情况存在,它给灾民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马峦写道,“死者哭相连,生者坐浩叹……亲戚幸生存,奔走唁忧患”,亲人的生还就是他们最大的慰藉,此外别无他物。“亲戚幸生存,奔走唁忧患。”“予阖家幸无恙,因急令人候亲族之最关切者,俱幸无恙。”[2]383“父陨其子,夫遗厥室,弟抱兄哀,仆为主泣。”[12]237能与家人团聚是灾难中最低需求却也是最高奢望,失去亲人很容易令幸存者失去生存的意志,从而增加死亡人数。正如地震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的往往不是地面震动或者掉入裂缝,而是房屋倾轧和灾后的饥荒、瘟疫及动乱,失去生存意志遑论重建生存条件。
(三) 失去生存条件的绝望
灾民失去生产条件,地震“没麦败田,圮屋覆灶,屋多焚”[9]29,屋舍破坏、良田湮没,失去生存条件的灾民后继饿死者不可胜数。1793 年的宁夏地震,相关文献记载“冬夜家设火盆,屋倒火燃,城中如昼”。其与1556 年这场地震同样发生在1 月,所以关中大地震也必然是同样情况,房屋相继倒塌和焚毁。“水涌若墨漆,米贵似珠钿”展示了物资缺乏时灾民们缺水少粮的艰苦生活。对于往日家园的一片狼藉,灾民们心理和生理上都无力快速重建,泾阳二功臣祠在地震中倒塌,“过者恻然”却觉自身难保“无暇为也”[2]389,只得无奈。
因为生存条件的丧失,灾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抢粮的动乱,“奸人趁乱剽掠,或相击杀”[9]29,各地奸人相杀、无籍见扰民,有记载的有蒲州、渭南和同州,“时地方乘变起乱,省城讹言,故可畏矣渭南之民抢仓库……蒲州居民掠财物……同州之民劫乡村”;渭南“是时邑令亡,恶少肆掠,几大乱”;同州“盗麻沸,所在钞掠”[2]384-395。《地震叹》也记载了无籍流民“乘机扰良善。白昼夺积粮”。可以说是天灾人祸,“盗贼群起”,一时间“人心汹汹”“人人自危”,不敢动作。地方政府的解决方法有疏有堵,既有杀人以树威,也有招抚流民之举,在此不做赘述。
(四) 讹言造成心理失衡与迷茫
谣言可以说是灾民心理最大的敌人,有记载的地震后广泛传播的谣言有三:一是“蝴蝶杀人”,“马祖师术,有物如蝴蝶,入人家,变幻飞走,御之,则刀仗伤人,夜魇人致死”[10]1456;二是《地震记》记载的“城东北阿儿朵回人反”;三是选绣女谣言“时流言选取绣女,未越月,男女配殆尽”[13]。谣言传的都是灾民当时最惧怕的想象,它的传播对重建工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首先因为道路被阻断,谣言很难被证实或证伪;其次灾民陷于迷茫中无法辨别是非,于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惶惶度日无法全心全意投入重建工作,要么躲藏,要么聚众发生武力冲突。对于此类事件,官府只能尽力破之,以安抚民心,如逮捕发出“蝴蝶杀人”谣言的马道士。为了重建政府威信,同州知县甚至勒令其弟自尽,以威慑贼人[2]395。治盗使灾民能够全身心投入重建活动,治讹则维护了一个良好的灾区重建氛围,使希望取代迷茫。
以上消极心理的轻微状态基本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但严重的情况就会带来真正的难以痊愈的心理创伤了,灾民可能出现完全否认地震及其对自己所带来的一切伤害的表现,从而造成精神错乱;有可能彻底失去求生欲望而做出轻生举动;也有可能被恐惧和暴躁的激情支配从而做出反社会的举动等。这都是现代地震灾后心理援助团队所发现和重视的。
四、灾后心理重建行为
灾害是一种文化的概念,有灾不一定有荒,灾后有无荒,很大程度取决于当时的赈救力度。这也就使赈灾救灾成为灾荒史研究重点之一。当许多学者关注灾害中的人身财产损失、钱粮调度效率并取得成果之余,也有人开始关注灾害对灾民心理状态的影响。灾后灾民很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各种应激反应,如果不及时地开展心理干预和重建工作,这些不良情绪可能恶化成精神疾病,不仅威胁灾民个体的健康,还会影响整个灾区的氛围,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中国古代虽然并没有“灾害心理”与“心理重建”等概念,但是各赈救主体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灾民心理的变化并做出了一些有意识的,旨在抚平、恢复灾民情绪的针对性举措,可以算得上是有“实”而无“名”了。此节以各类民间文献为史料基础,灵活运用心理学分析方法,从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的救灾主体入手,于宏观的救灾行为中归纳总结出针对灾民心理重建的部分。
(一) 各级政府赈恤——有针对性的救助行为
赈救主体与方式的多样化被称为“社会化的民间施赈主体”[14]88。多样性的主体又包括政府荒政、民间义赈、宗教组织的赈救与灾民自救等等,其中政府的救灾行为是最有针对性、有效和快速的,这点谁也无法否认。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仅5 月13 日一天,空运救灾军队就高达11 420 人,这是当时我国空军运输能力的极限——没有什么能比军队给灾民更强的安全感。
1.“祭告山川”
三十五年岁初嘉靖帝派左侍郎邹守愚前往山陕赈恤灾民、祭告山川。相关记载有陈增美的《祈禳地震文》和收录于《武乡县志》中的《祭告》一篇。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文中作者认为“夫变不虚生,必有所生之自,孽不妄作,必有所以致之由”,即地震肯定是有原因而生,肯定了“人事乖乎下,灾异见于上,考古镜今,锱铢不爽”[3]61,更进一步表明了对上层的谴责立场。然而在祭告中却说“天子明、圣道在”[15]30,完全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做作地以谦卑之姿态“惧神之不安于居”,希望神明能“潜消劫难,赐福人民”。诚然这是朝廷对灾区人们的安抚措施之一,表明朝廷对灾情的关注和反思,但实际上流于形式,真正的效用可想而知。当然在民间的祷文中也有“天胡降殃,坤灵失职”之类的慨叹,邹守愚甚至因为随之而来的瘟疫死在长安。
2.“问民疾苦”
在《荒政要览》中俞汝为[16]428总结了11 种救荒措施,其中记载明代确有“问民疾苦”之传统,也就是政府的“抚恤”措施,虽与今人的心理救援有一定差异,但还是表明古代的荒政中,是有安抚百姓、体恤灾民的行为存在的,其目的不是解决灾民的心理危机而是基于稳定社会秩序。上文提到在“天谴论”的影响下,大地震震时情况被虚报,所以此措施甚少见于正史。笔者只能大胆推测,这个传统从宣德帝得以留存下来。
3.“收瘗死者”
从制度层面看,赵诏[7]在《明代的灾荒救治》中提到“养恤制度”,其中就包括收养遗弃、抚恤鳏寡孤独、施药、掩埋遗体、为贫困家庭赎还妻子等。《世宗实录》记载,“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5]7449,即官府组织收埋死者,并于祭坛祭奠。 《地震记》载“其又骸骨暴露者,督令有司掩埋”也是如此。收敛暴尸不仅是为了预防疫病,也是对死者尊重,是对生者心灵的慰藉。“收尔游魂,敛尔精魄,以慰我思”[12]237,中国传统有“入土为安”的说法,虽然在地震中横死,至少将其遗骨收束,这样死者的游魂才能顺利进入地府或是转生,而非在人间徘徊。
4.“为神建庙”
把重建城隍庙与重建城池、祭奠山神和赈灾救民放到同样急切的程度,可见重建宗教信仰,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是很重视的。重建工作是地方官的最大职责,受灾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屋舍衙府倒塌是地震中破坏最严重的方面,“从蒲至关陕,无庐可完缮”,灾民“度日真如年,何时复安宴”。所以知县们与民休戚,同时加紧修缮。高陵李翰“设处葺理,民不告扰,而诸工就绪”;兴平县朱文“以才能调兴平,学宫、宫府、县守、城埤俱任怨修葺”;耀州李廷宝“宽简,一切与百姓休息”。而值得注意的是对城隍庙的修缮工作,几乎是与城池的重建同时进行。比如蜀泸朱候在地震第二年下华州,第三年即重建神庙。还有鄂县的城隍庙“经地震之灾坏,再明年丁巳会四街居人为修复谋”,比之文庙、学署,可见其在百姓心中之地位[2]387-394。城隍庙是一方百姓的精神支柱,是守护神,城隍庙的修缮给灾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无力重建地方的灾民只能“过者恻然”了。赵双业[13]在《明代地震与灾后救助》中还提到僧人团体,他们尽早修缮寺院使得灾民们可以进入以获取庇护和心灵的平和。
5.“纠宗守望”
官方与民间赈灾的互动,由官府主导,乡绅实操,两相配合.一方面官府无法忽视民间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必须抑制地方势力的膨胀。隆庆《华州志》记载,“杨纟采……纟采丁内艰,比境四民将蜂起以掠,劝借富家以给赈民之粟”,便是官府向民间富家求助的例子。天启《同州志》载,“命时宅忧,纠宗守望,其弟弗良,即勒令自尽,于是威望大著,贼不敢近”。嘉靖《耀州志》载李廷宝“会年饥,后有地震,廷宝宽简,一切与百姓休息”[2]394-396。震后基层政府为了治灾民骚乱,以暴制暴和与民休息并行之。因为中央收集信息和传达命令的滞后,所以更多时候灾区的工作必须由各级政府与乡绅合力完成。地方官吏的角色主要是秩序的维护者,是赈灾的主体。不仅要承上层政府的命令,更是“父母官”的责任,为了维护灾区秩序,拯救子民于水火,地方官们往往刚柔并济、上下联通。此间宗族的凝聚力也尤为重要,因为一个聚居区往往为一个大宗族,富豪与乡绅在所居区域有一定声望,震后就成了政府与基层灾民的桥梁。富豪地主和乡绅在震死概率方面与贫民并无两样,但是富豪之家毕竟有积粮,较贫民来说更有秩序,往往能较快恢复。
(二) 社会团体与灾民自救——广泛的自救行为
1.“悉出券焚之”
据正史记载,中央最早的一批赈灾款要到次年三月,陕西灾情比山西严重,但就记载看对山西的赈灾在时间和力度都明显更强,所以自救就显得更为重要。在自救的多样主体中灾民对于乡绅往往是感恩的态度,而对商人则是矛盾心理,既恨其屯粮提价,又依靠他们运粮贩卖。党孟辀是韩城富商,灾后贷粮予百姓,“贷者不能偿,辀悉出券焚之”[2]396,也就等于送粮给灾民,体现了富商们在灾后重建工作中的态度。民间本有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思想传统,灾后富商此举也算得上是“为富有仁”,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灾区社会矛盾,也使灾民之间联系更加紧密。
2.“相见忻问慰”
灾民们“竭筋力膏血勉造房屋”却因恐惧余震不敢安业,《地震叹》载“亲戚幸生存,奔走唁忧患。相见忻问慰”展现灾后血脉亲人间的相依为命、互相慰藉以继续生活的场景。“因急令人候亲族之最关切者,俱幸无恙”[2]383-384。因为血缘亲人和乡民都是灾民们所信任和熟悉的,所以相较于前来慰问的官吏,抱团取暖的作用会更大一些,相互扶持、彼此帮助建立信心是灾民们顺利度过心理危机的最强动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中大地震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除了本身震级较高的原因外,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自然现象与人文社会结合起来成为官员评价政绩的标准,灾区真实情况可能并未达上听,导致赈灾不及时、不彻底,这也极大地影响了灾民的心理状态。受制于自然科学水平,灾民对地震感到未知与恐惧,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夸大和妖魔化,最终导致流言四起,形成恶性循环,非常不利于灾区恢复建设。为了遏制这一现象,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乃至灾民个体的赈救措施中均包含了针对抚平心理创伤的相应内容,即使长久以来并未被独立讨论过,但心理重建无疑是赈救行为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对历史上灾民心理的考察也对现代震灾的防治有着警示作用。虽然在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和广布的网络环境下,当代地震在救助方面几乎不存在懈怠,然而在本身就有着情感缺失问题和功利主义的当代,灾民心理问题却还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环,亟待全方位的监控和干预。
注释:
①分别是1960 年李善邦、1971 年中央地震小组和1983 年顾功叙版三个版本。
②分别出自宋立胜《1556 年华县8 级大震死亡人数初探》,单修政《1556 年华县地震人口死亡原因浅析》和王汝雕《1556 年华县地震“震亡83 万人”质疑》。
③米歇尔·麦克尔平:《遭遇饥荒:西属印度的粮食危机与经济变化,1860—1920》,转引自李文海、夏明方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美]李明珠著,《华北的粮价与饥荒》,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