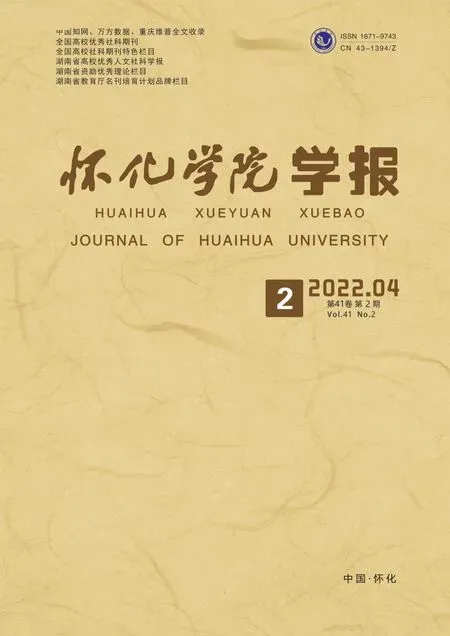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警察与地方社会治理
吴铁稳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历史上一段全面繁荣与和平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英国率先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确立了种种现代社会秩序雏形,对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期,被称之为英国历史上的“改革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人见证了现代职业制服警察的诞生、全国范围内有效警务的创建和发展。英国警察参与维多利亚时期地方社会治理,在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责任,为英国在19世纪转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
一、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警察的建立与发展
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打击犯罪、确保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核心力量。19 世纪20—50年代的英国人见证了英国警察的诞生,19 世纪下半期还经历了英国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和发展有效警务。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从一个警察很少、经常“粗暴”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管理思路、警察治理有力、更为“体面”的社会[1]44。作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警察自身也发生了转变。他们由一群不自律、将警察职业视为权宜之计、对工作几乎没有认同感、缺乏忠诚的人,转变为训练有素、不断成长的“职业”男性,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具有独特作用和责任的职业群体。
19 世纪早期,持续不断的民众抗议引发社会动荡,面对犯罪浪潮,传统治安力量无法应对,英国开始建立现代警察制度。1829 年6 月,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敦促议会通过“改进大伦敦及附近警察法案”。根据法令,在大伦敦及其周边地区(伦敦城除外) 建立一个新的警察机构[2]。随着1835 年《市镇自治机关法》的颁布,自治市警察力量此后稳步发展。1834 年时大约有20 支警察力量,19 世纪40 年代初增加到130 个,直到1856 年一直保持这种水平。到19 世纪70 年代中期,165 个自治市已建立警察力量,但随后的小自治市与郡合并警察,1914年警察力量数略低于130 支。郡警察力量的建立始于1839 年《郡警察法》的通过,此后英国开始在各郡乡村地区建立警察制度,以增强地方治安力量。1839 年郡警察力量有6 支,19 世纪50 年代初也仅有26 支。1856 年《郡和自治市警察法》的通过为全国警察制度的发展建立了框架,从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个郡和自治市都开始建立警察力量[1]45。
与此同时,随着规模的扩大,警察总人数也相应增加。1861 年,警察总人数为20 488 人,1911年扩大到54 314 人。这样,每位警察对应的英国人口数从980 人下降到664 人[3]。大伦敦警察规模最大,拥有英国最多的警察人数,其最初只有800 多人,1851 年增加到5 500 多人。相比之下,1840 年代末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警察人数分别为445 人和806人[4]42。到1871 年,伦敦警察力量总数已超过9 000人,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则超过22 000 人。这时,伦敦的警察与总人口比率全国最高,1 位警察对应350 人[5]。在伦敦之外,最大的警察力量是郡警察,特别是兰开夏(Lancashire) 和约克西区(the West Riding),其警察数到20 世纪初超过1 000 人[1]46。随着英国警察体制的确立和警察规模的不断扩大,预防犯罪、维护秩序、保护民众生命与财产的安全成为其分内之职,他们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预防和打击犯罪
英国警察承担预防犯罪的功能早在其建立时就已经明确。1829 年大伦敦警察厅发布《警察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预防犯罪’。警察应朝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它会使我们更有效地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实现警察其他的所有目标。警队中的每位成员都应时刻牢记、铭记于心,并把它作为行动指南。”[6]
在大伦敦警察创建之初,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希望通过警察巡逻街道实现预防获罪,因为警察在街道上不断出现会给人一种警察无所不在的印象,从而消除犯罪者有机可乘的念头以及得逞的机会。因此,巡逻是新警察的核心工作任务。基于1829 年以前教区巡夜看守效率低下、犯罪不断增加以及缺乏统一管理,为了弥补治安制度中存在的这些不足之处,新警察成立后立即建立起日夜巡逻制度。最初要求每名警员每隔10 分钟对所属巡区(Beat) 巡逻一次,但很快发现巡逻的时间因巡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圣吉尔斯(St.Giles) 每名警员完成其巡区巡逻需25 分钟,而在早晨及晚上,两人换班时间完成巡逻只要13 分钟。在格林尼治(Greenwich),巡区范围更大:夜间巡逻是500 法定英亩(statute acres),或783 平方英里;而在霍尔本(Holborn) 夜间巡逻范围是3 英亩或4 英里。到1862 年,巡逻范围平均是160 英亩,或2 495 英里[7]。
警察在街道上巡逻,能够在街道上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及行事标准。新警察在一个地区建立后,增加了对微小犯罪及轻罪分子的管理:街道小贩、成伙的年轻小混混、妓女及流浪汉们被要求不能在街道上停留;醉汉被带往警务室,让他们在这里入睡;闹事的醉汉被强行带走,交通得到较好的控制;运货马车、出租马车及公共马车的车夫被禁止游荡;疯狂及醉酒驾车、没配缰绳的马车都是警察管辖的事情。19 世纪30—40 年代,不仅新警察担负这些职责,而且根据《1833 年照明及看守法》建立的治安力量也要如此;罗伯特·设菲尔德爵士(Sir Robert Sheffield)坚持认为他所在的林肯郡督察也同样有效[8]60。
新警察最擅长的是逮捕那些街道上的轻微犯罪人,从而降低了街道抢劫案的发生。在警察自己看来,侦查的重要性次于预防犯罪。1842 年6 月,大伦敦警察厅长梅恩(Mayne) 说服当时的内政大臣詹姆士·格雷厄姆(Sir James Graham) 授权任命了2 名督察及6 名警长从事侦查工作[4]62-63。到1862 年时,各分区警察署大约有200 名便衣侦探。1869 年,埃得蒙·亨德森上校(Colonel Edmund Henderson) 接任警察厅长。他认为,过去那种各警署的一些警员临时充当便衣侦探的应急措施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建议每个警察署都应该建立一个由10 人组成的侦查小组,而总部的侦探应增至40 人以上。警察署的侦探将应付日常的犯罪侦查工作,而总部的侦探则负责重大和特殊案件,或在政府的鼓励下参与调查外国侨民的活动及引渡罪犯等事项。1874 年内政大臣任命了一个部门委员会,专门了解大伦敦警察厅侦查机构的纪律和组织等状况。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建立一支统一的、与众不同的侦查力量,作为警察机构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它的“构成人员应该有较高的级别,其地位要优于制服警察和犯罪预防机构中的警察”,并建议这支队伍由一位担任过地方法官的律师领导[9]。1878 年,犯罪侦查处重新组建,不同于各警察署,它可以直接从苏格兰场或任何一个制服警察中招募成员。到19 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几乎所有的警察局都建立起独立的侦查部门。随着侦查工作的开展,侦查机构内部进一步分化,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专门的分支机构相继出现。专门侦查机构的出现和扩大,使得打击犯罪职能得到进一步增强,侦查部门的侦探成为打击犯罪的主要角色。
新警察不仅担负预防犯罪、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而且还是重要的公诉人。许多以前因为缺乏法律知识而不愿起诉罪犯或因贫困没钱起诉的受害人现在都可以得到警察的帮助。新警察的产生增强了公民知法、守法的观念,为英国过渡到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做好了精神素质方面的准备。总之,鉴于新警察领导人对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重视,19 世纪以更加精确的形式出版的犯罪统计数据表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严重犯罪率从19 世纪50 年代后期开始长期下降……一直持续到19 世纪末。虽然在20 世纪初略有轻微的上升,但并没有恢复到19 世纪中期的水平”[10]281。
三、控制社会秩序,实施新的道德标准
尽管大伦敦警察们的首要任务是预防犯罪,但是他们经常被派往各郡处理大规模的骚动。英国虽然没有卷入1830—1848 年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的革命,但是却出现了19 世纪30 年代的内部骚动和40年代的饥荒。在镇压骚动及结束严重的混乱状态时,新警察与以前的教区警务员和因突发事件而宣誓就任的临时警察相比,作用更大。在类似事件中,他们也比军队更少地造成人员伤亡,故而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镇压骚动。如在1833 年伦敦的科尔德巴斯广场骚乱(the Cold Bath Fields riot) 中,虽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但没有一个示威群众被杀。
警司马丁(Superintendent Martin) 认为,在处理骚动时警察比士兵更可取。他指出,警察可以一只手握警棍,而士兵必须双手握枪,并且没有什么力量来协助他……如果士兵被调派去制止骚动,他被迫要么实行警戒,要么开枪,并且这样做的话很容易给骚动群众带来伤亡,不能很好地逮捕他们。19 世纪30、40 年代,内政部经常从伦敦调派小分队处理新济贫法骚动、宪章派的骚动等民众抗议活动。当骚动发生时,大伦敦警察的小分队通常被要求站在军队的前面制止抗议群众,但他们也经常与军队一起出动,紧密配合。大伦敦警察G 区的督察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 于1853 年给特别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他被派往地方各郡的详细情况:1837 年选举骚动期间调往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 及迪士伯里(Dewsbury),1839 年前往伯明翰,1843年前往南威尔士。他指出,在每次行动中警察与军队一起出动;在南威尔士,少量士兵与身穿便服的警察驻扎于小的、可疑的、有危险的社区[11]。
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除了具有政治镇压的职能之外,还同时实施新的道德标准。警察通过实施新秩序的标准及街道日常礼仪原则,加强对社会的管理。警察的到来,意味着英格兰大街小巷的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监督,各种活动受到控制,其中许多活动长期被社会习俗认为是合法的。罗伯特·斯托克(Robert D.Storch)曾明确指出,警察被期望“对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持经常的、不断的监控压力”,并且在理论上(如果不总是在实践中) 代表了“国家道德和政治权威”的“显著增加”[12]。警察以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要求并塑造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因此,警察也被称为“国内传教士”(“domestic missionary”),担负执行文明化及礼貌原则教育的责任。为了达到这样的结果,警察需要执行一系列的法规。新警察建立之后,对于以前法规的执行,如没收星期天还在出卖的货物,驱赶街道上的小贩及逮捕那些扰乱社会治安的骚动者变得更加严格。警察对工人阶级纪律性的要求扩展到他们休闲的生活,斗鸡、斗狗、赌博、安息日的狂欢、啤酒店的酿酒、买卖淫秽书籍、嫖妓、在街头兜售商品都会招引来警察,甚至小孩在街道上玩铁环和踢足球也可能被拘捕。亨利·梅休(Henry Mayhew) 曾采访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位小贩对他说:“我恨警察,……他赶我们走,我们只能到处躲,根本没法摆摊。”[1]105警察试图以道德教化干涉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努力遭到了工人的反抗。警察也十分清楚他们担当教化的角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大伦敦警察的厅长们及各级警官在命令他们的警察去执行这项任务时,相当谨慎。
警察在街道上执行新的道德标准及秩序也包括对妓女采取行动。对于卖淫行为,警察依照一系列的法规如流浪法(Vagrancy Laws)、改善法(Improvement Laws) 及执照法(Licencing Laws) 进行执行。1864—1886 年通过并实施的三个传染病法(the thre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1864 和1866 年两个法案持续时间很短,1869 年法案延续到1883 年,直到1886 年才废除),旨在通过授权大伦敦警察在18 个海军及驻军城镇可以临时派遣小分队,身穿便衣对妓女们进行查访,并且让她们接受政府医生们的性病检查,从而控制卖淫问题。此外,为了抑制卖淫问题,19 世纪中期的警察通常依照1847 年城市治安法(the Town Police Clauses Act of 1847) 来执行,要求这些妓女在11 点后离开他们所负责的巡区街道,并且不许她们在一些特定的地方闲逛,或勾搭过往的行人……如果她们不扰乱治安,警察不会闯入房子干涉她们。19 世纪末期,剑桥警察局长还从邻近郡借调一些机智的年轻警察,以便让妓女对他们进行勾引,然后,这些女性将被成功起诉,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妓女产生威慑作用[8]78。
立法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责任,警察活动的范围也在扩大。国家扩大权力,试图改革人民的道德。酗酒、赌博和卖淫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事实上,到20 世纪初,警察的责任已延伸到预防犯罪的基本教育,打击有关食品掺假、虐待动物、虐待儿童等犯罪,还颁发养狗和经营爆炸物的许可证。他们对无证经营的沿街叫卖者、小贩和搬运工,还有旧金属经营商和街头儿童商贩进行检查和处理。他们必须处理一系列有潜在冲突的事件,如各种形式的赡养,包括有关私生子条例、《1885 年简易司法管辖权(已婚妇女) 法》(the 1885 Summary Jurisdiction(Married Women) Act) 规定的赡养条例、(改造犯罪青少年的) 工读学校和感化院学校维护费用条例。其他立法则意味着他们向习惯性酗酒的男人发出命令,涉及《1875 年雇主和工人法》(the 1875 Employers'and Workmen's Act) 法令、《1896 年友好社团法》(the 1896 Friendly Societies Act)、支付账款的法令等[1]91。
总之,新警察在处理抗议集会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和温和性,而且其无处不在、昼夜巡逻也便于加强社会管理,从而满足政府用来控制社会治安秩序的要求。自新警察建立以后,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不再由军队承担,并且到19 世纪下半叶警察的这种职责逐渐获得社会认同[13]。罗伯特·兰沃西及劳伦斯·特拉维斯Ⅲ认为,维护秩序是警察的首要职责,他们是最明确地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职责的机构[14]。
四、提供辅助服务
新警察除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以外,还提供其他一些辅助服务。警察不断巡逻,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一天中的24 小时,民众都可以找到警察,而且警察有负责管辖的权力,通常对大部分难题都能采取措施。当面临紧急事件或其他困难时,民众就与警察联系,寻求帮助或指导。因此,英国警察时刻都是向民众提供救援和帮助的主要力量,成为解决各种难题的理想“救助机构”。店铺老板求助警察赶走沿街叫卖的小贩,牧师希望警察驱散安息日的狂欢活动,邻里及家庭内部借助警察解决冲突,甚至有家长叫警察对付不听话的孩子。1871 年3 月,警员亚历山大·亨尼西(Alexander Hennessy)被一位母亲叫去逮捕她15 岁的孩子凯瑟琳·德里科尔(Catherine Discoll),原因是这个孩子偷衣服[15]。1883 年10 月,伍斯特郡警察局(Worcestershire Constabulary) 的警员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答应霍利斯先生(Mr.Hollis) 的请求,给他旷课、夜不归宿的儿子一顿暴打[8]80。警察不愿意卷入家庭事务及争端,除非这些争端在公共场合或非常严重。然而,当有暴力倾向的家人的行为超过受害人所能接受的程度时,警察通常能够满足这些寻求帮助人的需要,采取行动。
他们还帮助寻找和收容迷路的小孩。一些警队也开始建立慈善基金,用于对穷人进行救助,大部分是给他们提供衣服及鞋子。1870 年代晚期或1880 年代初期,兰开夏郡警察局的两名警监(superintendent)在他们的警区设立施食处,以赈济贫困的小孩,为他们提供衣物,甚至安排夏天进行短途旅行。“我们认为这些仅仅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警司理查德·杰维斯(Superintendent Richard Jervis) 说道,“警察除了预防及打击犯罪之外,我们认为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杰维斯筹集到的资金最初来自警察运动会,用于捐助当地的医院、当地照顾和保护年轻女子协会(a local society for the Care and Protection of Young Girls) 以及救助斯凯尔默斯代尔矿工的寡妇及孤儿。1893 年,北安普敦自治市的警察建立慈善协会,同一时期在利物浦也建立了警察资助衣物协会(Police-aided Clothing Society)。除了这些帮助之外,警员也接受事故现场救助训练。这样,当人们受伤时,警察能够在事故现场进行最初的救护。1883 年11 月,《泰晤士报》(The Times) 曾报道1 224 名大伦敦警察(相当于总人数的1/10)从圣约翰救护协会(St John's Ambulance Association)获得证书,能够进行现场急救。同一时期,在伦敦的大部分警察局都配备有救护车[8]81-82。在各自治市及地方各郡,许多警察局长在皇家警务督察卡特赖特(William Cartwright) 敦促或中央济贫委员会的支持下,安排警员担当济贫官员助手的工作[16]。
在自治市或各郡,警察还需要承担其他的工作,任务范围日益扩大。他们既要担当市场税征收员,又要依照《鲑鱼法》 (the Salmon Fishery Acts) 担当辅助的看守。1871 年复活节时,汉普郡警察局长在提交给警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内政大臣的法令可能需要他的警员从事一些其他的工作,他警告说这些可能使财政部停止拨款,特别是担任家畜检查员、牲口收押人员(impounders of cattle)、检查小贩执照人员、郡桥梁检查人员、间接税务局官员的助理(assistant excise officers) 及公路监督员助理(assistant surveyors of the highways)[8]84。这样,每一支警察力量都需要执行这些额外的工作,直到19 世纪末他们一直不断扩大,并且城市交通的增长及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地占去警察的工作时间。例如,1880 年代期间,伯明翰市警察调派13 名警员用于检查有轨电车及控制交通,并且由于交通量的日益增加,不得不把16 名用于夜间巡逻的警员转为日间执勤。这些工作的一部分以前是由当地政府承担,警察被看成是当地政府的仆人,特别是自治市更是如此,因而由警察去实施。
以上这些辅助服务,充分说明了英国新警察的任务范围日益扩大,他们既是消防队员、济贫法官员、市场税征集者,又是交通疏导者、抢险救灾以及处理其他紧急事件的后备力量。这支训练有素、能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治安力量效率大大超过以前的临时警察,其在社会服务中通过调解各种社会不平衡因素与社会矛盾,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根本上减少和抑制犯罪。此外,警察在社会服务工作中培养了公众对警察认同感,获得群众支持。公众为纪念罗伯特·皮尔对创立新警察所做的贡献,将警察昵称为“伯比”(bobby)(即罗伯特的昵称)[17]。
总之,治理是一个过程,注重多主体协调,强调持续的互动与合作[18]。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新警察的出现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偏僻小巷和贫民窟,他们(警察) 代表法律和秩序,他们又是真正的街头杂务工,是一群没有依靠或保护者的人的最好的朋友[1]89。在社会发展中,新警察不仅预防和打击犯罪,镇压骚动,维护社会秩序,而且还承担了一些辅助的服务功能,从而推动了英国社会的发展。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19 世纪晚期英国的警察似乎赢得了与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的斗争。今天,警察成为英国社会整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几乎很难想象没有他们存在的状况。警察是政府最显著的代表,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警察是他们经常遇到的当局人物。犯罪者害怕他们,醉汉、流浪者及驾车者注视着他们,小孩畏惧他们,即使守法的成年人也敬重这些身穿制服人员的权力。此外,警察也是刑事司法体制的关键。“诉讼人及法官不抓捕也不能抓捕罪犯”,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Friedman) 写道,审判及判决只有抓捕罪犯以后才能进行。警察是整个体制(刑事司法体制) 运转的关键[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