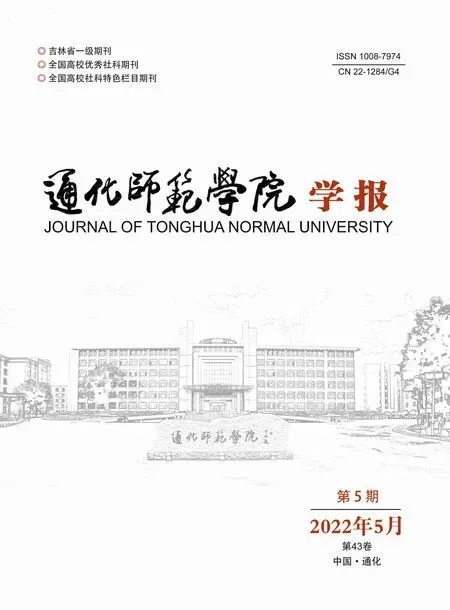读者、译者、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比较
何瑞清
国内有些学者在运用阐释学理论进行翻译批评时出现一些偏差。其一是混淆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其二是混淆翻译研究范式;其三是混淆不同翻译主体(读者、译者、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这些偏差相互联系,引起翻译批评的乱象。因此,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翻译主体的阐释学立场。本文针对第三种偏差,探讨读者、译者、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差异及其原因,分析混淆主体所致的阐释学立场错位个案,并讨论阐释学立场错位原因。
一、读者、译者、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差异
读者对文本可以自由阐释,持现代本体阐释学立场。读者阐释以阅读的文本为对象,文本自足,阅读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受其知识结构和阅读能力影响。读者自己对文本难点和隐晦点的阐释对错,自己不得而知。读者阐释正确与否,由别人按照作者意图或者阐释学共同体主流标准来判断、评价。现代本体论阐释学派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应看作是主观的行为”[1]40,主张把真前见与“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区分开来”[2]101。但是,他同时认为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3]105,由于阐释者视域偏离、超越文本视域产生误读和“创造性”。
不同的理论赋予译者不同程度的译者主体性,译者在作者中心和读者中心之间游移。译者的阐释学立场动态变化,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译者的最根本立场是古典方法论阐释学立场。“翻译本质、翻译伦理等诸多因素要求译者持有古典方法论阐释学立场,而委托人、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有时迫使译者持有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立场。”[4]35
在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下,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是不同的。传统翻译学与古典方法论阐释学的理论本质契合,译介学与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理论本质契合,译文学与一般方法论阐释学理论本质契合。此外,进行不同类型的翻译批评时,翻译批评者阐释学立场是不同的,“语言批评(尤其涉及翻译标准时)应该持一般方法论阐释学立场,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美学批评应该持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立场。”[4]28-29
二、读者、译者、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差异的原因
阐释学各个学派的理论各有所用。我们应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应该将其主张与阐释主体对应起来,或者与阐释的条件结合起来考虑。读者、译者和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是不同的,理由在于他们的身份不同,阐释对象不同,阐释活动制约的因素不同。
(一)阐释者的身份不同
读者、译者和翻译批评者身份不同。在阐释活动中,与他们相关的主体构成的关系网络不同。由于身份赋予阐释活动的性质、责任不同,他们的阐释学立场也就不同。
读者不同于译者、翻译批评者。读者阅读为了自己,阐释是自由的。按照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的观点,一般读者阐释没有对错之分,只看其合理与否;读者阐释不必忠实于作者,误读被认为是积极的行为。尽管事后古典阐释学派会批评读者误读,读者阅读时不会顾忌别人的批评。
译者处于作者、读者中间,既要忠实于作者,又要忠诚于读者。译者阐释和翻译肩负伦理义务,对作者甚至肩负法律义务,翻译制约因素较多。译者阐释学立场并非始终不变,它是动态变化的。但是,译者对作者的忠诚,对原作的忠实是不变的。当然,对原作的忠实是相对来说。译者这个时候持有古典方法论阐释学立场。而考虑读者需要,考虑文本的功能,译者翻译时做出一些变通,这时译者持有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立场。翻译批评者关系网络较为复杂,包括译者、作者、读者、原著、译著。围绕某个批评对象构成某种关系网络。翻译批评者阐释学立场受客观条件制约,因条件变化而变化,也是动态变化的。
(二)阐释的对象不同
读者阐释对象是作品,即便是“译作”,在一般读者看来还是作品。因为一般读者阅读“译作”,没有原作参照,一般来说也不会去参照原作。
译者阐释对象是原作。在翻译过程中,译作始终以原作为参照。《国际译联章程》规定译者有忠于原作的道德和法律义务。
翻译批评者阐释对象很广,涉及译者、作者、读者及他们之间关系,原作和译作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阐释学等翻译理论之间关系。但是,这些对象处于特定的场景,阐释的具体内容不同,翻译研究的范式不同,都影响翻译批评者阐释立场。
(三)阐释制约因素不同
不同主体的阐释活动受到不同因素制约。
读者读的是作品,作品文本意图不是每个读者阐释必须追求的目标。如果读者阅读的是译著,原著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对他们的阐释没有制约,读者可以自由阐释。读者视域是影响读者理解的因素。如果原文意义隐晦,不同读者阐释具有差异性。理解的多样性说明意义开放性、不确定性。
译者不是一般读者,要努力弄懂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译者对原著的阐释受翻译本质、翻译伦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可以自由阐释原著。译者的阐释学立场不因翻译研究范式变化而变化,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译者身处作者和读者之间,受以作者为中心和以读者为中心的种种互相冲突的理论困扰,译者常常面对忠实与叛逆、翻译与创作、异化与归化等两难选择。
翻译批评不是天马行空,既有标准可循,也有制约因素。制约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翻译研究范式和翻译批评类型。“每种翻译研究范式有其中心任务,有其适用的理论。翻译批评的内容决定翻译批评所适用的阐释学”[4]28-29。
三、混淆主体所致的阐释学立场错位
翻译批评者究竟应该持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立场,还是持古典方法论阐释学立场,或者区分不同的主体性,在不同场合分别运用这两种阐释学来阐释译者的主体性?
探讨译者主体性适宜用一般方法论阐释学,兼顾作者和读者。主体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5]38。然而,不少翻译批评者忽视了译者的“受动性”,即忽视译者对作者、原文忠实的天职,忽视作者中心论的古典方法论阐释学,只看到译者作为读者的属性,仅仅运用读者中心论的现代本体论阐释学探讨译者主体性。
有些翻译批评者从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的“合理偏见”的观点出发,为误译辩护,宽容误译。例如:
“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6]123。“如果强求要达到作者本人的原意,只准有一种解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6]127。
有些翻译批评者从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的“意义不确定性”的观点出发,对传统翻译标准提出异议。例如:
“文学翻译标准需要……,把文本意义看成具有确定性的‘忠实’标准转移到文本意义具有无限开放性的新的文本观研究基础上。”[7]113
“翻译标准不应该是规定性的,而应该是描述性的。……所谓的翻译标准和‘准确’‘完整’‘对应’‘切近’云云,就可以不谈了。”[8]87
“既然意义没有确定性,翻译就更不应该有确定的标准。”[9]69
为误译辩护,虚化、泛化翻译标准的观点,混淆了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混淆了读者和译者的阐释学立场,混淆了翻译批评者和译者的阐释学立场。
“合理偏见”的观点助长读者过度阐释,“误译合理”的观点导致偏为读者的译者主体性过度张扬,虚化泛化翻译标准致使翻译实践和批评失去客观标准。变译(创译)是部分偏离原文作者意图,偏向读者的折中策略。译者“不能抛开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这个根基。从翻译的本体论出发,翻译的标准还是忠实,文学翻译创造性仍然受制于原文或作者原意”[10]72-73。
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肩负忠实于读者和兼顾读者需要的双重义务。译者在内容意义上忠于原文、作者,在形式上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能动性、创造性不应该建立在背离作者原意的基础上。有些文体翻译创造性、灵活度大些,但是,总体上没有背离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译者必须尽可能靠近作者,读懂作者意图,在最大程度上使译文再现原文,这时候,译者的立场应该是古典方法论阐释学立场。
翻译批评者对译者行为批评,既不可以把译者当成一般读者,也不可以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译者。译者的阐释学立场由其身份、诸多外部因素决定。“一般读者阐释用现代本体论阐释学来批评;译者阐释用古典方法论阐释学来批评。”[4]35,[11]71
四、阐释学立场错位的原因
阐释标准是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还是读者意图?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有什么关系?作者意图对文本意图是否操控?读者阐释偏离文本意图即误读是否合理?这些是阐释学不同派别比较关注的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阐释学立场。利科[12]78指出,“解释学多样性反映了技术的差异和知识论的差异”“解释学领域的冲突场景表明不可能用一种解释学把种种相互竞争和冲突但又同等有效的解释统一在一起”[12]3。阐释学立场错位的原因在于不区分不同主体的阐释学立场,同时忽视阐释学派别的本质冲突。阐释学派别的冲突体现在阐释标准不同、本质属性不同和适用范围不同。
(一)阐释标准不同
读者按照自己视域自由阐释,否定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文本意义是开放的;反之,读者克服自己视域偏见,追求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文本意义就是封闭的。
古典方法论阐释学派以作者意图为阐释标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古典方法论阐释学承认“最终意义”和作者权威,阐释目标就是要“消除前见、避免误解、寻觅原义”[13]310。古典方法论阐释学派以理解作者意图为目标,以作者意图为参照,甚至把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加以等同。作品永远受作者原意支配,不以时间为转移。赫施指出,“作者原初所确定的含义并不会发生变化”。解释学理论中的混乱,源于忽视区分“本文含义”和“本文对作者来说的意义”。本文含义、本文意义分别是解释和批评的对象[14]18;7。读者尤其是译者没有随意阐释的自由。
现代本体论阐释学否定以作者意图为阐释标准,这是“现代阐释学的一条基本原则”[15]21。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现代本体论阐释学否定“最终意义”和作者绝对权威;伽达默尔肯定“前见在理解中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16]5,认为理解“永无达到本真世界的可能”[13]310。德里达要求人们在阐释文本意义时,“还要进一步发掘那些超出作者意图之外由文本本身所表现出的东西”[13]286。在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看来,读者阐释的文本意义大于作者的原意,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这些观点否定把作者意图、文本意图看成阐释标准。
一般方法论阐释学以文本意图为阐释标准。贝蒂批评伽达默尔“把解释对象(客体)与解释(主体)混为一谈的本体论思路”;他既承认文本的客观自在性,同时又承认读者对作者思想的再认识,“这是贝蒂认识论、方法论诠释学与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最大的不同”[16]13-14。
利科主张以文本意图为阐释标准、目标。“言说一旦被书写下来就成为某种自律的主体(文本意图)”[3]105。艾柯认为,文本意图“被用来反驳毫无根据的阐释”[17]10,[18]94,把文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检验文本意图的猜测。[19]65,[15]73文本内在统一,内容和逻辑的一致性是阐释合理性的依据。
(二)本质属性不同
如上文所述,各阐释学派在阐释标准方面有分歧。不同的阐释标准反映出不同阐释学的本质。古典方法论阐释学对作者意图孜孜以求,本质是“作者中心论”。现代本体论阐释学解构作者权威,不追求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认为读者误读是“创造性”理解,本质是“读者中心论”。一般方法论阐释学一方面是“文本中心论”,没有放弃对作者原意的追求。“诠释学的对象自主规则”、“诠释学的意义符合规则”反映了这种追求[20]52。另一方面,一般方法论阐释学“理解的现实性规则”与现代本体论阐释学“视域融合”如出一辙。一般方法论阐释学本质是“文本中心论”。朱立元认为贝蒂的一般方法论阐释学的意义观,“似可概括为融合作者与读者为一体的文本意义中心论”[16]14。
(三)适用范围不同
阐释学理论本质属性决定了阐释学适用范围。古典方法论阐释学适用于传统翻译批评,因为古典方法论阐释学、传统翻译观本质都是“作者中心论”。而现代本体论阐释学适用于文学批评,在于现代本体论阐释学、文学批评本质都是“读者中心论”。一般方法论阐释学兼顾了读者和作者,结合了古典阐释学和现代本体论阐释学的特点,适用于广泛的翻译批评,它的适用范围大于古典阐释学或者现代本体论阐释学。
五、结语
读者、译者、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然而,有些翻译批评者却无意中忽视了这个命题。我们需要重视阐释学不同派别理论的本质冲突,注意它们的适用范围,将读者、译者和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区别开来,避免误用阐释学或者混淆不同主体的阐释学立场。对混淆不同翻译主体的阐释学立场个案的评述,将有助于减少阐释学的误用和滥用现象,使翻译批评回归理性,减少翻译批评乱象。
制约翻译批评者、译者的阐释学立场的因素不同。翻译批评者的阐释学立场受制于翻译研究范式、翻译批评内容。译者对原著的阐释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受诸多因素制约,译者的阐释学立场不因翻译研究范式变化而变化。翻译批评者不能将自己的阐释学立场强加于译者,需要客观审视和批评译者行为,尊重译者在具体条件下应该持有的阐释学立场。
——关于海德格尔的“那托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