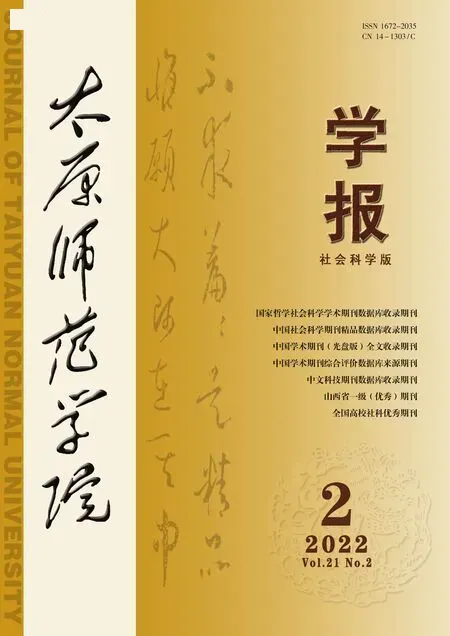中国辞格论辩观源流考
——兼与西方辞格论辩观比较
袁 影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在辞格的认知性研究普受重视的今天,渊源深厚的辞格论辩性却遭遇了不应有的忽视,本项辞格论辩观源流考力图引发关注,探寻古今辞格论辩功能的宝藏,以丰富和拓展辞格转向研究的学术空间。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从容按节地考辨,我们将划分适合的历史时段,各时段先引介相关著述,再聚焦代表加以细察,最后概述总体特征。在综合参考了《中国修辞学通史》《中国修辞史》《中国辞格审美史》(1)三部先后为: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王俊衡著《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宗廷虎、陈光磊著《中国辞格审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等的基础上,并根据出现的相关重要著作,我国辞格论辩观宜分为五大时期:先秦、汉魏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近现代、当代;在各时期的考辨中我们也将与西方修辞学史中大致对应的时期略作比较, 以明特色并示宏貌。
一、先秦:辞格论辩观的萌发
先秦具体指从东周之始平王迁都洛邑(公元前770年)至秦王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此段历史约五百五十年,开端较古希腊时期早一些,时间跨度也略长。先秦时尚未出现相当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系统著作,我们所见是一些零星讨论,主要散见于诸子经论当中,如《周易》《礼记》《老子》《庄子》《鬼谷子》《论语》《荀子》《墨子》等。这些著述中不乏各种修辞思想,甚至涉及一些辞格的定义、用法、重要性等,但大都片言只语;比较而论,孔子、荀子的言说中所涉稍多且反映了一定的辞格论辩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的修辞观体现在《易传》《礼记》《左传》《论语》等中,虽然尚未出现“辞格”之称,也鲜有论及具体的格,但已在多处谈到“文”“辞”“修饰”等可视为包含所有辞格在内的表达艺术。对含有这些词语的精言名句细加体会,对各种诠解谨慎甄别,将有助于我们探得其辞格论辩观的星光。如: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论语·颜渊》)
此两段大义相同,无论是孔子还是师承其思想的子贡均认为:文与质同样重要,君子需体现两者的完美结合。其中的“文”大都理解为“文采”,各类辞格无疑是其主要实现手段。《论语》在此强调了“文”不可轻视的重要地位。不仅于此,在《左传》中还发现,孔子甚至论及了“文”的巨大功效: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此段中的“文”,一般也理解为 “文采”或“文饰”/“修饰”,显然与辞格的运用密切相关。其中常为后世引用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指如果言辞不加修饰将难以流传,所体现的观点也就不能在现实中产生功效,因而需“认真慎重地‘文’其‘辞’”[1]28。这一见解实际上已关涉文饰或辞格的运用可以增加表现力,以使言辞产生吸引受众的在场等论说功能。而孔子在《论语》中其实还涉及了“文”的两大方面: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
此句谈论的是郑国撰写一篇外交文书需四位大夫各显其能,经四道手续合力完成。其中的“修饰”“润色”应各有所指,据李炳南《论语讲要》,前者指“修饰文句”,后者为“润色辞藻”。[2]241此两大文略与前面的内容要义之构建与讨论在整个过程中各占一半,也是质与文同等重要的又一阐发。而外交文书尚属于应用文一类,文史哲类作品就更是如此了,可见,在先秦,“文”之作用是广受重视的。
那么,孔子是否论及了体现“文”的具体辞格及其具体的功能呢?经由细辨,笔者认为具体的格在《论语》中至少有一个,即隐喻,但不易觉察,如: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孔子两次提及学《诗》的必要性,后者可以视为对前者的解释。而与辞格直接相关的是“兴”。李炳南据郑康成、郑司农、孔安国等所作注解,认为“比是显喻,兴是隐喻”[2]308。《诗经》中对草木、鸟兽的描写即可作为喻体以鲜明或含蓄地传情达意。比喻在言说中的这种话语建构功能引起了夫子的高度重视,《周易·系辞》中亦有显示: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系辞》)
其中的“立象以尽意”,《中国修辞学通史》将其理解为“注重比喻等形象手法的创造,以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力”[1]10。这与《系辞》自身的解释是基本相合的。与上述引文相隔数行,出现了核心词“象”的定义:“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其义大致为,所谓象是圣人借以用来显现天下事物深藏的道理者,它模拟各类事物并做到恰如其分。《易》中的卦和爻都是象,而《诗》中的比与兴也是象。(2)对“象”的这一界定说明是综合参考了《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及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27页)中的解释,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因此,我们可将与“言”相关的“象”主要视为比喻(兼含明喻和隐喻),语言中“立象以尽意”所表示的作用则类似于西方辞格论辩观中的理性或逻辑诉求功能。辞格的这一具体功能还可从以下名言的独到释解中推演而出:
子曰:“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此句以语录形式出现,因缺少语境,产生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大多数人认同孔安国之注:“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2]282本研究倾向于清代魏禧为代表的释义:“辞之不文,则不足以达意也。”[1]29因为这与孔子在《左传》中被引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意思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再次推出辞格之达意或传旨等的逻辑功能。而其他论辩功能亦可通过甄别相关名言的阐释进行发掘,如:
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礼记·表记》)
此句出现在该篇倒数第二段末,前人通常将两个小句作为平行关系加以解释,如孔颖达认为:“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礼,与巧言令色者异也。”也有将“情欲信”视为前提[1]28-29。笔者认为,根据此句的上文或整个段落的意思,我们未尝不可将两个小句视为因果关系,甚至将前者视为果,后者视为因或条件也似乎符合逻辑,即“情意要表现得真实,言辞也需讲究(恰如其分)”,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西方修辞学史中辞格的情感功能。而细加辨察,其他诉求功能也不难发现。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乾·文言》)
此为《文言》用以解释乾卦中的倒数第三阳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其中“修辞立其诚”的解释歧义较多,关键在于孰为因果。如果理解为“修辞要出于真诚”[1]32,那是将“诚”视为因,而如果按文天祥将其释为 “修辞所以立其诚”(3)此句出自文天祥《西涧书院释攥讲义》:“修辞者,谨饰其辞也。辞之不可妄发,则谨饰之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信。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吾之业顿隳,而德亦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致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辍,乃居业之义。”(转引自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王俊衡著《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那么“修辞”/“修饰言辞”是因,“立诚”/“树立忠信”是果,如此可以推出辞格的人格诉求功能。
以上分析显示,在数部著作中,先圣孔师已有诸多精言涉及与辞格密切相关的“文”/“辞”的重要性和各种功能,这些功能虽表述宽泛、颇具争议,但我们仍有理由推导出与西方辞格论辩观相似的逻辑、情感、人格三诉求等说服功能。
被视为先秦最后一位大儒的荀子(约前313—前238),其修辞观不似孔子散见于多部要论,而是集中于《荀子》一书。该文集共三十二篇,其中约有十篇或隐或显地关涉了文饰或某个辞格的功用等问题。论说较多并较为直接的主要有《非相篇》《非十二子篇》《正名篇》,以下即聚焦此三大代表篇目中的相关要语进行解析,以提取荀况辞格论辩观的精华。
《非相篇》中有数处关涉“文”/文采在辩论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末段中谈论三种辩说时,无论是“士君子之辩”还是“圣人之辩”,“文”均是其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
其中的“成文而类”“文而致实”,依据孙安邦的解释,意为 “既富有文采又合于礼法”“既富有文采又细致实在”[3]45,由此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文采的辩说或论辩功能。文采可涵所有辞格,辩说亦具各个方面,虽然无所不包,但尚不够明晰,而以下这段中的表述就较为具体了: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疾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櫽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
此段中的“未可直至也”,陈光磊等将其诠解为 “直白明说是达不到目的的”[1]51,这与后面的“曲得所谓焉”,即用委婉表达以说服对方的意思相一致。结合其上下文语境可知:一些具有婉说效果的辞格,如比喻、借代、低调陈述等,在论辩中可以具体起到“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契境功能。此处的论辩功能似较为具体,但相关辞格仍需从宽泛表述中加以推导。以下三处则向我们明确了所论之格: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欢、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非相篇》)
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非十二子篇》)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 (《正名篇》)
前两例中的“譬”及末例中的“比方”,均可理解为含明喻和隐喻在内的比喻,前两句中的功能主要是指用比喻的方法便于说清并易使对方明白,而这一功能本身并无善恶,因而也会为心术不正者所利用。第三例中的“比方”,据其《强国篇》中的“譬称比方”,其实是“譬”的代称,此句中的功能即为命名功能。概言之,荀子在此三处直接点明了比喻格并涉及了其命名、说理等逻辑功能。而对于“譬”的该项功能,他不仅仅是揭示者,《荀子》中的许多篇目就是通过广泛地运用比喻使得说理生动晓畅并深入人心。如《劝学篇》中,“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驽马十驾”等十个比喻都是为了阐明其观点:“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可见,荀况既发表了较为鲜明的辞格论辩思想,(4)他的辞格逻辑功能体现在多个环节中,据陈光磊等对《正名篇》中关于命(命名事物)、期(组词会意)、说(说解道理)、辨(论辨疑难)的解释,这些方面“都需要文饰”,参见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王俊衡著《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同时也力行实践了自己的这一论辩观。
先秦时谈到辞格逻辑功能十分显著的还有《墨子·小取》。该篇不仅对“辟”/譬予以了界定,“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即以他事物来说明此事物,还将其视为四种论辩方法(辟、侔、援、推)之首。(5)四个方面的完整表述为:“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据陈光磊等所释,“侔”可含对偶、排比等格,而“援”含反诘(参见《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那么,可以说《墨子》中的辞格之逻辑功能就不止于比喻了。其实,《老子》中也涉及辞格的逻辑功能,典型地体现在第七十八章所总结的“正言若反”这一反言格(相当于Paradox),即表面矛盾,而实际不无道理的话语,如“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 无疑,此格具有表达哲理的逻辑功能,且为《老子》五千精妙的立言主方。《庄子·天下》也涉及辞格的论辩功能,如“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以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中,可以明确的辞格就有寓言和重言/用典,所发挥的论说作用至少有契境功能,《庄子》本身就广泛地使用了此两格,作为在乱世中托言传意的主要手法。此外,考察《鬼谷子》诸篇,其《反应》中的“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要让对方敞开实情,可用比拟等引导他,以驾驭其言辞),及《揣篇》中的“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也”(揣摩对方实情时需修饰言辞使具文采,然后再作议论),(6)此两句释义借鉴了白松青的《鬼谷子》相关中译,参见《孙子兵法·尉缭子·鬼谷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221页。我们或可得出辞格还具有导引功能和揣情功能。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已出现对比喻、对照、排比、反问、用典、反言诸多辞格的讨论,与古希腊在数量上相当,虽然在具体的格上有出入;所涉论辩功能也较为丰富,逻辑功能为主,情感、人格、契境、导引、揣情也颇为鲜明,而后两项功能在考辨西方辞格论辩观时,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其他时期均无发现,可谓我国辞格论辩观的独特贡献。总之,先秦的辞格论辩思想虽星星点点散见于诸子文集,将之汇聚,熠熠之光不逊于古爱琴海的论辩涛声。
二、汉魏南北朝:辞格论辩观的茁生
汉魏南北朝时期实际上跨越了从秦统一(公元前221年)至陈朝灭亡(公元589年)约八百年历史,主要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因秦统治仅15年,故标题中未加体现。这一阶段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的古罗马时期基本相当。此间关涉修辞问题的著作明显多于先秦,且总体上论说较为具体、深入,亦不乏辞格论辩观的各种阐述,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说苑》、扬雄《法言》、王充《论衡》、挚虞《艺文类聚》、沈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等。其中,以东汉王充的《论衡》与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最具代表性,后者所展现的体系与精微,堪与古罗马《献给赫伦尼厄斯的修辞学》(7)该书(Rhetorica ad herenniu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首次系统阐述了五大修辞范畴,即修辞发明、布局、文体、记忆、发表,并对辞格作了最早的体系性论述。该书作者佚名,洛布文丛将之暂归西塞罗。媲美。
王充的《论衡》涉文、史、哲、语言、科学等众多领域,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有关修辞的论述十分丰富,被誉为“中国修辞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座丰碑”[1]239。其辞格论辩思想主要体现在《物势》《超奇》《书解》《自纪》中,以下即选此四篇中的要语来考察王充辞格论辩观的风貌。
首先,《物势》篇中的末段就十分鲜明地反映了辞格的论辩功能:
一堂之上,必有论者。一乡之中,必有讼者。讼必有曲直,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亦或辩口利舌,辞喻横出为胜;或诎弱缀跲,蹥蹇不比者为负。以舌论讼,尤以剑戟斗也。利剑长戟,手足健疾者胜;顿刀短矛,手足缓留者负。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 故夫得其便也,则以小能胜大;无其便也,则以强服于羸也。[4]49-50
该段生动地指出:论辩中“辞喻横出为胜”;“辞喻”如“利剑长戟”,可使言者“手足健疾”,因其“巧便”不仅易于得胜,且“以小能胜大”。而“辞喻”,据上文所论的“夫比不应事,未可谓喻也”(比拟如不与所论之事对应,则非比喻),主要指包含明喻和隐喻的喻格,因之可将该段概括为比喻的论辩功能。至于具体的功能尚不明显,但依据《自纪》中的“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我们不妨将其视为说理或逻辑功能。
辞格的这一论辩功能也反映在《超奇》关于“奇巧”的论说之中:
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 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銛则割不深。[4]213
此处将含辞喻的“论说”比作射箭中的“弓矢之发”,论说到位比作“矢之中的”,而“奇”或“巧”,即言说中的高招,其实与“心”/质是一体的,也就是前述的“文犹质也”。因而王充认为,“足不强则迹不远”,可理解为文不妙则意不能远传,联系其上下文,指的应是:只有具奇巧表达效果的辩说才能真正将言者的情志充分表现出来。
情志的抒发需通过妙辞来实现似更为清晰地体现在《书解》中,如在开首王充即指出:
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扎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 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4]431
该段阐明了圣人、大人也要通过“辞”/“文”来传达深情与厚德,但普通的文辞未必会产生理想效果,必须具有“炳”(光彩鲜明)的特性,这样的文辞通常不能不运用比喻等辞格。分而述之,“德弥盛者文弥缛”不妨视之为辞格的人格功能;“圣人之情见乎辞”“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可视为辞格所发挥的情感功能。
王充的修辞观相比于先秦的片言只语已然详实了一些,但《论衡》中鲜有相关专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却可谓一部围绕“文”的修辞学宏著。《文心雕龙》洋洋五十篇,关及文辞论辩性的篇目众多,代表性的有“总论”中的《原道》《徵圣》《宗经》,“创作论”中的《情采》《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前者发“文”之宏论,后者阐“辞”之精微。“文”不容轻忽之功用在首三篇中均有论述,如“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原道》)、“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徵圣》)、“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8)此句之意,周振甫译为:“文辞凭德行来建立,德行凭文辞来传播,孔子用文辞、德行、忠诚、信义来教育人,而以文辞为先,可见文采跟其他三者的互相配合。”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宗经》),限于篇幅不予展开。以下将聚焦创作论中的诸篇以提取刘勰辞格论辩观的精要。
《情采》可谓《文心雕龙》辞格功能论的序曲。刘勰所说的“情”为“情理”,“采”即指“文采”,包括“对偶、声律、辞藻”等[5]285,该篇指出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即辩说是情和辞/采两者的经纬相合,并且主张“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而艳说辩雕的目的则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理”,显然这已涉及了文采(辞格)的理性或逻辑功能了。但此篇尚未论及具体辞格,对偶、比喻、夸张、引典及其功能则先后出现。
《丽辞》专论了对偶的成因、分类、优劣、功能等,与论辩功能相关较紧的有最后两段中的“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及“左提右挈,精味兼载”,前句可理解为运用对偶应起到说理圆整、用例丰富的作用;后一句周振甫释为“像左提右带,精华和韵味两样都备”[5]321。综合此两句,我们认为,刘勰论及的主要是对偶的说理或逻辑作用,但也含有一定的情感功能。
《比兴》讨论了两个辞格,“比”相当于明喻,“兴”可视为隐喻,作者在首段即对两者的定义、特征、功能等予以了鲜明阐述: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关于功能,“比”起附理作用,即“切类以指事”(用打比方来说明事物),这无疑是属于逻辑功能;“兴”则为了起情,即“依微以拟议”(依照含意隐微的事物来寄托情意),这应主要属于情感功能。然而,之后比的“畜愤以斥言”(怀着愤激的感情来指斥),兴的“环譬以托讽”(用委婉的譬喻来寄托用意)似又表明此两格可交错其功能。(9)此段括号中的释义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由此,刘勰认为“比”和“兴”都具有逻辑和情感功能,而比/明喻偏重论理,兴/隐喻倾向情感。
一格可具多种论辩功能更充分地体现在《夸饰》中: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
在此开篇语中,刘勰实际上指出了无论是形而上的道还是形而下的器都需通过夸张手法才能将其奥妙和真相淋漓尽致地描摹出来,这种“豫入声貌”的摹画理应是兼具理性与情感功能的。而其末段中的,“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周振甫认为夸张如果能“尽量抓住事物的要点,那末读者心理的共鸣就会蜂拥而起”[5]335,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夸张的认同功能。
关于用典格的《事类》则集中阐述了说理功能。首段中,刘勰即鲜明地指出: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此段首先给出了“事类”的定义,“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即用经典的“前言往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一界定即已体现了该格的功能——论证。之后的“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则再一次阐述了用典格“明理”或“徵义”(证明某义)的逻辑功能。
从秦汉至南北朝,相关辞格的论辩功能较为直接的还有西汉后期的刘向、扬雄,晋代的挚虞,齐梁的沈约等。刘向不仅强调“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说苑·善说》),(10)此处引文及本段中的其他引文取自《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该著为此两阶段的梳理提供了诸多重要线索。且指出“连类引譬”是“惟若辩通,文辞可从”的一大方法(《辩通传·颂义小序》),即比喻具有辩明道理的论说功能。(11)刘安及其门人所编撰的《淮南子·要略》中亦不乏相关论述,如“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转引自祝克懿等编《启林有声》,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66页)。扬雄在对文质关系的讨论中其实也涉及了辞格的论辩功能,所谓“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太玄·玄莹》),也体现了“文”/“辞”的理性与情感功能,而由“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法言·寡见》),似还可得出“文”(此处为“修饰”)具有传道功能。挚虞在《艺文类聚》中更为直接地关涉了“辞”“象”的情感等功能,如“情之发,因辞以形之”,再如“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沈约则在《谢灵运传论》中阐述了情志与所用表达手段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思想(“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那么作为表达效果突出的辞格自然有助于实现情感、人格诉求等功能。
总体而言,汉魏南北朝的辞格功能观主要涉及逻辑、情感、人格、认同、传道功能,虽然理性功能仍占主导,但情感与人格功能似比先秦更受重视,各论辩功能的阐述也趋于鲜明和具体,并出现了《文心雕龙》颇具体系性(12)《文心雕龙》的体系性表现在既有关于修辞的总论——原道、宗经等,又有文体、创作、批评的细论,可以说是一部集修辞哲学、修辞诗学、修辞技艺及修辞批评于一体的系统之作。的修辞学著作,虽然刘勰未如《献给赫伦尼厄斯的修辞学》作者那样对辞格加以分类论说,所涉辞格也远不及其多,但《文心雕龙》对比喻、夸张、对照等的论辩功能阐述之精微,比古罗马修辞手册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唐宋元明清:辞格论辩观的延展
由于隋以后数个朝代,含辞格论辩观较为鲜明的著作并非很多,因而将其组在一起,从6世纪末至19世纪末约一千三百年,大致相当于西方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其间出现的相关论述较突出的有唐代刘知几《史通》、韩愈《争臣论》,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南宋陈骙《文则》,明代高琦《文章一贯》、郭子章《喻林序》,清代魏源《诗比兴笺序》、包世臣《安吴四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陈骙的《文则》(被誉为“中国修辞学成立的标帜”[6]241)及高琦的《文章一贯》。下面即以揭示此两书中的相关要语为主,以其他各著中的言论为辅,大致反映这一时期的辞格论辩观。
陈骙的《文则》地位显耀,被视作我国首部修辞学专论,此誉虽不无争议,但该书对辞格研究的贡献还是十分突出的。其中列述的辞格先后有:反复、对偶、倒装、比喻、援引、层递、反语、排比。对这些辞格的讨论大都涉及了论辩性, “《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说明《诗》中的“比(比喻)”所起的作用如同《易》中的“象”,因此所谓“达情”也有“尽意”之义,我们应将此处的“情”作广义理解,达情的作用既有情感功能又有逻辑功能,甚至不乏人格诉求的作用。这种一格数项论辩功能的情况也出现在陈著对反复、复叠的论述中:
《诗》、《书》之文有若重复而意实曲折者。《诗》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贤之意自曲折也。(甲六 词语反复,表意曲折)
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后已。《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丁二 复叠修辞释例)
如果我们将反复、复叠视作一个类别的辞格,(13)宗廷虎等在《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讨论梁章钜《退庵随笔》中的“复叠”时,认为这即是“修辞学中的反复辞格”。可以说前一段指出了该格的委婉功能,而后一段清晰地表明了其“析理”功能,即“反复剖析事理,直到把道理讲透才停止”[7]66。
相关于论理或逻辑功能的还有其“援引”,即用典格:
且左氏采诸国之事以为经传,戴氏集诸儒之篇以成礼制,援引《诗》、《书》,莫不有法。推而论之,盖有二端:一以断行事,二以证立言。(丙二 论援引的作用及方法)
此处不但说明了用典的逻辑功能,还细分出了两类:“用引文来判断所作的事”;“用引文来证实所说的话” 。[7]50《文则》中辞格的逻辑功能还涉及了其他维度,如论排比时,“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则表明了该格具有增广含义的作用。再如论倒装时,“于文虽倒,而寓意深矣”,揭示了该格可起加深文义的功能。
因此,笔者认为《文则》对辞格的论辩性是有较强意识的,尤其是在理性诉求方面,此前著作中未见含如此之多的理性维度。但陈骙对辞格的其他论辩功能仅略有涉及,关于对偶、层递、反语的论述并未体现论辩观,可能是由于对这些格的讨论过于简略所致。
同样可视为具有一定修辞思想体系的还有明代高琦的《文章一贯》。但高著似只有日本翻印本存世,可能因此未引起我国修辞学史家的重视。该书由两卷组成,卷上围绕“立意(文章主题)、气象(作者的气势)、篇章句字”[8]136汇集相关资料,卷下则聚焦于相关篇章句字的修辞“九法”,即起端、叙事、议论、引用、譬喻、含蓄、形容、过接、缴结,其中有多法关涉了辞格及其论说功能:
文之律渊乎,其寡谐哉!意不立则罔,气不充则萎,篇章句字不整则淆。吾于是立起端以肇之,叙事以揄之,议论以广之,引用以实之,譬喻以起之,含蓄以深之,形容以彰之,过接以维之,缴结以完之。九法举而后文体具,体具而后用达,执一贯万,嗣有作者其弗渝哉![8]132
此段中的“引用”“譬喻”“含蓄”“形容”四法或涉一格或含数格,且均与论辩相关。“引用”与“含蓄”主要体现逻辑功能,前者着力于提供论据,如所提14种引用之一的“列用”,即“广引故事,铺陈整齐”[8]134;后者(似可含反叙等格)旨在微妙地表达深义。“譬喻”似更多地体现了情感功能,而含比喻、借代等格的“形容”,则有彰显内容使其更具有在场性的论辩功效。(14)《文章一贯》可能仅存日本宽永翻印本,笔者未见因而不能给以具体阐发。此部分的梳理主要依据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2-137页)中提供的材料。此四大相关辞格的手法与其他五法同为“文之律”,即《文章一贯》中的“一”之所指,而“一贯”,即“执一贯万”[9]67,意为掌握了“九法”文律就能写好各种文章,可见高琦对于修辞手法/辞格的语篇功能是十分重视的。
此阶段其他著述对修辞的讨论虽未成体系,但也含有较为鲜明的辞格功能论。初唐刘知几的《史通》就作了相关论辩性的阐发,如“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自序》)及“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叙事》)皆较为明显地含有辞格的理性功能。而盛唐时韩愈的“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可谓涉及了辞格的最高论辩功能:明道功能。北宋沈括《梦溪笔谈》里也论及了众多辞格,其中一些涉及论辩性,如认为倒装具有“语反而意全”的理性功能,又如指出错综格具有“语势矫健”的功效。为我国第一部比喻辞典(徐太元《喻林》)作序的明代郭子章则生动地论述了辞格的明道与理性功能,如“议道匪喻弗莹,议事匪喻弗听”(《喻林序》)。为另一修辞要著作序的清代魏源还指出了辞格的委婉功能和情感功能:“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词不可径也,故有曲而达;情不可激也,故有譬而喻焉”(《诗比兴笺序》)。从晚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的“托谕不深,树义不厚”(“谕”即“喻”),也可得出比喻的鲜明说理功能。比较而言,包世臣《安吴四种》中有更多讨论,无论总述还是细论时均有相关言说:
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 《文谱》)[6]544
至于繁复者,与垫拽相需而成而为用尤广。比之诗人,则长言咏叹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极情尽意,茂豫发越也。[6]546
第一段中所谓的“六者”含有不少辞格,如对偶(“偶”)、复叠(“复”)、倒装(“逆”),而如果对这些手法不明白则不能深知古人的文意或文旨,我们可视之为辞格的理性或逻辑功能。第二段论及复叠格的作用,“极情尽意,茂豫发越”,则既有逻辑又有情感功能。
总之,唐宋元明清涉及了诸多辞格的讨论,辞格论辩观的维度也更为丰富,除了此前提及的主要功能外还有在场、委婉等功能,而逻辑功能的体现尤为细致,如断事、证言、广文义、深文义、明道等,但论述大多停留在片言只语,缺乏深入具体的阐述。西方此阶段辞格论辩观进入了繁盛期,出现了中世纪圣徒比德《转义与非转义辞格》、文艺复兴时期威尔逊《修辞艺术》与皮查姆《雄辩园》、启蒙时代坎贝尔《修辞哲学》与布莱尔《修辞与美文》(15)五部代表作先后为:The Venerable Bede,Concerning Figures and Tropes,in J.Miller,et al.,eds.,Readings in Medieval Rhetoric,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pp.96-122;Wilson,T.,The Art of Rhetoric,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Peacham,H.,The Garden of Eloquence,British Library,1593/2011;Campbell,G.,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3;Blair,H.,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Bibliolife,1819。等一批相关力作,深入探讨的论辩功能除了逻辑、情感、人格,还有丰裕、简约、活力等,显示出比我国辞格论辩观更为强劲的势头。
四、近现代:辞格论辩观的渐兴
此处的近现代与《中国修辞学通史》中的时段相仿,主要指20世纪上半叶,与西方修辞学中的近现代时期基本一致。随着西学东渐及日本修辞学的影响,我国在此阶段,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引起学界关注的修辞学专论,大多为当时的教科书。但涉及辞格论辩观的并不多,主要有:唐钺《修辞格》(1923)、王易《修辞学通诠》(1930)、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193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章衣萍《修辞学讲话》(1934)及陈介白《新著修辞学》(1936),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唐钺《修辞格》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修辞格》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辞格(也是该名称之首现)的专论,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作为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唐钺的辞格研究体现了视野的宏阔与精锐,与当时甚至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不同,他仅视辞格为“修辞法的一小部”[10]89,而对此小部分的考察也反映了其眼光的精锐。他从逻辑和心理的维度出发将27个常用格划分为五大类(16)该分类系统,唐钺在《修辞格》(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3页)“绪论”中称“略依纳斯菲高级英文作文学(Nesfield’s Senior Course of English Composition)里头的分类而斟酌损益”形成的。:其一,根于比较的,含类似(如“显比”“隐比”)与差异(如“相形”/对照,“阶升”/层递);其二,根于联想的(如“伴名”/转喻,“类名”/提喻);其三,根于想象的(如“拟人”“呼告”);其四,根于曲折的(如“诘问”“婉辞”);其五,根于重复的(如“反复”“排句”)。这一分类本身体现了辞格的论辩功能,前两类主要关涉逻辑功能,第三类更富有情感功能,第四类相关人格功能,最后一类则反映了在场功能。唐钺的五类辞格相比其他分类,如《修辞学发凡》中的 “词语上的辞格”“章句上的辞格”等,更具论辩色彩;但这一论辩性又未必是有意识的,从他综述的辞格三作用,即“帮助人们发展自表的能力”“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一种美感的娱乐”[10]2,还看不出明显的论辩性;而在专论27个辞格时,主要是提供中文典籍中的语例,在很少的功能论述中,仅个别辞格涉及了论辩性,如“欲表现强烈的感情或意见”[10]80的反复可谓体现了情感与逻辑功能,“表面上好像含着两个互相矛盾的意思,但是却有深意在内”[10]33的反言隐约涉及了逻辑功能。因此,可以说唐钺《修辞格》中的论辩观尚属于非自觉的性质。
被视为我国现代修辞学创立标志的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深获学界重视,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其辞格的论辩功能尚未获得关注,以往的研究着力于《修辞学发凡》中辞格的定义、分类或例证特点。确实,陈望道关于积极修辞的讨论围绕的正是这些方面,鲜有论及功能。但我们在其开宗明义的“引言”中却发现了几处颇具代表性的相关阐述,如:
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 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11]3
该段中,首先陈望道先生对“修辞”作了重要界定:“达意传情的手段”,之后对此进行了释义,其中反复强调的是为了“意”和“情”,而《修辞学发凡》中的修辞手段含积极和消极两大类,积极修辞即辞格。那么这些辞格的作用就是为了“达意传情”,也就是相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逻辑功能与情感功能。而在比较两类修辞的差异时,陈望道又强调:“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11]9。”似乎相比于“传情”功能,辞格的“达意”功能并不突出;然而积极修辞显著的“应境”功能“正是灌输题旨的必需手段”,引言在其后作了如下补充:
这种随情应境的手法,有时粗看,或许觉得同题旨并无十分关系,按实正是灌输题旨的必需手段。…… 也就是要根据写说时的实际情况,调动和创造各种表现手法,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地传达自己的观点、意志到对方。可以说,语言是我们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或武器。我们倘若用武器来做譬喻,便也可说修辞是放射力、爆炸力的制造,即普通所谓有力性动人性的调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同立言的意旨无关的。[11]11
此段无论是开头还是结尾都表明了积极修辞的应境与传达“意旨”的密切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境/契境功能与逻辑功能是一体的。而该段中,陈望道将辞格比作具有“放射力、爆炸力”的“武器”,又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西塞罗的《论雄辩家》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拉米的《言说艺术》中所发出的辞格武器说。(17)所涉两书先后为:Cicero,On the Ideal Orato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Harwood,J.,The Rhetorics of Thomas Hobbes and Bernard Lam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总之,在《修辞学发凡》中,辞格也绝非简单的装饰,而是兼具应境、达意和传情的工具或武器。
除了陈望道与唐钺的辞格功能观外,同时代王易的《修辞学通诠》则注重于“如何表达”才能令人“动情”[12]331。章衣萍《修辞学讲话》发表了类似观点即“能令人感动,就是修辞格的用处”,并认为有助简洁化、具体化的辞格及增强语势的辞格“是使人感动的最大的方法”。[12]438而陈介白《新著修辞学》在论及各个辞格时几乎均展现了情感功能,但也涉及了加强注意力等功能,如认为表出类辞格因“形式非凡”而能起到“刺激感情与注意较强”的效果,“对于思想的集中,更加一层便利”。[12]342比较而言,与《发凡》同年出版的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对辞格论辩功能的表述更为鲜明,在讨论“藻饰”/辞格时他指出:
所谓藻饰者,非镂月裁云,雕章琢句之谓,亦谓正言之不足以道达情意,乃求一曲达之方之谓也,其所以名藻饰者,亦因袭成文,取其为人所习知也。[12]529
金兆梓之论颇似陈望道的“达意传情”,并且还细化出了辞格以实化虚、以动化静、以浅化深等五种实现曲达情意的途径。
总体而言,我国近现代对辞格的研究突出表现在分类的细致与语例的丰富,功能讨论相对较弱,而辞格的论辩性集中于情感与逻辑,人格、契境、在场等功能也时有论及。与尼采《论修辞与语言》、伯克《四大转义主辞格》(收于《动机语法学》)和《动机修辞学》、约瑟夫《莎士比亚的语言运用艺术》(18)四书先后为:Gilman,S.et al.,Friedrich Nietzsche on Rhetoric and Langu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Burke,K.A,Grammar of Motiv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5/1969;A Rhetoric of Motives,UCP,1950/1969;Joseph,M.,Shakespeare’s Use of the Arts of Langu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7/2013。等同时代西方力作中的辞格论辩观相比,我国此阶段主要借鉴了欧美及日本较通俗的相关研究,对辞格论辩功能的探索尚缺乏哲辩性与体系性。
五、当代:辞格论辩观的多元化
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约七十年间,除去文革阶段的停滞,辞格的研究可谓成果连连,涉及论辩功能的著作主要有: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朱祖延《古汉语修辞例话》(1979)、钱钟书《七缀集》(1985/1994)、吴士文《修辞格论析》(1986)、王德春等《现代修辞学》(1989/2001)、李济中《比喻论析》(1995)、王希杰《修辞学通论》(199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2004)、谭学纯等《汉语修辞格大辞典》(2010)、袁影《修辞批评新模式构建研究》(2012)等。以下选择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与刘亚猛的《追求象征的力量》分别作为上世纪后半叶与本世纪初的代表作予以重点梳理。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被公认为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又一里程碑。该书有多章专论修辞方式,共涉及三大类(描绘、布置、表达)24个常用辞格,突出之处在于,作者在论述各辞格时不仅有定义、分类、例证,还有十分鲜明的功能讨论,如他对描绘类辞格中比喻的作用说明:
比喻在社会交际中能起种种作用。主要的是利用这一种描绘手段帮助大家对事物特征的具体认识;利用喻体的形象引起想像,让大家受到感染(喻体鲜明、生动,听众读者就会受到强烈的感染)。比喻的实际价值就在这里。[13]83
此段中分号前后其实各涉及了一个论辩功能:逻辑与情感。此两功能还可从张弓对“比喻式”所作的界定阐释中获得进一步确认:“比喻可以造成语言的具体性、实感性、鲜明性,并且可以通过‘喻体’透露说话人对本事物的爱憎情感,表示对本事物的褒贬意味、肯定否定态度。”[13]82如果说逻辑功能尚属勉强,其情感功能无疑已经表述得相当细微了。对于逻辑功能该书在对其他辞格的讨论中作了十分典型的揭示,如关于布置类辞格中的排迭式即排比,张弓指出,“政论文、科学论文、论理文用排迭,可以将道理阐发得透彻充分”,并且他发现“现代汉语,复句分句排迭(因果、让步、条件、时间等复句的偏句的排迭)特别发达。这样的情况反映出思维的精密性,反映事物的复杂的因果关系”[13]155。与大都侧重排比的情感功能讨论不同,张弓更着力于凸显该格的逻辑功能。
除了逻辑和情感功能,《现代汉语修辞学》也涉及其他论辩功能,如在论述表达类辞格中的问语式时,张弓指出:
这种问语具有艺术性,能正确反映思维过程,能掀起说话或文章的波澜,能使群众集中注意力,能引起深刻活泼的思考,有的并能激起群众的感情。[13]177
各类语体,文艺作品、政论文、科学论文、公文、口头语、书面语,都有时需要问语式。诗歌和文艺散文的问语式,有抒情作用,通过问语(正问式)可以委婉地深刻地表达情感。政论文、科学论文的问语式,有的是解说,有的是辩论。解说辩论用问语式,主要是为的树立对立面,揭露矛盾的实质。[13]185
这两段关于修辞问句作用的说明,至少包含了逻辑、在场、情感与委婉功能,而逻辑功能实际上又划分出了“解说”功能与“辩论”功能,在上世纪60年代对辞格的功能有如此具体的总结十分难得,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辞格视域,甚至还直接与“辩论”挂上了钩。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可谓我国迄今体现辞格论辩性最为突出的著作。该书以整个人文学科为宏阔背景,对修辞学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结合当代西方主流话语作了鞭辟入理、新见迭出的阐发。全书由五章构成,末章“修辞格与修辞‘密码’”浓缩了作者对辞格论辩功能的诸多深见,尤为突出的是鲜明地提出了“辞格是修辞发明的基本手段”这一至关重要的命题。“修辞发明”(Invention)是西方修辞学中与说服最为密切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总结的三大说服手段——逻辑诉求、人格诉求、情感诉求,即从属于此范畴,《追求象征的力量》在论证该命题时侧重于逻辑诉求并聚焦于其中的命名功能和创新功能。
关于辞格强大的命名功能,作者精到地分析了“9·11”事件中布什政府所运用和配置的几个“基调辞格”——“战争”(将该事件作定性夸张)、“反恐”(以属代种的提喻)与“邪恶轴心”(喻指与美敌对的国家):
从使用几个精心挑选的辞格为一个突发的不可名状的事件命名开始,作为美国首要政治修辞者的布什成功地主导了对宏观“修辞形势”的界定,密切了自己与目标受众(也就是美国公众)之间的关系,促成了一整套新形势下的话语规范的形成,控制了公共舆论的生产,并且赢得了公众对他的政府在“反恐”的名义下采取的一系列越轨的国家行为的普遍支持。[14]238
《追求象征的力量》不仅揭示了辞格举足轻重的命名功效,也对与之紧密相关的创新功能予以了深入阐发,认为任何新观点、新模式、新思潮等都可视为“一个新出现的隐喻”,因而任何突破性的思想观念“不能不以一个全新的隐喻被发明出来为前提” 。[14]241这一看似颇难证明的论断,我们在该章第七节“辞格与修辞的创新策略”中发现了具有信服力的论证:
就是在日常语境中,一个真正新奇的说法、论点或表达要想在话语的激流中站稳脚跟也不能不倚重辞格的应用。蒲柏在修辞仍然为整个西方社会所敬重的十七八世纪之交对它进行的讥讽和批判,是通过隐喻(修辞作为一个分格多斗橱)和反喻(正儿八经地提出公众出资制造这一个大橱子的建议)的融合进行的。辞格的巧妙应用既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修辞抱有的那个在他所处的时代显得匪夷所思、怪异新奇的视角,又使得这一观点的表达听起来谑而不虐,可以为一个新古典主义时代的保守受众所接受。[14]250-251
以上的典例分析说明,尽管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对修辞所发的新论不无偏失,甚至有失公正,但通过“分格多斗橱”这个新隐喻,让这一不寻常的看法深入人心。
《追求象征的力量》对辞格论辩性的探讨并未限于创新功能与命名功能,在评述热奈特、伯克、科恩等20世纪思想大家的辞格观时还丰富地诠解了吊诡、转化、亲近(19)亲近功能源自Ted Cohen关于隐喻的功能;转化功能源自伯克四个转义主格(隐喻、提喻、转喻、反讽)的“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并由此产生“模棱多可”的论说效果;吊诡功能源自热奈特所论,辞格“可能很普通又绝对不简单,因为它同时负载着在场和不在场成分”。参见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0-222页。等尚未引起关注的辞格论辩功能,并通过布什政府所用的那些喻格之功效,对佩雷尔曼的“论辩性辞格”(20)关于“论辩性辞格”,佩雷尔曼在《修辞学王国》中指出:“如果辞格的使用导致视角的改变,而且这一辞格在其带来的新形势中显得毫无反常之处,那么它就是一个论辩性辞格。”参见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9页。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发。
前文提到的其他研究者也对辞格的论辩性或显或隐地发表过诸多值得关注的观点。朱祖延在《古汉语修辞例话》中划分比喻类型时曾指出,“推理性的比喻,其特点在于它能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道理,使人对所论证的命题确信无疑,因而可以增强文章的逻辑说服力”(21)此处及相关李济中的引文参见郑子瑜、宗廷虎主编,吴礼权、邓明以著《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250页。,即十分鲜明地揭示了一些比喻所具有的逻辑论证功能。比喻的这一功能,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也有相关表述:“‘如’而不‘是’,不‘是’而‘如’,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钱钟书在此也谈及了比喻的“情感价值”[15]43,而于《管锥编》中所阐发的著名“喻之二柄”(“取譬相类,而命意适反”)和“喻之多边”(“指同而旨则异”)(22)此处引文转引自宗廷虎、陈光磊、冯广艺主编,高万云著《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2页。之说依然体现了该格的逻辑与情感功能。被视为喻研佼佼者的李济中在《比喻论析》中更为直白地论述了该格的诸多重要功能,总结的五功能里就有三个关涉论辩性,即“深奥道理浅显化”“事物本质鲜明化”“爱憎感情强烈化”,分别涉及了逻辑、在场、情感功能。吴士文则在《修辞格论析》中首次提出了辞格的畅通信道功能:“根据一定的题旨、情境恰当地运用修辞格是能够使信道畅通,增大语言的信息量,从而加强说写的效果的”[16]13。王德春、陈晨在《现代修辞学》中也涉及了该功能;他们还论及了辞格的逻辑功能(对偶和引用等)、情感功能(排比和呼告等)及谋篇功能(反复和层递等),并显示了一格具有多种功能,如排比“在内容的表达上能够多侧面、多层次地来集中事理、渲染感情,使叙事说理周密细腻,表达感情奔放舒展”[17]326,可见,他们认为排比兼具逻辑与情感功能,且该格也是其谋篇功能的代表。关于谋篇,谭学纯在《汉语修辞格大辞典》的前言中尤为强调,并细化出了“辞格的叙述调节功能和语篇建构功能”[18]7。辞格的谋篇功能,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也举了对照和反复在余光中《乡愁》里的典型体现;同时还论及其他诸多功能,新颖的有“修辞格的解码功能”,即“没有修辞格知识,就不能正确地进行解码活动”[19]406。笔者的《修辞批评新模式构建研究》[20]则通过修辞手段(含转义与非转义辞格)与修辞发明(含修辞推论与争议点)的互参来评价各类语篇的修辞得失,这种互参关系也是辞格论辩性的一大反映。
以上梳理显示了当代辞格论辩观的自觉化和多元化,论辩性的探讨不止于逻辑、情感等常见功能,还出现了创新、吊诡、谋篇、畅道、解码等功能。但我国现今的辞格论辩性研究缺乏系统性,上述发现均取自综合性著作,尚未见相关专著面世。西方当代不仅出现了一批发表在《论辩》等大刊上的专论,如科兹《辞格的论辩功用》、勒布尔《辞格与论辩》、克劳斯《从辞格到论辩》等,还出现了法恩斯托克《科学中的修辞格》这样深入剖析辞格论辩性的专著,(23)四作先后为:Kozy J.,The argumentative use of rhetorical figures,Philosophy & Rhetoric,1970,pp.141-151;Reboul O.,The figure and the argument,From metaphysics to rhetoric,Springer,1989,pp.169-181;Kraus M.,From Figure to Argument:contrarium in Roman rhetoric,Argumentation,2007(1),pp.3-19;Fahnestock J.,Rhetorical figures in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这些着力于逻辑功能的前沿成果预示了系统探索辞格论辩功能的广阔前景。
六、结语
至此,我们扼要考辨了中国辞格论辩观史,虽远非全貌,但在有限的篇幅中,可领略我国辞格论辩观两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景况。源流考从先秦、汉魏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近现代、当代的相关要著中考辨出近二十种辞格论辩功能,如逻辑、人格、情感、契境、在场、谋篇、吊诡、认同、传道等;细察了诸多论辩性辞格,比喻、夸张、用典等转义格与对照、反问、反复等非转义格;简要比较了西方相应阶段的辞格论辩观。研究发现,我国涉及的论辩性辞格及辞格的论辩功能与西方大致相当(虽各涉一些独特功能),甚至在总论方面也有相似处,如源自先秦的“文犹质也”“文质彬彬”与始自古希腊的“饰”即为“论”的饰论不二观较为接近;主要差别则在于中国辞格论辩观在古代大都是吉光片羽,在现当代仍较零散,未能如西方的专论产生冲击。辞格论辩性的系统研究应成为我国辞格转向中的后浪,在激发自身能量的同时,可推助辞格认知论等的深入,或可引动论辩产生知识的辞格认识论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