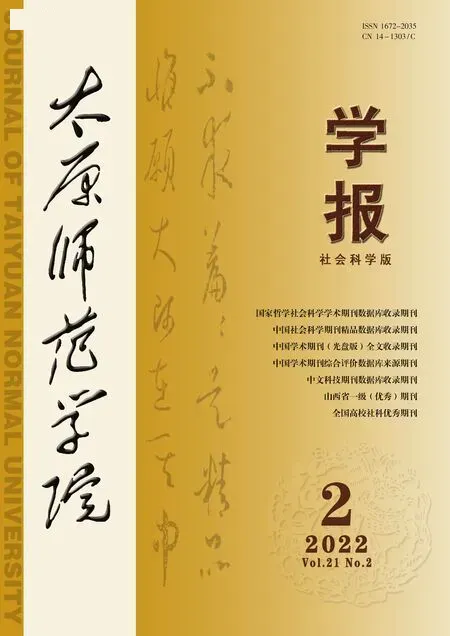《日近长安远》的主体意识
王 敏,刘小晋
(1.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2.陕西省人民医院 党委宣传部, 陕西 西安 710068)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变迁、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是当下时代的重要文化命题,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关注的一大焦点。陕西女作家周瑄璞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描写了农村姑娘罗锦衣和甄宝珠从高考落榜开始在都市二三十年的奋斗史。小说中真实的地名,对场景、行业的细致描写,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场感。这两位人物一在官场,一在市场,摸爬滚打,用尽心力,又终在人生暮年发现满目皆空,回到故乡寻找人生归宿。
以小人物来表现大历史,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柳青、路遥以来的陕西当代现实主义作家一脉相承的文学精神。然而,不同于之前男作家着力于男性人物形象,周瑄璞小说更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意识突出而深入:“我要写出女性的‘人’,而不是男作家笔下的‘女人’,也不是被赋予高尚光环、女性楷模的女人,而是诚实地写出女性身心的变化,成长的轨迹,写出生命之花的绽放与凋零,写出女性的忧欢,梦想,痛苦,流血,孕育,撕裂,伤痛,愈合……这是作为女性的我的责任,也是本能。总之我想要提供女性身心成长和衰落的样本”[1]。作家从人性角度来对小说中的这两位女性人物进行塑造,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温情的叙述者声音,构建出鲜明的主体意识,带领读者将社会历史的、人物命运的况味细细品尝,一唱三叹。
一、意识流与梦境:喧哗时代里的内在自我
《日近长安远》是农村到城市打拼者的命运交响曲,“欲望”二字是小说的核心词,它是人物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引导着人物在一个个人生关口作出她们独特的抉择;它也是小说所描写的时代的内在推动力量,一个喧哗的、沸腾的时代。在描述人物辗转更迭的人生故事的同时,小说穿插使用意识流手法,用如流动河水一般的心理描写,将人物内心世界坦陈在读者面前,关注人物心灵的渴望与焦灼。
甄宝珠是两位女性主角中的一个,构成了小说双线结构中的一条线索,然而人物自身却不像另一条线索的罗锦衣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她是一个少言寡语、心思单纯的女性。从人物形象塑造的立体程度来看,她的作用更多是引出一个有着鲜明主体意识的人物——丈夫尹秋生。宝珠弄丢了教师工作,迫不得已与秋生一起来到西安谋生,追求着心中的发财致富梦。熙熙攘攘的都市环境让初来乍到的宝珠夫妇眼花缭乱:“那康复路上,天天像过大会一样拥挤,打仗一般激烈,每个人的目的,都是要将自己一身力气和手中货物变成钞票。”[2]100头脑灵光的秋生,审时度势,顺势而变,开小饭馆做故乡特色胡辣汤、菜馍。从一开始的真材实料、慢工细活,到后面的偷工减料、粗枝大叶,他琢磨出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的办法:“要快,要饱,要实在。没有人计较你特色不特色,风味不风味,也没人在乎你跟你家乡感情深不深,甚至没有人要求你货真价实”[2]94。秋生的这些体会来自于生活本身,这正是当代高速发展、效益至上的工业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制度区别于传统社会秩序的因素中,“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传统的文明形态也许比其他的前现代体系更富动力性,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速度却是更加神速”[2]5。快、急已然成为现代都市的精神特征,与慢、缓的传统乡村精神形成对比。“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3]32“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3]34小说中的北舞渡胡辣汤,作为特定地域传统文化的承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沉淀了一代代人的故土情怀、情感记忆,给予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滋养;然而,快节奏的、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导向的现代城市里,那些历史的、地方的、情感的文化内涵被削平和遗忘,人也隔断了和故土、历史的情感关联,服从于社会理性的划一性要求。这种服从意味着初心的失落,这一点让人物内心并不安宁:“为了不在夜深人静时过于自责,他最后给自己定出一个底线,不能害人,不能给锅里放人不能吃的东西,只从偷工减料上做文章”[2]98。秋生有着来自土地的质朴和善良,在行动上努力适应着时代环境,然而杂乱的内心独白,却反映出在这理性的适应过程中人物悄无声息的心理挣扎与不可避免的失落心情。
相比甄宝珠和尹秋生在都市的艰难谋生,罗锦衣在跌落云端之前则一路顺畅亨达。她被心中燃烧的权力欲望所推动,在权力面前放下尊严,以她认为“正常人,合格人”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过分膨胀的欲望。然而,在觥筹交错的社交宴席上,她不由地想到了当年带着神圣感情说出“佳肴”二字的高中女同学;在虚与委蛇的时候,她不自觉地想起当年向她借过肥皂的叫霞的女生,“雾气的镜子里现出霞当年羞怯的笑脸……伸出霞的手……迈开霞的腿……”[2]138这是意识流的自由联想手法,打破固定时空限制,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自由转换。这两位对城市文明充满向往的朴实女生,之所以会令她不自觉地想起,因为她们恰是罗锦衣旧日的自我形象。今昔对比,她一方面陶醉于握在手里的繁华,另一方面也对那已远去的纯真时代真诚怀念,她已离最初的自己越来越远。
除了意识流手法,梦境在小说中也成为人物心灵迷失的表征。弗洛伊德认为,“梦在分析之后,乃是一种充满意义和情绪的思想过程的代替物”,是“被压抑欲望的化装的满足”[4]632。罗锦衣在她最高的位置上“夜夜有梦,常常回到从前,二十四岁的她,在田野里走,走着走着迷路了,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走着走着脚下土地松软,变成沼泽,她的身体一点点往下陷;走着走着飞起来了,飞过村庄飞向城市,地面的人越来越小,她看到房顶和树尖,道路变成一根细绳,飞着飞着突然掉落下来,赶忙睁开眼睛……”[2]252“迷路”“下陷”“掉落下来”,这都是罗锦衣心中彷徨与恐惧心理的外化。她的现实生活正如梦中情境,离开了生养她的村庄,在城市上空越飞越高,但她一直是依附他人的寄生性存在,故而那种飞翔无根无系,并不让她坦然,灵魂无处安放;同时,她的生命也从引以为傲的青春蓬勃,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老。人物的喃喃自语、虚实梦幻,是身体冷暖自知的细腻感受,是内心的激荡与沉落,是潜意识深处的迷茫与呼喊。
除了具体的、微观的梦,人物对作为整体的现实人生也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罗锦衣在失去官职后回到故乡,“炉边半小时,人间数十载,在罗锦衣心里,是做了一场长梦”。[2]332罗锦衣的一生都在失去与获得之间较量跌宕,却难以平衡和谐。年轻时,她以青春换取地位;青春不再时,她以地位换取自我认同。从极度渴望鱼跃龙门,到幡然醒悟“人与人,原来是没有差别的”,辉煌抑或平淡都是一生,这领悟对于罗锦衣而言,是精神的死亡与再生:“或许那一切,都是个梦,而她,没有离开过北舞渡,她还是当年那个和宝珠一起走在通往县城路上的卑微少女,能在北舞渡当个老师,有个城镇户口,就知足透了”[2]340。三十年前的简单愿望安抚了她躁动的灵魂,心情平复,“不再愤怒,不再冤屈”,真诚地向卢双丽道歉,云淡风轻,尘埃落定。如同庄周梦蝶,乡村的罗锦衣、城市里的罗锦衣,不知哪一个是梦,哪一个是真。城市天空跌落下的罗锦衣,似乎从梦跌进了真实,这正如作者的自述:“关于罗锦衣的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主人公的命运,仿佛一场梦境,‘绿城’或许只是化城,只能看见,却摸不到,抓不住,只有主人公打回原形,踩到故乡的土地,才像是从云端回到大地”[5]。“罗锦衣”这一形象,揭示了唯我主义和欲望膨胀必然带来的主体失落和自我迷失。沉迷于世俗欲望中的人格,反过来也被世俗标准所物化,故而,城市里拥有的现实人生令她产生如“梦”的虚幻感。虽然故乡给罗锦衣带来了精神抚慰,然而细究起来,故乡也无法真正成为她的归宿,化了蝶的罗锦衣无法再复归最初的自我。乡村是罗锦衣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归来时单纯的怀旧只能让她“归于平静”,而不能给拥有新视野的她带来全心全意的满足与安妥。
二、隐喻与象征:寂然凝虑处的生存本相
《日近长安远》最大的艺术魅力,在于以精细的笔墨写出了宏大的时代精神。秋生、宝珠所做过的营生,从康复路贩衣物到郭杜卖、在康复路开小饭馆、在东郊马路边收停车费,桩桩件件,小说描述行业底细丝丝入扣,以秋生夫妇的视角看人情百态,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景、细节如在眼前,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体现。然而在脚踏实地的现实精神之外,小说也表现出轻盈、空灵的浪漫气质,一些凝练的意象表达出了人之生存本质的诗性体验。
罗锦衣三十年的奋斗史,是一条攀爬之路,她喜欢的是高高在上的感觉,攀援的凌霄花、节节高的竹笋、不断上升的电梯都成为她的自我心理形象。“一片凌霄花,开得悲愤激烈。她停下来,痴痴地看着,那些花儿,也激昂地面对她,每一个红色小喇叭奋力向上昂头,发誓要夺取胜利的样子,它们纷纷伸向绿叶之外,形成一层红幕,像是一队人马在呐喊。她一下子鼻子发酸,就要落泪了,觉得这些花,正是此时的她。”[2]112“凌霄花”意象很容易让人联系到舒婷《致橡树》中赋予这种花朵的象征意味——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性。小说中形容凌霄花,用语则更显阳刚,“悲愤激烈”“呐喊”“夺取胜利”,如同锦衣强劲有力的内心欲念。相似的植物意象还有生命力旺盛的“竹笋”:“竹笋在短暂的春天里要拼命长高,几天内蹿到跟竹林同样的高度,否则它够不到阳光,就会死去。……而她,是那个奋力生长的竹笋,终于长上来了,和别的竹子一样,平分太阳的光辉。”[2]240人和万物一样,生长本是一种恬静的自然状态,但在锦衣心里,生存是一种竞争,需要夺取养分和阳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她一度成为胜利的竞争者,靠着不可阻挡的欲念和行动力,攀爬到了她想要的高处。
罗锦衣心里有高低区分,便有了睥睨人间的虚荣。“她就是愿意感受一下在扶手电梯上向上升的感觉”,“不管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凡是双脚踏上这种购物中心电梯的女人,像是上了一条神奇的传送带,立即被塑造成普天下一个模式:骄傲,轻浅,内心温柔,对物质依恋而顺从,被现实生活彻底征服,为着这楼上某一件心仪的东西,新奇和激动……电梯将她越带越高,她将楼下正跳广场舞的女人,将那些当妈的当奶的当姥姥的人,将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人们,踩在脚下”。[2]74这里的“普天下一个模式”即商品拜物教模式,缓缓上升的商场“电梯”意象,写出了人物潜意识中肤浅的自我陶醉。获得城市身份的锦衣,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的存在,用占有商品来获得优越感,她对都市文明的理解只停留于外在的、物质的层面。这正如波德里亚《消费社会》中所说:“这里‘通过物的证明’,通过消费获得的拯救,在其没有反映思想的目的性过程中,上气不接下气地、毫无希望地想获得一种人赐的、天赋的和宿命的地位。”[6]33消费社会中的商品,以其光鲜的外表和“富足”“高级阶层”等内在符号涵义而使消费者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然而由于这一认同遵循的是外在、物化的标准,并未“反映思想”也无法内化为主体精神,因而人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被商品所架空的。很快学会了所谓大城市做派的罗锦衣,心理上却一直是卑微的,她渴望通过权力地位,也通过消费中虚拟的主体地位来获得自我确认,然而权力、商品都以外在“物”的形式对心灵化的主体进行了挤压,最终让依附于此的主体变得空洞而虚弱。
对于另一条情节线索的秋生,小说用“黑洞”这一意象来表达他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体验。秋生两手空空地来到城市,积蓄不断增多,早已超过了最初的预期,他体会到“可能从前穷得太久,饿得太狠,金钱的重要性突然间无比强大。可是,它们只带来了短暂的幸福和安慰,却立即转化成了永不知足的黑洞,带来了无尽烦恼。刚挣到一千元的时候,欢喜半天,立即又有一种饥饿和恼怒,为什么不是三千、五千?”[2]95-96他联想到小时候捉知了时碰见的一些深洞,本是怀着捉到知了的欣喜,却因洞里藏有一条怪虫而受到惊吓。而今让他惊吓和恼怒的“怪虫”,不是外物,而正是他内心深处难填的欲壑。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却找不到安放的家园,在对金钱缺乏理性的追求中失去了幸福和满足。
秋生、宝珠这样拼体力的农民工,他们自身的存在状态具有异化性质,小说用“机器”来比喻之:“二人已经交了四十,身体拿机器作比,只是使用,连续转动,从不维修、保养、擦拭,任由它磨损、生锈、破败。宝珠夜里醒来,能感到后腰、膝盖隐隐地痛。这样下去,身体将直至成为一堆不可收拾的废铁”[2]110。人俨然成为赚钱的机器,虽然在城市赚到了钱,然而付出的是身体的过度损耗。秋生在家乡盖好了气派的“尹张第一楼”,却来不及和宝珠返乡养老就病倒在城市。夫妻二人常年离家,孩子丢给老人,人伦亲情、子女教育统统无法兼顾,他们是机械性、工具化、单向度的生存状态,而缺失的一切都只能由他们自己全盘承担。
小说另一个诗意的象征性表达,是开头、结尾处的“老妇”形象。在人物内心,老妇赠送的苹果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少女锦衣获赠的是一个又大又圆的苹果,正如她蓬勃美好的生命,结尾处她轮回般地又在路上碰见一位老妇时,好奇“她的身上,有没有藏着一个枯皱了的苹果?”枯皱了的不是苹果,是她凋零的生命力量。“老妇皱纹堆积的脸,苍凉而慈悲。锦衣和宝珠转头对视,心里一惊。时光老人在设置我们的生活时,常常动用了一些特殊手法,拼接闪回,倒带定格,人生某些场景,是否会重新上演。”[2]342携着苹果的“老妇”此处已超越现实主义的写实性,宛如《红楼梦》中青埂峰上的一僧一道,说出了“人的命,天注定”的超验性话语,让尘世中的锦衣与宝珠凡俗的生活获得超脱的、哲学的审视,也使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之外拥有了幽玄的内涵与意蕴。
三、反讽与悲悯:叙述者的理性与温情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指所言和所指恰恰相反:“说出的话和心内相反,偏又让人知道弦外之音,就是反讽。”[7]175反讽是一种自我辩证法,是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对自我内部的审视。《日近长安远》的总体反讽,表现为主题内涵上的辩证性。叙述者在讲述一些故事、现实,然而叙述者的讲述常常流露出对于这些现实的否定性态度,体现出叙述者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
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小说的重要主题。在小说中,乡村是他们想要摆脱的现实,城市是他们追求的梦想。悖论和反讽之处在于,人物极度想要走入的城市并不是甜美光明的桃花源,他们身在都市二三十年却无法安身立命,终究还是故乡接纳了宝珠衰老的干不动的身体,安顿了锦衣浮躁的迷失的灵魂。“城里再好,那不是咱的家。”秋生的内心独白道出了小说众多人物共同的心声。城市化历程中的乡村被抛弃和遗忘,然而喧哗的城市缺乏人际间真诚的关怀:“在老家里,去这村那村,总有人打招呼,主动相问……城市里到处都是人,但每个人,都不在别人的眼里。”[2]28人只能看见自己,看不见别人,这是秋生对都市人冷漠精神状况的体察,实则反映出对人文生态的忧虑。这正如汪民安在《现代性》一书中指出的:“这些敏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千篇一律的退隐状态。人们的分明个性在不断地消失。而且,都市中物质文化的主宰,都市中压倒性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越来越孤立。”[8]25“人与人之间以前那种个性化的富有特色的交往,现在荡然无存。”[8]24秋生所怀念的乡村传统社会中相对稳定的人际交往和人情温暖,在高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都市变得越来越稀薄。人群的流动性加强,个体的人越来越独立的同时,也越来越孤独。“乡村”与“城市”充满反讽意味的关系是《日近长安远》的核心内涵,并且,“从本质上说,现代性的空间生产几乎能够体现在所有的乡土叙事中,‘诗意的赞美’与‘行动上乖离’的割裂从‘五四’一直延续至今”[9]。情感上的赞美、行动上的背离,这悖论性的现实反映出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和城市外来务工者的尴尬处境。
城市作为人生存的空间,本应和大地一样供予人诗意的栖居,然而在经济至上的时代,城市就像一个大市场:“九十年代,中国人好像从一个千年睡梦中醒来,揉揉眼睛,复苏了自己的各种需求,市场这个词,从遥不可及的,陌生可怕的,变得亲切迷人,让人痴狂。……我给你钱,这几个字,可让暴烈者变得温顺,坚硬者很快柔软,铁面孔立马和善,可使一切不配合、不对接、不可行,调转为亲密咬合,如鱼得水,刚才还是此路不通,转眼化为放行通过,从前谨慎慢行,今朝加速前进”[2]95。这一段话,显然不是人物形象本身所能做到的对社会的宏观理解,而是叙述者借着人物的感受所作的理性思考,这里表达的反讽性,与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泰门讽刺金钱的独白有异曲同工之妙,酣畅淋漓地指出了市场、金钱的魔力及其给人性带来的巨大改变。小说叙述者进一步思考这种市场化给整个社会精神所带来的侵害:“有形的、无形的市场,变为中国人头顶的蓝天,呼吸的空气,人们的生活、情感、理想,以市场的晴雨表为参照。好像一切都要面向市场,文化,精神,友谊,爱情,人才,事业,信念,所有事情,其最终的管道和归途,都得放入市场的大容器里来挑选、称量。”[2]174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时代的弊病,经济的洪流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冲击着旧有的理想信念,异化着人们的心灵,新的价值体系亟待建设。
除了主题内涵上宏观的反讽性,小说在细节处也常常体现出微观反讽。在康复路上的小饭馆,“那些夜色中走进来,叫了几个凉菜一捆啤酒的人,偶尔谈着一桩大得吓人的生意”,“话题中的大事业才刚起步,断不可随便收场”,听众则是“崇拜地看着,认真地听他们大谈未来”。[2]99他们谈论的无非是从康复路批发倒卖床单、袜子这样的小生意,小说有意用“大事业”“崇拜”“大谈未来”这样的夸大叙述,然而,紧跟着的一句“胡吹冒撂之后,回去睡一个长觉,所有的誓言和感慨都会忘掉,偶然激起的斗志,像云一样被风吹走,而口中的大事业,一生都在筹划之中”[2]100,这样凄凉无奈的话语,让前面庄严宏大的用语轰然倒塌,显现出人物窘迫、困顿的生存真相。“嘉宾换来换去,主题总是不变,皆是发财版本……听多了,秋生心说,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抓住的。秋生想起上学时候学的一句话,假如给我一个杠杆,我将撬动整个地球。”[2]170“撬起地球”这样宏伟瑰丽的想象,实则只是一个底层百姓的发财梦。大与小、庄与谐之间的对比,更显小说文本表意的丰富与张力。
两位女主人公的命名暗含褒贬,也可视为小说中的反讽性表达。三十年后罗锦衣在面对甄宝珠时有这么一段内心独白:“她始终那么安静,这个大院子里,几十年的时光在等待着她。真正的珍珠,沉在海底,被沙子打磨成坑凹不平的麻子脸,而那些又光又圆的珠子,大多是假的。”[2]337同样的高考落榜,从同样的民办教师身份出发,两个姑娘命运大相径庭,看起来罗锦衣风光无限,甄宝珠默默无闻,然而,锦衣夜行的虚荣、真正宝珠的实在,两个姓名的对比,作者悄无声息地表达了情感倾向性。罗锦衣这一人物放大了欲望对人的异化作用,甄宝珠则表现出传统女性的性格特征:内敛、温柔、不卑不亢。相比锦衣夫妻的勉强凑合,宝珠夫妇则情投意合、夫唱妇随:“两人从没有吵过架,好像对方说什么,做什么,他们都支持,都同意,他们看对方,就像是另一个自己,完全的满意和爱惜”[2]64。欲望与本分,两位人物恰好形成一种对比与互补,二者共同塑造出女性整体的心理状态。对这整体中的两端,小说致力于展现她们心中的波涛汹涌或是轻轻涟漪,并没有作直接的道德评判,然而语言本身却作出了诗意的裁判,小说这样描写罗锦衣的心理:“没来由地心虚,觉得这人像宝珠,她跟宝珠一样,恭顺地待在自己的命运里,而她罗锦衣,只是个欲望捆扎的草包,由一种莽撞而不竭的力量,憨胆大,一次次撞向生活的大门。”[2]133由此,安静而纯洁的女性,最终获得礼赞。
反讽手法体现出小说叙述者的理性与智慧,对小人物的关注则表现出叙述者的悲悯情怀。小说笔墨所到之处,不管是主角还是次要角色,个个皆是栩栩如生的形象,普通民众的生活细节、辛酸故事、灵魂深处的细小角落,皆被记入。高考落榜的农村孩子、为生下腹中孩子而失去公职的张老师、想生下男孩而把一个个女儿送给他人的母亲秋云、被骗钱依然和孙腊梅凑合过日子的老朱……最典型的是小说叙述的那一场非法集资事件,秋生、老朱这样拼体力一天天积攒的血汗钱,实在来之不易,但在一场骗局中荡然无存,这样的情节来自真实的生活,谁来聆听他们心里流泪与流血的声音?用文学来书写那些角落里的伤痛,这本身就是小说的人文关怀,作家以真诚的笔触关心那些失去家园、缺少眷顾的人们。萨特曾在论著《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作家对于自己所书写的现实生活必然是“介入”性的:“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10]20小说中所揭露的人性和人生真相,即使充满了痛苦和失败,也是现实世界的对照反映,对读者具有启发效应。周瑄璞也强调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态度:“白天与黑夜构成这个世界,光明和暗处是文学永远的吟唱和交响。好作品首要标准是:真诚。”[11]《日近长安远》通过对生活表象背后历史真实的揭露,通过对人物命运及心理的内在挖掘,启示着读者去审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多元文化精神,去辨析和选择,从而承担自己的人生责任,创造更为理想和美好的现实生活。
“日近长安远”,空间上的远与近,终究是相对的,是对于主体心理而言的。小说中把“长安”当作梦想来追逐的普通人,他们与都市、与故乡之间远近不辨的生存状态是小说题旨所在。小说通过种种艺术手法,奏出了这些典型人物在背井离乡岁月里的心灵协奏曲,在塑造出人物内在的自我形象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时代精神的关注与思考,体现出了鲜明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