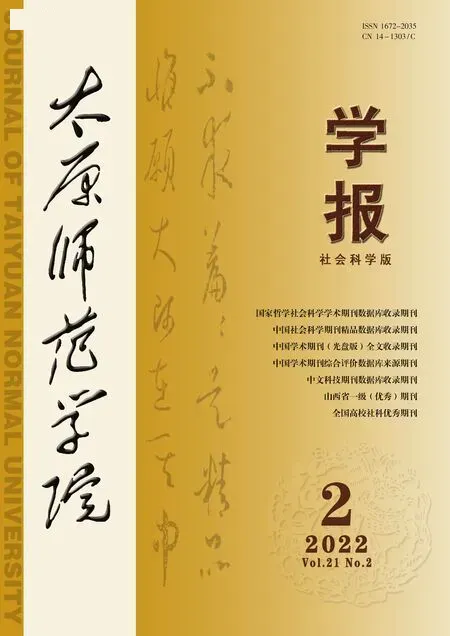论宋诗的“自得”精神
姚 晨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宋诗以其迥异于唐诗的美学风范以及其自身的非凡成就,和唐诗一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唐代诗歌的卓然独立,在盛极难继的压力下,宋人另辟蹊径,匠心独具地诠释出以“筋骨思理见长”的宋调之美,为古典诗歌在唐诗之外确立了另外一种美学典范,其贡献不可谓不大。江西诗派作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其诗歌创作风貌鲜明地体现了宋诗的诸多特征。但自南宋后期永嘉四灵、江湖派对江西诗派提出批评,转而向晚唐诗风复归开始,由江西诗而宋诗,都一直饱受非议。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26, 而宋诗却陷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1]27的魔障。张戒《岁寒堂诗话》亦称:“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2]455如果说这时人们的不满还表现在对江西后学逐渐僵化死板、流弊日显的批评,那么之后就逐渐将目光投向了元祐诸家乃至整个宋诗。譬如,张戒进而言之:“自建安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2]455王夫之云:“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3]120
梳理诸家所言,其对宋诗的大肆批评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宋诗一反唐诗审美风范,“唐调亦亡”;二是宋诗在创作中存在着资书为诗、抄袭前人的现象。江西后学确有失当之处,对前人模仿太过,拘泥僵化,缺乏韵味,诸家所言,颇中要害。但将宋诗异于唐诗之貌一同视为宋诗之失,则未免失之公允。相反,宋人正是在对唐诗的学习、继承、发展过程中,坚持“自得”,自我树立,才使得宋诗能够自成面目,卓然自立。查洪德先生在《论“自得”》一文中,爬梳罗列了“自得”在历代论学、论艺、论诗方面的内涵及意义,尤其是在元代诗论中的丰富含义。其中,“文章以自得、不蹈袭前人为贵”的自心独得中体现出“自我意识”,则是“诗学中很值得重视的精神”。[4]笔者从“自心独得”的视角对宋诗进行观照,分析自得精神在宋诗自我树立中的重要意义。
一、梅尧臣:于唐诗之外别开生面
有宋三百余年国运,诗派众多。自《沧浪诗话》之后,元人袁桷《书汤西楼诗后》、清人宋荦《漫堂说诗》对宋诗流派的划分分别代表了“以人而论”和“以时而论”两种分派法,其所分派别大同小异。在《宋诗研究》中,胡云翼罗列宋诗诗派有九:西昆体、晚唐体、白体、唐体、元祐体、江西派、理学派、永嘉派、江湖派,并注明各体各派所师法的对象。[5]19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人选择师法对象时,唐诗是其绕不开的话题。经过唐朝的诗歌盛世,宋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必然会师法其中足资借鉴的创作经验,一如唐人对汉魏六朝诗的学习一样。“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6]11而在笔者看来,宋诗的“大幸”还在于,面对唐诗包罗万象的巨大成就,宋人尽可以放手向唐诗学习,进而做些入室操戈的功夫,便足以自成面目。当然,宋诗的成就远不止于此,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对唐诗进行审视、反思,进而自我树立的过程中,对宋诗有开创之功的首推梅尧臣。
刘克庄云:“本朝推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之下。”[7]22《宋诗钞》引元人龚啸语赞曰:“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8]207叶燮称:“开宋诗一代之风气者,始于梅尧臣、苏舜卿二人……自梅、苏尽变昆体,独创生新。”[9]67历来对梅尧臣的高度赞扬,均着眼于其对昆体风气的荡涤。作为宋调开创者,梅尧臣在宋初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将师法对象确定在韩孟诗派上,这固然有时代风云的推动,但韩孟诗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唐诗美学风范(这一点在韩愈身上尤为明显)而开宋调之先声已是学界共识。梅尧臣正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将其扩而充之,真可谓巨眼英豪。梅尧臣从学韩愈入手,以唐诗为标杆,通过对唐诗题材上的拓展、风格上的反动,在物我对立中体现出宋诗的特色和价值。
韩愈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向古人学习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的杜甫虽然自言“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赞扬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但这种学习更多是一种诗人自悟式的揣摩、领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风神传达。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师其意不师其辞”,则是将对古人的学习落到了实处。虽然这些观点是针对散文创作而言,但在后人推崇、学习他的以文为诗时,将这些文章学的理论一股脑儿全搬了过来,而不只是其诗歌好议论、散文化的写作方式。
以韩孟诗派为师法对象,在题材的选择上,除却一般士大夫的感时忧民、体物缘情之作外,梅尧臣“有意识地”开拓新诗境,积极搜寻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题材,或于前人已有题材上着力翻新,“有意识地”向各种更个人化、生活化、琐碎化的自然景物、生活场景、人生经历开拓。在他笔下,破庙、妓女、虱子、跳蚤,乃至厕所中的蛆虫,都是可以资之为诗的对象,真正做到“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这当然是从韩愈那里学到的本事。韩愈在与孟郊穷形尽相、连篇累牍地进行排律联句时,就已经指出了一条迥异于唐诗风貌的诗歌发展道路。虽然梅尧臣的创作初衷在于力矫西昆体雕琢词藻、华而不实的习气,但也开了宋诗竞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为宋诗在唐诗之外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唐人浅言少言,则宋人深言多言之;唐人已言泛言,则宋诗精言切言之,必期至于淋漓酣畅而后已。”[10]248而与题材琐细化、生活化一并产生的好议论的风气也同样可以在梅尧臣的诗歌里看出端倪。“历来不在诗中歌咏的卑小的事物,例如虱子等等,他(梅尧臣,笔者注)也有意识地采入,加以人世间的批评性议论”[11]120。“在以琐碎平常的生活题材入诗时,很容易显得凡庸无趣味,于是梅尧臣常以哲理性的思考贯穿在其中,加深了诗歌的内涵,使之耐人寻味……这也是宋诗在热情减弱以后,向其他方向发展的一个途径。”[12]334
在风格上,梅尧臣推崇平淡、追求老境美。欧阳修在《再和圣俞见答》中称:“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梅尧臣自言:“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但需要注意的是,梅尧臣所提倡的“平淡”是经过诗歌创作过程中反复锤炼所达到的平淡妙境。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中云:“大抵欲造平淡,当从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梅圣俞《和晏相》诗云:‘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词未熟圆,刺口剧菱芡。’言到平淡处甚难也。所以《赠杜挺之》诗有‘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13]484朱自清先生在《宋五家诗钞》中说:“平淡有二:韩诗云:‘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平淡即此种。”[14]369由此可见,梅尧臣所提倡的“平淡美”是在他潜心学习唐人瑰丽宏肆诗风之后刻意收敛的平淡,这与之后黄庭坚所倡导的“平淡”是一脉相承的,即“平淡而山高水深”。梅尧臣论诗同时标举李白、杜甫、韩愈,“既观坐长叹,复想李杜韩。愿执戈与戟,生死事将坛。”(《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摩拂李杜光,诚与日月斗。退之心伏降,安得此孤陋。”(《答张子卿秀才》)他所追求的理想诗境正是李、杜、韩那样内容充实、形式朴素而又情味隽永的平淡境界,是将浓郁强烈、深刻隽永的思想感情内蕴,用朴素平淡的语言表达出来。平淡其表,深邃其里,在貌似枯燥平淡的外表下,传达出强烈的认识和感受。平淡美不仅仅是梅尧臣个人的创作追求,而且逐渐成为宋诗的共同审美取向,这与宋人面对国势不振的忧患意识、趋于内敛的创作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梅尧臣的有意平淡所达到的老境美,却用事实上所形成的对唐诗诗美风格的反动,经过后辈诗人的继承发扬,形成了与唐诗“风神远韵”双峰并峙的宋调之美。
二、黄庭坚:在历史困境中敢为天下先
在宋诗自我树立的过程中,黄庭坚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所创作的“山谷体”和以之为宗的江西诗派,都是宋代诗歌中最能代表宋诗面目的典范。刘克庄赞黄庭坚:“荟萃百家句律之长,极历代体制之变,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为本朝诗家之祖。”(《江西诗派小传》)苏轼作为一代文宗,其文学成就远在黄庭坚之上,自不待言,但就体现宋诗面目以及因对后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诗史典型意义而言,则黄庭坚具有比苏轼更为特殊的文学史价值。黄庭坚以其力矫宋初以来诗歌平直浅露之风的曲折诗境,自成一家独具风神的诗歌成就,循序渐进、有门径可循的诗歌理论,深为当世服膺。
黄庭坚论诗最重要的两点是“点铁成金”说和“平淡”说,二者是取法前人到自我树立的诗艺指点和诗歌境界要求的相互补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即在广积学问、研习前人经典作品的基础上,利用诗歌艺术上的技巧极力生新,最终出之以平淡之境。
梅尧臣创作中的“自得”主要着眼于诗歌题材的开拓和诗境上对唐音的反动,黄庭坚在沿着梅尧臣的路子前进时,除了进一步发挥诗境上的“平淡美”之外,其诗论的重点还在于如何在继承、汲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见出自家风味。“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15]90王安石此言充分流露出宋人在面对唐诗时的焦虑。唐代士子或身居庙堂,或远赴幕府,或归隐山林心忧天下,或身在魏阙志存江海,其视角遍及宫闱市井、关山大漠。宋代在更为稳定、成熟的封建社会形态以及科举选士制度下,趋于单一化的士人生命历程远没有唐人那样异彩纷呈,人生阅历的匮乏导致诗歌题材和生命力的萎缩,加之国势不振、党争激烈,宋人渐趋内潜的诗歌视角逐渐投向书斋生活和日常器物,着重表现内在心灵世界的自足体验。这是梅尧臣的功劳。黄庭坚诗歌在思想内容上踵武前人,唱和、赠答、题咏等题材在他的诗集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得在黄庭坚这里主要表现为对诗歌技艺的探索,而对诗歌技艺的探索又根本于对古人的学习。
黄庭坚于《答洪驹父书》中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6]316这段话历来被视为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他所提倡的“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和在对杜甫拗律学习时提出的“宁律不协而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的主张,几乎涵盖了诗歌写作技艺的方方面面,炼字、锻句、用典、律法,极尽人工技艺之能事,而其中的创新精神格外强烈。顾随《宋诗说略》中云:“诗之工莫过于宋,宋诗之工莫过于‘江西派’,山谷、后山、简斋……宋人对诗用工最深。”又说:“凡山谷诗出色处皆用人之诗,整旧为新。”[17]277这里准确概括了黄庭坚诗歌创作论的特点:在对前人诗作揣摩学习的基础上,刻意锻炼,极力生新,以自成面目。如果说向古人学习是宋诗在历史的焦虑中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黄庭坚的自得生新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中欲有所作为不得已而为之,欲自树立而已矣。
而对于诗歌的自我树立,黄庭坚又是极为重视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黄庭坚在学杜大潮的背景下能够脱颖而出,自成一家,正是其极力生新的自得精神的成果。“近世人学老杜多矣,左规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终成屋下架屋,无所取长。独鲁直下语,未尝似前人而卒与之合,此为善学。”[18]596黄庭坚对江西诗派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诗歌技艺、门径的指引上,其创新精神亦为江西诗派所继承、发扬。至于江西后学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弊病,则是任何一个诗派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流弊:学韩孟则陷险怪之失,学元白则有浅俗之陋,学姚贾则生雕琢之病;广言之,学六朝易病于繁缛侈丽,学盛唐易流于粗犷豪横,学晚唐易患于气格不胜,何独江西也哉?我们更应注意江西诗派在面对自身弊病时是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发展的。曾季貍《艇斋诗话》云:“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说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19]296陈师道、徐俯、吕本中、韩驹等江西后劲针对诗派发展中出现的泥古过甚、刻板拘泥等倾向,纷纷参以自我创作中的心得,不断进行自我修正,正是得益于自黄庭坚以来一以贯之的创新自得精神。《清波杂志》载:“公(徐俯,笔者注)视山谷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贽见,盛称渊源所自,公读之不乐,答以小启余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20]194钱钟书先生讥笑徐俯“成名之后,也不肯供出老师来,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指出“他舅舅文集里分明有指示他作诗的书信;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找得出他承袭黄庭坚的诗句的证据”。[6]171以山谷诗名之盛,徐俯大可不必掩饰黄庭坚对他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批评也是切中肯綮。但徐俯虽以师礼事山谷,却未矩步山谷,想要自出枢机也是毋庸讳言的。《清波杂志》注下引赵鼎《建炎笔录》称:“宋高宗谓徐俯:‘万年学李白,稍放肆矣。’”且注亦云:“可见其‘欲自立名世’,诗风实有所变。且不徒诗也,所操之术事事欲以人异。”笔者在此无意探求徐俯之于山谷所变几何,但从其自述和他人评价中可知,徐俯作为江西后劲所体现出的想要自成一家、自我树立的自得创新精神,与黄庭坚确是一脉相承的。
三、杨万里:于江西末流中破而后立
在江西诗派诗法指导和自得精神共同浇灌下所结出的硕果便是南渡之后跻身中兴诗坛四家的陆游、杨万里二人。二人学诗皆自江西而入,陆游师从曾几,杨万里则私淑“江西诸君子”。二人在江西诗法的指导下对诗技、诗艺进行锤凿锻炼之后,参以自身学力和功力,分别拈出“诗家三昧”和“晚唐异味”,冲破江西诗派的藩篱和禁锢,自得自证,自成一家。二人在创作中均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唐音和宋调的融合,成为南宋诗坛唐音回归的先声。在当代对二人的接受中,以恢宏踔厉的爱国诗篇见长、被刘克庄赞为用尽天下好对偶的陆游收获了更多的赞誉,但就对诗风的革新意义和诗体的自我树立而言,杨万里则更具有代表性,“诚斋体”是《沧浪诗话》“诗体”以人名体中南宋仅有的一例。
杨万里在诗集《荆溪集序》中自述其学诗历程:“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杨万里从师法江西诗派入手,逐渐转益多师,进而自出枢机,成一家风貌。杨万里在沿着江西诗派给出的广积学问、师法前人的诗法道路进行实践时,却陷入了“学之愈力,作之愈寡”的困境,创作上的轧轧难造促使他对江西诗派进行反思,深入其里,洞悉其弊,江西诗派末流显现出的弊病成为杨万里超越江西诗派束缚的直接动因。
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突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走出书斋,不再埋首书卷寻章摘句,从古人那里讨生活,与江西诗派末流分道扬镳。“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题唐德明建一斋》)杨万里转而回归自然,直接以自然为师,从自然万物、生活小景中捕捉诗情。“欲具江西句中眼,还须行礼问云山”(《题照上人迎翠轩》),杨万里将师法江西诗派所习得的诗歌技巧应用于大自然,达到“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荆溪集自序》)的状态,形成一种亲近自然的清新活泼的表现方式。
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突破还表现在对晚唐诗风的赞赏。晚唐诗风是江西诗派鄙夷的对象,一直到陆游那里,依然对晚唐诗风颇有微词。杨万里敏锐地认识到晚唐诗歌的轻快灵动对于江西诗派刻板拘塞、缺乏韵味的补救矫正作用:“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颐庵诗稿序》)他汲取“晚唐异味”,以补江西之弊。如果说黄庭坚是“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21]26,那么杨万里庶几就是“以江西工夫,造晚唐之境”。“诚斋体”轻快流利,又多有所本,明显带有合江西、晚唐两体之所长的意味。杨万里于“四灵”“江湖”未起之先,独倡晚唐,既是对宋初宗唐风尚的历史回应,又是南宋后期乃至南宋以降“诗史的逻辑起点”。这不能不说是其独具慧眼的创新自得精神的成果。
江西诗派对诗法技艺的精研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而杨万里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如何在以江西诗法入门,进行诗歌艺术技巧锻炼后形成自家风味的道路。他学习江西诗派,不仅仅学习其诗艺技巧,更重要的是领会和继承黄庭坚自成一家的创新精神。“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三首》)强烈的自得树立意识,正是他从江西诗派中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这也解释了他在摒弃江西之后,依然对黄、陈二人推崇服膺的原因。
铺观列代,不难发现,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重新回到起点的从头再来,相反,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整合之后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承认对前人成就继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后辈作家的创新和发明。全祖望《宋诗纪事序》称:“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之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诗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之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四璧俱开;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之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相率为迫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22]3在全祖望所言宋诗四变中,除却宋末家国存亡、社稷鼎革之际在外力刺激作用下兴起的爱国诗、遗民诗等“迫苦之音”外,宋诗在自身三次自然演变中,从翕然宗唐,到自立宋调,再到唐音回归,在继承发展中树立自身独特的宋调之美。而于三次转折中具有开创之功的梅、黄、杨诸人或别开生面、或敢为天下先、或破而后立的自得精神,则是宋诗于波澜迭起间珠玉满目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