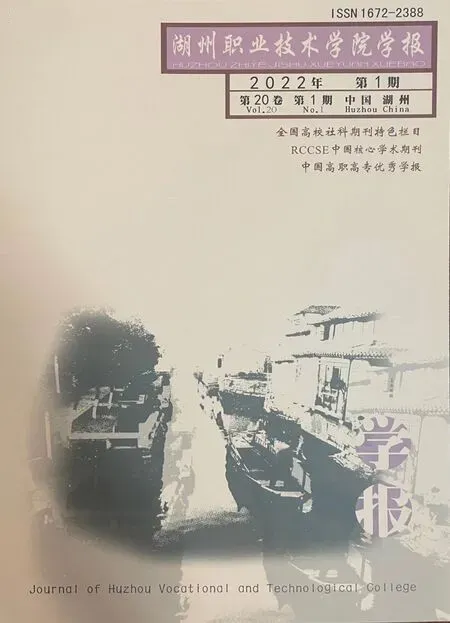论叶芝面具理论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共通性*
张 迎 , 李 立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西方文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两位批评家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4-1939年)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Mikbailovich Bakhtin,1895-1975年),在同一时代先后提出了面具理论与复调理论。前者侧重于诗歌、剧作理论,后者侧重于小说理论。两者都是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丰碑。对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学界的视野焦点多落于其复调性本身。本研究拟从叶芝面具理论的视角,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复调性成因进行探究,分析后者文艺理论中作者面具的内涵,以及由多张作者面具相互间的辩驳所带来的多重声音的对话性,由此对两者的共性进行再思考,并进一步发掘两者文艺理论的思想价值。
一、作者与面具
(一)面具的内涵
叶芝面具理论的作者观与他在浪漫主义时期所提倡的独白型作者不同,更倾向于减轻作者的存在痕迹。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所呈现的作者观也具有类似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巴赫金极其推崇的作家。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在研究陀氏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陀氏作品中,作者、主人公以及其他意识共同形成闭合的力量角逐场。作者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对分析多重声音复调性的成因极为重要。而叶芝有关“作者面具”的理论可为陀氏作品中看似透明的作者身份提供解释的新思路。
叶芝所处的时代恰逢浪漫主义时代的尾声。时代的变化使原本宣泄式的写作方式渐渐无法深层次地触及人类灵魂。此时,叶芝“面具理论”便在吸收前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叶芝提出,要塑造另一个自我,间接表现个人感情。这样,诗歌由对现实的宣泄,正式发展为隐匿在面具后的诗人对现实的反思,借此摆脱了单一情感的喷薄宣泄,维持了优雅委婉的诗歌传统,完成了对浪漫主义不足的有效弥补。
纵观叶芝的诗学理论,面具的意义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意象,或我们所崇敬的意象。”[1]28它代表着多层次不同维度的“反自我”的展现。叶芝的创作主张倾向于表现大范围的人类情感,这较之个人的情感更为复杂,需要更深层次的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因此,叶芝提倡作者在创作时戴上“作者面具”,即“主张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努力创造第二自我,不断地体会与自我相反的各种人格”[2]31。“作者面具”意味着作者借面具隐匿自身,以不完全真实的状态示人,有意识地进行表演,与荣格的“人格面具”类似,表现为一种社会化自我。叶芝理论中戴着面具的作者接近于隐含作者。作者在接受过程中,只建构成其理想中的作者形象。叶芝在创作中常常采用第三人称,作者戴着另类的意象面具出现,为读者和有关作者的想象提供多种可能性。如《为小女祈祷》中叶芝自称“傻瓜、流浪汉”,《驶向拜占庭》中以“衰颓的老人”暗指自我,《马戏团里动物的背弃》称梦中“傻瓜和盲人偷走了面包”[3]287,《伟大的日子》中欢呼革命的场景里“一个马上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欢呼革命,而大炮又来了/乞丐换了位置,但鞭打仍在继续”[3]267,借循环的暴力场景暗示其对革命无进步的失望悲观。不论是傻瓜、老人、流浪汉、盲人还是乞丐,都是戴着面具的叶芝悲观情绪的外化,作者躲在面具的身后,宣泄着对这场虚无结局的革命的多角度抗议。叶芝并非诗作中的某一形象,但每一形象无一不是他。
(二)作者身份之新变
在陀氏小说《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争辩展现了对人性恶与善的辩证探讨。戴着不同面具的作者,在争论着的不同声音的背后发挥着作用,并借此发出自我真实的声音,这与上述叶芝的诗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作品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在批判继承俄国学者维诺格拉多夫“作者形象”理论的基础上,巴赫金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曾提出对作者角色的理解:“真正的作者不可能是形象,因为他是作品中任何形象、整个形象世界的创造者。因此,所谓的作者形象只能是该作品诸多形象中的一员。”[4]378巴赫金否定了作者单一性形象的存在,认为作者在创作小说世界时,不自觉地戴上面具,变形为不同形象。而最接近于作者原身的隐含作者,在模糊自身的界限后,常常成为其诸多形象中的一员。隐含作者具备与作品人物相同的未完成性,成为可供读者批评的审美对象。借用叶芝的面具理论,巴赫金的作者观念可解释为:作者在隐入作品形象的过程中,为减少自我的突出痕迹,常戴上多样化的面具。“作者描绘世界,或者从参与所写事件的主人公视角出发,或者从叙事人的视角或伪托作者的视角出发,最后或者是不利用任何中介,直接以自己纯粹作者的口吻叙述(利用作者直接引语形式)。”[5]458戴上面具的“作者”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客体概念,这恰与叶芝的作者面具定义相吻合。作者在作品中表现为不是“创作者”的作者,而是以变形姿态呈现,各种人物成为戴着不同面具的作者的替身,具有不同的独立意识,相互间产生思想碰撞,代替作者沿着逻辑脉络发声,最终构成与各人物间多重声音的复调关系。
作者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在作品内容上,而且在不同的叙述、修辞、体裁等表现形式上都会有所显现。就作者观的整体历史发展来看,巴赫金复调理论中的作者,可被视为独白型作品创作中权威型作者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创作逐渐打破了固定模式,为不同形式作品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整部作品完全由四种不同的意识构成。作者戴上面具游离于各个声音以外,读者甚至难以发现其踪迹,但其始终存在于作品之中,这正是巴赫金复调理论批评下陀氏类作品在时代上的再次迈进。
二、多重声音的对话
(一)对话性的产生过程
细究叶芝的面具理论,可见其倾向于展现有别于真实自我的状态。隐匿于不同面具背后的作者,为彰显自身思想的复杂性,势必会使不同的思想意识进行碰撞,这恰好还原了巴赫金复调理论中复调声音对话性的出现过程。
虽然,叶芝的面具理论未成系统,但是,整合其各类文论著述,有关“自我”与“反自我”的观点是其理论的思想核心,与多重声音对话性的成因有一定相似性。“反自我”即为“面具”的代名词。叶芝在随笔《人的灵魂》中提出:“另一个自我,即反自我,或者有谁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正相对立的自我……”[6]71面具作为真实自我的对立面,以一种经过修饰的虚构“自我”的方式出现。叶芝提倡以反自我的方式使人格得以完善,表现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即是以自我期待为目标,创造出不同意识的人格。在这一过程中,作品中同时并存“我”在变形状态下的多重声音,以及未完全隐匿于面具后的隐含作者的声音,它们相互独立、各自具备完整的价值,共同构成无等级性的对话关系。
无等级的对话关系正是巴赫金所提倡的。他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复调小说所具有的特点:“各种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之正的复调,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征。但这不是多种性格和命运在他的作品里在统一的作者意识这层意义上的统一客体世界里被展开,而正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其世界的平等意识结合成某种事件的统一,同时这些意识又保持着自己的不相混合性。”[7]3在复调小说作品中,主人公作为作者传声筒的身份彻底消失,各种意识的存在源于叶芝理论中作者的“反自我”,多重声音对话性的意义在不断的思想碰撞中产生。比较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不难发现两部作品在多重声音对话性背后的共同理论价值。
(二)《1916年复活节》与《罪与罚》的对话性分析
《1916年复活节》创作于1916年爱尔兰革命被血腥镇压之后。叶芝许多曾经的友人死于这场毫无结果的流血事件。叶芝带着对此次革命的震撼与迷惘,完成了这一作品。诗作的开篇,发声者以平和的姿态表达自己对这批牺牲者的追忆:“我”与他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或作无意义的寒暄,或曾在他们中间呆一下,有过礼貌而无意义的交谈”[3]146。这一群曾带着活泼神采的泛泛之交,不过是路过发声者的世界。即使这群人曾与“我”有瓜葛,“我”对此也仅仅是略显惋惜。此时,发声的叙述者“我”,情绪是平静自然的。当“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3]146时,诗作所表达的感情进入了转折——这位好虚荣的酒鬼,“他曾对接近我心灵的人/有过一些最无理的行动”,却“从荒诞的喜剧中/辞去了他扮演的角色”[3]147。此时,叙述者的发声中有难掩的钦佩与震撼。叶芝通过发声者表达了自我对此次革命的看法——不过是一场“荒诞的喜剧”,可这群人却因此而亡。发声者无法控制地流露出心中的惋惜与对这些无结果牺牲的不解,这代表着对革命无知的广大群众的意识。下一小节,新的意识出现:影子“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变化”,唯有“石头是在这一切中间”[3]148。这一意识属于历史无意义论的悲观者。他们觉得,在分秒时间的流逝下,一切事物的变动都显得格外渺小,是非对错早晚烟消云散。最后一个意识则认为:“太长久的牺牲/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3]148“这死亡是否必要呢?”[3]149这一意识属于革命中未被处死的反思者的意识。流血牺牲后,他们开始冷静地看待这次无结果的起义,对此有所怀疑,也有所坚持。这一意识说明,包括叶芝在内的对非暴力革命抱有幻想者,对英国政府的信守承诺尚有一丝天真的期待。诗作中的四种声音都属于作者的“反自我”,有关此次起义的思考在不同意识的表露中更具完整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同样展现了多重声音对话性的价值。作品中最具思辨意义的桥段:主人公在杀死高利贷者后,就自身背负的罪恶与索尼娅展开争辩,实则是作者对其杀人之罪的矛盾思考。最具有作者“反自我”价值的是其作品中的主人公。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其主人公大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无论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又或是伊凡·卡拉马佐夫、“地下室人”等,他们大多摆脱了被作家控制的命运。这些主人公们“在思想观点上自成权威,卓然独立,他被看作是有着自己充实而独到的思想观念的作者,却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满的艺术视觉中的客体”[8]3。借用叶芝的面具理论分析,主人公本身所彰显的就是作者的矛盾性思想。当主人公开始关注自身并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时,化抽象能力为具象的表现形式则是各种类型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对话的基本规则是:“表现为‘我’与‘别人’对立的人与人的对立。这种对话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另一种则是人物自身内心的对话。这后一种对话往往又有两种表现形式,即自己内心矛盾的冲突和把他人意识作为内心的一个对立的话语进行对话。”[9]197多重声音的复调从不止步于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罪与罚》中充满了双声语对话。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常常在心中与自己及其他人物进行对话。每当遇到波折时,就在其不同自我意识间产生激荡。收到母亲的来信,得知卢仁提亲,拉斯科尔尼科夫被打击得无比沮丧。他开始挖苦嘲讽自身:“不让这门婚事成功,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去阻止吗?你有什么权利?”[9]197当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与其无辜的妹妹后,他的思想争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他而言,真正的惩罚来自灵魂的拷问,不同意识存在相互驳斥,以至于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举起斧头的刹那,同样杀死了自己。作者通过展现主人公与自我内心、其他人物间的意识对话,使作品展现的人性思考更加全面。
巴赫金复调理论所崇尚的复调关系达到了叶芝“反自我”的评价标准。比较叶芝的诗作《1916年复活节》及陀氏小说《罪与罚》,发现不同意识间的争辩使得文本更具有张力和深度,呈现出作者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多元思考。两者的理论共性是在思想内核上均崇尚作者戴上面具,实现多重声音的对话性价值。20世纪初是思想激荡的大时代,欧洲社会文化信仰危机出现,人们开始怀疑一切,急需深度思想作品的补给。无论是叶芝的面具理论还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均体现出:在时代的要求下,作者需要表现的感情应该更丰富立体、更具多维性。两种理论的提出为具体文学作品的创作开辟了新道路。
三、结 语
人类的思维并不遵循固定的发展模式,而是处在无限的变化波动、消亡再生中。历来的文学作品关于精神世界的描写更倾向于单维度,具有多重声音对话性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恰好打破了这一局面。它以极大的限度展现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打破了文学作品形式上的固定不变,尽可能地还原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多维度思考,拓宽了作品的表现领域。从叶芝面具理论视角入手,重新发掘巴赫金复调理论,可为后者理论价值的显现提供更多可能。
同时,这两种理论并非文论史上的古董摆设,在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仍有精神上的启示意义。娱乐性消费品无止境地为文化工业所生产,“在文化工业的操控下,大众文化失去了艺术应有的批判社会功能、自由超越精神以及独一无二性,它导致了一种艺术的‘物化’现象”[10]104。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读者,其想象力与创造力都在不断地萎缩。文学若完全由文化工业所操控,经典作品的产生将不得不沦为历史。前人以理论的方式开疆扩土,后世的文学创作者是选择以表现自我思想的多维立体性为己任,抑或是选择顺从当前的流行标准?若是选择后者,或许离文学的末日就不远了。
叶、巴二人的理论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进步意义。时至今日,他们的传统作者形象或许已无法适应环境,但其理论显现出的对人类思想多元化的追求,创作者应当责无旁贷地去实践。文学与文化不应幻灭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创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怀揣展现自身思想多维性的目标不断前进。
叶芝面具理论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提出,对西方文论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从叶芝面具理论的视角分析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其理论中复调关系的成因具有新的价值。巴赫金的理论在思想内核上同样显现出作者面具的存在,对多重声音复调关系的出现具有催化意义,与叶芝的面具理论存在一定的共通性。两种理论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当代,作品需要更大程度地体现人类思想的矛盾性、多维性;同时,作者主体性的下降也为多种形式作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借叶芝面具理论重新思考巴赫金复调理论,对我国新时代文学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