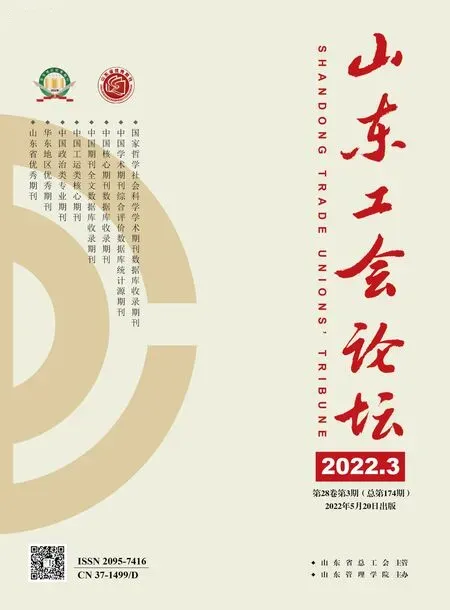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的适用
刘 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问题的提出
诚实信用原则(以下简称“诚信原则”)原本主要适用于债权法,但随后其适用逐渐扩展至其他部门法领域,劳动法亦在其列。尽管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条第1款①已明文规定了诚信原则,但是对该原则究竟谓何以及如何适用未予说明。此外,虽然学术界对诚信原则在劳动法中的适用大多持肯定态度[1],且民法学界对该原则应当如何具体适用进行了一定的积极探索②,但基于劳动法自身的特点以及诚信原则内涵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劳动法中适用诚信原则无法完全照搬民法学者的研究经验[2]。其中,劳动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劳动法的核心制度之一,在实务裁判中与诚信原则的衔接事关劳雇双方的切身利益。因此,如何在坚持劳动法本色的前提下适用诚信原则,形成统一的审判逻辑,避免误用与滥用情形的出现,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在学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法院相关判决进行梳理,尝试提出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制度中的适用建议。
二、诚信原则及其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类型化适用的必要性
(一)诚信原则概述
国外学者当前对“诚信”一词的语义主要存在八种理解:太抽象以致不能讨论(Too vague to discuss)、经过考察才了解(I know it when I see it)、合同利益(Benefit of the bargain)、正当价值(Good cause)、非恶意排除定义(Not bad faith excluder definition)、实质诚意(Honesty in fact)、团体规则或商事实践(Community standards/business practice)、平等交易(Fair Dealing)等[3]。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采用概括方式对诚信给予一般性的定义。例如,我国学界从语义、结构、功能、地位等角度对诚信进行界定,形成了语义说、一般条款说、立法者意志说、双重功能说、衡平说、两种诚信说等各类学说[4]。由此可知,诚信原则的内涵是开放的,对其准确定义存在困难。因此,跳出概念的枷锁,透过诚信的理念,通过个案裁判的梳理进行类型化的情景讨论,是当前各国司法界的常见做法[5]。
(二)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类型化适用的必要性
于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适用诚信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相当频繁,大致有四种适用情景[6]:一是宣示性适用,即在引用诚信规定之后指出某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理念③。二是逃避性适用,即省略说理的过程,跳过原有的法律依据而径直引用诚信原则进行裁判④。三是解释性适用,即对模糊的法律或合同约定用语进行扩大解释,并使之具体化以满足裁判之需⑤。四是补漏式适用,即以诚信原则填补法律漏洞,以恰当平衡当事人权益⑥。
毋庸讳言,以上四种形态下法官对诚信原则的释义均较为单薄。除此之外,甚至有许多案件在裁判过程中对此未进行任何论证说理⑦,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矛盾,反而还会招致更多纠纷的出现,同时也将导致判决标准飘忽不定[7]。为缓解这一尴尬局面,实有必要通过现有案件对诚信原则进行类型化梳理,以明确适用该原则的前提与要件,保障裁判的稳定性。
三、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适用场景的类型化
类型化适用是指在涉及适用诚信原则的各类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通过分类型归纳总结,清晰地展现诚信原则的适用形态,从而明确该原则的适用情景。
(一)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适用的功能体现
在德国学者的视野下,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适用时,有四项功能体现:一是充当理论的基础,用以论证义务的存在;二是担当判断标准,对权利的行使加以限制;三是对权利进行再解释,用以拓宽原有权利的范围;四是奠定法律基础,以帮助当事人调整合同风险[8]。而在王泽鉴教授看来,德国学者所述的第一、第三项功能本质上均为补充性功能,即在不对契约作出根本变更的前提下,创造出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利或义务,以达到个人契约目的;第二项功能为限制性功能,即不得随意滥用权利,并对行使权利的行为加以限制;第四项功能为调整功能,即在某些情况下更改法律行为的内容[9]。在诚信原则的上述功能之外,需要探讨的是基于其产生的一些具体法律制度或原则,如伴随补充性功能而产生的附随义务要求、限制性功能所对应的禁止权利滥用要求、修正性功能所确定的情势变更原则。从诚信原则的这三项功能出发,通过类型化分析,可使法律适用更加稳定,贯彻和维护平等原则[10]。
(二)诚信原则的补充性功能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的适用
补充性功能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的适用主要表现为附随义务的扩张。且基于《劳动法》在立法上较多规定用人单位义务、较少规定劳动者义务的特点,诚信原则的此项功能在司法中主要是用以推导出劳动者的附随义务,以平衡立法对劳动者的偏重。通过现有判决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者的勤勉义务与注意义务
主要是指遵守约定的工作时间与工作纪律、恪守基本的职业道德,在提供劳动时,尽到合理注意。实务裁判中,对于无故旷工、不听从单位的合理岗位安排;工作时间内以及未经过批准的病假期间处理个人事宜;公司通过如张贴公示、微信等多种方式对劳动者进行充分告知后,劳动者仍未到新工作岗位报到并提供正常劳动;故意拖延不续签劳动合同以图获得双倍工资;未获得用人单位授权及支付相关费用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将其他经营主体纳入到用人单位与第三方的销售环节等⑧,法院均根据诚信原则推导出劳动者违反勤勉义务或者注意义务的结论,并进而判定劳动合同的解除于法有据。
2.劳动者的竞业禁止义务与保密义务
主要是指劳动合同解除后,其不得为自己或他人利益而投资或者经营与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活动,同时对自己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予以保守。《劳动合同法》第23条⑨已有对劳动者离职后竞业禁止义务以及保密义务的规定,据此,法官在实务中判断劳动者负有该项义务似乎无需仰赖诚信原则,而只要援引本条规定即可。但根据该条文表述可知,法律未苛求劳动者肩负此种责任,其对劳雇双方关于竞业禁止协议的要求仅以“可以”而非“应当”二字进行规定。不难想见,在法律的宽松要求下,实务中劳雇双方没有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或保密协议的情形并不足为奇。当事人未有协议之约定,法官便无法律之凭据,此时后者仍需按照诚信原则推导出劳动者的相应义务。
3.劳动者的不当言论禁止义务
劳动者的言论自由是宪法中公民言论自由权在劳动法领域的具体化,理应得到保障,自不待言。然而实践中劳动者的该项权利往往与用人单位的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越来越多因为劳动者言论不当而给用人单位带来负面影响的案例。如2018年6月29日,上海某小学发生恶性事件,“58同城”一员工在朋友圈发表言论称,若其本月业绩不达标,将复现此类恶性案件。此番言论在互联网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对此,“58同城”官方回应:“该员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其应履行的工作义务(意指不当言论禁止义务),伤害了公众感情,已与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案件中,用人单位便是根据诚信原则推导出劳动者的不当言论行为违反了其应尽的义务,并进而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此外,法院在认定劳动者是否违反不当言论禁止义务时,往往也需要借助诚信原则作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
(三)诚信原则的限制性功能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的适用
诚信原则的限制性功能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主要表现为禁止某些权利的行使,即从反面定义诚信原则。该原则在此实质上充当着判断标准的功能,用以检视权利运用的限度、定义权利的边界[11]。从现有判决来看,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引用诚信原则大多出于此项功能的运用。不同于诚信原则的补充功能,限制功能并不局限于劳动者,还同时适用于对用人单位的规制。其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对劳动者权利的限制
一种情形是对劳动者滥用二倍工资请求权⑩的限制。实践中出现不少劳动者滥用该条款的情形,即利用用人单位在签订合同中的程序瑕疵来请求双倍工资。对此,上海法院率先以诚信原则对劳动者滥用权利的行为进行了限制,其认为,用人单位是否需要支付双倍工资,应当考虑其是否履行诚实磋商义务,以及是否存在劳动者拒绝签订等特殊情况。此外,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标准应该更加严格,因为此类人员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相较于其他普通员工具备更多的劳动法知识与个人技能,并不像后者那样弱势。
另一种情形是对劳动者单方辞职权的限制,包括预告辞职和即时辞职两种方式。从预告辞职的角度来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可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只要经过了法定程序,即便对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失,也无须担责。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用人单位经营的稳定性,因此部分法院通过诚信原则对劳动者的预告辞职加以适当的限制,以保护用人单位的信赖利益。如在林某与清流县某医院劳动争议一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林某在接受了该医院的医师规培协议(明文规定了医师的服务期间),与之存在事实聘用关系的情况下,主张预告解除,给医院的人事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违反了诚信原则,故判决林某败诉。从即时辞职的角度来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可知,法律规定了用人单位的过错情形,只要实践中出现了相应情形,劳动者甚至无须经过一定的程序缓冲即可主张解除劳动合同,显然该规定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更为不利。因此实务中同样通过引入诚信原则作为判断标准,对劳动者的即时辞职权利加以限缩,认为合同一旦确定,劳雇双方均应恪守诚信原则,除非用人单位主观存在恶意,其他情况下若要认定劳动者的解除权,条件均较为严苛[5]。
2.对用人单位权利的限制
劳动合同解除中,用人单位的权利主要是指解雇权。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解除权相类似,《劳动合同法》第38条、39条、40条规定了用人单位的预先通知解雇权与即时解雇权。不难想象,该权利一旦被滥用,将对劳动者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法院强调用人单位应谨遵诚信原则。例如,我国法律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规定了一些保护条款,但这却在客观上增加了用人单位的劳动力成本,于是用人单位便以经济性裁员等理由“曲线救国”,以实现解雇目的。对此,法院并不囿于法律规定,而是从诚信原则角度出发对用人单位是否滥用解雇权进行权衡。可见,利用诚信原则对用人单位的解雇权进行限制,即在必要情况下介入适当干预,可以有效促进劳动关系的动态和谐,从而充分尊重和发挥劳动力市场的引导作用[12]。
3.对双方共同权利的限制
一方面是对劳雇双方的诉讼权利的限制,避免二者在劳动诉讼成本低的情况下出现滥诉现象;另一方面是对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限制。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第466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存有分歧时,应根据诚信原则并结合相关契约条款,确定当事人的真意,这便是借用诚信原则控制合同内容,避免当事人双方在解除契约时出现利益失衡的情形。如在陈某与新疆某食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法院认为根据诚信原则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并从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三方面来细化诚信原则在本案中的运用,综合这三方面分析得出该公司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结论,从而判决陈某败诉。
(四)诚信原则的调整性功能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的适用
诚信原则的调整性功能在劳动合同解除中主要表现为情势变更原则,该原则是指在客观事实发生变化之际,对契约的内容或效力进行调整,从而保障公平正义,维护诚信原则的理念[13]。
实践中,工作场所租约到期未再续约、政府政策导致双方合同成立的基础和环境发生变化等各类客观情形,均被认定为情势变更。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之下,情势变更原则于实务中的适用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如在王某诉山西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民事二审一案中,被上诉人即辩称因为受疫情影响,其对公司架构和人员岗位进行优化调整,因此上诉人所在的数据分析岗位被取消不属于违约,而属于情势变更。类似的情形在实践中大量出现。由此观之,情势变更原则在实务中呈现不断扩张之势。然而,情势变更原则系诚信原则之例外,实务中对之适用不应如此频繁,应予以适当限缩。
四、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的适用情景明晰
结合上述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的适用形态来看,若不注意对其适用边界加以限制,则会使诚信原则的内涵无限扩大为“遵守法律”,因此有必要明晰其适用场景,厘清其适用边界。
(一)适用对象
诚信原则是适用于当事人之间,还是适用于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存有争议。分歧焦点在于诚信原则是否适用于法院。否定者认为诚信原则不适用于法院与法官,主要理由在于司法实践中难以识别与判断法官的言行是否有悖于诚信原则;肯定者认为诚信原则不仅适用于当事人,同样也适用于法院,理由是将法院纳入诚信原则的规范范围有助于提高司法品质[14]。由前文所述判决可知,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诚信原则的适用存在两种情形,一类情形是当事人一方提出诉求时,以对方违反诚信原则作为支撑理由;另一类情形是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根据诚信原则来判断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诚信原则的意涵。由此,诚信原则的适用对象似乎仅为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未有对法院诉讼行为的约束功效。然而实际上,从我国民诉法的立法精神来看,诚信原则同样适用于法院(法官)[13]。
在此讨论民诉法上的问题,似乎有偏离主题之嫌,然而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实体法律关系的解决难以从诉讼程序中剥离,前文所提及之诚信原则适用不当的判例,绝大多数与法院的不妥诉讼行为相关联。在补充性功能的适用中,法院对劳动者的附随义务说明较为随意,如所谓的“不当言论禁止义务”,其在法律条文中实则于文无据,只是与劳动者的忠实义务似有关联,但法院仍然以劳动者违反不当言论禁止义务为由进行推理裁判。不难想见,未来必然会出现更多的新兴科技领域,若凡遇新情境便在原有的劳动者义务基础上自由解释,诚信原则将可能沦为滋生不当造法行为的温床,司法与立法的边界也将日益模糊。在限制性功能的适用中,法官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满足法定解除权的行使要件时,又进一步动用裁量权判断过失方主观是否存在故意,如此一来,相当于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人为地改为过错责任原则,造成架空法律规定的不当结果。在调整性功能的适用中,法官将当事人意料之外的情形均解释为“情势变更”,实际上是以缔约时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想法作为判断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造成情势变更原则乃至诚信原则的滥用。由此可知,实践中往往过于关注当事人双方是否对诚信原则予以恪守,而忽略法院(法官)对该原则的遵循,这便很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诉讼程序指挥权、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进而出现上述诚信原则适用不当的窘境。因此需要明确,在劳动合同解除中适用诚信原则,受该原则规制的不仅包括实体法律关系当事人,更应包括法院,其在诉讼中应始终保持审慎态度,不可随意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说明。
(二)何时适用
法官在裁判中对诚信原则说理释义的随性态度,实则从本质上反映出其对诚信原则启用标准的理解较为模糊。因此,除了对其审判态度加以端正之外,若申明适用该原则的事前审查标准,或可从源头有效避免该原则的滥用与误用。通过参考法国民诉法学界对民事司法实践滥用诚信原则的批评,拟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明确:
1.适用诚信原则应当具备必要性
部分案件适用诚信原则缺乏必要性,因为援引劳动合同解除的有关法律规定足以解决,越过其他特别条款直接适用诚信原则或附带援引诚信原则实无必要。这种情况在诚信原则的补充性功能适用中体现较为明显,劳动者的附随义务来源包括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如劳动合同解除后的竞业禁止义务与保密义务),最后才是诚信原则的推定。判定因为劳动者行为不当而解除劳动合同,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推导出劳动者未遵循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即可。然而实践中法院往往会越过前两个环节,直接根据诚信原则得出劳雇双方违反各自义务的结论。如高某与抚顺市东洲区某教育培训中心劳动争议一案即属此情形,在双方当事人有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况下,法院不依照该协议进行裁判,却根据诚信原则来判定双方是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而判决当事人是否有违约情形。
当然实务中更常见的情形是,在前两个环节之外根据诚信原则得出劳动者行为不当的结论,其中,法院除了说明劳动者违反《企业保密协议》外,还额外指出了其行为与诚信原则背道而驰。实际上法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6条和37条即可解决本案争议,并无必要援引诚信原则。在已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基础上适用诚信原则,将导致诚信原则的内涵异化为“无欺诈”。
2.适用诚信原则应当具备相关性
部分案件适用诚信原则缺乏足够的相关性。所谓的相关性,其实是指法院的裁判结果是否必然由诚信原则推导出来,也即诚信原则与案件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四川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王某劳动争议一案中,法院认为,劳动者故意在《员工离职申请表》中添字成“主、被动离职”,导致语义含混不清且未告知公司,企图造成该申请表不发生法律效力,有违诚信原则,因此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不违法。该案援引诚信原则,与判定用人单位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间并无足够的因果联系,因为法官判断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正当的直接依据为《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相关特别规定,诚信原则充其量只是本条第5项款规定“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背后所隐含的法律理念。众所周知,私法领域的绝大多数规定都难以摆脱诚信原则的影响,若认为法律规定所彰显的法理念亦为裁判的直接相关依据,恐会使裁判逻辑更加凌乱。可见,比起诚信原则适用的必要性,相关性适用对法官的个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这也凸显出相关性适用的重要性,其将直接影响到诚信原则的适用边界,若处理不当,轻则会弱化判决的说服力,重则将降低司法公信力。
(三)具体要求
上述对于必要性、可行性的把握,主要是从方法论角度对法官的宏观操作行为和审理态度进行指导。然而,实践中各类案件千差万别,仅有粗糙规定难以精准解决难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诚信原则的三大功能,进一步明晰诚信原则的适用场景。
1.补充性功能的适用要求
在劳动法立法对劳动者利益进行倾斜保护的背景下,由诚信原则的补充性功能推导劳动者的附随义务,应对推理过程加以必要限制,如若不然,便会对用人单位的利益失之过宽,违背劳动法的立法初衷。其中需要考量的要素包括:
首先,应以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作为重要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劳动者的附随义务来源有三:第一是法律规定,第二是当事人约定,第三才是诚信原则的推定。因此,由诚信原则推导出附随义务存在的思路,是前两种推理方式的缺漏兜底,实务中不可直接跳过法定和约定而由原则进行推理。如,以法律规定为前提适用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做到:判决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劳动合同法》第39条、40条、41条和42条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尽力审视劳动者是否确实存在这些法律规定的不当行为,而不是从用人单位存在损失的结果出发,定要为其找寻一个责任主体,并以诚信原则作为万金油式的依据。又如,以劳雇双方的约定为前提适用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做到:法院援引诚信原则来判断劳动者是否存在违反前文所述之竞业禁止义务与保密义务,应以劳雇双方之间无相关协议为前提。若劳雇双方之间有约定,则按其协议之约定进行审判即可。可见,诚信原则的适用顺位尤其重要,其直接影响了裁判的准确性与专业性。
其次,应结合劳动者的个人具体条件确定附随义务标准。一是不同职位的员工应承担不同种类的附随义务。如我国《公司法》第148条第5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期间的竞业禁止义务为其法定义务,无须双方约定。其潜在逻辑是,这些人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在工作中接收的信息更为私密、更有技术性,一旦他们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害是普通员工所无法比拟的。相反,对于普通员工而言,其工作内容可替代性高,且不涉及商业机密,在私法自治理念与商法营利价值的指导下,法律对其无须课以竞业禁止义务。二是不同职位的员工承担同一附随义务的程度应有不同。以勤勉义务与注意义务为例,比起普通员工,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应承担更严格的勤勉义务标准。三是有关附随义务的岗前说明义务由用人单位承担,若未事前说明,则劳动者的过失行为不得成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四是授权用人单位以内部章程规定其损失的标准、认定严重损失成立与否以及其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的具体机构与程序[15]。
最后,应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调和。“自由得因维护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必要而受限制。”[16]不可否认,在诚信原则的理念下,劳动者应积极维护用人单位的利益,但若用人单位的行为有损社会公益时,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对抗行为便可有利于大众权益。如曾引发热议的“空姐微博吐槽案”即为一例。该案中,航空公司宣布将启用新的餐食服务,两名空姐转发并评论称,该餐食所包含的食物量少而口感差,只更换餐具根本无用。随后公司将她们解雇,理由是其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的内容影响恶劣,对公司造成了损失。但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空姐的评论并非无益。可见,判断劳动者揭露言论行为的正当性与否,应采纳客观判断标准,不应偏颇、机械地认为利益衡量的天平两端只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而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兼顾劳雇双方的权益。
2.限制性功能的适用要求
不同于诚信原则的补充性功能通常在于设定义务,且主要是为劳动者设定义务,限制性功能则是基于劳雇双方的利益进行综合考量,竭力避免权利边界的无度扩张,其审视视角更为周全。但该项功能在劳雇双方行使解除权的适用方面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外,补充性功能对义务的设定功能类似于司法中的“立法”,天然地决定了法官在论证说理环节将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这也是限制性功能在实践中所无法相比的。综合这两方面来看,诚信原则限制性功能的发挥或可从法官的说理论证环节加以规制。
首先,应强化论证说理,避免诚信原则的道德性适用。在限制性功能运用的裁判中,基于权利法定原则,法官通常不会在说理论证环节耗费过多精力,经常直接作出判决结果。如在陈某与西安某中医心脑病医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西安某中医心脑病医院有限公司以辞职为要挟,使陈某无法接受其要求的薪酬并解除劳动合同,只得选择原薪酬继续工作,对其进行变相剥削,法官在无推理过程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该有限公司违反诚信原则的判断。这种方式虽简明扼要,但其适用具有强烈的道德性色彩。因此可以通过强调法官在适用诚信原则时的说理论证义务,增强判决的信服力。
其次,应通过详细阐述或将下位原则具体化,精细化适用诚信原则。上述法官对诚信原则的适用过程较为模糊,本质上是由法律原则本身并无明确适用标准这一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实务中如不对其适用语境和构成要件加以明晰,难免会造成诚信原则的空泛化,使得裁量权过度膨胀。如前述陈某与新疆某食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法官从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三方面来细化诚信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最后,法官不应过于谨慎对待有关劳动合同解除条款的适用。该项建议是在前两项建议的基础上,从反面对限制性功能的适用进一步具体化,因为一旦法官深陷说理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过度追求原则适用的准确性,可能会造成矫枉过正的结果。例如前文提及的林某与清流县某医院劳动争议一案中,法官纠结于判定劳动者行使即时解除权是否恰当,便是因为过度审慎甚至走向了忽略法律规定的另一极端,而这不能不说是自由裁量权肆意的另一种体现。
3.调整性功能的适用要求
若认为限制性功能的适用更多是对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限制,则调整性功能无疑更侧重对法官裁量权的限制,即要求其在实务中限缩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场景。结合前述案例总结司法实践中“客观情势变更”的类型,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因政府行政行为导致契约基础根本动摇或履行困难;二是市场环境变化造成合同基础丧失或履行困难的其他情形;三是第三人原因导致契约基础丧失。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以疫情为代表的传染病属于自然灾害,原则上应当归属于不可抗力,而非客观情势变更,但疫情带来的影响除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外,还包括因疾病流行造成的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履行困难,如疫情期间国家宣布对国内跨区域以及跨国旅游活动的限制,此时合同面临的状态属于履行困难,而不属于履行不能——这便是“不可抗力”带来的“客观情势变更”。
概言之,一方面,法官不可随意放宽“客观情势”的范围标准,凡遇超出当事人主观之外的客观情形,便将之纳入到“客观情势变更”之列。若确有放宽之需,应严格参照前述诚信原则的补充性功能与限制性功能的说理适用过程,慎重适用。另一方面,法官不应一律将不可抗力排除在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在疫情期间对合同效力的检视应当更加关注细节。
(四)法律责任
针对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建立一套相应的责任体系,无疑可以为诚信原则的适用提供有效保障。主要从当事人和法官两个方面加以规定:对于当事人个人而言,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责任无需赘述,因为对其责任的追究权已交由法官落实——法官在审判中自然会申明其在程序法上的败诉后果和实体法上的民事责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法官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责任,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对诚信原则的适用状况纳入到业绩考核当中,并根据具体情况追究其法律责任。但须注意,法官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时,若因为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不应认定为违反诚信原则。
五、结论:类型化下的谨慎适用
劳动契约虽仍属民事契约,但相较后者而言,其特有的身份性与继续性对合同双方的彼此信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一方诚信缺失,都将严重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故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引入诚信原则,一方面可以有效衡平劳雇双方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规范法院的裁判行为。然而由于诚信原则的抽象性,其适用情形并不像一般法律规定那样清晰。正如卡尔·拉伦茨所言,法律原则非为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规则。于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适用诚信原则,应严谨审慎:在已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前提下,无适用该原则之必要;若裁判结论并不必然由诚信原则推理得出,亦无适用该原则之必要。此外,根据诚信原则的三大功能,在个案中适用该原则应进一步具体化。于补充性功能,劳动者的附随义务应严格以法律规定为前提;于限制性功能,应注意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于修正性功能,应遵循例外情况才予以适用的原则。最后,应对相关主体课以一定的法律责任,从而加强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案件中适用的保障,维护司法稳定性。
注释
①《劳动合同法》第3条第1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原则。
②梁慧星教授在《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中提出:其一,诚信原则的使用裁量权应仅授予最高法院;其二,应优先适用具体法律规定,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其三,应优先适用类推适用等漏洞补充方法,禁止“法律的软化”;其四,适用诚信原则与适用判例得出同一结论时,则适用判例,反之则适用诚信原则。徐国栋教授在《诚实信用原则二题》中提出,诚实信用分为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我国把诚信原则的适用局限于客观诚信,这一理论存在缺陷,应吸收先进的研究成果再造。
③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再79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申7号民事裁定书。
⑤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1306号民事判决书。
⑥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申5866号民事裁定书。
⑦参见《海淀区劳动争议审判情况白皮书——暨十大涉诚信典型案例(2012—2013)》。
⑧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民终1465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2165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4840号民事判决书。
⑨《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⑩《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