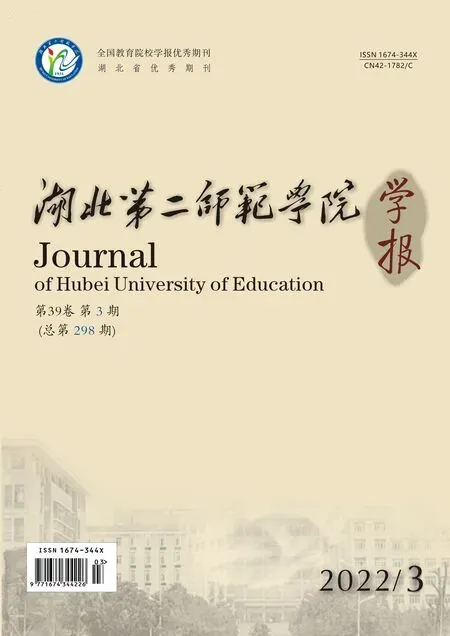论《太古和其它的时间》的三种时间
刘康蓓,吴 昊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2.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410081)
《太古和其它的时间》是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于1996年发表,并为她赢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美誉的代表作,组委会认为托卡尔丘克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太古和其它的时间》虚构了一个叫做太古的乡村小镇(太古之境可以视为人类生存秩序与大自然和神的秩序互相接壤的地带),描写了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直至二战结束几十年之后小镇的现实故事与虚幻梦魇。故事在现实与幻境之间游离,通过当地居民的生死变迁、动植物的风雨飘摇和上帝的创世游戏展现了作者对时间的三种不同审视维度。
《太古和其它的时间》是托卡尔丘克创作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她用细腻敏感的笔调来叙述人类的爱和欲望、时间的流逝和更迭、世界的存在与虚无,以含蓄多变的视角展现轻盈灵动的文本语言,在一首真实又虚幻的交响曲中吟唱出对时间的哲学思考。太古三代居民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里的世事浮沉贯穿于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之中,这一行文线索流露出“人虽然是世界的主体却不是世界主宰者”的观念,人要对世界存有敬畏之心,人类中心主义之下的“物”和“上帝”都是“非人的存在”,但它们同样构成了作者审视自身与他者的重要主体。众所周知,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三维世界。但是小说呈现的世界观超越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那个从小被认为有病的伊齐多儿是太古唯一的智者,他透过阁楼上的四面窗户得出了异于常人的发现:其实世界是由四种元素构成的,第四维便是时间。作者在书中打破了人类自以为是的三维科学观念,把以往易被忽视的对于时间的思考提到了重要地位,从而把人过分自信的主体性从神坛拉回了凡间。时间概念是作者行文布局、凸显主题的关键要素。
“太古的时间由三层结构组成:人的时间,大自然的时间以及上帝的时间。这三层时间结构将叙事者提及的所有形象,所有现实和非现实的存在形式,完整地、均匀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一首既具体又虚幻的存在的交响诗。”[1]5小说的题目与时间有关,每一章节也以“XXX的时间”为名,托卡尔丘克无疑是一个善于思索乐于探析时间本质问题的人。下面笔者将从小说中的“人”之有限坚忍的时间、“物”之无限自由的时间和“上帝”之权威中立的时间这三种审视时间的角度来探析文本背后的主题意蕴。
一、“人”之有限坚忍的时间
“人”是小说重点描绘的主体对象,以有限生命角逐永恒真理的欲望之举铺满了他们生命的时间轨道,可以说人的庞大欲望下至日常的吃喝拉撒睡,上至永恒的生命和无限的时间。
太古的居民祖祖辈辈从没有人离开过太古,即使有人曾试图跨越边界,那也只是在交界线上进入了梦乡。只有当他们意图返回太古时才能从梦中苏醒,并将梦中的际遇误认为是真实的回忆。所以,太古对于这里的人们而言是宇宙的中心,除了这片天空下的一切,其他都不存在,太古的所有时间都与小镇居民有关,居民的时间也无法脱离太古的时间而存在。某种意义上太古的时间就像一个封闭空间一样笼罩着所有故事的开端和结束,而人本身又是欲望的载体,在有限生命中恋恋不舍地寻找着无限,渴求在自我掌控中寻找完美与不变,却往往无功而返。书中米哈乌为了拖延女儿米霞的婚期提出要花三年的时间来修缮婚房,麦穗儿不愿让女儿鲁塔嫁给富商而全力挽留,帕韦乌年迈之际回忆以往四十年岁月他有的只是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没有满足的欲望,溺死鬼普卢什奇期待在他人死去时以借尸还魂的方式来帮助自己重获新生……人们害怕短暂有限的时间,惶恐不确定的变化,恐惧未知的将来,太古居民的挣扎和哀求在单项时间维里显得无力且被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注定是渺小和脆弱的,相反,面对生活的缺失和命运的拨弄,他们能够在生活的甬道里直觉本真地活着,于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静默坚忍地生存。
文中的地主波皮耶尔基斯财运亨通、荣获四方,当疾病来袭、死亡威胁生命之时,他感受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剧感,他总觉得世界在消失,世界上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都在消失”[1]83,于是他开始反思自身存在和生命本质的问题:“我们要去向何处?时间的尽头是什么?”[1]85这是地主后来在纸牌游戏中苦苦寻求的谜面之解,也是作者借人物之口抛出的人类永恒之思。人类在有限的时间里充满了无限的追寻,面对不可逆甚至不可为的时间之问,人依旧保持着最大的憧憬,戴着镣铐起舞,如同地主波尔皮耶尔斯基没日没夜地摆弄上帝无解的纸牌游戏那样,可见,人是集束缚和自由于一体的矛盾生物。
作者托卡尔丘克在书中借主人公伊齐多尔之口说道,“人给自己的痛苦套上了时间。人因过去的缘由而痛苦,又把痛苦延伸到未来。这样便产生了绝望。”[1]123如果说人痛苦的来源是源源不断的欲望,那么人痛苦的持续则来自于有限的时间。一方面,人受困亦或是受苦于有限的生命,欲望诉求永无止境,悲哀痛苦亦永无止境;另一方面,苦难又推动着人成为自己的救世主,对无能为力的真相怀抱大无畏的热忱的英雄主义精神。时间概念是太古居民自己强加于自己的,他们也明白时间是不可逆的,因为这不可逆的法度,米哈乌无法阻挡三年后如约而至的婚期,麦穗儿也无法说服去意已决的女儿。人不仅有来自于满足和纵容自我需要的欲望,而且还渴求以自身的微薄之力来试图挽留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纵然历史事实早已告知人类,结局只可能是事与愿违,但置身于历史盛衰兴亡中的人类还是会驻足在时间漩涡之中,默默忍受着确凿的时间流带来的一切结果,因为我们无法消弭自我内心深处对他物无休无止的渴望和欲求,所以也无法抛却追逐永恒时间的念想。此外,只有当抽象的时间有了精准刻度,人的存在才有标准的衡量意义,这正是人最脆弱也最坚忍之所在。
回到地主思考的那个问题:时间的尽头在哪?毫无悬念,答案是时间没有尽头,就像时间没有开端一样,太古居民所生活的时代和年份是从零开始计数的、并由一代代繁衍的子嗣继承和流传下来,虽经历了历史的淘洗,但终究不过是自己设定的圈套,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时间的全部概念,是太古小镇的操盘手,可以用自我主体性来捆绑世界所有的存在。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的时间能够超越太古世界的永恒时间而存在,太古是生生不息、循环不已的象征,人也只是活在太古底下的一环、一角而已。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古的时间是因形形色色的人们之存在而成为无尽黑暗中闪烁的光芒,不管它来自太古居民原始的性欲、钱权的追逐,还是仁慈的善良、隐忍的母爱,人类时间的有限和太古世界的永恒彼此束缚,永生共存,互相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借此提醒我们,人可以拥有在有限时间里追逐他物的欲望,但诉求不能毫无底线,否则即便是用飞蛾扑火的决心奔向未来,也只能沉溺于无尽的虚妄,在绝望和沉沦中形神俱灭。人不应做时间的奴仆,也不应做时间的君主,应该跟时间做朋友,这样人才有可能以主体性的地位在浩浩汤汤的时间流中施展宏图。
二、“物”之无限自由的时间
物体的时间跟人类的时间不一样,它们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生与死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达到永生。物没有人类社会生活体系,更无时间维度,物只是依附自身而存在。换句话来说它们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时间对它们而言,仿佛永不存在。亘古不变的太古、数年如一日转动的咖啡磨、生长在森林深处的菌丝体、拥有苹果年和梨树年的果园、长久静默如初的椴树等的时间是永恒不变的,它们不像人类那样追逐毫无节制的欲望,也不奋力挽留无法停滞的时间,它们不将过往的痛苦蔓延至未来,它们只活在唯一的当下。当下即永恒,永恒即当下。正因为这种“永恒”,让它们的时间维度呈现出无限自由的状态。
托卡尔丘克在获得诺贝尔奖时说道,“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2]作者认为文学现实主义的表达已经无法反映当下复杂矛盾的世界,所以她一直渴望突破文学叙述常规,采用不同而且容易被忽略了的碎片视角来拼接丰富独到的世界,于是我们才会在小说中看到除了人以外的“非人存在”,而这些细小的微粒也拥有着温柔强大的力量。
在椴树的时间里,“椴树像所有的植物一样活着,就是一场永远不醒的梦。梦的开头蕴藏在树的种子里。梦不会生长,不会跟树一起长大,梦永远都是那副样子。树木被禁锢在空间里,但不会被禁锢在时间里。他们的梦将他们从时间里解放了出来。而梦是永恒的。树木的梦不会像动物的梦那样产生感觉,不会像人们那样产生形象、情景”。[1]237现实之境的纷纷扰扰并不干涉椴树的永恒之梦,因为它脱离了时间概念而存在,也意味着从死亡中解脱出来达到永生。椴树不为寒夜暴风雨袭来撼动,也不为秋日落叶飘荡而忐忑,在暗潮汹涌的时间流里,它无欲无求,只学会了深深扎根土壤静默不动。
对于太古里像椴树一样的“物”而言,它们不像人类成为了时间的囚徒,它们在无限自由的时间维度里参与着太古的一切活动,它们认识自我、对话自我。米歇尔·福柯曾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3]束缚人的不是具体的物理空间,而是无形的时间空间,局促持续的变化给人们带来惶恐和不安,激发欲望和诉求。而“物”最异于人类之处就在于它们从不追赶时间,把自己从束缚的时间观中解放了出来,享受当下无限自由的欢愉。在作者眼中,“物”并不是世间飘浮的琐碎存在,相反,它是跟人类一样重要的本真存在。“物”的时间是暗藏隐蔽的时间,尽管人类难以发现它们的时间存在,但它们却是突破人类现有狭隘、自私、片面角度的新起点,也是寻找时间真正存在意义的下一个出口,因此作者才让“物”发声。
托卡尔丘克认为比起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因此这部小说的目光对准了那些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碎片对象,以“物”的新奇视角来还原世界的本真面貌。《太古和其它的时间》以温柔细腻的笔调展露物体自由无限的时间维度,作品触摸到了当下喧嚣时代最安静、最自然的声音,而读者也不难发现托卡尔丘克也醉心于这些可爱小物件的微观视角中,感受着它们时间的脉搏。
三、“上帝”之永恒悖论的时间
上帝之神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地主玩耍的棋牌游戏现身。上帝不属于人间,不存在生死,所以他拥有永恒,他是时间的永恒主宰者。如果说人类在时间之下,物体在时间之外,那么上帝则在时间之中,上帝与时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他用一种权威中立的态度审视所有存在,他给予万物生命的同时又无法让他们避免死亡,也就是说某种宇宙之道位于上帝之上。在上帝时间范围之内,他的权威无人可挑战,可对于超越了时间的部分,上帝就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了,于是上帝的时间形成了一种悖论,因而上帝对待世间既是温情的,又是残酷的。人和物的时间不断在重复,人靠持续生殖繁衍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永恒的追逐,物靠连接梦境重复时间来达到永恒,而上帝永不重复自我,他只重复世界。
在托卡尔丘克笔下,上帝他可以创造世界和人类,又可以破坏一切。上帝改变不了人世间起承转合的规律,就像上帝即便是现身于麦穗儿体内,使其可以用奶水治好太古居民的疑难杂症,但这些痊愈的人们终究会在战争中死去,上帝赐予人间的灵药只是延缓了人们生存的步伐,并无法使人们逃离死亡的命运。当太古的居民遭受战争的磨难时,文中人物也不止一次对上帝发问:既然上帝是仁慈和善良的化身,那为什么上帝还容忍恶行和苦难的存在?历经磨难的伊齐多儿在对上帝存在问题思考许久后得出了答案,“‘上帝啊’听起来如同说‘太阳’,如同说‘空气’,如同说‘地方’,如同说‘田野’,如同说‘海洋’‘粮食’一样,都是中性名词,跟‘黑暗的’‘光明的’‘寒冷的’‘温暖的’这些中性形容词也没什么区别”[1]243。上帝关注流逝的时间,关注人间的苦难,关注从新生开始的死亡,关注从死亡开始的新生。经历了创伤、打击与混乱之后,伊齐多尔大病一场,他看破了上帝的本质,决心自己救自己。
上帝在棋牌游戏创造的第八层世界中自白道,“创造世界达不到任何目的,不能发展,不能扩大,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创作是徒劳的”[1]311。世界是上帝看到的循环往复的游戏,结局早已注定,纵然对于上帝自身而言死亡并不存在,但他无法让人类超越时间规则限制达到永远存在。托卡尔丘克笔下的上帝不是无所不能的,他是万物之主但同人类一样迷茫。上帝创造一切也在试图了解自己创造的一切,给予一些人帮助的同时又对更多人袖手旁观。上帝拥有权威永久的时间,可他只能以一种矛盾的视角审视万物,因为有一种未知的秩序超越了上帝,这便是《太古和其他时间》背后的神秘主义指向,来自超越时间的不可知部分,即便是上帝也要对其存敬畏之心。可以说,毋庸置疑的永恒力量是上帝的明信片,超脱了死亡禁锢于永生是上帝的墓志铭。上帝象征着人类的最高信仰追求,某种程度上无所不能的上帝也是人类自我理想的化身,上帝不容置疑的权威也包含着几分人类渴望通过宗教的方式主宰一切的野心。在书中,托卡尔丘克利用对上帝时间的思考将这种恒定的权威做了拆解,也解构了人类不可一世的妄想。
托卡尔丘克的祖国波兰是一个拥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信仰天主教,上帝是波兰人信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上帝的勇气和意志在数百年的战争浩劫中给了波兰人民莫大的支持与鼓舞,但战火过后,宗教在世俗社会中的作用变得复杂多样起来,上帝与教徒的关系多了几丝微妙谨慎。托卡尔丘克在书中并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而是用一种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的态度审视上帝在当下时代的意义。既然上帝也无法解答作者追寻的时间之问,也和万物一样身处某种不可抗力之中,那么人们在受难时为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目光投向上帝呢?作者认为上帝虽然是权威不可侵犯的,但是人除了获取宗教精神的力量外更多时候还需要现实自救,由此可见托卡尔丘克的叙事结构包含了更多诗意化的现代性思考。
综上看来,托卡尔丘克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将无数细微的故事碎片融入了一个灿烂绚丽的星丛结构中,以多维复杂的方式描绘了“人”“物”和“上帝”的故事。“这三者的时间维度能够以无限的方式互相参照,可以跨入彼此的故事建立联系”[4]。没有一个时间维是完美无缺的,每个时间里快乐与悲伤都并存着。但这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相信一种时间的存在,而放弃思索其它的时间角度。托卡尔丘克始终相信万物都处于无所不在的联系中,时间也是如此,小到自然界的一株植物,大到被奉为至尊的天神,综合开放的视角才是突破局限的钥匙。作者背后蕴藏的其实是一种万物有灵论、万物平等观。她反对当下科技时代人类居高临下的暴力姿态,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带来更加包容、自由和博爱的世界,反而把极权主义和个人偏见推向高潮。如同太古小镇里凌辱妻子的丈夫和悍然发动战争的军队那样,他们都是把自我利益看得过重。所以,托卡尔丘克推崇的是一种更为包容、多样、平等的审视角度对待自我,对待亲朋,对待自然界,对待上帝。人类要学会从那些以往被轻视、被忽略、被排挤的对象上学会用心灵发声,这样的世界才会是一个趋向完满、和平、美好的状态。
四、结语
在《太古和其它的时间》中,人类是世界的主体之物,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构成了太古最生动的自然图景,但人们并不拥有生命绝对的主导权,他们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声色犬马却无法控制流动的时间和遏制有限的生命。单调沉默的物之存在似乎无足轻重、任尔东西,但是它们则是在当下即永恒的时间流中感受自己美妙独特的生命存在,不受困于有限的时间概念中而无法自拔。上帝是拥有永恒权威并且掌握世界的时间存在,可难以更改超越了时间限制的不可知的宇宙法则。托卡尔丘克并不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对现实进行审判,而是借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思索人类未来的出路,跨越了生命的边界和学科的体系,涉足“人”和“非人”对象。“托卡尔丘克则充分发挥‘碎片化写作’的优势,游离于历史时间和个人时间之中,以微见大,以轻驭重,”[5]利用文学的方式联系哲学、心理、宗教等相关知识,将时间观念和盘托出。
事实上在波兰文坛中,托卡尔丘克并未完全被大众所接受,她更像时代的逆行者,“她因对波兰多民族混居史的描写,对波兰当政者粉饰和捏造历史的批评,对波兰长期掩盖曾作为弱小民族的压迫者、蓄奴者和犹太人谋杀者的无情揭露”而遭到许多非议。[6]因此在面对未来世界走向的问题上,托克尔丘克依旧选择为易被轻视的群体发声,就像太古里那些非人的渺小存在一样。她肩负作家的时代责任与担当,通过“人”“物”和“上帝”这三个维度向读者展示了三种不同的时间维度。她并非以简单的好坏标准来叙述不同时间维度的孰是孰非,而是以神秘、温柔、和置身事外的叙述者身份,提供了一个可以看到任何碎片事物的时间角度,借此发出警醒:既然所有存在事物的时间维度本就是一个不可切断的整体,那么人类又何以固守自我,而忽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呢?如若人能超越现有经验,那无论是物还是神,它们最终会帮助人类往谦逊、包容的方向迈进,同时跨越时间共同构成世界原本温柔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