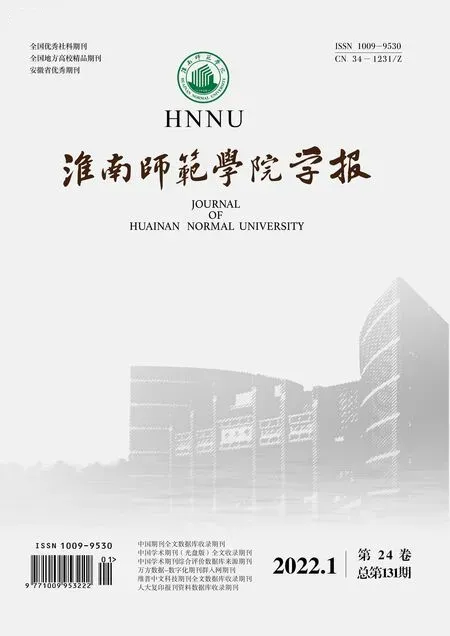功能对等在语篇翻译中的运用
王功菊
(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商旅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1)
“功能对等”也称“动态对等”,该理论以表达方式的完全自然为目标,尝试将接受者与其自己文化语境中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力求达到高层次的对等(maximal equivalence) ,即“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译文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 的 反 应 基 本 上 一 致 ”[1](P396)。 而 最 低 层 次 对 等(minimal equivalence) 是“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译文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1](P396)。 简而言之,翻译就是在译文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首先是实现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是实现文体(风格)上的对等。
一、功能对等在语篇翻译中的运用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准确有效的翻译往往建立在上下文语境中,单一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单词只能单纯地理解为句意或词义而不是译文,因此翻译一般都是语篇翻译。 语篇翻译可以从词汇对等、句法对等、语篇对等和文体对等四个层面达到对等。下面我们主要从原文的语篇和文体层面,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分析阐述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创作出较为理想的译文。
(一)语篇对等
胡壮麟先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一书中,他是这样定义语篇的:“语篇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意义的自然语言”。 从中可知, 语篇是一个具有连贯和衔接的单位, 而且在一定语境下具有完整意义。 而语境又分为言内语境(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和言外语境(由语言与社会环境关系构成),言外语境又可分为显性情景语境和隐性的社会文化语境[2](P56)。语境对翻译的限制性可以体现在凸现语义、延伸语义和取舍语义等方面,因此语篇翻译的过程中离不开原文语境。
许渊冲教授认为,西方各种语言的词汇基本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表达,所以“对等翻译”是可以采取的。他主要提倡意译,用最美的语言表达最相近的原文意思和情感,万变而不离其宗。这种看似没有“忠实”原文的翻译方式能准确而恰当地体现出语篇对等翻译的精髓,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翻译语篇时译者在通读全文后需从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等层面进行考量和斟酌,顺应语境的要求,选择恰当而贴切的文体和风格,翻译出准确、流畅和得体的译文,从而使译文和原文达到较高层次的对等。
1.上下文语境对等
上下文语境主要指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一个单词或语义单位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在翻译过程中抛开上下文语境直接把字典里的解释或释义搬到译文中,这样的译文有时会与原文意思大相径庭,甚至会错误地传达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在实际翻译中我们欲在译文中找到相对对等的意义或让译文与原文达到最高层次对等的效果,则需将该单词或语义单位放在语篇中推敲,即要进行上下文语境分析, 从而打磨出最合适的译文。 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Politeness be sugared, politeness be hanged,
Politeness be jumbled and tumbled and banged.
It's simply a matter of putting on pace,
Politen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ase.[3](P18)
这段文字来自Norman Lindsay的The Magic Pudding,原文中布丁的性格是脾气暴躁,不拘于繁文缛节,豪放直爽。 翻译这段话时可以看出,其中sugared 作动词用时,原义为“加糖于”。如果直接用原义,那么翻译出来就是“被加糖的礼貌”,这样读起来让人不知所云。 而另一个词hanged 作动词用时,原义为“悬挂,装饰,绞死”。同样,如果直接用原义中任一个意思翻译过来均不合适,与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不符。 根据语言背景和上下文语境,寻找并推敲出与这两个词相对应的意义, 可以分别译为“粉饰”和“做形式”,这样既可保证译文准确,又可体现原文人物形象,传递出作者强烈的主观审美意识,且押了尾韵。
Jane Eyre中有一句话 “the distracting irritation I endured from”,吴钧燮先生把它意译成“痒痛难熬的滋味”,比完全照字面意思翻译要形象得多,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和感同身受的体会。而这种感觉和体会有助于读者理解简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她经历的种种不幸。吴钧燮先生反复斟酌了上下文语境,即小说的主人公简被寄养舅妈家和寄宿学校的痛苦经历给她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翻译时把当时的情景描述得越真实越生动给人的印象则越深,也更能打动译文读者的心。 从而使译文在表达效果上与原文达到了较高层次的对等。
2.情景语境对等
情景语境主要指言语行为发生的地点、 场合等。 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翻译诗歌等语篇时,即使通过上下文语境也无法弄清相应词句的确切意义,译者必须参考作者在写这些文字时发生的事情、人物和场景等因素才能确定对等的意义。如许渊冲教授在翻译李清照的《声声慢》时便力求情景语境对等,他主要采用意译、增译的方法把作者当时婉约失落的心情表达了出来。 (完整译文可参见许渊冲教授翻译版本, 中译出版社出版的 《画说宋词》(2017 年版)一书)
他在整篇译文中并不拘泥于某个字句,而是大刀阔斧地体现作者要表达的意境。但在部分细节处强化技巧, 不经意地把作者的情感自然地流露出来。 如在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句话时,许教授增译了一个“I”把原文中的虚化部分变成实体的主人公, 这种译法将原文的孤独情感传递给译文读者, 从而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境。 另外在译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和“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时用的是疑问句, 这样处理充分表达了作者当时的愁绪, 将原文中表达的沉重情绪通过疑问的表现形式真切地传递给译文读者。
再如The Magic Pudding中有一句话:Prayers and entreaties to remove the whiskers being of no avail, Bunyip decided to leave home without more ado.这句话按字面意思的译文是: 苦苦恳求叔叔剃须不起作用,宾叶决定无烦恼地离家出走。 但此种译法略显语言平淡无味,且体现不出宾叶这个人物的强烈情感,与原文作者想表达的意境不符。 原文中这句话的情景语境是,宾叶因不喜欢叔叔瓦特贝里的胡子,屡次劝其剃掉,但叔叔坚决不剃。要表达的是宾叶讨厌叔叔的胡须但又不得不和他住在一起的无奈心情。经过情景分析之后,将译文改为:苦苦恳求叔叔剃须,无果,宾叶只好决定离家出走,眼不见心不烦。 采用增译的方法,增加“只好”“眼不见”, 道出宾叶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 激化故事矛盾,使下面的情节顺理成章。
3.社会文化语境对等
社会文化语境主要指社会文化、 风俗习惯、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等。语篇翻译中译者需在两种社会文化中找到共同点,采用使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产生共鸣的语言进行表达,最终达到两种语言的高层次对等。 再如The Magic Pudding中的一句话:It's worse than beetles in the soup, It's worse than crows to eat.按字面意思翻译是:比汤里的甲虫还要坏,比吃了乌鸦还要糟糕。这个译文,中文读者读起来会不知所云,甚至会感到困惑:甲虫和乌鸦能吃吗?其实,中文里我们有与之对应的比喻,比喻破坏原本比较美好的事或物的东西——老鼠屎,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比喻让人心里感到非常不快的事或物——苍蝇, 如 “像吃了只苍蝇一样恶心”。了解这些汉语文化背景之后,采用归化法把这句话改译为:比汤里的老鼠屎还坏,比吃苍蝇还恶心。这样翻译会使得母语为汉语的读者都能很好地领会故事情节中布丁主人在上当受骗、丢失布丁时的心理感受。 文中还有一句话: “Put 'em up, ye puddin' -snatchers,"shouted Bill. “Don't keep us sparrin' up here all day. Come out an' take your gruel while you've got the chance.” 其中的 “gruel”原义为“稀饭,粥”,但此处及前后文并未涉及这类东西。 但英语中有短语“have one's gruel”,意思是“应得之物,应受的惩罚”,gruel 指代“不值钱、比较廉价的东西”。中文语言文化中,对自己看不上眼的东西都会说“下三滥,烂货”等。 作者在这里欲表现一种愤怒、粗暴、孩子气的情绪,不妨译为:比尔叫道,‘举起手来! 你们两个布丁强盗! 不要让我们一天到晚在这儿纠缠。趁给你们机会,滚出来,带着你们的烂东西!’。这样翻译充分表达出原文中布丁主人对布丁贼的愤怒、厌恶和不屑,使译文读者在欣赏译文时与原文读者在欣赏原文时所做出的反应几乎达到一致。
(二)文体对等
一般来说,根据文体的正式程度可把语言分成庄重文体、正式文体、商议文体、非正式文体和亲密文体五类[2](P216)。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如科技文体主要为正式文体,其语言简洁准确且词汇含义较深,语法结构严谨,陈述客观,逻辑性强,专业术语较多;口语体是非正式文体,表达性很强,语言生动具象,结构较松散,逻辑不严谨;而文学文体,语言多变,较富个性化并具有独创性,文字往往生动而感人。
译者在动笔对语篇进行翻译前需要先通读全文,了解原文整体风格与体裁,并在掌握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特征、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忠实于原文风格, 再根据译文相应文体习惯进行翻译,才能翻译出准确体现原文语言风格的译文。如我们在翻译议论文和说明文等较为正式的文体时,用词需谨慎精确、多用专业术语,杜绝使用模棱两可、主观猜测的词;而在翻译文学作品如诗歌时,需用一些情感丰富表达力强的语言文字等。如上文中许源冲教授《声声慢》的英译本中除了把内容完美地用英文呈现出来, 还通过押韵等形式把原文平仄交替、抑扬顿挫的音韵美也向译文读者展现出来。 既达到信息内容的对等,还完美地完成了形式上的对等。
又如,The Magic Pudding体裁为童话,语言幽默诙谐,节奏简单明快,其内容蕴含着儿童特有的单纯天真,外加有一点无厘头的元素。 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打油诗和唱词, 语言形式押韵富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在忠实于内容的基础上, 尽量使译文语言形式与原文一致。下面一段内容是布丁主人们第二次丢失布丁后感到极度沮丧和绝望时考拉熊宾叶鼓励大家的话,中英文对照如下:
The grass is green, the day is fair, 草青,天好,
The dandelions abound. 蒲公英四处飘。
Is this a time for sad despair 这样的时光,
And sitting on the ground? 怎能坐地沮丧?
Let gloom give way to angry glare, 让忧伤变成怒火,
Let weak despair be drowned, 把沮丧淹没,
Let vengeance in its rage declare 让复仇在愤怒中宣告:
Our Puddin' must be found. 我们必须将布丁找到。
Our Puddin' in some darksome lair 我们的布丁在黑暗的角落,
In iron chains is bound, 铁链把它捆绑,
While puddin'-snatchers on him fare, 任由布丁贼糟蹋,
And eat him by the pound. 吃了一磅又一磅。
Then let's resolve to do and dare. 让我们决心去挑战,
Let teeth with rage be ground. 让我们愤怒地咬紧牙,
Let voices to the heavens declare 向上天发誓:
Our Puddin' MUST be found[3](P61).我们一 定将布丁找到。
这段文字的译文欲与原文风格达到对等,我们除了采用直译法,还需要尝试意译、归化等方法。如“The dandelions abound”这句话,如果直译就是“蒲公英丰富”,会显得很生硬,毫无感情。 而这段话原文作者在语言形式上进行了押韵,目的是让大家放松,振奋精神。译文一方面要在形式上与原文呼应,另一方面意境也要与原文一致,可译为“蒲公英四处飘荡”,但与前面的“好”字不押韵。为了在形式上实现对等可将之改译成“蒲公英四处飘”。 这样,既表达了“丰富”的字面义,又与前面的“天好”押韵,整句话富有动感,活跃了气氛。同样,后面的内容基本可照此方法进行翻译。只要弄清宾叶这段唱词的目的在于鼓舞士气和斗志,在译文内容风格的把握上就会尽力使语言简练、流畅、有力,从而让译文读者体会到宾叶坚强的意志力和与布丁贼斗争到底的决心。
二、功能对等在翻译实践中的局限性
译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正如奈达所说:各种不同的译文其实只是代表着不同程度对等。这便意味着“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而只能理解为近似,即,接近于功能对等不同程度的贴近。也就是说任何译文不可能与原文达到完全等同。
兼顾但不能并重内容与形式。奈达的翻译理论也强调忠实于内容大于忠实于形式。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只好选择更忠实于内容。 正如上文提到的,The Magic Pudding原文贯穿很多打油诗和唱词,注重押韵且富有节奏感。 翻译的时候尽量做到与这种语言形式保持一致,但如果我们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字词,无法达到押韵的效果,就要服从内容的需要,而不是牵强附会,曲意而从形。
翻译不是万能的。在英语原文中个别词语在工具书中没有对应的解释, 无法找出与之对应的词汇。翻译时只好通过前后文语境和情景推测它的意思,或者采取略译和不译的处理方式。 但杨绛先生认为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文的内容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4](P198)。 所以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测或略译、不译,无疑会违背“忠实”的原则。 因此如何处理作者生造的词语,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翻译中经常出现文化缺失现象。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会出现英语文化中的俚语、谚语等,如果不深刻了解其中的文化背景和习俗,只按字面意思翻译会失去原有的意味,造成文化缺失。 如何避免和处理文化缺失是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译者可以借助奈达的“协商”法,即“The translator is engaged in negotiating with the source text in order to determine its meaning,most of which is overt,although much is always covert.A translator must also negotiate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target audience in order to arrive at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5](P159)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如遇到一眼看不出意义的词句,译者需在与原文、译文读者“协商、谈判”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工作,从而译出较为对等的译文。 而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遵循奈达的“六条要求”,尤其是其中的第六条,即, “The translator should not only make use of the best scientific philology and exegesis,but also invoke and rely upon divine grace for the fulfillment of his task”[6](P24)。 作为翻译者不光要有熟练的语言技巧,还应有对原文的尊重和对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与较强的责任心。在处理一些跨语言、跨文化问题时,译者在忠实于原文字的基础上还应多调查、多求证、多推敲,最终翻译出原汁原味的译文。
三、结 语
翻译工作对促进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建设文化强国等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文化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离不开精益求精的态度,杨绛先生把译者比作译匠。 我们只有传承老一辈的匠人精神,才能译出具有高层次对等的译文。
此外,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词汇量、知识面、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都是影响高质量翻译的因素。实践出真知,只有大量积累经验、知识,不断实践、总结,才能成为优秀的翻译工作者。翻译工作者需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讨并尝试多种翻译形式与方法,力求切实解决翻译领域现存的一些问题,为我国翻译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