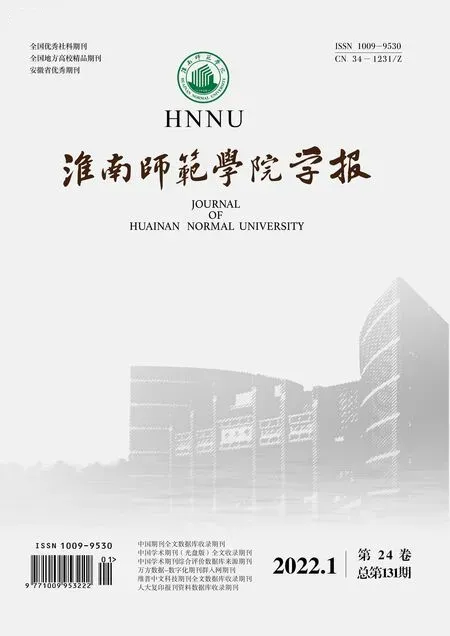西汉淮南王研究二题
李正君,霍嘉琪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西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以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为淮南国,英布为第一任淮南王。高祖十一年(前196 年)更封刘长为淮南王。 文帝七年(前 173 年),淮南国除,十六年(前 164 年)分淮南地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封刘长子刘安为淮南王。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年)除淮南国为九江郡。关于西汉淮南国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刘安在位时期,尤其是对于刘安本人的研究,如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①,王云度《刘安评传》②,孙纪文《淮南子研究》③,姚治中《重评“淮南狱”》④等。 对于英布以及刘长时期的淮南国研究相对缺乏,同时还应跳出对刘安的个人研究,上升至对整个淮南国的研究。 故文章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讨论西汉淮南王的两个问题: 其一, 刘长的出生问题;其二,刘安历史形象的构建问题。
一、西汉淮南厉王刘长出生问题辩误
淮南王刘安是安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在汉代的政治和学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部《淮南子》堪称不朽之作。人们似乎更多地关注其生平和在学术上的贡献,但对于其血统却鲜有人质疑。 据史籍记载,其父亲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淮南厉王刘长,但对刘长的出生问题史料记载却相互矛盾,而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史记》和《汉书》在记载上的差异。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对于刘长的出生这样描述道: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 厉王母得幸焉,有身。 赵王敖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 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彊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 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厉王母真定。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 ”[1](P3075)
以上这段材料提到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是高祖“从东垣过赵”的时间,一个是“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的时间。
(一)高祖“从东垣过赵”的时间
1.《通鉴》:“(八年) 冬, 上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过柏人。 ”[2](P384)
2.《汉书·高帝纪》:“八年冬, 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 ”[3](P65)
3.《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汉八年, 上从东垣还。 过赵,贯高等及壁人柏人,要之置厕。 ”[1](P2583)
此三条史料分别出自《通鉴》《汉书》和《史记》,但也只能确定高祖“从东垣过赵”的时间是“八年冬”。冬天到底包括哪几个月呢?《汉书》中数次提到“春正月”和“秋九月”,所以“冬”只可能是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这个在农历历法上也属常识。 另据《汉书·高帝纪》:“八年冬, 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还过赵,赵相贯高等耻上不礼其王,阴谋欲弑上……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十二月,行自东垣至……春三月,行如洛阳……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 ”[3](P65)
从以上的材料可知,高祖“从东垣过赵”是在高祖八年(前199 年)十月。
(二)“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的时间
1.《通鉴》:“(九年)十二月,上行如洛阳,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 ”[2](P386)
2.《汉书·高帝纪》:“(九年)十二月,行如洛阳,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 ”[3](P66-67)
3.《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汉九年, 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 ”[1](P2584)
这个时间较为明确,“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的时间是高祖九年(前198 年)十二月。通过比较两个时间,高祖“从东垣过赵”事在高祖八年十月,即此年第一个月。“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的时间在高祖九年十二月,即此年第三个月。 由前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可知,高祖八年十月“厉王母得幸焉,有身”,高祖九年十二月,仍有身。中间相隔十四个月,岂非怪哉?
对比《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的记载就有所不同。
“淮南厉王长,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帝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美人,厉王母也,幸,有身。 赵王不敢内宫,为筑外宫舍之。 及贯高等谋反事觉,并逮治王,尽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 厉王母亦系,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 ’吏以闻,上方怒赵,未及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不肯白,辟阳侯不强争。 厉王母已生厉生,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 真定,厉王母家县也。 ”[3](P2135)
高祖八年十月,刘邦过赵使厉王母有身,到十二月刘邦回到长安这两个月的时间,刘邦可能在哪里? 史书中并无记载。 只是记述了对战死的士卒们进行了抚恤,“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3](P65)我们可以推测从高祖八年十月到达赵地,至十二月回到长安,这段时间刘邦可能都在行进途中,笔者认为刘邦不太可能在赵地逗留太多的时间,因为刘邦在赵地遇到了“柏人事件”。那么刘邦从赵地回到长安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这主要是由两地的路程和皇帝车驾行进的速度决定的。
自古以来,从赵地都城邯郸到长安,可能要渡过一些大小河道,而其他的均以土路为主。 这些土路的走向后来发展成为修筑西安与邯郸之间现代公路的基础。 而如今从邯郸到达西安,依据现在导航系统,主要有三条路线可走:
其一,青兰高速转京昆高速,全程671 公里;其二,京港澳高速转连霍高速,全程717 公里;其三,青兰高速转连霍高速,全程695 公里。(以上数据来自高德地图)
当然从汉代至今已经过去了2200 多年, 西安到邯郸的三条线路均有较多局部变化,因此两地的里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而刘邦车驾的速度我们也可以从史料中大体推算出来。《汉书·贾捐之传》载:“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千里之马,独先安之。 ’”[3](P2832)汉文帝时距高祖时期较近,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西安到邯郸的里程我们不妨以三条路线的中间方案695 公里为基数计算, 若皇帝车驾行进的速度区间为12.47-20.78 公里(汉代一里为415.8 米)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刘邦从邯郸回到西安要花费34—56天。 而由于汉代的道路相对恶劣,交通工具又较为落后,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大大增加,所以从高祖八年十月刘邦到达赵地,至十二月回到长安,这两个月内刘邦均在回长安的路上。 由此可以推断,厉王母的妊娠期至少在12 个月以上, 但该结论明显不符合常识。
关于《史记》与《汉书》在记载刘长出生时间上的矛盾,前人也有一定的关注,在此主要列举周寿昌、王先谦、赵翼、《史记会注考证》以及今人王云度先生的观点。
1.《汉书注校补》:“《史记》作‘得幸上,有身’。赵翼曰:‘是时厉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宜从《史记》作“有身”为是。 ’寿昌案,上云赵王献美人,厉王母也。幸,有身。《史记》同。此云‘日得幸上,有子’,已生子也。下云厉王母已生厉王,言既已生,厉王非云甫生也。考高帝于八年冬从东垣过赵,赵献美人,幸,有身。九年十二月贯高等谋反事始觉,计已逾一年矣。岂有身而尚未生乎? 赵氏考之未审也。 ”[4](P632)
2.《汉书补注》:“先谦曰:‘赵翼云《史记》作“得幸上,有身”。 是时厉王尚未出生何得言子,作有身为是。’周寿昌云上云有身,此云有子,盖已生子也。下云厉王母已生厉王,言既生厉王,非是甫生。高帝八年冬,过赵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贯高谋反事始觉,计已逾年,岂有身而尚未生乎?赵氏之考之未审也,先谦案《史记》作有身,周说盖得其实。”[5](P3519)
3.《廿二史札记》:“淮南厉王传,《史记》, 高帝过赵,赵王献美人,帝幸之,有身。会贯高等谋反,帝令尽捕赵王家属系之,美人亦在系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 ’吏以闻,上方怒未理。 及美人生厉王,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令吕后母之。《汉书》叙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 ’按是时厉王尚未生也, 何得先言有子? 《史记》 以为有身较稳。 ”[6](P20)
4.《史记会注考证》:“《汉书》:‘身’作‘子’,周寿昌曰:‘高帝八年冬,过赵,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贯高谋反事始觉,计已逾年,盖已生子也。 ’”[7](P4810)
从以上四则材料可以看出,只有赵翼一人认为《史记》记载不误,而王先谦、周寿昌均对《史记》提出了质疑,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只是复述了周寿昌的观点。
最后,王云度先生的《刘安评传》也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提出了质疑,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刘长是刘邦的养子。 他的理由如下:
1.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厉王母的妊娠期过长,不符合常识;
2.刘长体质、性格与刘邦及刘邦的其他几个儿子截然不同;
3.当刘恒被立为帝后,刘长自知继承皇位无望,曾向文帝提出:“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 ”表明他心中只认生母,并不认自己是刘氏骨肉[8](P64-65)。
综合以上各家的观点,王先谦和周寿昌都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矛盾,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提出了质疑,而赵翼似乎站在《史记》的角度,认为淮南厉王刘长应为是刘邦的亲子无疑。笔者经过分析,同意赵翼的观点,并将理由罗列如下:
第一,养子之说并不能成立,因为刘邦根本没有收养子的理由。首先,刘邦子嗣众多,除淮南厉王刘长外,还有齐悼惠王刘肥、汉惠帝刘盈、赵隐王刘如意、汉文帝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和燕王刘建。 而刘邦更没有收养厉王的需要,一则厉王母只是在刘邦过赵时临时宠幸过,就连其有身孕都不知道,而由于贯高的谋反,赵王张敖受到株连,后来虽然因为鲁元公主的原因,没有处死,只是降王为侯,因此刘邦不会收养“罪人”姬妾的儿子。 另外,如果刘长是刘邦的养子,史书中不可能不留下明确的记载。
第二,不管是《汉书》还是《史记》,虽然对这个事情的记载有些许出入,但能够肯定的是,刘邦从东垣过赵,临幸厉王母令其有身是事实。 而在张敖得知厉王母有身孕之后,作出了“赵王不敢内宫,为筑外宫舍之”这样的举动,可见赵王对这一事件的重视,同时大大降低了厉王母接触其他男子的可能性。
第三,从日后汉文帝与刘长的关系来看,文帝即位后, 刘邦的儿子仅剩文帝和刘长两人。 文帝能够长期纵容刘长的骄横行为, 在臣下的反复建议后, 才开始对刘长进行一定的处罚和限制,两人应是亲兄弟无疑。 刘长死后, 当时民间有歌谣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3](P2144)汉文帝也因刘长事件而心怀愧疚,善待刘长的四个儿子,又分封其为王。
综上,笔者认为淮南厉王刘长应该是汉高祖刘邦的亲生儿子,《史记》的记载应当不误。
二、中古时期淮南王刘安历史形象的构建
在《史记》《汉书》中淮南王刘安反叛被诛身死,此已为不移之论,然而其形象在后代的记忆中不断被神化,自身的负面因素被淡化,历史形象也逐渐演变。
在《汉书》中淮南王刘安被描述成了“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言神仙黄白之术”[3](P2145)的形象。尤其其喜爱方术的特征被后世不断放大加工,逐渐演变为最终得道成仙的结局。而《汉书》中刘安身上的许多元素也成为后世刘安形象的重要素材来源。
早在两汉时期, 刘安成仙的传说就已有流传,刘安形象的构建与其和八公的关系密不可分。刘安与八公的组合及其传说也被一步一步构建起来。东汉时期的《论衡》中就说:
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 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述,莫不争出。 王遂得道,举家升天。 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 ”[9](P317)
黄晖先生通过史料对比认为,“儒书言” 应是“传书言”之误。 此处提及刘安最终的归宿是“举家升天”。 在这则刘安升天的故事中, 只云 “道术之士”,并未言明是八公。 而刘安之所以能够成仙,原因是“道士之士”和“奇方异述”。 此条材料现存于《论衡·道虚篇》,王充认为这种传言是不可靠的,并进行了批驳,坚信史料记载的正确性,其辩称:
案淮南王刘安,孝武皇帝之时也。 父长以罪迁蜀严道,至雍道死。 安嗣为王,恨父徙死,怀反逆之心,招会术人,欲为大事。伍被之属,充满殿堂,作道术之书,发怪奇之文,合景乱首,《八公之传》,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状。 道终不成,效验不立,乃与伍被谋为反事,事觉自杀。 或言诛死。 诛死自杀,同一实也。 世见其书,深冥奇怪,又观《八公之传》,似若有效,则传称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实也[9](P319-320)。
虽然王充并不认同刘安得道成仙的传言,但此等传言毕竟在当时社会已有广泛的流传,并非空穴来风。 王充提及《八公之传》此书,无形中就把传说中刘安的成仙与八公联系了起来,但具体关联仍然语焉不详。
另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俗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秘苑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升天。
谨按《汉书》,淮南王安,天资辨博,善为文辞。武帝以属诸父,甚尊之。招募方技怪迂之人,述神仙黄白之事,财殚力屈,无能成获,乃谋叛逆,刻皇帝玺,丞相将军大夫已下印,汉使符节法冠。赵王彭祖列侯让等议曰:“安废法行邪僻, 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背叛宗庙,春秋无将,将而必诛,安罪重于将,反形已定。 图书印及他逆无道,事验,明谋皆收,夷,国除为九江郡,亲伏白刃,与众弃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养士,或颇漏之,耻其如此,因饰诈说,后人吠声遂传行耳[10](P114-116)。
由此可见应劭也是不赞同刘安成仙的说法,然而其中仍未明确提及八公对刘安成仙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此时刘安成仙的传说出现不久,传说的细节不够丰满, 加之东汉距刘安生活的年代较近,史料遗存较为丰富,当时的学者普遍依据史籍记载驳斥刘安成仙的传言。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安的神仙形象才开始慢慢丰满起来, 其与八公的关系也变得扑朔迷离。 晋人干宝的《搜神记》记载:
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诣门求见。门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难之。曰:“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 ”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 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 ”[11](P4)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据高诱《淮南鸿烈·叙目》载:“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12](P2)今人多据此八公姓名为神仙八公。而到了此时,八公成为传授刘安神仙方术的人,同时也体现出刘安礼贤下士,热衷仙道的品质。 八公至此与刘安成仙取得了直接联系,八公的形象也愈加丰满起来。而后葛洪撰《神仙传》更加清晰了刘安与八公的关系,以及八公的具体特征。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 海内方士从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诣之,客状衰老枯槁,伛偻阍者,谓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长生久视之道,必须有异于人,王乃礼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见也。”拒之数四,公求见不已,阍者对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见,却致年少,又何难哉?”于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劝之状,阍者惊而引进,王倒履而迎之,设礼称弟子曰:“高仙远降,何以教寡人? ”问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谓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 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廻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也。”时王之小臣伍被,曾有过,恐王诛之,心不自安,诣阙告变,证安必反。 武帝疑之,诏大宗正持节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谓王曰:“伍被人臣而诬其主,天必诛之,王可去矣。 此亦天谴,王耳君此事,日复一日,人间岂可捨哉?”乃取鼎煮药,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余人,同日昇天,鸡犬舐药器者亦同飞去,八公与王驻马于山石上,但留人马,踪迹不知所在。 宗正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诛伍被,自此广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药,竟不得。 其后王母降时,授仙经,密赐灵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丹出人间,抱犊道经,见于山洞,亦视武帝不死之跡[13](P31-32)。
《神仙传》 中八公被赋予了各自的姓名和各种神异的能力。在淮南狱中,刘安也是被伍被陷害,不得已在八公的带领下飞升而去。 刘安成仙也是“取鼎煮药,使王服之”的结果。材料的最后还通过汉武帝的悔恨之心以及以后的求仙行为来反衬刘安的无辜和形象的伟岸,对于刘安的反叛行为则只字不提,故意掩盖。八公身上的奇异色彩愈加丰富,神通各异,其自身形象也由方士彻底上升为仙人。
到了唐代,八公被赋予了刘安之师的定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成书于唐贞观八年至显庆四年间,辑录了大量唐代以前的重要资料,对炼丹术及科技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14]。其中就有关于淮南王刘安的记载:
八公者,汉淮南王安之师;刘安者,汉高祖之亲孙,其父厉王也。 于时天下贵人莫不以都邑畋猎犬马为事业。 王独爱仙道,偏崇秘术,论仙之道,闻有变化,道术之士,虽遥千里,卑辞厚币,请致之,莫不集之如云,数千人也。所撰《内书》二十一篇,《中篇》八卷,《鸿宝方》三卷,而又布远近,遂降八公,感之愿,为之师也。
初,门吏不纳八公,八公现以老少之质,门人以闻之王,足不暇履,肘步而前延公,登思仙之台,设锦绮之帐,进金玉之机,执弟子之礼,请长生之诀。八公曰:“修学仙道,先作神丹,乃可长生不死耳。我能煎泥成金,凝汞成银,水渍八石,飞腾流珠,转化玉金,凝变七宝,服之者能乘云龙浮,遊太清,出入紫阙宴寝玄都矣, 此云腾羽化之妙事也, 王宜修之。 ”
安重叩头流涕,乞长生之诀。 公遂哀矜,授《王灵神丹上经》及三十六水法与安,安即登坛,立盟歃血,跪金以受神丹方,起炉火也,遂获药成。 安为五利所僭于帝,帝怒,乃遣宗正执节收安。 八公难曰:“阿安今可去矣,夫有神仙之籍者,谋之者死,犯之者灭门,其五利未几是八公言也。”谓安曰:“天遗如此,王足为恨。”公乃与安登山大祭,即日昇天,所践大石人马之迹,千古见存焉,是以鸡鸣天上,犬吠云间矣[15](P111-1112)。
与葛洪《神仙传》相比,《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故事梗概更加具体。 首先,八公不再仅是求见刘安的方士,而成了刘安之师,刘安对八公“执弟子之礼”。 其次,《神仙传》中八公的神异能力比较全面,涉及呼风唤雨、变化驱魔等各个方面,由于《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收录的多是炼丹术方面的内容,所以八公的能力多集中在具体的物质变化上。最后,《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的故事更加细节化,八公授予刘安“《王灵神丹上经》及三十六水法”,刘安并非得道成仙,而是本身就具备“神仙之籍”。 道教信徒对刘安形象的构造或许是出于宗教宣传的考虑,毕竟一位因叛乱而身死的诸侯王形象与超凡脱俗的仙长形象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并在正史中留下传记的人物,刘安的仙人形象不断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被重构和加深。
经过历代学者和道教信徒的精心塑造,刘安慢慢脱去了反叛者的身份,成为礼贤下士、追求仙道、进而得道成仙的高人形象。汉代是道教的孕育和草创时期,其神学理论和教理教义较为简单,淮南王成仙的故事可能在此时仅仅是一个传说,其升仙细节亦不够丰满,这也是这一传说能够受到学者驳斥的原因之一。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出现分化,在分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经过士族知识分子的改造充实,开始慢慢演化为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官方宗教。 随着道教的发展,其理论构造也得到了完善,出于宗教宣传的需要,淮南王的形象以及与八公的关系愈加细致丰满,其成仙的传说也流传愈广。 而在唐代崇道思想的扶持下,道教迎来了鼎兴期,全国兴建道观,优宠道士。故而经过历代的累层,唐代淮南王升仙的故事最为细致完整,同时出现了前代没有的元素。 不得不说, 淮南王刘安历史形象的演变与道教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刘安形象的演变反映历史记忆的复杂性以及宗教宣传的现实性。而这种形象与《史记》《汉书》记载的淮南王刘安的形象大相径庭。拨开历史的迷雾,剖析刘安形象演变的过程,是我们正确评价刘安的前提。
注 释:
①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②王云度.刘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③孙纪文.淮南子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④ 姚治中.重评“淮南狱”[M].合肥:黄山书社,2015.